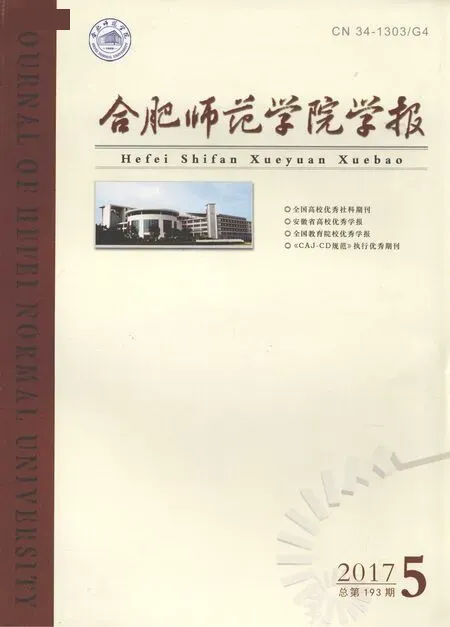从“玩偶”的人生到“玩偶”的救赎
——东野圭吾小说《白夜行》的女性主义解读
张 娴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合肥 231131)
2017-05-21
张娴(1983-),女,安徽淮南人,安徽工商职业学院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生态美学。
从“玩偶”的人生到“玩偶”的救赎
——东野圭吾小说《白夜行》的女性主义解读
张 娴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合肥 231131)
以女性主义批评视角解读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白夜行》,女主人公以卑劣且邪恶的方式对自己“玩偶”式命运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其本质仍然是以始终遵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及固有习俗和规则为前提的。作家通过一种近乎极端的现代女性形象,颠覆了过去那种默默忍耐、甘为人后的传统女性形象,使女人看似具有经济和人格的双重独立,但在以“男性”价值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中,现代女性徒有独立的表象,最终还是脱离不了“他者”的悲剧命运。
东野圭吾;《白夜行》;女性;他者;男权社会
东野圭吾是当今日本乃至亚洲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家之一,其小说多以深刻尖锐的文字、缜密完美的推理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读者。小说《白夜行》创作于1999年,正值东野圭吾创作的高峰期,它以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衰退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手法,通过各种情节矛盾的碰撞及案件的推理,揭示了男、女主人公扭曲的人格及其阴暗的一生。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作品描写了很多女性人物,她们对小说情节的推动及案件的展开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在推理小说作品中塑造如此多的女性形象,并且将女性人物在叙事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不多见的。可以说,女性是东野圭吾小说创作长期关注的焦点和极力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一。
一、女主人公的“玩偶”人生
《白夜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生活困窘、缺少经济来源的单身母亲西本文代,出于生计所迫,强迫自己仍是小学生的女儿——西本雪穂与有恋童癖的中年男子桐原洋介进行性交易。在某次桐原洋介对雪穂进行性侵犯时,恰巧被他的儿子、雪穂的青梅竹马——桐原亮司跟踪发现,亮司亲眼目睹了父亲的丑恶行为,震撼与悲愤之下用剪纸剪刀捅死了父亲。此案发生后,为了不让亮司暴露,也为了摆脱自己低贱的命运,雪穂间接杀害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之后被唐泽礼子收养,改名唐泽雪穂。此后的二十年,为了顺利度过案件的追查期限,雪穂与亮司背负着各自的原罪走上了扭曲的犯罪人生道路。世人眼里他们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两个人互利共生:雪穗在明,骗取他人信任,攀爬上流社会;亮司在暗,为雪穗犯罪扫清不利人事,牟取物质利益。最终,在雪穗的奢侈品店铺开张之日,警方发现了亮司的行迹,对其进行抓捕。亮司跳楼身亡,雪穗则在现场拒绝向警察承认与其有关系,转身离去。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到开始出现石油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历经资本主义社会泡沫经济的破灭时期。整个故事从发生到结束,涵盖了日本将近20年的现代发展史,描绘出日本当时迷茫无序而又浮躁动荡的社会变革,及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生存着的女性的命运与人性的悲剧。
(一)“玩偶”的自我塑造
女主人公雪穂的童年是令人深切同情甚至是愤慨的:自幼丧父,与母亲一直住在大阪市的贫民区,母亲在荞麦面店做临时工,微薄的收入让她们母女的生活显得拮据而窘迫,雪穂的母亲终因不堪生存的压力,在雪穗不到十岁的时候迫使她与有恋童癖的中年男性进行性交易,以此贴补母女的生活开支。而这些男性“雇主”当中,恰恰有一位就是自幼就与她惺惺相惜的男主人公桐原亮司的父亲。对于一个年幼的少女,人生里美好的东西无外乎亲情、童贞、友情、爱情……但是,女主人公从童年开始就将这一切纷纷失去,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被迫走上了一条男权社会里作为男性“玩偶”式的人生道路。
在雪穗与其伙伴桐原亮司无意间犯下了杀人罪行后,“玩偶”开始“苏醒”,极力想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和不公的命运。她变得世故、冷漠,且工于心计,企图通过各种不磊落甚至罪恶的行径完成对自己“玩偶”人生的逆袭。她首先凭借温柔乖巧的心机讨得中产阶层单身女性唐泽礼子的欢心,在间接杀害了自己的生母之后,顺利成为唐泽礼子的养女,改姓唐泽,以此给自己争取来一个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及社会地位。她跟着养母学习茶道、插花,改掉自己显得土气的大阪口音,努力习得大家闺秀的风范,进入贵族女子中学读书,在学校里是一个认真努力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她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允许自己在学业上有任何瑕疵,在感到数学课程的学习稍有吃力时,她让养母出钱给自己请来家庭教师单独补习。她美丽优雅,待人接物圆滑,对周围所有人都伪装出一种友善与高贵,并且聪敏得体,游刃有余,在学校里赢得了众多异性及同性的追捧。进入大学后,她主动靠近富家子弟高宫诚,与其恋爱至大学毕业,在准备谈婚论嫁之时,高宫诚却发现自己真正爱的是另一个女人三泽千都留,对于跟雪穂的婚事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动摇。雪穂通过电话监听,了解到高宫诚与这个女人的爱情计划之后,设计通过桐原亮司从中破坏,使两人产生误解,高宫诚最后还是不得不与雪穂完成了婚事。
唐泽雪穂在1985年与高宫诚结婚后,日本社会开始进入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社会泡沫经济危机的形成阶段,1985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大量美国资金流入日本的房地产与股票、艺术品投资市场。”[1]婚后雪穂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向以投资股票为主,“报纸最少看六份,其中两份是经济报与工业报。”[2]191为了积累原始资金,她协助桐原亮司复制电脑游戏软件,盗版出售获取大量非法收入,并配合桐原亮司窃取丈夫高宫诚的用户名与密码侵入丈夫公司的电脑系统,利用公司内部的工作站复制了整个生产技术专家系统,获得重要数据,开发出金属加工专家系统软件,借此操控股票市场,迅速敛财。小说对桐原亮司使用计算机进行犯罪的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个人电脑”作为新兴科技产物进入民众生活难以普及、社会计算机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电脑数据系统存在众多安全漏洞、著作权及知识产权未能覆盖新兴科技领域等一系列计算机时代到来之初的无序混乱。正是这种混乱的社会状态,为唐泽雪穂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撺掇桐原亮司犯下种种罪行提供了土壤。
(二)疯狂的“不归路”
1989年,日本股市全面崩盘,地价下降,泡沫经济开始破灭。与社会经济迅速滑坡形成强烈讽刺的是,日本在这个时期奢侈品市场却异常繁荣,随着商业领域的这一海市蜃楼的出现,在赚足了敛财道路上的第一桶金之后,唐泽雪穂的“事业”的重心,又由购买股票转移到了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繁华地段开奢侈品连锁经营店。在感到丈夫高宫诚对自己已没有多少利用价值时,她开始蓄谋,又一次成功设计使高宫诚主动离开了她。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女性如果没有十分正当的原因,主动与男性离婚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非议和舆论压力的,所以她精心策划,一步步把离婚的责任推到高宫诚那边。她想方设法使高宫诚与他的旧情人三泽千都留见面,并且假装性冷淡让高宫诚无法与自己过正常的夫妻生活,高宫诚抵不住诱惑与三泽千都留发生了婚外情。最终,雪穂成功地将自己的丈夫与三泽千都留撮合到了一起,而自己则以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身份顺利脱身。与高宫诚离婚后,雪穂很快找到了下一个“猎物”对象——筱冢康晴,一个丧偶的大型药品董事集团的常务董事,雪穂再次用她迷人的外表和深藏不露的心机快速俘获了筱冢康晴。美丽的外貌,优雅的举止,得体的言行,天衣无缝的待人接物,唐泽雪穂展现在外的都是迎合社会大众审美的如“芭比娃娃”玩偶般无懈可击的完美形象,但在背后,她一步步利用桐原亮司进行欺诈、监听,甚至是强奸、杀人,任何阻挡她前进的绊脚石都会被她无情扫清,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说唐泽雪穂在幼年时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出于保护自己和桐原亮司的无奈之举,那么,后来她所做出的种种恶行,就是一种疯狂的对人性的肆意践踏了。她带着玩偶般的面具在人群中貌似优雅地穿行,却越来越罪恶,越来越铤而走险;她不顾一切地攀爬着自己人生的黄金阶梯,但每一步的上升,背后都藏匿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丑恶罪行,任何阻挡她前进的“绊脚石”都会被她扫清。她开始变得疯狂而极端,她不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也残忍地摆布着与她生活有过交集的周围人的命运:她让亮司去施暴与自己形成竞争者的女同学,然后嫁祸于菊池道广,就因为菊池道广有雪穗和亮司父亲的合影;她以同样的手段陷害她的女伴川岛江利子,原因只是一直作为她的陪衬的江利子也受到了富家子弟、大学社交舞社团社长筱冢一成的追求;与高宫诚离婚后为了顺利嫁给董事集团董事长成为董事长夫人,她又再次故技重施让亮司去施暴董事长的幼女,而自己则以守密者的身份出现博取董事长女儿的信任与依赖……她的良知彻底泯灭,她开始越来越邪恶,她一次次地走向罪恶的深渊,最后竟然唆使亮司亲手摘下了因生病而住院的养育了自己十几年的养母唐泽礼子的氧气管,无情地结束了其养母最后的生命,在这条罪恶的“不归路”上她越走越远,最终走向毁灭。
二、走向毁灭
在东野圭吾的众多推理作品中,案件几乎都是立足于日本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应该说正是这些现实问题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时除了专注于离奇案件的本身之外,又能对案件所带有的社会问题感同身受。”[3]东野圭吾在一次对他的专访中说:“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比如社会的凉炎。我想,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因此,不存在‘过气’的危险。”[4]这种对于社会与人性的深入挖掘在《白夜行》中表现得尤为深刻。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然而,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促进垄断大企业的高积累,也给社会生活各领域造成了扭曲和错位,并且逐渐引发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低工资、高物价、低福利、住房严重不足、环境污染等,这些都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苦难。战后美国文化的涌入,也瓦解了日本社会固有的价值体系,思想上的混乱,世界观、价值观的沦丧,导致黑社会横行、卖淫普及。80年代后到90年代末,日本又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和泡沫经济,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计算机技术犯罪、通货膨胀、商品囤积、全民炒股、房价高涨、抢劫、偷盗、高失业率、高离婚率、“少子化”加剧等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日本社会的变迁,尖锐的社会问题展露无遗,追求物质利益成为了当时很多日本民众生活的唯一目标,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小说主人公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和人生的悲剧。
(一)灵魂的灭亡
在唐泽雪穂罪恶的人生道路上一直有一个隐藏着的同盟者——桐原亮司。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对此进行过描写,无数个章节和片段中看似他们也都是独立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直到小说的最后,随着十几年老警察对他们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跟踪调查的结果渐渐清晰,两人的同盟者关系才浮出水面。为了掩盖亮司杀父和雪穗因此间接杀母的事实,从案件发生开始两人表面上是形同陌路,互不来往的,但实际上这十几年中雪穂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次遇阻,都会有亮司在暗中为她扫平一切,而在亮司有所危机时,雪穂也会挺身而出,无条件地去帮助他。正如书中老警察所说,雪穗和亮司的关系像“枪虾和虾虎鱼,他们是明暗互补、互利共生的。……不知两人是如何协调约定的,或者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约定,他们只是想保护他们的灵魂。”[2]419大阪新店开张庆典的那个晚上,雪穂的人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至高点。此时的她应该是得意与满足的,但她并不知道,在金碧辉煌的店堂外面,她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也正向她逼近:警察发现了店外正在装扮圣诞老人为小朋友发放剪纸的亮司,展开了对他的追捕。为了替雪穂掩盖罪行,亮司用他的生命最后一次守护了这朵“恶之花”:拒绝被捕,跳楼身亡在她店堂的大厅里……面对亮司的尸体,“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2]467。
不可否认,雪穗想要的东西很多,金钱、名誉、地位、权利、家庭、别人对她的尊敬、对她的爱慕、对她的嫉妒……,然而实际上,她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的本身。比如金钱,雪穗敛聚了很多金钱,但我们却没看到她花用;比如权力和地位,我们也并没有看到雪穗用它向别人发号施令,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谦卑有礼;比如来自外界的爱慕与嫉妒,是可以让人获得心理满足的,但雪穗也并没有陶醉其中。那么,她究竟追求的是什么?是掠夺!她的整个生命都用在了掠夺上,一生费尽心机、如履薄冰,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只为不断夺取自己曾经被掠走的东西:贞洁、尊严、地位、名誉……可是这些东西也并没有使她幸福,她的整个身心已经彻底扭曲,她是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幼年的遭遇让唐泽雪穂的灵魂彻底迷失,除了在物欲的世界里不断得到,在众人面前不断汲取满足,似乎什么也无法填补她的欲求。
小说里,成年后的雪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这份光,我便能把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2]439太阳在雪穂的内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是雪穂发自本能的对人生美好事物的向往,是藏匿在雪穂灵魂深处的一点温暖光明的东西。表面纯洁美丽的雪穗是罪恶的,她黑暗的童年阴影无法去除,所以生命中没有太阳,桐原亮司表面上是神秘且阴暗的,但他承担了父亲罪行的后果,为了雪穗不惜一切地去赎罪,而他代替了太阳,成为雪穗的亮光,她便可以在白夜中行走。对雪穗来说,桐原亮司就是她黑夜中唯一的一点光,也是她最后残存的一丝人性和一点点灵魂,所以亮司的死也让她的灵魂随之灭亡了,她生命中仅存的一点感情和属于真善美的东西,已经被桐原亮司的死彻底带走。
(二)无望的自我救赎
雪穂曾经说过:“婚姻就是长期卖淫,如果没有利益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2]97她非常清楚,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若想取得事业上的一席之地,仍旧需要依靠男人,需要遵从男性制定的社会游戏规则进行。在与高宫诚结婚后,雪穂没有出去工作,而是做了家庭主妇,这显然不是她的初衷,只是暂时遵从了社会习俗的约定俗成。稳定了婚姻后,雪穂开始打算学习炒股,同时她也更加卖命地做好家务,学习厨艺,让高宫诚在外以自己娶了一个美丽又厨艺精湛的贤妻而骄傲,她把高宫诚的日常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只为了能够争取到高宫诚的同意,让自己每天能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股票市场看股市行情,而且再三保证不会耽误料理家事。即便如此,高宫诚对妻子的不满还是越来越多,虽然雪穗百般道歉,但高宫诚仍有一种无法释怀的感觉,尤其是在他慢慢意识到雪穂的智商、能力、生意头脑都明显强于自己的时候,作为男人特有的大男子主义情结爆发,他向雪穂莫名发火,他觉得雪穂的优秀伤害了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雪穂与高宫诚的婚姻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无疑是一个女性通过牺牲自己的爱情、婚姻换取事业上的支撑的典型,成年后的雪穂极力地改变自己,想摆脱曾经的“玩偶”命运,却又再一次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玩偶”角色里去。
雪穂在童年时期就一直渴望成为《飘》的女主角郝思嘉那样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女人,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抱有深深的自卑与厌恶,想极力摆脱。她不想成为母亲那样无能、堕落的女人,不想再次沦为男人的“玩物”,她要掌控自己的命运,成为这个男权社会里自我命运的“主宰者”。她把“郝思嘉”奉为自己模仿的偶像,但实际上,作为独立女性的典范,郝思嘉在她所生存的男权社会里是我行我素的,不受社会习俗束缚的,而唐泽雪穂在努力实现自己人生追求的过程中,始终是以遵照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及固有习俗与规则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所做的一切看似自我救赎,实际上是无望的,徒劳的。雪穗是需要被救赎的,也是可以被救赎的,但是社会并没有去拯救她。在日本这个传统的东方社会,女性一直是受到压抑而不被宽容的,舆论不但不会放过一个被伤害的少女,反而会加倍地用鄙视的眼光在她已经饱受伤害的灵魂深处再雪上加霜。雪穗的恶,其实也是日本社会的恶;雪穂的悲剧,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社会资本携带有天然的社会治理要素,如组织、习俗、规范、网络、理解、信任、合作、认同感以及共享的知识与价值观、共担的责任和义务等。一个社会拥有的社会资本储备越多,社会秩序便会越良好,制度运行便会更和谐、更有效。社会资本的社会治理功能如下。
三、作为“他者”的女性
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论著《第二性—女人》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对男人来说,女人最直接的定义就是性,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征服和占有,这种女性与男性的不平等地位,致使女性成为了“他者”。[5]467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除了女主人公唐泽雪穂外还刻画了很多女性人物,如西本文代、唐泽礼子、川岛江利子、栗原典子、桐原弥生子、西口奈美江、花冈夕子等,这些女性,有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也有在面馆、酒吧打工的底层妇女,有在银行、医院工作的职业女性,也有寂寞空虚的中年家庭主妇。她们性格迥异,生存处境也各不相同,她们或是感情上被男性欺骗而受到利用,或是有着空洞的婚姻却无力挣脱,自我放纵。身为“第二性”的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人格上她们都不是真正独立的,都是以作为男性社会的“他者”的身份而存在的,这些女性最后的命运也都是令人惋惜的,或是令人悲痛的。
(一)小说中的女性群体
唐泽雪穂的生母西本文代,婚后不久便丧夫,在这样一种以男性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社会环境下,失去了丈夫,就等同于失去了经济的主要来源。而社会能给她的价值定位,也只是一个底层的荞麦面店的零时工。作为导致雪穂“玩偶”命运第一帮凶的西本文代,身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无疑是可憎可恶的,但对于一个柔弱的经济上不能实现独立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条道路的选择,或许多少也反映出一个女性无法改变自身生存境况的无可奈何,以至于最后麻木不仁地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对社会的残酷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
唐泽礼子是一个长年单身、没有子女的中产阶层的中年女性,也是雪穂的远房亲戚、日本花道界的花道老师,这样一个单身中年女性,虽然经济上能够丰衣足食,但她的生存处境其实是让人同情的:感情上缺少慰藉,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朋友,很少与外界沟通;精神上孤独寂寞,缺少社会的关爱,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她对唐泽雪穂毫无保留地投入了所有的母爱:将其收为养女,改姓唐泽;供其就读贵族学校;为其提供优越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环境。然而,唐泽礼子的晚年却死于与其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养女唐泽雪穂之手。在雪穂的大阪新店即将开张之际,礼子准备挖出家中庭院里种植的仙人掌做盆栽,挖土的过程中发现了埋在庭院里的白骨,她隐约感觉到了白骨与雪穗有关,出于对雪穗深沉的爱,她没有报警,把白骨重新埋好;其后,雪穗在与唐泽礼子的交谈中,无意间得知她已发现尸体,在给自己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后,雪穂授意桐原亮司潜入医院,拔下了正在住院的唐泽礼子的氧气呼吸管。
川岛江利子是唐泽雪穂中学及大学时代的同伴,与雪穂的童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岛江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成长之路也一帆风顺。川岛江利子有着善良的内心和胆小谨慎、甘作陪衬的性格,但正是这种性格,使得她过于柔弱,缺少主见,在这个社会里始终没有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从中学时代开始,江利子对雪穂就是崇拜与跟随的,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唐泽雪穂的这份友情,她把雪穂视为自己的密友、学习崇拜的对象。在与学校的富家子弟、筱冢药品的第二代接班人筱冢一成恋爱之后,江利子身上特有的单纯与美好也被筱冢一成充分发掘出来,这一点刺激了雪穂自卑而扭曲的内心,让她再次感到命运的不公。于是,江利子的单纯与美好被雪穂亲手破坏——雪穂唆使桐原亮司对其进行袭击并拍下裸照,制造其被强奸的假象,直接促使江利子主动与筱冢一成提出分手,就此与一份美好又令人向往的爱情生活告别。
栗原典子这一女性人物是在小说的中后期才出场的,书中关于她的描写笔墨并不多。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有爱的单纯女人,但是,正因为她的单纯,她一而再的被这个社会里的男性所欺骗,感情上的不独立,亦使得男人们对她从没有给予过真正的尊重与关爱。认识桐原亮司之前,她对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死心塌地的爱着,甚至还为他买了一个公寓,期望能以此和他建立一个家庭,但最后却被那个男人所抛弃。初遇桐原亮司时,亮司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了伤的落魄男人,她不假思索地出手相助;和亮司在一起后,尽管她对他一无所知,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信任他,这也导致了她自始至终只是桐原亮司故意靠近并利用其大学医院药剂师的身份进行犯罪的一个工具。她让亮司带自己回大阪,因为她想了解他的家乡、他的过去,这可以看出典子的爱是很单纯而又真挚的,但单纯的另一面,也折射出她感情人格的不独立、对男性的过于妥协。作为大学医院里药剂师的她,明明知道氰化钾作为剧毒有多危险,却仍然妥协地将它偷出交给了桐原亮司,在看到氰化钾变少后,她已经猜到了些许什么,却不敢问不敢说;在不了解亮司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她为了保持和亮司的情人关系忍住内心所有的猜疑,并默默忍受亮司平日里对她的冷漠。这些都只能说明,栗原典子对男人的爱过于盲目与依赖,感情上的强烈“依附”使她失去了应有的理智。
此外,小说还刻画了诸如桐原弥生子、西口奈美江、花冈夕子等这些因婚姻生活的空虚乏味而去偷情、买春的已婚中年妇女角色。小说的男主人公桐原亮司的母亲桐原弥生子,就是那个时代贪恋物质、沉溺欲望、不负责任的女性典型,她原为酒吧的陪酒小姐,嫁给亮司的父亲桐原洋介后,发现桐原洋介性取向上有恋童癖,这一点给她的婚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苦闷,于是她不甘寂寞,与当铺店里的店员松浦勇长期偷情,而这也恰恰给童年时代的亮司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阴影与伤害。西口奈美江、花冈夕子是桐原亮司高中时代做拉皮条生意的常客,她们都有着空洞而无味的婚姻,长期的性压抑导致她们背地里找高中英俊男生进行性交易,借此麻痹自己的感情生活和内心欲望。这些都反映出当时日本许多中产家庭已婚妇女心灵空虚的状态,而导致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女人们在男权社会里无法像男人们一样独立、体面、有尊严地活着:她们必须要依附男人,依附婚姻,社会的风俗和对她们性别角色的定义使得她们无力改变自己并不幸福的婚姻,她们只能成为男权社会里的受害者、牺牲品。
(二)东野圭吾的女性观
小说《白夜行》中那些以唐泽雪穂为代表的生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女性,无论是柔弱的、多情的、空虚的,还是强硬的、冷酷的、奋发的,都生动而丰富地为我们展现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日本女性的种种生存境况与命运。小说在叙述女主人公命运悲剧的同时,还对社会的种种弊漏作了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和思考,作者将很多埋藏在日本当代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的东西挖了出来,给读者展示出一个逼真的社会情境:在两次泡沫经济危机的席卷下,在拜金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下,在男女不平等观念的根深蒂固下,女性在这样一种价值沦丧、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该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东野圭吾在其众多推理小说作品中都要塑造一种“坏到极致的女人”,如:《放学后》中的惠美、惠子、裕美子,《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靖子,《圣女的救济》中的绫音,《白夜行》中的雪穗,《幻夜》中的美冬……等等,她们一般都具有美艳的外表,且头脑敏锐,做事冷静,为周围的男人所爱慕,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她们不择手段。她们就如同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暴露了夫权制、拜金主义、道德沦丧、性侵犯、性压抑等各种女性生存困境。东野圭吾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大都生活在“二战”之后,女性自身解放的需求与战前封建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在战后的日本社会里一直矛盾的并存着,这是东野圭吾小说作品的文化背景,也是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现实。
在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中,女性既是社会大时代里的挣扎者,也是勇敢的反抗者、坚强的追求者,从对这类女性角色的解读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的女性观:他希望通过一种近乎极端的人物塑造,试图颠覆过去那种默默忍耐、甘为人后的传统女性形象,使其看似具有经济和人格的双重独立,但在以“男性”价值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中,现代女性徒有独立的表象,最终还是脱离不了“他者”的悲剧命运。同时,东野圭吾作品里的女性人物,也为我们展示了新一代日本女性的另一面,她们不再逆来顺受,她们的精神世界如此丰富,她们的智商甚至高于男性,她们的人格受到凌辱后会报复、会反抗,并为之燃烧自己全部的力量,这样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充满魅力。
[1] 张景一.东野圭吾作品的社会性——以《白夜行》为中心[J].作家,2013,(6).
[2] [日]东野圭吾.白夜行[M].刘姿君,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3] 牛丽.从《白夜行》看东野圭吾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人性[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0,(7).
[4] 何映宇.我不介意更温情一些——日本推理小说第一人东野圭吾专访[N].新民周刊,2012,(34).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FromDoll'sLifetoDoll'sRedemption——AnalysisofFeminisminKeigoHigashino'sNovelWalkingintheWhiteNight
ZHANG Xian
(SchoolofEconomy&Trade,AnhuiBusinessVocationalCollege,Hefei230001,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Keigo Higashino's novelWalkingintheWhiteNigh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criticism,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heroine redeem herself from her fate like a doll in a manner of despicability and evilness, its essence is still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ety for women and inherent customs and rules are the premise of her self-redemption. By building a near extreme image of modern women, the writer hopes to subvert the female image of silently suffering and devoting to create women of “real strength” with 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economic status, but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the independent image of women is just pure illusion; they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tragic fate like a "the other".
Keigo Higashino;WalkingintheWhiteNight; female; the other;male-dominated society
I106.4
A
1674-2273(2017)05-0083-06
(责任编辑何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