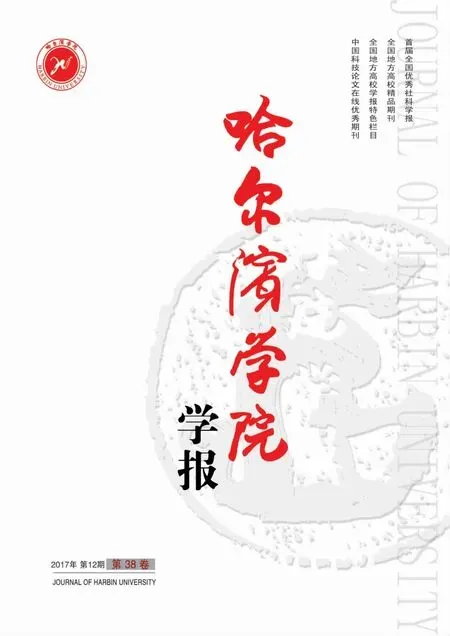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实质分类
李庆航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实质分类
李庆航
(华侨大学 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我国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传统分类依据注重升格条件要素的表面化差异性,与德日刑法理论强调升格条件的实质内涵区分迥然不同,后者具有简约性与明确性,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足。构成要件的违法性是升格条件的形式区分标准;责任主义原理是升格条件的实质区分标准。区分纯正加重犯与不纯正加重犯,能够更好地从理论架构上解决这种既存的弊病。
法定刑升格条件;形式区分;实质区分;责任主义;纯正加重犯;不纯正加重犯
一、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分类依据
(一)传统的分类依据
费尔巴哈是将构成要件引入实体刑法的第一人,他认为构成要件不包含主观构成要件而仅包括客观构成要件。[1]俄国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传入了构成要件的概念,但刑法学者在费尔巴哈的构成要件概念基础之上升华加工,进而形成了主客观相统一的构成要件的概念。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苏俄刑法学家提出了“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则是犯罪成立条件的总和,由此可见,传统四要件显然不是以构成要件为基础的。苏联刑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大陆法系刑法学的弊端过程中提出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试图构建出社会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2]我国刑法理论沿袭了苏联的“四要件说”犯罪构成体系,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但是“四要件说”在认定犯罪过程中不是一种开放的、立体的、阶层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其在特定时期存在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体系上无法弥补的漏洞。
加重构成是相对于基本构成而言,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加重了某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使之转化为罪质更深的犯罪。根据我国“四要件说”的犯罪论体系,加重构成犯罪可以分为客体要件加重、客观要件加重、主体要件加重和主观要件加重四种类型。与之对应,加重构成也可以相应分为侵害客体加重的构成、客观方面加重的构成、主体加重的构成和主观方面加重的构成。[3](P30)我国刑法学界关于法定刑升格条件就情节、结果、数额、身份、对象、手段、时间、地点、行为等要素而分为九种加重犯。申言之,上述法定刑升格条件有时是在某种加重构成犯罪的罪状中单独加以规定,或者在同一加重构成犯罪的罪状中却出现数个加重犯罪构成,如我国《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中就不同的加重因素分别列举了八个升格条件。
(二)新型的分类依据
我国的刑法理论追根溯源,实际上得来于苏联的刑法理论蓝本,二者都模糊地把构成要件概念与本土的犯罪构成混为一谈,认为犯罪的实体是不法与有责,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相较于德日的构成要件是成立犯罪的条件之一,我国的犯罪构成等于犯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张明楷教授认为,“倘若将犯罪构成作为成立犯罪的全部条件,则要求犯罪构成包括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而仅将客观要素或者只将主观要素纳入犯罪构成的话,就必然造成客观归罪或者主观归罪的诟病。”[4]张明楷教授站在客观主义刑法立场上,整合了德日刑法的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①主张不法与有责的二阶层犯罪构成理论。
通观我国的刑法理论,加重构成与法定刑升格是两个内涵与外延截然不同的概念,两者的着力点不同,前者倾向于法定刑,后者倾向于构成要件。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因为传统上来讲,所有的升格条件皆是犯罪构成要件。众所周知,法定刑加重与构成要件要素变化不是正相关的关系,前者加重,后者不必然改变,反之亦然。德国把加重犯分为构成要件的变异与单纯的量刑规则的通例。例如,甲男潜至乙女家中实施了强奸,随后,又在马路上偶遇仇人丙女,不顾其幼年子女又当面实施了奸淫。由此推之,前后两个强奸行为分别构成普通强奸罪与加重强奸罪。倘若按照“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就是一罪”的原则,那么,两个危害行为就认定为两个犯罪。但是,无论刑法理论还是司法解释仅规定了一个罪名。由此,张明楷教授根据法定刑升格条件后的加重犯是否改变了基本行为类型,将刑法分则条文单纯以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以及数额或数量(特别)巨大、首要分子、多次、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犯罪行为滋生之物数量(数额)巨大作为升格条件时,视为量刑规则;而条文中其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改变了其行为类型的,进而加深了违法性程度,并加重法定刑时,才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5]这种建之于不法与有责的二阶层之上的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缺乏责任主义原则的有效制约。
二、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分类标准
(一)形式区分标准
按照构成要件理论,构成要件是违法的行为类型,是将侵害某类法益的不法行为进行类型化,具有定型性与违法性的双重特征,二者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定型性特征是“图像”,而违法性特征是“实体”。根据刑法理论通说,认定犯罪应当根据客观主义归责原则,犯罪行为都是有责的不法,遵循由不法到有责逻辑顺序,亦即从客观层面的违法到主观层面的责任的定罪思路。对于构成要件,宾丁认为只是违法性的“征表”,而梅兹格则认为是违法性的内在依据。②因而,在考量构成要件要素时,也应该将其实质违法性作为判断基准。因为形式违法性是违反刑法规范,而实质违法性则是侵犯法益。
囿于违法性因素的差异化而致使升格条件产生了形式区分标准。就传统的升格条件分类,周光权教授认为,“加重构成基于构成要件添加了加重要素,塑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基本犯的既遂与加重构成是否成立并不相关。”[6]依据刑法分则中法定刑的配置来看,加重构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衔接式加重”,例如《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另一种是“交叉式加重”,例如《刑法》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罪刑规范的目的是保护被危害行为所侵害与威胁的法益。换言之,只要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的行为就是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李海东博士认为,“其加重要件是基本构成通过增加了加重要素而转化来的。”通俗来讲,加重构成是在基本犯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法要素,即具有超过基本构成要件要素的加重要素。
以结果加重犯为例,即行为人的基本行为造成了超出基本犯罪构成的重结果。例如我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基本犯的故意伤害行为过失的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重结果,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加重犯。根据罪数理论,亦即“一罪符合一个犯罪构成”,那么,故意伤害行为与致人死亡行为则符合两个独立的犯罪构成,且犯罪构成要件的违法类型不同。再者,以侵犯的法益为立场,一种是身体健康的法益,一种是生命的法益。根据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客观的危害结果是违法要素,这就意味着,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较之于单纯的故意伤害罪而言,在不法层面的危害结果因素上加深了违法性程度。概言之,传统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形式分类标准,以先符合基本构成要件为前提,在没有修正基本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单纯的增加了其不法层面的要素。
(二)实质区分标准
按照新型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分类,加重构成改变了基本的违法行为类型,例如,“持枪抢劫”“入户抢劫”等,使抢劫行为的基本行为类型发生了变化,故转化为加重犯。而量刑规则并没有改变,比如,“首要分子”“多次”等没有改变基本的违法行为类型,故是一种单纯的裁量规则。再如,《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组织考试作弊罪,立法者基于社会中考试作弊的常态化行为,结合责任性与预防性的归责原则,分别设置了从重处罚情节:特殊身份的从重处罚、行为次数的从重处罚、涉案金额的从重处罚,亦即身份加重犯、次数加重犯、数额加重犯。[7]德国责任主义原则有别于我国的刑事责任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是包括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分为积极责任主义与消极责任主义。纵观国内外的犯罪论相关理论,无论德日的三阶层抑或二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还是我国传统的四要件说,判定犯罪行为都是把责任的认定放到最后的位置。责任主义的机能贯穿于犯罪论与刑罚论,不仅是成立犯罪的必备条件之一,起到了归责之功用,而且在裁量刑罚时为确定刑种、刑量提高了基准。总之,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实质分类标准为:在加重犯的罪质相同的前提下,看其罪责是否坚持了责任主义原理。
笔者认为,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别在于:一是构成要件上的变化;二是量刑规则仅是处刑的裁量依据。诚如张明楷教授在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时认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有具体与抽象之分。除了抽象升格条件都是量刑规则外,具体升格条件还存在加重构成。”[5]张明楷教授一贯主张客观主义刑法立场,对行为人归责的根据是客观的违法事实,而且对客观事实要具有责任。上述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分类中,刑法规定了犯罪构成与量刑规则,前者具有加重构成该当性且违法,后者仅决定法定刑幅度的选择。综上所述,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分类标准采用形式区分标准与实质区分标准,就是针对传统分类与新型分类而言的。传统分类强调违法性因素的差异化,而新型分类则强调升格条件后是否坚持了责任主义原理。
三、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分类特征
(一)递增性
无论是传统加重犯分类中的情节加重犯、结果加重犯、对象加重犯、数额加重犯、时间加重犯、地点加重犯还是行为加重犯,或是新型升格条件分类中的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均呈现出违法程度的递增性。加重构成犯是在责任主义视野下的不法与有责的统一体;量刑规则是单纯的构成与否问题。如上文所述《德国刑法》第243条的规定,加重了盗窃罪的基本犯。加重情节作为抽象的升格条件,其严重性程度是由主客观要素相统一的形式加以体现,进而决定加重刑罚的综合指标。以张明楷教授所主张的观点来看,“刑法分则条文中单纯以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以及数额或数量(特别)巨大、首要分子、多次、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数量(数额)巨大是法定刑升格条件,而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使行为类型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违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时,才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5]
笔者认为,法定刑升格条件乃是启动加重刑罚量的前置条件,加重构成修正了基本构成要件,增加了违法性因素。量刑规则虽未修正基本构成,但却出现了更严重的危害结果,故也呈现了违法程度递增性。例如,我国《刑法》第383条依据贪污数额逐渐增大,而正相关地加重刑罚。无论是传统分类还是新型分类,实质上均是基本犯的危害结果在违法性程度上呈现正相关式的增加。
(二)离散性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责任性与预防性,或言报应性与目的性,其中的报应是责任报应。所谓责任报应,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做的行为具有责任,并由责任界定刑罚的上限。责任贯穿于犯罪论与刑罚论,既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又是裁量刑罚的基础。根据基本法定刑与升格法定刑罪名一致性,基本法定刑与升格法定刑的根据均是责任主义,只是后者加深了责任程度而已。以我国刑法分则的罪状为分析样本,尚存两种升格条件:其一,升格条件是加重构成,修正了基本构成要件,行为人对升格条件具有责任;其二,升格条件作为单纯的量刑规则,未能修正基本构成要件,只是处以刑罚的裁量标准。两种升格条件彼此独立,互不交叉,具有离散性。例如,我国《刑法》第383条贪污罪与第386条受贿罪的罪状中规定的加重数额,均是单纯的量刑规则,不受责任主义所制约。
(三)耦合性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法定刑升格条件既包含加重构成要件又有量刑规则,二者相互交织,难以判定,呈现出耦合性。责任主义的机能既体现在定罪中,也体现在量刑中。通常来讲,对行为人裁量刑罚受制于责任性限制,亦即责任性制约预防性。而且,根据客观归责主义原则,升格条件中加重构成事实必须是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客观事实。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刑升格条件,依据张明楷教授的定型性标准来看,第四项规定的“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属于量刑规则,其他则是加重的犯罪构成。然而,柏浪涛博士在批判张明楷教授观点时则认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以违法性标准为标尺,分为真正的不法加重要素与表面的不法加重要素。定型性标准与违法性标准,实质上得来于犯罪构成的两大特征,其最大分歧就在于数额犯中的单次数额与累计数额。笔者认为,对于单次数额由于具有明确性、可知性,应当归于加重构成;而对于累计数额具有模糊性、未知性,应当归于量刑规则。由此可知,“数额巨大”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单次数额巨大抑或累计数额巨大是加重构成还是量刑规则的问题,进而导致司法人员缺乏统一的可操作性标准。
四、区分纯正加重犯与不纯正加重犯的必要性
(一)纯正加重犯
责任主义原理要求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至少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具体而言,即使危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全部要素,给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侵害或者危险,倘若对行为人没有非难可能性,故也不能课以刑罚。正如上文提及的“无责任则无刑罚的原则,在保障人权与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在德国,裁量刑罚时要以责任为基础,责任主义为量刑提供思想基础和适用标准。一方面,责任主义要求量刑与责任的程度和大小相适应,即责任大刑罚相应就较重,责任轻刑罚相应就较轻;另一方面,责任主义要求量刑不得逾越责任的限度。由于责任评价的对象是行为,故应当将同行为责任无关的因素排除在量刑时考量的因素之外。因为责任性制约预防性,所以增加预防性的刑量始终不能越过责任性的上限。
所谓纯正加重犯,是指在满足基本构成要件全部要素的基础之上,法定刑升格条件修正了基本犯的构成要件,导致基本行为类型有所改变的加重犯。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构成要件是“A+B+C”与“A+B+C+D”的关系,新补充的不法要素“D”具有将构成要件特殊化的作用。不法加重要素既包括“质”上的变化,也包括“量”上的增加。例如,抢劫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中“抢劫数额巨大的财物”与“抢劫军用物资”都是增加了行为对象,但前者的行为对象仅仅在量上增加了违法性,属于单纯的量刑规则;而后者的行为对象在质上增加了新的违法性,也即侵害了“国防军事利益”,属于纯正加重构成。依据直接关联性原则,倘若基本犯为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那么,纯正加重犯具有未完成形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适用于基本犯而且也适用于加重犯。纯正加重犯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依附于基本犯而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例如,行为人在其密闭的房间内未能强奸一女子与在广场上当众也未能强奸一女子相比,尽管两者都是强奸未遂,但是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个加重要件,即“当众”。由此,前一行为构成一般强奸罪的未遂,而后一行为则构成强奸罪的加重犯的未遂。
(二)不纯正加重犯
张明楷教授认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应分为具体升格条件与抽象升格条件。就其如何区分,上文已做阐述,在此不再详论。而像情节严重(特别严重)、情节恶劣(特别恶劣)等之类的抽象升格条件,张明楷教授则主张作为加重构成要件处理。[9]笔者认为,张明楷教授之观点尚为不妥,正如上文所言,在明确区分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德国,其法律规定抽象的升格条件进而加重刑罚以及相关范例,只是裁量刑罚的量刑规则。王彦强博士也认为,“量刑规则,即刑法中规定的法定刑升格条件,只是决定量刑幅度如何选择,而不具备加重构成要件的特征。”[10]因此,对于像“情节严重(特别严重)、情节恶劣(特别恶劣)”之类的抽象升格条件,则需要在责任主义视野下,对客观构成要件具有认识的可能性。
所谓不纯正加重犯,是指在满足基本构成要件全部要素的基础上,具备法定刑升格条件就加重基本犯的刑罚,但却未能修正基本构成要件的加重犯。不纯正加重犯具有纯正加重犯那种加重其刑罚量的刑罚特征,但又区别于严格意义上加重犯。例如,我国《刑法》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贪污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与第383条第2款规定的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由此可知,贪污罪的法定刑升格后构成不纯正加重犯。就行为人单次贪污数额(特别)巨大的升格条件,应当具有认识可能性,亦即坚持责任主义原理,属于纯正加重犯;而多次、连续贪污的累加数额犯的升格条件,则不需要具有认识可能性,亦即只要累计数额达到了加重处罚标准就应当升格法定刑,属于不纯正加重犯。简言之,纯正加重犯与不纯正加重犯的实质区分意义在于,将法定刑升格条件作为加重其刑罚量的驱动器。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有益于法官裁量刑罚的明确性,防止裁量的擅断性,更好地保障人权。
五、结语
关于我国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区分,刑法理论界有定型性标准说与违法性标准说。定型性标准说从客观主义刑法立场出发,分为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违法性标准说从是否坚持责任主义,分为真正的不法加重要素与表面的不法加重要素。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实质区分,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标杆,以责任主义原理为根基,打破了仅凭一种不明确性的分类标准来划定升格条件的分类局面。纯正加重犯与不纯正加重犯,二者在保持与基本犯罪责相一致的前提下加深其罪质与刑量,突出了法定刑升格条件后的罪责与罪质的特点。
注释:
①德国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中,第二阶层被称为“违法性”,又因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因此,将构成要件该当性且违法称为“不法”。
②Edmund Mezger,Strafrecht,3.Aufl.,Duncker&Humblot,1949,S.182,转引自:柏浪涛,《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实质区分》,刊于《法律科学》,2016年第6期。
[1]何秉松,〔俄〕科米萨罗夫,〔俄〕科罗别耶夫.中国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何秉松.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与现状[J].法学研究,1986,(4).
[3]卢宇蓉.加重构成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4]张明楷.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J].现代法学,2009,(6).
[5]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J].清华法学,2011,(1).
[6]周光权,卢宇蓉.犯罪加重构成基本问题研究[J].法律科学,2001,(5).
[7]沈文俐.对考试作弊行为入刑的必要性思考[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8).
[8]〔日〕西田典之.金光旭.论刑法中的“责任”概念[A].冯军.比较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张明楷.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识[J].政法论坛,2009,(9).
[10]王彦强.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罪量加重构成概念之提倡[J].现代法学,2013,(3).
TheNatureClassificationoftheConditionsfortheStatutoryPenalty
LI Qing-hang
(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China)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tatutory penalty in China depends on the apparent difference of the condition elements.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ounterpart in Germany and Japan,concerning the nature and connotation,which is much more brief and definite. However,there are inadequacies in the legal practice. To distinguish the pure and impure aggravated offences may solve th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tatutory penalty;the formal distinction;the nature distinction;the pure aggravated offences;the impure aggravated offences
2017-03-02
李庆航(1990-),男,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刑法研究。
1004—5856(2017)12—0048—05
D924.1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12.011
孙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