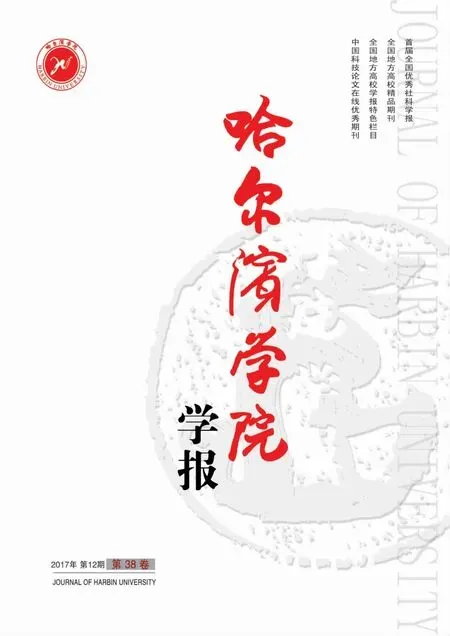叙事范式与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相关性分析
赵传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3)
叙事范式与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相关性分析
赵传珍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3)
叙事离不开话语,话语则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形式。叙事与意识形态教育的相关性不仅彰显在各种叙事范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方面,还体现在意识形态教育所具有的独特叙事效果方面。“日常生活”实践是通达叙事和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辩证统一的“桥梁”,也是治愈意识形态教育因叙事话语不当而出现教育“乌托邦”病症的“良药”。
叙事范式;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性;话语;日常生活
叙事是面向事实的一种教育范式,是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教育不可规避的形式。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主要被人们看成是纯粹理论或观念的说教,忽视了叙事作为方法论与意识形态教育之间的相关性。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叙事的意识形态特性,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效果,以及日常生活实践是通达叙事效果和意识形态教育效果辩证统一的“桥梁”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叙事范式与意识形态教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是怎样发生效果的。
一、叙事的意识形态特性
叙事,就是用语言讲述一个或多个事件,提倡面向事实本身或者从事实本身中探寻讲述对象的内在结构和本质。叙事范式是在哲学、文学、修辞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影响下产生的,注重从社会历史、教学对象以及研究对象的历史感知视角来进行探讨的一种方法维度,旨在把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拓展与继承自身叙事相结合。叙事范式的本质是“描述事实”(describe the fact),“描述”离不开“话语”,而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教育总是借助话语的宣传和教化来践行的。叙事的意识形态特性是经由话语这个媒介,尤其是话语权来执行。例如,我们的新闻联播每天都在叙述报道发生在国内国际各地的新闻,这些叙事通过广泛的传播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说新闻联播的叙事确立了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那么意识形态教育上的叙事目的也在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权利体系。具体而言,有两种形式各异但同质的叙事,同时相应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特性。
一种是虚构叙事的意识形态特性。虚构的叙事发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等,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生活,显现为宗教故事以及世俗的教育小说、教育诗歌、教育故事、教育电视、教育电影,等等。例如,《皇帝的新装》《圣经》《爱弥儿》等都是虚构叙事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通过叙事的方式发挥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虚构的叙事不仅运用在文化教育领域产生教化、引导意识形态的作用。还出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彰显其统治民众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价值。“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是一对孪生姐妹。意识形态是权力话语,而权力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固化物。意识形态就是要用话语来维持社会的权利结构。”[1]意识形态的这种话语权力通过叙事的方式,以一种隐蔽、内在的力量发生作用。尤其是这种虚构的叙事更具有一种强大的隐形扩张力。例如,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渗透,就是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虚构叙事方式实施的,他们所倡导的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西方话语”和“西方价值”,却偏偏要叙述成“全球”和“普世”的虚构场面。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这样叙事,不仅在于虚构叙事的效果好,也在于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他们才有这样叙事的话语“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98-99)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虚构的叙事带有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特性。虚构叙事的这种虚假意识的特征,是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视角中确定的,这种虚假的意识“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先辈的思维中引出。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3](P726)这是一种根植于唯心主义思想土壤的意识形态,把人与社会的实践割裂开来,背离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因不能正确反映存在和事实而成为的“虚假意识”。
另一种是真实叙事的意识形态特性。真实的叙事相当于实证叙事。区别于文学领域的虚构叙事,真实叙事主要应用在对历史和当下客观事件的描述。或者说,“真实性”是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的首要原则。真实的叙事可以分为“生活真实、逻辑真实、情感真实”三个层面。生活真实,主要指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过或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或故事。例如,“完璧归赵”叙述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蔺相如不负赵王所托带着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去见秦王,并利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让宝玉完整无瑕地回到赵王手中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真实叙事。逻辑真实,是指根据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推导出的有可能发生的某个事件或故事。例如,通过“完璧归赵”和“负荆请罪”的故事,我们可以推论出蔺相如是一个既机智勇敢,又心怀宽广忠于君主的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做出为保护赵王而牺牲自己的事情。情感真实,是指能够引起人们情感共鸣或心灵共融的事件与故事。虚构的叙事没有真实叙事三个层面的约束,虚构的叙事可以是对现实的虚构,也可以是对没有逻辑的超现实社会的虚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叙事中的虚构可以算得上是逻辑真实或情感真实,但是它需要生活真实的历史资料作为根据。这种具有三个层面的真实叙事的意识形态特性散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实践的方方面面,例如,我们通常会给学生或子女叙述真实的历史故事,比如发生在1900年6月17日的八国联军(英、法、德、俄、美、日、意、奥)侵华事件,这些真实故事的叙事就会转化为他们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野蛮暴力侵略行为的痛恨,让他们自觉升华一种爱国护国之情,从而达到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可见,真实叙事具有社会学意义“意识形态”特性。从一般意义上说,自从人类有了精神活动,也就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内部包括各种丰富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历史、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卡尔·曼海姆认为这种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无关,以此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雷蒙德·盖斯也把这种具有描述意义的意识形态看成是一定社会的文化体系,不带价值评价,只是中性和客观的描述。从意识形态教育的视野来看,这种不带任何价值评价的事实叙事恰恰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最佳教育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虚构叙事,还是事实叙事,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或者单独发生意识形态教育作用的。任何虚构的叙事都有一定生活的“原型”,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任何事实的叙事也都不可能是绝对百分之百对客观事实的“还原”,尤其是历史的事实叙事。真实的情况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辩证统一在实践之中。那么,作为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教育,如何通过巧妙的叙事达到一定的教育效果呢?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效果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二、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效果
意识形态教育,是通过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受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的自信和认同,维持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教育却往往因为叙事话语不当而出现“教育乌托邦”的尴尬现象。那么,怎样才能彰显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效果呢?把这种教育落实到实处呢?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关系上澄清“意识形态”教育的本真之意,是达到一定叙事效果的认识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影响的教育,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4](P6)突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现象,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般特点,又具有反映一定阶级社会占统治阶级经济基础的阶级性。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意识形态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但是,意识形态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从发挥功能的角度来看,面向受教育者传播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而意识形态教育不仅具有促进个体成长和社会功能发展的作用,而且具有链接一个社会或国家与世界联系的功能。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5](P197)阿尔都塞也强调:“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6](P201)可见,意识形态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以及个体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的精神和价值诉求,这种价值层面的内涵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本真之意,而且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效果是通过一定的话语权力来获得保障的。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是怎样经由话语权而发生的呢?
所谓的话语权,就是一个人通过说话,通过一定的语言符号来传达命令并确立起自己权威的地位。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因为人类正是通过话语来进行日常社会实践活动的。例如,教研室主任对新来的同事说:“我们这个学期教学任务繁重,你需要每周安排20节课。”对于这样的现象,哈贝马斯分析认为,这涉及到客观事实、主观思想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例如,这个学期的教学任务是不是真得很繁重,是不是教研室其他老师都需要每周上20节课,教研室主任有没有资格在别人没有承担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前提下让新老师上这么多课,新老师有没有上这么多课的需要等。在这里,教研室主任让新来的老师一周上20节课,实际上就体现了日常话语交流中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1]这正如布迪厄所言:“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不仅是知识的工具,而且还是权力的工具。一个人(说话)不仅要努力被人听见,而且也努力被人相信、被人遵从、被人尊敬、被人称颂。”[7](P47)这种经由语言符号传达和表征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力,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训导植入人们的心灵深处,会在不自觉中成为人们的行为习惯,即形成“物化意识形态”浸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例如,本来教研室主任要说话,安排新老师每周上20节课。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这种由新来老师承担更繁重工作的习惯已经形成了,主任不发话,新老师也会主动要求承担更繁重的工作。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是话语,不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人们的日常行动,是固化在行动中的权力关系,是灵魂技术学,即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1]可见,意识形态不仅只以观念形式存在,而且还以物化形式存在。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仅就单个的主体某个个人而言,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者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8]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物质化的社会当中。在社会这个大机器中处处呈现出被意识形态浸染的痕迹。人类被这种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实践所包围,无处可逃,无处可避。如果前面案例中新老师追问:“为什么他要一周上20节课”,那么周围的同事会告诉他,在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这是延续下来的习惯。这种习惯(即物化的意识形态)为人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可见,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最终是由人的实际社会行动来彰显。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叙事效果是通过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或一种指导思想体系只有物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实际地发挥作用。因此,研究意识形态教育就需要研究它如何通过叙事效果物化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践中。
三、日常生活:叙事效果与意识形态教育辩证统一的桥梁
实现叙事效果与意识形态教育的统一,需要我们关注“日常生活”这个基本向度,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还具有生存论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P32)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个体物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考察,目的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对个体的压制和“异化”。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体论思想,他充分肯定了日常生活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互相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生活需要的——特性,通过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9]可见,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日常生活的本体论意义,从本体论的角度强调了日常生活相对于科学和艺术等非日常生活活动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即“日常生活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来理解叙事范式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相关性时,“日常生活”这一基本向度必然会进入到我们研究的视野之中。“意识形态是物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向所有大众日常生活开放的发展过程。“意识形态教育是日常的”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且有力地批判了文化精英主义。只有当我们把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也纳入“意识形态教育”领域时,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叙事的效果,才能说明意识形态教育并不只是面对少数精英人物的“专利”,而是要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民大众达到更佳效果的意识形态教育宣传工作。那么,“日常生活”作为实现叙事效果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统一的桥梁,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首先,叙事逻辑应该尊重群众日常思维发展规律。无论是虚构叙事,还是真实叙事,都遵循有一定的逻辑。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把人类的思维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的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10](P1)意识形态教育若想要为大众接受和认同需要转化叙事方式,尊重大众思维发展规律,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是通过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民众良好的素质,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在这里,要使起源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民众认同并接受,需要在叙事上注意一定的方法,使原本具有西方逻辑思维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中国老百姓思维所接受,需要结合中国社会具体的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使叙事方式与中国大众的认知逻辑契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注意叙事方式,还要善于把叙事的理论话语转化成日常话语,使理论“深入浅出”,符合大众的思维规律,最终才能为民众接受,实现叙事效果与意识形态教育的统一。
其次,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内容要生活化。当我们应用叙事范式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时,应该善于从社会实践生活中选取恰当的热点问题和案例进行整理和提炼,把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内容嵌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使大众在无意识中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话语,从而通达叙事效果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统一。日常生活实践的流动性和变异性决定了意识形态教育叙事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恰当的话题,并将其切入理论叙事话语之中。例如,通过阐述并分析发生在香港的“占领中环”(以下简称“占中”)事件,对于大部分香港大众而言,“占中”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交通堵塞和生意无法继续等,看似是一场“民主政治”诉求的运动,殊不知却是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令“占中”发起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运动带给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由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教育“回归生活”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以叙事为主要范式的意识形态教育更需在内容上“回归生活”,以实现叙事效果和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的高度契合。
最后,“日常生活”是避免意识形态教育叙事落入“乌托邦”的“良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的那样:“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如何避免让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落于“乌托邦”,找到治愈意识形态工作“乌托邦”病症的“良药”,是值得我们关切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用不同方式都在卖力地讲述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例如,我们通过讲述近现代历史故事,进行社会热点问题剖析,甚至用煽情感人的真实故事让大众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但是,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话语没有关切人们实际的社会生活状况,并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么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叙事效果都是短暂的。在社会实践中,真正能够起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意识形态教育不是这样的,而是那种内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化意识形态”。这种落实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育才最有可能实现叙事效果与教育效果的辩证统一。例如,我们进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需要“关注大学生的兴趣点和热点问题,兼顾他们遇到的现实问题,提高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效率,增强教育的感染性和实效性。”[11]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时,并不是从高在云端的高深理论出发对工人阶级进行洗脑,而是直接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境况出发,用他们最关切的叙事话语来展开意识形态教育。取得了世界所有无产阶级者的支持,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国际联盟组织。因此,落实在日常生活实际中的意识形态教育叙事才能真正实现两者效果的统一。或者说,“日常生活”是我们避免意识形态教育叙事落入“乌托邦”的一剂“良药”。
[1]王晓升.权利、话语与意识形态[J].哲学动态,2012,(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教育出版社,2001.
[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Cf.John B.Thompson,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8]赵传珍.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及其限度[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
[9]〔匈〕卢卡奇.徐恒醇.审美特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0]孔德.论实证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1]余世建,朱松节.网络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7).
NarrativeParadigmandtheEffectofIdeologyEducation:CorrelationAnalysis
ZHAO Chuan-zhe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 510303,China)
Narration is made of discourse while discourse is the main form of ideology educa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s reflected not only from the ideological aspect but also from the unique narrative effect of the ideology education. The “daily life” practice is the “bridge” of for the unity of understandable narration and ideology education effect,which is also the cure for the illness of education “Utopia” caused by the ideology education with inappropriate narration.
the narrative paradigm;the ideology education;correlation;discourse;daily life
2017-02-2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项目编号:GD14XMK18;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7YJA710043;广东第二师范学院2016年博士科研专项经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ARF14。
赵传珍(1972-),女,湖北南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1004—5856(2017)12—0031—05
B036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12.007
魏乐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