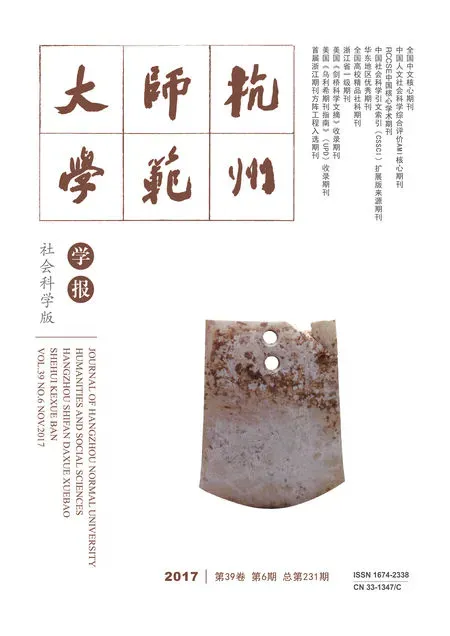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王汶成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文艺新论
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王汶成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文学话语是文学交际活动的产物,文学文本是文学话语的主要形态之一,而文学文体则体现为文学文本在风格和体式上的不同类型。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审美性的追求,在于以审美性而不是以功利性为基准。因而,研究文学文体类型主要是研究各种文学文本的审美特点。在这种研究中,诸如研究的对象、方法、分类标准和类型变异等基本理论问题,必须首先予以澄清。
文学话语;文学文体;文体类型
一、何为“文体”
文学话语是指将文学活动理解为言语交际活动所产生的作者言语、文本言语、读者言语、评论言语等一切话语形态的总和;其中文学文本不过是文学话语的诸种形态之一,文学文本又体现为诸种文体类型。“文体”一词,原本来自语言学范畴,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语言学里,研究文体现象的学问被称之为“文体学”。后来,文学理论、语言哲学、话语理论等也都开始研究文体问题。那么,什么是文体?人们说话、写文章总是在一定的场合和情境中进行的,并涉及一定的交际目的、交际信息、交际媒介和交际对象等;交际的场景、目的、信息、媒介、对象不同,人们所说的话或所写的文章也就不同,有着不同的风格和体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语体(说话)或文体(写文章)。譬如同一个人,当众演说时说一种话,跟朋友私下聊天时又说另一种话。写作也一样,起草官方文件是一种文本,写一首诗歌、小说等或者写一篇学术论文,又构成了其他的文本样式。这些话语和文本在语言风格和体式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分属不同的文体(广义的文体,也包括各种语体)。因此,所谓文体大约可以这样界说:特定的言语主体在特定的境况下,出于特定的交际目的,面对特定的交流对象而发出的具有某种特定内容和结构形态的话语或文本之体式、样式或风格。或者简单地说,文体即是话语或文章的风格。在英语中,文体和风格原本是一个词,可以通用。当然,目前学界对文体概念的理解分歧很大,我们的理解仅为其中的一说。
我们的理解显然涉及了文体形成的全部要素,这就是“谁何时对谁说何种话语”。这就是说,某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性特征的形成,离不开六个要素,即“谁说”(话语主体)、“谁听”(话语受体)、“何时说”(话语环境)、“为什么说”(话语目的)、“说什么”(话语内容)、“怎么说”(话语构建)。其中,第一、第四和第六要素偏重主观因素,其余的要素偏重客观因素。话语主体在文体形成中具有最强大的能动性,话语主体按照传达和交流的意图,主动地选择、构建出一定的言语体式。当然,整个言语体式的选择和组建过程又受到其他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这六个要素在文体形成中的作用并不总是平衡的,对某种特定文体来说,要素甲或要素乙可能起着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对另一种文体来说,要素丙或要素丁的作用可能更为关键。由此产生了有关文体形成的各种理论,如变异说(强调话语主体的创新)、选择说(强调话语主体的动机和目的)、个性说(强调话语主体的内在气质和品性)、特指说(强调话语内容对话语形式的限定)、 认知说(强调话语接受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等等。当然,无论对哪种文体来说,都离不开上述六个要素的协同作用,都是六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说,某种文体的区别性特征的生成,正是上述六要素的相互制约与综合作用的结果。
上述六大要素都是可变要素,都是作为文体形成的变量而存在的。六要素中只要有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文体特征的相应改变。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改变只是微小的、数量上的,不至于引起质的变化。因此在这个限度内,不断变化的文体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在这个限度之外,它就变为另一类型的文体了。为了更好地把握文体间的这种家族相似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体类型之间的区别性特征,文体学还需要对文体进行分类研究。
二、如何对文体分类
对文体类型的划分向来比较复杂,关键在于所使用的分类标准不同。分类依据的标准不同,划分的类别也就不一样。一般而言,文体研究中较为通行的分类方法,一是依照交际方式的不同进行划分。人们使用语言交流信息时采取的基本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口说,一种是书写。这两种基本方式,由于交际时的话语主体间的关系、客观语境、使用的媒介等不一样,因而由此形成的文体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一般的口语交际(利用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口语交际可能稍有不同),交际的双方都在现场,可以互相倾听和观看,这种情况使得双方的发言必然是即时性的轮番进行,并且可多方面利用所谓副语言特征(表情、手势、体态等)以补充单纯言语传达的不足,因而在措辞、句式、语法、语义等方面都必然是简约的、默契的、相互诱发的、不一定严格合乎语言规范。而在书写的交际中,交际的接受主体并不在现场,完全凭单方面的书写文本来传递信息,许多语境因素必须交代清楚,所以在用语和行文的体式上就体现了力求规范、相对完整详尽、经过用心筹划的特点。在这两种交际方式下构成的文体显然有着本质差别。前者实际上是一种直接对话或会话的文体,语言学一般称之为口语文体;后者则是一种独白的(巴赫金认为本质上也是对话的)文体,一般称之为书面文体。这就是以交际方式为主要依据划分的文体类型。
二是从交际场合以及交际双方的关系方面划分。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时所处的交际场合是千差万别的,有时这种交流是在庄重、严肃、认真的氛围中展开的,交际者之间的关系也保持一定的间距,其中往往包含了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内涵,例如上下级之间、长幼之间、尊卑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流等等。有时,交流又是在较为轻松随意的状态下进行的,交流主体之间的关系一般是私人性的,较为亲密,甚至是亲密无间的,例如家庭成员之间、夫妻之间、情人之间的关系即是这样。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产生的文体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可称为正式文体,后者则称为非正式文体。试想一个人在课堂上讲的话与在家里讲的话有什么不同,就不难明白上述两种文体类型之间的区别了。
三是从话语主体所使用的民族语言以及地域语言的不同着眼的划分。语言是民族特性的重要表现,一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语言的不同,而民族之间的沟通也主要依赖语言沟通。所以,即使在现代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和交流也必须建立在语言的互译和转换上。因而,迄今为止,要谈共同语也只能是民族共同语,只有在同一民族的范围内,才有所谓的共同语言的存在。超出民族的界限,就只有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了。至于这种影响和渗透能否最终产生出一种世界共同语,这取决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未来发展能否推动这样一种需要,以及这种需要有没有条件得到满足了。至少就当今情况看,语言还是以民族划分的,所谓世界共同语,可能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奢望。而民族共同语并非意味着同一民族的人所操持的语言完全相同,而是指一民族的语言总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一性。正是以这种一致性和同一性为基准,每个大的民族都会选定本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方言系统,并将其确认为该民族的标准语。这就是说,在一个民族内部,虽然存在着共同的语言内核,但由于该民族成员居住地及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民族共同语也会分化为种种不同的变体,语言学称之为区域性变体。一般说来,处于中心区域和社会上层的语言变体被确立为标准语,而其他居住区域的语言变体则称之为方言。这样,在民族语言内部,按照居住地域和社会分层的不同划分,可区分出使用标准语或方言两种不同的语体或文体;其所使用的方言还可进一步区分为种种不同的类别。例如汉民族语言,其现行的标准语是以北京地区的方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汉民族居住区域的广大和地理条件的多变,使得汉民族方言的分布极为复杂和细碎。其大的方言系统就有北方话、吴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等,小的方言就更无计其数了。这些方言都各有其发音、词汇、句法上的特点,有的差别很大,甚至无法听懂。但无论差别多大,这些方言都具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本民族语言的内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方言(包括标准语)理解为民族语言的不同的变体,而用不同变体的方言说话、写文章,即可据此区分出种种不同的语体或文体。
四是按照文章风格的不同而划分的。文章就是用文字写出的话语篇章,所有的书面语体应该说都属于文章的范围。人们写文章总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出于不同的目的、面对不同的对象去写的,由此写出的文章在措辞用语、章法格式等诸多方面都不一样,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章风格。前面说过,在英文里风格与文体是一个词,文章风格其实就是狭义的文体。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讲的“文”就是指所有的文章,他根据文章风格的不同区分了文体的类型,提出了著名的“本同而末异”的理论。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把文章区分为四类八体,他的分类及其对各文类风格特点的概括现在看未必妥当,但他提出的理论具有开创性价值,他开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和文体风格论的先河。在曹丕之后,陆机、刘勰等人又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文体分类理论,从而使文体分类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有建树的几个分支学科之一。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始于六朝的“文笔”之争上。南朝宋人颜延之最早把文章划分为“文”与“笔”两大类,其后,文论家们就“何者为文、何者为笔”展开了争论,提出了各种观点。刘勰主要是从文章的形式上解释“文”与“笔”的区别,认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1](P.525)稍后于刘勰的萧绎,主要从文章性质上划分“文”与“笔”,认为像“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情摇荡”的文章,也就是能够打动人的情感、讲究文采和音乐美的文章,才可以称为“文”,而“善为奏章”、“善辑疏略”的论事说理实用之文,则叫作“笔”。[2](P.368)其对“文”、“笔”的辨识,后人仍聚讼纷纭,但基本上仍为上述两种观点的继续。中国古代文论家把文章区分为“文”与“笔”两大类的观点,应该说是富有见地的,基本上抓住了从文章风格的角度划分文类的要领。西方现代文体学家对文章风格的分类与中国古代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们也主要是从文章有无艺术性、审美性着眼来辨别文类的。他们认为在所有的书面文字中,有一些文字是专门用来叙事说理、说明情况、传递信息的,或者是出于某种功利性目的而写的,并不特意追求用语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而另一些文字则与此相异,无论是描写、叙述、议论、抒情,都乐于以用语的巧妙、别致、富于创造性和审美感染力为己任。前者被称为科学文体和应用文体,如科学论文、调查报告、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公文、广告词等等;后者被叫作文学文体,如诗歌、小说、剧本、文艺性散文等等。由此可见,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审美性的追求,就在于以审美性而不是以功利性为基准。而非文学文体则追求一种实用效果,是以实用性为基准的。例如,一首抒情诗和一则通知的区别就是这样。
上述四种文体分类的方法,都是文体分类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对同一篇文章如果运用不同的方法,可能被划归为不同的类型。但只有第四种分类方法才涉及文学文体。
三、“文学文体”研究的文艺学路径
文学文体可以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不过,这两种研究有着性质上的差别。语言学研究文学文体,是把文学文体作为运用语言系统的一个特例来看待的,最终还是为了印证语言系统的某些特征。文艺学研究文学文体,则是从文学使用语言进行言语交际方面研究文体,或者说是研究文学话语的文体,目的是为了揭示文学文体的审美特性。文艺学对文学文体的研究当然可以借鉴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但其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是与语言学的文体研究截然不同的。文艺学的文学文体研究最终要落实到对文学话语的形态特性、语用特性及其作为一种文体的审美特性的研究,也就是文学话语与科学话语、日常话语、实用话语等相比较而见出的特殊性。语言学也可能研究文学文体的审美特性,但这种研究最终要归结为一般语言学理论。就是说,这两种研究虽然研究的对象是交叉重叠的,但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服从于不同的学科使命,一种是把文学话语研究放到文学研究中,一种则把文学话语研究归之为语言学研究。在进行文学文体研究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是需要首先加以分辨和区别的。
我们知道,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一直是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普遍关注的论题,因而有关文学文体的研究在整个文艺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韦勒克认为,文体分析“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3](P.193)是否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文学作品的特质,诚然可以存疑,但文学文体研究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则应该是毋庸置疑。
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多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对文学的内部研究、特别是对文学文体的研究重视不足。须知,文艺学研究无论如何是不能缺少文体分析这一重要环节的。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如果我们不能从文体方面认清它的特质,也就不能真正地认清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为正是它的文体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外部世界系统中的地位和功用,所以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理应与内部研究、特别是与文体学研究结合起来。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本体论理论的引入与流行,我国文艺学在文体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文体分析日益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但是,我国文艺学的文体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发展阶段,要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有待时日。正如韦勒克所说:“如果没有一般语言学的全面的基础训练,文体学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文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当时语言的一般用法相对照。”[3](P.189)因此,进一步发展我国文艺学的文体研究,关键在于研究者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素养、分析技术的训练和提高。
正如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一般语言研究和文体分类研究一样,文艺学的文体研究也可划分为一般文学话语研究和文学话语的文体分类研究。一般文学话语研究主要是把文学话语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研究文学话语的与众不同的结构形态和语言运用的方法;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研究,主要是对文学文体进行分类研究,把文学文体区分为各种类型,分别研究它们各自的审美特性。这两种研究是互补耦合的,后一种研究应该作为前一种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显得益发重要。当代波兰学者米哈伊·格洛文斯基在谈及文类研究的重要性时说:“当研究人员把言语作为分析对象时,他们开始借助更广泛的文类来描述言语的文类情况,他们知道,言语有自己的参照范式,即使具体实现过程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个性化语言,并不因此而减少对这些范式的并不和谐的指令的服从。”[4](P.100)这段话告诉我们,文学话语的一般形态和语用特征应该是研究者从它的各种文体类型中概括出来的,而各种文体类型的特征又应该是研究者从具体作品的言语形式中概括出来的。这样一来,文体类型就成为联系一般文学话语与具体作品言语的中介环节。对这个中介环节的研究在整个文学话语研究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对具体现象的总结,又是对一般特质的印证。
四、如何划分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
探讨文学话语的文体类型,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文学话语的文体进行分类。正如前面讲到的,一般话语的文体分类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文学话语的文体分类当然也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例如,我们可以按照概括范围的大小将文学文体依次划分为个人文体、流派文体、时代文体,直至民族文体。正如韦勒克说的:“假如我们能够描述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我们也就无疑能描述一组作品和一个文学类别的文体风格、哥特式小说、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玄学派诗歌,我们也能够分析像十七世纪散文中的巴罗克风格的文体种类。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总括一个时代或一个文学运动的风格。”[3](P.199)当然,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总括一个民族的文体风格。从个人文体风格到民族文体风格,概括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最终将形成一个民族的文体风格学。这种研究对于辨识和鉴别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乃至一个民族的文体风格特点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按照审美范畴的不同来区分文学文体。上文说过,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具有审美性,但这种审美性又体现为不同的风格类型,如优美的、壮美的、悲剧性的、喜剧性的、写实的、浪漫的、幽默的、讽刺的、怪诞的、惊悚的等等,据此可以相应地区分出优美的文体、壮美的文体、幽默的文体、怪诞的文体等等。对具有各种不同审美风格的文体进行分类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学话语的各种审美风格的特点,而且还可以丰富和充实我们对文学话语的一般审美特性的认识。
更为常见的文学文体的分类研究,是依照文学体裁的不同而划分的。文学体裁是指文学文本的不同样式和格式。这种样式和格式既可体现为文本的形式特征,也可以体现为文本的内容特征。例如,中国古代习惯上把文学文本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有韵之文谓之韵文,无韵之文谓之散文,这就是从文学文本的形式方面区分的。而西方古代则主要是从文本内容划分体裁的,把文学文本区分为抒情的、叙事的、戏剧的三大类。其实戏剧作品也是叙事的(有抒情因素,但不占主要地位),若将其归之于叙事类,也是两大类。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戏剧一直较为发达,戏剧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早已形成了一些独具的特点和创作模式,因而在体裁划分上也将之单列为一类了。无论中国的“二分法”还是西方的“三分法”,都是传统的文学体裁分类法,显然都不适合近代以后文学写作的新变化、新发展了。近代以后较为流行的体裁分类方法,采取了一种综合的分类标准,既顾及文本的内容,又顾及文本的形式,这就是著名的“四分法”,即把文学体裁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这种“四分法”与“二分法”、“三分法”相比,更有包容性和理论阐释的优势。但随着当代电子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崭新的文学样式,原有的“四分法”显得越来越不适用,又有了“五分法”、“六分法”甚至“七分法”的体裁分类。总之,以体裁划分文学文体类型,不仅受制于采用的分类标准,更多地还取决于社会历史及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
以上我们阐述了三种对文学文体分类的方法,一是按概括范围划分,二是按审美风格划分,三是按文本体裁划分。对文学话语之文体类型的研究来说,这三种分类方法都很重要,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中,按概括范围的分类,主要是从创作主体的独特性着眼的;按审美风格的分类,主要是从接受主体的感受着眼的;按文本体裁的分类,主要是从作品文本的语言格式着眼的。这三种分类视角正好构成“互补”,分别从三个方面透视文学文体的类型,共同担负了文学话语文体类型研究的总体任务。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以“新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文体类型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文本体裁的研究上,甚至将文体类型的研究等同于文本体裁研究,从而排斥了基于“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等方面的研究,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其理论上的片面性主要体现为:将文学本体归结为文学文本,从而未能认识到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际中的话语活动,文学文本不过是整个文学话语中的一种形态而已。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西方文体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从以文本体裁为主导的研究转向了以“审美感受”为主导的研究,产生了所谓“认知文体学”的新学说。[5]这种新学说是对“文本中心主义”的纠偏和补充,的确值得我们在研究文学文体类型时予以借鉴和汲取。
尽管我们不能将文学文体类型的研究简单地归结为文本体裁的研究,但文本体裁的研究仍然是文学文体类型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是由文本语言在整个文学话语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首先,文本语言虽然不是文学话语的全部、只是它的诸种形态之一,但文本语言又是联系文学话语其他形态的中介。若没有这个中介,文学话语的其他形态,诸如作者言语、读者言语、评论言语之间就不可能发生联结。显而易见,文学话语的任何一种形态必须通过文本语言这个中介才能与其他形态相互关联。其次,文本语言虽然不是文学话语的“本体”、“中心”,但它显然是文学话语赖以构建的“基础”。若没有文本语言,也就无所谓作者言语、读者言语、评论言语,当然也就无所谓文学话语的存在了。再次,作为文本语言不同格式的文本体裁,自然也就成为文学文体类型研究的逻辑起点。正是从这里开始,才能构筑起文学文体类型理论的大厦。即如米哈伊·格洛文斯基所说:“体裁变成了文学语言的原型……分析这些原型有助于提炼出真正或从内在角度把文学语言与其他言语类型区别的因素。……分析也可以揭示任何言语类型所共有的本质的东西。”[4](P.101)其意思是说,要把文本体裁作为文学话语文体类型的“原型”加以研究,通过对各个“原型”特征的研究而上升到对文学话语文体类型的一般认识。因此,当我们致力于文学文体类型研究时,则不得不特别重视文本体裁的研究。但为了克服“文本中心主义”的片面性,除了将文本体裁研究与作者言语、读者言语、评论言语的研究结合起来,还要注意科学地理解文本体裁的规范与变异的关系问题。
五、文本体裁的规范及其变异
我们知道,“体裁”这一概念除了标记某一类文本的语言特征,还含有为这类文本确立体式和范型的意思。体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文本的规约,有了这种规约,无论是作者的写作还是读者的接受就有了共同遵守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交际活动将无法进行。因为这种活动是一种需要众人参与的活动,凡是需要众人参与的活动都需要制定游戏规则。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文学写作活动又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活动,它不仅不排斥个体的创造性,而且还要以这种个体创造性为动力,才能不断推动自身的进步。在体裁的使用上,创作主体也不是绝对服从体裁的常规惯例,而是一有机会就试图突破这些已有的常规惯例,竭力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文本体裁的规范与变异的关系问题。
总括地说,文本体裁的规范和变异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即规范必然导致变异,而变异又可以转化为规范。何谓规范?规范是由约定和习惯造成的行为规则和范式。譬如写小说,大家都这样写,并且认为就应该这样写才是小说,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写小说的规范,随后就建立了小说这种体裁。小说的体裁一旦形成,对每一个写小说的人就成为一种客观的规定和约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种规定和约束,以便写出来的东西像一篇大家认可的小说。但是,由于每个写小说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种独特个性在实际的创作中虽受到已有体裁范式的约束,但不可能完全被压制,总要或多或少地有所表露。这种表露有时可能是不自觉的,但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势必会导致对体裁规范的某种偏离。这时,所写的小说就不全像已有的小说,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就是体裁的变异。如果这种变异比较突出,引人注目,并被许多人仿效,就有可能变成新的体裁规范,并被补充到原有的规范体系中去。这样变异又转化为规范了。例如,“意识流”小说的写法,一开始只是小说体裁的一种变异,但后来这样写的人多了,才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小说规范。总而言之,规范和变异的对立并不绝对,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并随着范围和时间的变化而互转,因而不能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
当然,在范围和时间一定的情况下,对体裁规范与变异的界限区分还是确定的,不可相互混淆。规范毕竟是对变异的约束,而变异毕竟是对规范的冲犯,两者在体裁形成及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由于规范的存在和作用,任何体裁都有较为恒定的一面,都有一套被多数人认可的、较为通行的规则系统。作为一种文本体裁样式,如果失去了一套较为稳定的规范系统,自然就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其能否持续下去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同样,由于变异的存在和作用,任何文本体裁都有其变动不居的一面。变异在突破了原有规范的同时往往又建立了新的规范,从而推动体裁处于不断的运动和流变之中。从历时态的角度研究体裁的流变,应该是文学史的学术任务;而从共时态的角度研究体裁较为稳定的规范体系,则显然属于文学话语文体类型的研究范围。当然,所谓体裁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研究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历时中有共时,共时中也有历时,这两种研究应该相互参照和互为依托。故而,我们所主张的共时态研究是以承认体裁的历时态变化为前提的,我们要从体裁的不断流变中发现某些不变的因素,进而予以阐发和论证,以便确立体裁规范相对稳定的一面。因为在我们看来,某种体裁的变化不论多么剧烈,总是包含着一些相对稳定、不变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存在对这一体裁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企图彻底推翻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必将使体裁区分陷入全面的混乱状态,而这种全面混乱状态的出现,正是某一体裁系统面临解体的先兆。因此,文本体裁的共时态研究不仅不反对体裁创新,反而会成为正常体裁创新的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保证适当的体裁创新不致脱离原有的轨道而陷入混乱。
韦勒克曾把文学体裁类型的研究区分为“古典的”和“现代的”两种。他认为,“古典理论是规则性的和命令性的”,“古典主义理论不但相信类型与类型之间有性质上和光彩上的区别,而且相信它们必须各自独立,不得相混”;而“现代的类型理论明显地是说明性的。它并不限定可能有的文学种类的数目,也不给作者们规定规则。它假定传统的种类可以被‘混合’起来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种类(例如悲喜剧)。它认为类型可以在‘纯粹’的基础上构成,也可在包容或‘丰富’的基础上构成,既可以用缩减也可以用扩大的方法构成”。[3](PP.266-268)从古典理论到现代理论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文学文本在言语操作上越来越倾向于无定性和随意性,越来越倾向于违反既定格式和求新变异。如诗歌创作中的超现实主义派、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和新小说、戏剧创作中的荒诞派等,即是这种倾向的突出代表。这种倾向有其彻底反传统、反规范的过激的一面,但其表现的强烈创新意识和可贵的文体实验精神是不应轻易加以全面否定的。
按照韦勒克的这种“古典”和“现代”划分,我们的文本体裁研究首先是认同现代理论的,我们将摈弃“命令性”的研究原则,而坚持一种“说明性”的研究原则。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从已有的文本体裁出发,总结各类体裁的语用特征,并以这些特征为核心,据此概括出各种体裁的较为稳定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又否认这些规范体系是永恒不变的、牢不可破的。各种文本体裁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的规范不断地被打破,新的规范不断地建立,且各种体裁之间总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之中的,它们之间的分界也并非绝对泾渭分明。因而,我们所概括的各种体裁的规范只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这些规范可以作为一种约定、一种建议或者一种参照而提供给文学交际的主体,但不可以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法规和条令强加给文学交际的主体。这些规范可以作为一种体裁创新所依托的“平台”而对其构成一定的制约,但不可以作为体裁创新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而对其构成一种阻压。这就是说,我们的文本体裁研究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讲规范,不讲创新;另一种是只讲创新,不讲规范。这两种倾向体现在创作中就是“墨守成规”和“随意翻新”,也就是韦勒克说的,“文学作品给予人的快乐中混合有新奇的感觉和熟知的感觉”,“整个作品都是熟识的和旧的样式的重复,那是令人厌烦的,但是那种彻头彻尾是新奇形式的作品会使人难以理解,实际上是不可理解的”。[3](P.268)让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文本体裁研究的原则是:在重视体裁规范的前提下支持一切体裁创新的尝试,但也不能为了支持一切体裁创新而放弃体裁的规范。
[1]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黄叔琳等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 萧绎:《金楼子·立言》,郁沆等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4] 米哈伊·格洛文斯基:《文学体裁》, 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5] 刘国辉:《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与认知》,《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
SomeTheoreticalIssuesintheStylisticStudyofLiteraryDiscourse
WANG Wen-cheng
(Centre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Aesthetic Studies, Jinan 250100, China)
Produced in literary communications, literary discourse is mainly manifested through literary texts, which embody various types in styles and forms. The pursuit to be aesthetic over pragmatic is the standard that distinguishes the literary types from the non-literary. Accordingly, the study of literary stylistic types is the study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literary texts. Meanwhile, it is a priority to clarify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ory, namely the target and approaches of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of categorization and the variations of types.
Literary discourse; literary style; stylistic type
山 宁)
2017-10-09
王汶成,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艺传播学的研究。
H052
A
1674-2338(2017)06-0082-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