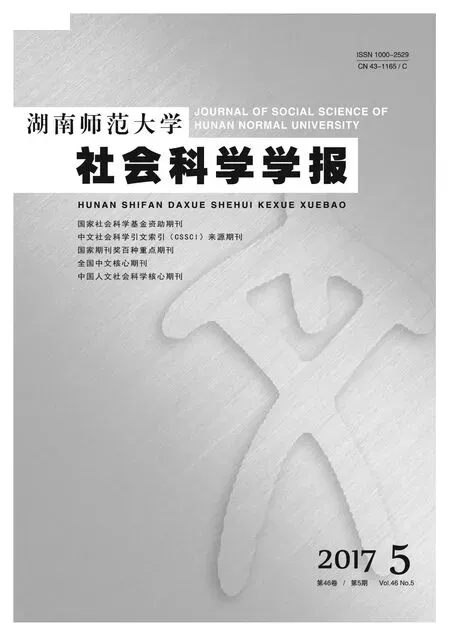论福泽谕吉的公德观及其现代启示
于建东
论福泽谕吉的公德观及其现代启示
于建东
福泽谕吉吸收与改造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论、传统儒学的天理观与日本传统伦理文化的思想资源,以其独具特色的“天赋人权”理论为本体论基础,以平等观为价值基础建构的公德观,主要从政治道德与社会公德两个维度展开。福泽谕吉的公德观不仅推动了日本明治时期公共道德的近现代化,而且对于我国的公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福泽谕吉;公德;天赋人权;政治道德;社会公德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伦理学家。梁启超认为“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是“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1]。福泽谕吉的公德与启蒙思想深深影响着日本文明的近代化进程,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因此,研究福泽谕吉的公德观,探索其公德观的本体论基础、价值论基础与基本内容,吸取其中的积极因素助推当前我国的公德建设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福泽谕吉公德观的理论目的
福泽谕吉高度重视公德对于国民摆脱陈规陋习的束缚、培育爱国精神、实现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其公德观具有明确的理论目的。
1.革除封建儒学的弊病
福泽谕吉从“智”“德”一体的角度阐释其启蒙思想,认为文明就是一个社会与个体智德共同进步的状态,“智”与“德”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表现为衣食富足而使人的身体安乐,而内在的文明表现为品质高贵而使人的道德高尚。福泽谕吉认为外在的文明易取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因而仅仅从可见的外在文明向西方学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以智德为表征的内在文明。在此基础上福泽谕吉把道德分为私德与公德,认为传统日本社会“认定的道德,是专指个人的私德而言的”[2],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仅仅依靠私德就难以应付,由此必须把人们的私人道德发展到公共道德。“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显著,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2]但是长期以来德川幕府推行的日本封建儒学意识形态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因此为了使日本社会摆脱“半野蛮半开化”的蒙昧与迷信状态,培养新型公民,提升国民的公德水平,必须移风易俗,对封建儒学的弊病展开全面清算。
福泽谕吉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智的开化,仍然不能冷静地审视封建儒学的弊病,还试图以内在的、无形的道德施于外在的、有形的政治力图谋求公共秩序的建构,“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就好似“在陆地行舟”,“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2]。而且日本之所以不能“真正开放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我深信这完全是汉学教育之过”[3]。在福泽谕吉看来,封建儒学是“远离实际不切合日常需要的”[4]的虚学,它把人分为智愚上下,并以纲常礼教美化为万世不易的天性,其实质是为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张目。这种儒学只能培养出来“臣民”而不是“公民”,他们只懂汉儒腐论而不懂买卖营生,导致家业衰败,他们对上阿谀谄媚,服从等级尊卑,对下颐指气使,欺软怕硬,这种风气只能塑造国民的奴性与扭曲的人性,造成国民公共精神的缺失。为此福泽谕吉排除障碍,大力倡导变革人心,希望日本的青年人认清封建儒学的弊病而汲取西洋文明,这“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3]。
2.实现社会文明
福泽谕吉的公德观极力主张革除封建儒学的弊病,其目的就在于对日本社会公德不振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为汲取和实现西洋文明开辟道路。福泽谕吉认为,今日日本的文明还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文明,它只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4]。“日本社会从上古以来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因素,并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2]。对于日本社会来说,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又受到专制的压迫。对于掌权的人来说,一旦他们身在政府手握权力往往就陶醉于其中,忘乎所以而恣意妄为,在人民的面前作威作福,进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传统日本的所谓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把君主的尊贵视为天理,为了便于统治使人民畏惧,还要把君主、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被设定为上下、主从的关系。然而统治者的道德堕落迟早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被统治者。“一个玩弄虚假欺诈的政府必然会使社会流行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伪善习气。如果一个政府是高压和专横的,它就会使整个国家谨小慎微、了无生机、相互猜忌和奴性十足。”[5]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必然缺失公共理性,人人被人欺负,又人人欺负别人,他们只知畏惧权威,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公共事务全部掌控在政府的手中,人民放弃了个人的权利,只剩下卑躬屈膝,日本国民“生活在权利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2],这与维护自己权利的先进的西洋文明相比形成鲜明对照。
3.实现国家独立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和公德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近代日本的国家独立。福泽谕吉认为:“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2]日本应该坚决汲取先进的西洋文明,改变传统社会政府与人民对立的状况,重新阐释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性,这样才能凝聚国民的精神,形成政治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新秩序。如何实现日本的独立呢?福泽谕吉认为首要的前提是实现个人的独立,使人民具有独立的思想,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前提与基础。福泽谕吉说:“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奴隶性,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3]。个人在物质、精神上的独立是国家、民族独立的基础,因为“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4],在一个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被统治者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一定是漠不关心的。不仅如此,“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4]。更有甚者,福泽谕吉认为,“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作坏事”,“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4]。因此福泽谕吉大力倡导培养日本国民的独立精神,以充分发挥国民的智德去保卫国体,实现国家独立。
二、福泽谕吉公德观的内容
公德,又称公共道德,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品质的总和。福泽谕吉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公德观的层次,但却是自觉地从政治道德与社会公德两个基本维度展开论述的,形成了其公德观的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天赋人权:福泽谕吉公德观的本体论基础
福泽谕吉接受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思想,并利用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与传统儒学的“天道”、“天理”观对它们进行了转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其公德思想提供了本体论基础。17—18世纪流行于西方的自然法理论认为: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宇宙是受自然法统治的;造物主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生而平等;国家和政府是出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根据人们达成的契约而产生。福泽谕吉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4],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其天赋人权的思想。与西方不同,福泽谕吉用传统儒学的“天理”观念代替了西方自然法中的造物主和人类理性的位置。在福泽谕吉看来,上帝和天理都内在于自然中,但是上帝是超自然的自立的实体,而天理则始终内在于自然而不超越自然,人的自然是没有必要与天理对抗的,因此福泽谕吉把西方启蒙学者所说的“上帝”或“造物主”直接译为“天”,把人性和权利的根源诉诸于天理,以宋明理学的“天理”保障其自然权利的权威。在这里,天理成为宇宙与人所共同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方面它是先验地以天为根源的,“天者理也”[6],因此成为万事万物的终极根源,即“所以然之故”,另一方面,它是内在于人的超越者,指示着人的应然存在状态,由此成为万事万物的普遍法则,即“所当然之则”。程朱理学的这一中国式自然法指涉自然之理与事物之理,完全是按照天理的内在性,即天理平等地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而具有超越的普遍性。但是由于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福泽谕吉的公主要是领域之公,不具有普遍超越性。“日本的公和私本身,是公开与隐蔽、对外与对内、官事或官人对私事或私人的关系,或者到了近代以后,是国家、社会、全体对个人、个体的关系等,没有任何伦理性。”[7]日本文化中的天之公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天之公,它们没有更高层次的原理性、道义性、普遍性的意思。天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超越性存在,因此,普遍存在的天理不会平等地具体存在于所有人那里,事物之理只限于社会规范方面。因此,作为事物之理的公德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充当了维系公共秩序的客观的规范。在福泽谕吉看来,在国家之外不存在普遍的、绝对公平的天地之公道,指望那种所有藩(国)必须遵守的天地之公道,是迂阔之甚!这就为福泽谕吉的政治公共道德最终蜕变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埋下了伏笔。
2.平等:福泽谕吉公德观的价值基础
福泽谕吉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形上学根据,将传统儒学以性善论与“人皆可以成圣”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平等观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平等观,为其公德观奠定了价值基础。传统儒学强调的是人在天性与德性上的相同性的平等,宋明理学的“天理”、“天命之性”更以自然之理的形式彰显了仁义礼智之性在世界万物之中平等的、普遍的存在。那么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呢?朱熹借助于“气质之性”来论证这种不平等的合理性。朱熹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8]朱熹将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视为天命所致,其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这种专制主义视民众为奴隶,民众也自视为奴隶,是不会有自觉的爱国心和人人关心公共事务的公德心的。福泽谕吉则把万物本源的天理确立为平等的终极依据,将平等仅限于基本权利、机会和人格的平等,合理地阐释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从而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平等转化为权利平等,使得日本近代社会从权利出发形成公共秩序成为可能。在福泽谕吉看来,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是基本权利上的平等,与身份的差异无关,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因而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由于“日本人思维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以自己所属的封闭性的社会组织为中心,而无视普遍性事物”[9],所以与西方具有独立意识、自成一体的权利平等观不同,福泽谕吉的平等观在保证基本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凸显了个体对参与其中的共同体的义务,强调了个体独立对于国家独立的重要价值。“小我”的权利和共同体中相互关联的他人联结起来,使得福泽谕吉的平等观虽然打破了传统社会一人垂直施与之下众人被“平等”对待这一等级平等的秩序,但是仍然具有领域内平等的特征,而且把共同体、国家的价值置于个体之上,成为构建其公共规则的价值基础。
3.政治道德:福泽谕吉公德观的理论指向
政治道德体现在公民与国家、政府这一政治公共生活的核心和国家权力的代表的关系上。从其天赋人权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出发,福泽谕吉继承与发展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阐述了其关于公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力图把人民从神权政府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福泽谕吉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4]人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是由于人数众多不能人人执政,由此政府根据人民订立的契约而成立,“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设立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政府所受人民的委托所办之事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共事务,“由此可见,所谓政府,就是承受了人民的委托,遵行约法,使全国人民,无分贵贱上下,都能行使其权利,并须做到法制正确、奖惩严明和大公无私”[4]。福泽谕吉主张一方面通过共同协商建立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充分体现公共规则的公平与正义。
另一方面,福泽谕吉认为“凡属一国的人民,均须尊重国家法律”[4]。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论一致,福泽谕吉认为,政府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行使其职权,既然政府及其法律是全体国民平等权利的体现,那么国民服从政府也就不单纯是服从政府制定的法律,也是在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哪怕感到国家、政府制定的法律尚不完备,也不能肆意破坏。否则,这样会导致“养成轻蔑国法的习惯,助长一般人民不诚实的风气,不遵守应当遵守的法律,终于酿成罪行”[4]。倘若政府施行暴政,人民卑躬屈膝屈从暴政固然不可取,但是用实力对抗政府也不是上策。在福泽谕吉看来,正确的做法是人民应当“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4]。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大写的个体与个体的联合建构公共秩序的方式不同,福泽谕吉的个体不是分散的、独立的个体,而是存在于共同体中的个体。对共同体生活的重视使得福泽谕吉舍弃了西方社会契约论中平等的相互性,在政治道德中凸显了国家、政府等政治共同体的地位,而加强了对国民的约束性。
4.社会公德:福泽谕吉公德思想的理论旨趣
与政治道德的纵向交往关系不同,社会公德主要涉及公民之间的横向交往关系,是全体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应遵循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意识与规则。卢梭曾说:“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10]福泽谕吉从其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出发建构其社会公德。他认为,基于平等、契约基础上的公民的自愿交往,会由于对处于同等地位的他人权利的尊重,厘定出权利的边界和个体自律的范围,“本分就意味着基于天理,顺乎人情,不妨害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4],形成遵守社会公共生活的普遍规则。福泽谕吉教导国民“不可忘记人与人平等的原则。我既不愿他人损害我的权利,我也不可损害他人的权利”[4],这一原则既是社会公德的大义,又要靠国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福泽谕吉还力求在国家主导社会公共秩序的传统模式外发挥社会公德在建构社会公共秩序中的作用。福泽谕吉认为,社会公德水平的提升也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一定要有先进者和向人民示范的人”[4]。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在公共道德形成过程中的自主性。
三、福泽谕吉公德观的现代启示
福泽谕吉公德观的提出,不仅适应了日本社会近现代化的需要,推动了日本明治时期国民价值观的转化,而且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德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
1.研究福泽谕吉的公德观,有助于确立现代公德观的权利基础
在日本近代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中,福泽谕吉的公德观虽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强调国家共同体的价值,但却充分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在政治、社会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由此确立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在权利基础上的统一。由“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设立保障权利的最终的形而上学依据,否定了以公灭私的传统公德观,有力推动了日本公德观的现代化。在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较早接受了天赋人权的理论。康有为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11]梁启超则指出在中国专制社会的条件下“人人天赋之权”常常被侵夺而不自知。但是在这里国家、团体的自由仍然被赋予价值上的优越性,压倒个体的自由,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仍然得到认可。梁启超说:“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灭。”[1]孙中山也说:“个人不可太多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是大家牺牲自由。”[12]国家依然具有强烈的相对于个人权利的压倒性的绝对价值地位。而严复与孙中山则直接拒斥了“天赋人权”理论,他们认为“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12],“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13]。虽然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都是在政治权利的层面上理解的,但是他们所说的人人只是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不具有独立个体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西方的自由与平等可以带来人民的解放与发展,但是他们不理解西方的自由与平等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不理解个人权利之于公共生活和公共道德的基础性作用。孙中山说:“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人民来争来交到他们。”[14]因此在近代中国,平等虽然已经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已经取得了其自身的意义,但是由于其缺乏本体论维度,实质上没有真正实现其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化,建立其相对独立的绝对性。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只能用国家道德、意识形态代替政治道德、社会公德,恢复到传统社会通过“道德革命”实现新民,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福泽谕吉对权利的突显,使福泽谕吉的公德观避免了传统儒学公德思想的缺陷,使传统社会以个体对他人的义务为基础的道德平等观转化为现代社会个人对他人的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平等观,有助于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共同点所涉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点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近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性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5]这就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在现代社会,权利是对主体自由平等价值的确认,从而为人们的政治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共同的规则框架。不仅如此,福泽谕吉的天赋人权拥有自然法的本体论基础。相对于康德从人的内在理性中找寻人自由、平等根据的逻辑思路,福泽谕吉承自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然状态的假设还是由外在的自然法和自然状态保障下的外在的自由和平等,但却为个体权利确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和范围。“只有当生命个体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免于强制的生活空间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自由的。”[16]
2.研究福泽谕吉的公德观,有助于革除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弊病
福泽谕吉的基本权利虽然继承了洛克消极自由的传统,但是它设定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他是不受他人侵犯的‘自由人’,在这个范围内他将自己作为‘自由’的主体人来意识”[17]。拥有同样自由平等权利的主体一方面会要求国家、政府尊重与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会要求彼此的尊重,成为彼此行使权利的限制与界限,形成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和秩序。而传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以至于中国人习惯上把社会生活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部分,一部分是陌生人社会,另一部分是熟人社会。“一方面是对陌生人——‘一般他者’的坑骗、假冒、行贿、收买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对有‘私人关系’者的特许、‘睁一眼闭一眼’,偏护甚至合谋侵害他人等等。”[18]这种差序格局对公共生活秩序和社会普遍规则的破坏都是灾难性的。
在福泽谕吉看来,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机构,国家和政府是所有公民协商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强调社会成员对公共规则的普遍遵守,国家与社会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要求个体承担其责任,履行其义务。“由于权利是需要人们彼此相互承认的,所以权利必定是有边界的,这就设定了我们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这一边界,从而也设定了人们相应的相互义务。”[19]只有自由平等的个体才能形成现代契约社会普遍遵守的公共规则,也只有拥有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人,才能自觉承担起责任与义务。福泽谕吉说:“我们做人的道理,就在于不妨害他人的权利,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只要“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从旁议论其是非的理由”[4]。福泽谕吉对个体权利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远离被给定的政治、社会和道德,抵挡传统社会对个体任意强加的、单向度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差序人格的产生。但是福泽谕吉强调个体权利,并不意味着对义务的忽视,他融合了传统儒学重视他人、义务的思想,把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福泽谕吉说:“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4]福泽谕吉公德观对义务的重视,又防止了权利沦为个体之私的庇护所,避免了以私灭共的公德观的弊病。
结 语
福泽谕吉的公德观一方面拖着“崇公抑私”的国家、政府至上的这一传统文化的尾巴,另一方面又有过分夸大社会公德的作用之嫌。福泽谕吉看到了社会公德所具有的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功能,因此极力主张借助于智慧的作用拓展公德发挥作用的领域。福泽谕吉认为社会公德对社会精神面貌的影响与私德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他说:“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就真正实现了太平盛世,到那时,君臣卑贱早已被遗忘,政府成为真正的管理机构,社会上违约背信之人与盗贼已经消失殆尽,家庭之内彬彬有礼之风盛行,“全世界的人民恰如被礼让的风气所抱拥,又如同沐浴在道德的海洋”[2]。尚且不说智慧是否真正能够起到化私为公的作用,其对社会公德作用的泛化,又陷入了传统的道德万能论。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576,5026-5027.
[2]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京:商务印书馆,1959:74,112,53,153,151,186,111-112.
[3]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M].马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9,170,246.
[4]福泽谕吉.劝学篇[M].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47,57,14,16,18,1,6,9,12,39,38,36,42,4,38,22,45,15.
[5]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M].蒋庆,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284.
[6]程颐,程颢.二程集(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2.
[7]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M].郑静,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9-10.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
[9]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M].林太,马小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98.
[10]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
[11]康有为.大同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52.
[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21,725.
[13]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
[1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721.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
[16]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0.
[17]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申政武,渠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3.
[18]廖申白,孙春晨.伦理新视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5.
[19]詹世友.论权利及其道德基础[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1):1-12.
On Fukuzawa Yoshi’s View of Public morality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YU Jiandong
Fukuzawa Yoshi absorbed and reformed the natural law theories of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s,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Justice Concept and traditional Japanese ethical culture thought resources.His view of public morality was constructed on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unique theory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basis of equal view as value basis,mainly expanded from the political morality and social morality of the two dimensions.Fukuzawa Yoshi’s concept of public morality not on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morality in Meiji period of Japan,but als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morality in China.
Fukuzawa Yoshi;public morality;natural human rights;political morality;social morality
(责任编校:文 涵)
于建东,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河南新乡 453007)
10.19503/j.cnki.1000-2529.2017.05.010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私和谐的传统路径与现代建构”(2015BZX019);河南师范大学国家级项目培育基金“公私和谐的传统路径与现代建构”(2016PY32);河南师范大学博士启动课题资助项目(QD14214);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研课题“马克思的公私权思想研究”(SKL201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