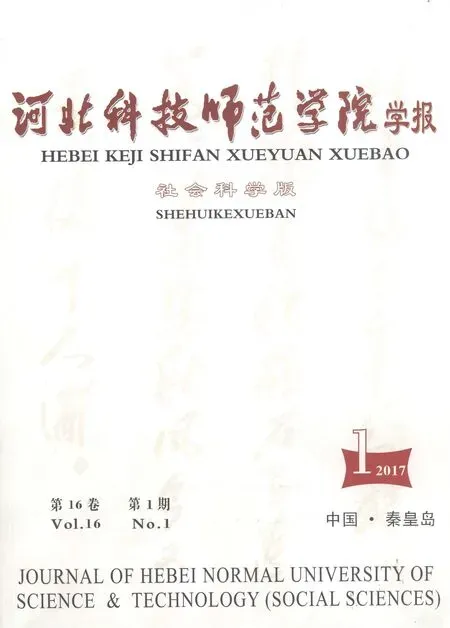从“现实主义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
王宝迪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从“现实主义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
王宝迪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学界倾向于把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界定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现象,论文从语言循环发展观与现代性发展进程的角度分析了“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在本质上的相通,认为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是人类踏上“回归”途程的关键一步。
“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语言循环;现代性;主客体
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将“反传统”“非理性”界定为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突破,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发展思潮。笔者从语言循环发展观和现代性发展进程角度,运用马丁·海德格尔、瓦尔特·本雅明和诺斯洛普·弗莱的相关理论分析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在本质上相通,即它们都是人类理性发展催生出的产物,都企图用理性来把握一切,现代主义文学对“非理性”的大肆表现也是人类要求更高标准地运用理性来把握非理性的结果。从这种人类理性的极致发展中,人类将自身奴役在人为制造的主客体对立关系中,并且在不断遭遇“惊颤”体验的同时,呼唤着本己向源头处的回归。
一
“在人群和喧嚣中随世沉浮,到处是不可共忧的、荣华的奴仆,这才是孤独!”——拜伦
作为文学流派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先后在文坛取得绝对优势并发挥影响至今。启蒙,人类发展史中的一次脱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发出了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声音,宣扬“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的宗旨,将“文明”“进步”塑造成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行为的绝对目标与根本准则。与此同时,现代性伴随着人类意识层面上的“脱魅”,最终表现为与中世纪“神学社会”形态相对的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世俗社会”形态,这一形态“本质上是宗教的控制与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应的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的过程”[1]。伴随着这种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人类将理性与主体性的权威发挥到极致,于是在把上帝拉下神坛之后,重又将“理性”推向世俗社会的至高处。“我思故我在”,从神性的牢笼中逃脱,人又坠入理性所禁锢的牢笼。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对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异同比较从现代主义文学登场之日起就开始并延续至今。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哲学观,对比逐层深入且有理有据。然而,本质上讲,“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对应“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潮吗?
大部分的文学史教材习惯性地对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行逐条分析,“反传统、非理性”也早已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在反复强调中为我们所接受。文学发展的历史固然有求新求变的特性,“反传统”自然也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任何一个在后的文学思潮所具有的特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创作中也有对人的潜意识、对人的内在情感等被“现代主义文学”大肆表现的非理性内容的书写,如英国早期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就认为,“只有反映人性或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才算得上真正有价值的真实”[2],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与其同时代作家的突出不同就是他的作品更加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更是使他将现实主义描写的“触角”伸向了心理过程的形态和规律,从而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内容,同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文学史对他在文学创作流派划归上的不确定就能认识到,单单从“非理性”层面区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及受其影响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所存在的局限性。结合具体文学创作分析,也不难理解这一局限。
法国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德·巴尔扎克并不认同“现实主义文学”的镜像摹仿反映说,他认为,视现实主义创作就是“照镜子”式地摹仿历史这一认知是对“镜子说”的误解。因为在他看来,这面镜子是“一面无以名之的镜子,整个宇宙就按照他的想象反映在镜子中”[3]4。所以,在巴尔扎克的小说王国《人间喜剧》中,构建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这三大体系,一一对应着呈现在表层的结果、浅层的原因以及在背后其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这三个层面,这样的结合才使得巴尔扎克成功地运用这面“无以名之的镜子”将《人间喜剧》中的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在这里对于现实的细致观察同样包括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刻画;一贯被文学史视为开现代主义文学先河的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主张“小说应当科学化”,倡导“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认为小说写作应当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实事求是,这种“零度写作”“科学剖析”的态度,足以说明福楼拜力图精准把握其笔下人物的外在及内心全部活动的决心,显示了他在描写真实细微的心理活动方面的极高造诣的短篇小说《一颗简单的心》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传神刻画,对于心理描写上所使用的多样手法,如内心独白、梦境描写、意识流等,都掺杂在他的现实主义写作之中。而被文学史确切界定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流派——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较之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著不同是在其背后有了命名确切的哲学学说的依托,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但在内容描述和表现形式上对比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只能说他们在对于“非理性”的理性把握方面具有层次和程度上的轻重之分,或者说没有区分,一如魔幻现实主义经典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认同西方学界将自己反映拉美大陆奇特生活现实的作品归之于现代主义文学之列,并不断说明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发生在拉美大陆上的现实。因此,将“非理性”视为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间的关键性差别有失合理。对于这一点,可以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相关学说再次获得肯定。
暂且视“现实主义文学”为我们一直以来所认定的那个“我”,一个为大多数“一般人”所自以为自成一体的理性主体。发展到“现代主义文学”,这个“我”被分解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真实的“我”被挤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认识中的那个“我”的最下一层,相对完整意义上的主体的“我”已然不在。从“我”到“本我”,对真实的追求贯穿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写作的始终。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文学中着力表现的非理性,作为这一阶段作家学者所认定的“真实”,作为这一阶段作家学者所引以为理据来与传统划清界限的基础,仍然置于人的理性认识之中。从这一层面上来讲,“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都高扬理性的大旗,只是在对“真实”的把握层面,“现代主义”比“现实主义”更深一步,将“非理性”的部分也归于人的理性层面并企图对其展开科学的剖析。因此,本质上说,“现代主义”只是人的理性发展的又一阶段,在根本的哲学认识上与“现实主义”并不存在本质差别。但是,从“我”到“本我”,抛去人在理性认识层面上的深入这点不谈,不能无视伴随着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在主体认识层面上从“我”到“本我”的变化,这就关涉到主客体关系发展上的极端状态,即主体也成为它所创造出来的客体的一个部分。作为人的“存在”本质层面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社会现实、文学、哲学等都对其进行了描写与表现。语言,这一存在的家园,更是从本质上揭示了导致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变化发展的根源之所在。
二
“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史蒂凡·格奥尔格
历来哲学家无不对语言格外关注,马丁·海德格尔、瓦尔特·本雅明、诺斯罗普·弗莱等都对语言问题进行过哲学层面上的探讨。语言,作为一个神学或哲学概念,代表着一种世界观。譬如海德格尔,只要谈及“存在”,他必谈论语言。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海德格尔讲到:“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4]在他看来,追问存在问题必须把存在带入言词。因为语言使存在者得以敞开,语言在完成对存在者的命名之后把存在者首次带入词语,并使存在者显现。本雅明的语言观与之相似,他通过对《旧约·创世纪》的独到阐释建构了他充满神学色彩的语言观,并奠定了他进行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础,揭示了人类自启蒙时代以来所推崇的“文明”“进步”观念的虚伪性,将“人类历史的自由落体”归因于语言的堕落,即语言从以上帝为灵感的命名语言堕落到为人所使用的符号语言这一过程,伴随着语言这一从原初的是(being)到有(having)的变化,主体缘起,客体出现,人类开始擅自命名世界。在此过程中主体一再使世界物化,主客的对立形成并逐步加深,这一点弗莱在其《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同样进行了阐释。
或许是都曾受到宗教神学的影响(海德格尔最早攻读神学而后转向哲学研究,本雅明从犹太教的卡巴拉阐释学中继承奥义,弗莱更是以从圣经研究角度从事文学批评而闻名),海德格尔、本雅明与弗莱的语言观或多或少都渗透着犹太教圣经的启示,具有一种神秘的回归传统的救赎意味,这一点在本雅明的语言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历史、传统,他们都有一种崇拜并渴望复归的情结,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根本就是从源头的脱落与堕落——“源头并不比由它发源的东西更‘细弱’,……一切‘源出’都是降格。”[5]381本雅明在《神学——政治断章》中将历史与弥赛亚时代比作是两个方向相反的箭头,弗莱则称无论社会条件怎样千差万别,每个人的头脑都还是原始的头脑。这类带有弥赛亚救赎情结的现代性批判侧面表现了自启蒙运动后,受制于理性奴役的哲学家们对现代人所置身其中的生存境况的关切与思考,而从“现实主义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这条现代性救赎之路上的“关键一步”,并与主客体关系的畸形发展这一因素密切相关。对于这一主客体关系畸形发展的表现,社会现实、文学艺术等都早有论述。20世纪以来,伴随着当代西方哲学范式的转变,人类越来越认识到不是人在利用语言,而是语言在利用人。作为“语言的孩子”,通过对语言的关照,我们更能从本质上领会主客体关系在其缘起和发展历史中所出现的偏误。
(一)“回归”的路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是现代世界中第一个认真思考语言发展的循环问题的人。在他看来,历史的循环发展中存在着三个时代:“神话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即贵族时代;以及凡人时代。而后又回到起点,循环不已。”[6]22在每一个时代都产生一种与它自己相适应的语言,这样就有了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弗莱将这三种文字表达类型称为寓意文体、神圣文体和通俗文体,并将与这三种文体相对应而形成的语言称为隐喻的语言、转喻的语言和描述的语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由于两者之间所固有的类型学关系,在间接记录着西方思想发展史与语言演变史的同时,还真实“言说”着其中的变与不变,为我们透过语言认识人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里就从对“A是B”这一带有命名色彩的语言表达的考察入手,分析语言自古而今在不同阶段所传达出不同时代的信息。
1.A as B——隐喻的语言
语言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隐喻的语言,即语言的隐喻阶段。考察《旧约》中的语言表达特征,当今的我们只能采用A as B这种形式来概括表达隐喻语言阶段语言表述中“A是B”的意思。对于这一语言隐喻阶段的语言形式,现代人接受起来时明显感觉到不妥:A是A,B是B,他们明明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怎么能够忽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而划等号呢?于是,如今就习惯性地认为这种难以理解的语言现象皆是由于“古人”运用了隐喻的结果。其实,这反映出的问题正是,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的语言,一旦在同一时空内共处时所必然产生的认知与理解冲突。用as的目的也是为努力将这一冲突化解到最小,因为对于语言第一阶段中的人来说,A和B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差别,而是都具有某种同源联系,当这一阶段的语言使用者认定某一个个体是他所属的群体中的一个个体时,他们就认定个体A就是(as)群体A。
用现在的语言“A as B”希求尽力描述出语言在第一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这一阶段主要是柏拉图以前的阶段,从荷马史诗、近东的圣经前文化以及大部分《旧约》圣经中都使用这一隐喻的语言。于是更能理解《出埃及记》中上帝给自己起的名字是“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that I am),这一“命名”在今人看来似乎根本就不能叫做“命名”,因为它在把握对象时根本就不具备有效性,就像一句出现在语言第三描述阶段的格言——“如果你说的是任何数量的事物,实际上就什么也没说”。然而在语言的第一隐喻阶段,这种命名却是完全成立的,并且展现了隐喻语言的原貌:在这种语言中,相对来说并不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明显分割,而是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由一个共同的力或能连接在一起。其中对于“命名”这一事件的认识,依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通过命名某种东西实现的是它被作为某一特定事物并得到领会,“命名不是贴标签,不是使用语词,而是唤入言词。命名呼唤。”[7]正是因为这一命名,才引出距离,正是凭借这一呼唤,才让被呼唤者保持其距离从而成为独立的物,于是事物在呼唤中到场。这也就是本雅明在绝望中希望实现的回归,即回到那个没有主客分别、天地浑然一体的前天堂时代。
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隐喻语言的特点,“知道一个神或神灵的名字可能使知者获得某种对它的支配能力;在为人或地点取名时使用双关语和通俗的词形变化又影响着被命名的人或物的性格。”[6]22因而,武士在战斗前的自夸是最让神仙厌烦的,与其说是厌烦不如说是畏惧,神仙们担心武士通过自夸从而真正获得相应的能力。这些现象都表明语言所具有的主客不分的特征,用本雅明的“单子”概念来理解的话,此时的天地万物都属于一个统一的单子,所以在命名的过程中,as是对一个统一单子内的各个事物的命名,各个事物之间不存在主客体的概念区分,而是具有一种共有的能,其中包蕴着统一而强大的隐喻力量。
2.A with B——转喻的语言
自柏拉图以来,我们进入了语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转喻阶段[6]23。这种语言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语言,而是一种“以文化为主的语言,一种在当时或后来被它所在的社会赋予了特殊权威的语言”[6]23。转喻的语言更加个性化,而且词汇变成了将内心的想法公开表达出来的形式,主体与客体变得越来越分别开了,头脑里的智力活动也逐渐与感情活动区别开来,一种独立于情感以外的理智也在朝着逻辑的方向发展。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分割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当这一语言阶段的人们面对前一阶段语言中难以理解的表达时进行“想当然”地能动诠释的能力。在这一转喻语言阶段,注释的大量使用或可表明人在其中的主体性参与和作用。这里选择使用“A with B”(这指的是那)来概括这一阶段语言使用的特征,是因为同今天的语言相比,这一阶段的语言还带有一定的隐喻痕迹,A和B之间的关系还不足以用“=”来直接对等,也不足以用“≠”来彻底切断。但是,这种表达已经更多地表现出人类动用理智来把握难以认识的对象的努力,“这指的是那”的表达方式已经将当时人们在理解上的难度从as (是……)降到了with(指的是……)。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带入,语言使用中逐渐发展出用个体指代群体的思想,王权也因此作为这一语言表达的产物不断在语言的命名中发挥作用。《新约》中耶稣受到审判,控告他的人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约翰福音》),或许就是对这一由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所带来的各方面之变化的说明。
与隐喻语言阶段的词语魔力相比,语言在其第二转喻阶段更加看重词语在顺序或线性排列之中所形成的理性化魔力,这种魔力来自于规范而不是某种合一的能。受这一语言特点的影响也就出现了中世纪人们对演绎推理的狂热,“梦想以启示为前提推演出所有的知识”[5]28。而这一推演出的知识在本雅明看来却是应当受到批判的“非真理意义上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是意识编织的产物,是意识的猎取物,这种知识意味着占有,因为它出自人们“在意识中建立起来的自圆其说。……如果知识有整一性,也是以个别洞见为基础,由这些个别洞见互相修正和在一定范围内的那种逻辑连贯,而并不具有直接关涉事物本质的内在整一”[8]29-30。这一由于人类理性与主体性逐渐觉醒以后人类为自己建构起来的虚伪性的知识,与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密切相关。从“A as B”到“A with B”,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语言已经经历了从“生命之树”到“知识之树”的蜕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人的语言和人的法则,于是人的主体性诞生并发挥作用,人类与自然、与世界分裂开来。伴随着人类理性的进化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文明”进程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善恶两极为原型的二元对立世界的形成,打破了天人合一的本原状态,人类也开始在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中走向迷失。
3.A is A(A)——描述的语言
语言的第三阶段大约开始于16世纪,这一语言阶段是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某些倾向同时产生的,到了18世纪语言就具有了文化优势。在这一阶段,主体和客体已经完全分开,“从感觉的经验来说,主体把自己暴露在客观世界的冲击之中。”[5]30人类在这种认知习惯之下把语言作为主要是对客观自然的描述,以真实为模型、根据相似的原则,把通过词语所要获得的想象中的事物勾勒出来。语言结构的使用与所描述的客观对象很接近,并且在对“真实”的无限追求中渴求达到认识的最高程度。于是,“A is A”(A)这种客观、科学的表达备受推崇。这一阶段的语言在人们看来仅仅是一种工具,一套由人类所创制出来的符号。
从本雅明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的批驳中就能够认识到,语言发展到今所经历的“堕落”的彻底性。结构主义语言学似乎并不理解语言“堕落为符号”的说法,相反却在不经意间认可这一堕落的结果,因为他们无视语言发展的历程,他们认为语言符号原本就是任意性的,他们并不去思考语言是如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或者说“堕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后来者取得了阐释的绝对话语权的第三语言阶段里,尽管语言的任意性——这一索绪尔语言学的公理性基础,在本雅明看来本不是一个语言的客观、结构的事实,却还是通过“扶持”而建立起堕落语言的专断独裁,本雅明因此认为:“符号之间无休止的互相指涉并不是如同索绪尔及其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切语言的差异条件,而是语言原初的灾难。”[9]34于是,这一堕落同时引起发生在一切错误知识、异化、认识论上的二元论,使得一个深渊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横亘在人类社会中的主客体之间。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全面的征服随之而来。使造物受制于自己独断的统治并不仅仅是把自然简化为一个客体对象,同时也如同魔法师的徒弟一样,使自己受制于自己的法术的奴役、受制于那没有目的的手段机制的奴役。”[8]32这一奴役过程中的主客关系,并不简单地呈现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而是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主体与客体明显分离的意识——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态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却走得太远而开始进入了它的尽头。已不再可能将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分隔开来,因为观察者也得成为被观察的对象。”[5]32这就是说,“这种新生的奴仆辩证法关系转瞬即逝,对主子的奴役并不同时带来对奴隶的解放,人类似乎拖着造物走向下坡。”[8]32
文学发展史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就同时存在于这一语言阶段,而且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就是对这一主客关系“发展到尽头”的文学化反映。也就是说,到了“现代主义文学”阶段,在对“真实”的把握上人们还遵循着“A=A”的现实性原则,不同的是,变化已经深入到A的内部,新的奴役关系已经消无声息地侵入到并不敏感的主体内。如同弗洛伊德对“我”的分析,“现实主义文学”阶段里那个主体的“我”到了“现代主义文学”阶段,已经被理性地分解为“超我”“自我”和“本我”。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语境下,谈“我”,谈个人具有主体性,但在这个“我”的义项中同样具有被理性、被权威所压抑着的“超我”的存在,那么,真正主体意义上的“我”应该从何处寻得?如今的我们已经使得“无家可归成为一种世界命运”,迷失了自我,破坏了语言,制造出“言词破碎处,无物存在”的生存困境。身处困境却不自知的我们将要走向何处?在为理性所奴役着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下一步的走向关涉着的不仅仅是文学,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程。
(二)关键一步:“A=A,A=A1+A2+…,A1≠A2≠…”
通过对上述语言循环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梳理,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中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进行了定位,它们都受到理性的操控,搭乘着现代性发展的顺风车顺势发展,将人类对“真”的追求发挥到极致,也将二元论的认识方式应用到极致,使得当今时代的主体更加难以把握自己的存在。根本上讲,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真正实践了主客关系由彼此截然对立到彼此奴役的转变。譬如英语中的“主体”(subject)一词,原意指的是对客观进行观察的人。除此之外,这个词还具有政治意义,指从属于所在社会当局或统治者的个人,将“主体”一词的这两个义项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可惜的是,而今的我们在想当然地陶醉在对这一虚幻“主体”的强调中时,却从不曾主动地去思考“主体”的第二层含义,这种语言上的“暴政”归因于而今统治者对这一堕落语言所具有的独裁功能的有效利用。虽然在当今社会,作为自己“主人”的个体已经对超凡的领袖、独裁者之类产生了本能性的抵触,但作为利用语言或者说是被语言利用着的孩子,人类却难逃语言在其发展历程中由于王权意识的残留而锻造出的更为细密、微观的牢笼。就像今天的我们经常无意识地把国家当作个体来对待一样,我们在新闻话语中最常接触这类语言表达,它给我们带来这种认识:世界舞台中的奥巴马就是美国,同样,普京也就是俄罗斯。原以为人类已经克服了专制与独裁,然而进入语言与思维的内部,却发现王权意识的残留根本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清除,它们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重又植入到人类的无意识中,将我们推向因“一步错”而致“步步错”的发展泥潭当中。
这就是从语言循环发展观和弗洛伊德理论的角度对造成文学由“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发展的原因的揭示。两种文学类型间的相同点,有如它们同处于语言循环发展中的第三阶段,都是语言描述阶段的产物,他们在本质上同源等。它们的相似性从语言层面上讲就是它们都要求语言能够达到精确表达意义的最高程度。这一阶段的命名者也象征性地站在与每一个个体平等的高度,用大家所一致推崇的理性、科学态度去命名一切,于是出现了“A=A”“B=B”的言语表达方式。“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都是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对“真实”的把握让这一语言阶段中的人们急于命名、急于划等号,通过这种命名与划等号的过程来树立他们期望确立的权威,又进一步采用将这些概念纳入知识体系的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其实这种知识不过是人类在意识层面上精心建构起来的新的一套自圆其说而已,难称真理。而造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差异的根本原因,导致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阶段发展的关键就掩藏在“A=A”这一表达中的等号(=)之下所发生着的新一轮的命名行为,本质上讲也就是语言学层面上对主客关系的新一轮操纵。人们都认可“A=A”,但是却鲜少有人去思考在这一A的内部所悄然发生着的变化。A的义项在数量上可以增多,有“A1”“A2”“A3”……而在它们内部各个义项间的关系上,或者是的确具有词源学意义上的关联,或者根本就只是已经取得绝对优势的掌权者所精心设置的逻辑陷阱。当人们偶然发现问题并进行质疑时,掌权者们又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字(法)典上就是这么规定的”,于是基于人们自古以来就被培养出的对知识、字(法)典的绝对尊崇,这一问题就这样在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根源处”得以“解决”。这样,难得产生质疑的人们再一次将问题消解在为人所精心设计的骗局中,而这一过程继续深化着主客体之间的奴役。这种奴役笼罩在我们身边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朝夕共处的语言更是难逃魔掌。然而,也正是因为语言在我们身边的无所不在,同时也让我们在这场新型奴役关系中“在劫难逃”。这种压迫在文学由“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转变中也有直观体现,从本雅明在现代性救赎方式上的悖论式转向中同样能够体会到这种主客关系畸形发展的严重性。
本雅明的现代性救赎方式是复仇[10],即通过“爆破”的方式复仇。本雅明自己明确表示“建构的前提是拆毁”,这也就意味着他首先要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历史观进行一番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先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文化和思维定势,以摧枯拉朽来铺设救赎之路”[9]30,本雅明选择的方式是“爆破”,即拆解历史被物化和神化的虚假连续性和史诗性,把本原作为一个单子从这种空洞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这种“爆破”就是本雅明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提到“爆破”就不得不联想到本雅明的“灵韵”,就像提到本雅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不得不提及他在现代性救赎方式上的转向。从前期的语言批判到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本雅明研究重点的转向因其表现出来的悖论性而为研究者所不解。实质上,本雅明并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相反他认为理念决定物质现象,而且在他看来,人与物的本真存在方式是“精神”,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去甚远。他之所以放弃他在现代性批判前期所采用的意识形态上的启迪方式,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机械复制时代,面对工具理性对人的大幅度物化,这一启迪方式在对抗现代性异化方面已经收效甚微,主客体的关系仍在难以遏制地恶化,所以为了早日实现人类向本原状态的回归,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借鉴了其中偏重实践的一面,重塑自己的现代性批判方式,以期能够唤起大众的觉醒。也就是说,前期的本雅明致力于使人们恢复本原时期的那种“灵韵”状态,采用对“灵韵”的强调与呼唤去启发大众。然而面对主客体的彼此奴役已经使主客分离都难以实现的困境,这种意识上的启发只能使本雅明所致力于实现的没有客体,只有主体,主体都是一种共同的“反射的媒介”。借助这种自我反射,它们产生自我认识,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使我们认识它们的道(Word),沦为本雅明所分析过的克利画作中的那个“天使”——被现代性发展的大风所推送,被动地飞向他所背对着的未来。于是,本雅明在绝望的谷底寻求革命与突破,“巴黎拱廊街计划”的实施就是他现代性批判方式发生转向的标志。
不难从这一悖论式的转向中认识到本雅明对主客体之间这种彼此奴役状态的绝望,然而在本雅明辞世20多年以后,当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统治似乎已经把社会推向单一向度的发展轨道时,赫伯特·马尔库塞正是从本雅明式的绝望中看到希望所在,在《单向度的人》的结束语中,马尔库塞总结到:“批判理论既不提供希望,也不展示成功,而是始终如一的否定。因为它要始终忠实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已经和正在为大拒绝贡献终生的人们。在法西斯主义初露端倪的时代,本雅明就写道:‘正因为那些不抱有任何希望的人,才有希望存在’。”[11]因而,在本雅明看似悖论式的现代性救赎思想的背后,体现着一种绝望的希望,一种悲观的革命,这种悲观不是被动,不是奴役,而是对行动、对革命的呼唤。而呼唤的原因,也就是促使本雅明产生这一现代性批判方式转向的原因,则与主客体关系上的恶化密不可分。这样,对于文学上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发展关系也就能够从语言与哲学层面上进行本质性的认识与把握。
三
“言词如此破碎,正是真正回步踏上思之途程。”——海德格尔
从语言学与哲学的角度,我们认识了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原因所在,剖析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其中,“不变”揭示了原因,“变”则实践着人类在救赎之路上的关键,这也是本雅明以一种“约书亚的姿态”,为走向完善的人类生存状态而摇旗呐喊的驱动力之一。因为在本雅明看来,“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但是“必须在炸药包爆炸之前切断燃烧的导线”,从而得以实现对现代性畸形发展的救赎,实现对人类生存本原状态的回归。弗莱同样指出,“从荷马时代至我们自己现在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走完了一个巨大的语言循环。在荷马时代,词语使人联想到事物,而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则是事物呼唤词语。而且我们就要开始另一轮循环了,因为我们现在似乎又一次面对一个主体与客体都共有的能,它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隐喻来加以文字表达。”[5]32就这样,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现实主义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无论知或不知,我们都已经走在“回归”的路上,而且本雅明用以激发人们在现代性发展的陷阱中觉醒的“爆破”,也因为现代社会对“灵韵”的大幅度破坏而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更多“震颤”制造出更多“顿悟式的畏”,引导我们去思考本真,渴望回归。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现代性救赎的紧要关头,那么,之后呢?
弗莱认为现在的我们又一次面对主体与客体所共有的能,但这个能与人类生存的本原状态下词语之间所产生的能存在根本不同。就像海德格尔将最初的语言看作是本真的诗,将今天的日常言谈看作是被遗忘了的因而是精华尽损的诗一样,在“本真的诗”与“精华尽损的诗”之间,精髓已经改变。在本雅明那里,堕落后的语言取得了“主体性的胜利和对物的独断统治”,与堕落前的语言并不传达什么意思、它们只是传达自身的状态已经相去太远。现代性的批判者都意识到现代性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已经迈向了趋于回归、等待救赎的关键之处,但之后的路到底要怎么走才能在根本上规避再次跌入类似于上帝崇拜、理性崇拜的牢笼?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中或许能够得到启发。
海德格尔崇拜本原,他把西方哲学史视为从希腊源头的降格与堕落,他认为西方思想史不但不是进步史,相反它简直就是一部退化史,因此他认为只有到源头处才能克服西方精神的根本态势,这就是说:把它源始的真理指引到它本己的界限中从而使它重新得以树立。通过考察西方思想史,他发现正是主观主义导致了主客体的划分与畸形变异,而主观主义的根子则深埋在往昔。于是追本溯源,海德格尔提出“存在的遗忘”,这种存在状态已经“从存在本身剥离而交给存在者,交给上帝,交给理性”。这一从“存在”到“存在者”的人之在世状态的转变皆与主观主义的发展有关,因此需要克服主观主义,找回人的本真存在。然而“克服主观主义,不是要转向客观主义,而是要深入到比主客观分野更原始的境界”[12],用“此在”(das Dasein)这一说法来代替“人”,是海德格尔展开这种努力的第一步。因为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使得存在的原始性不再显耀。而此在,即在此存在,是存在通过人展开的场所和情景,“此在就是它……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在就是它所能成为的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有所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5]170。
海德格尔的历史角色就是克服主观主义,他通过克服主观主义而进入一种新型的“思”,“思”存在本身,并将存在视为一种不断敞开着的疏明,这一此在只经验生命中可经验的,思考可思考的,通过这种方式,把一切都各自带回到其本己所是的存在状态中。他借鉴并改造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发展了自己的关于人的现象学。在他的现象学中始终遏制主观主义思想的浸入,从本真处入手,根本性地抵制由于主体性的规约而给人类发展所带来的灾难,从“现实主义文学”到“现代主义文学”,就体现着这一灾难在文学上所产生的效应。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正是他于言词破碎处引导大家踏上“在世存在”之途程,规避继续堕落之惯性而做的努力。
四
“唯当此在在,兹始予在。”——海德格尔
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人类费尽心力打破了神学禁锢的魔咒,却重又将自己推入理性崇拜的陷阱,而且越陷越深以致从中迷失。主观主义的发展、主客奴役的灾难、个体迷失却不自知,这些改变使人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存在着的人了,而这也恰恰带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赎契机。海德格尔启发我们,“人”这一名称从根本上就不应存在,有了人就有了物,有了人和物的具体对立也就有了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只有“此在”,只有将人和物都视作此在,才能实现每一个此在共同在世的状态。通过“思”,领悟“在”,把“在”保持在“在的疏明”之中,这样才能实现本雅明向本原状态的“回归”,才能领悟弗莱所讲的“新一轮的循环”,才能于语言破碎处借助“思”来回归,以一种本真的状态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
[1]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2]殷企平,朱安博.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18.
[3]巴尔扎克.驴皮记[M].郑永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4.
[4]马丁·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6.
[5]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樊振帼,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马丁·海德格尔.语言[M]//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990.
[8]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9]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语言和语言的种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0]汪民安,陈永国.尼采的幽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49.
[11]赫伯特·霍克海默.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16.
[12]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90.
(责任编辑:刘燕)
From Realistic Literature to Modernist Literature
Wang Baodi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 Shandong 264209,China)
The academic circles tend to define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Modernist literature as two distinct literary phenomena,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ame essence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Modernist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ity process.This paper held that the development from Realistic literature to Modernist literature shows the key step human walking on the way to return.
Realistic literature;Modernist literature;language circulation development;modernity;subject and object
I06
A
1672-7991(2017)01-0060-08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1.010
2016-12-15;
2017-02-25
王宝迪(1992-),女,山东省济南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