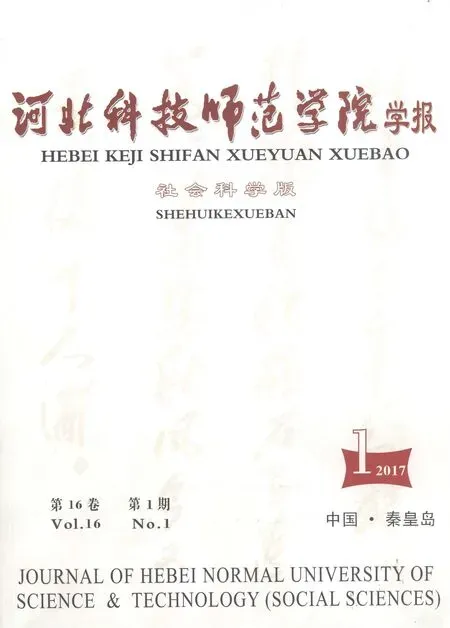论杜夫海纳的语言观
董惠芳
论杜夫海纳的语言观
董惠芳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杜夫海纳的语言观是对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回应。他主张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语言,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客体和工具,而是强调人与世界的平等,语言是人与世界的基础,世界向我们说。他还认为人与世界的根源在于造化自然,诗唤醒了造化自然的诗性状态,诗是人类的初始语言,诗使人类与世界回复到了最自然的状态,这正是艺术的意义。杜夫海纳的语言观依然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并贯穿着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杜夫海纳;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艺术;人与世界
作为现象学美学的集大成者,杜夫海纳的国际声誉主要来自他在美学领域的贡献。因此,无论国内外,研究者们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他的美学理论上。事实上,杜夫海纳的语言观也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夫海纳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持续体现在《语言与哲学》一书、论文集《美学与哲学》(三卷本)和专著《诗学》中。《语言与哲学》是杜夫海纳1959年秋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公开演讲,在此书中,他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哲学。在《美学与哲学》(三卷本)、《诗学》中,有关艺术与语言的思考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这样,哲学语言观和艺术语言观共同构成了杜夫海纳的语言观。
杜夫海纳的语言观是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大潮中诞生的,不仅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具有密切关联,而且也与现象学的语言观一脉相承。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杜夫海纳的语言观,一方面,可以厘清杜夫海纳语言观与其整个美学理论体系的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认识现象学语言观的演变,同时深化语言学大潮中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20世纪的语言学大潮。
一、杜夫海纳的哲学语言观
自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以来,语言已经成为一个哲学话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逻辑学和语言学的深入发展,为语言哲学的产生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杜夫海纳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是对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回应。他注意到语言学的进步、符号逻辑的发展,以及哲学反思都推动了这一转向。杜夫海纳将所有有关语言的哲学反思总结为两种趋向:一是朝向语言的本体论,一是朝向言语的现象学。在他看来,前一种趋向强调的是语言的力量,即通过语言揭示存在,显示意义,如海德格尔、谢林、黑格尔、赫拉克利特等人的研究。杜夫海纳本人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在《语言与哲学》一书中,他以“语言与语言学”“语言与逻辑”和“语言与形而上学”三个部分完成了他的言语现象学研究。杜夫海纳认为,言语的现象学将使我们返回到语言的形而上学领域。而且,现象学与本体论能完美地相符合。他还相信这一条道路会带领我们到达语言自身的源泉,最终循言语之迹返回诗,这也使他最终转向了艺术与语言关系的思考。
杜夫海纳首先审视的是语言学领域的语言研究,他最为关注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他虽然承认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制定的基础规则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他更意在指出索绪尔语言学的不足。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并把言语从属于语言,于是,语法学在地位上便优越于语义学。因为语义常常带有偶然性,而一种给定的语言却可以是一个确定的客体,它相对稳定,并独立于特定的环境,有字典和语法可依据。但在杜夫海纳看来,语言作为客体,关注的就不是它的内容与意义,而是它的物质基础,也不再关注它的独特之处与发音,或者它的语法顺序,而是仅仅寻求它们的共同之处。而且,把语言视作一个客体就是把它视作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它的各要素被法则支配构成了一个整体。
对上述问题杜夫海纳都很不满,他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思想中存在某些模糊之处:其一,支配各要素的法则模糊不明。其二,系统思想本身也存在模糊之处。而事实上,区别规则系统和要素系统的不是规则和要素,因为每一个系统都包括这两者。杜夫海纳又进一步质疑规则系统和要素系统:“规则是任意的,其总体性既不连续,也不彻底、饱满。相比较而言,一种给定的语言的各要素构成的领域却真是一个系统,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结构。”[1]24即对于语言学来说,规则系统其实是不存在的,而“结构”这个概念也是模糊的。根据杜夫海纳的理解,结构的概念一方面有生物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有数学的内涵。这样,结构实际上包括了两种不能同构的模型。
更重要的是,“结构”这个概念逐渐被构想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一点的影响尤为巨大。格雷马斯曾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模式所引发的影响进行了概括,他称之为“两轮光辉”:第一轮主要发生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领域,特点是根据某一学科的需要以通俗化的名义对语言学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结构进行扭曲和变形,甚至不惜抹去语言学中某些基本概念之间的根本对立。另一轮光辉是方法论上的,不过,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方法借用,而是一种从认识论角度所取的态度:若干模式、若干发现程序的移植,极大地丰富了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等人的思想[2]。无疑,索绪尔语言学的大肆扩张都是以某种抽象的结构和模式的应用为前提的,因此语言学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各种社会文化领域中被应用起来,杜夫海纳谴责“结构主义与控制论结盟。语言学加入了实证主义的时代”。杜夫海纳的批评揭示出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忽略生动的言语活动而奔向言语背后恒定不变的语言规则与结构。这一点既使语言学到处攻城略地,也导致它常常受到人们的指责。
运用结构理论,结构主义总是企图发现“科学的”“客观的”人文科学事实,在杜夫海纳看来,这是异常危险的:“结构分析处于危险之中,即屈服于用本体论的观点看待纯形式的诱惑。那么,这个理论掉进了它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必须注意不要在现实之上设计形式结构,也不要忘记物质结构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一旦一个人将此定义为一种无意识的逻各斯,而这种逻各斯形成了整个文化的特定的、逻辑的形式,那么,一个人不是正在创造一个只是人类学家自己的逻辑操作计划的客体吗?这正是一个人自称发现了他已经放在那里的物体。”[1]38这无疑是说,结构主义按照自身的逻辑提前预设了自己想要的结论。德里达的批评意见与杜夫海纳有相似之处,他说:“结构首先说的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工程,一种装配、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在特定地点建立起来的、可见的建筑。”[3]这就表明,结构主义试图达到的客观、科学的结果实则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杜夫海纳还非常严肃地批评了语言学领域中忽略语义的情况。他指出,受索绪尔的影响,结构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语言的现世维度。语义学通常是被结构语言学忽略的,因为结构主义处理的是符号,而非意义。意义被减少到了对声音的清晰理解,好像仅有的问题就是正确传送或登记信息,而不必说明或解码。而实际上,语言具有突出的多样性,这一点不仅影响语言,还有文化、宗教、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甚至家庭关系和社会制度。语言与社会制度总体性的联系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这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杜夫海纳重点分析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所开创的道路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许的,但这种方法必然带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当运用语言学精确分析语言的时候,文化必须服从于仅有的观测技巧,这一点尤其在考虑其总体性时表现得分外突出。因而,结构人类学的结论只能是总体文化的部分表达,它被迫遗失了部分更好的意义。
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见解相反,杜夫海纳特别强调意义对于语言的重要性。索绪尔批判语词中心论,主张代之以整体论的意义理论。而杜夫海纳认为语词中心论与意义的整体性并不冲突,甚或意义整体性以语词中心论为前提:“人们能从无中引出意义吗?不能。要给词以意义,单靠句子是不够的(神话对神话素、旋律对音符、影片对一组镜头、绘画对色彩也都是不够的)。句子要有意义,词必须先要有意义。”[4]149词与句子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互相依赖的,词语不仅与整个语言体系,而且还与它指向的事物本身是姻亲关系。语言之所以能使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交流得以实现,因为意义启用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杜夫海纳的言语现象学对于语言与逻辑的关系也予以重新阐释。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哲学问题归根结蒂是语言问题,因此,他们把对语言进行有效的逻辑分析以澄清误解当作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杜夫海纳发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论文》(Tractatus)中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逻辑创造逻辑语言,他曾一度认为逻辑的语言就是语言的逻辑,以后他才明白话语表现的是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随语言的运用而千变万化,同时也是令人困惑的。”[4]78他声称:“现象学将重新发现内在于语言的逻辑。但它将在人与世界的联系的更普遍的哲学中为此寻求辩护。正是在那样的联系中,语言找到它的根源;正是在同样的语境中,语言可以被自然地说出。”[1]39由此可知,语言的逻辑应该从人与世界的联系中去探寻,他的研究方向完全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
关于逻辑的阐释,杜夫海纳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源头,他说:“我们真的远离了逻辑的传统概念。……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制定的规则不是主观任意的选择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存在的本质。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那样的逻辑预设了语言与存在之间的不言而喻的协议:语言是真实的并且是真实的条件,因为它是存在的语言并且它的规范从存在出发。”[1]44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传统的逻辑概念认为语言与存在之间具有不言而喻的关系,但形式逻辑在后来逐渐成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逻辑在认识和强调言辞本身的客观逻辑结构上具有强有力的作用,杜夫海纳不能认同的正是这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语言分析逻辑。
杜夫海纳把语言看作人与世界关系的纽结,与语言相比,他更为关注活生生的言语现象,他说:“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意义的语言所有权,集中于人类制造的语言的使用——那就是说,集中于说话的人,集中于说的语言本身。”[1]70那么,为什么要重视“说的语言”呢?他这样解释:“经验是我们与世界第一重要的联系,这正如在感知中生活和用言语来命名。因为言语是与世界的最初始的结,这个世界与感知同在,并且不能脱离它。第一意识(承担逻辑的意识)是一种‘说’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逻辑语言植根于自然语言,正像是形式思想植根于直觉。现象学,被视为先验逻辑,邀请我们从被说的语言回到说的语言,正在说的语言,因为人们说,而且因为这个世界向人们说,这一点,反过来,因为人与世界真正的联盟甚至从诞生以来已经形成。”[1]67-68这说明杜夫海纳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正在被使用的言语,这样的言语中包含着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与感知,“说”的意识本身承担着说清楚的目的,内在地承担着逻辑的意识,这种极为平常的现象中恰恰蕴藏着逻辑的根源。像英美分析哲学家那样冷静客观地解释语言中的逻辑,杜夫海纳是完全不能赞同的。
杜夫海纳还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对语言展开了思考。与传统的把语言看作工具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语言与说话者是一体的,二者不可割裂。在《语言与哲学》一书中他反复表示如下意思:“当我说的时候,我就是我说的话;我与我的话变成一体。当然,正如我已经说的,说话把我放到了与我所说的一定距离处。但在我的意识与我的言语之间根本没有距离:我与我用的语言是一个整体。”[1]84语言不可证明同一于任何一种工具,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通过语言,人与他人、自己和世界得以交流,但人不是通过语言而存在,人与他的语言就是一个整体。海德格尔认为,人之说是无意义的,遮蔽了语言之说,与之不同,杜夫海纳却充分肯定了人之说。
不仅人之说是有意义的,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揭示的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因此,意识到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对自身的意识,“从一种生存状况到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怎么可能?依靠语言是可能的。正是语言引进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必不可少的距离。正是利用语言的调解,间隔(interval)被创造出来,在那里思想开始起作用。然而,我们将很快看到,调解是一个——同时分离与统一。假如语言在世界与我之间挖了一条沟,它也在上面架了一座桥。词语插入了事物与我之间。但仍然,词语没有恢复事物的实际呈现,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意义。”[1]73这就是说言语表达与思维具有同一性,这为杜夫海纳提出的“前意象”(preimage)奠定了必要的前提。
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基本关系,杜夫海纳并不承认世界变成了语言的对象,他强调的是世界在说,这是最为根本的。“自然语言既不是由智力组织也不是由情感推动。它表达的不是人的本质,而是造化自然本身。说,首要的是让世界为自己而说,就好像它通过诗为自己而说。”[1]97-98世界之说是通过“前意象”展开的。“在这种我们称作前意象的水平上,人类感知而不是看到。但在情感上已经总是有一种意向性:情感不是无可救药地疏远于它的主体性。人类感到的是打动他的东西,是向他说的东西。”[1]94-95“世界利用来宣称自己的语言已经呈现,同时还有情感。情感在话语(words)中表达自己的同时,它使自己在意象中更明确。我说前意象,因为世界的这些粗糙的意象没有描绘明显的可识别的对象。”[1]95由此可知,“前意象”是人类因被打动而模糊地感知到的那些关于世界的初步意象。“前意象”实则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原初联系,这种联系证明,在根源上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作为人与世界原始交流的装置,诗是语言的第一形式,因此,艺术与语言的关系必然上升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杜夫海纳的艺术语言观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巨大影响下,当巴尔特的符号学将艺术视为语言时,杜夫海纳对于艺术与语言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人们总是按照语言的特殊模型去给意义整体下定义。在符号学领域,“这特殊模型就是用来交流信息、也就是说交换意义的代码(code)。‘代码’和‘信息’,就是语言和话语(parolc)。”[4]74运用此种方法,符号学可以把各种意义整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巴尔特把研究对象甚至扩大到了服装、食品、汽车和家具。在这种背景下,艺术也被同一于语言。如果非要用代码与信息的系统来给艺术找一个位置的话,杜夫海纳认为在符号学的中央应该是语言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信息与代码互相依存,二者是平等的,人们能利用代码传递信息。在这个中心的两端分别存在着次语言学领域和超语言学领域。次语言学领域包括所有尚未具有意义的系统,有代码,但没有信息,意义被还原为消息。杜夫海纳认为艺术属于超语言学领域,并且是超语言学领域的最佳代表。在超语言学这个领域里,系统是超意义的,它们能传递信息却没有代码,或者说是这种情况:代码越不严格,信息越含糊不清,意义就主要是为了表现。根据这种划分,可以体会到,杜夫海纳并不认为艺术是语言学的正统对象,艺术可能也受语言学规则的支配,但却是超越语言的。所以,他的艺术语言观集中强调的是艺术对于语言的超越性。
杜夫海纳认为艺术与语言虽然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艺术不能等同于语言,艺术也并不适合符号学的研究。如果按照符号学的研究思路来看艺术,首要的是找到各种艺术中存在的“系统”,可是,各种艺术千差万别,到哪里才可以找到一个艺术的系统呢?如何把艺术当作整体给它下定义呢?“人们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寻找哪些词汇和语法是创造者所使用的,二是首先在被创造的作品中,也许也在作品的整体中去寻找能满足一个系统的东西来。”[4]81但是,艺术毕竟不可能像语言那样被划定范围。“语言是在言语的整体中表现的,它给每种言语规定出某种共同的东西,从而使这些言语构成一个同质的总体。而一定的艺术的作品整体却没有显示出一个系统所表现的性质。艺术是各单独创造者的结果,创造性的实践总是无政府状态的。”[4]82如果非要把艺术视为语言,这一思想应该要从以下两点去解释。其一,作品是设定某种代码的一种言语;其二,艺术家是通过作品说话的。这两点显然是回到了语言和话语的区分,或者代码与信息的区分。杜夫海纳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言上,他细致、深入地考察了音乐、绘画和电影的情况,逐一证实了自己的看法:艺术不能像其他社会人文现象那样,如人类学、叙事学等,被当作语言来进行代码与信息的二元对立的研究。
那么,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与语言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只有对于那些二流艺术家,艺术才仅仅是语言:“关于二流艺术家,关于一切没有天才的艺术家,应该说他们也遵循一种代码,这种代码不是他们的种族的代码,而是他们的时代的代码。对他们说来,艺术是一种语言,符号论说得有道理。这也就是为了什么符号论选择工业品或手工艺品作为研究对象而不选择真正艺术作品的原因。”[4]105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审美创造似乎没有语言。更正确地说,艺术确实含有代码,但这种代码既不是确定的也不是严格的,尤其是它只在审美实在的周围、在观众的经验和创作者的行为之内起作用。”[4]101因此,杜夫海纳着重从观众的经验和创作者的行为这两方面研究了艺术与语言的关系。
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来说,“语言的地位完全是奇特的:它是工具,又是非工具;它在我之中,又在我之外。”[4]104这正是艺术创造的特殊之处。因为艺术家的作品最需要的是独创性,他并非是在从事一种单纯的编码工作,虽然不同门类的艺术各有自己的一套程序与规则,但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并非是完全受制于这些程序与规则,杜夫海纳指出:“艺术不同于语言,更加普遍地说,艺术不同于真正的意义系统。总而言之,目的是为了表明语言学范畴是如何只能有保留地加以使用:它们与创造行为所不了解的或所忽视的代码有关。如果想要把它们运用于创造行为,那就必须指出这行为是如何超出这些范畴的。”[4]108显然,艺术创造更加愿意突破常规,发明句法,产生自己的语言,这也是艺术成为自身的重要手段。
对于观众的经验来说,艺术家想表达自己这一观念甚为流行,人们经常提出这个观念来证明“艺术是语言”的说法。作品确实会发出一种信息,那这种信息是什么性质?该如何来界定呢?针对这一问题,杜夫海纳认为:“不是艺术家在说话,而是他的作品在说话。甚至在说双重的话:它在揭示属于作者的某个世界的同时代表作者。艺术家的真实在他的作品之中。需要追寻的就是这种作品的真实。”[4]113我们知道,作品客观上会流露出艺术家本人的情感,他思考的东西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和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但首先要承认,艺术家通过作品传达的不是他个人的信息,不是自说自话,或者说,展现他自己不是他创作的目的。作品风格也不是作家刻意营造的。就好比说,某些程度地展现艺术家自己,是创作的副产品。
作品确实在说话,但它不是述说它的作者,杜夫海纳提出,是自然在借助艺术家说话:“自然为了说出自我求助于人,为了能被理解求助于文化。因而,艺术确实是言语,不过,在艺术领域是自然在说话,就像有时自然通过某些自然物说话一样。”[4]116这显然又回到了创作问题,但凡伟大的作品总是使人产生如有神助的感觉,诗中萌动着自然的请求。在《诗学》中,杜夫海纳进一步说,是自然唤起了诗性的状态和诗性的语言,“自然需要人,因为自然需要人来点亮她。而且应该说自然需要言语的人,而人类最初的话语就是诗。”[5]226
与海德格尔一样,在各种艺术中,杜夫海纳特别偏爱诗歌,他赋予了诗歌语言以特殊的使命,诗歌不是语言哲学,而是初始语言,“诗就是第一语言,一种人类回应自然的语言的语言,或者说一种使自然作为语言显现的一种语言。”[5]229诗歌语言不仅在人与世界中起着原始交流的作用,它的表现性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直接感知到人与世界的本然关联,这种关联证明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平等的。“语言是联系人与世界的滋养性的结,它也是人解放自己和确证自己愿望的手段。人能认识和掌握事物仅仅因为他能命名;他能命名仅仅因为事物向人揭示自己,因为‘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发明了语言并召唤人来说。这就是诗人知道的、他的诗歌说出的东西:诗提出了语言的问题并以它自己的方式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1]101这又体现了杜夫海纳不同于海德格尔语言观的地方,海德格尔把语言视为存在之家,把语言和存在结合在一起,从本体论的高度研究语言,杜夫海纳则把人与世界的根源归于造化自然,而语言是人与世界的联结点。
整体上看,对于艺术与语言的关系,杜夫海纳反对通过语言去理解艺术,而主张通过艺术去理解语言。他特别强调的是艺术的独特性、创造性与心灵的自由,虽然艺术与语言一样是一种表达活动,但艺术的表达在本质上绝对不同于语言,艺术的表现力唤醒的是人与世界的和谐感,唤醒的是造化自然的诗性的状态和诗性的语言,这是艺术与语言最大的不同。
综上所述,杜夫海纳主张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语言,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客体和工具,而是强调人与世界的平等,语言是人与世界的基础,世界向我们说。世界之说通过“前意象”而展开,“前意象”暗示了人与世界的本源和谐。人与世界的根源在于造化自然,诗唤醒了造化自然的诗性状态,诗是人类的初始语言,诗使人类与世界回复到了最自然的状态,这正是艺术的意义。与分析哲学重视语言与形式逻辑、语言与本体论等问题不同,杜夫海纳的语言观基本符合存在论现象学关注语言与思想、诗歌语言的传统。而杜夫海纳对结构主义等流派的批判,根源正在于杜夫海纳思维方式与索绪尔语言学思维方式的对立。那么,在语言问题上,杜夫海纳延续了他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确立的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总体上服务于他长久以来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探索。
[1]MIKEL DUFRENNE.Language and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Henry B.Veatch.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3.
[2]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M].吴泓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4.
[4]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孙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MIKEL DUFRENNE.Le Poétique[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3.
(责任编辑:刘燕)
本刊加入《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声明
为了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继续扩大学术交流的渠道,《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04年1月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其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编入该光盘版和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On Dufrenne’s View of Language
Dong Huif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Bohai University,Jinzhou Liaoning 121013,China)
Dufrenne’s language view is a response to the 20th century linguistic turn.He advocats the study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no longer regards language as the object and tool,but emphasizes the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He also believes that the root of man and the world lies in Nature,poetry has awakened the poetic state of Nature;Poetry is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human beings,and it brings the human and the world back to the most natural state,which is the meaning of art.Dufrenne’s linguistic view is still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and run through beyond subject-object duality of thinking.
Dufrenne;the linguistic turn;Saussure;arts;man and the world
B83-069
A
1672-7991(2017)01-0016-06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1.00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杜夫海纳美学思维方式研究”(13YJC720009);辽宁省社科联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杜夫海纳的语言观研究”(2015lslktziwx-05);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现象学‘诗之思’的嬗变研究”(W2015013)。
2016-12-20
董惠芳(1977-),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