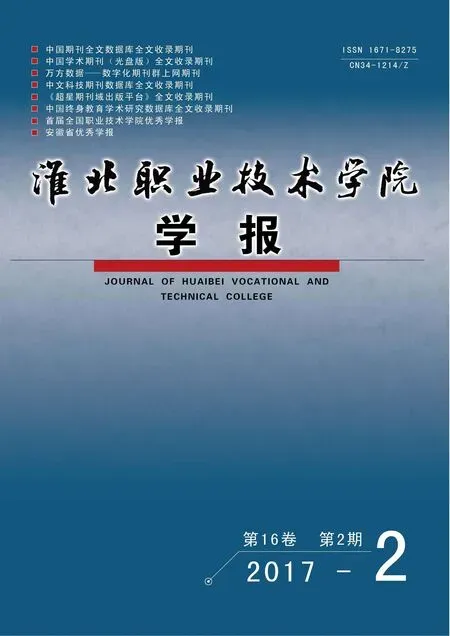《篆隶万象名义》特殊编撰体例例释
马小川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篆隶万象名义》特殊编撰体例例释
马小川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篆隶万象名义》因全用汉字写成,一直被视作与中国字书并无甚差别的汉文字书,学界对其利用亦建立在此先入观念上。然而,作为一本独立成形于日本中世的辞书,它自有独特的编写体例和原则,而不见于它书,也使其在内容上产生大量疑难费解之处,妨碍了对此书的正确、精准利用。在此即试论《篆隶万象名义》的若干特殊体例,举例说明,并解决了部分疑难问题。
《篆隶万象名义》;编撰;体例
关于《篆隶万象名义》(以下简称为“《名义》”)的论著,历来多注意于其所保存的丰富的中古文字、音韵、训诂资料,而对文本本身的探讨不多。尤其为学人所忽视的一点是,它虽自汉文字书原本《玉篇》脱胎而成,却全由日本人删截编撰,虽整体上与中国字书面貌相似,却带有不少异域书籍自有的特色。研究者如果不把握清楚其编撰体例、成书原则而贸然加以使用,很可能会因材料的错误定性而使结论成为空中楼阁。如吕浩的《篆隶万象名义校释》,虽完整校勘、录入了《名义》一书,利用方便,影响甚大,但仍存在种种舛错,这是由于其不明《名义》体例而造成的。本文将分别以举例方式,论述《名义》迥别于其它书的编撰体例。
一、带有和风特色
以《名义》为代表的日本古辞书,本是为方便日本人学习、查找汉字而撰成的。既成书于日本人之手,又经其传抄,近千年的辗转流布,虽同样使用汉字记录,却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和风痕迹,其中的一部分还不易察觉。此时必须谨慎处理材料。
如,《名义·目部》:“瞳,徒公反。目玉子。”[1]125
按,《宋本玉篇·目部》训作“目珠子也”。[2]85又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之一引原本《玉篇》作:“瞳者,目珠子也,即黑睛中小珠子也。”可知《玉篇》的“瞳”原即释作“目珠子”,再遍检中国经传注疏及各类字、韵书,均释之为“目玉子”,而“玉”也并无“圆珠”义。因此,我们推测以“目玉子”释“瞳”字或并非汉文训解,转求日语,才发现“玉”可读作たま(tama),义同“球、珠”,是最常见的基本词义,此条义项才找到合适解释,此处应是编撰者编写或传抄时为更符合日本习惯而所作的修改。
又如,《名义·车部》:“辈,怀概反。部也,类也。”[1]182
针对此条,吕浩《校释》曰:“《残卷》作‘博概反……野王案,辈犹部也。’”[4]295亦是认为反切下字为“怀”可疑。按,“辈”,《宋本玉篇·车部》音“布妹切”[2]337,《广韵·队韵》音“补妹切”[5]112,均声在帮母全清合口一等。其它韵、字书同此。而“怀”,《广韵·皆韵》音“户乖切”[5]26,声在匣母,全浊合口二等,与“辈”无任何声之联系,也无相通或历史演变痕迹。但在日语中,“辈”音读为ハイ(hai),正可与此处相对应。此或亦是经日本人改字处理而致。
上类情况仅见于日本古辞书,且数量很少,但仍能反映情况,即处理文献材料需谨慎考察背景信息,弄清源流。否则,若在撰写论文或编写中文字典时,贸然视“目玉子”为“瞳”的新义项,或以为“辈”历史上曾有过声在匣母之音读,都是不可取的。
二、注音字混于训语内
《名义》注音,兼用反切和直音。反切以“XX反”明确标示。直音却既不以“音X”表示,也并不一定紧连字头,而是以“X 、”的方式与义项并列,颇不易窥觉认读。
此条《校释》注曰:“舌未详”[4]112。其实,是因不明白《名义》编撰体例而未能正确认识此字,“舌”当是“”的直音法注音字。《名义·舌部》“舌”音“视列反”[1]46,与“”读音“上列反”近同。而《类聚名义抄·肉部·佛中》:“,音舌。”亦可为证。
此条《校释》无说明。其实,“的”排在“至也,善也”之后,却并非其义项,而是“”又音的直音字,需出校解释。《宋本玉篇·辵部》:“,丁狄切。至也。又都叫切。”[2]197“丁狄切”恰即音“的”。又,《广韵·啸韵》:“,苏弔切。至也。又音的。”[5]119可为旁证。
三、妄加误训
作为手抄本,《名义》基本保留了中古字形特点,俗体、异体、简体字形满篇皆是。两个正体字形有别、俗书却相似或相同的文字,有时会被误当成一同个字,义项也常随之混误,甚至原本《玉篇》所不载的义训也会在编写时被擅自加入。
如《名义·示部》:“祖,子鲁反。始也,转也,居也,上也,摇也,本也,解也,法也。”[1]101
按,“祖”无“解”义,此是将“祖”误认作“袒”字而窜入的误训。《说文解字·衣部》:“袒,衣缝解也。”[7]170《广雅·释诂一》:“袒,解也。”可知“解”正是“袒”的正训。 “祖”“袒”形似,俗书犹莫能辨,以致训语不确。
又,《名义·言部》:“謱,洛口反。不解也,重也,忌謱也。”[1]82
综上所述,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建筑工程主体结构质量检测非常重要,能够及时的发现建筑工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保证了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建筑工程领域,必须要加强对建筑结构质量检测方法的创新,加强检测方法的检测效率,从而保证对建筑工程结构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检测,保证建筑行业安全、稳定发展。
吕浩《校释》:“‘忌謱也’未詳。”[4]132按,“忌謱”本当作“忌讳(諱)”,本为“讳”字的训语,此处误加入了“謱”字下。《名义》“韋”字的下旁“飻”均俗写变作“女”,形与“婁”近同,使得“謱”“讳(諱)”也几乎形同,编写或传抄者未能分辨,从而产生了此疑难点。《名义》将“讳”字正训作“隐也,避也,忌也,溢也,忌讳。”[1]84又原本《玉篇·言部》:“讳,《周礼》:‘小史掌讼王忌讳。’”[9]282都确实出现了“忌讳”一词,证明此解释合理。
四、误截《玉篇》书证作义项
原本《玉篇》的编撰体例是先释义,后引经据典,《名义》有时不注意分别,将引证内容也误认作义项抄录,以致意义不明,令人生疑。
如《名义·口部》:“吷,休悦反。啜,饮也。有嗃。”[1]46
吕浩《校释》曰:“《说文》以‘吷’为‘啜’之或体。《名义》‘有嗃’义未详。”[4]76按,《庄子·杂篇·则阳》:“惠子曰:‘夫吹筦也,犹有嗃也;吹剑首者,吷而已矣。尧舜,人之所誉也;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譬犹一吷又如。”可知《名义》此处的“有嗃”应是作为书证的《庄子》内容之误截。
又如,《名义·目部》:“眭,下圭反。弘字,深目。”[1]36
吕浩《校释》曰:“‘弘字’未详,疑当作‘弘字反’。”[4]61按,《校释》误。“弘字”声、韵不可相拼,无法切出正字,非为“眭”的反切音注。查《说文新附·目部》:“眭,深目也。亦人姓。”[7]68《宋本玉篇》释为“人姓”和“目深恶貌”[2]86,可知“眭”亦指一种姓氏。西汉有姓眭名弘字孟者,《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眭弘字孟,鲁国藩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辩解,从嬴公受《春秋》。”则《名义》此处的“弘字”应是文献用例的错误截取所致。
五、义项层次不分
《名义》一字所收的多个义项常常不仅包括本字本义和引申义,还杂糅并列了其同源字、假借字、古今字的义训,造成了义项层次相混不清的问题。
如,《名义·心部》:“惟,役蔡反。思也,有也,为也,辞也,忧也,庆也,侯也,伊也,谌也,陈也。”[1]73
吕浩《校释》作:“‘侯也’未详。”[4]118按,“惟”与“维”字通,《尔雅·释诂下》:“伊、维,侯也。”应是《名义》此条出处。邢昺疏作:“皆发语辞,转互相训。《邶·谷风》云‘伊余来堲’、《大雅·大明》云‘维此文王’、《小雅·六月》云‘侯谁在矣’。”可知此处的“惟”训“侯”,亦是由于杂糅了其通假字“维”的义训而致。
再如,《名义·止部》:“歫,渠举反。至也,推挌也,自也。讵也,违也,止也。”[1]102
吕浩《校释》注曰:“‘自也’未详。”[4]138按,原本《玉篇·言部》:“讵,《字书》或歫字也。”[9]289《名义》亦以“讵”为“歫”字。而《国语·晋语六》:“讵非圣人,必偏而后可。”韦昭注:“讵,犹自也。”当即《名义》此条所本。此处“歫”训“自”,列入的正是其同源假借字“讵”的释义。
以上主要就带有和风特色、注音字混于训语内、妄加误训、误截《玉篇》书证作义项、义项层次不分等几方面,讨论总结《名义》的特殊体例, 或许因撰者汉文不够精深,又或许是因抄者草率,其中多是一般编写抄纂所不可采取的误例。当然,除以上所列举,类似的特殊用例在全书还大量存在着,也可算作《名义》一书的自身特色,还有必要继续加以分辨、总结、研究。
[1] 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 陈彭年.宋本玉篇[M].北京:中国书店,1983.
[3] 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141.
[4] 吕浩.篆隶万象名义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5] 陈彭年.宋本广韵[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6] 菅原是善.类聚名义抄[M].正宗敦夫,编订.东京:风间书房,1978:247.
[7]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8] 王念孙.广韵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4:28.
[9] 顾野王.续修四库全书·玉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894.
[1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53.
[12] 尔雅注疏[M].郭璞,注.邢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4-85.
[13] 国语[M].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7.
责任编辑:张彩云
2017-01-24
马小川(1991—),女,四川达州人,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语言学典籍整理与研究。
G256
A
1671-8275(2017)02-00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