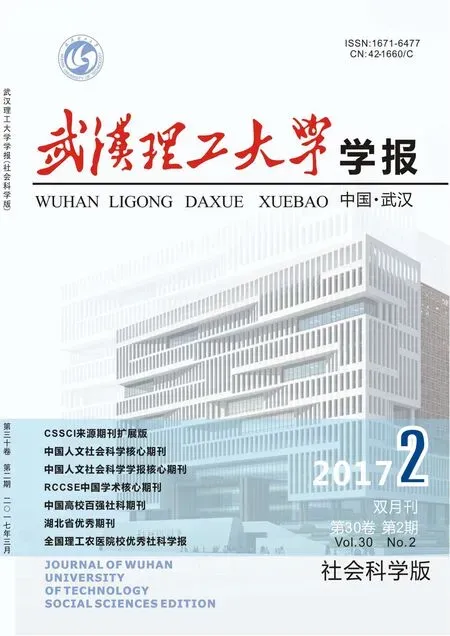田汉:从新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
方 舟(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田汉:从新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
方 舟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以1930年为界,田汉戏剧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剧作表现灵肉分裂的痛苦,以及对灵肉协调一致艺术理想的追求,其新浪漫主义艺术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交叉、渗透,是对西方与传统两方面文艺资源的借鉴、吸收。后期剧作积极介入时代、拥抱现实斗争,强烈的战斗性、饱满的政治热情、情节的传奇性构成革命浪漫主义戏剧的艺术重要特征。田汉两个时期戏剧创作的变化不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变化,而是从新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的变化,浪漫主义这一根本精神贯穿始终,没有改变。
田汉戏剧;新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
田汉前期剧作呈现出新浪漫主义的特质,对此已有多人予以论述。1930年,基于时代与个人的种种原因,田汉发表长篇宣言《我们的自己批判》,对此前10多年的思想、创作及活动予以检讨和清算,宣告向左转的志愿与决心,此后的创作呈现出别一种不同的风貌。据此有人认为“田汉的剧作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轨迹”[1],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本文通过梳理田汉的创作历程、解析代表剧作对这一约定俗成的看法提出反驳。
田汉说:“我看Neo-Romantic的剧曲从《沉钟》起,至今Rautendelin Heinrich的印象还是活泼泼的留着,同时一股神秘的活力也从那时起在我的内部生命的川内流动着。我于是以为我们做艺术家的,一方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间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一方面更当引人入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Artification),即把人生美化(Beautify),使人忘记现实生活的苦痛而入于一种陶醉法悦浑然一致之境,才算能尽其能事。比如《沉钟》本是描写一种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之冲突的悲剧,然而我看到末场了不觉得有甚么悲苦,却和Heinrich一样,我们的灵魂化入the land of ecstacy去了。世间尽有悲极而喜,喜极而悲的。可见悲喜诚如Chesterton所言,不过一物之两面。悲喜分的明白的便是Realism的精神。悲,喜,都使他变其本形成一种超悲喜的永劫的美境,这便是Neo-Romanticism的本领。”[2]51-52这就是田汉所理解的新浪漫主义,他还把新浪漫主义概括为“醒梦”,物欲横流、纷扰熙攘的尘世只是一场春梦,新浪漫主义者站在高处,以“醒梦”的目光超越尘世,把生命美化,抒写幻美人生,表现对彼岸未知、神秘的灵性世界的热烈追求:“所谓新罗曼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3]这对处于理想与现实、灵与肉分裂的矛盾痛苦中而又缺乏心灵皈依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田汉主张灵肉协调一致的自然、理想境界:“诸君要知道过重灵魂而轻蔑肉体的,莫不否定现实,认这个世界为万恶,我们只有遁出这个浊世,别寻所谓天国。既重灵魂又重肉体的,他便始终到底要肯定现实,觉得我们所能求的天国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却在现在。那怕这个世界无一毫价值,我们凭着努力可以使他有价值。那怕这个世界无一毫意义,我们凭着努力可以使他有意义。这就是希腊灵肉调和的思想的由来。”“我们‘老年的中国’因为灵肉不调和的缘故已经亡了。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一方要从灵中救肉,一方要从肉中救灵。惠特曼是灵人而赞美肉体的,主张灵肉调和的思想,所以要纪念他。——蔡孑民先生主张美育代宗教,就是希腊肉帝国精神之一部,因希腊精神是灵肉调和。”[4]
田汉的新浪漫主义剧作首先展现的便是人所遭受的灵肉分裂的痛苦和痛定思痛之后灵的张扬,以及对灵肉协调一致理想的追求。田汉说自己的处女作《梵峨璘与蔷薇》是“一篇鼓吹Democratic Art的Neo-Romantic的剧曲”[2]35,灵肉观念在这个剧作中同样得到充分表现。爱与美、恋情与艺术是灵的体现,生活保障、留学资金是物的追求、肉的需要。没有学费旅资,秦信芳的艺术只是圆不了的梦;没有生活保障,柳翠只能掩泪装欢,卖艺为生。要成全秦信芳的艺术之梦,柳翠只能牺牲爱情,与李简斋达成肉的结合。尽管柳对秦痴心依旧,但这种爱情却因灵肉分离而好梦成残。最后李简斋慷慨解囊成人之美,灵肉分离的悲剧变成好人相助的大团圆喜剧,这种情节安排体现出剧作家的美好理想。《灵光》为赈灾而写,目的是鼓舞人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动恻隐之心,出救难之力,剧末耶稣像头上的灵光不只是神示,更是灵与肉两方面自救与救人的精神,灵肉观念依然存在于这个剧作中。但是在这里,使民众灵肉得救的不再是身为富商的第三者,而是身体力行的自己,这种实现灵肉调和、心物同一途径的微妙变化,对于田汉思想、情感及人生道路的选择意味深长。《乡愁》中的家象征世俗的肉的生活,漂泊象征着精神的灵的追求,漂泊虽然辛苦,却因灵的追求而别有一种诗意、浪漫与感伤。把这种漂泊的诗意、浪漫与感伤发挥到极致的是抒情诗剧《南归》,流浪诗人一生奔波,命途多舛,然而无论到哪里都无法安置漂泊无定的心灵。当他南归发现给自己温暖慰藉的春姑娘已被母亲另许他人,不得不再次踏上艰辛而漫长的漂泊之旅:“我孤鸿似的鼓着残翼飞翔,想觅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痕将养。但人间哪有那种地方,哪有那种地方?我又要向遥远无边的旅途流浪。”在《咖啡店之一夜》中,白秋英深爱李乾卿却被无情抛弃,林泽奇因包办婚姻而与所爱的人永诀,两人同样遭受灵肉分裂的痛苦,因而互相安慰,重新振作。剧作家以此表达人在灵与肉、精神与物欲、理想与现实的相互矛盾及对抗中灵、精神、理想一方的张扬,这种矛盾对抗给人带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5]86。此外,田汉前期剧作还表达了主人公为维护灵的神圣所作的抗争及付出肉的牺牲:为了与表兄的真爱,莲姑直面家长的威权宁死不屈(《获虎之夜》);为了追求至纯的美与艺术,刘叔康(《苏州夜话》)遭受战乱兵祸、家破人亡而矢志不移,刘振声(《名优之死》)不惜以身殉道;为了维护真爱、艺术与灵性之光,白薇死而复生,生而又死(《湖上的悲剧》),诗人追随所爱的姑娘投身古潭(《古潭的声音》)。可见,灵肉冲突、重灵轻肉是田汉前期新浪漫主义剧作的基本主题。
田汉说:“新罗曼主义,是直接由旧罗曼主义的母胎产下来的。而他‘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3]从艺术表现上看,田汉前期剧作的新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交叉、渗透,是对西方与传统两方面文艺资源的借鉴、吸收、融合。
田汉富有浪漫色彩的奇思异想首先得益于西方文艺资源的启发。如在歌德《浮士德》影响下创作《灵光》(《灵光》初名《女浮士德》),读波特莱尔《悲壮的死》而创作《名优之死》,受日本芭蕉翁诗句“古潭蛙跃入,止水起清音”启发而创作《古潭的声音》,《生之意志》受柏格森和厨川白村哲学思想影响,视“生之意志”为“原始的神秘的‘生命之力’”[6]88。孤独、死亡、梦幻是现代派戏剧表现的重要内容,田汉前期剧作不能不受影响:孤独、感伤的旋律萦绕于《咖啡店之一夜》、《南归》等剧中;在《古潭的声音中》,古潭的诱惑就是死的诱惑,主人公投身古潭是对生存痛苦的反抗,也是对死的向往与探索;《灵光》中的顾梅俪在梦中看到故国民众的悲惨处境,为其归国救难提供心理发展逻辑。总之,田汉的新浪漫主义剧作从创作灵感、主题表达到艺术手法均深受西方现代派戏剧艺术影响,在写实的框架下融入梦幻、象征、变形、夸张等现代派手法,表达灵与肉、孤独与死亡等现代主题。
田汉的新浪漫主义剧作既吸取异域戏剧资源营养,又采撷传统戏曲艺术英华。田汉自小酷爱民间戏曲,帝王将相的家国情怀,忠奸斗争蕴含的惩恶扬善,神仙鬼怪寄寓的奇思幻想,才子佳人的抒情咏唱等在他幼小的心灵种下戏剧艺术的种子,为以后走上戏剧创作打下根基。[7]434-435浓烈的抒情性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特征,许多剧目并没有多少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主人公酣畅淋漓的抒情咏唱征服观众。田汉前期剧作继承了传统戏曲这一特征,不重视精确的客观叙事而重视强烈的主观抒情,不重视人生图景的真实描绘而重视优美诗意意境的营造,把抒情诗与戏剧巧妙结合,不以情节生动、结构谨严取胜,而以抒情的浓烈与语言的诗化动人,形成重抒情、重写意的艺术风貌。《获虎之夜》中黄大傻大段大段的抒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南归》以简化的情节、真挚的吟唱传达悲怆、悠长的诗意感伤,其他剧作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抒情性。情节的传奇性是传统戏曲的另一特征,甚至明清戏曲直接被称为传奇。田汉前期剧作也很注重传奇色彩,常借偶发事件使剧情突转,造成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艺术效果,富翁纳妾变成慷慨解囊的成人之美(《梵峨璘与蔷薇》),咖啡店内痴情女巧遇负心郎(《咖啡店之一夜》),暗枪猎虎打中的却是女儿的恋人(《获虎之夜》),这些情节都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性与富于诗意的戏剧情境紧密结合,从而形成独特、动人的戏剧艺术风格。
1930年,田汉发表近10万字宣言书《我们的自己批判》。他对自己领导下的南国艺术运动作出回顾与检讨,对自己的艺术道路尤其是戏剧主张与创作实践作出批判和否定,告别旧我,走向新我,投身左翼文艺阵营。这标志着田汉从思想、行动到艺术创作全方位地向左转,从此他的戏剧活动融入左翼戏剧运动,他成为左翼文艺阵营的领导人,而他的戏剧创作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①。
田汉向左转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社会革命思潮的激励;二是南国社内部矛盾分歧所致,一些左倾成员要求田汉转向,其中部分成员不满于田汉的“右倾”而离去,还有的则有别立门户的动向;三是与安娥的恋爱,田汉元配易漱瑜英年早逝,安娥是共产党员,参加南国社负有争取田汉的任务。[1]最根本的原因是田汉本人的左倾激进思想已有长期的酝酿、发展并体现在戏剧创作中:留日期间对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前期剧作表现出一定的抗争意识,随着思想、人生观的变化,这种抗争意识越来越强烈,其中包含自觉不自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以至出现集中表现民族、阶级的压迫与反抗的剧作如《午饭之前》、《黄花岗》、《孙中山之死》、《火之跳舞》、《一致》等。尽管现在看来这些作品艺术上乏善可陈,但对于考察田汉的思想与心路历程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认识到田汉前期思想和创作已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反抗、斗争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的向左转。
但是,能不能由此判定田汉戏剧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呢?不能。田汉创作的转向主要表现为从专注灵的世界到专注物的世界,从抒发心底的诗情到表现身外的现实,从追求较为抽象的灵肉调和到追求现实层面的艺术与时代的结合。但是田汉转向后的创作不但没有放弃浪漫主义,而且进一步深化浪漫主义,由新浪漫主义转向革命浪漫主义,他的作品在艺术与时代的结合中走向成熟,当然这其中有艰难的探索,有一度的徘徊,而且以某种程度的艺术牺牲为代价。
转向后的田汉在戏剧创作上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当他走出艺术象牙塔后,唯美精神和情感自我宣泄淡化,代之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表达、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他对现实的不满、抗争上升到为大众、为民族,为反抗阶级压迫、异族侵略而鼓与呼,强烈的现实战斗性是后期剧作的首要特征。《顾正红之死》、《洪水》、《姊妹》、《乱钟》、《扫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战友》等剧作积极配合现实斗争,语言铿锵有力,现实感很强,演出效果很好,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对人物性格缺乏深入开掘,常以表现革命者群像为主,传达一种政治革命意识。值得一提的是《梅雨》、《月光曲》两部剧作表现工人受压迫剥削的命运及其反抗斗争的时代主题,比较注意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展现不同性格的人物在时代风暴中的不同反应及结局,在主题表达、形象塑造及艺术表现方面都有明显进步。
真正体现田汉革命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剧作是《回春之曲》。全剧将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男女主人公高维汉和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交织在一起,洋溢着海外游子报效祖国的赤诚和激情,切合时代审美需求,产生很大影响。《回春之曲》是田汉转向之后的一个戏剧高峰,然而这种高峰创作并没有持续下去,此后尽管他创作颇丰,但艺术上却良莠不齐,《梦归》、《械斗》、《号角》、《卢沟桥》等是紧追时代、仓促成篇的宣传鼓动剧,《黎明之前》、《初雪之夜》、《晚会》、《女记者》等充满直露的说教。真正能够与《回春之曲》的革命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相媲美的剧作是《秋声赋》和《丽人行》。《秋声赋》通过家庭矛盾、爱情纠葛塑造抗战文化人徐子羽的形象,背景开阔,情节曲折,由欧阳修《秋声赋》感发而作,却由悲凉凄清的哀感一转而为秋的催人奋发的飒爽之气。《丽人行》通过受侮辱的女工刘金妹、软弱动摇的知识女性梁若英和坚定的革命者李新群3个不同身份、性格的女性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沦陷区民众的苦难与抗争,同时隐喻抗战后的黯淡现实,内涵丰富,视野开阔。1949年后田汉的代表作是《关汉卿》和《文成公主》两部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渐趋成熟。田汉认真研究关汉卿的作品与时代,融进自己作为剧作家的遭际和感情,从而创作《关汉卿》,塑造关汉卿这一心系苍生、爱憎分明、凛然不屈的光辉形象。本剧体现出田汉作为浪漫主义剧作家对史实依据与艺术想象关系的处理方式:“零碎不多的史料记载,被作家重新组合,并加以虚构性的扩展,而形成了细节有所据,而整体构架则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这一格局。”[8]170《文成公主》服务于汉藏永好、民族团结的时代主题,充满浪漫瑰丽的奇思幻想。
饱满的政治热情是田汉革命浪漫主义剧作的另一特征。文艺发挥最大的现实作用,鼓舞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必须有灼人的激情与强烈的感染力。《回春之曲》喷涌着灼人的爱国热情,梅娘的一曲高歌声情并茂,使无数观众倾倒,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秋声赋》不如《回春之曲》激情充沛,却也运用抒情写意手法表现人物,许子羽在风雨声、号子声中读欧阳修《秋声赋》,写《新形势下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人物情感、时代忧患在这个情境相生的场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丽人行》饱和着忧国忧民之泪,燃烧着抗敌御侮之火,一句“中国快天亮了”道出无数人心中的期盼,鼓舞他们抗争的信心与勇气。《关汉卿》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流泻着诗意之美,剧作家与剧中人达到心灵、精神的契合。关汉卿在狱中所写的长曲《双飞蝶》,句式长短错落有致,对仗用典语词精美,音韵铿锵朗朗上口,慷慨激昂寄情遥深,既是悲壮的战斗宣言,又是忠贞的爱情誓言。
情节的传奇性是田汉革命浪漫主义剧作的第三个特征。浪漫主义之不同于现实主义,除了浓烈的主观抒情外,还有瑰丽浪漫的奇思异想,这在田汉前期新浪漫主义剧作中已有表现,在后期革命浪漫主义剧作中得以延续并加强。《回春之曲》中的高维汉在战斗中受伤失忆,受到爱人3年的精心护理,在除夕的鞭炮声中恢复记忆,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传奇。《秋声赋》展现胡蓼红和秦淑瑾与日本兵的搏斗到关键处戛然而止,后通过书信讲述结果,这种情节暗转先在前面留下悬念,又使后面颇有层次波澜。《关汉卿》从整体上讲,更是一部传奇剧,关汉卿的生平事迹见之于史籍记载者甚少,这给剧作家创作带来困难,同时又带来不受史实约束、大胆想象创造的自由。田汉借关汉卿的躯壳使自己本真的感情与生命得到一次尽情爆发,“戏中戏”的结构安排更增加本剧的传奇性。《文成公主》中的文成公主为抑止思乡之情完成汉藏联姻大业而丢弃日月宝镜,宝镜化成日月山,这一情节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她勇斗猛虎巧得松赞干布相助,猛虎成为二人相见的月老,与《获虎之夜》中老虎拆散有情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节巧合也是本剧传奇性的表现。
通过以上对田汉戏剧创作历程的梳理及对代表作的解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1930年为界,田汉的创作有变也有不变,发生变化的只是浪漫主义的某些表现方面,而浪漫主义这一根本的特质、精神与手法却是贯穿始终的,田汉剧作经历是由新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的转变,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
注释:
①人们习惯以1930年和1949年为界把田汉戏剧创作分为前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其实1949年后田汉的创作与此前相比无论是观念、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都可称之为革命浪漫主义,而且1949年后田汉剧作比较可观的只有《关汉卿》和《文成公主》,无论质还是量都很难单独构成一个阶段,因此本文采用两分法。
[1]蒋 益.论田汉的戏剧创作:纪念田汉诞生一百周年[J].长沙大学学报,1999(1):11-17.
[2]田 汉.致郭沫若的信[M]∥田汉文集:第1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3]田 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复黄日葵兄一封长信[J].少年中国,1920,1(12).
[4]田 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J].少年中国,1919,1(1).
[5]穆 旦.出发[M]∥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陈瘦竹.田汉的剧作[M]∥现代剧作家散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7]田 汉.在戏剧上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M]∥田汉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文 格)
2016-11-10
方 舟(1990-),女,湖北省武汉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I207.3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