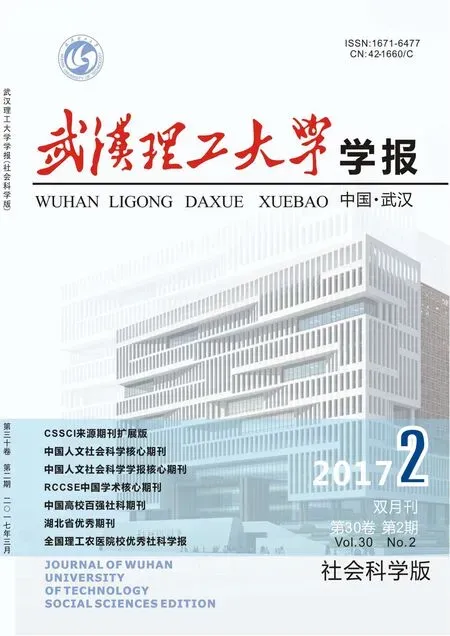社会信任、社会认同与社会距离研究*
——以农民工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枭枭,侯志阳(华侨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社会信任、社会认同与社会距离研究*
——以农民工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枭枭,侯志阳
(华侨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促使农民工作出与城市居民交友决策的主要因素为何,是我们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以福建省为例,建立了社会信任、社会认同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社会信任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即较高的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愿,从而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较高的文化认同、社会地位认同和城市归宿感认同有助于缩短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社会信任;社会认同;农民工社会距离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58年开始,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工业化发展、稳定城市秩序、保障城市供给、控制城市规模,在城乡之间实行严格的迁徙和流动限制的区别化户籍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出现了许多不合理性,日益割裂着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越来越多的外来农民工受到文化排斥、歧视、偏见以及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不公、城市生活成本高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融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此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农民工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从现有的文献中找到两种主要的答案:其一是社会资本差异、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的影响[2];其二是阶层群体固有差异与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3],其中包括地理空间分布差异、文化差异、种族差异和经济地位差异。前者强调社会资本上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彼此的社会融合。后者强调社会阶级环境差异化(如经济收入不平等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产生的社会距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距离还与年龄、婚姻状况、个人的成长环境以及家庭子女数量有着密切联系。尽管已有的研究也涉及到社会认同(如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等)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研究。但鲜有学者从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这个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事实上,社会信任是缩短人们社会距离的有效工具。如果农民工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既对自己具有影响所处的邻里社区环境的市民生活有信心(普遍信任),也对家人和朋友对自己的诉求作出反应有信心(特殊信任),他们可能对缩短其自身的社会距离就有较高的期许。而从社会认同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可以从农民工对其自身的角色定位来探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壁垒。毕竟,作为外来的、试图融入城市既有群体或者文化的农民工而言,如何归属和认同自己的城市角色,拉近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是对某一城市特定社会形态的认同,更是对处于这个特定城市社会形态中群体和市民的认同。认同的结果往往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偏好[4],进而影响彼此的交友决策及其社会距离。基于此,本文将探讨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信任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距离被用于衡量人们之间情感的亲密程度和关系的紧密程度,它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交往间心理距离的一种反映。人与人之间之所以存在不同大小的社会距离或者说是心理距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体无法在复杂的、不确定性的未来环境中准确地预测和监督他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又是人类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因此,在缺少直接或者完全控制他人行动的客观复杂环境中,信任变得格外重要。信任的大小直接预示着信任双方关系的亲近或者亲密程度,如果将信任的同心圆扩展到更为抽象的社会客体中,所建立的信任,我们称为“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指公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双方相互信任的程度,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6],或者说是彼此对对方能作出符合制度行为的持续性期望[7]221。社会学学者将社会信任划分为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和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 trust)两种。普遍信任是指个体对市民社会、体制和陌生人的一种信任[8];这种信任表明了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于双方之间的持续的相互认可和解释的期望程度。特殊信任是指对家人或者朋友的信任[9];这种信任表明了家人和朋友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个体认可和接受的期望。较低的普遍信任一般表现为对社会的冷漠,他们认为除了自己的家人,其他的人或者事物都不可信,都很现实。社会信任较低者往往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不愿和人交流,因为他们害怕被欺诈。社会信任较高者往往表现出对人和事物较高的依赖,且倾向于彼此的互惠。因此,社会信任能有效促进民众之间的交流并形成某种较为公正的意识和增进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福利[10]。
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个体的社会距离或者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社会信任是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社会信任与社会距离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如果说社会信任是一种人与人交往间的情感润滑剂的话,那么通过交往而衍生出来的社会距离就能得到有效的缩小。“社会距离可以划分为主观个体社会距离、客观个体社会距离、主观社会距离以及客观社会距离。主观个体距离可以看作个人对他人的看法、偏见,客观个体距离指的是个人之间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差距、主观社会距离表示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群体之间观念差异的来源、客观社会距离反映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在整体文化、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从广义上讲,社会距离的作用因素包括了个体本身的主客观认识差异和个体与社会其他事物之间的主客观差距,即个体对整个社会的人和物的认识差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而这种内在屏障则表现为个体的关系、交往和感情冷淡[11]。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认为较高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社会距离,当个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能有效缩小社会距离。因此,社会距离被用于刻画人与人在社会中关系情感的紧密程度,这其实是对人与人之间社会资本强弱的一种反映[12]。而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任,自然也能被用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已有的一部分研究已经证实,信任有助于调动个体行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个体与他人交往的频率[13],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信任是重要的,被信任也是很重要的”[7]213-238。换言之,当个体接收到他人的信任时往往会提高自身在其他事物中的可信性。因此,社会信任可以激励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扩大个体的社会网络、互动的范围、促进彼此沟通、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接受等,从而降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的一部分。但目前较少学者具体从社会信任的角度考察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唯一的例外就是胡荣和王晓2012年的研究[2]。他们的研究中将信任、网络关系与社团参与作为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的因素。他们发现较高的信任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探讨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综上文献之检视,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普遍信任有助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即农民工的普遍信任越高,其社会距离也越小。
假设2:特殊信任有助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即农民工的特殊信任越高,其社会距离也越小。
(二)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认同
在心理学领域,认同是一个同时发生“求同”和“存异”的过程。认同是一股非常独特而强大的力量,虽然它是一种无形的想象,但是它本身是可以建构出来的。当人们的认同存在差异时,社会的形态也会产生差异[14]。建构主义者认为,认同是个体或者群体在一定环境诱因下,对自身身份的选择和界定,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产物[15]。“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一。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更进一步地说,社会认同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对特定阶层产生的归属感”。这种阶层归属感是阶级差异所引起的,而阶级差异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拥有的,故人们之间各自内化自己身份的归属感也在某个时期是主客观并存的。因此,这种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直接引起了个体或者群体的社会认同差异。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社会认同,造成了不同阶级之间的观念和认知等鸿沟和差异现象。而这种认知差异或者鸿沟便演化为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西方学者将这种群体间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的差异以及客观的文化、教育和地位之间的悬殊差距称为社会距离。因此,社会认同与社会距离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属阶层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等的认可和肯定的话,那么社会距离便是个体理性分类后对自己归宿身份感的重要表现。当个体和群体对自己群内偏好和群外偏见的认同感越强烈时,群体之间为了保持各自认同的“优越感”或者消除“自卑感”而努力与其他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实际上在无形中为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设置了阻碍[1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要保持一个长期的“敌对”状态,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距离。按照普遍怀疑主义学者的观点而言,当个体处于某个固定环境中时,他(她)不会一成不变地接受,他(她)会通过比较与不断地怀疑、计算和筹划来获取新的社会认同,塑造新的社会身份。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农民工对城市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或者对自身城市人身份的归属感越强烈时,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愿往往较高,社会距离也越小。亦或是农民工对自己的城市地位有较高的认同时,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向往往较高,社会距离就越小。
就中国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主要产生于国家制度和国家传统文化两大体系。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层体系,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治社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它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位置划分体系中将生产资料、收入、市场地位、职业、政治权力、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社会声望等分层对待和分层处理。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农村居民的社会权利,也显得有失公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距离,阻碍着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另一方面,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等级层次的社会,凡事都讲究级别顺序,如饭桌礼仪、会议发言等都遵循严格的先后顺利,它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等级层次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社会分层现象。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团体因占有资源的差异而产生的社会群体地位之分的现象。它实际上潜在地反映出不同层级人群因为文化、社会地位和主观心理偏见的不同而造成人与人之间观念和认知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异所衍生出来的分层认同。不同层级的人和群体会自觉将自己归类,以提升自己的“本体性安全”。当然,这种自我归类的过程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某个个体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时,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的“本体性安全”,会努力重塑自己的行为规范以期与周围环境所规定的社会规范相协调。这一过程就是个体“去个性化”和“去旧群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个体“去环境压力”的过程。因此,个体会在新环境中努力学习新的文化规范,采取各种策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最终重新获取自己的社会认同感和被认同感。这具体表现为对所处环境文化的认同,对自身地位的认同以及对自身归宿感的认同,而这些认同便造成了今天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可见,农民工社会认同是农民工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学界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农民工社会认同对于其社会距离的影响。唯一的例外就是1995年李强和2011年王桂新和武俊奎在其研究中有所涉及,他们认为外来农民工在心理上有意识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以及同群共通的偏见和价值将会扩大农民工与市民的距离等,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将社会认同作为主要测量指标,且没有细化社会认同的测量指标,这不利于深入分析农民工社会认同对其社会距离的影响。因此,本项研究将在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背景下,探讨其社会距离这一问题。根据对上述文献之综合,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认同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有关,即社会认同感越强,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反之,社会距离就越大。
三、相关数据统计和变量测量的方法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源于2015年12月在福建省泉州市、福州市、漳州市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我们随机调查了福建省外来打工较多人群的泉州市、福州市以及漳州市。我们随机抽取20个工厂,每个工厂随机抽取40~50个外来农民工进行调查访问。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800份,回收780份,回收率为97.5%,有效问卷685份,有效率85.6%。
(一)因变量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受访者的社会距离,我们根据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将其操作化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意愿(交友意愿越大,社会距离越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因变量的问题是: “您(农民工)是否愿意和本地居民交往?回答选项为:(1)不愿意;(2)愿意(0=不愿意,1=愿意)。
(二)预测变量
主要的预测变量分为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两类。测量社会信任的两个指标,即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通过对问卷中如下8个项目的因子分析获得:您与家里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邻居老乡领导的信任程度如何?回答选项设置为:“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一般”、“比较可信”、“完全可信”,依次分别赋值“1”到“5”。这8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高达0.895,表明其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我们用主成份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普遍因子包括5,6,7,8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626,0.934,0.845,0.934,特征值为4.683,解释方差为41.821%)。特殊信任因子包括1,2,3,4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860,0.746,0.632,0.694,特征值为1.616,解释方差为36.907%)。
对于社会认同,我们采用三个指标进行测量,文化认同、社会地位认同和个体城市归属感认同因子,其通过来自问卷中10个项目的因子分析获得:(1)我特别喜欢和当地居民一起过这里的习俗活动;(2)我比较喜欢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3)我比较喜欢本地居民的语言和服饰;(4)我比较喜欢参加本地居民举办的社区活动;(5)我对社区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会被采纳;(6)虽然自己是农民出身,但当地居民比较尊重我;(7)当地街道办事人员重视我们的态度和看法(8)我经常和本地居民吃饭聊天;(9)我感觉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本地居民一样;(10)虽然我是个外来农民工,但很容易融入本地居民的生活圈子;针对问题的回答选项分为:(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这10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高达0.893,表明其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我们用主成份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文化认同因子”、“社会地位认同因子”、“城市归属感认同因子”。文化认同因子包括1 ,2 ,3,4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956,0.884,0.870,0.885,特征值为5.206,解释方差为35.613%)。社会地位认同因子包括5,6,7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935,0.851,0.830,特征值为1.888,解释方差为26.309%)。城市归属感认同因子包括8,9,10项目(其因子负荷分别为:0.837,0.834,0.792,特征值为1.580,解释方差为24.819%)。
(三)控制变量
我们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及个人家庭和工作背景特征的变量。年龄和收入是定距变量。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中学=2,高中=3,大专=4,本科及以上=5),工作性质(低技能=1,高技能=2)为定序变量。性别(女=0,男=1),婚否( 是=1,否=0),您是否从小生活在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是=1,否=0)为虚拟变量。
表1展示的是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量。我们通过对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共线性诊断,发现模型中所有预测变量的VIF都低于10,特征值也都大于0.01。因此,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四、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农民工对市民的交往意愿)为二分变量,我们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因变量因素进行拟合。为了获知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的每个自变量的影响力,我们先将控制变量全部进入回归方程,得到模型1,然后逐个将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的每个自变量逐一引入回归方程,与农民工社会距离做嵌套模型,得到模型2、3、4、5、6。表2呈现了嵌套模型的所有回归结果。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建立了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我们首先来分析模型1的回归结果。模型1中的7个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除了“婚否”、“工作性质”、“家庭成长环境”外,其他变量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正。具体来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交往意愿越大,且男性的交往意愿高于女性。而农民工年龄越大,其交往意愿越小。高收入农民工的交友意愿高于低收入的农民工。从整个回归结果来看,模型1解释了34.2%的方差。虽然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家庭成长环境”这两个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它们的回归系数是正的,这表明所调查的样本存在一种趋势。即高技能的农民工的交往意愿高于低技能的农民工。即高技能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小于低技能的农民工,其社会融入能力也强于低技能的农民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婚否”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已经结婚的农民工的交往意愿低于未婚的农民工。
注:*P≤0.1 ,**P≤0.05,***P≤0.01,****P≤0.001,括号中标出的是标准差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普遍信任”这个自变量指标,结果在所有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模型2的NagelkerkeR2达到了36.8%,且系数显著为正,普通信任进一步解释了农民工交往意愿2.6%的变化。普通信任与农民工对市民交往意愿呈显著正向相关,表明对同事、老乡、邻居和领导充满信任的农民工的交往意愿往往较高,其社会距离相对较小。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特殊信任”这个自变量指标,模型3的NagelkerkeR2增加到39.7%,且系数显著为正,特殊信任又进一步解释了农民工交往意愿2.9%的变化。特殊信任与农民工对市民交往意愿呈显著正向相关。这表明农民工较高的家人、亲戚、同学和朋友的信任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交友意愿。总之,在社会信任的两个因素中,农民工较高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有助于增强其交友的意愿,缩短其自身的社会距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模型2、模型3与模型1的比较来看,在引入社会信任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即在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显著影响下,农民工的收入高低在交友意愿的问题上变得没有差异。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认同”因子,模型4的NagelkerkeR2提升至48.3%,且系数显著为正,文化认同又进一步解释了农民工交往意愿8.6%的变化。文化认同与农民工交往意愿呈正相关,这表明农民工的文化认同越高,其交友意愿越高。换言之,当农民工对当地的文化习俗具有较高的认同或者接受度,那么他们就有更高的意愿与城市居民交往。模型4的结果还显示加入“文化认同”这个变量对于模型3呈现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即男性和女性在与市民交友意愿的问题上没有差别,而是否结婚变得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已婚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愿低于未婚的农民工。产生这一结果可能与个体的情感需求有关,已婚的农民工可以从家庭婚姻中得到情感满足因而其交友意愿低于未婚的农民工。
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地位认同”因子后,模型的NagelkerkeR2在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了5.2%,且系数显著为正,地位认同又进一步解释了农民工交往意愿5.2%的变化。地位认同与农民工交往意愿呈正相关。这表明农民工对自身地位的认同与其交往意愿有密切关系,即农民工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度越高,其交友意愿就越高;反之,越低。模型5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在社会地位认同的显著影响下,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在其交往意愿上变得不再显著,即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其交往意愿没有差别了。
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归属感认同”因子后,模型6 的NagelkerkeR2提升至57.8%,系数显著为正,城市归属感认同更进一步解释了农民工交往意愿4.3%的变化。其说明“城市归属感认同”对其农民工的交友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个体对自身城市归属认同感越高,其交友意愿就越高。模型6还显示了在个体城市归属感认同的显著影响下,收入对其交友意愿的影响变得显著,但与模型1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即在没有个体城市归属感认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交友意愿越高;而在带有个体城市归属感认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其交友意愿越低。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个体持有的金钱主义观有关。
综上,我们发现,当农民工对整个社会具有较高的信任和社会认同时,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愿变得较高,社会距离变得越小,而性别、教育程度、工作性质以及家庭成长环境变得并不重要了。模型2、3、4、5、6的结果表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2015年对福建省外来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在控制了受访者的人口学变量等变量后,以农民工为视角,建立了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从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角度探讨了外来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我们假定了较高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能够有效缩短其社会距离。研究发现:首先,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信任主要是通过农民工对家人、亲戚等的特殊信任和对老乡、领导等的普遍信任来影响其社会距离。个体的社会信任越强烈,越有利于消除农民工自身与城市居民交友时的心理障碍和顾忌,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子,缩短彼此的社会距离。其次,农民的社会认同也显著地影响其社会距离。我们通过社会认同中的三个指标证明了这一假设,即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地位认同和城市归属感认同是影响其与城市居民交友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当城市文化得到农民工较高的认同时,越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当农民工感受城市居民和政府机构以及相关的事业单位等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时,他们对地位高低差异的认同感就越弱,从而越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缩小其社会距离;当农民工对城市归属感认同越强烈时,越有助于减少农民工对城市的偏见,增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从而缩短其自身的社会距离。为了更进一步剖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下面我们通过比较现有的研究文献来阐述本文研究发现的理论含义和政策价值。
王桂新、武俊奎教授[12]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受自身所属群体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也就是说,个体所属的群体认同或者接受另一个群体时,个体也会接受和认同那个群体的成员。反之,当个体所属的群体不认同或者不接受另一个群体时,个体便会疏离那个群体的成员。因此可以说,农民工是否愿意与城市居民交友,主要是基于自己对自身所属群体角色的判断而归类的。那么这就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我的身份角色决定了我的群体归类,我的群体归类决定了我与其他人的社会距离。显然这样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忽略了环境压力对人的经济理性选择,也忽略了个体对自身群体归属具有能动性和自由建构权力的特点,即当个体处于一个新的社会环境时,他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诱惑、价值判断而决定自己的群体归类。是接受原来群体的内化,还是拒绝而重新塑造新的身份,主要取决于行动者对新环境的经济理性衡量和判断以及自由选择。换言之,当个体感到原来群体在某个具体的新环境中不具有优势时,个体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而选择脱离原来的群体,以努力融入新的群体。那么,影响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察:
(一)社会信任与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它对于保障社会有效运行和促进社会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社会中,信任为市民社会中的自由人提供相互交往的秩序基础,而这种秩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事实上,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与其他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资本”的投资过程。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存在一种对他人未来可能采取有利自己行为的赌博。正如Luhmann比喻的那样,信任是一种预付款。因此,当农民工来到陌生的城市后,他们为了应对不确定和无法控制的未来,往往会采取一种至关重要的策略——即信任所产生的关系资本。信任可以划分为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又可以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种。其实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并没有显著的差别。按照福山的话来说,信任存在渐进和扩展的半径,在半径之内信任就是最小信任或者说是对亲近家人的特殊信任。而在半径之外的信任就是对社会客体的信任,我们可以称它为普遍信任。人的信任总是从最小的、最具体的信任到最抽象、最普遍的信任。信任还可以提升人际关系,如果按照社会群体凝聚力的观点而言,人际关系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它能将不同个体黏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社会团体或者小群体。因此,依此逻辑,当农民工融入城市环境时,总是将特殊信任作为一个起点,不断向周围扩散,建立人际关系圈,比如农民工利用信任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到城市求职、安家、租房等。利用自身的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与城市群体发生交往和互动,进而不断改变自身的社会距离。
(二)社会认同与社会距离
建构主义者认为,社会认同是不同主体在某一种特定秩序的约束下,通过交流、沟通等手段而形成的,它是一种去“个性化”的认同过程,是个体或者群体在一定环境下塑造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或者说是,个体和群体融入某个既成群体的互动过程,而这种互动过程就是对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的认同。因此。农民工融入城市、缩短社会距离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城市体制和城市文化形态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在城市环境的感染下逐渐形成的,即社会认同是某种环境的产物。当农民工置身于城市环境中时,因受到巨大的城市文化的冲击,其原有的群体认同感要么消失,进行“反身性筹划”,重新进入一个新群体,要么强化原有群体的认同感。当然,这与感染所具备的互动性和模仿性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当农民工受到社会排斥或者社会接纳时,其社会情绪和行动会在群内散布和群外扩散。如果社会排斥越强烈,个体对自身的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越强烈,而群体之间相互认同感也就会随之产生巨大差异。那么,不同群体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就变得越来越远。如果社会接纳程度越高,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就越强,彼此间的社会距离也就越近。因此,个体或者群体的社会认同的构建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和偏好,对于个体融入社会生活,确立生活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个体层面来讲,构建与城市文化和体制相融的农民工社会认同感有助于减小农民工城市融入困难,即城市为农民工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地位以及身份归属是其缩短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催化剂,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点。从社会层面而言,环境对于界定或者划分群体界限和符号具有重要的影响,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群体价值观和认同感。因此,营造一个较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降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具有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调查样本的范围只限于福建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样本的代表性。
第二,本文并没有将“经济地位”、“种族差异”以及“空间分布差异”等有效的几个预测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而这些变量对社会距离的显著影响已经被大量学者所证明。例如,经济地位和种族差异是民众社会距离的有效预测变量[3]。同样,空间分布差异也会对民众间社会距离产生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把上述几个变量也纳入模型,这样或许可以更合理地解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第三,本文将因变量衡量社会距离指标的交友意愿作为二分变量进行测量,尽管这一做法在以往的文献中并不少见,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将农民工的交友意愿假设成两个可能值,而可能忽视了农民工交友意愿更为细化的等级程度,不利于更细化地考量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因变量作为多级定序变量来测量农民工交友意愿。
第四,本项研究只是从农民工视角出发,探讨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而没有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交友意愿纳入分析框架,这将不利于深入剖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与此同时,由于本项研究是一次横剖研究,即在单一时点对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无法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在回归模型中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农民工交友意愿有统计显著性影响,但严格说并不能就此说明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只能说前者与后者统计上相关。要解决这一问题,尚待以后通过多时点收集数据的纵贯研究。
毫无疑问,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是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农民工缩短社会距离的助推剂和润滑剂。对于中国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来说,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政策意义上应该有两点启示:其一,我们发现诸如较高的社会信任能够增进农民工的交友意愿,缩短其社会距离。因此,政府应该加快相关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不再存在因身份差异而演化的阶层冲突和阶层分化。其二,我们的研究表明,农民工较高的社会认同有助于缩短其社会距离。其具体表现为文化认同、社会地位认同和城市归宿感。因此,当前,政府可以加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有效融合和发展,以建立更公正、更公平的社会治理机制。当然,影响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因素是复杂的,相关制度和措施的改革虽然也不一定能保证增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但是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门槛。
注释:
①参见王桂新、武俊奎的《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一文,刊载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28-47页。
②参见张虹的《重构中国中产阶级认同》,刊载于《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年第7期第94页。
③参见冯仕政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一文,刊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27-133页。
④本体性安全是指对自然界与社会世界的表面反映了它们的内在性质这一点的信心或信任。转引自李友梅的《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28-44.
[2]胡 荣,王 晓.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J].社会科学研究,2012(3):101-106.
[3]Verkuyten M B.Kinket.Social Distance in a Multi Ethnic Society: The Ethnic Hierarchy among Dutch Preadolescents[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0,63(1):75-85.
[4]李友梅,肖 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
[5]Short,J.Jr,Hazard,risk,and enterprise:Approaches to science,law,and social policy,in:Law and Society Review[J].1990,24(1):179-198.
[6]魏永峰.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J].理论界,2009(2):193-194.
[7]Gambetta 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M].Oxford,UK: Basil Blackwell,1988.
[8]Uslaner,Eric. M.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35-60.
[9]Zmerli,Sonja.Applying the Concepts of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to Empirical Research[J].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2003,2(3):68-75.
[10]巴 伯.信任的逻辑与限度[M].年 斌,李 红,范瑞平,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20-21.
[11]Simmel,G.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K.H.Wolf(ed. & trans.),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M]. New York: Free Press,1964:23-56.
[12]Marshall,G.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2nd Edition)[M].IL:The Free Press,1950:224-225.
[13]Luhmann,N. Trust and power[M].New York: John Wiley,1979:25.
[14]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0.
[15]亨延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0-21.
[16]Nosanchuk,T.A. &B.H. Erickson.How High is Up? Calibrating Social Comparison in the Real World.[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5,48(48):624-634.
(责任编辑 王婷婷)
Social Trust,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Distance Researc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JIN Xiao-Xiao, HOU Zhi-Yang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362021,Fujian,China)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social distanc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residents, making friends with city residents, is the main problem to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e establish the model of the social trust,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easant workers social distanc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distance on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identity of migrant workers .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higher social trust helps reduc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distance. Namely, the higher particularized trust and generalized trust is helpful to improve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dating, and reduces the social distanc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higher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status identity and the sense of city belonging can help shorte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trust; social identity; migrant workers social distance
2016-05-20
金枭枭(1988-),男,贵州省遵义市人,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政府行为和社会保障等研究; 侯志阳(1980-),男,福建省南安市人,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研究。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6年度项目(FJ2016B010);华侨大学2014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项目
C931.7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