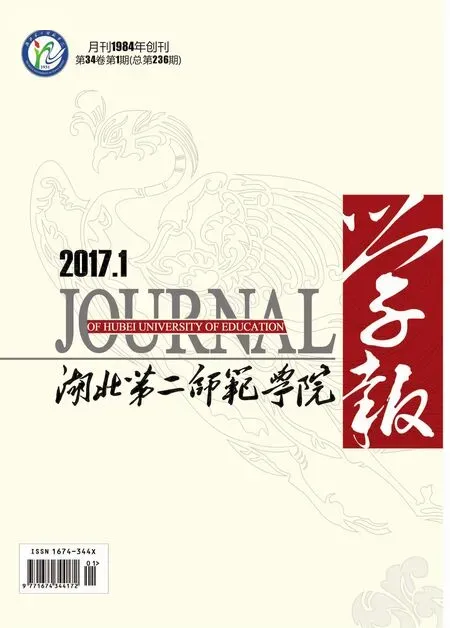论我国宋明时期的知行观
张智涛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长沙 410000)
论我国宋明时期的知行观
张智涛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长沙 410000)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千年来人们都热衷于对它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是在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而,研究宋明时期的知行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智慧,而且还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当今的知行观,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理学; 知行观; 知先行后; 知行合一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人们观念的一个命题即是:“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然而这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对于它的科学内涵我们还得通过比较才能有所了解。宋明时期是我国继先秦之后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很多重要的哲学命题都被提了出来,而且还对以前的哲学命题进行了系统化研究。从当时学术繁荣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来说,宋明时期无疑是其他时代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对于知行问题的研究,使得我国的哲学思想更加地走向了系统化。
一、先秦时期的知行观
先秦时期是一个动乱时期,但是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国思想界却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百家争鸣”,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派别,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针对当时动乱的社会状况,思想家们都提出他们各自的主张,知行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根据知与行的关系,我们暂且把它们分为主张“知”决定“行”的唯心派和主张“行”决定“知”的唯物派。
知行观上的唯心主义主要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孔子说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在这里,孔子显然把生而知之者放到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上,生而知之很显然是一种先天的“知”,它是不以经验为基础的。从这个逻辑路径肯定会得出认识决定实践这一结论。孔子强调知行统一,讲求学以致用,他认为行是学的目的,又是检验学的标准,这反映在其名言“听其言而观其行”中。[1]14孟子更是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他认为人先天的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就是来寻回在尘世中所放逐了的这个“心”。所以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吿子上》) 这里所说的“放心”,就是那个被尘世所遮蔽了的现实的“心”。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求放心”的过程,而这个活动说到底其实还是“心”的本能活动,这就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走向了唯心主义。
知行观上的唯物主义主要是以墨家和儒家的荀子为代表的。他们认为人们的认识是一种后天的认识,认识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一种能力,是客观物质的一种属性。墨子明确说道:“天下之所以查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明鬼下》) 墨子把闻见与否作为判断客观事物“有”“无”的根据,显然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没有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直接经验,也就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看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原则的。[2]66荀子也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 这里他们都是把人的认识看做是一种后天的习得,对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的本质做了规定。
从先秦时期的知行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知行问题其实是作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来呈现的,并且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论是孔孟的唯心论还是墨家和荀子的唯物论,他们都看到了知行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它当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来看待,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知行问题尽管在先秦时期一直是发展着的,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成熟,他们虽然看到了知行二者的关系,但是还没有从二者的关系本身中来考察,所以他们的探索还带有朴素性。到了宋明时期,知行问题又有了长远的发展,并且此时思想家对知行问题的探讨也到了最高峰。
二、宋明时期的知行观
宋明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哲学思想所达到的思辨程度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肩的。在那个时候,面对外来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当时的士大夫在吸收佛教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学术思潮,那就是理学。理学是儒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吸收了当时在社会较有影响的各种学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理学是新时代下对传统儒学的扬弃。比之于传统的儒学,理学的思辨性更强,并且其体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他们除了讨论物质世界的本体之外,还把体现人们实践生活的知行观也纳入了理学的范畴。根据当时学者们对世界本体的不同理解,我们大体可以把理学分为三个派别:“理学派、心学派和气学派。”
1.程朱理学派的知行观
在程朱那里,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理”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它其实就是人们认识的终极对象,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以认识这个终极的存在作为目的的。二程认为:“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矣?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的存亡加减?是佗元无少欠,百理具备”。(《二程遗书》 卷二上) 朱熹也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走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走父子之理。不成元无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朱子语类》 卷九十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天理论是只接二程的,他也认为天理这个终极存在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他又说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行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理。”(《朱子文集·答黄道夫》) 这便是理学派的天理论,从这个逻辑径路我们就可以理解程朱的知行观了。
在二程这里,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知行观,但他们却以“格物致知”作为他们认识论的命题。把这个命题一分为二,我们就可以得出偏向于实践的“格物”和偏向于认识的“致知”这两个基本命题,但是理学派的天理论把天理作为了人们认识的对象,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以天理为目标的。所以作为实践的“格物”在这里就成为了通向天理的手段,作为认识结果的“知”就成为认识的目的。所以他们必然是重视“致知”甚于“格物”,也就是说,他们在知行观上把“知”看做了第一性的,把“行”看作是第二性的。尽管程颐区分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但他显然是更重视后者的。比之于二程,朱熹的知行观更为精到,他对知行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并且他的考察层次和高度是远远超过二程的。朱熹的知行观包含有三个基本的命题。第一是知先行后,他认为:“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朱子文集·答吴晦叔》) 第二是行重知轻,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故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子文集·答程正思》) 第三是知行互发,他认为:“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语录 卷九》);“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同上);“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语录》 卷一百一十七) 这便是朱熹的知行观,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知行的考察是在知行关系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他没有单纯孤立地去考察知和行,相比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2.陆王心学派的知行观
心学派与理学派都把天理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它既是宇宙万物产生和运转的缘由,更是人类社会产生和运动的根源。但两派却对天理与人的认识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前者认为天理在人的认识之外,它是一种有待认识的认识对象,它是一种外在性的存在,但是后者却认为天理是一种内在性的存在,它就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只是还没有被人所意识到罢了。心学派的代表陆九渊说:“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与赵监》) 从这里可以看出,比至于理学派,心学派的天理论更符合孟子的仁义先天论,他们把人的认识上升到了本体的层面就得出了这个结论。所以在心学派这里,对于天理的探求就不能通过外求格物的方式去获得,而应该把探求的方向由外转向内,这样,格物致知的认识路径就被完全颠倒了。
陆九渊在认识论上的观点主要是发明本心。他认为:“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此心为之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一溺于此,不由讲学,无自而复。故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与李宰(二)》) 至于发明本心的方法,他说道:“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唯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闲其戕贼之端,日夕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如手足之幹头面,则岂有艰难支离之事。 ”(《与舒西美》) 所以,陆九渊的方法就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反观,这种方法说到底就是一种意识活动,他把天理这个终极的存在看作是认识的对象和目的,同时这个“绝对”就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之内,这样,人的一切追求天理的行为就都变成了主体的意识活动。理学派在知行观上固然重视作为认识的“知”,但他们也同样强调作为实践的“行”,而在心学派的陆九渊这里,“行”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他已经被人的意识活动给消解。这很显然就是一种佛家所主张的修行方法,把它作为一种修养方法倒是可以的,但它在现实中却是有着极大的危害。
王阳明是心学派的集大成者,在知行问题上,他明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按照王守仁的看法,正是朱熹的知先行后在社会上造成了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恶劣风气,有些人正是借口先知后行而对伦理道德不肯躬行的。[3]9在他看来,把知和行分开的做法是不符合圣学的宗旨的,所以他才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他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 在王阳明这里,他把知和行看作了一个过程,把知看作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而把行看作是这个过程的结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王阳明这里,他与理学派的逻辑径路是相似的,都把知和行放在了一个统一的关系中去考察,而不把二者孤立起来。他还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固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若行而不能精觉明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殆’,所以必须说个知; 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功夫。”(《传习录》 上) 二者离开其中一个,他的原有意义就会失去,所以对于他们必须在二者的关系中去理解。我们通常对“行”的理解是所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形式。但既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则所谓“客观”,实际上即是“主观”的表达形态或实现形态,也即是“主观”的存在境域发生了转移而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阳明遂将“知”理解为“行”的某种“前形态”而纳入于“行”的一般概念,同时又将“行”理解为“知”获得其“客观化”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作为“行”的“前形态”的“知”获得不断显化而被表达于经验领域,同时又使“行”的内在形式获得其外在化,“知”“行”无论如何都是同时存在于这一过程之中的,因为正是这一过程使“知”“行”同时获得了显化。[4]17
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把二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创建,撇开王阳明的天理论不谈,似乎王阳明在知行观上对于二者何者为第一性并没有表态,但是只要明确他的心学派立场,我们还是会得出他对于行的肯定,可以看到,他在知行关系中,把行看成是知的结果,显然同朱熹一样是重视行的。而这一切都是以儒家的平天下为目标和起点的,所以王阳明在知行观上是重视行的。
3.气学派的知行观
在宋明时期,不论是理学的哪个学派,他们都会讲理气关系,他们的学问路径也有相似的地方,“理”在他们那里相当于是构成事物的质料因,“气”相当于是形式因,他们的主要区别集中于二者之间何者为第一性这个问题上,理学派和心学派都是理本论者,他们在理气关系上认为理是最为根本的,朱熹在论述理气关系时就指出,理是形而上的,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而气则是形而下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宋明理学分为气学派和理学派两派,基本说来,前者一般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他们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性,在认识论上他们也是如此,坚持人的认识对象是客观事物,由于不论是理学派还是气学派,他们的目的都是求理,所以气学派在认识论上往往可以看到认识具有层次性,但理学派则不一定。
张载是气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哲学命题。他这里所说的气并非指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它所指的则是与理相对的一种物质性。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 这是说所有的物质形态说到底都是物质或者说具有物质性,这是他从形而下的角度对于物质世界的概括。他继而说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行而。”(《正蒙·太和》) 如果说张载对于“气”是从形而下的层面描述的,那后者无疑是从形而上的层面上进行的,它不仅把可见的物质世界看作是物质的,而且还把不可见的世界也看作是物质的,这样,“理”就是“气”的属性了,这在本体论上无疑是坚持了唯物主义。既然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所以我们的认识无疑是从接触这些具体的物质开始的,但是认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找到那个支配具体事物的理,所以认识又不能仅仅限于对于具体物质的认识。
在认识论上,张载区分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认识,说它们是两种认识,其实只是从认识程度上的一种区分,相当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根据张载的观点,前者必须依赖于人的“见闻”,也就是说“见闻之知”是人们在应接事物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只是认识的低级阶段。“见闻之知”是建立在五官基础上的“物交而知”;对人来说,见闻之知虽然必不可少,并且也是人的所有认知活动的初始入手,但如果拘泥于所见所闻,就会陷入“以见闻为心”。[5]39而与它相对应的“德性之知”则是不依赖于见闻的,是超越具体认识的,是一种高级的认识。根据张载的看法,这种高级的“德性之知”就是对于天理的认识,人的认识只有达到这个阶段才可以说把握了天理。
三、宋明时期知行观述评
在我国宋明时期,哲学的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思辨程度之高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以往时代,并且体系化程度也是越来越高,这些都表明,在宋明时期,我国的哲学思想走向了成熟。宋明理学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知行观的发展,它表明原先那种人与物的朦胧关系在这个时候已经走向了明朗化,人们把研究的重点由研究人类社会转向了研究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无疑都是当时社会进步的标志。
理学家已经敏锐地感到知行问题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此时对于知行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先秦时期的那种朴素的方法了,他们此时的研究已经是带有思辨性的哲学研究了,他们看到了知行二者的不可分割性,把知行问题的研究放在了二者的关系当中去。儒家的最终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在知行问题上这无疑是属于行的层面,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理学家们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只要牢牢把握住了这样一个儒学的前提,我们就不至于在看待理学时走向偏颇。尽管宋明时期的哲学认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并没有像西方的认识论那样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恰恰还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宋明时期,认识论主要是以价值论的形式来体现的,认识论主要还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认识论,理学家们的目的是为了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他们的学问都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标的,所以他们研究的本体其实就是道德的本体,这无疑缩小了哲学的范围。
[1]王俊涛.中国哲学中知行观的争论和演变[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5).
[2]张洪波.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的论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魏义霞.王守仁“知行合一”与宋明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J].贵阳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4,(6).
[4]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5]方克立,郭齐勇,等.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胡栩鸿
On View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ZHANG Zhi-ta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eople are keen on its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Neo Confucianism focused on this debate, and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y cultures, not only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wisdom of ancient Chinese thinker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s view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helps us establish scientific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Neo Confucianism; view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2016-11-15
张智涛(1990-),男,甘肃陇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生哲学。
B244
A
1674-344X(2017)1-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