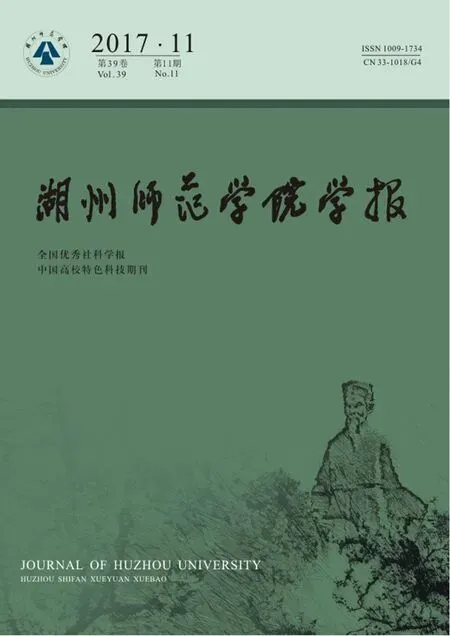孙大雨的海洋诗及新诗“音组”理论建构*
黄 健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孙大雨的海洋诗及新诗“音组”理论建构*
黄 健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孙大雨是“新月”诗派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坎坷,创作的诗歌数量并不多,但独具特色,显示出强劲的新诗创作实力。特别是他受大海的启示而创立的新诗“音组”理论,对推动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上来看,他提出的“音组”理论,是具有创意和创新精神的,其特点是主张以“音组”这种最小的音顿和节奏为单位,形成诗歌内在的“秩序”,构成诗行,再由诗行发展为诗节、诗篇,形成新诗独有的格律、节奏和韵律,从而为新诗建立新的格律规范,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思路和实践方式。
孙大雨;海洋诗;“音组”;新诗格律
作为“新月”诗派的重要成员,孙大雨①孙大雨(1905~1997),原名孙铭传,“新月派”诗人、诗歌理论家、著名翻译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留学,专攻英文文学,回国后在多个大学任教,曾被打成右派,后平反恢复名誉。的诗歌创作尽管数量不多,但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仍享有较高地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上,同时也包括他对新诗理论建设所作的贡献上。从现存为数不多的孙大雨诗歌来看,他创作的海洋诗则占据一定的数量,也颇具特色,而这些诗歌也典型地表现出他对新诗“音组”理论建构的理念和实践。结合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认真探讨孙大雨的海洋诗创作及其对新诗“音组”理论的建构,对于探寻中国新诗发展特点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1920年5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发表了孙大雨的诗作《海船》,共20行。此时,他年仅15岁,诗歌是以“守拙”为名发表的:
一
黑沉沉的海
澎澎滂滂的恶浪,
呜呜的风
四边环绕着。
二
重重叠叠的云,
铁壳似的包围着。
向外眺望,
不见一些儿微光。
三
努力前进,
浪愈急,风愈猛;
但摇摇摆摆的东荡西飘,
没有一些儿疑虑和恐惧的样子。
四
澎澎滂滂的努力前进。
他前进得愈快,
海浪狂风攻击得愈猛,
四面的沙滩暗礁都渐渐的拢来了。
五
四面的沙滩暗礁都渐渐的拢来了。
海浪狂风攻击得愈猛,
他前进的愈快,
前面一点灯塔的微光也渐渐的拢来了。
虽然这首诗歌创作不够圆熟,透露出稚嫩的气息,但从中可以看到他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影响而产生的那种勇往直前的青春毅力,表达了不畏艰难险阻的青春朝气,显示出追求光明的思想,向往美好未来的人生理想。在“海船”的意象里,寄寓他——一位15岁青年的远大志向。这首诗也是孙大雨创作的第一首与海洋有关的诗歌,换言之,也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是从创作海洋诗起步的。
大海之所以广袤、深沉,在于它的视野与胸襟广阔,能够容纳所有的江水、河水、溪水,构筑了有容乃大的襟怀和博大。青年孙大雨迈入诗坛,发誓要向大海那样,树立远大志向,谱写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同时,从诗歌创作艺术特点上来看,他从创作海洋诗起步,诗歌多与“水”的意象密切相关,似乎既具柔情,又具深沉的“水”的意象,更能表现他对人生,对“爱”与“美”的理想和诗歌艺术审美的理解和体悟。1922年,在《时事新报·学灯》上,他就发表了一首题为《水》的诗:
水呀!你是何等清洁可爱,
你是至公无私的救主!
你能洗涤一切尘垢污泥,
能救人于危急——渴极。
江河大海是你的形体,
荒山深谷有你的踪迹,
冰霜雨雪是你的变相。
不信贫的,富的;贱的,贵的;弱的,强的;
小的,大的;你都是一样待遇,
没有一些儿分别。
总之,你是普遍公平……
也许是对大海的倾心向往,择“水”的意象来展现他对公平、平等意识的渴望和赞美,表现出受“五四”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价值取向,尽管也还显得十分的稚嫩,但却始终洋溢着青春气息。同年,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上,他又发表了《滴滴的流泉》小诗共33首,以下节选几首:
一
滴滴的流泉,
滴破了坚固的磐石,
却滴不损柔和的沙土。
二十三
夜间我醒了,
一切都很沉寂:
“喔!明月!
原来是你!”
三十三
住在心的深处罢,
天真呵!
让我拿灵魂的火炬来照你!
这些择“水”的意象而创作的诗歌,明显带有“五四”白话新诗潮中的“小诗”创作痕迹,*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五四”时期所出现的白话“小诗”创作,擅长写刹那间涌现出了的人生哲理思考片断,诗歌的风格也多是晶莹清丽,蕴含着讴歌人性之美的心灵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思想。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缀结而成的“小诗”,内容自由活泼,形式不拘一格,往往是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五四”时代的新思想、新风尚,也与新诗独立于旧诗之后,扬弃旧诗模式化的抒情而转向重视理性阐发的创作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创作“小诗”的诗人较多,形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小诗”运动。其中,冰心、宗白华等人创作的“小诗”,具有较大的影响。思想纯洁,晶莹可爱,清新可诵,富有哲理,不仅赞美“清洁可爱”,“能洗除一切尘垢污泥”的水,而且也抒发出了对于自然、人生、青春、爱情的思索和感受,表现出受“五四”思想和文化启蒙而获得新生的那种多思、坚强、流动的心灵情感。
到了清华后,孙大雨的诗歌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在《我与诗》一文中,他曾这样回忆道,1922年夏考入清华学校后,又取别号子潜,兴趣“朝诗歌方面发展”,特别是对英文诗歌非常感兴趣。他说:“我向往雪莱的高渺幽微的激情遐思和弥尔顿的崇高浩瀚的气魄意境。”虽然,当时世界知名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列斯多夫》等散文作品也使他兴奋而神驰,但是相比较而言,他则是“更向往于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1]获得这种诗歌的创作情怀,应该说,与他对大海般的人生向往的志向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海的广阔,大海的深沉,大海的力量,给予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和情怀。
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孙大雨觉得当时的新诗意境太过于淡漠空泛、粗疏平淡,且声腔节奏几乎和白话差不多,因此,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来为新诗寻找一种新的格律。他说:
自从1917年有些富于新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写白话文的新诗,我在二十年代中期总觉得新诗的意境太淡漠空泛,粗疏平淡,声腔节奏跟白话散文怎么那样差不多,可说并无显著或微妙的区别。胡适所提倡的散文里的明白清楚,为了使读者理解学问的实际情况,固然有它的必要,但诗歌若仅仅止于理解现实的细关末节,没有想象与玄思的微妙、光焰、气氛、超脱、深沉、广大与隆重,那它跟散文还有什么多大的区别?[1]
孙大雨认为,非格律诗就不叫诗,而格律诗既非“豆腐干”诗,也非简单刻板的平仄押韵的诗。格律诗应该有自己特有的韵律、节奏,特有的意蕴和特有的形式规范。如果说古人创造了适合于文言表意系统的古典格律诗,那么,现代人也就应该创造适合白话表意系统的现代格律诗。在新诗格律的讨论中,孙大雨多次表示尊敬闻一多,钦佩他的为人厚道和学问扎实,但对他的新诗格律理论却持不同意见,并当面争论过,也开展过批评,指出他在理论上的不完整性。*在1985年12月6日给卞之琳的信中,孙大雨说:“一多是个诚实的人,……是我很好的朋友,1925年冬1926年四、五月间有半年多,我跟他来往很密切;他为人富于正义感,极正派,极厌恶弄虚作假。”
二
清华毕业后,孙大雨仍然没有放弃他追求“爱”与“美”的人生和艺术理想,没有放弃如何在新诗创作中展现这一理想的艺术途径和方式的探索。受泰戈尔和英国浪漫主义,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审美理想的影响,他一直都在对“五四”以来自由诗体式进行深刻地反思,从而萌发了他建立新的诗歌语体和格律体系的构想。当时,他已取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即将赴美学习,主修英文文学,兼修西欧哲学史和美术史。按当时的规定,他在赴美留学前,可以先在国内游学一年,广泛接触社会。他原先想去湖南长沙、岳阳,去探访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然而,当他来到屈子庙所在地——君山时,*君山位于湖南岳阳西南约15公里的洞庭湖中,总面积0.96平方公里,由大小七十二座山峰组成,与千古名楼岳阳楼遥遥相对,被“道书”列为天下第十一福地,传说舜帝的二妃娥皇、女英曾来到这里,死后即为“湘水女神”,屈原称之为“湘君”,故后人又把这座山叫“君山”。听说当地土匪多,难保人身安全,他只好中止行程,改道去了浙江的普陀山。*普陀山位于浙江东北部,舟山群岛东南部,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素有“东海明珠”之美誉,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此时的孙大雨,一边游学,一边正苦苦寻思新诗的格律问题。来到浙江普陀山后,他入住佛寺圆通庵客舍,在那儿盘桓了两个来月。孙大雨后来回忆道:
我到海上普陀山佛寺客舍里去住了两个来月,想寻找出一个新诗所未曾而应当建立的格律制度。结果被我找到了,可说是建立了起来,我写了新诗里第一首有意识的格律诗,并且是一首贝屈拉克体的商乃诗。[1]
在清静脱俗的“海天佛国”——普陀山,孙大雨朝闻晨钟梵音,夜伴莲池冷月,“两耳不闻寺外事,一心只悟商乃诗”。白天,游山逛水,领略海天佛国美丽的自然风光,晚上,面对着皎洁的月光,汹涌澎湃的大海,用英语吟诵名诗,回应大海的涛声。海涛看似无规律,无节奏,却有着内在的韵律和深沉的力量。在普陀寺,他读书、写诗,仔细地琢磨白话新诗与古典诗在思想内容与情感形式上的联系、区别,以及古典诗歌、白话新诗与外国诗歌,主要是与英语诗歌之间的内在关联。终于,有一天,他灵感顿发,摸索出了一套关于新诗新的格律形式,那就是他从白话新诗这一独特的形式规范中,发现了汉语诗歌内在的节奏性问题——音组。*所谓“音组”,按照孙大雨的解释,即是以两个或三个汉字为常数而有相应的不同变化的结构来体现新诗的内在意蕴和节奏、韵律。它有别于英文格律诗中的“feet”,而是基于汉语的意蕴而生成的一种格律。因此,孙大雨不同意闻一多将“feet”译为“音尺”的说法,认为所谓“音尺”(feet)实为“音步”,最多是一种外在的格律形式规范,与他主张的“音组”有很大的区别。参见:《孙大雨诗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他认为,音组才是以白话汉语,也就是以现代汉语为主导的新诗韵律形式,它是打通古典诗歌(古代汉语诗歌)和外国诗歌(主要是英语诗歌)内在关联的一个重要关键点。他后来以《黎琊王》(今通译《李尔王》,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一段译诗为例,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
听啊, 造化, 亲爱的女神, 请你听!
要是你 原想 叫这 东西 有子息,
请拨转 念头, 使她 永不能 生产;
毁坏她 孕育的 器官, 别让这 逆天
背理的 贱身 生一个 孩儿 增光彩!
孙大雨指出,在这首诗中,首先是由两、三个汉字作为“常数”来进行句式上的变化,一般每句都有五个音组;其次,以“音组”这种语言韵律、节奏的方式,可以更好传达出源自内心的思想情感,不会流于标语口号式的空喊和过于直白的言说。在他看来,就像大海内蕴着自身韵律一样,每一首诗的构成要素,应主要是它的“情致、意境、风格和音组”,而音组就如同富有韵律和节奏的涛声把大海的力量展示出来一样,也把诗的情致、意境、和风格展示出来。如果把诗歌比作为人,那么,情致相当于人的精神和生命,意境相当于人的肢干轮廓,风格则为人的仪态风姿,而音组则是人发出的声音行动。*参见孙大雨:《诗·诗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页。
也许是汹涌澎湃的大海节奏和海天佛国的宁静,从“动”与“静”两个既不相同又彼此密切关联的方面,给了孙大雨追求“爱”与“美”的人生和艺术理想的情感体悟,给了他致力于探讨白话新诗内在韵律的灵感和智慧。在短短的两个来月里,孙大雨以诗人特有的激情、睿智和源自生命情感冲动及其所产生的灵感,对白话新诗的格律终于有了大智大悟。当他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发现了白话新诗的这个新的格律后,感到异常的兴奋,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从普陀山返回北京,迫不及待地要和诗友们交流、分享。在得到诗友们的肯定之后,他开始自觉地运用音组理论来创作诗歌,先后写出了《诀绝》《爱》等三首中国式的十四行诗。他首先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爱》:*刊于1926年4月10日《晨报副刊·诗镌》,署名“孙子潜”,早于闻一多的第一首格律体新诗《死水》(1926年4月15日《晨报副刊·诗镌》3号)。
往常的 天幕 是顶 无忧的 华盖,
往常的 大地 永远 肆意地 平张;
往常时 摩天的 山岭 在我 身旁
屹立,长河 在奔腾, 大海 在澎湃;
往常时 天上 描着 新灵的 云影,
风暴 同惊雷 快活得 像要 疯狂;
还有 青田 连白水,古木 和平荒;
一片 清明, 一片 无边沿 的晴霭;
可是 如今,日夜是 一样地 运行,
星辰底 旋转 并未曾 丝毫 变换,
早晨 带了 希望来, 落日底 余辉
留下 沉思, 一切都 照旧地 欢欣;
为何 这世界 又平添 一层 灿烂?
因为 我掌中 握着 生命底 权威!
据专家后来的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首格律严谨的十四行体诗,也是孙大雨有意识地用“音组”格律体来创作新诗的一次重要的实践。特别是他将十四行诗的“音组”格律理论直接运用于新诗创作实践,并取得了成功,获得了认可。从中国新诗创作发展历程来看,孙大雨的“音组”理论是具有创意和创新精神的。如果说古典格律诗以古汉语的单音节的字作为词来传达诗意,那么,现代白话新诗就是以现代汉语的双音节的词作为最小的表意单位来构成诗歌的抒情结构和形式格律。换言之,这也就是说孙大雨所倡导的新诗,格律就是由“音组”这种最小的音顿和节奏单位,通过诗歌的内在而特定的“秩序”来构成诗行,再由诗行发展为诗节、诗篇,形成新诗的格律、节奏和韵律。这样,孙大雨的“音组”说,就为建立白话新诗的新格律规范,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思路和实践方式。
孙大雨对新诗格律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与理解,这在他创作的《决绝》一诗中有充分而体现:
天地 竟然 老朽得 这么 不堪!
我怕 世界 就要 吐出 他最后
一口 气息。 无怪 老天 要破旧,
唉,白云 收尽了 向来的 灿烂,
太阳 暗得 像死尸的 白眼 一般,
肥圆的 山岭 变幻得 像一列 焦瘤,
没有了 林木 和林中 啼缘的 猿猴,
也不再 有山泉 对着 好鸟 清谈。
大风 抱着 几根 石骨 在摩娑,
海潮 披散了 满头 满背的 白发,
悄悄 退到 沙滩下 独自 叹息
去了: 就此 结束了 她千古的 喧哗,
就此 也开始 天地和 万有的 永劫。
为的 都是她 向我 道了一声 决绝!
全诗严格按照十四行的格律而创作,每行五个音组,形成鲜明的节奏。前八行分为两节,每节第一、四行与第二、三行押韵,后六行转韵,并以“弱声字”押脚韵而结束。这样的建行、音组和押韵,为新诗克服那种无结构的散乱、无章的自由状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在诗歌的最后二行处,语句和语气都是突然转折,同时又在急转处作结,从而形成“道了一声决绝”声的震撼效果。当然,前面所作的情感抒发,都为这最后两行的转折进行了内在的铺垫,作了一种情感上的“蓄势”。
在孙大雨看来,这就是他所要倡导的新诗格律、节奏和结构,因为它有助于克服新诗在情感抒发过程中的无序、泛滥的现象,像郭沫若的《女神》那样:“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欢唱、欢唱、欢唱”,虽然有情感的气势,但毕竟缺少诗歌的音顿、节奏和内在韵律,长期下去,自然就会造成新诗流于标语口号式的空泛、苍白,缺乏诗歌独有的艺术感染力。他从英语十四行诗中的起承转合和中国古代诗歌格律规范中获得启示,使诗每行五个音组,形成明快的节奏,让新诗的建行、音组和押韵等都有格律可循,而不是放任情感的无序流动和抒发,使新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过于自由散漫,无格律可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大雨为新诗构建新的格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他看来,早期的新诗形式自由散漫,毫无节制,是诗歌滥情的表现,也是对浪漫主义抒情的误解。那种以为浪漫主义诗歌就可以不加节制的情感抒发,可以没有格律、结构和形式规范的观点,才是新诗发展的最大障碍。孙大雨和后来的“新月”同仁们主张把诗歌的抒情放在特定的格律里来进行,展现新诗的内在韵律,在当时的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由此形成一种新的诗风,消除了一些人认为新诗可以任意而为的看法,写诗的草率态度也开始好转,自由散漫和滥情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一批年轻的诗人也在这个艺术阶梯上逐渐地成长起来。
从追求“爱”与“美”的人生和艺术理想来说,孙大雨对新诗的探索,不仅仅只是源自他对诗歌的单纯爱好,更重要的还是诗歌这种抒情的方式,能够充分地抒发他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新的人生理想。他的诗歌创作,总是具有一种内在的气势、激情和审美的活力,气势恢宏,格调雅致,境界高尚,像《诀绝》一诗,大多用的是具有恢宏气派的“天地”、“世界”、“白云”、“太阳”、“山岭”、“树林”、“大风”、“海潮”等意象,“千古的喧哗”、“天地和万有的永劫”的情感抒发,使他的诗歌韵律雄浑、厚实,有着大海般的深沉力量,充分地表现出他对于人生“爱”与“美”的理想追求,如同梁宗岱在《诗与真》的《论诗》中所评价的那样:“单就孙大雨的《诀绝》而论,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不绝的十四行诗,作者底手腕已有不可及之处,虽然因诗体底关系,节奏尚未能十分灵活,音韵尚未能十分铿锵。但是题目是决绝,内容是决绝后天地变色,山川改容;读者的印象如何呢?我们可曾感到作者底绝望或进而与作者同情,同感么?”梁宗岱还深情地指出:“我也知道最高的文艺所引动的情感多少是比实际美化或柔化了的!济慈底Isabella那么悲惨的故事,我们读后心头总留着一缕温馨;莎翁底黑墨墨的悲剧《李尔王》(King Lear),结局还剩下Duke of Albany,Edgar,几个善良的分子作慰藉,我们从人心最下层地狱流了一大把冷汗出来后的一线微光,正如梁山泊底卢俊义从弥天浩劫的恶梦在一个青天白日的世界里醒来一样。但是,怎么!读了《诀绝》之后我们底心弦连最微弱的震动都没有!我们只看见作者卖气力去描写一个绝望的人心目中的天地,而感不着最纤细的绝望底血脉在诗句里流动!更不消说做到那每个字同时是声是色是义,而这声这色这义同时启示一个境界,正如瓦格(Wagner)底歌剧里一萧一笛一弦(瓦格尼以前的合奏乐往往只是一种乐器作主,其余的陪衬)都合奏着同一的情调一般,那天衣无缝,灵肉一致的完美的诗了!”*梁宗岱:《论诗》,《诗刊》1931年4月第2期。唐弢先生也特别推崇《诀绝》,他说:“我爱闻一多的《奇迹》、孙大雨的《诀绝》……”。此外,卞之琳认为:“也只有孙大雨写了几首格律严整的十四行诗。”朱光潜也说:“有一派新诗作者,在每行规定顿数,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便是好例。” 参见:徐鲁《最后的月光——新月派诗人孙大雨》,《现代文人的背影》,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社(台湾)2010年版。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而产生的,它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五四”新文学的海洋里,孙大雨的诗歌就是这海洋的一朵浪花,他的诗歌创作也是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影响下,个人的兴趣爱好与时代潮流和发展相对接、相对应的结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革命,然而,在“破”旧“立”新的同时,新的价值理想与新的终极关怀又在哪里呢?“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先驱者们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孙大雨的诗歌创作也汇入了这种思考的洪流之中,这也是他的诗歌坚持“爱”与“美”的人生和艺术理想的重要原因。从文明发展的维度来看,在文化转型之际,传统的精神偶像被打倒,新的终极关怀尚未建立之时,人的精神世界就往往会处在无所适从、无所凭借的境地,心灵在漂泊,精神在流浪,生命无所皈依。著名的诗歌理论家孙玉石先生曾以“内心痛苦与失落的叹息”为题,分析了孙大雨的《诀绝》一诗,指出了他的诗歌创作体现这种时代思考的原因。[2]可以说,新文学的先驱者们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通过各种方式留下了这种思考新的人生意义的精神烙印,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学创作为什么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新文学的作家看来,探寻新的人生意义和人生理想,目的就是要给予处在新旧交替的现代中国人以新的人生价值关怀和新的人生意义的领悟。孙大雨诗歌创作坚持“爱”与“美”的人生与艺术理想,正是吻合了“五四”新文化发展的主流,从而显示出他的新诗创作的独特价值。
三
1926年8月下旬的一天,孙大雨乘“麦钦莱总统号”(Mckinley)油轮开始了赴美留学的行程。海上的生活既风光无限,又显得单调乏味。只身一人离开艰辛抚养自己长大的孤独老母,离开生养自己的这一片土地,无限的思念涌上他的心头,不禁潸然泪下。站在甲板上,他遥望一望无际的大海和高远的蓝天,思绪也随着海风飘荡起来,碧海、蓝天、流云、船上的旅人,……他憧憬着大洋彼岸的学习生活,不禁文思涌动,诗性勃发,于是挥毫写下了充满豪情的诗篇《海上歌》: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看海上的破黎。/ 破黎张着一顶嫩青篷;/ 太阳出在篷东,/ 月亮落在篷西,/ 点点滴滴的大星儿渐渐消翳。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看海上的风波。/ 浪头好比千万座高山;/ 大山是一声喊,/小山是一阵歌,/ 山坳里不时浮出几只海天鹅。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游水底的宫廷。/ 龙皇生满一身的毛发,/ 鲨鱼披着银甲,/ 星鱼衔着银灯,/ 响螺同海蚌在石窟底下吹笙。
我要到海上去,/ 哈哈!/ 我要会海上的神仙。/ 神仙不知道住在何方:/ 好像是在海上,/ 好像是在天边—— / 我寻了许久寻到虚无缥缈间。
这首诗后来刊发在1928年10月10日《新月》月刊第2期(第1卷第7号)上,全诗4节,每节7行,以大海为抒情对象,不仅表达了他人生的远大志向,同时也非常注意诗歌的形式之美,*1980年台湾诗人舒兰(戴书训)评论这首诗的特点是:“很旷达深远,不失新诗中清新脱俗的情趣,在诗人的角色中,他的确……很成功。”参见:舒兰《北伐前后的新诗作家和作品》,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也是他所提出的“音组”理论的一次真正的创作实践。
在“新月”诗派提倡新诗格律当中,孙大雨不同意闻一多的“音尺”说和饶孟侃的“音节”说,他主张诗可以不押韵,但必须有“音组”,因为它是“一切诗歌的韵律方面的骨干,只有韵文里才有它”,可以保持新诗内在的节奏,显示出新诗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他看来,新诗所必须有的是“整齐的语体韵文的节奏所赖以体现的音组”,而“音组乃是音节的有秩序的进行。”[3](P46)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新月》第3卷第10期上,他发表的题为《一支芦笛》的诗,印证自己的诗学观点:
自从 我有了 这一支 芦笛,/ 总是 坐守着 黄昏 看天明,/ 又望得 西天 乌乌的 发黑:/ 从来 我不曾 吹弄过 一声,/ 我生怕 人天 各界 要心惊。
我只须 轻轻地 吹上 一声,/ 文风,苍鹰,与负天 的鹏鸟,/ 山中 海上 不经见 的奇禽,/ 经不起 这一声 青芦 号召,/ 都会 飞舞着 纷纷的 来朝。
要是 我随口 吹上了 两声,/ 不知 要吹出 几多的 懊恼,/ 几多 骇人的 失望 与欢欣,/ 萧霜的 白发 会回复 年少,/ 少年人 顿时 变成了 衰老。
我假如 放胆 吹得 第三声,/ 就有 阵阵的 天风 高缅藐,/ 吹落 那一天 的日月 星辰,/ 吹得 长虹 四窜兮 仙山倒,/ 弥勒 拍手兮 麻姑 哈哈笑。
自从 我有了 这一支 芦笛,/ 总是 坐守着 黄昏 看天明,/ 又望得 西天 乌乌的 发黑:/ 从来 我不曾 吹弄过 一声,/ 我生怕 人天 各界 要心惊。
全诗的每一诗句都是由不同的二字组、三字组构成,对“意象”的选择也具有古典的高贵、雅致风味,如“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这种意象的运用,加上富有韵律的“音组”节奏,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神秘、深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富有深厚的底蕴。后来,他还用自己的翻译进行举例,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在孙大雨看来,素体韵文的诗是“不押脚韵”的韵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有“音组”,进而就有内在整齐的节奏,虽然不押脚韵,却不是漫无法度的散文断片,而是有着诗的内在韵律和节奏。他认为,语言中存在“通常一个词或一个语式往往凝结两三个字(语音)在一起的那个意义或文法所造成的语音关系”,写作者便是要充分“利用了这语音之间的粘着性”。后来,他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一文中进一步强调:“我必须声明我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自由诗’,只是说有些人无条件地反对格律诗,认为写‘自由诗’方是正路,写格律诗便是封建,乃是完全错误的。我主张散文、散文诗、自由韵文和格律诗,都可以随各人的喜爱,自由写作,不过对于这四种写法如果想做一个科学的认识,应当知道散文诗和自由韵文只是散文和诗歌(即格律诗)二者中间的交界地带,而不是和格律诗势均力敌、平分诗国秋色的写作方式。我并未否定惠特曼,只是批评他,说他在形式方面是西欧和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开端,说他的作品混乱了诗歌与散文的形式,或者说,摧毁了诗歌的形式,如此而已。”[3](P151)
平心而论,无论是闻一多的“音尺”说,饶孟侃的“音节”说,实际上与孙大雨的“音组”都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他们的诗学观点所不同的是,各自切入的角度和认识、思考的路径不大相同。闻一多以“音尺”为基础,要求新诗具有“节的匀称 ”和“句的均齐”的诗歌形体的“建筑美”,但真正地实践起来,又不免会过于的机械,毕竟是白话作诗,不是文言作诗,过于机械的“音尺”,有时就会出现“麻将牌”和“豆腐干”的形式僵硬诗作。孙大雨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在一篇回忆朱湘的文章中说:“朱湘也是格律体新诗的赞同者和实行者,但他囿于所谓建筑美而创立的一种每行字数划一的诗体则被后人诟病为豆腐干诗。”[4]而按照他的“音组”理论进行新诗创作,虽然强调每行的音组数大致相同,但并不要求每行字数完全相等,这样对新诗的格律进行有效的艺术规约,就能够避免“麻将牌”式和“豆腐干”的创作尴尬了。他坚持认为,诗如果“只有格律没有变换,读者就会因过于矫揉造作、拘泥形式而感到腻烦;如果以变换为主,做得过火,诗行最后势必变为散文。” 为此,他非常赞赏布里奇斯的说法:“说到韵律就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那就是一般的韵律应该是人们所熟悉和热爱的,这可以说是基本规律,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的听觉便会感到不满足而希望这种韵律应该要有所突破。如果有人会对单一的韵律产生迷恋或满足且不允许有变换的话,那只能说他们缺乏对鉴赏韵律的天赋了。真正懂得并热爱韵律的人会觉得如果没有一定自由度的变换,就不能称为韵律,也就是说,只有在单一的韵律有所突破、有所变换时,韵律才能真正地开始显示出内在的美。”[5](P634-635)孙大雨以“音组”的方式来创立新诗格律,目的是为了提高新诗的艺术性,突出新诗的格律和结构,倡导一种与惠特曼的影响不大相同的“诗情诗意以及诗人们底人生态度”。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曾指出:“新诗的发生,在文字方面讲,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但新诗之所谓新者,不仅在文字方面,即形体上艺术上亦与旧诗有不同处。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试取近年来的新诗以观,在体裁方面一反‘绝句’,‘律诗’,‘排韵’等旧诗体裁,所谓新的体裁者亦不是‘古诗’,‘乐府’,而是‘十四行体’,‘排句体’,‘颂赞体’……,大多数采用的‘自由诗体’。写法则分段分行,有一行一读,亦有两行一读。……同时在艺术上也日趋于洋化。”[6](P8)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维度来说,“新月”诗派对新诗格律理论的建构,特别是孙大雨的“音组”理论的创立,为推动中国新诗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方面,孙大雨的功绩不可抹杀。
[1] 孙大雨.我与诗[N].新民晚报,1988-02-21.
[2] 孙玉石.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孙大雨.诗·诗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
[4] 孙大雨.我与朱湘[N].济南日报,1993-08-07.
[5] 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 梁实秋.梁实秋自选集[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
OnSunDayu’sOceanPoetryandtheTheoreticalof“SoundGroup”FormationforChineseNewPoetry
HUANG Jian
(Depar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Sun Dayu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Crescent” School. He has had a hard life, and the number of poems he has written is not much, but his poems hav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demonstrate writing strength for new poetry. In particular, His the new poetry “sound group” formation theory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and it has a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spirit. Its characteristic is advocated by “panels”—— the smallest sound and rhythm as the unit which helps to form the inner poetry order, poetry lines, poetry section and poetry chapter so that a unique rhythm of new poems can be achieved, thus to establish a new standard for new poetry and provide a constructive way of thinking and practice.
Sun Dayu; the ocean poetry; “sound group”; rhythm
I226.1
A
1009-1734(2016)11-0016-09
2017-09-27
黄健,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陈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