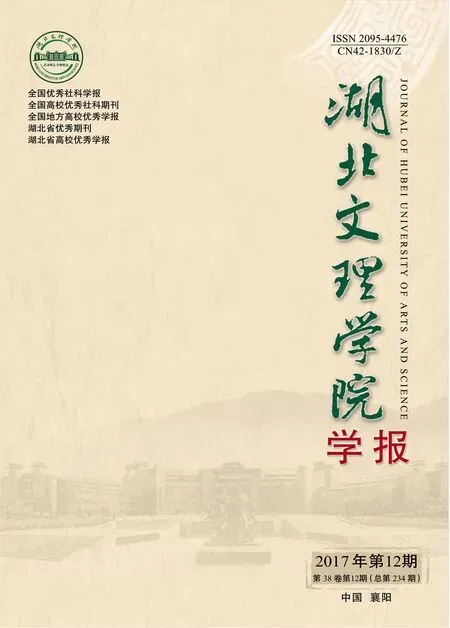邪恶美学与邪恶伦理
——论伊格尔顿对“邪恶”话题的探讨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
邪恶美学与邪恶伦理
——论伊格尔顿对“邪恶”话题的探讨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
为了弥补文化理论家的缺陷,并回应当代社会中新的邪恶现象,围绕邪恶话题,伊格尔顿在多本著作中,从美学、现代性与恐怖主义等几个层面展开讨论。邪恶与美学关系密切,不仅因为在悲剧思想中负载共同体罪恶的替罪羊历史悠久,邪恶主题在经典作品中屡屡出现,还因为邪恶的创造性、以其自身为目的的特征等都与审美存在共同点。现代性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惊人的邪恶一面。不应满足于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还应具体分析其背后的伦理与政治问题。
伊格尔顿;邪恶美学;邪恶伦理
I01
A
2095-4476(2017)12-0039-04
2017-08-28;
2017-10-17
王 伟(1977—),男,安徽砀山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博士。
身为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心中有数,讨论邪恶这样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问题,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依然执着地沉浸于邪恶话题,而且乐此不疲。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试图弥补文化理论家的短板。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先是肯定了文化理论取得的成绩。譬如,开辟了性别与性欲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且不乏给人启示的洞见。尽管如此,伊格尔顿还是对左翼文化理论心存不满,认为它不能总是纠缠于一些不可或缺的话题——如性别、阶级与种族——之上,而应正视被它所忽略的、那些看似过时的论题。譬如,道德、真理、死亡、邪恶、苦难,如此等等。否则,就很可能一直困于既有的偏见或成见之中,难以扩大理论视野。其二,回应当代社会中新的邪恶现象。伊格尔顿认为,邪恶并没有一个形而上的不变定义,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时代意义。具体分析这种意义,解释邪恶在新的语境下的种种表现,而非简单地将其归入邪恶之列就万事大吉,是知识分子理应担负的责任。基于上述考虑,伊格尔顿在多本著作中,聚焦邪恶话题,从美学、现代性与恐怖主义等几个层面展开讨论。无疑,伊格尔顿所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伊格尔顿对邪恶的现代性批判,二是伊格尔顿的神学转向,三是伊格尔顿重建文化理论的策略,四是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政治”批评,五是邪恶的语言维度。[1-5]由此不难看出,从美学与伦理视角对伊格尔顿的邪恶论述进行阐发还有待加强。众所周知,从建立伊始,美学就并非单纯研究美的学科,因为人的自由与价值一直是它密切关注的主题。换言之,美学与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保持着强劲的互动关系。尽管后现代美学确有以美学取代伦理学的倾向,但伊格尔顿仍然坚持两者的关联传统,从美学入手探讨邪恶的前世今生,而落脚点却始终是邪恶的伦理问题。
一、邪恶与美学
邪恶与美学密切相连,首先因为悲剧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替罪羊传统,以至于伊格尔顿认为悲剧的最佳翻译为“替罪羊之歌”。即便把悲剧起源的问题放在一边,至少对于某种类型的悲剧而言,替罪羊的形象本身也是不可或缺。“替罪羊在象征意义上负载着共同体的罪恶”,意味着“一种神圣的恐惧”,“一种更加积极形态的活着的邪恶之死”。[6]293换句话说,作为献祭的祭品,替罪羊既让人敬而远之,又让人心生敬畏。通过杀害或驱逐替罪羊,共同体得以救赎自己的罪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堪称典型的悲剧性替罪羊。伊格尔顿认为,虽然存在很多没有替罪羊的悲剧,但“对献身观念的怀疑不那么容易消除,尤其是在行为的主要人物是妇女的情况下”。[6]305譬如,霍桑《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即是如此。伊格尔顿指出,她是一个被逐出共同体的祭品,但她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人性,因此,她又是一个神圣的罪人。一方面,她不被社会的道德机构所接纳,游荡于道德的荒野,成为男男女女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与普通的女性迥然相异,她佩戴的红字表征着能力与越界,她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一种超越父权压迫的努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着眼于悲剧艺术之外,伊格尔顿还联系时代政治来谈替罪羊。如果说,传统的替罪羊可以被当作卸载集体罪行的客体,被逐出城外,那么,“现代替罪羊对于将其排斥在外的城邦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它不是一个关乎几个受雇乞丐或囚犯的问题,而是关乎全部挣血汗钱、无家可归者的问题。”[6]309他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面前,身受剥削的弱势群体都是替罪羊。不言而喻,为了改变日益加深的贫困,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贪婪的资本结构必须被打破。正因如此,伊格尔顿指责文化左派纸上谈兵,泯灭了革命热情。
其次,邪恶是文学经典经常涉及的主题。在《论邪恶》一著中,伊格尔顿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文学经典中的邪恶。其中,威廉·戈尔丁的小说《品彻·马丁》,描绘了马丁竭力拒绝死亡的故事。马丁是一名低级的海军军官,此人贪婪、淫邪、控制欲极强。在作战时,落水的马丁被海浪冲到一块礁石上,他“以惊人的求生欲望和极端自私的邪恶本性与死亡抗争”。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马丁的躯体已然死去,那个仍在进行抗争的是其不甘的灵魂。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邪恶包括了肉体与精神的分裂——代表了统治与毁灭的抽象意志,与这意志所栖居的无意义的血肉之躯的分裂”。[7]43通过展示马丁在礁石上备受折磨的过程,作家意在凸显一个罪恶的灵魂在炼狱中所应受到的惩罚。伊格尔顿认为,戈尔丁的很多小说都与原罪相关。譬如,《蝇王》中,建构文明秩序的努力终被暴力与宗派主义摧毁,由此揭示了人性的黑暗;《继承者》则对比原始人与新人的文化差异,描绘了人类向上的堕落;而《自由堕落》以回忆的笔触,展现了人性之恶。此外,在伊格尔顿看来,弗莱恩·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是一则关于地狱的寓言,表现了邪恶的诸多特征:异乎寻常、低劣不实、肤浅、欠缺生命向度、精神麻木等等;而格兰汉姆·格林的小说《布莱顿硬糖》,则刻画了一个彻底邪恶之人,提醒人们思索邪恶与善良之间的隐秘纠结,如此等等。
再次,某种程度上,邪恶与美学共享一些特征。众所周知,审美不是仅仅机械地反映现实,富有独特的创造才是其让人交口称赞的更高境界。邪恶也有很强的创造力,伊格尔顿指出:“恶魔对创造兴趣浓厚”,“魔鬼之以其邪恶的方式具有创造性,就如同神的力量会具有毁灭性一样”。[6]263实质上,这种创造性并非通常的创造性,而是魔鬼的颠倒镜像。不仅如此,这种创造与审美一样,都以自身为目的。伊格尔顿以纳粹集中营为例,强调“邪恶并不简单地就是不道德的事情,而且也是在人类的痛苦和伤害中获得能动的施虐快感的事情,这种施虐快感明显沉溺于以这种伤害本身为目的的过程中”。[8]换言之,若是从经济或军事的角度来看,纳粹集中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可以采取更为便捷、省时省力的残害方式。而令人惊骇的地方恰恰在于,纳粹的邪恶不以实用功利为主要目的。有意思的是,那位经常遭到伊格尔顿嘲讽的美国哲学家罗蒂,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罗蒂认为,韩波特与金博特这两个人物是纳博科夫有关残酷的作品的核心,这种残酷并非希特勒式的,“而是指那些善于美感喜乐的人也可能会犯的一种特殊的残酷”。[9]即是说,聃于审美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从而陷入邪恶的渊薮。
二、邪恶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影响,众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讨论甚多。在借鉴韦伯、马克思、本雅明等人论述的基础上,伊格尔顿认为应辩证看待这一问题,否则,就无法把握现代性的两面性,要么过分拔高某一方面,要么有意回避另一方面。“在当代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强调现代性乃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革命性进步,而且它还以同等的热情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场漫长的屠杀和剥削的噩梦。似乎没有任何其他思潮能够让这两种描述处于紧张之中,既要面对贵族的怀旧情绪,又要面对极度的进步主义或后现代的健忘症。可是,把握着现代性之答案的,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必要关系。”[6]255换句话说,现代性成就斐然,但它带来的邪恶也罄竹难书。关键在于,不能只盯着后者而哀伤地怀恋过去的好日子,或者,被成功的喜悦冲昏头脑,不愿直面或者轻视现代性的负面能量。如果说,前者是一味向后看的怀旧主义,那么,后者则是一味往前看的盲目乐观主义。显而易见,两者是两种迥然相异的历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攻讦、难分难解。其实,由于未能在共时的结构中看待问题,它们都不免堕入片面的泥沼。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过去成为衡量现今的理想标杆时,应予追问的是,这种过去是怎样的过去,人们是否愿意接纳与其同时的其他部分。而当历史被视为奔向进步、光明前程的线性过程时,则需拷问现代性的阴暗面何以被低估或漠视。
回顾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东西方阵营之间的长期对立,还是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都给男男女女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灾难。因此,对伊格尔顿而言,善良与邪恶是一种悲剧性共存。更准确地说,除了较为短暂的状况之外,美德甚至很难在公共事务中得以发展,而往往被限定于私人领域中发荣滋长。因为“大多数的人类文化都已经变成了掠夺、贪婪、剥削的叙事。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喧嚣世纪,已经被无止境的鲜血所玷污,已经被数以万计不必要的牺牲所标记。”[7]197换言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前者滋生邪恶的可能性更多,危害性也更大。因此,面对种种邪恶事件,伊格尔顿更注重考察邪恶生成的外部缘由,而非个体邪恶的内在本性。应该说,这也是其《论邪恶》一著的运思方式。伊格尔顿坦言,这种方式针对两种错误的流行性看法:一是认为若是行为可以解释,那就不再是邪恶的;二是认为若是行为邪恶,那就无法对其进行判断。伊格尔顿承认,就算不少男女与生俱来的邪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的邪恶都是体制性的”,作恶者“都是既定利益以及隐秘操控的结果,而不是个体恶意行动的后果”,“大部分的恶性都深深地嵌套在我们的社会系统之中,为这些系统所服务的个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行动的严重性”。[7]193如此一来,邪恶就主要不是如康德所言的那样,源于自我的放任。沿着同样的道路,阿伦特得出了“平庸之恶”的结论。她认为,邪恶的恐怖在于“思想的轻信或缺乏”“对习俗的抵制、停止和组织所有批判性的质问和怀疑”“缺乏内心的自我对话”等。[10]这就可以充分解释,为何参与纳粹大屠杀的男男女女,都是普通人而非恶魔。
值得留意的是,讨论现代邪恶时,有学者以是否能激起人类的恐惧感与崇高感为标准,将其分为“好的邪恶”与“坏的邪恶”两类,并将它们分别等同于康德的“根本之恶”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前者因为以自身为目的,或者说,为邪恶而邪恶,所以“让人莫名其妙地喜欢”,而后者则因无以激起人类的恐惧感,令人生厌。[11]上述分类与对应的好恶,都可以推敲。具体而言,当论者谈论好的邪恶时,肯定性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一段话:大屠杀“以毫无意义的行为、折磨和被折磨、因自身原因毁灭、及其憎恨世界和对其自己受轻视的存在怀有极大仇恨的人类为乐”。[6]269既然如此,那么,这会让谁喜欢?是否需要付出那样的代价,让男男女女来体验恐惧感?再有,平庸之恶与恐惧感并非相互绝缘,相反,在纳粹大屠杀中还扮演着更让人恐惧的功能。可以补充的是,伊格尔顿确有谈及邪恶的两幅面孔,而且是天使与恶魔形态的邪恶。“前者压制其自身存在之缺乏,后者则得益于它。值得注意的是,纳粹主义将这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6]275可以看出,它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区分。
三、邪恶与恐怖主义
对于恐怖主义行为与美国的解决措施,伊格尔顿都有态度鲜明的批评。就前者来说,恐怖主义代表了最为强烈的偏见与偏执,是宗教本质主义。很大程度上,它们受到邪恶的、落后的意识形态的暗中支配。就后者而言,美国用恐怖或暴力的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不仅不可能彻底消灭邪恶,而且还会招致愈来愈多的恐怖,从而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痛苦。因为暴力固然能有效反击恐怖主义,但它同时又不断促进恐怖主义的生长。因此,伊格尔顿认为,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其实反倒将问题恶化,乃至“在不知不觉间,与你真正诅咒的野蛮串通一气”。换言之,这必将落入以暴制暴的怪圈,进而忽略恐怖行为发生的真正根源。伊格尔顿指出,对“911”事件,不能止步于邪恶的描述,而更应将其归罪于“阿拉伯世界在漫长的历史中,所遭受的西方政治上的凌辱,以及由此所累积的愤怒与羞辱”。[7]210-211也即是说,伊格尔顿提醒世人,这起事件既是他们政治不满、政治诉求的曲折表达,又是一次情感的宣泄与喷发。还须注意的是,美国的邪恶行径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杀害的平民数量是“911”事件中的几百倍。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避免类似邪恶事件的再次发生。在《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中,通过梳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史,展示它们在处理陌生人时遭遇的诸多麻烦,伊格尔顿最终诉诸马克思,给出了社会主义的互惠发展这一可行性方案。伊格尔顿宣称,“社会主义是恐怖的解毒剂”[12]50。他辛辣地嘲讽说,到了世贸大厦倒塌那一天,那些洋洋自得宣布历史终结的人,以及坚信资本主义永远胜利的人,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曾是那么的愚蠢。
到了《神圣的恐怖》一书,伊格尔顿则将恐怖主义追溯至前现代世界,从而揭示恐怖与神圣、暴力与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果没有抓住这种两面性,就不能理解恐怖的概念。恐怖起初是一种宗教观念,今天的许多恐怖分子依旧如此;宗教是深层的矛盾力量,同时使人狂喜和灭亡”。[12]4伊格尔顿把狄奥尼索斯归入最早的恐怖主义者之列,强调他在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同时,还有着难以平息的怨恨与攻击性。通过对比恐怖分子与绝食抗议者、自杀弹客、真正的殉道士等之间的异同,伊格尔顿断言他们都死于致命的意志,揭示了自由意志兼具创造性与毁灭性。有学者批评伊格尔顿此书没有政治倾向性,更为沉醉于恐怖的美学层面,而这不是一个因对文学做政治批评而知名的学者该做的事情。[12]91事实上,由于伊格尔顿主要是以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为例,来阐释、分析恐怖主义,因此,美学味道十足就在所不免。然而,这并未遮住伊格尔顿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
为了弥补文化理论家的缺陷,并回应当代社会中新的邪恶现象,围绕邪恶话题,伊格尔顿在多本著作中,从美学、现代性与恐怖主义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邪恶与美学关系密切,不仅因为负载共同体罪恶的替罪羊在悲剧思想中历史悠久,邪恶主题在经典作品中屡屡出现,还因为邪恶的创造性、以其自身为目的的特征等都与审美存在共同点。现代性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惊人的邪恶一面。不应满足于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还应具体分析其背后的伦理与政治问题。
[1]陶 蕾,佴荣本.伊格尔顿对邪恶的现代性批判[J].江淮论坛,2017(1):161 -166.
[2]刘 静.天主教激进神学的探讨——伊格尔顿神学转向的背景研究[J].社科纵横,2017(4):72-75.
[3]胡小燕.论伊格尔顿理论的重建策略[J].江西社会科学,2012(2):99 -103.
[4]林骊珠.邪恶与罪恶: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政治”批评探析[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2):313-321.
[5]王 健.通向暴力的“语言乌托邦”——论伊格尔顿关于“恶”的话题[J].文艺理论研究,2017(2):200 -205.
[6]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M].方 杰,方 宸,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8]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修订版.王 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396.
[9]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0.
[10]沃尔夫冈·霍尔.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69.
[11]肖 琼.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21.
[12]陈奇佳,张永清.左翼立场与悲剧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倪向阳)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