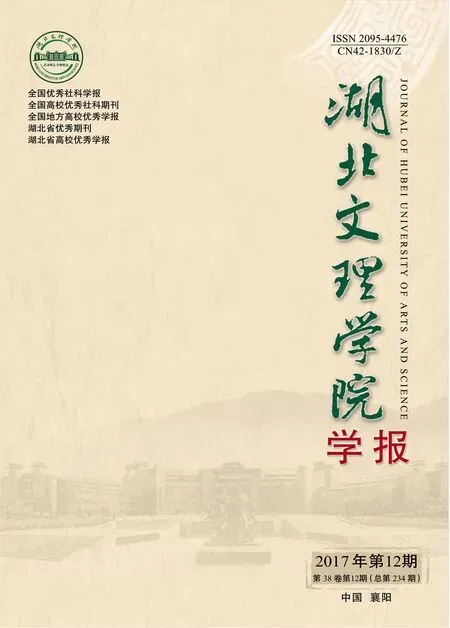《三国演义》明清序跋脞论
陈婧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三国演义》明清序跋脞论
陈婧玥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从早期嘉靖壬午本到最终定型的毛评本,明清人为《三国演义》撰写的序跋对其文本定位始终是带有道德教化作用的“羽翼信史”。在此基础上,明清序跋作者对《三国演义》文本的关注点逐渐衍生出新的旁支,《三国演义》文本内容的艺术价值日渐得到人们重视,并被概之以“奇”。序跋内容的重心偏移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紧密。通俗小说在官私目录中的类属缺失及基于艺术批评而建构的“奇书”统序,都标示着在杂文学观念的背景下,纯文学观念开始萌生。
《三国演义》;明清序跋;羽翼信史
I207.413
A
2095-4476(2017)12-0020-05
2017-08-23;
2017-09-29
陈婧玥(1993—),女,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明清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因“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①随缘下士.林兰香[M]//古本小说集成.据清道光十八年本衙藏板本影印本.逐渐形成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四种章回小说类型。其中,《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体小说的典范之作,内容取材于三国史实,是近于“史”而有别于“史”的典型文本。由于《三国演义》为世代累积型作品,因而版本众多。在《三国演义》现存的诸多版本中,每个版本几乎都带有相应的序跋文字,从早期嘉靖壬午本到最终定型的毛评本,序跋文字的价值判断直观体现出明清时人对《三国演义》文本的认识轨迹。因此,通过梳理《三国演义》明清序跋对于理解明清时期三国文本的认知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一、“羽翼信史”:《三国演义》的“史余”价值
从早期嘉靖壬午本到最终定型的毛评本,明清人为《三国演义》撰写的序跋对其文本定位始终是带有道德教化作用的“羽翼信史”,《三国演义》作为正史附庸而存在的“史余”价值一直为人所认可。
题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嘉靖壬午本是《三国演义》目前可见的最早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刻于嘉靖壬午年(1522年),前有蒋大器托名庸愚子于弘治甲寅年(1494年)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和张尚德托名修髯子于嘉靖壬午年(1522年)所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两篇序言,两篇文字虽成文时间相去二十余年,但序跋作者所给予《三国演义》的文本定位却不谋而合。其中,蒋大器认为《三国演义》一书“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1]232,将《三国演义》视为一种有别于正史的史书。张尚德则是在否定人们质疑《三国演义》“几近于赘”的基础上,指出《三国演义》的成书是为弥补“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而成,其成书目的在于达到“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的教化效果,因此他将《三国演义》定义为“羽翼信史”之书。[1]234由此可见,这两篇序言的作者都将《三国演义》定位在了“稗官野史”的层面,并指出《三国演义》有益于道德教化。
在这两篇序言中我们可以发现,序跋作者对于《三国演义》文本的“史余”价值持十分认可的态度。蒋大器在序文中谈及自身对于有益之书应是“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1]233可见,他推崇《三国演义》的动机也在于此书能使读者辨明忠奸善恶。对此,张尚德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更系统地阐明《三国演义》成书之于社会的重要意义:
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硕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櫽栝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1]234张氏认为,教化的核心要素是以“忠孝节义”为主的道德观,读者在读完《三国演义》后需领悟“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的是非道理,以此达到“裨益风教广且大”的教化效果[1]234。作为目前可见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嘉靖壬午本的序跋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在三国文本流传早期,明代时人已承认《三国演义》等讲史小说是具有辅助正史这种相对严肃的社会功能的。蒋大器、张尚德之后,明代李祥、吴翼登、博古生,清代李渔、毛宗岗等人所作序跋亦以“忠孝节义”作为三国文本重要批评标准。
《三国演义》的早期传播中,道德教化意义是时人眼中的主要文本价值,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统之必以正者为尊”[2]892的正统观,二是传统“忠孝节义”[1]234之说。在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序跋中,二者相互勾连,不可分割。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正统问题,所存序跋不约而同地倒向蜀汉政权一边,表现出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三国演义》嘉靖壬午本序言对待曹、刘的态度已相当明显:蒋大器定义曹操为“万古奸贼”,“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为身谋”;而赞刘备为“汉室之胄”,称蜀汉“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1]233。张尚德则直言《三国演义》教化人心之处正在于其“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的文本主张[1]234。其后,凡有《三国演义》序跋几乎都要在贬斥曹魏、孙吴政权的基础上为蜀汉正统正名一番。如李祥《三国志传序》云:“三强鼎峙,英雄迭出,然吴、魏僭窃,竟不能与蜀共居正统”[1]235;吴翼登《叙三国志传》亦称“抚昭烈帝之潜跃,按卧龙之终始惟以仁以义,无诈无虞。……曹鬼孙犬,何敢望其后尘”[2]892。如此等语,皆为正统观念驱动下的“拥刘反曹”。道德教化的价值判断始终贯穿于《三国演义》序跋,至清初,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也在开篇便强调“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且直言“正统者何?蜀汉是也”,以引起读者对三国政权正统性的重视[1]235。
虽然无法确定《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三国演义》文本的最早版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嘉靖壬午本无疑是《三国演义》早期流传的版本之一,其所存序跋代表着当时人们对三国文本的初期判断。在看待《三国演义》的文体归属上,序跋作者的认识并未脱离文学传统,张尚德仍将《三国演义》喻为“牛溲马勃”不入流之辈,但“羽翼信史”的文本评价显然是肯定了《三国演义》教化风俗民心的社会功能,因此《三国演义》虽为历史演义,仍“为世道重轻”[1]234。
二、奇书之“奇”:《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
在重视《三国演义》正统教化的同时,明清序跋作者对《三国演义》文本的关注点逐渐衍生出新的旁支,《三国演义》文本内容的艺术价值日渐得到人们重视,并被概之以“奇”。
明代后期,人们不再完全拘泥于对三国文本社会功能的深究,转而将《三国演义》的文学艺术价值纳入关注范围,从文本结构、人物塑造、艺术手法等方面解读《三国演义》。以人物品评为例,早期在正统观的统摄下,《三国演义》序跋评判文本人物仍以忠孝节义为纲,对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及其对于文本的重要意义几乎视而不见,以符合《三国演义》的道德标准。到李贽《三国志叙》时,李贽评骘人物高低的标准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文曰:
马来西亚测绘局(JUPEM)为了推进马来西亚空间数据基础设施(MyGDI)建设,于2002年12月设立了马来西亚地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中心(MaCGDI),归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与环境部(NER)领导,取代了之前的土地信息系统国家基础设施秘书处(NaLIS)。MaCGDI负责协调各级政府部门的地理空间信息存取与分发工作,确保能不间断地存取和使用最新的、最精确的地理空间数据。
乃吾所喜《三国》人物,则高雅若孔北海,狂肆若祢正平,清隐若庞德公,以至卓行之崔州平,心汉之徐元直,玄鉴之司马德操,皆未效尽才于时。[1]238
显然,李贽此言未以道德准绳臧否人物,他将“高雅”“狂肆”“清隐”“卓行”“心汉”“玄鉴”之类的个性标签与所好人物相匹配。这意味着,序跋作者的关注点已由人物道德品行转向人物形象的独特个性,并由此展开人物艺术层面的探索。
明末清初,金圣叹、李渔、毛宗岗等人所作序跋对《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解读明显增多。李渔《古本三国志序》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作品并称为“四大奇书”: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2]899
李渔明确指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之所以能并列为“四大奇书”,关键在于四部作品同为“奇书”典范,都将“奇”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而《三国演义》因从史传脱胎而来,“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2]899,其“奇”更有别于其他三者,因此李渔称“奇又莫奇于《三国》矣”[2]902。 《三国演义》被冠以“奇书”之名,可见《三国演义》在辅佐正史的“史余”价值之外,其作为稗官小说的“奇书”价值逐渐得到关注。随着《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不断挖掘,《三国演义》所具备的奇书之“奇”的特点频频出现在序跋内容中。清代莼史氏云:“《三国志演义》一书……夫文章莫不妙于平庸陈腐,而莫妙于奇”[2]907,穉明氏称“《三国志》之奇,固不若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之文之尤奇也。”[2]904如此等语都意味着《三国演义》艺术价值逐渐被发覆的过程。《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文体特征日益明显,其“史余”的教化作用为人所称道的同时,“四大奇书”的艺术价值也成为人们商榷的新热点。
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奇”,李渔在《古本三国志序》中有言:
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异代之争天下,其事较平,取其事以为传,其手又较庸,故迥不得与《三国》并也。[2]900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为一篇。[1]266
毛氏认为,《三国演义》叙事比之《史记》更难于把握,其难在于《三国演义》叙述的是历史事件,却通过叙事技巧将繁杂历史逐一列述,相当于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等类合为一篇。《三国演义》因而承续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两种传统,在行文中呈现出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一条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时序进行编年,一条对同一时间发生的多个事件进行加工处理。内容方面,《三国演义》对史实进行进一步的文学加工,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中的诸多“奇手”总结提炼为“追本穷源”“巧收幻结”“以宾衬主”“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星移斗转,雨覆风翻”“横云断岭,横桥锁溪”“将雪见霰、将雨闻雷”“浪后波纹、雨后霹霖”“寒冰破热,凉风扫尘”“笙箫夹鼓、琴瑟间钟”“隔年下种、先时伏着”“添丝补锦、移针匀绣”“近山浓抹、远树轻描”“奇峰对插、锦屏对峙”等笔法[1]258-266,使之更加系统化。
三、《三国演义》序跋内容与明清社会经济的关联
自宋以来,中国传统文学因市民文化的浸染呈现出一种雅俗共存的状态。在明清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雅俗共存的文学市场开始大规模地全面打开,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吸收,雅俗融合,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日渐兴盛。这一时期,基于通俗小说传播的需要,小说序跋的内容偏重也随之从单一的伦理说教迁移至更易于接受的文本艺术层面,形成以“奇”为核心的审美趋势。
明初,通俗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勾栏瓦肆间的口头说书,由于印刷业的落后,抄录誊写依然是人们获得小说文本的主要途径。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大幅改进,书坊业随之得到长足的发展。据瞿冕良先生《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收录,明代书坊数量从正德时期起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书坊规模也不断扩大,汲古阁等著名书坊相继涌现。杭州、湖州、苏州等江南一带更凭借运河优势而一跃成为全国书坊重镇。书坊业由此进入历史发展的巅峰。明中叶以来,由于“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3]1,通俗小说拥有了广阔的阅读市场。正德、嘉靖至万历年间,各地书坊为盈利,渐从明初偏重儒学著作转而刊刻通俗小说文本,一时间小说刊印蔚然成风,“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3]1。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不再是著书立说之举,转而成为商业销售的必备环节。
作为古代小说文本传播的重要一环,读者之于小说流传意义重大。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中云:
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4]282
由此可知,读者的需求是小说创作兴衰的主导因素。书坊主为保证收益,遂将如何满足受众需求视作小说刊刻的第一要务。明代中期,通俗小说读者的群体范围不断扩大,上至王公贵胄,下至普通百姓,均嗜好小说。在如此庞大的接受群体中,新崛起的市民阶层逐渐成为通俗小说的主要受众。以《三国演义》为例,明清序跋中所提到的读者阶层渐呈下移趋势。早期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附蒋大器序称:“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233这时的阅读主体由文人士大夫构成。至万历年间,周曰校在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识语中所提受众仍为“士君子”之流[2]890,而同时期的另一刊本《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中却开始出现“愚夫俗士”一类读者[2]892。到崇祯五年遗香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则直接将读者群体圈定为“愚夫愚妇”、“愚夫妇”等“目不识丁之流”[2]896-897。明代中期以后的读者主体构成,正如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所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5]213-214由于“农工商贩”这类读者的知识局限,正统思想主导下的伦理教化已经无法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故书坊主从读者审美心理出发,重新考察小说文本在教化之外的其他意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为世代累积型作品,文本内容因而保留了较明显的说话艺术特点,其中跌宕起伏的情节、环环相扣的描写往往是下层读者最为关注的地方。因此为迎合广大受众的审美需求,序跋作者开始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中以“奇”为核心的种种艺术表现,以此吸引广大受众,达到小说传播的目的。
另一方面,明初问世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相继刊印之后盈利甚厚,书坊主们基于商业利益纷纷趋之若鹜,市场竞争也随之愈加激烈。为使通俗小说得以畅销,明清书坊业在小说版本、小说评点、小说图像等方面推陈出新,通过多种销售策略提高销量。其中,小说评点作为书坊销售广告中的主要宣传手段,备受重视。著名的小说评点如袁无涯刊《水浒传》李贽评点本,贯华堂刊《水浒传》金圣叹评点本,世德堂刊《三国演义》毛纶、毛宗岗评点本等都因评点精当而使小说文本盛行于世。序跋作为小说评点的组成部分,对小说文本的售卖有直接的引导作用。序跋包含了执笔者对小说内容的评价、总结,集中反映出序跋作者的文本主张、喜恶偏好。相对于小说内容评点,序跋对读者购买小说的导向作用更大,故书坊在商业操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小说的序跋编写。明清时期,由于小说观念的内涵变迁,通俗小说文本中的文学艺术价值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读者对通俗小说的阅读期待更倾向于文本内容中“奇”的表现,序跋内容对小说之“奇”的偏重显然适应于市场趋势,对通俗小说的销售大有裨益。
四、明清奇书统序的建构与现代纯文学观的萌芽
明清序跋对《三国演义》文本艺术价值的关注使得以“奇”为核心的奇书观念成为这一时期评价小说的重要标准。虽然李渔在《古本三国志序》中以“经史”“词曲”“小说”这些目录学标准为依据确定“四大奇书”的实指作品,但纵观明清官私书目,通俗小说基本处于类属缺失的状态①如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均无著录通俗小说,更无专门类属。。而以“奇”为核心所建立的“奇书”统序,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这一缺失。同时,基于艺术批评而成的“奇书”统序也透露出杂文学观念的背景下,纯文学观念开始萌生的讯息。
《三国演义》序跋在以正统教化为主的“史余”价值之外,衍生出对文本艺术价值的关注与挖掘,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从审美角度发现通俗小说所共有的艺术特质,并概之以“奇”,“奇书”及其所指称的对象也随之进入了人们的关注视野。经过知识要素的不断积累,以“奇”为核心的“奇书”统序也逐渐形成。传统目录学之外衍生出的“奇书”统序,标志着杂文学观念下逐渐萌芽的纯文学观念雏形。中国传统杂文学观念对于文学的界定宽泛模糊,不仅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审美艺术特性,还过分强调其社会功能,在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文学的指称对象往往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传统目录学中的类属几乎都可以被纳入广义的文学之中。而纯文学观念所指称的对象范畴则相对狭义,不再与经、史等统序杂糅在一处,对于作品的关注点也从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更多地倾向文本艺术价值,明清时期人们对于“奇书”之“奇”的挖掘正是这种纯文学观念萌芽的最初表现。
实际上,“奇书”一词最初指称的是“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的道家之书,与小说并无关联。据《说文解字注》,“奇,异也。不群之谓。一曰不耦。”[6]204这就说明“奇”的所记录的内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直接的对应事件,因“奇”的本义带有“不群”“不耦”之意,故“奇书”在一段时间内常指晦涩难懂之书,如“所有奇书难字,众所惑者,随宜剖析,曲尽其源”[7]2595,所强调的就是书本内容的意蕴艰深。此外,“奇”又指“怪”“异”,据《说文解字注》,“异,分也。……徐锴曰:将欲与物,先分异之也。……又不同也。……又怪也。《释名》异者,异于常也。”[6]105“奇书”因此也带有不合常理、外门邪说的意味,遂有“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8]1111的说法。“奇书”与小说开始产生关联始见于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昏昏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9]1635-1636
袁宏道认为《水浒传》之“奇”,“奇”在文本“明白晓畅,语语家常”的行文特点,袁氏虽未明确使用“奇书”这一名称指代小说,但认定了“奇”与《水浒传》的文本特质存在一定必然联系。后明末张无咎因《玉娇梨》《金瓶梅》二书“另辟蹊径,曲终奏雅”,首次用“奇书”一词指称小说类别中的作品,“奇书”与“小说”间开始形成明确的指代关系[10]536。其后,随着“奇书”系统所囊括的知识要素不断堆叠累加,《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琵琶记》等一类书均被冠以“奇书”之名。奇书之“奇”作为古代通俗小说的重要特征,在知识要素的不断累积后,形成传统四部分类法之外的“奇书”统序。这一时期,“奇书”成为明清通俗小说的统称。
目录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治学的根基,具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1]1806的特点。在明清官私目录中,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和子部没有《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可归入的类属,而后来在人们对通俗小说艺术性的提炼与总结中出现的“奇书”统序,则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通俗小说一个类似于目录学意义的类属,使之“有家可归”。同时,“奇书”统序源于针对通俗小说的艺术批评,这也标示着在杂文学观念的历史背景下,纯文学观念开始萌芽,这是中国古典小说观念乃至整体文学观的一种发展与蜕变。
[1]朱一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2]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M]//冯梦龙,编.新列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叶 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许 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张无咎.三遂平妖传序[M]//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郑 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Argument 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Preface and Postscrip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Jing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From the early Jiajing Renwu version to the final Maoping versi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written by peop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r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are always “Yu Yi Xin Shi” with the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On this basis, focuses of the author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more ex⁃tensions on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The artistic value of the content of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has been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hich was quoted as “Qi”.The focus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has changed,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generic absence of popular novels in official and private catalogues as well as the“Qi Shu” system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criticism indicate the sprout of pure literature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mixed literature concept.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 Yi Xin Shi”
陈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