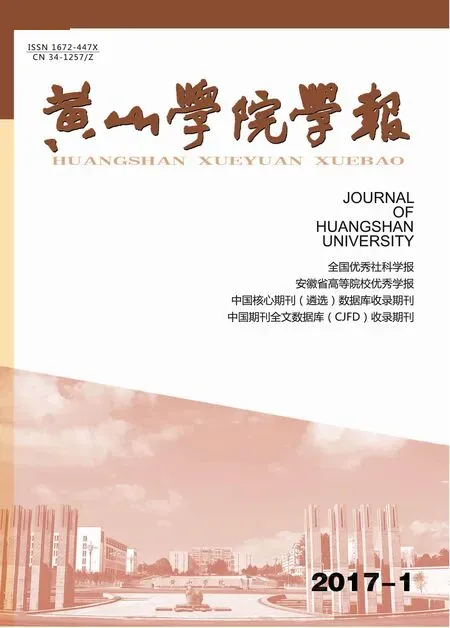《史记》为“文化复仇”之书辩
潘定武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文化·艺术
《史记》为“文化复仇”之书辩
潘定武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司马迁因受宫刑之辱,并有著名的“发愤著书”之论,但此“愤”字主要并非怨愤,更非私愤。将《史记》解作司马迁的文化复仇之书同样存在理解的偏颇。《史记》体现司马迁宏伟的著述宗旨,亦是作者经受挫辱之后人生价值的全部体现。如因宫刑之辱就认为其在著述中恣意发泄情感,甚至充满复仇心理,则难免偏离其既定的著述宗旨,降低《史记》的光辉价值。
《史记》;文化复仇;发愤著书;著述宗旨
一、问题的提出
司马迁因受宫刑之辱,有著名的“发愤著书”之论。对此“愤”字,历来颇有歧见,而多数都将其理解为“怨愤”或“愤懑”。虽然顾易生、蒋凡等人认为“司马迁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创作动力的‘怨愤’,主要的不是一己之私怨,更不是违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私愤”,[1]487但其实质强调的仍是怨愤。
新时期以来,陈桐生、过常宝等人又提出了司马迁借《史记》以实现其文化复仇的观点。陈桐生说:“对司马迁来说,这种伟大的事业就是《史记》著述,就是愤书。从愤书以洗刷耻辱这一角度来说,愤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复仇。”“司马迁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记述了历史上一个个艰辛卓绝可歌可泣的复仇故事,……他把极大的同情、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崇高的礼赞都给了复仇者,这些都是司马迁复仇心理的投射。”他又总结司马迁文化复仇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其动力来自于人生的困厄与耻辱;其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去忍受屈辱,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最辉煌的目标;其特征为一种不见诸流血行为的非暴力复仇;其对象不是具体、单一的个人,而是把复仇目光投向文化学术事业;其目的是要对此前所受耻辱实现补偿或过补偿。[2]124-129
过常宝则认为:“司马迁的‘发愤著述’实际上是指人生缺陷赋予作者以发泄愤懑的权利,而这样的著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复仇性就不难理解了。”“司马迁身怀史和士的双重理想,对先行文化制度展开了顽强的批判,那是挣扎,也是文化报复。”“司马迁对已经衰落的传统理念复仇,是在史官传统内部进行的,……他代表整个史官传统,向着独大的统治展开了猛烈的复仇。”“在复仇面前,司马迁将所有那些孝道、君臣之道、宗国之道,甚至信义、人格尊严等等都看做‘小义’,认为都是可以舍弃的。”“司马迁的复仇虽然有着强烈的个人因素,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化复仇,司马迁代表了悠久的史官传统对现实政权的复仇。”[3]366-386
两位学者虽然都将司马迁著《史记》视作文化复仇之举,但二人的理解有同有异。二人都认为遭受宫刑与司马迁著述态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亦即其文化复仇与其人生罹难直接相关。不过,陈桐生主要从司马迁受刑前后经历及个体身心发生巨大变化出发,认为其文化复仇主要是借著史之文化行为实现其人生目标,并借描写诸多复仇故事投射其复仇心理。过常宝则从中国原史文化的大背景出发,认为司马迁所代表的实际是原史文化传统,其在现实中遭遇巨大皇权统治,虽难以战胜,但仍力图以顽强的批判来进行文化复仇。
二、《史记》非“文化复仇”之书
首先,要承认“诗可以怨”,何况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遭受过宫刑的奇冤;但是更要真正了解司马迁父子的史官文化情怀。作为先秦以来的史官世家,尽管其家族先人的地位已今非昔比,所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少卿书》),但司马迁父子仍然以史职为重。司马谈自己早有论载天下史文的宏愿,又极看重其太史令掌史记事职责。元封元年(前110年),其因重病不得从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被其视为人生极大之憾恨。尤可注意且为人称道者,司马谈对其家族史学传承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在司马迁幼年时,司马谈就对其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培养,不但教导其子广从名师,博览群籍,而且令其子纵游天下,饱览山河。司马谈赍志而没,临终谆谆遗命,其中显现了对其子的高度了解与自信,更明确传达了一种史官文化责任。司马迁则俯首流涕,慨然受命,同样传达其与父亲一样具有清晰的史官文化意识与担当。有鉴于此,司马迁父子的著述虽非出于汉武帝明确的诏命,然则出于史官文化的传统与职责;其所著述亦非私史,而乃国史。现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史记》属于私史或半私史。①因此其著述中,虽有对汉代统治者(包括汉武帝)种种批评之词,但恐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司马迁敢于坚持“实录”,是对史官文化优秀传统的一种继承。何况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的著述宗旨,如其著述过程中因李陵事件而恣意发泄其情感,甚至充满复仇心理,又何以实现其既定的著述宗旨。
因此,对司马迁所论的“发愤著书”,也应以知人论世的态度考察,宜真正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把握《史记》的整体思想倾向,然后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发愤著书”的内涵。然而,由于人们习惯把司马迁著述与其遭受宫刑之辱过于密切地联系起来,甚至认为《史记》的创作因李陵事件而发生了质的变化或方向性改变,又由司马迁曾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深刻同情屈原之词,故而很自然地将其所言的“发愤”理解为发泄一种愤懑情感。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史记》主要是一部发司马迁个人怨愤的复仇之书,极端者则称之为“谤书”。当代学界视《史记》为“谤书”或泄愤之书者已不多见,而且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顾易生、蒋凡的观点较前人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张峰屹也将“发愤著书”归纳为“遭际不平的怨愤”与“有所作为的发奋”这样两方面的意义。[4]200以上二说较前人之论无疑深入、全面很多,然而仍值得商榷。
有必要再来看司马迁表达“发愤著书”的那段文字。他所引八例之中,唯有屈原之著《离骚》最易让人联想到抒发怨愤不平的情感,《离骚》的确饱含对国君的怨怼之情,而其余七例中,都不易找到发泄怨愤而著述的依据。《周易》中很难说隐含了文王被拘絷的幽愤之情,参之《太史公自序》中另一段文字: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以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之大道者也。
可知司马迁称赏《春秋》的,正是其明辨是非善恶以垂法后世,如果仅为发孔子愤世之情,又何以能存亡继绝,承载大道,为百王之法?同样,《国语》中也并无所谓作者的私怨,孙膑《兵法》内容其实与其膑脚无关。《诗经》之中,虽有部分怨刺现实之作,但其内容之丰富,来源之广泛古今共识,称之为大抵圣贤发泄愤懑之作显然不符《诗经》的创作实际。要之,司马迁所举之例,与史实多不相符,这是相当显明的事实,而其所以如此,只能说明“作者不过借古人发愤著述之例,以说明挫折、打击对一个人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当士人不能正常用世之后,为解除心中的郁结,往往只有通过著书留名这种自我振作、自我奋斗的方式,让后人于其著述中了解其人生价值”。[5]64
因此,“发愤著书”应是作者经历刀下刑余、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沉痛思考之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它促使司马迁以超凡的毅力去完成无比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司马谈的郑重遗命)。其含义实是人生遭受困辱之后的自我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智激烈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华夏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的弘扬,更是古代士人以弘道自任、愈挫愈奋的优秀传统的体现。孟子有言:“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上》)司马迁高度推崇孟子,其著汲取孟子之精神力量处极多,故其应当与孟子一样,“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在“身毁不用”之后,是全部通过《史记》而体现出来的,他的“一家之言”是一种本着“实录”精神,将其究天人、通古今的卓越史识见诸三千年历史之中,述往思来,垂法后世,以展现大丈夫“不移、不屈”的光辉,而不是将一己的愤懑与不平倾注于其中,那样只会有损《史记》的光辉。
陈桐生认为司马迁的文化复仇实即愤书以雪耻,基本不错。只是需要进一步了解,司马迁之雪耻,确有一定意义上的借描写种种复仇故事以投射自己的复仇心理,但更主要的则是通过描写诸多复仇者、不屈者、励志者,展示他们的人生价值虽经压制、磨难而仍能得以实现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大丈夫精神。司马迁之雪耻,是通过著述以证明其人生价值不因宫刑之祸而丝毫受损,其著述之宗旨不会因此而改变,其思想之光辉不会因此而蒙垢。司马迁之雪耻,是一种刚大自显,亦即通过著述证明士的身体可以被摧残,士的精神则无法被摧毁。
过常宝追溯中国原史文化,认为司马迁是为捍卫原史文化传统,其在现实中遭遇巨大挫折,但仍力图以顽强的批判来进行文化复仇。司马迁内心无疑洋溢着先秦士文化精神,作为史家,他努力弘扬先秦史文化的直书志事、明心志道传统。汉武帝承汉兴以来海内艾安、府库充实之利,而又心慊于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故卓然一改休息无为之传统,内外兼作,大用文武。《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盛称其事: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破蝉,其余不可胜纪。
汉武帝之用人,的确颇具眼光,但其起用既果决,废杀亦果决,其雄才大略的另一面则是刚愎独断,其专制与严苛时常令臣下胆寒。司马迁出于史家职责向其陈述对李陵降敌的看法,却遭受酷刑。此事确给司马迁以巨大打击,尤其是其痛感史文化观念遭受猛烈冲击,同时对皇权专制文化有了切肌入骨的感受。司马迁是有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精神的,其求生看似屈辱,实为成仁,为完成立言以不朽。何以不朽,是要其著述真正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何以传之百世,则必须立旨崇高,识见非凡。故司马迁代表原史,维护原史文化,虽有时激情难抑,而始终不出理性范围。鉴于此,称其著述是“代表整个史官传统,向着独大的统治展开了猛烈的复仇”似乎略有偏颇;而认为司马迁在复仇之火燃烧下,将一切孝道、君臣之道、宗国之道,甚至信义、人格尊严等均被视为“小义”而可以舍弃,则更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不但汉代帝王宣扬以孝立国,司马迁亦颇重孝道。《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遗命,要求司马迁立功名、扬父母,彰显大孝,司马迁则俯首流涕,谨遵教诲;《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则以身遭戮辱为对父母之大不孝。《史记》所描写的复仇人物的典型伍子胥,所以不从父兄而死,绝非背叛孝道,而是要隐忍存世以复父兄之大仇,此非大孝而何?同样,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君臣之道、宗国之道。司马迁歌颂了大量爱国忠君的历史人物,即使对其并不欣赏的法家人物晁错,也推崇其“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太史公自序》)。当然,司马迁受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观念的影响,倾向于君臣关系的互忠互信与人格平等,因而反对暴君虐政,也不欣赏迂腐愚忠。
司马迁反复申言忠信道义的重要,对因名利而背信弃义之徒给予无情的贬斥。其列吴太伯为世家之首、列伯夷为列传之首,也被公认为具有弘扬道义的意旨。而一般认为,司马迁因在李陵事件中痛感人情淡漠、信义稀少,故而着意褒扬信义、讥刺势利。其实,以司马迁之禀性,本以坚守信义为尚,而鄙薄势利世故,宫刑祸殃只是加深了司马迁对世道人情的认识而已。司马迁坚守信义,是因为其自身具有并崇尚正义之人格。司马迁不仅能妙笔著文章,更能够铁肩担道义,尤尚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而对希世度务、丧失人格尊严之辈则讥贬不置。需要注意的是,对那些隐忍以立功者,司马迁绝非认为他们丢弃了人格尊严而加以批评。如韩信早年甘受市井无赖胯下之辱,显示的是其能坚忍、不轻仇的为人,这种人品正是成大事者的基质之一,也恰是司马迁所要颂扬的。“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赞》)“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报任少卿书》),这此警句,正是司马迁深刻的生死哲思。
三、结 语
司马迁为人能坚守大节,主动肩负大道,其著述更有伟大宗旨并始终贯彻。称司马迁著述有雪耻的动机并无不可,而且司马迁并非超尘脱俗之圣人,其一己之情有时难免呈现于著述之中,但就此认为《史记》是一部文化复仇之书,则显然欠妥。《史记》非为复仇而作,即便以文化复仇来图解,似仍流于表面之见。《史记》的圆满完成,是司马迁百折不挠精神的证明和对自身高度信任的回应,也是其人生价值的充分展现。古人往往认为《史记》是太史公哭泣之书,对此同样必须理解为司马迁是将其强烈的历史责任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投注于《史记》之中,而不是将其一己之悲怨弥散于字里行间。因为《史记》是历史的“黄钟大吕”,绝非个人的浅吟低唱。
①《后汉书·班固列传》载:“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可见私作国史,罪行极重。司马迁如属私著国史,以汉武帝为人之严酷,后果可想而知。
参考文献:
[1]顾易生,蒋凡.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3]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潘定武.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5(4).
责任编辑:吴 夜
A Refutation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or“Cultural Revenge”
Pan Dingw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lthough suffering the humiliation of castration,and known for his idea of“Fa Fen Zhu Shu” (putting full energy in writing),“Fen”here is not out of discontent and indignation,not to mention personal spite.And it’s a misunderstanding to regar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s a book about Sima Qian’s cultural revenge.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reflects Sima Qian’s great ambition in writing and his value of life after being humiliated.Assuming that Sima Qian,full of hatred,willfully let off his anger in his book because of castration would inevitably deviate from Sima Qian’s aim of his creation as well as reduce the magnificent value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cultural revenge;put full energy in writing;aim of creation
I206.2
A
1672-447X(2017)01-0080-04
2016-11-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ZH097)
潘定武(1967—),安徽舒城人,黄山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