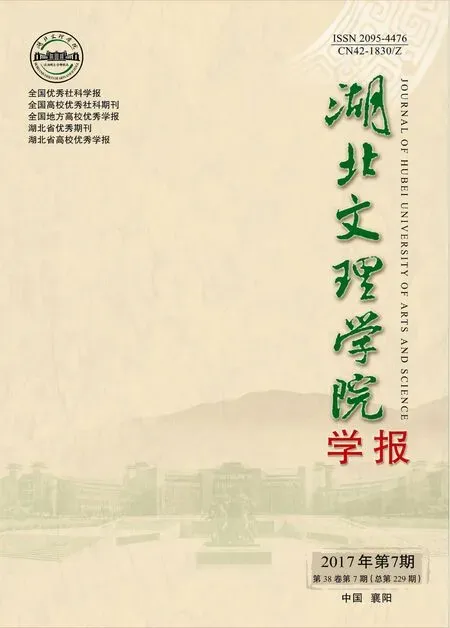童年的呐喊:莫言童年记忆与苦难书写的创作立场
赵 璐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童年的呐喊:莫言童年记忆与苦难书写的创作立场
赵 璐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童年是作家心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形成期,作为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莫言经历了一个充满苦难的童年。莫言的童年记忆作为艺术元素和叙述资源,是他创作的灵感和来源。莫言从人道主义出发,把人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对苦难生命本身赋予关怀,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个体生存的关注。童年的饥饿书写表现了饥饿对人的异化,以及人在苦难面前努力超越自身的精神渴求。父爱的缺失性记忆和母爱的救赎,经过长期心理沉淀,在作品中莫言塑造了众多被弱化、丑化的父性形象和无私无畏的“地母”形象。童年记忆与苦难书写是莫言小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莫言创作的立场。
莫言;童年记忆;苦难书写;创作立场
一、苦难的继续延写
(一)童年记忆与苦难书写的交织
一般认为,8~15岁是一个人的童年阶段,也是作家心理结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形成时期,这期间作家在不自觉地收集艺术材料,其创作素材和创作基调的选择已经慢慢积淀。谈及童年,很多作家都不回避它对于文学创作的价值,认为这是他们人生中不可复制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童年经验作为一种艺术元素和叙述资源,作家在想象中虚构文学世界时,会选择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作为材料,或潜意识里受到童年记忆的影响,创作中无意流露出童年视角的痕迹。童年经验作为人生经验的源头对人的一生产生极重要的影响,且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关于父母意象、故乡记忆、社会反思等方面的选择均是童年经验影响的使然。虽然莫言的童年也有快乐的日子,但在其创作中,苦难成为他的作品里无法拒斥的主题。作家的使命不仅仅是叙述故事,而是要关注社会和人的发展,因此很多作家在创作中书写生活的痛感。对于莫言,这一点在他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莫言无条件地为弱势文化、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和申辩,体现了他的写作姿态。莫言2001年在苏州大学所作《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演讲中,提出作家要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作家要作为老百姓去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感受到的一样的。”[1]287循着这个思路,莫言确立了自己的民间立场,在小说中表达他作为老百姓自我的苦难和体验。
莫言的童年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五六十年代,亲身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事件。作为在底层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言对苦难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最早将目光投向莫言的童年记忆的评论文章是1986年刊于《上海文学》的程德培的《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读莫言的小说,我原以为会更多地看到一个成年人的世界,结果却是看到一个植根于农村的童年记忆中的世界,一种儿童所独有的看待世界的全新眼光。”[2]20文章对莫言缺失性的童年经验与其创作之间的关联做了详细论述。本文将从莫言的童年记忆和苦难书写出发,挖掘莫言小说的话语心理动因。
(二)莫言苦难书写的深刻性
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的《呐喊》为标志,开创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鲁迅站在启蒙立场上,喊出了反封建的最强音,对“吃人”的充满苦难的社会做了尖锐的批判。到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们延续五四运动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大量书写苦难记忆。但大部分作家对于苦难的理解有所偏差,受“以苦为荣”的理念驱使,塑造了一个个接受苦难勇敢生存的“受难者”,这种“受难者”是带着受难的闪亮光环的崇高形象,因而这类小说的文学价值不高。但莫言的小说选择主动与意识形态话语疏离,把人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对苦难生命本身赋予关怀,从根本上将“历史中的人”转换为“个人的历史”,这表现出莫言苦难书写的深刻性。
莫言笔下的人,是在艰难残酷的处境中仍保持着独立个体的人格精神的人,他们以理解、顺应的态度对待悲苦的命运,并把这种苦难看作是生命的馈赠,是命运的必然伴随。童年、少年的悲惨经历在莫言心中隐隐作痛,对莫言来说,故乡是造成他不幸的源头,那么逃离故乡就是逃离苦难。而当莫言怀着对故乡的“仇恨”逃也似地离开故乡后,他渐渐意识到故乡是他无法忘却的“精神血地”,尽管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肮脏和污秽,但也只有在故乡的往事中他才能找到创作的灵魂和源泉。如《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莫言回溯了其童年的饥饿、幻想、母爱救赎与父爱的缺失等创伤性记忆,通过童年书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的人生哲学和生活伦理,这与莫言苦难叙事的民间立场和底层视角有关。莫言在谈到《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的形象,“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3]小黑孩几乎是莫言童年时的写照,在恐惧和孤独中度过,面对小铁匠的歧视和欺凌,他选择沉默和主动逃离,用奇特的幻想让自己处于神游状态,暂时忘记现实中的不幸。莫言怀着作家的忧患感、责任感,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在这样的意义上,莫言的创作是为悲惨不幸的童年所作的“呐喊”,他用创作来对抗沉重的人生局限,补偿了童年的种种不幸与缺失。
二、照进现实的饥饿书写
(一)饥饿“梦魇”下的呐喊
1956年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这是一个十几人组成的大家庭,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哥哥姐姐了,所以莫言的出生并没有给家中带来多大的欢乐,反而意味着又多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莫言长到四五岁的时候,三年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莫言的家乡也遭遇了这场劫难。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所有能吃的食物都被吃光,物质极度匮乏。吃野菜、树皮、泥土甚至煤球。饥饿是当时孩子共同的童年记忆,也是整个民族的梦魇。
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对这段饥荒历史进行了反思,饥饿主题的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首先描写了农民群体的饥饿,这是首部涉足这段历史的小说,但由于政治的关系,掩饰了当时农民真正悲苦的生活处境。之后张贤亮描写了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高压下经历的饥饿,《绿化树》《灵与肉》《习惯死亡》等,张贤亮以自我为原型,把饥饿的真实体验写进作品中,赋予人物在苦难中磨砺意志的精神诉求。但深究这种诉求,并不是以真正确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精神主体为目的,而是将希望寄托在社会理想上,即出现一种不再让人挨饿受苦受难的政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知识分子对政治开始疏远和边缘化,“‘个体’的独立话语逐步凸显出来,作家们的思考也开始从自身文化的狭小空间向人类整体精神诉求的世界性视野转移。”[4]130莫言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家,在莫言的作品中,他撇弃了社会政治理想化的话语方式,而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灾难中饥饿的人上,探索其生存之道,以老百姓的姿态去书写对于苦难的体验。
(二)饥饿的异化和精神的超越
莫言坦言他的文学创作动机来自于“吃”,莫言小说中饥饿的身体书写是另一种话语方式,不是对饥饿现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对肉体和精神经历的双重痛苦进行描写。在饥不择食的年代,人的全部生活意义都是吃。莫言曾自述其创作经历,“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5]76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黑沙滩》《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中,均有对饥饿触目惊心的描写。例如《丰乳肥臀》中写到饿殍遍野的1960年春天,人变成具有反刍本领的食草动物,吃野菜、野草,闲暇时会像牛一样将胃里的草再回到嘴里咀嚼,馒头可以成为炊事员诱奸女性的诱饵。上官金童的六姐乔其莎,虽是医学院的校花,可在饥饿的驱使下委身给猥琐不堪的炊事员张麻子,回归到人原始的进食状态,像动物一样匍匐在食物面前。莫言以其没有节制、一泻千里的语言,刻画了人对食物的畸形渴求。“她像偷食的狗一样,即便屁股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也要强忍着痛苦把食物吞下去,并尽量地多吞几口。何况,也许,那痛苦与吞食馒头的愉悦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6]《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母亲到生产队用胃偷粮,短篇小说《粮食》里也有类似情节,母亲为了尊严不委身他人,先囫囵吞下磨坊里的豌豆粒,回到家再用筷子捣喉将胃里的豌豆吐出来分给孩子们吃。《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常在饥饿时怀念与父亲到野骡子家吃肉的场景,短篇小说描写“大跃进”时的农村景象:老太婆们在“公共食堂”熬野菜粥,成年人整天炼铁,两个小孩一起吃铁筋、铁锅、铁枪、铁车轮子,竟将坚硬无比的钢铁嚼得咯嘣脆。饥饿作为一种极致性的苦难,那些令人震撼的细节是莫言童年时留下的阴影,是莫言童年经验的外化。莫言的饥饿书写并没有着眼于宏观背景,而是有意淡化政治色彩,极力表现人的生存状态,饥饿对人的异化,以及人在饥饿面前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迫害。莫言的饥饿书写为苦难岁月的人发声呐喊,人在面对苦难努力超越自身局限的精神渴求。
三、父爱缺失性的记忆和母爱的救赎
(一)父性形象被“阉割”的创作倾向
童庆炳先生曾作为莫言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在《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一文中说道:“对于莫言来说,对他最亲切的、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是故乡20年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生活经历,以及以后要进入他的小说里的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姑姑、乡亲和朋友等。”[7]70莫言的家里,是“严父慈母”的典型。莫言的父亲是读书人,会打算盘,平时的工作除了算账还下地干农活,当他拖着疲惫之躯回到家中,总是板着脸,很少和孩子交流。莫言回忆年轻时的父亲十分严厉,莫言和兄弟都很畏惧父亲。莫父的严厉和不苟言笑让童年的莫言倍感压抑。而在作品中,莫言笔下的父性形象被弱化、丑化,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威慑性的象征权力的父性形象被“去势”,多平庸自私和卑微残酷的形象。这直接的原因来自于莫言童年时期父爱缺失性的记忆,对父亲极度畏惧的情感经过长期沉淀,在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对父性形象“阉割”的倾向。例如短篇小说《枯河》以一个不幸儿童的视角来表现充满苦难的命运,主人公小虎在生活中经常受到同伴的嘲弄、挨打,在一次为村长女儿小珍折树杈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摔下树来,还砸伤了小珍。这次事故导致父亲的暴怒,小虎遭到了父亲的毒打,身心俱创,最终小虎选择死来无声地对抗父亲的暴虐。在这篇小说中,父亲冷酷无情,暴打儿子,对待小虎不以爱来感化,只是一味地打压和管制,是没有血肉堆砌起来的强大。弱小无能的小虎以死对抗高大威猛的父亲,这种无言的“呐喊”表现了对父亲的不低头和不屈从。小虎的结局是命运的悲剧,更是父爱的极度缺失造成的悲剧。《檀香刑》中的孙眉娘的父亲孙丙,生活里他风流成性、见钱眼开,对女儿唯唯诺诺,卑琐无能,毫无父亲的威信和尊严。莫言有意丑化他,从肉体与精神上对父性形象的双重阉割,孙丙逛窑子被人薅了胡须是肉体的阉割,当他看到女儿从对头钱老爷处拿来的银子时,又不忍心撒手只顾银子的真假时露出的卑琐相,是精神的阉割。
(二)母爱的救赎与“地母”形象
莫言在父亲那缺失的父爱,在母亲那弥补回来。莫言的母亲高淑娟,是一个极善良极坚韧的农村妇女。在母亲那里,莫言感受到来自母亲源源不断的母爱,母亲是幼年莫言的精神支柱。相貌丑陋的莫言童年非常自卑,在周围人那里遭到冷漠与嘲讽,甚至遭到同村性格蛮暴的孩童的追打,内心敏感的莫言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母亲。同时莫言身为大家庭中的幼子,他比别的孩子更加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甚至依靠的畸形心态。即使莫言因为贪恋读书,而忘记了割草、干活,她都要想尽办法保护他。母亲是童年莫言的保护神,庇护他幼小的心灵。因此,母爱的救赎给了莫言巨大的温暖,莫言笔下的母性形象是坚强勇敢的,同时又有着善良仁厚、忍辱负重的坚韧品质。在莫言的最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中,莫言将一直淤积在心头对母亲的依恋、感恩宣泄出来,小说热情地讴歌了生命最原始的创造者——母亲上官鲁氏。小说开头,日本鬼子正在占领村庄,上官鲁氏正在生育,上官家的一头毛驴也在生产,可公婆、丈夫只关心难产的毛驴,并不关心只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的上官鲁氏。母亲经历了八次分娩的痛苦,这种肉体性的苦难,母亲都做到了顺应和理解。在战乱和饥荒年代不仅养育了自己的九个儿女,还拉扯着女儿们生的孩子,竭尽所能抚育这些孩子,她没有倒下,仅仅是因为不肯让自己倒下,在一次次绝望中咬牙挺住。莫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神圣“地母”的形象,浓缩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母亲”群像,她虽然卑微不已,但却有着大地般宽厚、无私、坚韧的胸膛,默默承受着命运中的大小苦难,以无畏的精神消弭生命中的一切苦难。“莫言的叙事目的不是要反映那段历史,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联系和规律,而是要揭示和呈现出母亲们在历史事件的变迁中所遭受的各种伤害,苦难书写就是莫言叙事的主题和目的。”[8]95
莫言充满苦难意味的童年记忆是其创作的直接来源,因此从童年记忆入手,能更好地把握莫言的心理世界,寻找到莫言写作的心理动因。莫言的童年记忆通过重塑和变形,人物达到“似是而非”的写作分寸,有像极了自己童年时期的小黑孩、有遭到父亲毒打的小虎、有为了喂饱孩子利用胃偷粮的母亲等等,尽管他们看起来卑微,但有着极坚韧的内心。莫言的童年记忆被作家具备的忧患感和使命感唤醒,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直觉把握个体的灵魂。莫言的创作不是为了写苦难而写苦难,是为了表现人在面对逆境时发出的“呐喊”,即接受生命中存在的一切苦难,有力量的“活着”,这表达了莫言对生命的尊重和人的关怀。童年记忆是莫言写作的叙述资源,而苦难书写是莫言叙事的目的和主题,彼此交织,也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立场。
[1] 莫 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287.
[2] 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童年创作中的童年视角[J].上海文学,1986(4):16-20.
[3] 莫 言.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N].文摘报,2012-12-13(8).
[4] 黄云霞.“苦难”叙事的精神谱系——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文革”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30.
[5] 莫 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J].法制资讯,2012(11):73-77.
[6] 莫 言.丰乳肥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11.
[7] 童庆炳.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69-75.
[8] 李茂民.论莫言小说的苦难叙事——以《丰乳肥臀》和《蛙》为中心[J].东岳论丛,2015(12):93-99.
(责任编辑:倪向阳)
The Childhood Scream: Mo Yan’s Childhood Memories and Suffering Writing Creation Standpoint
ZHAO L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Childhood is a time when writers constructed their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value orient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s of life, Mo Yan experienced a childhood full of suffering. Mo Yan’s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as an artistic element and narrative resource, is the inspiration and source of his writing. From the humanitarianism, Mo Yan liberated people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of history, gave solicitude for the life of misery, showed respect to the life and focus on individual existence. The writing of hunger in childhood shows how the hungry distorted human beings, and the desire that human beings strive to surpass themselves in face of misery. The memory of the absence of father’s love and redemption by mother’s lov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psychological precipitation, in the works, Mo Yan has created a number of characters known as weakened, vilified father selfless and fearless Mother. The writing of childhood memory and suffering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eatures in Mo Yan’s novels, and it is also seen as the standpoint of Mo Yan’s writing.
Mo Yan; childhood memories; suffering writing; creation standpoint
2017-04-10
赵 璐(1993— ),女,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04
A
2095-4476(2017)07-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