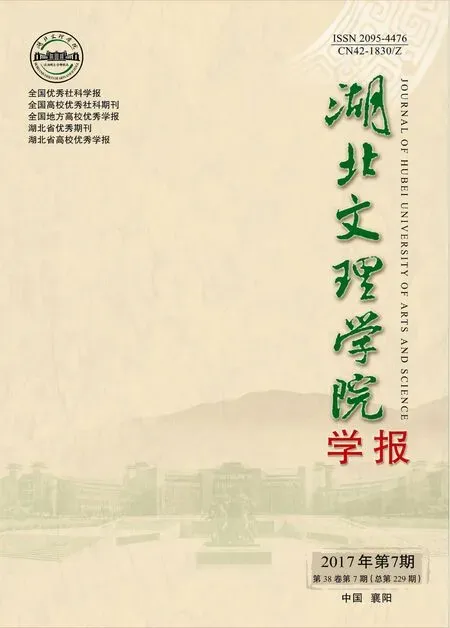《咱们死人醒来时》的地理空间建构及追寻主题的表达
潘丹丹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咱们死人醒来时》的地理空间建构及追寻主题的表达
潘丹丹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戏剧《咱们死人醒来时》的舞台幕景由山下海滨浴场、高山疗养区和疗养区所在的高山谷地三重地理空间组成。三重地理空间的地势由海平面到高山顶峰不断上升,其中的景物描写从静到动再到动静结合,随着地势的上升和周围景物的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也随地势从病态到修复再到蜕变的变化,戏剧的追求主题得到表达。鲁贝克和爱吕尼走向高山既是对地势高处的追求,也是对精神高处的追求。他们不仅实现了精神层面的爱情理想,而且,在一个没有尘世污垢的高山上,艺术和生活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达到新的平衡点,他们在新的平衡状态中重新认识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找回了各自迷失的灵魂和自然本性。地理空间建构和易卜生的“高处”情怀相关。
《咱们死人醒来时》;舞台幕景;地理空间;易卜生
易卜生说“我作为诗人所创造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在我的心境和处境里找到根源”[1]96,这句话表明他的戏剧构思和他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渊源。1897年6月,易卜生给勃兰兑斯*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易卜生的挚友。写信说自己正打算以戏剧的形式筹划着某些新的东西,海峡、大海上的船只、大海等给他带来新的创造力*易卜生在1897年6月给勃兰兑斯的心中写到“你能猜到吗?我在梦想、计划、在心里兴奋地描画着什么?在哥本哈根与埃尔西诺之间的一片海峡边,在某个自由、空旷的地点,我们安顿下来,看着还是正在起航和从远处归来的大大小小的船只,但是我在这里只能空想”,“在孤独中,我开始以戏剧的形式筹划某种新的东西,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观念”。此后于1899年他完成《咱们死人醒来时》。在此之前,他已经于1896年完成《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M].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43。。这些新的创造力两年后以《咱们死人醒来时》戏剧(以下简称为《咱》剧)的完成得以再现。在这部戏剧中,易卜生依托挪威的大海、海湾、高山等地理景观建构了戏剧人物的活动场景,给戏剧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影响力。本文将根据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分析本部戏剧剧本中由舞台建构的三重地理空间的内涵,文章在梳理这些地理空间的自身含义的同时,将探讨戏剧中所表达的追寻主题和剧作家易卜生的“高处”情怀。
一、地理空间的建构
马丁·艾思林认为戏剧舞台“本身就是一个产生意义的特殊物”“以自身的存在表明了一切发生的事物或能察觉到的事物的特殊意义和丰富含义”[2]。《咱》剧的舞台幕景由山下海滨浴场、高山疗养区和疗养区所在的高山谷地三重地理空间组成,这三重地理空间的地势由海平面到高山顶峰不断上升,其中的景物描写从静到动再到动静结合,随着地势的上升和周围景物的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积极的改变。
(一)山下海滨浴场的病态
故事开始于夏日清晨的一个海滨浴场附近,这里周围的景物错落有致。浴场外面的广场像个优美的公园,广场上不仅有古树、灌木、藤类植物等给休息的人们遮阳,还有凉亭和桌椅供人们休息。浴场后面有一片海峡与外海联系,可以看到远处的海角和小岛。这里宁静温暖,景色迷人,是一个修养身心的好地方,然而,这也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病态的宁静之地。首先,这片浴场附近的一切都是寂静或处于寂静状态,连城里的热闹之中也有点死气沉沉。火车一路上经过的小车站都那么寂静,寂静的声音可以让人听得见;火车在所有的小车站都停很久,虽然一点事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旅客上下火车;每一站总有两个铁路人员在月台上走来走去,他们在黑暗中交谈,但声音低得没有调子也没有意义;这个地方的人们生活空间相对狭小,他们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没变化,即便有一点小的变化也“不是朝着可爱亲切的方向变”[3]271。其次,来这里的人都是病人,虽然“没有病得非常厉害,必须夜里洗澡的人”[3]277,但大都身体上或精神上有病。到处旅行的鲁贝克和梅遏夫妇来到这里,他们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丈夫鲁贝克有病,他“心绪很不安宁,喜欢换地方”。[3]273不管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旅居到外国,他都不能安心地待着,“对工作失去了乐趣”。妻子梅遏虽然年轻神气,双目有神,但微显疲惫,且“在这里无精打采地过日子”。[3]271不仅如此,从他们之间并不投机的谈话来看,他们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相互之间流露出对彼此的厌倦。从国外归来的爱吕尼来到这里,她病得更厉害,需要女护士紧盯着。从相貌上看,她脸色苍白,“眼睛好像什么也看不见”,[3]278走起路来步法僵硬。从精神上看,她是“隔世的人”,“走进了黑暗”,“在坟窟里”。[3]286身体和精神都有病的爱吕尼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她不探望四周的环境,也不愿意搭理任何人。每年上山打猎都会经过此地的乌尔费姆也来到这里,在他眼中,这里是“一堆半死的苍蝇、半死的人”,[3]281他也有个人的烦恼。在病态和死气的海滨浴场里,主人公艺术家鲁贝克和从前的模特爱吕尼的关系处于断裂和停滞的状态。
(二)高山疗养区的修复
第二幕发生在高山疗养区附近,这里的自然环境呈现了动态的生机。溪水分成几股细流从石壁上泻下来,流过高原;溪水的那边,离高原不远处,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一群孩子们在唱歌、跳舞、游戏。他们的欢声笑语从远处传来,一直不停。不仅如此,在这里养病的人们也呈现出了活力:一方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缓和。鲁贝克决定结束和梅遏之间冷冷清清的婚姻关系,找一个真正帮助他艺术事业的人;梅遏则打算离开鲁贝克,摆脱牢狱一样的婚姻,远离艺术家的气息,寻找自由的生活。而对爱吕尼来说,她和鲁贝克重逢,他们之间可以像“活着的时候那么谈话了”。[3]308另一方面,人物的精神状态出现好转。鲁贝克耐心、仔细地看孩子们玩耍,在他眼中,孩子们的动作像音乐一样和谐。梅遏精力充沛,她刚爬山归来,舒服地躺在草地上,兴奋地不知道疲倦,她还“写了一首诗”,“得意洋洋地唱起来”。[3]319变化最大的是爱吕尼,她从“漫长无梦”的睡眠中醒来,“从坟墓里站起来”[3]307,“从极远的地方”回到了“心爱的丈夫”[3]309身边。她开始关心周围环境,和玩耍的孩子们低声细语,和鲁贝克敞开心扉,谈论以前和鲁贝克在一起、做鲁贝克模特的日子。在高山疗养区中,潺潺流动的溪水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这里添加活力,在这生机和活力的地方,由于人物之间的关系朝向好的方向发展,人物沮丧的心情和病态的精神开始修复,逐渐摆脱疲倦和衰弱的状态。
(三)高山谷地的蜕变
相对于山下海滨浴场与外界的隔绝寂静、高山疗养区的生机活力,通往高山的谷地地势较为复杂,并且气候多变。在这片高山谷地中,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首先,山谷的地势险峻,峭壁耸立,山腰荒芜坼裂。在荒凉的山腰里,所有想上山和下山的人必须经过“只有一条几乎无法走人的窄路”。[3]322山谷的右侧是雪山,山上迷雾重重,山谷的左侧是被暴风雪摧毁了一半的茅屋。其次,山谷中的气候恶劣,呼呼的暴风、翻腾的乌云和迷雾导致天气变化无常,暴风雪随时可能会出现。平静与暗动的完美结合是,此时的天色正在发亮,阳光即将冲破云雾照射雪山。在险峻的地势和恶劣的天气中,人物需要面临悲壮的选择,当他们的意志变得坚定时,他们内心的状态也出现全新蜕变。梅遏和乌尔费姆互相安慰,他们要“把生活的碎片”拼凑出“一种人的生活”,“自由自在、安安静静把真面目露出来”,[3]326他们要避开山中的迷雾和琢磨不定的天气,决定下山重新寻找生活。顺利到达山底的深谷后,梅遏得意地唱起自由的歌曲,“牢狱生活从此休,像鸟一样地自由”。[3]333与此同时,鲁贝克和爱吕尼找到了两人“像从前一样燃烧沸腾”的爱情,他们决定“在重新走向坟墓之前——把生活的滋味尝个彻底痛快”,[3]332他们决定“走上光明的高处,走进耀目的荣华,走上乐土的尖峰”在那里“举行婚筳”。[3]332但是,他们想要离开山上暴风乌云裹住的地方,离开“丑恶潮湿的尸衾拍击”的地方,需要考虑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如果像梅遏和乌尔费姆一样选择下山,避开迷雾和暴风雪,他们会活着;但是如果选择穿过迷雾,走上朝阳照耀的塔尖,他们就要面临即将到来的暴风雪,他们可能会死去,尽管如此,鲁贝克和爱吕尼义无反顾地坚持上山。复杂而险峻的地势预示着他们选择的艰辛;暴风和乌云给他们的选择涂上了悲壮色彩,但太阳的出现也暗示他们终将冲破生命中黑暗的阻挡。事实上也是如此,鲁贝克和爱吕尼决定抛弃当下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生活,迎接洒满阳光和自由的高处,他们期盼山顶的太阳,期盼山顶自由的生活。
随着地势的不断上升,人物的重逢、追忆及未来的选择逐步展开,人物的精神也随地势的变化发生从病态到修复再到蜕变的变化。海滨浴场的病态,是鲁贝克厌世气息、怀疑艺术、到处旅游却心神不定的象征;是爱吕尼从南美洲到俄国的凄惨经历以及回到挪威北部希望安定生活的象征;海滨浴场的寂静也象征鲁贝克和梅遏四五年冷清的婚姻生活、鲁贝克和爱吕尼四五年断裂的交往关系。在一个寂静和病态之地,让人呈现病态的往事及病人们需要疗养恢复的场景才能逐一展开。在第二幕的高山疗养区,流动的溪水和孩子们的笑声让周围的环境出现生机,人物之间关系出现缓和,人物的心情趋向美好。鲁贝克和梅遏直面二人冷清的婚姻,鲁贝克决定寻找艺术的灵感,而梅遏决定寻找自由的生活。同时,鲁贝克和爱吕尼对比了过去简单快乐的生活及现在荒凉衰弱的生命,决定去高山上寻找拥有爱情的自由生活。第三幕高山谷地的地势复杂,暴风、乌云、迷雾,还有即将出来的太阳,预示了人物选择的艰辛和悲壮,他们或许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梅遏和乌尔费姆决定下山寻找生活的真面目,而鲁贝克和爱吕尼则决定穿过暴风、乌云、迷雾,“走向光明的高处”,“一直走上朝阳照耀的尖塔”,即使死亡就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毫不畏惧。
二、追求主题的表达
高山是通往阳光和自由生活的地方,吸引着渴望新生的鲁贝克和爱吕尼。鲁贝克不止一次地答应过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女人(爱吕尼和梅遏,主要是爱吕尼),要把她带到一座高山上,鉴赏全世界的荣华。而爱吕尼和鲁贝克重逢后,也决定一起上山。“能走多高,就走多高。越高越好,越高越好——永远往高处走”。[3]292显然,舞台的地势不断上升,与剧中主人公对高处的追求紧密相连。在海平面上升到高山顶峰时,鲁贝克和爱吕尼也从海滨浴场走到高山谷地。在不断上升的地势中,他们的心理追寻也不断上升。向往自由、希望获得解脱的心理追求便在地势的升高中得到呈现,戏剧的追求主题得以表达。
(一)实现精神爱情的理想
精神层面的爱情理想是鲁贝克和爱吕尼二人的共同追求。多年前他们作为艺术家和模特在一起时,他们没有任何的肉体接触。鲁贝克追求精神层面的爱情理想,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和模特有肉体接触,他便没有能力创造出自己所极力追求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从来不忘记自己的艺术家身份,时刻坚守着身上固有的、与艺术相关的精神追求。爱吕尼也是如此,她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怀有崇高的唯美精神追求。尽管她一直恨鲁贝克没有对她的裸体动心,但是她时时刻刻在头发里藏着一枚尖针,只要艺术家接触她一丝不挂的肉体,她就会当场弄死他。多年之后,当他们重逢并携手走向高处时,还是保持着纯粹的精神恋爱。在高山之巅,他们怀揣着对彼此的精神爱恋以及对艺术的纯真追求,将精神交流到达相应高度。二人无需肉体接触,彼此两情愉悦,在相互爱恋中实现了二人精神层面的爱情理想。而在戏剧的结尾,当他们走向高山顶峰的过程中,双方死在了伴随暴风雨而来的雪崩中,他们之间纯粹的精神爱情也因为身体的死亡得以恒久。
(二)达到爱情与艺术的平衡
高山顶峰是一个人迹罕至、隔绝尘秽的地方,也是一个远离尘世生活之处,在这里,鲁贝克和爱吕尼可以逃离尘世生活的烦扰。鲁贝克可以忘记复杂的世情和丑恶的世间男女,可以重拾艺术家的任务和艺术家的使命;而爱吕尼则可以忘记多年以来苦苦寻找的爱情,可以忘记沦落风尘的流离生活和不幸遭遇。除了逃离世俗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远离人间的高度上,他们还可以找到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支点。高山之巅一直是鲁贝克想带爱吕尼到达的地方,雕像没有雕出时,高山是艺术信仰的顶峰,雕像成功后,高山是爱情和生活的顶峰。他们希望在一个远离尘世的高处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艺术和生活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艺术可以脱离生活达到一定高度,但是完全脱离生活,艺术将无法达到至高处。只有将生活和艺术结合起来艺术才能得到升华。而爱吕尼是鲁贝克的艺术源泉,和爱吕尼在一起,鲁贝克依然可以找到艺术的灵感,再次创作出更成功的艺术作品;和爱吕尼在一起,他可以拥有爱情,爱情也不再是艺术的对立面。而爱吕尼和鲁贝克在一起,她和鲁贝克的爱情可以指引她空虚的灵魂回归肉体。当爱情和艺术同时拥有,那么理想的生活就可以在二者的平衡关系中“自由自在、高高兴兴”。[3]332
(三)找回迷失的自然本性
在《咱》剧中,高山不仅仅是写实之景,它更具有象征和暗示的功能,与鲁贝克和爱吕尼的精神追求相呼应。鲁贝克和爱吕尼站在高山山谷品味生活,深感自我的渺小和生命的空虚,从而对生活的意义产生顿悟。对于艺术家鲁贝克来说,艺术高于生活,艺术是他生命的全部,但是,在缺乏生活的真空中,将一堆死的泥土、石头奉为人生圭臬,艺术的欲念会将人的自然本性压制,艺术家的精神追求会走向极端,从而迷失了自我的本性。正如在群雕中那样,鲁贝克坐在溪水边一遍一遍的洗手,他的良心受到谴责,自己给自己判了刑。站在高山之巅,他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所追求的艺术和他对爱吕尼的爱情不是对立的,艺术不能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即便为了艺术,黏土的艺术价值也远不如模特的生命价值重要,他不能为了雕塑出鲜活的艺术雕像而抛弃模特的灵魂和热情。而对于模特爱吕尼来说,虽然艺术家利用了她纯净的灵魂,并无视她的爱情,但她本人更应该对她的精神沦落负责。她失去了艺术家的爱情后,以糟蹋自己的人生来报复艺术家的举止只会让她的灵魂更加空虚以致无法得到解脱。当她和鲁贝克共同走向高处时,高山便成了她找回灵魂的寄托处,她在精神的高度再次将灵魂与肉体结合,重新认识了自我的本性。因此,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模特,二人都在高山之巅找回了自己迷失的天性,自我本性在对高处的信仰中回归到原始状态,这样,即使他们的肉体在雪崩中死亡,他们的灵魂也能够得到救赎,并得到全新的复活。
由此,地理空间的建构完成了戏剧人物对高处追求的主题表达。高山将写实之景与象征之意相结合,鲁贝克和爱吕尼在暴风雪中仍然愿意登上高山,并最终在雪崩中死亡,实现了他们纯粹的精神爱情的理想。他们走向高山既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离,也是对理想生活的一种追求。在一个没有尘世污垢的高山上,艺术和生活不再对立,而是达到新的平衡支点,他们在新的平衡状态中重新认识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在对高处的仰望中,他们找回了迷失的自我本性,灵魂和肉体再次统一并且得到了救赎。此时,高处已经不仅仅是高山的实体存在,它更是一种精神和信仰的象征。
三、易卜生的“高处”情怀
《咱》剧中地理位置不断上升和易卜生的“高处”情怀相关。汪余礼认为在易卜生的人生观中,其精神个性的内核是“永远向着‘光明的高处’,向着‘耀眼的尖塔’”[4],他的这一观点有力地解释了易卜生的高处追求和情怀。易卜生一直坚持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1]115,在剧中,高山之巅是极少数人才能到达的地方,也是掌握真理的人能够到达的地方。虽然梅遏和乌尔费姆成功下山,梅遏最终也获得了婚姻的自由,但是他更赞成鲁贝克和爱吕尼获得自由的方式,因为,依照易卜生的观点,只有坚持到达山顶的鲁贝克和爱吕尼才是掌握真理的少数人,他们登上高山是为实现唯美的精神爱情而战,为达到生活和艺术的平衡关系而战,为寻找迷失的自然本性而战。从《咱》剧鲁贝克和爱吕尼对高山的追求来看,我们可以窥视出易卜生个人人生观中精神个性的内核,正是他本人对高处和对光明的追求才有了戏剧人物对高处的执着。不仅如此,易卜生将他的艺术追求与高山相连,和易卜生本人的经历也有关系。据说他自小时候就喜欢站在高处观赏下面的世界,并对看到的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此后也形成了他的“在高处”哲学[5]。站在一个远离尘世的高处,鲁贝克和爱吕尼可以更清楚地判断尘世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从而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对艺术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有了深入的思考。在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相当困难,然而如果缺少对生命的尊重,艺术将失去源泉和生命。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易卜生的笔下,通过舞台地势的逐步上升,通过舞台景色描写的变化,鲁贝克和爱吕尼的高处追求得到表达,戏剧家易卜生对高处追求的理想也得到体现。
其一,易卜生通过对地势的上升表现了戏剧人物对高处的追求。三幕戏剧与三重地理空间的地势一一对应,每一幕都代表了人物或人物之间的状态。易卜生通过对比的手法,将低地的粗俗与高处的崇高区分开来。低地海滨浴场与大海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里是死寂之地,所以剧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状态都相当衰弱,就连当地人的生活也死气沉沉,摆脱不了粗俗的生活状态。地势升高到山谷后,这里成了疗养和修复之地,鲁贝克和爱吕尼、乌尔费姆和梅遏的精神状态比先前改善很多,他们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而到了最后,鲁贝克和爱吕尼愿意到达最高的山顶,寻找心中的梦想和光明。越是到高处,人们越是精力充沛,高山自然而然地成为攀登艺术高峰、追求崇高理想的象征。在对地势上升的描写中,易卜生完成了他剧中人物对高处的精神追求。其次,在地势的上升和人物的追求对应关系中,戏剧晦涩的台词得到进一步诠释。由于《咱》剧的剧情主要依靠人物的台词得以推进,而鲁贝克和爱吕尼之间的对话又比较晦涩难懂,因此舞台布局显然有助于读者/观众对人物对话和戏剧冲突的理解,而戏剧的冲突也因为舞台布局的不断变化得到立体阐释。再次,易卜生的“高处”情怀顺利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戏剧的高潮。随着鲁贝克和爱吕尼一步一步地走向高山的顶峰,戏剧的情节逐一展开,当二人冲破种种阻碍,最终走向心中一直向往的高山之巅时,戏剧的高潮出现,他们二人实现了理想的同时也埋在了雪崩之中。正是因为易卜生的“高处”情怀,才有了《咱》剧的地理空间与追求主题的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又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戏剧中人物之间的台词,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最终因为鲁贝克和爱吕尼到达山顶和雪崩的到来,戏剧出现高潮。这样的艺术手法显然增加了戏剧的可读性和观赏性,读者/观众在突然中断的戏剧高潮中对戏剧产生不同角度的理解,引起他们的共鸣并激发他们的进一步的深思。
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作品中的非人为环境不仅仅是具有背景的用途,而是开始表明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是密不可分的”[6]。《咱》剧中所建构的海滨浴场、高山疗养区、高山谷地的地理空间,是戏剧中人物活动的真实环境,也是戏剧家站在地势和精神高处对人类追求的严肃思考。戏剧正是建构了不断上升的地理空间,追求高处的主题才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达。王宁认为易卜生的作品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他们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新的意义[7]。而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解读作品,可以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视野、全新的认知与独立的观点[8]。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观照下解读《咱》剧的舞台设置,能拓宽我们对易卜生作品的认识,也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1] 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M].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 马丁·艾思林.戏剧:现实·象征·隐喻[M]//曹路生,虞又铭,编.郑国良,译.穿越前沿:外国戏剧篇.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8:96-106.
[3] 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七卷[M].绿 原,卢 永,贺 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 汪余礼.易卜生书信演讲集译者前言[C]//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
[5] 邹建军,杜雪琴.易卜生长诗《在高原》的哲学之思与生态之维[J].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1):55-61.
[6]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7.
[7] 王 宁.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J].外国文学研究,2003(2):8-15.
[8]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M].北京:中央编译局,2014:1.
(责任编辑:倪向阳)
Geographical Space Construction and Theme Pursued inWhenWeDeadAwaken
PAN Dandan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236041, China)
The stages in the dramaWhenWeDeadAwakenconsist of bathing beaches below a mountain, alpine recreational zones and the valley around the recreational zones. The terrain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geographical spaces goes up, and the scenery description changes accordingly: stillness to movement, to combination of stillness and movement, during which the spirit of a person changes: morbidity to recovery to betraying, and the theme pursued is obtained. The fact that Rubek and Irene walk towards the mountain shows their pursuit of highland and the pursuit of height of the inner mind. They realize the ideal of love at spirit level. Moreover, in the mountain where there is no defilement, the art and the life are not opposite to each other, but keep a new balance, in which Rubek and Irene re-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art, and find their lost soul and n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is related to Ibsen’s “highland” emotion.
WhenWeDeadAwaken; stage; geographical space; Ibsen
2017-04-20
2016年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710)
潘丹丹(1982— ),女,河南沈丘人,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讲师。
I106.3
A
2095-4476(2017)07-0047-05
——评葛斯著《易卜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