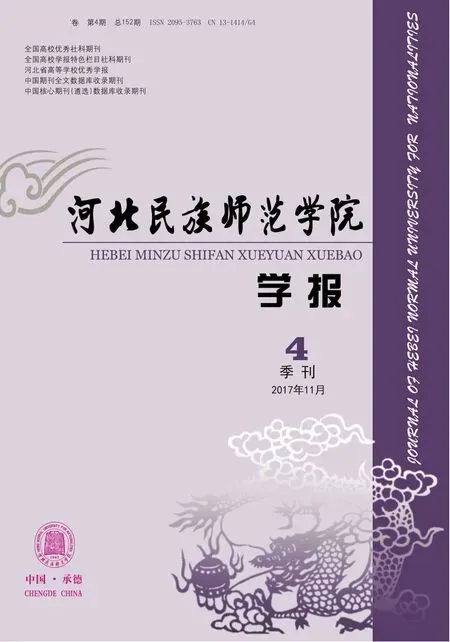大风起兮:浩歌与荣魄的联翩起舞
——支禄散文诗集《风拍大西北》艺术精神初探
范恪劼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大风起兮:浩歌与荣魄的联翩起舞
——支禄散文诗集《风拍大西北》艺术精神初探
范恪劼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新疆吐鲁番与甘南是支禄笔下大西北的对应点,也是其文思的衍生场,更是其竭诚而歌开心见肠之地。风拍之烈与西北之大,恰是支禄捕捉到的与这片寥廓天地相匹配的象征图式,也是诗人业已熟稔的观察视角和倾诉场域。由此,支禄的散文诗实现了地域性与普适性的融合与互生——自我铭痕确立的明晰和向他者渗透传示的可能。
支禄;《风拍大西北》;审美;人文;诗性
大西北是一个具有地理学意义的版图方位,更是一个充满粗犷雄奇浩远深邃意蕴的文学坐标符号。这种审美经验的获得,既源自于自然造化由来已久的雕琢之力,也传续于历代诗文的描摹之形。经验一旦确立,审美便有步入固化的窘境与怠倦的危险。恰在此时,一本散文诗出现在案头,一股原装的大西北的烈风沙雨淋漓人身、酣畅人心,这就是新疆作家支禄的《风拍大西北》。在诗人支禄那里,新疆吐鲁番与甘南是其笔下大西北的对应点,也是其文思的衍生场,更是其竭诚而歌开心见肠之地。读《风拍大西北》,让我眼前与胸中一直长风激荡。风拍之烈与西北之大,恰是支禄捕捉到的与这片寥廓天地相匹配的象征图式,也是诗人业已熟稔的观察视角和倾诉场域。这就是说,支禄寻找到了和大西北彼此互认、协率共鸣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文学地理宗主地的辨认和领受,找到了让自然内化、让生命外倾的诗性机制,找到了内心经验与造化自然的互证逻辑。由此,支禄的散文诗实现了地域性与普适性的融合与互生——自我铭痕确立的明晰和向他者渗透传示的可能。
一、风起于审美:洪荒中的生相物象
在《风拍大西北》中,触目皆是最为典型的大西北生相物象——沉默的沙漠、戈壁、黄土、雪山,动态的狂风、流沙、白云、野火,远处的群山岩画与鹰狼兔鼠,近处的庄稼村舍与牛羊驴骆驼。当这些素常的凡俗一旦遭遇诗人,当诗人胸间的激情与大西北彪悍的烈风相激荡,大西北一下子立体而灿烂、生动而真切。
这当然需要一双审美的眼睛——从粗粝中触摸到温润,从绝望中窥见复活,从寒凉中对接生发。这更需要一种大风起兮的精神超拔和俯瞰人间城郭的审美灵性。也许,正源于此,诗人不止一次地将翱翔苍穹的神鹰请到文字中:
鹰,飞过去两三天后。今夜,悄然而来。
鹰,悔青了肠子,已让一把一把的苍茫呛得不像个鹰的样子。
此刻,背负一塌糊涂的夜色,鹰静静地站在灯火最中心的地方。我稍稍一抬头,就隐约看见鹰内心的伤痕远比翅膀是哪个的伤痕重得多。
此刻,只要你愿意,鹰会把任何一节骨头抽出来。
递给你,今夜,让吹一支凄凉的《塞上曲》。(《苍茫》)[1]
城墙之上,一只鹰不停地拍打翅膀。
哗哗地响声,像一个黑衣人站在高处抖动衣服,多少黄沙一堆又一堆倒在古城墙下。(《嘉峪关下》)
风停后,鹰从一座山头把吹碎的云朵垒到另一座山头。鹰的力气大着呢,一会儿云朵就堆到高高的天空。(《大戈壁》)
这是一只大西北的寻常之鹰,也是支禄心中振翮飞动的意象之鹰。神性十足而喻像凝重,涵载丰富而命运坎坷。它回旋于苍茫,背负黑暗吹彻云朵,抱紧伤痕抽出骨头,始终静立在“灯火最中心的地方”。鹰乎神乎人乎,抑或就是支禄之魂乎?都可能是,都可以是。因为,这只抬头可见顺手写入的鹰,早已在诗人的心宇盘桓至久甚至与诗人合二为一,而大西北的天宇如果缺失这样一只意象之鹰一定是寂寥而虚空的。
进入诗人文学视域与美学向度较多的还有羊和骆驼:
羊半跪戈壁滩山,像半截木墩插在沙土中。骆驼没日没夜城堡样迁徙,越走越远,天空越顶越高。
背着口粮和柴垛的骆驼;背着高高雪山和茫茫大漠的骆驼;背过传说和神话的骆驼……
让风的缰绳牵着,一步又一步丈量时光堆在脚下的千万里黄沙。
骆驼的胃里把滚滚黄沙咀嚼成盐、草料。
骆驼的眼里是辽阔的地平线。
就是天下刀子,对于骆驼来说一旦踏上迢迢征途就不再回头。”(《河西》)
良善,良善到跪在石刀砂刺上也不负牧羊人;坚韧,坚韧到嚼沙为草料也不回避迢迢征途。从鹰隼到骆驼及至羊群,支禄在生相选择中有着清醒的捕捉和明确的定位,三种隶属大西北最有代表性的生物,分别从飞翔与梦想、远足与负重和固守与忠诚的层面,阐释着这一特定地域生命的脉象,间接传示着繁衍于斯的人的精神图景。正如鲁道夫·阿恩汉姆所说,“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棵婀娜多姿的垂柳……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在艺术家眼睛里也都具有和人体一样的表现价值,有时候甚至比人体还有用。”[2]P623—624
这种审美的构图制景调动了大西北所有的元素。犟驴,蜥蜴,沙枣,芨芨草,骆驼蓬,高粱,土豆,草娃娃与野花……不能不说说“草娃娃”。野生野长的野之草,侵入农田“挡住庄稼走的路”的草,让农人“心急火燎”的草,在诗人历数人与草永无休止的斗争之后,依然用葱茏草色描摹这些惹尽麻烦的“草娃娃”——“冬天来了,草娃娃让雪一巴掌接一巴掌打在脸上。草娃娃不敢吱声,草娃娃知道闯了大祸,在地头上一捆一捆蔫着头,像一个个低头认错的孩子”。复杂的心态,慈柔的心肠,正是大西北乡亲们才有的口吻与心性呢。
这不能不让笔者重看本书第一辑的命名:“风吹荒原,横渡苍茫”。大西北的风貌怎么写?荒原之荒是真的,荒原之原的苍茫是真的,换句话说,在仍然主要赖于传统生产方式而得以生存其间的大西北人眼里,这些真实之上,还有风吹之后的枯荣,横渡之后的通达。显然,支禄笔下的大西北审美得以成立,正是因有着与大西北人视角的同步和呼吸的同频,才得以呈现这种视角冲击的辽阔壮美、震荡人心的丰厚意蕴。
二、心植于人文:稼穑里的深情爱意
无疑,支禄是大西北的行走者。从甘南到吐鲁番,乃至大西北的山山水水。与诸多仅把大自然视为“第二情人”的远足、探险、旅游者的心怀不同,支禄有着深入大西北幽深处的深情触摸、与万物做同侪的齐物认同。更进一步,作为与稼穑农事纠缠终生的农人后代,作为生活于斯的大西北主人之一,他理所当然地把最为浓重也最为深情的文字留给了“我的黄土,我的村庄”。在这些文字中,诗人饱含对乡亲、对父母妻子、对所有稼穑于泥土上劳动者的体认与深情,时时疼痛,每每礼敬,再再讴歌。他写到赶鹞捉鸟一辈子“最后把自己追到黄土里。糜谷黄了时,鸟儿依旧从天空飞下来死死缠住不放”的“二爷”;写到“一曲唱完又一曲,直到把自己喊唱成古羌人,蹲在石头上,瞩望羊群沿着一波一波的风沙上岸后,湿漉漉的目光就盯住自己”的“牧人”;写到“把胸中的喜悦一次次打水漂漂样,沿着一条大河送向远方”的“鼓手”;写到心高运舛的“爷爷”、慈祥温善的“奶奶”、勤劳忍让的“母亲”、坚毅木讷的“父亲”、无私奉献的“妻子”——所有的“人间烟火”,“怀着对村庄的热爱,心窝里的泥土总是热热的。”在支禄这里,大西北固然辽阔浩渺,但人,仍然是直立于万物之上的中心,虽然,诗人的悲悯与仁心从来都施及众生。这是人本主义的光辉使然,也是人文精神的涵养所致。
乡土书写,如果没有对泥土墒情的透彻理解,对西北粗粝的迎面直视,没有对肌肤青铜光耀的体认和汗珠盐质火焰的熟稔,对大地苦难以及苦难之上坚韧的揭橥,就往往会流于浮泛空疏的想象式虚构或一厢情愿的愿景勾勒。比如《锄头》一篇,尤使我玩味再三:
锄头喊了一声“我是铁啊!”就推门匆匆忙忙赶往地里。
大风吹来,透过半尺厚的黄土看见锄头已经老了,满脸沧桑,看上去很是疲惫的样子,像是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福也没享受过的那种样子。
毒日头下,锄头依旧劳作着,压根儿忘记已经很老了。
……(省略)
一声不吭的锄头风里来雨里去。像是只要有一口气,即使让草碰得灰脸青鼻子,也要挺直腰板死死地揪住不放。
一把锄头,经常与草在庄稼地里整得起土冒烟,可锄头只要揪住草的尾巴,死活要把草从庄稼地里就出来。
……(省略)
锄头走过的路上,庄稼向粮仓汹涌而去。
锄头开辟的路上,庄稼就不怕让草碰到。
……(省略)
谁都知道斩草要除根,可有些草的根子实在长得太深了,锄头若要追出来就得一口气深入五千年的地底。
锄头,这种最早为农人发明并广泛使用的除草利器,经过千百年的被使用与被爱惜、被尊重与被依仗、被摩挲与被把握,它的木柄与锄刃早已成为农人的胳臂指节甚至就是农人自己。当现代化机械与耕作还没有能够深度更替这种工具之前,对于一柄锄头的理解与书写,就是对农人对农人后裔的作者自己的书写。而支禄,发挥并自豪着自己对农时农事的熟稔,对节令季候的敏感,对农作物和农业劳动的如数家珍与了如指掌,在细数泥土里深耕的日子中,持有不改的如初情愫,甚至在谴文造句的时候,更多出一重回放与回访的在场感。在一再的描摹与倾诉、刻画与书写中,诗人对生活的反思、对时代的体认、对自然力前人的命运的体察,都有着人文精神的闪烁与烛照。土地因而有了人情,庄稼因而有了人性,人也因而有了与时光相扶持、与生活相和解、与命运共相济的人文光辉。
大西北是多民族共存的生存家园,支禄一再留足笔墨,将文字流向众多的兄弟民族,勾勒各民族在严酷自然面前形成手足深情共同体的群像。像打囊人、鼓手、卓玛这样的取像,像江布拉克、七克台、塔河岸边这样的取景,像人间烟火、定西一带的麦子熟了、那羊这样取譬,无不在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生活现场中,不否认人世的亏欠也不掩饰既有的满足,不停止恩典的明证也不放弃力量的确认。于是,在苍茫的大西北,风拍着,终极意义也自始至终地储藏着发现着光大着,就像《拉瓦依坎》中眼泪与歌声的交合横溢:
在戈壁,流水让日子停下来。
日子停久了,就是片片绿洲。
就有了手鼓、萨塔尔、艾捷克、热瓦甫……
三、歌源于诗性:眉眼间的侔色揣称
相对而言,《风拍大西北》不乏知性但感性更重,甚至感性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诗人刻意凸显的。笔者以为,正是这种酣畅淋漓的抒发形式,这种将万千感喟凝而为诗的汁液饱满,这种以歌代思的喷薄而出,才更适宜大西北之猎猎雄风与漠漠大野,才更匹配诗人滔滔诗思和浩淼情肠。
或者,这恰是诗性当有的形貌风神之一种?!
在严酷的生态环境中,诗人当然要铺陈其目之所及的流沙飞石、连天狂风、枯草败叶、皲裂冰冷,但他更在意勾勒、聚焦大自然中那些富含精神寄养的生灵物象,更愿意为那些能够予以人类某种开悟的启迪赋形,更留心在自然褶皱中卑微而顽强地存活、繁衍甚至有着小小幸福的人们。于是,心灵世界重叠于自然世界,笔下风物浸透情感。那些耳鬓厮磨的牛驴骆驼,那些晨夕相对的风沙草花,那些一直未辍的耕作收获,那些长在心里的村课书声,那些返回梦中的借钱捡柴——看得见的是人间烟火,忘不了的是塞上黄昏,挥不去的是乡土草木。当这一切都成为诗人的眼中流水心上星火,他必采取与生活本色最贴近的原色着笔,其结果便是,直抒胸臆而感性汹涌,民间言语而通晓流畅,细节闪烁而直抵人心。“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3]P573,这种随心而出的率真、诚挚,不事雕琢的本色、原味,成为与大西北最相宜的抒情形式。可以随便拿出一节来咀嚼这种为支禄所特有的诗性之魅:
一些草哭着远走他乡。
一些草哭着又回来了。
多少草长跪不起,向着河西的苍天祈雨;多少草背井离乡,为的是找一条河流;多少草让风沙吹弯,低头发现还匆匆赶在路上;多少草让风沙打得鼻青脸肿,翻过年又若无其事的样子。(《河西》)
燃烧的果实,难道不是太阳沉淀的血色?(《沙拐枣》)
野火,一匹红色的马驹,不停地用舌头舔着天空。……火,坐过的地方,像是一滩夜的心事。(《野火》)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风拍大西北》中,支禄那些并不匮乏的历史沉思、自然启迪、生命顿悟与诗性的获得有了脱节和疏离。相反,在一部以地域为基本取景点、意旨相对一而惯之的散文诗集中,这些倾注着诗人精神与情感的发见、指认与明晰,正是这部散文诗集诗性获得的另一种关键性支撑。有所不同的是,支禄既不削足适履地让思想非要凝结成颗粒生硬嵌入自己的曲谱,也不屑于那种一再标榜式的自我张目,他更愿意通过浑然天成的个体隐喻和整幅歌唱的流程展示,来实现自己的和声走向。
支禄是具有文学大心志的自觉作者。从《点灯,点灯》到《风拍大西北》,他走得执著而坚实,这有他业已呈现的文体意识、文本诗性和诗学修为可资证明。散文诗已经步入一个长足发展的兴旺时代。作为一名散文诗实力作家,如果进一步锤炼自己的文本驾驭力,特别是在语言精湛和题材开拓方面的有所精进,笔者相信诗人更上层楼为期不远。
[1]支禄.风拍大西北[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2](美)鲁道夫·阿恩汉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M].腾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谢榛.四溟诗话——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A Gale has: Soul Train Dance and Hao Ge— On the Artistic Spirit of Zhi Lu’s Prose Poetry “The Wind Strikes the Northwest”
FAN Ke-jie
(He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Finance, Zhengzhou 451464, China)
Turpan and Gannan in Xinjiang are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of the northwest and the derivation field of their literary thoughts.The intensity of the wind and the size of the northwest, which is a symbol of the matching of the vast space, are the observation angle and the field of confiding of the poet. Thus, the prose poetry of the branch has realized the fusion of regional and universality, the clarity of selfinsinu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filtration.
Zhilu; “The Wind Strikes Northwest”; Aesthetic;The humanities; Poetic
I206.7
A
2095-3763(2017)04-0089-05
10.16729/j.cnki.jhnun.2017.04.013
2017-09-08
范恪劼(1963- ),男,河南郑州人,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韦伯国际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宋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