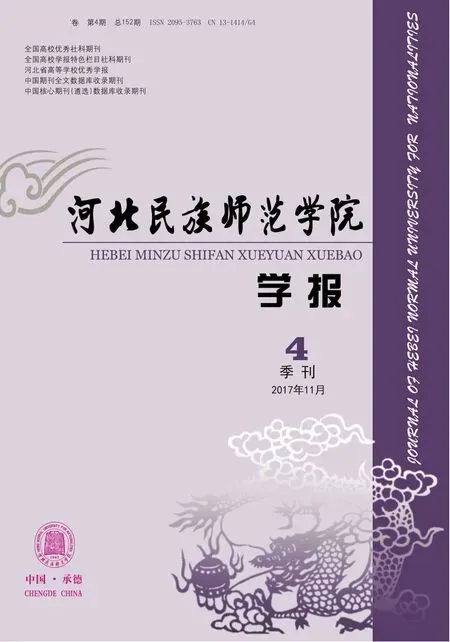余华“接近真实”的小说叙事特色
梅向东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余华“接近真实”的小说叙事特色
梅向东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余华究诘什么是“真实”,这是其理性思考的进程,更是其小说写作的进程。余华“接近真实”的创作之旅,其实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入文坛习作阶段,小说是大众化常识和经验的叙述,可谓是“实”而不“真”;第二阶段是突越常识和大众思维,实施极端个人化的精神冒险阶段,其小说是一种极端想象,可谓是“真”而不“实”;第三阶段余华再次呈现坚实的日常现实的“实在”,以这个“实在”使得宇宙人生的真相获得大众化的经验和现实形态,为真实的“此在”现身,可谓是即“真”即“实”。
余华;真实;实而不真;真而不实;即真即实
1989年余华说过一句至今依然十分经典的话:“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1]P158它朴素得就像《活着》里的福贵和《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然而,它却是具有某种真理性的表达,犹如罗伯-格里耶所说的,文学的不断变化,究其根底其实是真实性概念在不断改变。[2]P200余华究诘什么是“真实”,其实就是在究诘什么是小说以至什么是文学,而这在他那里,既是一个理性思考之旅,也是其创作之旅。余华的小说叙事,其实历经了三个阶段:从1983年首次发表《第一宿舍》到1986年,是第一阶段;从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到1990年是第二阶段;1991年发表《在细雨中呼喊》以后是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既各有差异,又前后有序,既反映了余华小说叙事的发展变化过程,又体现出余华小说叙事的个性化特色。
一、“实而不真”:余华小说叙事第一阶段
如果说余华“接近真实”的理性思考是从1989年真正开始的话,那么,他“接近真实”的创作实践之旅,却比这要早。它始于1983年,这一年余华的处女作问世。从这一年到1986年,余华发表了九个短篇小说,它们是:《第一宿舍》《“威尼斯”牙齿店》《鸽子,鸽子》(1983)《星星》《竹女》《甜甜的葡萄》《男儿有泪不轻弹》《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1984)《老师》(1986)等。可以说,这九个短篇小说构成了余华小说叙事的第一阶段。
显然,这一阶段的小说,是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中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哺育下产生的。当1989年余华反思那一阶段的作品时说,那时“所有思考都只是在无数常识之间游荡”“使用的是被大众肯定的思维方式”,[1]P161显然他所说的“无数常识”“大众肯定的思维方式”,即是指从伤痕文学乃至寻根文学的叙事理念和方式。也就是说,曾经一度,那些常识通过社会话语编织和再现出一个大众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余华就是在人云亦云中,遵从于既成的文学陈规,去叙述大众生活经验,与传统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并无二致。虽然这九个短篇小说是余华初登文坛的习作,尽管后来余华对它们再也不愿提及,它们没有进入余华的文集,也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批评视野,但当将它们置于余华小说叙事的发展历程考量时,便会发现它们并非没有意义。它们是余华小说叙事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余华后来究诘什么是“真实”,便是基于他第一阶段的创作经验,或者说正是对那一阶段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才真正激发了他后来“接近真实”的强烈诉求。1989年余华公然宣称:“生活是不真实的”[1]P164,实际上是说大众经验其实是“实而不真”。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真实,大抵有三种:或指经验的真实;或是科学的真实;或是新闻的真实。经验的真实遵从于大众化、固化的认知判断,它来自于习惯、传统、常识的尘封;科学的真实指向于世界是物质的,真实是原子、分子结构的构成;新闻的真实则只在于对外在世界的拍摄式成像。它们构成集体无意识般的现实原则。尽管后来的余华以为它们“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人淹没了自我的个性,泯灭了个体化经验,这使得文学“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1]P158-159但那种“实而不真”,却是余华小说叙事的最初姿态。在他那川端康成式的温馨、忧伤而诗意的叙述中,余华以感觉之手细腻而质感地抚摸着每一个事物,呈现出它们的轮廓、色彩和形态。就像每一条路有一个路标指向目的地,余华的语言平静而准确地指向事物。虽然年少的诗意织起的梦幻,掩饰和遮蔽了生活和人性的许多真相,但就像所有的现代主义绘画大师都必会经历了一个临摹写生的扎实训练,都有细腻写实的塑形功力一样,余华最初九个短篇小说的“实而不真”,正意味着他在形象、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扎实的写实基础的形成,它是余华踏上他的小说叙事之旅的重要标志。
二、“真而不实”:余华小说叙事第二阶段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向来是一个常识,当1989年的余华质疑这个源泉时,他已经相信“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1]164那是在1986年以后余华先后完成《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及《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现实一种》等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发生的。这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应是振聋发聩。那么,真实在哪儿?重新追问这个问题就是重新追问文学是什么。既然外在的生活是不可信的,那么就只有回返内在的精神。余华说:“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因为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在人的精神世界里,都将重新接受审判和裁决。“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的无边无际”[1]P164。从1986年开始,余华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精神里,去颠覆习以为常的生活提供的价值。也正是在那些创作的基础上,1989年的余华坚信,只有人的精神,才可以突越生活的不真实的藩篱,当破除既成经验常识的尘封和冰冻,世界的真实便广大无比,对此,直到十年之后的1999年,他还描述这样的广大:“伟大的作家的内心没有边界,或者说没有生死之隔,也没有美丑和善恶之分,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相处。他们对内心的忠诚使他们写作时同样没有了边界。”[3]所谓生死之隔、美丑善恶之分,正是出于社会——历史模式下的生活经验,就是“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而内心世界的广大无边,则是超越社会——历史模式进入宇宙——人生模式中才会显现的生命真实。大众化经验不是真实,理性认知的必然不是真实,新闻报道的事物不是真实;大众经验中、认知的必然里、新闻事件中,真实的事物抑或事物的真实往往抽身而走了,“不在”那儿,它幽闭了,障蔽了。那么,余华究诘的真实,就只有在作家的叙述中出现的个人化经验、偶然的现实,那是作家广阔的精神领域。如果说余华小说叙事的第一阶段是“实而不真”,那么从1986年开始,他进入的是“真而不实”的小说叙事。
1987年余华小说陡变,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标志,他开始了突越常识和大众思维,实施极端个人化经验表达的精神实验,由此余华进入了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1年的五年间,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1987)、《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死亡叙述》(1988)、《往事与刑罚》《两个人的历史》(1989)、《偶然事件》(1990)《在细雨中呼喊》(1991)等,展开了一种极端的文学想象,敞开出了余华式的广阔精神领域。他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汹涌井喷的,是关于暴力、本能、仇恨、杀戮、死亡、虐待、恐惧、阴私、猥琐、乖戾、凶残、欺诈、荒谬、野蛮、混乱、冷酷、堕落、痛苦……的空前想象,那是一个完全颠覆了大众化经验、理智的必然、新闻式言说的世界。从天空、大地、河流到道路、房屋、情感,从人性之恶到世道之厄、命运之舛,从社会——历史到宇宙——人生,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充斥其间的,是裸露的存在荒原、生命的深渊。那是本原性的存在真相。它鬼魅般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余华以自我式的精神冒险,曾猛烈地颠覆了1980年代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冲击着人们的阅读心理底线。那无法超越、无法救赎的绝望感,至今都令人战栗和不堪。这是之前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中所没有的,甚至也是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写作的世界里从未有过的。在之前的汉语小说中,从未有如此关于暴力与死亡的饕餮大宴;尽管之前的文学或许不乏悲剧,但它们大多是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中去揭示世道人生的悲剧,它是诸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是在历史主义的坐标中预设了一个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规律,因而是可以超越和救赎的悲剧。即便是像鲁迅直面的“惨淡人生”也是如此,至少人们大多是在中国式的启蒙立场下那样去接受鲁迅的。从1987年到1991年余华的小说世界所“现身”的,仿佛是从那社会——历史坐标游离而出的鬼魅般的宇宙——人生惨象,那是绝对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没有灵魂、没有皈依的存在性荒原和生命真实。余华自己都这样说:“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1]P162如果说1987年到1991年余华小说犹如一个实验场,那么那场精神实验,就是要以极端的个人化经验、偶然的事件、内心的冒险,去接近真实:“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1]P163这另一部分现实,就是余华揭橥的一种真实,那就是宇宙人生的悲剧性真相——存在的荒原。
三、“即真即实”:余华小说叙事的第三阶段
然而,1991年后,余华小说叙事再度发生急变。一改80年代后期的极端化文学想象,余华转向极端平实的生活现实,不再是极端的个人化经验和精神实验,而是以活生生的日常现实形态,叙述大众经验。从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具有了形下的坚实基础和现实形态,惟其如此,更有了形上的深度。这是《在细雨中呼喊》(1991)《活着》(1992)、《许三观卖血记》(1995)《兄弟》(上)(2005)《兄弟》(下)(2006)乃至《第七天》(2013)所共同呈现的。这些作品,其实都是在讲述“活着”。活着就是现实性的生存,它是衣食住行、生儿育女、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无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在活着;“活着”是永远的现实进行时,是富有质感的“此在”;“活着”也是“人生代代无穷已”的背负和行进。余华让宇宙人生的悲剧真相成为了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经验,从而更具有个体化、切身性,因而更具有普遍性。“活着”的分外平凡而悲怆,就在于它不是游离于社会——历史的框架而如鬼魅般飘忽,而在于就在日常的亲历中现出宇宙人生的真相:“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8]3;就在于它不是暴力和欲望扩张下存在的荒原,而在于卑微、琐碎和平庸中生命的华严。无论是福贵的活着,还是许三观的活着,李光头、宋钢的活着,杨飞的活着,莫不如此。如同他们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抑或说像他们那样实实在在的生活,正是余华1991年以后所接近的真实,那是宇宙人生悲剧真相的现实存在。正如意大利《共和国报》1997年7月21日有这样说的:“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去不死。”同年韩国《东亚日报》1997年7月3日也有:“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9]
在1991年写完《在细雨中呼喊》特别是在1992年完成《活着》后,余华的小说叙事再度发生陡变,那当然是因为余华的真实观再度发生了微妙变化。1989年他曾说,有关真实的思考还将继续下去,他已无法阻止自己的这种思考;它将是一个“思考的历程”,而不会有固定的答案。[1]P161这话果然成了现实。1993年,余华说:“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4]P2他所说的“过去的现实”,即是指他1987年到1991年间作品中的世界。显然他对那时的精神冒险、对那时的个人化经验开始有所反省,尽管依然认为“充满魅力”,但却“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1989年他宣称“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此时则认为“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既然生活中的现实是真正的现实,那么这就等于说“生活是真实的”。在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后,1995年余华更加明确地说道:“在过去,当我描写什么时,我的工作总是让叙述离开事物,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被描写的事物可以真正的丰富起来,从而达到我愿望中的真实。现在问题出来了,出在我已经胸有成竹的叙述上面,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5]P2551996年又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某种想象中的,现在的现实更接近于现实本身。”[6]在对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的比较中,不难看出余华对于它们的有所甄别,而这就是对两种真实的甄别:过去小说中的,是破除现实生活的不真实而展开的个人化想象,唯有让叙述离开熟悉的事物才感到不为物所役,因而“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4]1,从而抵达“愿望中的真实”。而现在小说中的,却是更接近于现实本身的现实,而这正是过去所拒斥的不真实,它正是大众化的经验。显然余华在1991年以后由想象的现实回到了生活的现实,过去所认为不真实的,现在则是他“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余华越来越坚信,那“活生生”的真实,不在于拒斥生活,而在于接近现实。就像他2002年所说的:“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7]P114
然而,并不能把余华的这种变化,看作是他对过去真实观的否定,就像他回到生活现实,却并非是否定内心精神的真实,也并不见得是对“生活是不真实的”的否定。恰恰相反,余华是为了生活现实和内心精神的统一,而不是过去两者的分离。过去以否定生活现实去求得内心精神的真实,而现在回到生活现实,就是回到作家自我的生命真实,或者说是作家自我的生命真实面向生活现实的敞开,因为只有在作家的叙述中自我生命敞开为生活现实时,真实才更是“活生生”的“现身”。比起先前,余华更加明白,真实就是“内心敞开”,内心的敞开,犹如光的烛照,生活现实才会“现身”而真正地存在,“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4]P1。
我们可以这样地说了:余华过去是以拒斥现实的方式接近真实,现在是以接近现实的方式接近真实;过去是以自我想象的现实接近真实,现在是以内心敞开为现实的方式接近真实。如果说过去是“真而不实”,现在则是“即真即实”。
四、结语
在“接近真实”之旅,余华写与思并行。什么是真实,是余华之思,它是真实观以至小说观、文学观;真实是什么,是余华的写,是小说叙述的呈现,它是小说的现实形态。就像余华1989年反思他第一阶段作品时所说的,那些习作中的世界,是大众化的常识和经验,它很“实在”,但却正是这“实在”淹没了真实,它使得真实无法现身,这一时期的小说可谓是“实”而不“真”。第二阶段的小说,余华拒斥和颠覆了大众化的常识和经验“实在”,谋求以极端想象和精神的现实,直接使真实现身,这一时期的小说可谓是“真”而不“实”。第三阶段余华再次呈现坚实的日常现实的“实在”,以这个“实在”使得宇宙人生的真相获得大众化的经验和现实形态,为真实的“此在”现身,这一时期的小说可谓是即“实”即“真”抑或即“真”即“实”。这让我们想到禅宗三关之说:第一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关见山非山见水非水,第三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余华的“接近真实”之旅和它颇有相通之处。
作为叙述形式的呈现,在余华那里,“实”而不“真”一如传统的写实主义;“真”而不“实”犹如西化的现代主义;即“实”即“真”或即“真”即“实”,则是像余华所说的“让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5]P255,如果叫什么主义的话,姑且可谓之“现代写实主义”。“实”而不“真”是“就事论事的写作”,它遵从现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逻辑和秩序去叙述。到“真”而不“实”,余华“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它背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1]P160到即“实”即“真”或即“真”即“实”,余华则用现代叙述技巧去写实,它既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叙述形式,也与传统的写实主义不同,它是但丁、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舒尔茨、辛格、鲁迅、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等共同哺育的结果。
一直以来,余华叙述形式的转换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人们事实上把余华视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先锋派迅速崛起和衰落的标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场无可阻挡、泥沙俱下而日渐深重的商业大潮席卷天下,甚至带走灵魂的历史情境中,新时期文学似乎显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就像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场流星雨一样的先锋派作家,此时似乎都别无选择地蜕变和转型,其突然性就像当初的崛起一般。这其中余华的确是那样的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然而,就像把余华看作这样的转折的标志其实并不合适一样,在那样的背景下按那样的逻辑去看待余华叙述形式的变化也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对余华的误读。因为按照先锋派从崛起到衰落的转型逻辑去衡量余华小说,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诸如:先锋精神的丧失;回归现实的妥协;想象力的枯萎;小说艺术的后不如前。如果说这在不少先锋派作家那里的确是事实的话,那么在余华那里却非这样。恰恰相反,从“实而不真”到“真而不实”,再到“即真即实”,余华叙述形式的转换,不仅是自我超越,而且更是后出转精;它是余华小说叙事的不断发展成熟,同时也是余华小说在发展变化中叙事特色的个性化呈现。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2]罗伯-格里耶.重现的镜子//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第3卷[M].杜莉、杨令飞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
[3]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J].读书,1999,(7):43—48.
[4]余华.活着前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后记. [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6]余华、潘凯维.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关于〈许三观卖血记〉及其他[J].作家,1996,(3):56—58.
[7]余华.说话. [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8]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9]余华.活着封底[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3.
Be Realistic but not True, Be True but not Realistic, Be True and Realistic——The Three Phases of Yu Hua’s Novels Narration
MEI Xiang-d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Yu Hua had made cautious inquiries about what’s the true and realistic, which was not only the course of his rational cognition,but also the course of his writing. In fact, he had undergone three phases in his writing of novels: in the first phase, what his novels narrated was the common sense and experience when he entered the literary world, the novels were realistic but not true; in the second phase, when he broke through the common sense and carried out an extreme personal spiritual adventure, his novels were an extreme imagination, which was true but not realistic; in the third phase, Yu Hua presented the solid reality again, and used it to get the common sense and realistic condition, his novels were true and realistic.
Yu Hua;True and realistic; Narration
I206.7
A
2095-3763(2017)04-0034-05
10.16729/j.cnki.jhnun.2017.04.005
2017-10-10
梅向东(1964- ),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小说发展史论”(编号:10BZW089)。
责任编辑:于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