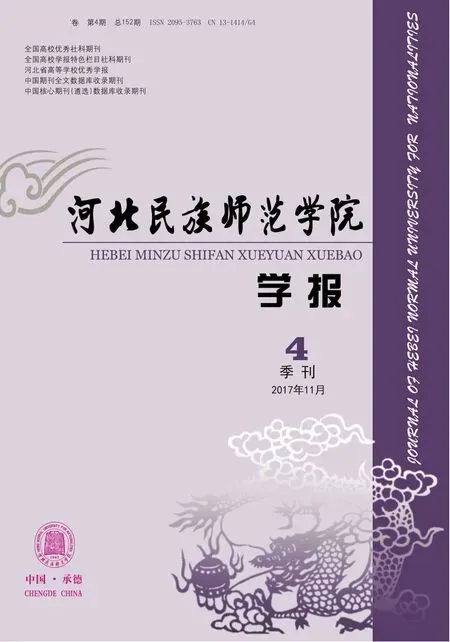满族文学历史想象的可能与文学经验的呈现
——以叶广芩的《采桑子》与《全家福》为例
王 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满族文学历史想象的可能与文学经验的呈现
——以叶广芩的《采桑子》与《全家福》为例
王 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满族著名作家叶广芩,因其正统皇族贵胄的出身,以及对家族历史风云与时代变迁的执着书写,成为当代作家中的独特存在。代表作《采桑子》和《全家福》,即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想象历史与呈现文学经验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在叙事话语的建构上,《采桑子》删繁就简,将宏大、玄虚的历史,落实到若干具体个人身上,造成小说总体结构的松散。而《全家福》则将家族故事完全纳入先后承续的历史时间框架中,陷入历史大于人的困境;此外,族性和现代性濡染下的“京味”也呈现出新变,即从意象化到虚化,乃至消弭于对时代表象的截取和拼贴中。保有“总体”和“断裂”的审美眼光,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而重新深化和提升对“贵族精神”的理解,并将其化入小说的创作实践,则是从源头上提升作品艺术品格的根本所在。唯此,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为一己、一个家族、一个朝代所限,发出保有自己族性特质的时代之音。
叶广芩;《采桑子》;《全家福》;历史;经验
少数民族作家因其独特的“族性”和视角,早已成为我国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曾入主中原的满族,则因其对整个华夏民族影响之全局性、深刻性和持久性,成为最应瞩目的力量之一。满清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衰朽与终结第一次有不可阻挡的现代性力量介入,于是,专制与自由、传统与现代、科技与迷信、野蛮与文明等因素从未像满清时期这样尖锐冲突过。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奇劫巨变”的时代。而如何想象和书写这段历史,也成为作家需肩负起的责任。检视百余年来的相关作品,我们发现,满清统治者多数是作为反动、腐朽力量的代表而被唾弃的,更不可能站在他们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反思。所以,在清朝灭亡之后,以前王宫贵胄、八旗子弟们的生活也一并被外界风起云涌的历史浪潮所吞没,无人再去钩沉和关注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无疑不是严肃的文学眼光,而是偏狭的政治眼光。而当代著名满族作家叶广芩,则以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将笔触伸向自己的家族,书写从晚晴、民国到现在前清贵胄们的生活,勾勒出一群失去政治特权的遗老遗少们,在波澜起伏的时代激流中的生命轨迹,在整个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本文选取叶广芩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采桑子》和《全家福》,作为分析对象。前者是具有自传性质的家族小说,作者对于满清没落贵族的复杂情愫在其中有突出体现。后者以民国至当下这段历史为背景,讲述了前清一户工匠世家几十年的悲欢离合。二者有共同的想象主体——历史,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满清和北京,也有共同的叙事载体——家族。更重要的是,两部小说较为全面地提示出作为一个群体的满族,是如何想象家族曾有的辉煌与现在的落寞,如何面对不可阻挡的现代性力量,如何看待跌宕起伏的民族命运,如何反思这一命运背后更深刻的奥义。在方法上,我们将在社会学、文化学基础上,结合经验美学的方法,力求进入创作规律的层面,对两部小说的得与失进行综合分析。
一、经验美学与叙事话语的建构
笔者曾尝试提出经验美学的概念,认为“人作为美的感性存在,总是洋溢着勃勃的‘感性冲动’,向往无限丰富的感性生存境界;人作为虚构的存在物,总是喷薄着不息的‘形式冲动’,力求赋予生活世界以把握的统一性。单独的感性和虚构都无法对人的生存作出全面描述,而经验作为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概念,它所欲描述、概括的正是感性和虚构这两种本能力量的博弈对人生存的塑造”。[1]文学经验就是对人之经验的呈现和凸显。对于作家而言,要呈现文学经验,首先需要总体性的眼光,抓住承载生活世界“可经验性”的文化记忆。同时,还需“断裂”的眼光,瞩目于人“感觉结构”的断裂处。这样才能捕捉到历史大转折时期,个体迸发出的感性因子。对于落寞的前清贵胄而言,他们是时代“断裂”的亲身经历者,其“感觉结构”必然也经历了断裂,在民国以来的百年风雨中,他们的人生际会无疑是多数人没有的。叶广芩感同身受般地抓住这一点,展开自己的叙事话语。
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满族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形态急剧地由低级到高级转变,随之而来的帝王霸业的成功与家族悲剧的形成,促使满族对人生具有特殊的体验和理解,影响到满族文学自始至终染上浓郁的感伤色彩。”[2]P4《采桑子》就是这样一部“感伤”的作品。小说中的“我”生长在一个晚晴旗人大家族,其祖父尚有“镇国公”头衔,兄弟姐妹多达14人,如何有效组织一条顺畅的叙事线索是作者的一道难题。总体看来,作者避开了网状结构的繁复,而是化繁就简,选择了几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即大姐金舜锦、二哥金舜镈、二格格金舜镅、舅姨太太、四格格金舜镡、侄子金瑞、老姐夫完占泰、七哥金舜铨。全书的章节就是根据上述人物的顺序依次展开的。这一设计有效规避了家族成员同质化的一面,凸显出其与众不同的一面,从而将家族成员的丰富性展现出来。于是,金舜锦的人戏不分、舅姨太太的因循守旧、老姐夫的走火入魔等特征均十分鲜明。叶广芩将相对宏大、玄虚的历史,落实到具体个人身上,让每一个人都负载历史、家族的某一部分意义,历史成为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物的人生道路,更多地是其个性使然,历史感和命运感不强。可以说,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是一篇独立的中篇小说。这一结构的设计造成了小说总体结构的松散,缺乏内部逻辑上的关联,尤其是各条线索之间缺乏必要、必然的情节铺垫。
我们认为,家族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同时呈现多个家族成员之间因血缘、生活而产生的复杂关系,亦即家族性。它的结构最好是网状的,任何一条线索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个人因有家族属性的注入,而更显其丰富性、深厚性。更重要的是,优秀的家族小说本身可以使我们通过窥见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进而从中体悟到某些规律性,乃至哲学层面的内涵。而且,对人生和命运的终极思考,往往是在对一个大家族成员总体命运的反思和感悟中才能体会到,举凡经典的家族小说,比如《红楼梦》和《百年孤独》莫不如此。所以,《采桑子》名为家族小说,但是其内在结构并没有充分发掘出“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能量。
与《采桑子》不同,《全家福》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小说紧密围绕王满堂一家的悲欢离合展开,一家人历经民国、解放、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可谓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初具“史诗”的规模。王满堂虽不是满清贵胄,但他却是京城“隆记”营造的第十九代传人。祖辈上自明永乐十五年起,便一直承担北京紫禁城等皇家建筑的工程,深得传统文化、皇族文化的濡染。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建筑,有一种源于骨子里的认同,这便决定了他在以后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但是,由于书中内容不像《采桑子》那样带有自传性质,作者便不得不借助于历史的力量来结构、推动全书。所以,总体看来,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并没有超出我们现已接受的教科书上的知识框架。换言之,该书的情节能量不是源于人本身,而是源于已知的历史。这种感受在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上尤为强烈。比如,小说第六章,讲述“文革”的发动。小说中写道:“梁子觉得他的妈是个大糊涂蛋,跟他妈说话太费劲,索性不理他妈了,这时门墩高高兴兴跑进来,报告他哥一个好消息:革命了!梁子问谁革命了,门墩说咱们革命了。梁子问革谁的命,门墩说革文化的命。”[3]P183显然,作者安排小孩来告知“文革”发动的消息,远未取得某种独特的“陌生化”效应。“文革”的酝酿和发动,必然在北京老百姓的政治、文化生活中逐渐产生影响,应当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得以窥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蛛丝马迹,这些才是文学艺术需要捕捉和呈现的经验。正如昆德拉所说,“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4]P47然而,作者这里的叙述并未提供“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突然就来了,王满堂家附近的老百姓们突然之间就顺当接受了革命的教义,他们是否有过困惑?是否有过犹豫?是否有过抗争?等等,这些更隐秘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唯一对此运动有剧烈反应的是精于风水术的老萧,他预见到,“我看这场运动我是在劫难逃,死活难论,有些事不如早做安排。”[3]P184但他的依据却是,“煞气直侵,以俭德退缩以避之已不可能,也是我祖上泄露天机太甚。事已至此,改着有此一劫。”[3]P185可见,作者并未在其虚构的世界中较深入反思“文革”发动的历史、文化根源,反而用风水师玄虚的言论轻而易举地回避了对这一运动的追问。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文革”小说在创作思维上经历了“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的转变[5],那么《全家福》中的“文革”书写则尚未融入这一文学思潮,影响了作品艺术水准的攀升。总之,整部小说中,人物似乎只是在事先划定好的历史区间内活动,人物的言行和思想在从一个时间段跨入另一时间段时,较少见出其转变的过程,这便导致人物的性格缺乏说服力。
二、族性与现代性濡染下的“京味”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旗人,对京味的追求是叶广芩一直的目标,并且向“京味”这一美学概念中注入了新的因素。有学者对京味小说作了代际划分,即老舍 是开创者,是为第一代,特点是描绘中下层百姓日常生活气息,熨帖、平易、亲切;邓友梅、陈建功等为第二代,着意于没落士卒和特殊行业的手艺人,由于他 们并非北京人,总觉“隔”了一层;王朔、刘一达等为第三代,他们则发掘北京的地理风俗、世故人情,但有“炫独”“炫奇”之嫌疑。[6]那么,叶广芩的京味小说应归于那一代呢?显然,独特的出身与写作方式使其不好轻易地归类。经过比较,笔者认为族性与现代性两种力量是决定叶广芩京味小说特质的两大根本因素。那么,京味这一文学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王一川教授对“京味”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他深刻指出,“京味文学的特质在于,它是一种回瞥到的故都北京的地缘文化景观,确切地说,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式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到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7]以此为参照我们发现,叶广芩的小说与其并非完全对应,各有侧重,凸显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族性与京味的意象化。与上述三代京味作家相比,叶广芩小说中的京味不再主要是渗透于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寄寓在几位落寞的皇族贵胄身上,他们的“皇气”“贵气”虽已不在,但骨子里面的那份清高、天真、偏执、玩世不恭却因王朝谢幕反而愈显强烈。由于作者本人抱以极大的唏嘘和深刻的“同情”来叙述这些人物,导致这些人和事本身成为审美的对象。其不再仅停留于情感上的抒发,更多的是凝定为一组历史“局外人”的意象。比如《采桑子》开篇对大格格金舜锦一生的回忆,就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个没落皇族大家庭对京戏的痴迷,以及在名利场上的挣扎。大格格一生的经历是简单的,因戏而生,因情而死,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这一态度本身就是审美的,这在五哥金舜锫身上则登峰造极。老五经常佯装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地在街边要饭,还故意在大饭庄门口扮乞丐要钱,以戏弄别人。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对他们来说是游戏的过程,从那自轻自贱中寻觅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乐趣,体味一种失落的兴奋。”[8]P215可见,作者对这一犬儒的“末世”情绪的理解是准确的,小说将其抓住,并涂抹于整部作品之中,逐渐形成足以高度概括清亡之后一代,乃至几代落寞皇族人生的审美意象。这一意象无疑应是“京味”的应有之义。
其次,族性与京味内涵的虚化。王一川教授曾概括出京味文学的五要素:地、事、风、话、性。即是说,要从这五个维度入手,才能最充分地发掘和表现京味。叶广芩没有选择面面俱到,而是从自身家族的独特经历和皇族文化传统出发,不再停留于日常生活中人情世故的玩味,而是瞩目于更具文化、历史意义的事物——建筑。两部小说都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了老北京的城楼,并由此引出大量传统文化中有关地理风水、八卦、陶瓷、砖木等方面的内容。但作者并不止于此,而是不失时机地将对建筑的留恋升华至对人生,乃至全民族认同的高度。比如《采桑子》中,廖先生雨中回忆城楼时说,“你看故宫三大殿,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地往那儿一蹲,任你再大的建筑,尖的、扁的、圆的、高的、矮的,谁也压不过去。为什么?建筑的气势在那儿摆着呢,这就是中国!”[8]P188《全家福》中,王满堂为保护东直门免遭拆毁,与柱子大闹一场。“文革”期间,王满堂向梁子索要集福寺上的“二凤”时说,“再过五十年、那时候二凤它还在房顶上站着,你在哪儿呢?”[3]P193类似这样的,堪称作者直接发言的段落还有很多,可见,叶广芩是精心选择了用古建筑来承载她对故都北京复杂的情愫。这里渗透出来的京味则已经超出传统“乡愁”的范围,不再是熨帖、平易和亲切的,而是以一种无法挽回的惆怅、衰颓为底色,并从今天的视角为其注入了一种更博大、高远、深沉的意蕴。由以上引文可知,这些话更像是作者本人情感的直接抒发,表达了对逝去王朝的留恋与认同。而在小说中由人物代言,难免有跳出故事情节的不适感。
最后,现代性与京味的消弭。王一川教授深刻指出,京味产生于“现代衰颓时段”,即是说,在北京城从千年古都向现代城市转变这一过程中,这座城市数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必将遭遇重大转型乃至断裂,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一种颓势。然而,就在这裂缝中,那些久已固化了的感性因子纷纷越出传统文化的地表,更显其生命力,这些因子乃是“京味”的内核。王一川教授将“京味”的这种独特审美形态概括为“流兴”,颇为传神。认为,“当原来生气勃勃的自足的感兴整体被无情地肢解、散落为碎片时,这些属于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典感兴碎片并不会轻易走向寂灭,而是会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流溢开来,生成新的流溢不绝的审美现象。”[9]P271可见,京味的“流兴”应产生于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语境的冲突之中,二者应在文化层面上进行对话,进而产生冲突,这样“感兴碎片”才能“流”起来,激起人不断“回瞥”的“兴味”。偏废任何一方,都无法切中京味产生的关键,而《采桑子》和《全家福》两部小说却在这里力有未逮。具体而言,《采桑子》中,作者沉湎于对家族往事的回忆,但对外界的现代性力量没有清晰的认知,京味因缺乏现代性力量的实际介入而变为简单的回味。在金家十四个子女中,真正介入现代社会的仅有两人,即五格格与六格格。前者解放后主动提出与完占泰离婚,并嫁给了已经是“副局长”的解放军战士王存,后者则成为一家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且笔墨不多。可见,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语境之间看不见实质性冲突。《全家福》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现代性的时间顺序来结构全书,尤其是后半部中,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向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于是,“经济承包责任制”“专利”“跳槽”“走穴”“练气功”“市场”“经济规律”“发廊”“传销”等这些改革开放催生出的标志性词汇系数登场。王满堂、大妞、门墩、周大夫、老萧、刘婶等主要人物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走马灯似的依次经历着每一个有代表性的发展阶段。表面看来,这些从传统中走过来的人物与现代性语境似有冲突,比如王满堂反对门墩为了钱而跳出国家的建筑队,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冲突多数是停留于人物的个性、性格层面,远未触及两种不同文化的根底。各种乱象好似幻灯片的拼接,流于表层。而京味,早已在这种快速的时间流转中难觅踪影。
由以上分析可知,族性和现代性力量是叶广芩京味小说书写需要重视的两个维度,也是时代给作家提出的新问题。族性,既可以提供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但也容易被其淹没,无法超拔出来发现更多的风景;现代性巨大的解构力量,在拆解传统文化形态的同时,也将传统文化更隐蔽的一面揭示出来,并有可能为京味注入新的质素,如何艺术化地将其呈现出来,而非一味的贬斥,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经验”的呈现与“贵族精神”的重铸
面对上述问题,仅从写作技术、技巧层面上无法触及本质,我们需要的是文学眼光的更新,这样才能较好地呈现文学经验。其中,“总体”和“断裂”的眼光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世界的可经验性是文学经验生成的外部语境,它需要文化记忆为其提供‘先验’预设和‘历史的经验总体’。如此,作家方能获得感受、想象和叙述世界的能力;断裂的眼光则是内在契机,它瞩目于人‘感觉结构’的断裂处。这里,固化的感性因子在断裂力量的撕扯下喷薄而出,成为凝集文学经验的内核。”[10]对于身世独特的叶广芩而言,尤需要同时具备这两种眼光,才能使其笔下的历史画卷不是沦为曾经有过的“经历”,也不是即时的“体验”,而是升华为内蕴丰厚的“经验”。
对于叶广芩而言,总体性的眼光并不缺乏,因为皇族的身世与大历史的主流叙述早已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文化记忆。而且,她还保有双重视角,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公共的。《采桑子》显然是前者的产物,《全家福》则是后者,依靠任何一种记忆,都可以迅速激活作者强劲的想象力。但是,当二者需要交汇的时候,作者则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掌控力,两种记忆都陷入萎缩,犹疑不前。特别是在两部小说的后半部,文化记忆的孱弱造成整部小说叙事动力的不足。因为在这一部分,现代性力量开始在故事的延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延伸到当下的现实生活,而这一段正发展着的“当代史”还没有被哪一种文化记忆所解释与整合,所以对其做文学想象的难度比较大。于是,在两部小说的结尾,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归伦理亲情,这当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犹疑在两种记忆之间的无奈之举吧!所以,为了获得总体性的眼光,作家首先需要整理、重组、探索自己的记忆资源,找准究竟那一种记忆足以长久地打开、支撑自己的艺术想象力。
作为个体的人是无限丰富的,他不可能被某一“总体”性的话语完全占有和宰制。所以,作家还需要一种断裂的眼光,以发现作为美的感性存在的人与外部“总体”性力量之间的裂隙。在这一方面,《采桑子》和《全家福》存在的不足就更明显了。作者本身沉湎于皇族文化记忆,这一已完成的“总体”之中,追念不已,缺乏从中超拔而出的艺术勇气。换言之,家族记忆厚重的作家在珍视这些记忆的同时,还需要保持一种“外位性”(巴赫金语)姿态,以获得一种人类学的、审美的眼光,将家族记忆中的人和事还原为一个文本加以二度经验,发现人物游离、逃离甚至反抗“总体性”力量的顷刻。艺术感觉尽量不为私人情感、情绪所左右,保持它应有的敏锐。对于现代性这一异质的力量,小说始终没有正面与其对话,我们看到的多是这一力量驱使下人物的左奔右突。我们认为,小说需要呈现出现代性力量是如何逐步进入人们生活的,人们的思维意识、行为习惯是如何逐步转变的,以及个体与其原来“总体”之间的裂隙是如何出现的。与之相比,张炜的名篇《一潭清水》在这一方面的艺术手法更为细腻和醇熟。
著名学者关纪新先生曾有一问,即“在世纪之交中华各民族争先恐后地向现代文明发起冲击的时候,满族的位置究竟应该在哪里?”[11]这一问,的确也道出了许多满族作家心里的忧思。满族,这一曾统一华夏大地的民族,在我们追赶现代文明的征程中如何自处,它身上有哪些精神素质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些重要问题决不能因清王朝的远去而被悬置。叶广芩为此作出了有益探索,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对“贵族精神”的阐扬。认为,“叶广芩文学世界中的‘贵族精神’以博学明理、儒雅知理、崇尚个性、律己修身、笃情重义为核心内容,分别从文化学识的素养、礼节礼仪的修养、审美情趣的培养、道德品行的涵养等方面对人的心灵操守和行为准则提出要求。”[12]我们认为,论者拈出“贵族精神”一词来概括叶广芩小说的内蕴追求是恰切的,但是对其内涵的阐释则仍停留于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和个人修为的层面,则有失深刻与时代感。毕竟,小说中还秉笔直书了金家后代许多玩世不恭,甚至龌龊不耻的一面。最让人为之心寒的是,《采桑子》最后写解放后我与一些亲戚去为祖母迁坟,不料一帮金家后人竟然为了争夺墓中的陪葬品而大打出手。叶广芩冷峻而又绝望地说,“我看见弟兄叔侄的眼睛已经发红、发直,彼此间谁也不认识谁了,露出毫不掩饰的憎恶,甚至谩骂与厮扭。”[8]P363作者将这一幕放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写,自然隐含了她对宗族命运的悲观情绪,并且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突围之路。
我们认为《采桑子》与《全家福》在精神指向上的模糊与困顿,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本人对“贵族精神”的理解需要深化和提升。这里的“贵族”当然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享有特权的统治者,“贵族精神”则与粗鄙、平庸、犬儒、媚俗、抱残守缺、玩世不恭、自轻自贱等相对,它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无必然关系。具体而言,“贵族精神”指的是“具有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道德性、创造性和审美性是其重要特征。”[13]P122对于满清贵族出身的叶广芩而言,其本身就自带一种贵族气息,她的怀旧、平和、幽默与智慧,正是贵族后裔的共同特征。但上述精神内容仍是纤弱、哀婉的,将其直接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则难以使读者获得精神品格的锤炼、熔铸与升华。所以,作者需要在原有贵族气息的基础上,反思和发掘出家族兴衰数百年来所散发出的“贵族精神”。由一个家族的兴衰,透视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品格,在道德、创造和审美三个维度同时为民族把脉。这样的精神境界才能廓大,才能不为一己、一个家族、一个朝代所限制,进而发出自己的时代之音。
结 语
叶广芩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这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中并不多见。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满族这一曾经问鼎中原的少数民族,今天依旧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光彩。独特的出身,再加上时代的变迁,使其创作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认为,一方面,作家尤需深耕满族自身卓异、丰厚的文化土壤,将根扎进满族文化的深处,找准满文化自身特色与其公共表达之间的结合点,这应是满族作家的立足之本;另一方面,作家仍需深切感知、感受、感悟时代、历史的变迁,力求对其形成自己的认识,并参照我国与西方优秀作家的艺术技法,探索自己的讲述方式。如此,满族作家才能讲好、书写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1]王岩.传媒文化语境下文学经验危机的美学反思[J].中州学刊,2016(7):157-163.
[2]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3]叶广芩.全家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4](捷)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李新亮.“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J].当代文坛,2011(4):44-47.
[6]王中.三代京味小说比较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5):188-198.
[7]王一川.京味文学的含义、要素和特征[J].当代文坛,2006(2):7-10.
[8]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9]王一川.文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0]王岩.“总体”与“断裂”:构筑“可经验”的世界——文学经验生成的外部语境与内在契机[J].文艺理论研究,2017(5).106-117
[11]关纪新.当代满族文学的“族性”叙说[J].民族文学研究,2012(2):53-67.
[12]席扬、林山.中国贵族精神的丰富性表达——再论叶广芩家族叙事的文化图谱与意义指涉[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5):119-123.
[13]田崇雪.文学与感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Literary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Ye Guangqin’s Caisangzi and Quanjiafu
WANG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The famous writer Ye Guangqin has been the unique existence in contemporary writers because of the orthodox royal family of origin and the writing of family history and time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Caisangzi and Quanjiafu reflect his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imagining history and presenting literary experience. On the one h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Caisangzi carries out the grand and lofty history on some specific persons, which leads to the looseness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novel. However, the Quanjiafu takes the family story into historical frame of succession, and falls into the plight that history is bigger than man. In addition, nationality and modernity bring new changes to the “Beijing Style”, from the image to blur, and avert in the intercept and collage of times appearance. Keeping the aesthetic view of “whole” and “broke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is tha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noble spirit” deeply, and utilize the spirit in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the novel. Only in this way, the minority writers could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oneself, family and one dynasty, and send out a voice of the age that retains its own identity.
Ye Guangqin; Caisangzi; Quanjiafu; History;Experience
I206.7
A
2095-3763(2017)04-0018-07
10.16729/j.cnki.jhnun.2017.04.003
2017-09-20
王岩(1987- ) ,男,江苏宿迁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文学经验的理论、方法与问题研究” (编号:2017SJB055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于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