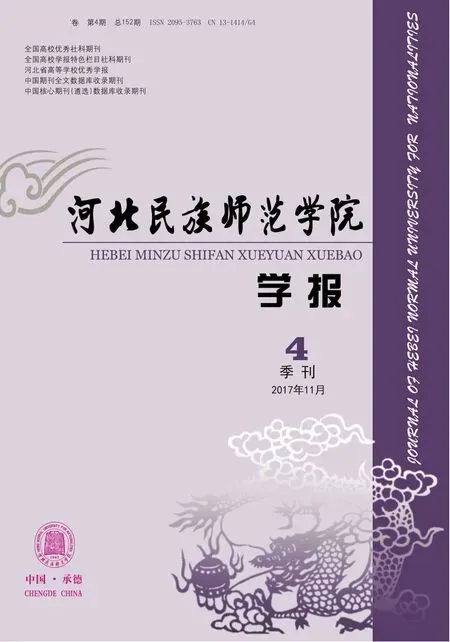论端木蕻良小说中萨满教文化的矛盾心理
曹亚鹏
(南京大学 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满族小说研究】
论端木蕻良小说中萨满教文化的矛盾心理
曹亚鹏
(南京大学 艺术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端木蕻良的小说中流露出对萨满教文化既肯定又批判的矛盾态度。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宗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最初具有现实功能的宗教信仰渐渐演变为了富于表演性的民间节日的娱乐活动,其审美价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端木蕻良身为满族作家,对满族信仰的萨满教文化具有天然的民族认同感,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萨满教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基于改造国民性的诉求,端木蕻良又对萨满教文化带来的愚昧落后的现象给予了有力批判。萨满教文化书写为端木蕻良的小说增添了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色彩,也为我们了解东北地区的民俗文化提供了有力借鉴。
萨满教;端木蕻良;五四;批判
萨满教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在我国主要流传于东北地区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多种民族中。在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进程中,萨满教文化作为人们特定时期的东北地域文化和心理积淀,深深浸润了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对东北作家的写作主题、思维和心理以及情绪状态和作品的审美特征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端木蕻良作为东北地区的满族作家,其文学创作受萨满教文化影响更深,在他的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萨满教文化的极为详尽细致的描写,透过这些描写,可以发现他对萨满教文化持有既肯定又批判的矛盾对立的观点,从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趋向。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萨满教文化的审美变迁
萨满教诞生之初主要凸显的是其现实功能。最初,萨满教只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活动,信仰萨满教的人崇尚万物有灵论和有神论,相信人类去世后还有灵魂存在,认为在人类世界之外还存有一个神灵世界,宇宙万物都有灵性,是神灵的寓所。萨满教经常举行的神事活动是“跳大神”,“大神”即萨满,是萨满教神事活动的主持者,他被认为具有通神能力并能得到神力救助的人,是沟通人类世界与神灵世界的中介者。在“跳神”过程中,大神需要手捶神鼓,口诵咒语,在急促的鼓声中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癫狂状态,还要完成一系列常人难以做出的高难度动作,从而使神灵附着于体内,或者大神的灵魂飞出体外与神灵进行交谈。在我国东北地区流行的跳大神仪式中,还有一位“二神”,他主要负责代表人间并将人间话语传达给大神,同时将大神说出的“神旨神意”给予回答或强调。萨满教通过“跳大神”等神事活动为民族祈福消灾、治病救人、祈求生产丰收和民族安全兴旺。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萨满教跳神活动由最初的宗教祭祀活动,渐渐演变为在盛大节日举行隆重庆典的仪式,萨满教的原始宗教功能渐渐淡化。萨满跳神作为民间节日的重要仪式,其娱乐功能则越来越被凸显:表演性更强,场面更为壮观,规模更加宏大,跳神过程也有所延长。大神和二神的穿戴也更加时髦复杂,头饰、帽饰还有手中所拿法器的种类也更加繁多,萨满教的跳神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集音乐、舞蹈、说唱为一体的表演艺术。歌舞、说唱不再像最初那样单一,而是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运动感,伴随着大神铿锵有力的鼓声,大神和二神的对答唱和直接渗透到人们内心。“东北萨满教的主要仪式——萨满跳神,是宗教活动,更是民众民间节日。灵佩斑驳的大神的狂歌狂舞。二神的接应答对,乞神保佑者的诚惶诚恐,围观者的如醉如痴指点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富层次感动态感的场面,可以说,萨满跳神仪式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融功利、宗教、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场面化效果。”[1]
萨满教主要功能的演变引起了萨满教文化的审美变迁,这在端木蕻良小说对萨满教文化的描写中有具体体现。在《科尔沁旗草原》中对丁老先生跳神治病的描写,虽然周围群众很多,但是跳神的只有丁老先生一人,动作极为简单,唱辞也只有简短的几句:“天灵灵,地灵灵,我有十万神兵,十万鬼兵,逢山山开,逢地地裂,逢水水涸,逢树两截,一切妖魔,随时消灭,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2]P15丁老先生的着装也很普通,这里主要突出的是萨满跳神的现实功能。然而,在《大江》中,“跳大神”的场面却变得极为盛大壮观,也更具娱乐性。大神不再是丁老先生一样的长有络腮黑胡子的老头,而成了年轻标致苗条的“花大神”九姑娘;跳神仪式也不再单调简单,而是锣鼓喧天极为热闹。九姑娘盛装打扮,身着翻花金线大红裙,耳挂琥珀环,边笑边舞得起劲。除了大神,还增加了远近驰名的二大神,两位大神都十分年轻漂亮。整个“跳神”过程变得更为漫长,从开始起舞到舞得疲倦但起劲,再到舞得更凶狂,好似一部舞台剧,一幕一幕情节跌宕起伏最终演到高潮。唱辞也变得冗长复杂,分为几个篇章,将请神、降神、送神的过程演绎得活灵活现。情节完整、表演性强的跳神活动正好满足了周围群众借此消磨时光和喜欢看热闹的心理需求,这里萨满教的娱乐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功能。“作家是把跳大神这一宗教活动同民间世俗、审美娱乐融为一体,并具有民间节日、宗教庆典的功能,这就使萨满文化精神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富有独特的景观,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3]
二、端木蕻良对萨满教文化的民族认同
萨满教一直是满族人民的信仰宗教,“从满洲民族的早期初民起始,他们就笃奉着一种被称为‘萨满教’的原始宗教。”[4]P2萨满教文化是满族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因素是将一个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对本民族的文化天然具有一种认同心理。端木蕻良的母亲是满族人,他自愿将自己的情感站位倾向于母系,并得到了民族身份的自我满足。所以,面对自己民族的萨满教文化,出于民族上的认同感,端木蕻良对萨满教文化所具有的现实功能和娱乐功能首先持一种肯定态度。
端木蕻良出生和从小生活的辽宁省昌图县是受萨满教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区,他的大舅是一为专管跳大神的萨满,在端木小时候经常参加跳神活动。端木蕻良的一位姓苏的娘舅是“二大神”,是负责辅助大神的神职人员。从小耳濡目染以及受地区浓厚萨满教文化氛围的熏陶,萨满教文化不自觉就进入了端木蕻良的文学视野,他说:“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5]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大地的海》等小说中都有大量关于萨满教文化神事活动的描写,在《科尔沁旗草原》开篇的萨满教“跳神”活动中,丁老先生是为履行治病救人的职责出场的,端木蕻良用简短的笔墨就把丁老先生跳神救人的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丁老先生走到青年少妇跟前把碗里的水朝少妇喷去,后来又把中指和食指掐成箭诀在水碗里沾了湿洒向空中,眼睛凝视空中并开始了咒语。这里丁老先生的“跳神”活动纯粹是为了救治发疯的青年少妇,少妇确实在丁老先生的“跳神”活动中得救了。从大神一出场大家立刻分辨出来并且知道苦日子到头了,到少妇被救治后的安心,周围群众的反应也能看出他们对萨满教的虔诚信仰,对萨满教大神具有的治病救人的现实功能深信不疑,看到少妇被救治,大家的情绪不再是恐惧而是“解放的、救渡的喜悦”。在丁老先生出场前的拜天活动同样彰显了萨满教的现实功能。人们虔诚满满地拜天,祈求瘟疫的劫数赶快了解。“无数的头颅俯在地上”,“这庄严的仪式,填满了这生疏的旷场”,“虔诚从心坎里向外涌着。人们都把信任寄托给无极的天空。眼睛代替了心的礼献,敬呈在老天爷的面前。于是他们的眼睛与天融洽了,流泄出感激和希望的泪水。天神骑着马,在空无的白云里飞奔。白云一丝也不动,在凝视着人间。人们仰望着。人们用心来祈祷。白云静静地聆着。于是宇宙的微妙和人心的微妙汇合了。于是,虔诚的心啊,都一同震颤了。”[2]P14盛大壮观的拜天活动,人们的虔诚被端木蕻良描摹的淋漓尽致,在端木蕻良的笔下,人们通过虔诚的祈祷达到了人神合一,人与宇宙相汇合的境界。
在对萨满教的潜在认同心理的作用下,端木笔下有关萨满教文化的书写,在客观上也具有了独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荒芜辽廓的农村里,地方性的宗教,是有着极浓厚的游戏性和蛊惑性的。这种魅惑跌落在他们精神的压抑的角落里和肉体的拘谨的官能上,使他们得到了某种错综的满足,而病患的痼疾,也常常挨摸了这种变态的神秘的潜意识的官能的解放,接引了新的泉源,而好转起来。”[6]P363作为萨满教神事活动的亲历者,端木蕻良在对萨满教文化的书写中情不自禁地掺入了自己的热情,他承认萨满教文化确实具有治病救人的功能,也肯定萨满教文化作为娱乐活动给村民闭塞落后的生活状况带来了清新的视觉和听觉的体验和感受。萨满教在这些人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使他们摆脱恐惧和不安,身体或者精神上的疾病也被治愈。“经常性的萨满跳神活动给北方民族沉寂、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不时吹去一股清风,带去一份振奋,送去一番喜悦。他们在观看萨满跳神的过程中体味和领悟到人生的欢乐与生活的美好,满足了自发的娱乐需求。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条件下,萨满跳舞是北方民族独特的最够刺激的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虽然称不上唯一的娱乐形式,但是最主要最经常的娱乐活动。”[7]
端木蕻良对萨满教文化的民族认同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大量关于萨满教神事活动的描写,还表现在,在端木蕻良的小说中,萨满教已经上升为一种渗透性的文化艺术精神。“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萨满教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以隐形深层的影响渗透并融入到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之中。东北作家身上存在着萨满教文化赋予的潜在气质,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8]萨满教跳神活动中的神秘癫狂的情绪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北作家,使他们在写作时也凸显出情绪激昂的萨满式精神气质。端木蕻良的《大江》《大地的海》就颇具这种气质。《大江》开头写大江浩荡滚流的气势,虽然语句短小,但是情绪激荡,气势豪迈仿佛萨满教神事活动中正在跳神的萨满附体,才让端木具有了这样书写的神力。在《大地的海》中,开头第二段的一组排比句,从气势和节奏上显然带动了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像萨满跳神癫狂状态的情感宣泄,在他的小说中还有很多。他说:“这里的感情是没有装饰的,如一个人在伤心,那么,在他的胸膛里,一定可以听见心的一寸一寸的磔裂声,如在哭泣。那滴落的水珠,也会透出一种颤动的金属声的,而且必然的整个灵魂都会激起一种沉郁的回响。”[6]P4无论是《大地的海》还是《大江》,端木蕻良都以强烈难以自抑的情感投入到东北特有的地域文化书写之中,萨满教已经成为了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精神,在东北民俗文化中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又长期影响和浸润着东北作家,在他们心里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萨满教文化处于我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区,受儒家文化等理性思维较少,所以那种迷狂式的张扬的文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宣扬,达到了一种活泼和动感的艺术效果。这也是使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端木蕻良笔下的女子都是水灵灵、清新脱俗、生性活泼的人物形象,在她们身上流淌着不受封建礼俗约束的血液,她们都性格刚烈倔强,敢于冲破一切世俗束缚勇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无疑不跟萨满教文化宣泄情感“外倾”式的精神气质有关。端木蕻良的小说都呈现出一种诗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就算是荡气回肠叙事宏大的《科尔沁旗草原》也被人称作“史诗”,这也彰显了萨满教文化作为隐性因子对端木蕻良的深刻影响。萨满教文化是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特定文化环境中精神因素和心理因素的文化积淀,所以,“端木蕻良对萨满教的描写,不仅在于反映一种人生境况和文化事象,而且深刻揭示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状况。”[9]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诉求
萨满教文化本身具有的现实功能和娱乐功能值得被肯定,但是作为原始宗教,满族萨满教毕竟是人们愚昧无知、文化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的产物,在萨满教文化中也存在愚昧、落后的不合理成分。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基于改造国民性的诉求,端木蕻良也对萨满教文化中的不合理成分进行了批判。
端木蕻良在小说中对萨满教神事活动书写时,除了展现其治病救人、祈福消灾的现实功能和作为民间节日活动的娱乐功能之外,还着力描摹了周围群众的“看客”形象,深刻揭示了他们沉迷于萨满教神事活动的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在《科尔沁旗草原》丁老先生为青年少妇跳神治病的场面中,见少妇安静了,周围群众就立刻想起来“看热闹了”他们是为青年少妇得救而喜悦,也是为在跳神过程中自己能够暂时沉浸其中忘却当前的苦难而喜悦;在《大江》中,人们由之前对萨满教的虔诚信仰变成了只顾欣赏大神歌舞的忘我陶醉。围观的群众似乎全然不顾病人的安危,而是一味陶醉在九姑娘的盛情歌舞中,在他们心中流淌着的只有终于看到标致伶俐的人的美貌和舞姿的喜悦和欢畅。他们挤满了屋子,连院子里也都是来看热闹的人们。“村里人都是喜欢看九姑娘跳大神的,他们觉得成天到晚让那伶俐的标致的妙人儿来跳舞,也不是使人完全讨厌的事。”“村上远近人家大小孩子都爱听,到这里来看跳神好像看一出大戏一样。”[6]P363虽然端木在行文中也几次提到九姑娘治病的本领也很强,但是人们对九姑娘美貌的欣羡,对其舞姿的沉迷远远超过了对其治病救人能力的关注。甚至连病人自己都沉迷其中“……病人躺在床上,眼巴巴的看着她,不肯放松每个细微的小节。”[6]P360“病人在床上把贪婪的野狂的眼睛睁得发亮。”[6]P362端木共描摹了三种人的“看客”姿态,从看热闹的村里人挤满了屋子院子,到小孩子顾不得好好吃饭就急忙等候着九姑娘跳舞,层层深入,将“看客”的扭曲心理和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揭露,更为讽刺的是连躺在病床上的等候被救治的铁岭的哥哥都把贪婪野狂的眼睛睁得发亮。与《科尔沁旗草原》中的描写相比较,《大江》中“看客”的心理状态发生了明显转变,前者在写到周围群众观看丁老先生跳神救人时,是在等到青年少妇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想起来看热闹的,他们在起初还是为少妇的生命担心、对死亡怀有恐惧的,然而在《大江》中,群众完全不顾病人的安危,就连病人自己也一味沉浸在了“花大神”曼妙的歌舞表演中,这种面对苦难和生死危亡全然不知的愚昧正好暴露了萨满教文化对人民的戕害,凸显了萨满教文化中的国民劣根性。在观看跳大神的过程中,“看客”们通过观看或欣赏别人的痛苦来宣泄自己的不幸和痛苦,以达到一种畸形的心理满足,从而得到暂时的解脱,这种“观看”心理和姿态对跳神中等待被救治的病人来说是极为残忍的。“看客”通过“看”和“欣赏”甚至仔细“品味”他人的不幸和痛苦,暂时性的忘却自身的不幸和苦难,却一味地深陷在了落后的萨满教文化对他的毒害和麻痹中而浑然不知,这对于“看客”来说也是极为残忍的。端木蕻良在“跳神过程描写中特别注意着渲染看客情绪的变化。第二天续演时,丁四太爷居然也被大家‘请’来出场,不动声色地与大神表演出绝妙的‘双簧’配合,赢得了全场心悦诚服的赞叹。小说对看客们麻木、愚昧、落后、迷信的精神世界的揭示,无疑点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统治者之所以强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常常利用鬼神迷信为自己制造强大的幻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被统治者对其强大的迷信。丁氏家族之所以能在草原上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即与草原群众的这种迷信意识相关,他们心甘情愿地作了丁府统治的精神支柱。”[10]虽然萨满跳神活动在视觉和听觉感受上给人以美的体验和享受,但是却腐蚀和麻痹和国民的精神,在面对落后的文化因素或统治阶级的欺负,他们只能选择盲目接受。基于改造国民性的诉求,端木蕻良有意识地对萨满教腐蚀和戕害国民性的方面进行了痛斥和批判。
端木蕻良同20世纪30年代很多年轻优秀的青年作家一样,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文化批判传统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他和那些觉醒起来的东北作家群作家,一起成为“改造国民性”精神的传承者,共同呼唤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思想,向愚昧的民众发出启蒙的声音,把文化批判矛头指向麻醉人和愚弄人的萨满教。鲁迅先生也对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跟鲁迅保持了很长时间的书信往来,“像一缕阳光似的,鲁迅的声音呼叫着我,我从黑暗的闸门钻了出来,潮水一样,我不能控制自己,一发而不可止的写出了那本《科尔沁旗草原》。奠下了我的文学生活的开始。”[11]鲁迅先生的书信鼓舞了端木蕻良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使他在困惑和迷茫中找到了出路,引导他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促使他很好地继承到了鲁迅先生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精神和主张。“20世纪30年代,接受了鲁迅的文化批判传统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还有骆宾基等人在文学创作动机上就对萨满教持有一种明显的拒斥和对抗心理,作品中往往突出了萨满教的负面影响,把萨满跳神和封建愚昧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此时,昌明‘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预示了萨满教文化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8]在端木蕻良的笔下,萨满教跳神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它不仅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中的底层百姓,更加重了他们精神的麻木和落后,在《大江》中,面对深陷于精神的麻木而不自知的村民群众,他终于让铁岭冲出封建礼教的牢笼,以“打了”大神作为对落后的宗教文化的反抗。在《科尔沁旗草原》中,萨满教文化不但是毒害民众的精神鸦片,还是地主阶层肆意吞并土地后借以掩人耳目的工具,端木蕻良对此种卑劣行径一并给予了有力的痛击。
结 语
端木蕻良是优秀的东北满族作家,他在小说中的萨满教文化书写为我们展现了东北地区满族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观,增加了小说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色彩,也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神秘的、酣畅的审美体验。在对萨满教文化的民族认同和自觉批判的矛盾心理作用下,端木蕻良的小说在思想上更具有辩证意味。萨满教文化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浸润到端木蕻良的潜意识里的,研究他小说的萨满教文化书写,也能洞悉到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文化涵养。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端木蕻良小说中的萨满教文化书写也为满族萨满教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端木蕻良小说中的萨满教文化书写,把握他对萨满教文化既肯定又批判的价值趋向,有助于我们形成对萨满教文化的全面认识,也为我们研究东北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提供了有力借鉴。
[1]逄增煜.萨满教文化因素与东北作家群创作[J].社会科学战线,1995(4):144-149.
[2]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3]李长虹.萨满文化精神与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J].东疆学刊,2007(4):23-27.
[4]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N].中流,1937-4-20.
[6]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陈柏霖.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原始娱乐功能[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1):81-85.
[8]闫秋红.论端木蕻良抗战小说中的萨满教文化因子—从长篇小说《大江》《大地的海》谈起[J].满族研究,2005(3):106-110.
[9]程义伟.“关东文化意识”与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J].理论界,2006(9):185-187.
[10]马宏柏.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11]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N].文学报,1942-6-20.
On the Ambivalent Attitude toward Shamanism Culture in Duanmu Hongliang’s Novels
CAO Ya-peng
(Nanjing University A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93, China)
Duanmu Hongliang’s novels reveal both positive and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 Shamanism culture. In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as a primitive religion, Shamanism, which initially had practical functions, ha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performing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for holiday entertainment. Its aesthetic value had also changed. As a Manchu writer, Duanmu Hongliang has a natural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Shamanism culture, 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has also been influenced and disseminated by Shamanism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based on the refor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ppealing, Duanmu Hongliang gives a profound criticism to the ignorant and backward phenomenon that Shamanism has brought. Shamanism culture writing adds distinctive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lor in Hongliang’s novels; it also provides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folk 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Shamanism; Duanmu Hongliang; May Fourth; Critique
I206.6
A
2095-3763(2017)04-0012-06
10.16729/j.cnki.jhnun.2017.04.002
2017-09-12
曹亚鹏(1990- ),女,河北石家庄人,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
2016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满族小说研究”(编号:HB16WX027)。
责任编辑:于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