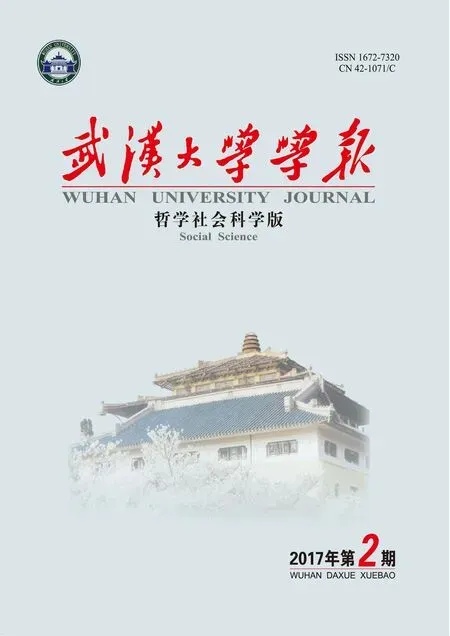刑民对话视野下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认定
李齐广
刑民对话视野下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认定
李齐广
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是处理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认定的关键,不能拘囿于刑法学界内部的研究,唯有采取刑法与民法对话的方法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民法学界因其具有一般财产的属性而将其认定为财产,其财产权是物权,作为物权的客体是一种无体物。在刑法学上,以民法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其无体物的形态认定为财物,纳入财产犯罪的保护范围,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会与我国民法相冲突。以刑法保护虚拟财产不会导致金融秩序的破坏。不能因为虚拟财产数额的难以计算,便否定其财产性。窃取虚拟财产的,认定为盗窃罪更为妥当,而不宜以计算机相关犯罪论处,否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或出现不必要的处罚漏洞。
虚拟财产; 刑民交错; 财产犯罪; 数额计算
一、问题与视角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游戏的日益普及,侵犯网络空间中虚拟财产的案件日益增多,例如窃取虚拟货币、游戏装备等。由于目前对虚拟财产的性质界定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司法部门对相关案件的处理可谓五花八门:
第一,不以犯罪处理。例如,案例1(张明楷,2015:15),曹某为腾讯公司员工,主要负责在举办活动时向参加游戏活动的用户发放游戏道具作为奖励。曹某从2012年9月自案发之日,多次将奖励给用户后多余的游戏道具通过该公司外部人员尚某进行销售,由尚某将外部购买道具人员的QQ号、密码以及需要购买的虚拟道具名称和数量提供给曹某,曹某在游戏系统中直接给用户QQ号码发放道具并与该号码进行捆绑,并给尚某反馈一个游戏道具CDKey号码,用户通过这个CDKey号码就可以领取到游戏道具。曹某和尚某通过上述方式私自售卖腾讯公司的游戏道具共获利1410987元。当地司法机关以虚拟财产不是刑法保护的财产,不予立案。
第二,以计算机相关犯罪进行处罚。例如,案例2(姜金良、袁海鸿,2015:92),2012年10月起,被告人岳曾伟以一个游戏账号及密码5.5至7元不等的价格从张翊处购得8.2万余个游戏账号及密码,在购买该账号和密码后,再安排被告人张高榕、谢云龙、陈奕达及岳磊等人,非法登录游戏账号窃取其中的“金币”,共计7.9亿余个,并将窃得的“金币”通过网站进行销售,非法获利72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张高榕、陈奕达分别非法获利1.1万元和1.3万元,被告人谢云龙非法获利6千元。二审法院认定被告岳曾伟等人成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第三,以侵犯财产罪论处。例如,案例3(赵秉志、阴建峰,2008:157),被告人颜某系网易公司工作人员,伪造玩家的身份证,将假的身份证复印件传真回网易公司,以安全码被盗为由,从网易公司骗取新的安全码后盗得玩家的游戏装备一批,获利3750元。经法院审理后认定颜某构成盗窃罪。
在案例1中,当地司法机关认为虚拟财产不具有财产的属性,不属于财产,因而认定为无罪。案例2在审理过程中,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窃取虚拟财产的应认定为盗窃罪;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虚拟财产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因而应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最后上诉法院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案例3中,审判法院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因而成立盗窃罪。上述案件虽同属窃取虚拟财产的案件,但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不难发现,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上。
可见在我国,要正确处理窃取虚拟财产的相关犯罪,就必须对虚拟财产性质作出准确界定。可是,在我国,经过多年的讨论,刑法学界对于虚拟财产性质的争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剖析刑法学者的相关研究。主张虚拟财产不具有财产属性的否定论者(侯国云,2008:55)是这样论证的:依民法学上的见解,财产应当具有效用、稀缺、流转三种属性。虚拟财产在虚拟世界可能具有一定的效用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效用性;虚拟财产能大量复制,因而不具有稀缺性;虚拟财产只能存在于虚拟世界,因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具有流转性。相反,肯定论者(赵秉志、阴建峰,2008:155)则认为,虚拟财产具有真实性、价值性、现实转化性,因而具有财产性。
可见,刑法学界已有初步共识,那就是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及其权利属性的认定应当以民法学为基础。目前,真正深入研究民法学对虚拟财产研究的刑法学者不多,这也是刑法学界对于虚拟财产的界定处于困境的根本所在。所以,本文尝试以刑法与民法对话的视角探讨侵犯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认定。
二、刑民对话视野下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
(一) 虚拟财产的概念及特征
对虚拟财产概念的界定,理论界存有很大的分歧。目前,关于虚拟财产的概念大体上可分为最广义说、广义说与狭义说。最广义说认为,虚拟财产是指信息社会主体在信息空间中所创造的能够代表一定利益关系的数字化对象(高德胜,2012:101)。广义说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既相对独立又具独占性的电子数据,包括QQ 账号、游戏装备等(林旭霞,2010:50)。狭义说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网络游戏中能够为玩家所拥有和使用的电子数据模块,包括游戏装备、游戏币等(钱明星、张帆,2008:6)。目前,有关虚拟财产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就是因为概念的分歧产生的,所以准确界定虚拟财产的概念对于问题的讨论实属必要。
那么,该如何准确界定“虚拟财产”这一概念呢?对于概念界定的正确与否,Puppe(2010:8)教授总结了三个判断标准:(1)立法者自己的使用方式,即立法解释;(2)一般的语言使用习惯,即客观解释;(3)法律适用上的实践后果,即目的论解释。第三个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标准,它不是或真或假,而是一种规范性的陈述,意味着依照法律适用者的看法去理解所涉及的抽象概念。对虚拟财产进行界定时,应采用第三个标准,即应考虑符合其自身的基本目的:为相关纠纷的解决提供合理的界限。
前述有关虚拟财产概念的三种学说是否满足了上述要求?首先,广义说存在外延过宽的毛病,将域名、网站、邮箱等没有凝结人类劳动、不具有价值的电子数据也认定为虚拟财产。其次,最广义说也同样犯了外延过宽的毛病,除了具有广义说的毛病外,还导致了一些不是虚拟财产的东西也被纳入进来。例如,银行存款、股票,它们也可表现为信息空间中的一定利益关系的数字化对象,但却并不是虚拟财产所讨论的对象。最后,狭义说将虚拟财产仅限定在网络游戏中,而将一些网络游戏之外的虚拟财产完全排除,这恐怕也不合适。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网络游戏之外的具有价值的虚拟财产也会逐渐增多。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具有现实交易价值,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既相对独立又具有独占性的信息资源。此概念与狭义的虚拟财产概念相比,外延上略宽,将一些存在于网络游戏之外的虚拟财产也容纳其中,能满足网络发展的需求;而与广义的虚拟财产相比则外延略窄,将一些并没有凝结一般人类劳动的虚拟物品,例如QQ号、邮箱等排除在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之外。采用此定义,虚拟财产的范围既不会过宽,也不会过窄。
与传统财产相比,虚拟财产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网络依赖性。网络依赖性是指虚拟财产只能存在于网络空间中;(2)数据性。虚拟财产实质上是一组存储于服务器上的的数据;(3)期限性。虚拟财产是依附于网络而存在的,例如游戏装备,一旦网络游戏被注销,其可能随之消失,因此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期限性。
虚拟财产因具有网络依赖性、数据性、期限性等特征而不同于传统财产,那么虚拟财产能否被认定为财产呢?如果是财产,其权利属性又是什么呢?以下将逐一予以探讨。
(二) 对虚拟财产财产属性的界定
所谓财产属性,就是指财产作为权利客体的特征。民法学界(林旭霞,2010:89;高富平、杜军,2008:14;杨立新、王中合,2004:7)认为,财产作为权利客体,需要具备价值性、稀缺性、排他性三个重要特征,而虚拟财产明显具备上述三个特征,具体如下:
(1)虚拟财产的价值性。所谓价值性,是指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或精神需求,并可以一定的货币予以衡量,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件物品如果没有“价值”,便不成其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游戏玩家通过虚拟人物将自己的人格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扩张,并从中获得感官和精神上享受,因此,虚拟财产具有使用价值。另外,虚拟财产的现实交易也遵循了价值规律的要求,因此具有交换价值(林旭霞,2010:89)。
(2)虚拟财产的稀缺性。稀缺性,是指某物相对于人的需求而言是有限的,稀缺性是物成为法律财产的必要前提。虚拟财产的稀缺性,一方面表现在游戏玩家并非轻易就能获得虚拟财产,而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另一方面,它对玩家的智力和技巧也有一定的要求,有的玩家投入再多也可能空手而归,这就使玩家的生产力上存在稀缺性(林旭霞,2010:90)。因此就玩家而言,虚拟财产的确具有稀缺性。
(3)虚拟财产的排他性。排他支配性意味着特定的财产只能由特定的权利主体所享有。虚拟财产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游戏运营商可以凭借现代技术对网络服务器上的电子数据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玩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账号、密码对虚拟财产进行管理(林旭霞,2010:32;杨立新、王中合,2004:8)。
在了解民法学对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后,现在可检讨反对虚拟财产财产性的刑法学者的观点。
第一,反对观点认为,虚拟财产在虚拟世界可能具有一定的效用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效用性(侯国云,2008:55)。此观点存在明显错误:(1)该论者明确指出,其结论以民法学理论为基础,可是民法学界却是完全肯定虚拟财产的价值性的;(2)不同财物具有不同特点,简单以能否拿到现实世界中作为区分对象是否财物的标准有欠妥当。例如,刑法第九十二条明确将股票规定为财产,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股票早已不在现实中而只是在电脑这个虚拟世界存在,可谁又会否定股票的财产性呢;(3)认为虚拟财产不具有价值与事实不符。反对者之所以认为虚拟财产没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其认为虚拟财产既不是玩家的劳动创造也没有凝结商家的一般劳动,从而并不具有必要劳动这一必要属性;可是虚拟财产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通过诸多人的设计、编排等劳动形成的,而且游戏玩家获得游戏装备后也会为提升装备投入大量的劳动。(4)反对者认为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交换的基本规则是因为“游戏软件的价值中已经包含了虚拟财产的价值,商家在出售游戏软件时,已经将虚拟财产的价值出售了,再将虚拟财产拿出来单独出售,等于将虚拟财产出售了两次”,这完全是对网游商家与玩家之间关系的一种误解。玩家通常所买的只是基本设备,而并不是买下了网游商家的所有的虚拟财产,要想升级还需另行购买装备或者依靠自己的劳动。可见,认为虚拟财产没有凝结一般劳动因而没有价值,与现实不符。(5)虚拟财产可以通过虚拟币进行交换,而虚拟币又可以同现实中的货币兑换,因而也是具有交换价值的(高富平、杜军,2008:14)。
第二,反对观点认为,虚拟财产能大量复制,因而不具有稀缺性。可是,该观点只是看到表象却没能认清本质。游戏运营商看似可以无限复制装备,但这并不能否认虚拟财产的稀缺性。因为一个网络游戏中的装备如果真的可以无限制复制,这样的游戏很快便会被淘汰,这也是游戏运营商所不愿看到的。
第三,反对观点认为,虚拟财产只能存在于虚拟世界,因而在现实社会中不具有流转性。“虚拟财产……根本就走不出电脑屏幕,无法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也就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进行流转。”(侯国云,2008:55)可是,流转性根本就不是财产属性的基本特征,只有排他性才是。而且,以是否能走进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来判断财产属性更是荒谬之举。诚如斯,则电也不属于财物了,因为吾人根本不可能将其从电路中拿出而让其走进现实世界。可是,刑法上对窃电的行为毫无疑问会以盗窃罪论处。
因此,反对观点明确提出要以民法学为基础来判断虚拟财产的财物属性,可是却又与民法学的研究明显不符。
综上所述,即使虚拟财产因为具有网络依赖性、数据性、期限性等特征,而与传统财产有所区别,但因为其仍然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排他性等基本特征,而具有财产性。相反,有的刑法学者却以民法学要求财产应当具有效用、稀缺、流转三种属性而虚拟财产并不具备为由,而否定虚拟财产的财产性(侯国云,2008:35),明显与现实不符。
(三) 对虚拟财产权利属性的界定
刑法学者对虚拟财产权利属性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是财物(赵秉志、阴建峰,2008:155)。该说可以相当于民法中的物权说;第二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一种财产性利益(董玉庭,2012:55)。该说可以相当于民法中的债权说。因此,准确界定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对于消除刑法在认识虚拟财产所产生的分歧至为重要。
目前,关于虚拟财产,民法学界主要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等几种学说:(1)物权说认为,凡是具有法律上的可转移性、管理可能性及一定的经济价值,就可以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物,虚拟财产具有这些基本特征,所以虚拟财产是物,可以适用物权法(杨立新、王中合,2004:9)。(2)债权说认为,虚拟财产是债权,是游戏运营商和游戏玩家之间服务合同关系的凭证(王竹,2008:65)。其中,运营商提供法定或约定的服务,玩家支付相应费用以获得该种服务,游戏本身以及各种附加装备都是运营商提供服务的一部分。因此,玩家并没有获得所有权。(3)知识产权说认为虚拟财产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应将其作为知识产权来保护(林旭霞,2010:95)。(4)新型权利说认为虚拟财产是一种新型财产权,其既有物权属性又兼具债权属性,体现了物权和债权的结合(王竹,2008:65)。
对于知识产权说和新型权利说,多数民法学者予以反对:(1)对于知识产权说而言,如果认为虚拟财产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则其只能是著作权。可是,著作权保护的是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而网络游戏中的“武器”或游戏币,既不是游戏运营商也不是游戏玩家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此外,这些“武器”或游戏币也没有体现出独创性,算不上“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杨立新、王中合,2004:10)。因此,虚拟财产是知识产权的说法并不恰当。(2)对新型的财产类型说而言:首先,该说过分考虑虚拟财产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忽视了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的共性特征。正如前述,无论是就价值性、稀缺性,还是排他支配性,虚拟财产都与传统的物相同。其次,该说加大了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的技术难度。因为将虚拟财产设置为一种新型的财产类型,会极度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即使增设这种新型财产类型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新的问题(杨立新、王中合,2004:10)。
现在,关于虚拟财产权利属性,民法学者主要在物权说与债权说间展开。那么,债权说是否合理?
在笔者看来,债权说有如下缺点:(1)债权说不能准确地揭示虚拟财产的属性。认为玩家与服务商之间存在某种合同关系,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认为虚拟财产本身是一种债权则极为不妥(钱明星、张帆,2008:6)。例如,将一辆小汽车卖给他人,可以说这种买卖关系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却不能说小汽车本身也是债权。游戏装备和小汽车一样,玩家将游戏装备卖给游戏运营商以外的第三人时,也同样存在一个基于买卖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本身是一种债权。(2)债权说将虚拟财产视为一种债权凭证,忽视了虚拟财产本身的价值问题(高富平、杜军,2008:18)。游戏运营商和玩家之间通常采用的是格式合同,在同一款游戏中,所有的格式合同内容完全相同,也即权利义务完全相等。依此推论,作为债权凭证的虚拟财产其价值不应存在区别,然而实际情形却是,不同用户的虚拟财产的价值相去甚远,有一文不值的,也有数以万计的,这显然与现实不符。(3)债权说自身还存有逻辑上的矛盾。该说一方面认为虚拟财产是债权,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玩家仅凭虚拟财产这一债权还不能行使债权,即不能直接进行游戏。如果想玩游戏,玩家还须另行付费。可是如果虚拟财产本身就是一种债权又何须另外付费?显然,其所谓的债权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利。因此,债权说明显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将虚拟财产视为一种债权并不妥当。那么,虚拟财产是否当然就是物权呢?要证明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是物权,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虚拟财产是否为物权客体;二是虚拟财产是否具有物权的支配性(钱明星、张帆,2008:7)。
第一,虚拟财产到底是不是物权的客体呢?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单从条文上看,并没有直接规定物的范围,虚拟财产是否纳入规范自然也没有明确规定。可是,判断虚拟财产是否是物的实质根据在于其是否具有物权客体的属性。作为物权客体的物,无论其表现形态如何发展变化,始终应具备一定的属性,即特定性和独立性(林旭霞,2010:75)。所谓物的特定性,是指由特定的时、空加以固定的一种现实客观存在。而物的独立性,是指按照一般社会观念得以完整存在(林旭霞,2010:104)。如前所述,虚拟财产是一种数字化的物理信息,是一种客观存在。玩家完全可以通过设置帐号密码来让虚拟财产存在于特定的时空,这充分说明虚拟财产具有特定性。此外,在社会一般观念上,虚拟财产都是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交易的,虚拟财产具有独立性。因此,虚拟财产完全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
第二,虚拟财产的存在和权利行使需依赖于游戏运营商,这便使得其作为物权的支配性遭到质疑,那么虚拟财产的财产权是否具有作为物权的支配性呢?“支配”的涵义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支配’已由事实支配发展到法律支配,由对实物的支配发展到对价值的支配甚至于通过与物的权利联系、实现对物的最终控制权而实现的支配。”(林旭霞,2010:95)物权的“支配”不再强调实际的占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实际占有某物,但只要在法律上拥有一定的权利,而且对物享有某种独立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依然可以认定为具有“支配性”。就虚拟财产权的“支配性”而言:(1)玩家和游戏商对虚拟财产具有“支配性”。 就玩家的虚拟财产而言,虽然他们的虚拟财产存储在特定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上,但并不由运营商控制,对于虚拟财产的具体处分,完全由玩家自己决定,不需要得到他人的许可。也就是说,玩家对虚拟财产具有“支配性”。当然,在不同场合,其支配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在线时,玩家通过自己的账号、密码即可实现对虚拟财产的直接占有。离线后,虚拟财产也不会就此丧失。当其虚拟财产受到侵犯时,完全可以寻求物权保护方式予以保护。更为重要的是,与现实生活中的物品一样,虚拟财产也可以在服务器上持续存在,玩家随时可以实现对虚拟财产的支配。此外,网络运营商对初始的网络游戏物品也享有直接的支配权。(2)虚拟财产权的行使虽然依赖于游戏运营商,但并不因此失去“支配性”。正如存单的持有人行使票据上的权利也需要他人的协助一样,“协作”的存在并不会改变存单持有人对存单的“支配性”。因为在此场合,支配意志对所要支配的财产利益仍然拥有最终的选择权与决定权。同理,玩家虚拟财产权的行使虽然依赖于游戏运营商,但依然具备了支配权“对财产拥有决策力并最终控制财产的前途和命运”的核心特征(林旭霞,2010:109)。
综上所述,虚拟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认定为物权更为妥当、合理。但由于虚拟财产属于无体物,而无体物是否属于我国刑法中的财物呢?
对财物范围的界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有体性说与管理可能性说两种学说的对立。有体性说认为,刑法上的财物只限于有体物,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无体物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管理可能性说则主张,只要可能管理的物就是财物。管理可能性说内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务管理可能性说”,认为凡是可以作为一种事务进行管理的物,都是刑法上的财物;信息、债权等仅具事务管理可能性的东西也是财物。另一种是“物理管理可能性说”,认为只有存在物理管理可能性的才是财物。 物理管理可能性说是针对事务管理可能性说而提出的,牛马的牵引力、信息等虽具事务管理可能性但没有物理管理可能性的,不属于财物(大塚仁,2003:174)。
在日本刑法学界,主张有体性说(齐藤信治,2001:90)的根据主要有:(1)从保持财物概念明确性的角度出发,有体性说更为妥当;(2)从刑法解释应按照日常用语进行理解这一角度出发,应将财物理解为有体物,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维持法的安定性;(3)如果将所有具有管理可能性的物质视为财物,则财物的范围难以明确。如果按此说,潜入他人公司复印、拍摄机密文件都要成立盗窃罪;(4)管理可能性说认为牛马的牵引力并不属于财物,可是按照管理可能性说,牛马的牵引力也具有管理可能性,可为何又不承认其为财物呢;(5)日本刑法第245条将原本不是财物的电“视为” 财物,是一种例外,是一种“拟制”性规定,因此财物应指有体物。主张管理可能性说(福田平,2002:214)的理由主要是:(1)财物的“物”有多种含义,不能仅局限于有体物;(2)刑法并没有就“物”下过定义,认定无体物为财物并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3)盗窃罪的行为是“窃取”,只要能成为盗窃罪的行为对象,无体物也可以被视为“物”;(4)有体物之所以是“物”,并非“有体”本身,而在于有体物具有可移动性及管理可能性。因此,如果具有可移动性和管理可能性,无体物也应当被视为“物”;(5)日本刑法第245条属于注意规定,该条旨在说明像电这样的无体物也属于财物。
其实,在日本刑法学界,管理可能性说之所以遭到有体性说的质疑,其深层根源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1)日本刑法学明确对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进行了区分,管理可能性说会导致刑法对利益性盗窃也进行处罚,与现行刑法所持的“利益盗窃不可罚”这一立场相冲突(山口厚,2011:200);(2)日本民法明确规定“物”限于有体物。
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对财物范围的界定的确有过于宽泛之嫌,有体性说能够明确划定财物的范围,但在当今社会,很难区分电力和电力之外的能量,因此贯彻有体性说已不足取(大塚仁,2003:174)。且物理管理可能性说以可移动性和管理可能性对财物范围的认定进行了限定。因此,如果坚持物理管理可能性说,不仅不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而且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处罚漏洞。
本文认为,物理管理可能性说更适合我国刑法,理由如下:
第一,将无体物包含在财物范围之内,与我国的刑法相统一。我国刑法第265条明文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接他人的通信线路就是一种非法取得他人无体物的行为,将刑法第265条理解为注意规定,认为刑法中的财物包括无体物,这种理解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第二,将无体物包含在财物范围之内,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协调。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一般认为,电力系属无体物。再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5月12日《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都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些司法解释均充分说明了无体物是财物,物理管理可能性说是得到承认的。
第三,将无体物包含在财物范围之内,与我国民法并不冲突。由于德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财物限于有体物,所以德国刑法学界通常认为无体物不是财物,因此德国现行刑法第248条c就单独规定了盗用电力罪。日本民法也采取和德国类似的规定,即财物仅限于有体物,这同样导致了日本刑法第245条的规定:“就本章犯罪,电气也视为财物”。在德、日,将电气以外的无体物理解为财物,可能存在规范上的障碍,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事实上,德国刑法虽然只处罚有体物的盗窃,但是德国刑法中第263条的诈骗罪,以及248条无权使用交通工具罪、266条背信罪等多个罪名可以将侵害无体物的财产犯罪进行妥当的处理(王钢,2015:41),但我国刑法缺乏这些相应规定,因此,仅将盗窃罪的行为对象限定为有体物,则会导致不必要的处罚漏洞。而且我国与德日不同,我国物权法并没有排斥无体物可以成为财物,而且,我国刑法265条使用的是“依照”,而不是“视为”,因此与德国刑法第248条c和日本刑法第245条这样的规定完全不同,因而完全可以将我国刑法第265条理解为注意规定,将无体物认定为财物。
综上所述,将虚拟财产认定为财物,以无体物这种形式纳入财产犯罪的保护范围,在刑法的可能语义范围之内,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三、虚拟财产刑事责任认定的可能“障碍”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学者们认为,将虚拟财产作为财产纳入犯罪处理,面临以下两个障碍:(1)肯定虚拟财产的财产性会严重扰乱金融秩序;(2)虚拟财产的价值很难估算因而不宜按照财产犯罪处理(侯国云,2008:35)。上述两个障碍是否真的存在呢?下面展开具体分析。
(一) 肯定虚拟财产的财产性是否会严重扰乱金融秩序
主张虚拟财产会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学者认为,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的兑换会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允许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自由兑换,将会不可避免的引起金融混乱,引起通货膨胀。这一观点主要针对的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的发行真的会有如此影响吗?
1.虚拟货币会否扰乱金融秩序
虚拟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的确会给虚拟货币的持有人带来一定的风险,但这种风险,还不至于导致金融秩序的紊乱,原因是(杨旭,2007:79):(1)对个人的风险不大。虚拟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极为方便,具有理性的人不会大量持有虚拟货币,毕竟其适用范围有限。所以,通常情况下,个人损失不会太大。况且在网络上,虚拟货币很容易兑换为其他货币,可以转移风险,因此,虚拟货币的发行带给个人的风险并不大。(2)对社会的风险也不大。虚拟货币的发行人,并不具有银行所具有的功能,所以即使出现虚拟货币贬值、发行方破产,也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太大的损失,不至于扰乱金融秩序。
2.虚拟货币会否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升,又被形象地描述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可即便商家为了追逐商业利益会大量发行虚拟货币,也并不必然会引发现实社会的通货膨胀,理由如下:(1)网络运营商不会无限制地发行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网络运营商用来满足用户的购买需要而发行的,它所发行的数量,取决于用户的购买数量。因此,网络运营商不可能像央行那样主动发行虚拟货币,而用户的购买量毕竟有限,所谓“超量发行虚拟货币”是不大可能出现的。(2)虚拟货币的增加,仅仅是商品的增加,而不是货币的增加。即使“有用户事先大量收购某种虚拟货币,之后在某一时间集中兑换成人民币”,也不会导致“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这一通货膨胀的现象出现。因为人民币的数额是相对固定的,即便真的有人集中把“虚拟货币”兑换成人民币,也只会使人民币减少,而不是大量增加(杨旭,2007:79)。虚拟货币目前并未像传统商品一样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种大量兑换行为也不太可能出现。
综上可见,虚拟货币的发行既不会扰乱金融秩序,更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现实是,虚拟货币发行业已多年,并未见其对金融秩序有何冲击,这便是最好的明证。
(二) 虚拟财产的价值是否能够合理估算
有刑法学者认为,虚拟财产的价值很难估算因而不宜按照财产犯罪处理。“即使同一种网络游戏装备,其价值也会随着玩家们兴趣的转变而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价值千金,明天可能只值分文。而盗窃等侵犯财产的犯罪,原则上是根据侵犯财产价值数额的多少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价值无法确定则无法定罪处罚。”(刘明祥,2016:158)
但是上述看法明显有失偏颇:(1)不能因为难以计算就径直否认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财产犯罪性。刑法上许多财产犯罪中的财物价值是难以计算的,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以财产犯罪论处。例如,两高2013年4月2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款规定:“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虽说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的价值无法准确估价,但也并没有因此而否认成立盗窃罪。既然如此,为何对于类似的虚拟财产就要否认其财产犯罪的成立呢。(2)虚拟财产其实也并非不可以计算。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一些计算方法(邹政,2014:75),虽没有取得完全统一,但并不意味着虚拟财产的价值无法计算。恰恰相反,这说明虚拟财产的价值是可以计算的,只是如何合理计算的问题。下面按照虚拟财产与法益主体的不同类型分别予以判断:
第一类,由玩家从网络运营商或者第三人处购买的价格相对稳定、不因用户的行为而发生价值变化的虚拟财产,其价值由运营商的官方定价进行计算。此类虚拟财产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运营商对此类虚拟财产有明确的定价,且价格相对稳定;其二,此类虚拟财产既不属于运营商也不是消费者凭借游戏中的劳动获得,而是由购买直接获得。例如游戏玩家购买的Q币、游戏点卡等,当行为人窃取这类虚拟财产时,被害人的损失数额与官方价格完全相当。因此,对此类虚拟财产直接以运营商的市场定价进行计算就是合理的。
第二类,由玩家从运营商或者第三人处购买后,经过游戏劳动使之升级的虚拟财产,可以按照虚拟财产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计算。此类虚拟财产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运营商出售时价格较低,但玩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使其升值;其二,此类虚拟财产属于玩家所有。对于此类虚拟财产如果仅以运营商的官方定价进行计算,就完全忽略了游戏玩家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对玩家太不公平。可如果按照玩家的投入成本进行计算,则又缺乏明确的标准。目前,网络游戏玩家群体之间在各种交易平台(例如淘宝)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虚拟财产换算与交易机制,大部分虚拟财产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价格,因此,对此类虚拟财产就可以市场平均价格进行计算。
第三类,属于网络运营商所有的虚拟财产。此类虚拟财产的特点是其直接由运营商开发所得,与玩家所有的虚拟财产存在重大区别。玩家虚拟财产的损失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损失相同,而运营商虚拟财产的损失与其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损失则有天壤之别。例如,腾讯被盗1亿Q币与其被盗1亿现金明显不同,在1亿Q币被盗后,只要有用户购买Q币,腾讯公司依然可以出售,因为只要其简单复制一下就可以,其财产损失并不明显。因此,其价值不宜直接以市场价格或是其官方价格进行计算。为避免量刑过重,对于侵犯此类虚拟财产的,宜按照情节而不是数额予以量刑。例如,行为人利用某网络游戏的漏洞,盗取该游戏运营商的游戏币1300亿个,如果按照当时市场价格计算,则价值5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按此数额给行为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则明显畸重。而如果按照情节来量刑,就可以避免数额过大所造成的量刑畸重的不利后果。如果认为情节严重,则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认为情节并不严重,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就能做到罪刑均衡(张明楷,2015:25)。此种情形下,并不是虚拟财产数额无法计算,而是为了解决量刑畸重的弊端而已。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作为财产犯罪其数额计算如此复杂,那按照计算机相关犯罪处理,不就免去此类麻烦了吗。事实上,如果将侵犯虚拟财产的犯罪一概以计算机犯罪论处,会存在明显的不足,尤其在行为人采取某种特殊方式抢劫、诈骗虚拟财产的场合,往往很难评价为计算机相关犯罪,导致形成不必要的处罚漏洞。例如,案例4,孙洋和李勇等人发现一网名“沈阳小伙”的游戏装备精良,于是在网上向其索要,被拒后,孙洋等四人于某日来到“沈阳小伙”上网的网吧,对其进行殴打、威胁,迫使其将1100余万个游戏币以及其他游戏装备转入行为人自己的账户。首先,该行为并不符合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因为该罪要求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很明显,进入计算机系统并且改变数据的是被害人本人,而不是行为人,行为人的行为与此不符。其次,行为人的行为也不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为行为人根本没有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更谈不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最后,行为人的行为也不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因为,行为人并没有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何来破坏可言。因此,对该行为不能评价为计算机相关犯罪。“显然,认为‘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建立在没有全面了解各种可能发生的案件的基础上”(张明楷,2015:24),会形成明显的处罚漏洞。
综上,单纯以价值难以估算并不能成其为否认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成立财产犯罪的理由。
四、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具体认定
对于窃取虚拟财产行为的认定,还涉及具体罪名的选择及罪数等较为复杂的问题。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在具体认定上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成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梁根林,2014:7)。该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生效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即使成立盗窃罪,都不应再以盗窃罪论处,而应当一律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处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成立盗窃罪(王志祥、袁宏山,2010:150)。该观点认为,非法获取虚拟财产以外的其他电子数据的行为侵犯的是网络安全,应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罚。以盗窃、诈骗方式获取虚拟财产这种类型的电子数据的,侵犯的是虚拟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益,因此应成立相应的财产犯罪。第三种观点认为,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同时触犯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邹政,2014:75)。第四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必然要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同时触犯盗窃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属于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邹政,2014:75)。
第一种观点一方面承认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可以成立盗窃罪,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将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一律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论处,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张明楷,2015:23)。例如,甲准备了60万元现金用于购买游戏币,但在购买之前被乙全部盗走。A用60万元现金全部购买了游戏币,但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B全部盗走。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将乙按照盗窃罪论处,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对于B则只能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便认为B情节特别严重,也只能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同样盗窃价值60万元的财产,却导致如此不同的处理结果,明显难以被人接受。
第二种观点结论或许正确,但论证思路却颇有疑义。如果将虚拟财产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对立起来,认为分别成立财产犯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事实不清、认识错误等场合会导致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罪,以至于出现不必要的处罚漏洞(张明楷,2011:126)。而且,虚拟财产本身的确是一组电子数据,说它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并没有问题,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而已。所以,认为虚拟财产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是一种排斥关系难谓妥当。
而第四种观点也难谓合理。如所周知,牵连犯是实质的数罪,即原本两个行为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只是因为具有类型性的关联而牵连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刑法对有些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对有些牵连犯则从一重罪论处。但牵连犯成立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二个以上犯罪行为,仅实施一个行为或数行为只成立一罪(复行为犯)的,不可能构成牵连犯。在盗窃虚拟财产的场合,行为人所实施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本身不可能成立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因为该罪要求的是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而普通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不可能入侵上述系统。此外,行为人所实施的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同时也是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从实质上来看,只有一个行为而不是数个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牵连犯。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适。当然也有学者(刘明祥,2016:152)认为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关系,应属于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那么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到底有何不同呢?所谓想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形。法条竞合,则是指刑法条文之间在内容上存在包容与交叉关系。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具体区别如下:(1)形式上的区别。就形式上而言,法条竞合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外延有重叠、交叉产生的,因此根源在于立法结构而不在于案件事实。换言之,在法条竞合时,不管现实案情如何,两个条文之间都有竞合关系。例如盗窃罪与盗窃枪支罪,均使用了“盗窃”这一动词,且盗窃的对象都可以评价为“财物”,因此这两个罪具有法条竞合关系。相反,想象竞合则取决于案件事实,亦即,犯罪行为触犯了两个不同的法条,这两个法条之间并不是必然而只是偶然因犯罪行为具有了重合关系。例如盗窃道路中央的井盖,导致行人掉进下水道摔死,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盗窃井盖的行为,而且只有在此场合才同时触犯了盗窃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两个罪名。因此该行为所触犯的两个罪就不属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2)实质上的差异。法条竞合时,只有一个法益受到侵害;想象竞合时,则有数个法益受到侵害(张明楷,2011:434)。在法条竞合的场合,虽然犯罪行为同时违反了数个罪刑规范,但由于规范之间存在包容与交叉关系,实质上仅侵犯了一个罪刑规范的保护法益。在想象竞合的场合,一个行为不仅违反了数个罪刑规范,而且实质上还侵害了数个罪刑规范的保护法益。当然,由于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所保护的是双重法益(复杂客体),因此,“只有一个法益受到侵害”是指行为仅侵害了一个罪的保护法益,“数个法益受到侵害”是指行为侵害了两个以上罪的保护法益。例如,盗窃枪支罪既侵害了财产又侵害了公共安全,但其侵害的法益并没有超出盗窃枪支罪的保护法益,因此“只有一个法益受到侵害”。其与盗窃罪之间是法条竞合。而盗窃道路中央的井盖时,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破坏交通设施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因此该行为同时侵犯了两个罪的保护法益,因而是想象竞合。就盗窃虚拟财产而言,在形式上,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本身并不必然同时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例如,在被害人同意进入其计算机系统后实施盗窃的就不成其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就实质而言,在盗窃虚拟财产时,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而不是社会秩序,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秩序而不是财产,因此该行为侵犯了两个罪而不是一个罪的保护法益,因此,在盗窃虚拟财产的场合,应属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
综上所述,盗窃虚拟财产构成犯罪的,同时触犯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应属于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按盗窃罪而不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论处。因此,前文案例3以盗窃罪论处较为合理。
在案例2中,对于张翊等专门盗取账号和密码并出卖的行为,因为账号和密码本身并不具有财产价值,因此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较适宜。对于后续收买人岳曾伟的行为,则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姜金良、袁海鸿,2015:92):第一种观点认为,后续收买人构成盗窃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后续收买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第三种观点认为,后续收买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其实,在上述案件中,后续收买人岳曾伟存在两个犯罪行为,其一是收购前盗窃人所获得的游戏账号、密码,其二是利用所收购的游戏账号、密码进一步实施盗取他人游戏金币、装备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虚拟财产不具有财产属性,而前面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本身有误。而第一、第三两种观点都只重视其中的某一个行为,而忽视了另一个行为。如果按照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前面的收购行为可以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后面盗取他人游戏金币、装备的行为则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即按照盗窃罪论处。因此,后续收买人岳曾伟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盗窃罪两个罪,且应数罪并罚。张高榕、谢云龙、陈奕达及岳磊等人则成立盗窃罪的共犯。
在案例1中,曹某身为腾讯公司员工,其职责之一是向参加游戏活动的用户发放游戏道具作为奖励。而其将多余的游戏道具进行销售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己有,应该成立职务侵占罪,尚某构成帮助犯。
五、结 语
同属窃取虚拟财产的案件,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虚拟财产性质界定的不统一。过去,我国刑法学界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缺乏与民法学界的对话与交流。因此,本文借鉴了日本学术界中“刑法与民法的对话”这一研究模式,以我国民法学者对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
通过检讨民法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虚拟财产具有网络依赖性、数据性、期限性,与传统财产有所区别,但由于其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排他性等财产的基本特征,因而依然具有财产属性,系属财产;虚拟财产既不是债权,也不是知识产权或者一种新型权利,而应该是物权,因为它既具有作为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和独立性,而且还具有物权的“支配性”。
既然可以认定网络虚拟财产为物,按照物理管理可能性说,即便是无体物,也可以将其认定为我国刑法中的财物,将其纳入财产犯罪的保护范围,这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与我国民法相协调。对于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数额计算的难题可以通过分类处理的方式得以解决:(1)由玩家从网络运营商或者第三人处购买的虚拟财产,其价值由运营商的官方定价进行计算;(2)玩家购买后又经过游戏劳动使之升级的虚拟财产,可以按照虚拟财产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计算;(3)对于网络运营商所有的虚拟财产,则可以按照情节来量刑,以避免数额过大所造成的量刑畸重的不利后果。按照上述方式对窃取虚拟财产的犯罪行为以盗窃罪论处,不仅可以使处罚妥当、均衡,还可以避免刑法上不必要的处罚漏洞。
对于窃取虚拟财产刑事责任的认定,自非本文所能彻底解决。本文的讨论,旨在希望引起刑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共同关注。就刑法与民法的对话而言,本文仅仅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
[1] [日]大塚仁(2003).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董玉庭(2012).论刑法中财物概念之解释——以诈骗罪为视角.当代法学,6.
[3] [日]福田平(2002).刑法各论(全订第3版增补).东京:有斐阁.
[4] 高德胜(2012).基于信息语境的信息法益的内涵与类型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5] 高富平、杜 军(2008).虚拟社区之用户创制物的财产法界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6] 侯国云(2008).论网络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不当性——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世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7] 姜金良、袁海鸿(2015).侵入他人游戏账号窃取虚拟财产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人民司法,6.
[8] 梁根林(2014).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以首例盗卖QQ号案的刑法适用为视角.人民检察,1.
[9] 林旭霞(2010).虚拟财产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10] 刘明祥(2016).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法学,1.
[11] [日]齐藤信治(2001).刑法各论.东京:有斐阁.
[12] 钱明星、张 帆(2008).网络虚拟财产民法问题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13] [日]山口厚(2011).刑法各论.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 王 钢(2015).盗窃与诈骗的区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第27号指导案例的展开.政治与法律,4.
[15] 王志祥、袁宏山(2010).论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正当性——与侯国云教授商榷.北方法学,4.
[16] 王 竹(2008).物权法视野下的虚拟财产二分法及其法律规则.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17] 杨立新、王中合(2004).论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及其基本规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6.
[18] 杨 旭(2007).我国网络货币的发展与政策研究.财经问题研究,10.
[19] 张明楷(2011).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
[20] 张明楷(2015).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法学,3.
[21] 赵秉志、阴建峰(2008).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法律科学,4.
[22] 邹 政(2014).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适用探讨——兼论虚拟财产价格的确定.法律适用,5.
[23] [德]Ingeborg Puppe(2010).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 媛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Stealing Virtual Property in View of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Law
LiQigua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games,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virtual property in cyberspace are in increase. In judicial practice,there are different judgment.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tole virtual property were sentenced to be theft, some were the crime of illegal access to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and the other were not guilty.For this reason,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make an in-depth and detailed study on this issue.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Is the behavior of stealing virtual property a crime? If it is a crime, is it theft, or the crime of illegal access to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How to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crime of stealing virtual property? Will the protection of virtual property disrupt the financial order and lead to inflation?The cases of stealing virtual property are the same in essence, but their judgements vary.The cause lie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virtual property.Some criminal law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this issu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virtual property in civil law.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failure to master the study of virtual property in civil law, the result is full of mistakes.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study of virtual property being in a dilemma in academic circles of criminal law.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tudy of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stealing virtual property in view of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law as a new perspective.By reviewing the study of virtual property in civil law, we can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Although virtual proper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dependence, data and time-limit and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roperty in some respects, it is still property because it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perty,i.e., value, scarcity and exclusiveness.What is the attribute of virtual property? Firstly, the virtual property is not intellectual property.Secondly,virtual property is not a new property right.Thirdly, virtual property is not credit right because the credit right can not accurately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ght of virtual property.In fact, the 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the real right because it has both the specificit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bject of real right and it also has the dominance of real right.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property, there are two opposing perspectives which are both the doctrine of ontology and the doctrine of possibility of management in criminal law.The possibility of physical management is more suitable for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In criminal law, virtual property is regarded as property which is in the scope of the possible semantic of our criminal law and protected by criminal law doesn’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In addition,the protection of virtual property by law wouldn’t disturb the order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lead to inflation.In fact, the virtual currency has been issued for many years and it has no adverse effects on the financial order.The major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based on the study of civil law,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property in criminal law and that,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imaginative joinder of offenses should be given a heavier punishment,the stealing of 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punished with theft and not the crime of illegal access to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when the two crimes exist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the value of 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he subject of legal interest.Firstly, when virtual property is purchased by a player from a network operator or a third person, the value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price of the operator.Secondly,when players purchase virtual property and upgrade it,the value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rading price in the market.Thirdly,as for network operator’s virtual property, it may be sentenced by the plot in order to avoid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amount of the operator’s virtual property.The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displays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the research method is not limited to the internal research of criminal law and is taken by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aw.On the other hand,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virtual property is found out. This solves the difficult problem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virtual property in the past.
virtual property; view of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law; property crime; amount calculation
D924
: A
: 1672-7320(2017)02-0085-12
10.14086/j.cnki.wujss.2017.02.008
2016-05-19
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课题(CLS(2015)D062)
■作者地址:李齐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Email:jianghu03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