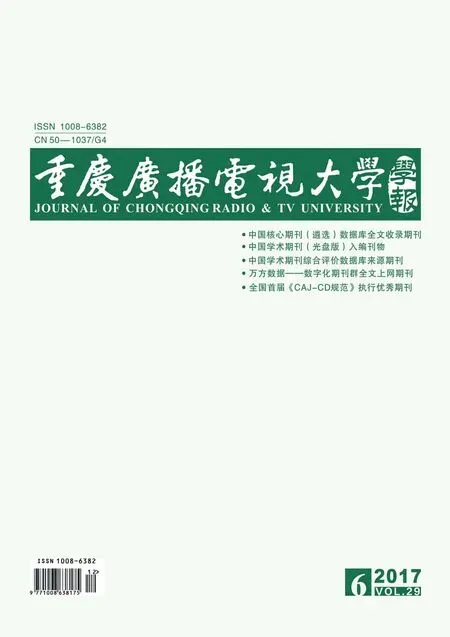论广告的制造“虚假需要”与“生产意义”悖论
邓胜月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广告制造“虚假需要”
马尔库塞认为“广告是一种催眠术”[1]74,可以迫使人们把虚假需要当成真实的需要,为人们营造虚假的幸福。所谓“虚假需要”是由外力支配和强迫的需要,民众受到奴役的本质,使得他们的需要也是虚假的;而真实的需要是不被强加的,是人们内心自发的欲望。
人们对“广告催眠术”深信不疑,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1]6。马尔库塞认为广告宣传的“需要”大多数都属于“虚假需要”的范畴。“虚假需要”不是人类本能的体现,而是物质消费的欲望。在这些“虚假需要”的统治下,人们逐渐陷入同一化的泥沼。人们的生命被消费,被商品所代表。马尔库塞说:“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1]11
这些“虚假的意识”让“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风景胜地,让打字员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连黑人也有了高级轿车。由于生活方式的同化,由于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那种在自由和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1]206。
在这样一种“虚假需要”的统治下,马尔库塞揭示人们正深陷消费异化的困境中,只能通过商品来认识自己,获取“虚假的幸福”。“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在消费异化的困境中,人与物的主客体位置发生颠倒。物质的关系掩盖了人际的关系。消费异化扭曲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阶层划分和获取归属感的途径是商品消费。人们可以通过拥有一瓶“香奈儿5号”跻身于更高级的社交圈子,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人们完全生活于商品设定的语境中,对任何事物的解释和认识都带着强烈的商品信徒的色彩。而这些在马尔库塞的眼中完全是统治需要的产物,是被强加的,是虚假的,目的是让人们变得同一化,在规定的秩序中进行选择。“人们就丧失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复杂的社会存在关系。”[2]人们失去了任何替代选择的机会和否定社会的力量,成了单向度的人,臣服于资本主义的统治。
二、广告制造“需要的规定性解读”
“需要这一概念成了现代思想和日常经验中一个最富于批判性的范畴”,《消费文化读本》一书中谈到,“现代人之所以变成一种‘单向度’的人,正是因为在一种消费和商品文化中,需要的概念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批判尺度”[3]。然而,马尔库塞用来对抗“虚假需要”的观点本身预设了一个理想的前提,这是乌托邦的,也是意识形态性的,自然削弱了他的理论批判力量。
实际上,广告制造“虚假的需要”这样的说法过于偏激。首先,人们根本无法分清哪些是“真实的”需要,哪些是“虚假的”需要;其次,“需要”都是源自于人们的内在动机。人类的动机很少被科学技术或是媒介手段创造出来。正如消费的动机不会由产品创造出来。克莱·舍基用城市和人类的关系来作出类似的比喻:城市是因为人们喜欢靠近彼此,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而不是因为有了城市,人们才开始交流[4]。
马尔库塞对“广告制造虚假需要”这一观点摇摆不定,他最后不得不将问题抛到个体的手中:“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求,什么是虚假的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回答。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下降到他们的本能上),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1]7
需要是先在的,无法被广告创造,所有的需要都应当是“真实的”。而在马尔库塞眼中,广告制造的“虚假需要”,其实是广告文本对“需要”造成的规定性解读。
本文选取一则美国20世纪60年代经典的广告案例(见图1),来解释先在的需要和需要的规定性解读。

图1 “幸福时光”香烟海报
“It’s toasted”是Lucky Strike(“幸福时光”香烟)的一句经典广告语,它利用了语言的双关性。Toasted既是烘焙过的意思,同时又有“被祝福”的含义。当时的美国正大力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人们对健康的担忧导致许多香烟无法销售出去。“幸福时光”香烟的宣传则巧妙地避开了人们的担忧。“幸福时光”香烟的海报如图1所示,海报呈现红黄的色调、海报上的人物是一名面色红润、健康刚硬的抽烟男子,甚至海报所用的字体都是红色的。这些显性的视觉组合带给消费者“被烘烤的炙热”的联想。“被烘焙过的香烟”降低了对人体的损害,积极的色彩和人物形象又再次加深了消费者对“toasted”(被烘焙/被祝福)的双关理解。因此,Lucky Strike获得良好的收益。
以上是广告文本造成的规定性解读。文本结构、语言能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促使人们坚定不移地朝着“被祝福”的含义解读,广告吸引了人们购买“幸福时光”香烟,但是人们抽烟的需要是先在的,而这种抽烟的需要又会被健康问题所阻碍。这时,恰巧广告给了消费者一个最合适的理由。这个广告文本当中的所有元素,无论是人物形象、色彩,还是文字,都在规定着消费者相信广告创造的理由,而不是给消费者创造一个抽烟的需要。
这就是马尔库塞混淆概念之处,这也是为什么他无法清楚地回答所谓“虚假需要”的问题。广告无法创造出先在的需要,但是它可以表达需要,又能够规定消费者的解读。
三、广告“生产意义”
广告在这个过程中规定了人们对商品的解读,为商品赋予新的意义,其中的作用机制既不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创造“虚假需要”来催眠人们,也不是商品拜物教所论述的“最重要的就是挖空商品的意义,藏匿真实的社会关系,通过人们的劳动将社会关系客体化于商品中”[5],而是构建广告主、商品、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广告中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和维护三者之间的关系。消费者表面上看到的是显性部分,比如文案、色彩、音乐等,而这些实际上都代表着商家对目标消费群的了解。这些显性组合背后隐藏的隐性联想最终影响目标消费者对商品、品牌的每一次感知、理解和记忆。这是广告最为关键的过程。
广告通过人们的解读而起作用,解读的同时人们又被拉入广告的体裁之中。这不是单纯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控制,其关系是相互的、多维的。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种符号化的系统化操控活动。”[6]
意义是主客体的关联,意义的定义也同样是双向的构成,意义由主体的解释决定,通过符号传达。相应地,主体存在于意义的解释之中,存在于这些符号之中。海德格尔说:“意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相交共生的,是主客体的契合。 ”[7]因此,广告生产意义的本质即是构建关系。
现在的广告活动的确更加注重构建关系,强调体验性。以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大楼的“玫瑰花海”活动和“熊猫求婚”活动为例。“熊猫求婚”是知名求婚钻戒品牌——Darry Ring(DR)所策划的广告活动。手捧DR钻戒的熊猫向他的“女朋友”求婚,数十万的群众来拍照围观。“玫瑰花海”则是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大楼的天台处点亮数千盏玫瑰花形状的灯,为人们呈现一场极其震撼的视觉展览,人们纷纷拍照转发。这两个案例获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注重消费者的体验,即消费者能够亲自参与到广告的活动之中。许多品牌商利用人们渴望联系的内在动机来加强用户的黏性,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魅族手机。魅族手机的定位并非高端精英阶层,但消费者对魅族的忠诚度和美誉度都极高,原因正是魅族建立了与消费者密切的联系。魅族为消费者打造魅族网络社区,消费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他们对手机科技、对魅族产品的想法。一群喜爱手机、喜爱科技的人通过魅族这个品牌联系在一起。每一年魅族社区都有属于粉丝的节日,喜爱科技的人在这里如同进入温暖的家庭。比起在消费者的耳边进行轰炸式的宣传,魅族如此打造消费者社区的方式显然对品牌的塑造和产品的售卖更加有效。因共同喜好聚集起来的消费者群体也更加忠诚。
四、广告在关系中发展
广告生产意义的本质即是构建关系。广告并非制造了“虚假需要”,人们也不再依靠商品消费确定的阶层表达自我,而是依靠关系联结的群体获得归属感,实现自我价值。个人价值不是必须经由消费来实现,人们选择通过创造主动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通过消费被迫获取阶层的认同。主动创造出个人的价值比起被迫消费获取的更加让人有成就感。人们在群体之中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解读社会。虽然马尔库塞认为人们处于被设计好的消费语境中,陷入资本家的圈套,但现在人们除了消费,还可以积极地进行创造和分享。因此,可以说人们正在慢慢走出消费异化的困境。在新时期可以表现为以下三点。
1. 人际关系从阶层划分转变为圈层集合。经过长时间的尝试和发展,技术得以进步,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融合变化。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跨越时空将人们联系到一起。新型的社交方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Twitter、Facebook、微博等改变人们的生活。比起试图在商品划分的阶层中寻找归属感,却获得更多的失落感和空虚感,人们更愿意参与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组建起来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而不是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彰显。如今,人们的组织关系不再是代表政治经济权利的阶层,而是蕴涵兴趣爱好的群体。人们从阶层的归属慢慢脱离,转型成为群体的归属。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组织兴起,人们逐渐倾向于与自己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的群体。比如,热爱动漫的青少年聚集在动漫社区,在群体中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而不再是通过消费商品来获取阶层的优越感。人们在维基百科上协同写作,互相补充,关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如果群体组织中的某个个体只有地位和财富,与其他成员却没有共同文化爱好,那么他将十分空虚和焦虑;除了彰显身份地位,他无法获得任何与自我心灵的对话,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社会性工具越来越多地让群体具有生长在一起并在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群体中的联系愈加紧密且群体的规模呈现上升的趋势,是因为人们渴望相互接触。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在他们作出消费决策的时候,也不再一味地迷信广告的“催眠”,比如“超过1/3的手机使用者会在购物时给朋友打电话,询问他们对某些商品的评价”[8]。
2. 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自我认同的方式从消费转变为创造。今天,联结社会的力量已经不再是消费,而是创造。较之工业社会时期,当今社会提供的是一种创造语境。自身的价值和认识社会的方式从消费转变成了创造。人们利用空余的时间进行价值创造,中国的猪八戒网站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人们利用空余时间在这个网站上接受企业或者个人发布的需求,完成之后获得相应的酬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斜杠青年”。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职业,而是追求更加多元的身份和生活组成;他们或许有一种赖以生存的主要职业,但是在这份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创造。社交网络中各种层出不穷的表达工具和文化潮流,使得网友们可以灵活动态地建构自己的多重身份。*李娟 论社交网络中的符号身份[J] 符号与传媒,2017(2):153“斜杠青年”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并没有禁锢在消费商品的既定秩序中,这种现象其实正是人们拨开了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束缚迷雾,找寻到了内在的动机,释放了人类渴望交流、渴望联系的天性。“斜杠青年”也逐渐成为全球的趋势。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追寻着自由,追寻着能够以多样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他们在尝试中挖掘自我,与不同群体的人们来往交流。
3. 社会的文化形态从单一转变为多元。大众化、一般化的社会也变得个性化和多元化。在人们相互的联系中,社会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在时空上更具有广泛性。人们能够从不同的渠道倾听不同的声音,也能够有机会从不同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各类社交媒体里交流互动,而不是被迫地接受广告、新闻等的控制,人们的传播更加自由。比如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传播力度远远超过了原本的事件。这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和自由性导致了内容的多元化,人们可以在网络的各大论坛、微博中找到自己的喜好,许多旅游爱好者、游戏爱好者、美妆爱好者也因此收获了大量粉丝。多元化的局面使人们群体意识苏醒,是人们自身的价值和认识社会的方式由消费变为创造的必然结果。就像现在的一些小众手工品牌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实际上,人们没有失去否定的力量变成单向度的人。人们正在拒绝标准化的生产,人们能够感知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社会也越来越丰富。
五、结语
广告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呈现同消费者的连接。比如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中的弹幕广告,观众在发送弹幕的时候夹带商品的信息,在嬉笑怒骂之中传递着广告。2016年的电视剧《盗墓笔记》,把广告制作成和剧情相关的小剧场,赞助品牌在画面中进行“吐槽”,观众并没有反感这些广告,反而对剧中的广告剧情产生了期待。在过去,如果电视剧播到一半突然插入广告,观众十之八九会选择换台,而现在这些全新的广告形式让消费者感受到了关联,感受到了互动和交流,自然他们的态度会完全不同。以往的广告制作得不像是广告,在消费者无法察觉的时候将广告中的信息注入消费者体内才算是广告说服的成功。然而今天,广告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人们的眼前,毫不避讳,表面上是一种网络反讽,实际上正是人们内在交流动机的觉醒,它正在冲破束缚的迷雾,完成自我的变革。
广告不再是单纯机械地售卖商品,它们注入了更多温暖的元素。人们除了希望能在商品中得到物质满足,更希望得到情感或价值的认同。2012戛纳广告节的获奖作品“Insight”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宣传片“Insight”是三星公司旗下一款相机的广告。它描述了一群盲人孩子是如何用相机记录生活的,他们的照片通过浮雕打印,可以被触摸和感知。广告的文案这么写道,“视觉不是感知这个世界唯一的方式,相机也不仅仅是为那些可以看见的人设计,张开心灵的眼睛”。三星相机的意义并不仅仅为那些看得见的人所造,更是为那些渴望捕获世界之美的人所造。捕捉生活之美,感受到世界和自己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是人们真正的渴望和诉求,是人类自我变革在广告中的体现。
我们更要认识和把握广告“意义生产”的本质——构建关系。树立起关于广告的新型思维,透过广告表达新时期人们的内在动机,注重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结。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胡水清.论审美能量的聚集——马尔库塞新感性理论再审视[J].文教资料,2011(22):101.
[3]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1.
[4]克莱·舍基,胡泳.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M].哈丽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18.
[5]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M].马姗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1.
[6]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3.
[7]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6.
[8]恰克·马丁.决战第三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与营销新规则[M].唐心通,张延臣,郑常青,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