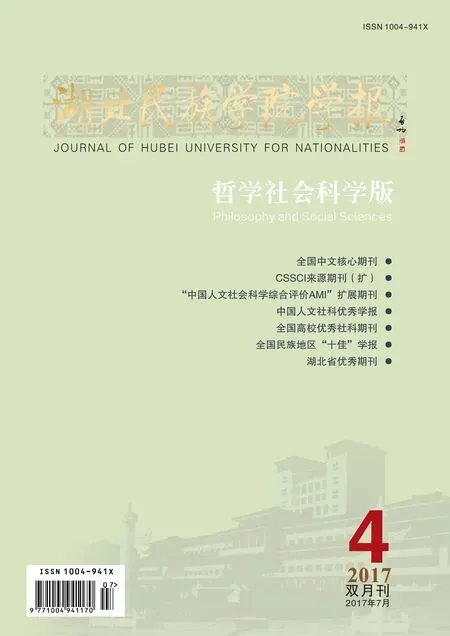全球化中的地方性与非地方性
——论湖北籍海外华文作家的地方书写
刘玉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有别于科学主义地理学的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所指的地方“是一种用来表达对世界的态度的概念,强调主体性和体验,而非空间科学的冰冷、僵硬逻辑”[1]20。具体到文学之中就是指饱含着作家情感体验、审美观照、认知投射的地方。由于视界处于国际、洲际范围之内,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地方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地方概念的扩大化、多元性。首先,作为出生地、生长地的故乡观念虽然仍旧存在,然而往往被地理范围更广的故国观念所替代;其次,地方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故乡、故国,他乡、他国也扩展为地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所指单一的故乡观念被打破后,必然演化为多元性的地方观念。我们认为,尽管相当多的海外华文作家仍然心存根深蒂固的“故乡”观念,但以“故乡”为核心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满足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阐释需求,而“地方”这一术语则在涵括故乡的同时,因其所指在内涵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故而在阐释海外华文文学时显得更契合、更有效。
一、从地方性的隐匿到地方性的显现
地方性如何可能在全球化语境中被书写?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显然蕴含着如下的逻辑:尽管人人都存在于地方之中,但地方性并非得到了每个人的关注。因此,地方性可以分为隐匿的地方性与显现的地方性两种形态。关注海外华文作家的地方书写,首先要解决如下问题:地方性如何从隐匿状态走向显现状态?全球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推动性还是阻遏性的?
通常,人们依据范围的大小标准来划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特殊与普遍,将范围较小的地方看作是特殊性存在,将范围较大的全国或全球视为普遍性存在。这种认识论固然没有问题,然而普遍与特殊毕竟处于辩证法的哲学逻辑中,我们是否可以倒转一下固有的认识,将地方视作普遍性存在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论述:“有之为有并非固定之物,也非至极之物,而是有辩证法性质,要过渡到它的对方的,”[2]192“当我们说到‘有’的概念时,我们所谓‘有’也只能指‘变易’,不能指‘有’。”[2]198也即,这里的“有”并非指原初的一,而是在“有”与“无”所形成的差异与辩证之中的变易(Das Werden),“变易既是第一个具体的思想范畴,同时也是第一个真正的思想范畴。”[2]199
黑格尔的这一关于认知过程的逻辑哲学观念,对应到地方与全球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时,则正如张旭东所持的观点:“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然而这种普遍性是“未经辩证思考的、未经世界历史考验的”,因此“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或自我意识一样,往往就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一个没有生产性的‘一’或‘自我同一性’”[3]。以上引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地方性在遭遇到另一种作为他者的地方性之前,往往并未认识到自己是特殊性的存在,而是将自己作为普遍性存在,几乎每一种文化对自己独特起源性的近乎强迫症似的建构无疑是这种普遍性的体现,这种原初状态的地方性可称之为隐匿的地方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族群的人类,都易于以‘自我’为中心去认知世界。自我中心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显得是普遍的人类特性。”[4]然而,“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普遍理念在逻辑上无疑是具有缺憾的,这种缺憾就在于它未经辩证法的考验、未经与他者的比较,这是未经批判的自我意识,是地方性的原初状态,也即隐匿的地方性。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在交流、联系日趋频繁之中似乎也逐渐被抹掉,人类将面临一种均质化的世界。也就是说,地方性在全球化中面临着日趋淡化甚至消亡的境遇。照此逻辑推衍,在全球化时代中,谈论地方性就成为无稽之谈。然而,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一语破的:“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5]如果说将上述关于全球化带来均质化的观点归为一种幻象的做法显得过于苛刻的话,那么,它也只能作为全球化两种甚至多种面相中的一种而存在。诺埃尔·卡斯特里十分充分地用五点原因解释了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中得以保持,而且给出如下结论:“人文地理学家已经证明地方之间的联系越多,地方之间的差异就越多。”[6]不难看出,全球化提供了一种认识论意义的变易,在与他者的辩证、比较之中,推动着隐匿的地方性走向显现的地方性。
倡导文学地理学批评的邹建军认为:“地理感知是作品产生的基础之一,地理感知是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7]75照此逻辑推论,全球化视野中的地方性问题,在文学创作者的地理感知之中成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自然成为应有之义。事实上,这一观点在海外华文文学之中确实得到了印证。海外华人文学中的地方性书写总是处于与他者进行对照的视界中,超越了单一性视角,地方性在相互比较之中得以更为真实的显现,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场域。
总之,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使得作者对地方性有着不同的感知。当他们身处国内时,地方性并未显示出其足够的独特性,往往处于相对隐匿状态,而当作者身处海外,地方性则真正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地方性是在地理、文化迁徙中得到作家的特别关注的,在湖北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中,的确显示出了这一特点,以下以其中三位作家为例进行简要论述。
在题为《荆门,不得不说的话》的散文里,程宝林十分坦诚地讲道:“我拥有两个国家,两种语言,两套价值观,包括价值理念。任何事情,我都有两套。它们在斗争,在妥协,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中斗争。这种斗争,激发起我的写作欲望。”[8]也就是说,国外的经历为创作者建构起一种新的认知与价值体系,在新体系的参照之中,国外经验不仅对创作者的故乡书写起到了激发性作用,而且使得这种故乡书写显得更为理性、客观。针对程宝林的散文创作,学者江少川在与作者的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有深意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这类写家乡、亲人、乡亲的散文,许多是你出国以后写的。假如没有出国,你会这样写吗?换句话说,移居他国后,给你写故乡的散文增添了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改变呢?”程宝林的回答是:“在移居美国10多年之后,这片英语和美元的国度,已经由‘别人的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国家’。在经过了海外的大量阅读后,回望故土,我将中国农民的整体性困境和贫困,以及触目惊心的对不平等与不公平的忍受和忍耐,放在中国现代、当代历史的不堪回首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和抒写。”[9]正如欧阳昱在小说《东坡纪事》中写到的,在澳大利亚只有道庄一人来自黄州,他对黄州的认知是在外国人麦克洛克林教授的推动下才更为深入的,认识到苏东坡之于黄州与自己之于澳洲之间存在着的同一性。
二、古典式恋地情结
以人地关系的亲密性(intimacy)作为区分尺度,可将人们对地方的态度分为古典的恋地情结与现代的非地方性两类。古典的恋地情结体现出认知主体在人地关系中的求定意志(will to certainty)。所谓求定意志,“意味着力图转化‘我们所处世界的不确定空间’,转化这种不定性和潜在的多重性——这是自然之狡计被解构的后果,将之变成导向明确的唯一性”[10]26。因此,求定意志不仅仅表现在对故乡、故国的追忆,往往也表现在对他乡、他国的认同上,甚至是故乡、故国与他乡、他国的双重恋地。
有哪些故国的地方性被海外华文文学所关注,它们何以在跨国、跨洲的远方仍然被人所记忆、所书写?古典式恋地情结在程宝林的创作中最为典型。程宝林尝试着在其散文中建构一种以歇张村为原点,经由沙洋镇、沙洋县,直至以荆门市为终点的地方性历史。在题为《我终将为他们作序》的序文中,不难发现他的这种壮志:“为什么我不能为这个村庄写一本《村庄史》?在这本只涉及一个中国小村的‘断代史’中,我要发扬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让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传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11]8然而,一个村庄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毕竟极其有限,哪些内容能够成为作家笔下的史事呢?作家对此并非没有深思熟虑,“小镇没有任何古迹,也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名人。小镇的全部风景,都在人心深处”[11]206。也就是说,程宝林意在透过地方性这一视角来镌刻出关于人心的史书。其实不仅沙洋镇如此,作者笔下故乡书写大都如此。“家乡是什么?家乡是出发的地方。但对于远游者来说,家乡是永恒的驿站,在那里,归者聚散,过客歌哭,交换行路人温润的目光。”[12]一方面,人心是地方之众人的人心,地方在此意义上是世界的一个子集或切面,地方史可以映射出国家史乃至世界史;另一方面,人心又可只是作者一人的人心,书写地方只是为了探究内心出发之处,地方史在此意义上又成为灵魂史。
聂华苓在终极意义上也是具有古典恋地情结的作家。她在自传《三生影像》中,以一首序诗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13]此“树喻”是聂华苓对“三生三世”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既然聂华苓活过了“三生三世”,回忆录也分为了三部分,每部分均以地理意象为核心要素加以命名:故园、绿岛小夜曲、红楼情事。“故园”指的是中国大陆、“绿岛”指的是中国台湾岛、“红楼”指的是美国爱荷华河畔的红楼鹿园。祖国大陆是聂华苓人生的起点,她在这里出生、成长,加之当时国内政局不稳、战火频仍,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武汉、宜昌、重庆、南京、北平等地成为她文学创作中最为常见的地方。三斗坪是湖北宜昌的一个小镇,抗日战争期间聂华苓曾在此住过一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就是以此段生活为基础写成的。她在《苓子是我吗?》一文中说:“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14]三斗坪尽管留存着很多青春苦涩的记忆,但这里毕竟是战火岁月中的庇护所,给作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中国乡村经验。作为武汉人的聂华苓,汉口租界、江汉关码头、东湖、武汉大学等武汉具有代表性的地点频频进入其作品之中。《千山外,水长流》中得到详尽描写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可以说集中了一个城市之所以被记忆的所有元素。武汉这一城市至少集中了两种人的地方感:对于美国记者彼尔来讲,出于两个原因要到武汉去,一方面他要去看看作为女友徐风莲出生地的武汉,另一方面彼尔正在研究中国的学生运动,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标示着高等教育承负着的民族抗争精神,因而武汉也是一块精神高地;而徐风莲却拒绝跟他一起返回故乡,因为她小时住在汉口租界,租界给她最深的印象就是那里的外国人与妓女,在她传统的母亲的观念中,只有妓女才和洋人在一起,武汉因而也与民族的耻辱感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来说,不仅仅故国的地方可以引起人们的依恋感,移居国甚至是旅游之地亦可成为情感认同的处所。吕红在小说《美国情人》中专辟一节,描述她心目中的旧金山,“新旧并存、传统与现代杂糅、东方与西方混合,构成了最具风味的地域特色”[15]93。旧金山在其笔下体现出了兼容并包的城市精神,这种精神“鼓励那些艺术冒险家、质问者以及探索者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15]95。作者在此借艺术家表达出的包容精神或许正是吸引各色人等的真正所在。在欧阳海燕的《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叶子的妈妈刘春来自江城(即湖北武汉),作为机械师的她,热爱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胜过机械,“家里那一面壁的书柜里,一大半是大小仲马、卢梭、左拉,是梅里美、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母亲选择来法国,定是与她心中固有的法国印象不无关系”[16]。这里体现出对法国的恋地情结。一般而言,是国外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吸引着相对落后国的移民,在吕红、欧阳海燕这里,却是非物质层面的城市自由精神和文学艺术成为人们产生恋地感的主要因素。
作为聂华苓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千山外,水长流》最能体现出作家的恋地情结,而且是中西双重的恋地。生活在美国石头城的祖孙三代都极具恋地情结,面对他人将石头城现代化的意图,坐在轮椅里的老布朗激烈反对,视此行为为挖他的老根。老布朗的儿子彼尔对石头城的依恋表现在,他在中国生死关头闪现于头脑的念头——“娥普西河边的黑色泥土真香啊!”[17]57老布朗的外孙彼利通过研究布朗山庄的建筑和历史来表达他对石头城的热爱,“我要生活在泥土上,生活在流水上。研究布朗山庄,就是为了要过那样的生活”[17]20。作为中美混血儿的莲儿,在探寻父亲与母亲爱情之谜的过程之中,也建构起她的恋地情结,她在母亲的信件中看到用别称“石头城”称呼南京时,作了如下眉批:“竟和爸爸的石头城同名!石头缘。”[17]286此种中美地理的亲和性,同样体现在文中多次提及的娥普西河与长江的亲和之上。莲儿的恋地情结正是在这种地方亲和中建构起来的,而地方的亲和正是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融合与相互认同。
与聂华苓有着类似人生经验的彭邦桢,生于湖北黄陂,后去台湾又至美国。以创作于美国的名作《月之故乡》为代表的一类诗歌表达出寄居海外的思乡情感,论家已多有论述。诗人的诗集《巴黎意象之书》却开掘出另一种书写地方的路径,他写的既不是故乡中国,也非移居地美国,而是旅途中的法国巴黎。诗人笔下的巴黎,并非一般游客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浮夸抒情,而是思想探求之诗:“关于巴黎,我曾知道很多。但我究竟该从何去写巴黎呢?是该作个纯粹感性的诗人曾在巴黎街头散步,还是该去作个哲学家的思想诗人曾在巴黎街头散步呢?应说这两者都可,惟我并不属意前者。这就是说,与其纯粹,不如思想;与其思想,不如探求。”[18]50十首诗歌前九首每首摹写一个地方,如香榭丽舍、亚历山大桥、凡尔赛宫、艾菲尔铁塔、红磨坊等地,后一首总结整个巴黎之行。巴黎这一地方一方面容纳进了诗人丰厚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也与诗人的故乡、移居地发生了联系。《香榭丽舍之秋》将秋天的法国梧桐拟人化,“当西风清曲梧桐:若梧桐诵读百科全书”、“当西风清角梧桐:若梧桐回忆华伦夫人”、“当西风清商梧桐:若梧桐浩歌悲惨世界”[18]1,进而在诗中融进了启蒙主义的伏尔泰、浪漫主义的卢梭和雨果,巴黎当时之景物与巴黎过往之历史如此在诗中得以联系。《罗丹纪念馆之石》摹写巴黎作为一个石头之城的独特魅力,而在此诗的注三中,诗人谈到自己从小对石头产生兴趣的两个原因:“因我的故乡就是个多石头的土地,那里有座矿山,几乎满山都是岩石。而我自小对文学产生兴趣,最早是从《石头记》开始。”[18]29《红磨坊之舞》则将红磨坊与麦子两种原本并无关联的意象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一方面与诗人从文学中得来的对“红磨坊”的想象之美有关,另一方面与诗人在故乡的种麦经验以及对麦子的审美好感有关。总之,《巴黎意象之书》这一诗集,表达出一种融合了故乡、移居国、旅游地三种地方的浓厚的恋地情结。
三、现代性语境中的非地方性
与古典恋地情结相反的是,现代性的反思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求知意志(will to know)。求知意志“解构一切确定性,打的名义是社会范畴和文化范畴要有能力揭示人为狡计,并由此规定自身在世上的定位和导向”[10]27。非地方性不是对地方性的无视、忽略,而是地方性的一种特殊形态,是面对地方性时的一种认知态度,即人的求知意志。非地方其实可以对应于段义孚所说的与地方相对的空间,而空间与地方并非是完全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关系。“即使地方的力量渐趋衰微甚至经常遗失了,作为缺席的它继续定义着文化与认同。作为在场的它也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19]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与欧阳昱的《东坡纪事》分别从女性与男性视角刻画了这种求知意志。
在聂华苓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中,依次由瞿塘峡、北平、台北、美国独树镇、田纳西、唐勒湖、第蒙等构成了一个多样的、动态的、变化的地方链条,地方不再是单一的、静态的、凝固的。在多个地方的流动之中,地方不再提供依附感,而为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建构提供了地理学意义的认知资源。桑青时期由瞿塘峡、北平、台北到美国独树镇的地理迁徙是被迫的、过去时的,带有强烈的压抑性。比如说台北带给桑青的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感。这种地方感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狭小逼仄的空间象征得以体现:桑青与丈夫沈家纲躲藏的台北阁楼,不仅仅只有四个榻榻米大小,而且屋子很低矮,以至于“我们不能站起来,只能在榻榻米上爬。八岁的桑娃可以站起来,但她不肯,她要学大人爬”[20]148。人原本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如今阁楼中的人却要爬行,退化为爬行动物。桃红时期地理迁徙的三种地方田纳西、唐勒湖、第蒙象征着反越战游行、西部拓荒、原始生活,不仅仅是主动的、现在时的,而且可以说是带有任意性的汪洋恣肆,主体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因而,有学者认为:“用弗洛伊德角度观之,桃红乃本我(id),桑青乃超我(superego),故事的发展由象征原欲动能的本我杀死象征道德教化的超我。”[21]桃红最后自诩为“一个来自不知名星球的女人”[20]196,这种主体性的无限放大藉由外太空星球这一地方来加以象征。邹建军认为地理是“天地之物”[7]6,不仅仅指地球,也涵括外太空在内。外太空的浩淼或许是最能象征人类的无限观念,赋予了人类认知的无限可能性。
欧阳昱尽管也书写祖国尤其是故乡等地方,但并非恋地情结式,他的地方书写带有浓重的现代反思精神。比如同是写武汉大学,聂华苓侧重于写历史事件中的武汉大学所担当的反抗精神,而在欧阳昱的《东坡纪事》中,道庄的妻子夏雨和吴聊均来自武汉大学,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功利性浓厚的留学跳板。有学者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22],这个判断恐怕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在欧阳昱小说、诗歌中复杂的人地关系,使得机械、僵硬的两分法失去判断效力。“反家园”与“非家园”之间尚存巨大的差异,如果从非地方性的角度看,说其“反家园”恐怕则是言过其实。对于欧阳昱的创作,更应以现代性的目光加以关注。
非地方性首先体现在故国、故乡层面。家乡的赤壁大学在是否聘用道庄这一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源于对他的身份困惑——他是不是澳大利亚人。如果他不是澳大利亚人,或者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被断定为非澳大利亚人,那么就没有聘用他的必要。“在中国,我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并非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是澳大利亚人。”[23]296其次,非地方性也体现在所移居的澳大利亚。小说第17章写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曾说……对我而言这却并不适用,所到之处我心恰恰无法找到安宁,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中国抑或是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23]289背后的原因何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没有做出过将澳大利亚视为可依附之地方的努力。道庄“曾寄厚望于澳大利亚……将其看作是一片机遇之地”,然而澳大利亚却只向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公民敞开,“即使我已向澳大利亚表示效忠,它却依旧视我为非澳大利亚人”[23]25。种族显然在此隔离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江少川认为唐人街作为独特的地理空间,既“是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飞地’”,又“见证着华侨残破的淘金梦”[24],《淘金地》中的柔埠,一方面体现出以广东人为主的淘金者对本土恶劣生存环境的逃避,另一方面,这种逃避无疑又陷入另一种恶劣环境。《东坡纪事》中强调“澳大利亚是一个起源于罪犯的国家”[23]53,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是英国人对罪犯的逃避行为所发生之地。欧阳昱描写的双重的逃避,其实也是双重的隔离:既与母国文化隔离,又与移居国文化隔离。欧阳昱在其创办的中英文文学杂志《原乡》(Otherland)发刊词中写道:“‘原乡’之于‘异乡’,正如‘异乡’之于‘原乡’,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宛如镜中映像。”[25]小说中道庄这一名字谐音“倒装”,作者确实就这一名字两字的前后颠倒显示出无所谓的态度,表面上这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却深刻反映出道庄的文化心理特征。也就是说,对一个地方的感受不再是单一性的了,而在现代性的格局之中变得多义而复杂,而这正是非地方性的面相。
在非地方性中,给作者带来的认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世界由实用理性思维主导。母亲的死正好发生在道庄找工作之时,加之家人也没坚持让他回国,因而他就没去奔丧。“她已经死了,回家去看她的死尸并无任何意义,因为我并不能跟她说话,而她也不能再看到我。”[23]31从道庄的这一番解释中,不难看出传统的断裂与现代性中以实用理性为主导的思维逻辑。“在我出生、长大、工作的家乡,我的记忆无非只是赚取金钱的现实,我现在强烈地意识到家不过只是过往云烟。”[23]73澳大利亚同样如此,“东方与西方之间并无区别。对二者而言,金钱才是绝对真理”[23]345。文学也被经济化,小说中写到的万事通(Ston Wan)弃文从商,认为从事文学实在是傻瓜们的职业。学术研究也无不充斥着实用理性思维,吴聊在澳大利亚的导师肖恩(Sean Dredge),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却拥有商人的头脑,他接收吴聊的惟一原因在于吴聊对他来说是有用的,吴聊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商品而已。
其次是价值虚无主义。实用理性思维主导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消解了人们原有的价值信仰,价值观念的模糊、消逝必然带来虚无主义。小说中对吴聊的姓氏“吴”做了一番介绍,“在汉语中,它听起来像极了无字。即使组成了新的词组,仍旧保有其空无的意义,还有无名的、空虚、无所事事、无处可藏等附加意,甚至无聊”[23]50-51。这种地方感是其精神状态的隐喻,其精神状态集中体现在其虚无历史观。在文本中吴聊是通过道庄来转述的,在某种程度上吴聊可看作是道庄内心的影子。
最后,是对虚无主义的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显得势单力薄。欧阳昱早年写于大陆的小说《愤怒的吴自立》中的吴自立,尽管对世界的无意义状态充满了愤怒,试图自杀,但最终在照录了一本捡到的日记后,“我胸中郁积已久的烦恼、仇恨、不幸、忧愁顿然消失,我不禁觉得我自杀的时机尚未成熟”[26]。在《东坡纪事》中,黄州与苏轼有关的地理意象、风物、古迹等几乎被写尽了:大到长江、龙王山、西山,小到赤壁公园里的雪堂、二赋堂、酹江亭、睡仙亭等,甚至写到很多与苏轼有关的食物,如东坡肉、东坡萝卜、东坡藕汤等。苏轼并非欧阳昱的同乡,只是被贬谪到了黄州而已,但他却成为黄州最为出名的文化符号。道庄说,“我甚至把自己想象成苏东坡,生活在一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联系自乐于她自己的百姓和国家事务的时代”[23]291,然而,“我只是一个堕落版的苏东坡,因为我连半篇诗赋也写不出来,甚至十分之一篇也不行,不得不满足于将一种语言的知识传授给一个将之视为普通交流工具、只对其商用价值感兴趣的民族”[23]311-312。《东坡纪事》中苏轼作为道庄的镜子,一方面是自喻,前人遭贬谪,今人被“流放”;另一方面,却更是自嘲,苏轼始终活得风流洒脱,千古留名,而道庄却沉沦于世,活不出人生之真味。《东坡纪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关注:道庄为自己过于中国化的名字重新命名为“Zane Dole”,吴聊不仅将澳洲当地人称为Reservoir的湖命名为“东湖”,“事实上,他最近将他周围所有的环境重新用汉语命名”[23]139-140。尽管前者是从中国向外国的转化,后者是从外国转化为中国,但两种重新命名所体现出的地方性认同是一致的。而“命名是赋予空间意义、使其变成地方的方式之一”[1]9。
恋地情结是求定意志的结果,人们对地方采取的是审美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人归于自然的态度;非地方性则是求知意志的产物,人们对地方采取的是认知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是人的自主性。人的求定意志与求知意志对应于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术语即地方(恋地情结)与空间(非地方性)。段义孚认为,空间具有运动性和敞开性的特点,而地方是被封闭和人性化的特殊空间,“与空间相比,地方是既定价值体系的宁静中心点”,由于空间和地方均各有利弊,因此“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生就是庇护与冒险、依附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在敞开性的空间中人可能强烈地意识到地方;在遮蔽之地的孤寂中远方广袤的空间又寻求着令人无法忘怀的在场。一种健康的生命应同时欢迎限制与自由、地方的界限与空间的敞开”[27]。在对湖北籍海外华人文学的探讨中,我们发现,尽管不同的作家对两种基于地理学的人类意志各有所侧重,但要想在严格意义上进行绝对区分也非易事,求定意志与求知意志往往以彼此交相呼应的状态共在于人们内心深处。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考察作为整体的文学创作群体时,还应区分完成状态与未完成状态两种作家。就本论题来讲,聂华苓、程宝林等当属于完成状态的作家,而欧阳昱、吕红、欧阳海燕等应列入未完成状态的作家。对于后者,理应持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加以关注和审视。借用段义孚的术语,他们时刻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广袤的空间”之中,在敞开性的运动之中,随着意义的凝结,新的地方也会因之生成。
[1]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4.
[2]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4]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30.
[5]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
[6] 诺埃尔·卡斯特里.地方:相互依存世界中的联系与界限[M]∥萨拉·L·霍洛韦.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黄润华,孙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1.
[7] 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8] 程宝林.故土苍茫[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17.
[9] 江少川.灵魂独立的自由言说者——程宝林访谈录[J].世界文学评论,2014(1):1-6.
[10] 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程宝林.少年今日初长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12] 程宝林.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159.
[13] 聂华苓.三生影像(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
[14] 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05.
[15] 吕红.美国情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
[16] 欧阳海燕.假如巴黎相信爱情[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1-2.
[17] 聂华苓.千山外,水长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8] 彭邦桢.巴黎意象之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19] Lucy R. Lippard .The Lure of the Local: Senses of Place in a Multicentered Society[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20.
[20]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21] 梁一萍.女性/地图/帝国:聂华苓、绸仔丝、玳咪图文跨界[J].中外文学,1998(5):63-98.
[22] 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78-82.
[23] Ouyang Yu. 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M]. Blackheath: Brandl & Schlesinger, 2002.
[24] 江少川.新移民文学的地理空间诗学初探[J].华中人文论丛,2013(3):6-13.
[25] 庄伟杰. 流动的边缘[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70.
[26] 欧阳昱.愤怒的吴自立[M].墨尔本:原乡出版社,1999:227.
[27]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