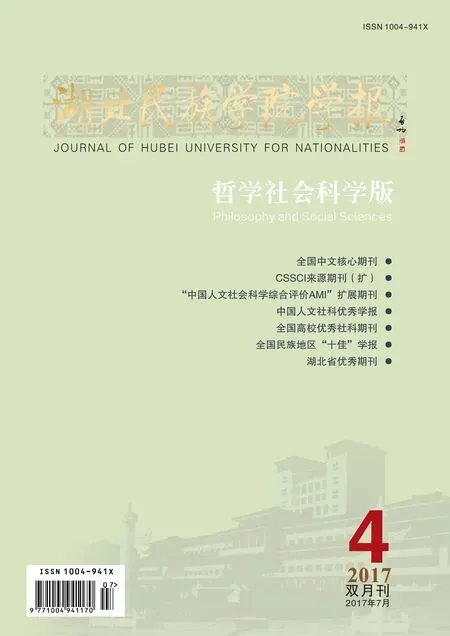流变与坚守:西双版纳傣族饮食文化研究
陈 刚,王 烬
(1.云南财经大学 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221;2.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研究背景与田野概况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为努力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迁:传统生计方式实现转型、经济水平逐步提高、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与之配套的服饰、饮食、建筑、交通及教育观念、婚育观念、风俗习惯等也在发生流变。反过来,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又是民族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标志,同样也是国家方针政策的体现。
张光直先生说:“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1]饮食,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和传承形式之一,受到人类学家的长期关注。饮食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运用文化视角来探讨人类的饮食行为和饮食文化,关于饮食的民族志研究主要围绕“食物的基本功能”、“食物与精神起因的关系”、“不同食物体系的文化特性”、“食物作为特殊的认知体系”等路径展开。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包括饮食的比较研究、食物研究、饮食习俗研究、饮食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饮食文化变迁、饮食文化与其他文化方面的关系等。[2]
就既有文献来看,人类学对饮食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研究,涉及的民族颇多,有壮族(罗树杰,廖国一,黄安辉)、瑶族(廖国一,徐靖彬)、苗族(许桂香)、土家族(王希辉)、黎族(廖玉玲,廖国一)、“客家人”(范增平)等以农耕为主的南方少数民族,也有藏族(贾鹰雷)、维吾尔族(阿达莱提·塔伊尔江)、哈萨克族(沙拉古丽·达吾来提拜)等以游牧为生的北方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王建基,高永辉)。
学者对民族饮食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也是以食物种类、饮食结构、饮食数量与品质、食物处理与加工方式的历史演变为主线,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饮食主体的能动性(如文化交流、族际互动)等角度对饮食文化变迁的内、外原因进行阐释,得出饮食文化的变迁是内、外因共同作用下长期而缓慢的结果。
傣族,我国南方稻作农耕文化的传统实践者,其饮食文化体系就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点。由于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因此学者对傣族饮食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也可按地域分为两类,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的关注点聚则焦于傣族饮食的保健功能(张庆芝,秦莹)、傣族饮食的象征意义(闫莉,莫国香)、傣族的饮食特征(童绍玉,高徽南,景德萍)等等。关于傣族饮食文化的“变”与“不变”,既有研究涉猎较少,且研究框架同其他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研究大同小异。
本文以西双版纳曼养利花腰傣寨为田野点,通过对笔者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的定性分析,从饮食人类学角度对当地傣族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饮食文化方面的“流变与坚守”的个案研究,探讨西双版纳傣族饮食文化演变的原因,希冀从中得出我国少数民族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变迁的普遍规律,并给出自己的拙见。
曼养利,隶属于嘎洒镇曼达村委会,距嘎洒机场几公里,寨门就建在214国道旁。地处北纬21度56分,东经100度43分,海拔540米左右,坝区地形,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2度[3]。据笔者调查,全村共有八十四户,约有四百五十几口人,除了来上门、打工、租住的外地汉族人和部分水傣,全村几乎都是花腰傣。
在城镇发展、多元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曼养利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转变,稻作农耕不再是主要或单一的经济来源,人们靠务工为主,村长告诉笔者,村子约有两百多名年轻人外出学习或打工,剩下的就是中国广大农村的样子“三八六一九九”队伍;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傣家“竹楼”已成“过去”,绝大多数人家都住进傣家别墅;传统服饰也只有老人、妇女及少数儿童在坚持穿戴,但日常的穿衣打扮已与汉族无异……在“流变”的过程中,有多少传统的属于本民族的族群记忆、符号象征、民族文化内涵还继续坚守?民族饮食工艺是否有人愿意承传?衣、食、住、行、用各方面都会在变迁的社会环境里发生流变,进行解构、融合、同化或者重组,而人们相对于味觉的集体记忆却难以被“覆盖”、“淹没”。萨顿在《膳食的印记》一书中谈到,“食物的记忆”是不同于一般记忆的“被沉淀于身体的记忆”,人们可以通过品尝和感受食物这种社会化的具体的身体经验唤起。
二、傣族饮食文化的“流变”分析
饮食文化,指食物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食物消费过程中的科学技术、艺术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传统、习俗、思想、哲学。简言之,饮食文化就是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4]。饮食文化内涵丰富多样,包括与饮食相关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所有内容。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变迁”既是背景,也是事实;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一般说来,器物层面的变化相较于精神文化层面更为明显且易于观察;而难以观察且变化较小的则是对民族精神核心的坚守。就饮食文化变迁而言,饮食人类学大致沿续文化变迁研究的思路,可分为自然变迁和引导变迁两大类。不仅如此,它更反映了“一个民族基本生活的改善和发展的情景”[5]。以饮食文化为例,不仅是傣族,其他少数民族或者汉族在饮食上的变迁也大同小异,“变”主要体现在器具、食材来源或者加工方法等饮食的形式上,而这也是其他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共性”。
(一)饮食器具的变化
饮食器具是食物的物质载体,属于饮食文化的物质文化层面,这不仅包括各种器材,如锅、碗、瓢、盆、灶、菜刀、砧板等配套设施,也涵盖整个饮食的物质系统及空间如厨房、餐厅。一户人家厨房及用餐空间的设置不仅反映家庭经济水平,也是当地人饮食习惯的表达。
傣家厨房大多设在一楼屋檐处的敞亮地带,不似汉族厨房那般“精致”,而显得“简单粗犷”:鲜有砌砖的灶台、专门的盥洗池,甚至很少有烟囱,不像印象中的“封闭式”,而是较为开放。灶台设置较人性化:安装两口锅,一口活动设计,可以随意取放,另一口锅则固定。桌椅是傣家特色的配套的藤编材质,轻巧灵便,但相对汉族的桌椅则较低矮。吃饭主要使用筷子,也会搭配仿银的勺子(用于喝汤)。此外,“手抓”也是一大特色,但现在仅限于吃糯米饭及少数凉菜,这与掺杂商业意义的傣味餐厅的“手抓饭”不同。
在没有电饭煲、电磁炉、电冰箱之前,柴薪是做饭的主要燃料,也兼用煤炭或煤气灶。家电普及时,柴薪的地位下降;加之单一的橡胶树替代了森林的多样性,生态环境逐渐变化,导致柴薪来源减少。此外,柴灶也是为烤酒的需要或停电时使用。虽说传统的杆栏式民居和现在的砖混房屋都设有“杂物堆放处”,但现在傣家房的空间格局改变,一楼已很少堆放柴火、农具,而是变成“私家车库”甚至“会客区”。
(二)主食尤其是早点的变化
作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百越族群中稻作文化的代表,傣族稻作文化的内涵不仅体现在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上,更深植于原始宗教活动、小乘佛教活动及生态文化观念中。[6]
受傣味餐厅菜单的影响,人们先入为主的将傣家主食与“菠萝饭”“竹筒饭”“手抓饭”联系在一起,而隐藏在背后的则是“糯米饭”。糯米饭的制作方法并不困难:头一天晚上将糯米用水泡着,第二天早上直接蒸熟。吃时用手将糯米捏成团,蘸着“喃咪”即可。
在笔者调查的受访者连续三天的早点中,52人中有10人的早点是糯米饭,10人中以老年女性居多。除了少数人“没吃”早点,其余人都吃的米干、米线或面条。根据个人喜好,可在家煮早点,也可去早店铺吃米干、米线。曼养利原有两家早点铺,其中一家因卖米线利润太薄而放弃经营。店里的猪肉米线卖3元,牛肉米线5元,刨去米线、包菜、鱼腥草、盐巴、味精、葱花、酸菜、辣椒油等食材及作料成本,盈利较小。
以前,糯米饭既是每餐的主食,又是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供品,还是上新房、结婚时不可或缺的食物,现在则沦为三餐中的早点,或个别老人坚持的“嗜好”:“因为糯米饭吃着方便,而且容易饱”。为何糯米饭从三餐主食的地位下降到早点一餐?受社会政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嘎洒附近的傣族其生计主要是依靠种植橡胶、香蕉等经济作物,同时兼顾打工,传统的稻作农耕不再是最主要的经济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补充。
从笔者个人在云南的调研和生活经历来看,人们的早点几乎以米线、米干(卷粉)、饵丝及面条为主,很少以米饭为早点。城市化加剧了人口的流动,受“主流早点”的影响,西双版纳的糯米饭早点传统也逐渐式微。另外,笔者走访的好几个村寨,每个村子都有早点铺,且生意红火。可见,人们吃早点的习惯已开始发生变化,早点正从自家的厨房走出,转向专门的店铺。
(三)食材来源不再“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谚反映了饮食文化与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环境决定论者,还是可能论者抑或环境适应者都达成了共识:即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7]。“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话已不再十分契合现在的傣族聚居区。由于地处亚热带地区,本来动植物资源丰富,而在广泛种植橡胶以后,生态环境发生微妙的改变,单一物种替代了生物的多样性。橡胶种植需要广泛借助草甘膦除草,同时外地租户在种植作物时也经常使用农药,不管是对土壤、水源还是物种多样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潜藏着风险。
村中老人告诉笔者,“小时候吃野菜的机会比现在多,虽然吃肉的机会少,一周能不能吃一次也不清楚,但是吃“野味”的机会多。现在种橡胶要打农药,种菜什么的也要打农药,所以很少捡野菜吃。自己现在没有地种菜,没有地方养猪、养鸡、养牛、养鱼,菜啊肉啊,好多都在市场买,在市场上买的就算是不安全,可还是要吃啊。水果啊,房前屋后也有,但并不是刻意种的,只是在街上买水果吃的更多了。”
在笔者走访的几个傣族村寨中,发现一个共性:每个村子几乎都有一个大型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同时中心也兼具开放市场。每到早上,就会有人卖食物、服装及日常生活用品,品种齐全。食材有生食,也有熟食;有自家种的,也有大棚种的。一般说来,若时令蔬菜虫眼较多,则是村民自种的,反之不应季、品种超多、没虫眼则是大棚种的。较大的村子不仅卖蔬菜、肉类,也卖米、油、饮品、烧烤以及生鲜杂货等。曼养利的老人上午会去田间地头摘些蔬菜,下午拿到村口卖,赚些零花钱。
受生态环境及社会政策的影响,人们吃“野味”的机会变少。由于适逢雨季,版纳的野生菌类(主要是牛肝菌)出产较多。由于售价较高(一市斤牛肝菌可以卖三、四十元),一些打工者会到处捡菌子,因为这比打一天零工划算。傣家人民喜爱炒食牛肝菌,也爱煮汤。后者较讲究:先将酸角叶放入锅中熬煮,放入洗净的牛肝菌,加入少量香茅草、荆芥、盐巴等佐料。关键是放入大蒜检验菌子有无“毒”性,若蒜颜色变黑则菌子有毒,反之则无毒,主人家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方法。煮的牛肝菌汤,汤鲜而味酸,口感极佳。
苦笋、蕨菜、青蛙、酸蚂蚁以及澜沧江里的青苔等动植物也是雨季的珍馐。苦笋和蕨菜的吃法相似,都是蘸着喃咪吃,只是喃咪不同。苦笋一般是煮熟后蘸着“螃蟹喃咪”“番茄喃咪”吃,蕨菜则用水焯过后蘸着“花生喃咪”吃。油炸青苔(又称“青苔松”),一道产自澜沧江的“野味”,只在五、六月份才有,一年只有一次打捞的机会。将打捞晒干的青苔经油炸后,放入少许盐巴即可食用,口感和“海苔”类似。
青蛙一般拿来煮汤:将去掉内脏后的青蛙剁碎,加入小米菜、盐巴混煮,最后将先前一起煮的成捆的香茅草捞出即可。李德宽、田广主编的《饮食人类学》一书详细记载了酸蚂蚁的吃法,作为一道“补充和完善主食营养成分”的副食,酸蚂蚁称得上傣族特色。酸蚂蚁生长在热带丛林,身体细长呈黄色,因其腹部有透明的储酸小黄球且成蚁味酸而得名,具有开胃、治腹泻的功效。可生食也可熟食,熟食是将蚂蚁和鸭蛋翻炒,加入油、盐巴、傣蒜、葱花,其“酸”可谓名副其实。
(四)流动的外来小吃摊
曼养利有许多流动的外来小吃摊,“流动”是因为这些小吃摊都是凭借摩托车或三轮车而“走村串寨”,最后到达本地人嘴里。有叫卖“北方烧饼”的湖南大哥,卖一块五一个的豆沙、南瓜、白糖及肉馅儿的烧饼;也有每天吆喝着卖馒头、豆浆的大姐;有远道勐海而来卖水果的傣家大姐;也有四川老乡,卖各种荤素串串、炒田螺、卤鸡脚、卤鸡腿,价格亲民,但由于口味原因销量并不乐观;还有骑三轮卖烧烤的贵州大哥,现烤现卖的小吃成了小孩的最爱。
除了本村、本地州、外省的零售小贩,在曼养利也可以看到国外进口的商品。一次笔者在村口转悠,见有户人家正把大袋的东西从车上搬下,一次就是好几百斤。走近一问原来是进口的缅甸大米,两块九一公斤,一袋约八十斤。买主说这些进口米主要拿来酿酒,少部分拿来吃,因为自家种大米的田地不够,所以买米吃。酿酒不单是傣家的传统工艺,也是村民的经济来源之一,曼养利八十多户人家约有三十来户在酿酒。酿的酒约有五十几度,十块多一市斤,刨去一斤谷子一块多的成本,加上酿造工艺、等待的时间成本,赚不了太多钱。除了缅甸大米,也有流动商贩在卖泰国的日化用品,如洗洁精、洗衣粉等,如此小的寨子竟也有“全球化”的苗头。
由此可见,除了饮食器具、食材来源、饮食结构上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尤其是人口的流动给傣族饮食文化创造了和其他饮食接触、“碰撞”的机会。受地产开发、交通因素、旅游政策等经济社会原因的影响,村寨人口结构变复杂,有常年租住的四川、江西两省的小卖铺老板,有流动的各地商贩,也有短期租住来自川渝一带的打工队伍,傣族在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文化交流与互动时,其饮食观念、烹饪技术难免会不受影响,虽然文化采借的例子不多,但也偶有发生,只是过程缓慢而持久。
笔者曾询问过川渝老乡对傣族饮食的看法,受饮食习惯的影响,务工者多数自己开火做饭或吃工地食堂,故与“傣味”结缘不深。一位重庆大哥告诉笔者,“除了早点吃的米干、米线和老家的米粉、面条差别不大,其他傣味自己也没怎么吃过。总体印象不是太好,比如手抓饭啊”。还有一位“有意思”的重庆大姐,她的印象是:“傣族人硬是啥都吃,尤其爱吃虫子,比如这个季节的‘涨水蛾’,除了油炸,还有洗干净了扯掉翅膀直接蘸酱吃,哎呀,恶心得很。还有些野菜,在老家分明是拿来喂猪的,这里的人啥子草草都吃。反正我是没咋吃这边的东西,一个酸辣,一个麻辣,虽然都‘辣’,但就是不习惯。”
从受访者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带有某种“偏见”或者说“刻板印象”在评价傣家饮食,诚如笔者给朋友介绍“手抓饭”时,那位朋友“本能”地认为怎么现在还这样吃饭?可见,人们在评价某种陌生食物时,在看法上有失偏颇。然而,从侧面也反映出味觉上的记忆带给个体实践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
三、傣族饮食文化的“坚守”分析
怎样判定一种食物是这一族群的特色而不属于那一族群?当我们在谈论“川菜”“粤菜”“淮扬菜”以及“傣味”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指它们的味道、颜色、营养搭配、烹饪技术不同于其他菜系?还是指某种饮食背后与某一特定族群相关的生存智慧、饮食风俗及精神内涵?这就关乎饮食与族群边界、族群认同的关系。器具可以更新,技术可以改进,来源渠道可以拓宽,可在“尝新”之后仍要坚持本民族的味道,因为它更符合自己土生土长的肠胃,因为它是本民族文化的符号表征,因为其背后蕴含着本民族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一)配菜“无喃咪不欢”
许多受访者认为傣族最有特色的是各种各样的“喃咪”。“喃”是傣话,意为水、汁;“咪”意思是舂拌或者调制。文山苗族吃饭时也离不开“蘸水”,但做法相比傣族又简单太多:直接将盐巴、味精、干辣椒面、生姜、大蒜、葱花放在容器里即可,再加入汤汁沾着吃。苗族的蘸水吃法较单一,而傣族的“喃咪”更为复杂和讲究。在《新编西双版纳风物志》一书中,编者也在“风味特产”篇指出了有名的“傣味酱菜”及其具体做法[8]。喃咪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菜酱”,一种是“肉酱”。
最常见也普遍适用的菜酱是“番茄喃咪”。番茄,也称“酸汤果”。将退皮的番茄与姜、蒜、小米辣、盐巴、味精、芫荽、葱花或“瓠果”(音译,内核有类似茄子籽的圆形小果子)一起放入舂对中捣碎、拌匀即可。退皮的方式有两种,可以在炭火上烤熟后退皮,也可把番茄装在塑料袋里煮熟后退皮。此种喃咪味酸而且辣,色泽红艳,可以佐竹笋,也可以佐油炸猪皮、油炸牛皮。其他菜酱有 “酸菜喃咪”“花生喃咪”。酸菜是用青菜为原料腌制的水酸菜,切碎捣烂后加入作料;花生喃咪则是将热锅翻炒、炮制后冷却的花生退皮,再用榨汁机打碎,加入适量的作料搅匀而成。这两种菜酱的“搭档”大多为水煮的时令鲜蔬,如扁豆、蕨菜等,口感清淡,老少皆宜。
肉酱有“螃蟹喃咪”“鱼仔喃咪”。以前的螃蟹喃咪颇具傣族特色,“将螃蟹烧熟后除去硬壳和内腹,捣碎后烘烤或晒干成一个个小饼。吃的时候用棒槌敲碎,将葱、姜、蒜、辣椒等与其混合,捣碎如泥,即可食用,也可以将它当作作料拌饭吃”[9]。现在的做法则简便、省时,直接用瓶装的螃蟹酱加入其它作料就好。螃蟹喃咪可以佐苦笋、糯米饭,但苦笋太苦,蟹酱太腥,一般人可能会吃不惯。“鱼仔喃咪”适合下饭,做法是:先将小鱼仔在炭火上烤熟,掏去内脏后捣碎,加入芫荽、苤菜末、苦菜荬末、荆芥末等作料舂碎,可以佐萝卜、莲花白等生食蔬菜。为了节省时间、方便食用,也可以将此喃咪罐装,随吃随取。
(二)从“客宴”及“赶摆”看傣味特色
“客宴”,一般来说最能反映出当地的饮食特色及宾朋礼俗。人类学最早对宴席的研究,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夸富宴”的研究,且直到今天仍是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夸富宴不仅是一种炫富的形式,也是“一种权力性的仪式场景,通过饮食媒介获得各种相应的转换价值”[10]。社会学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 更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里的宴席不仅仅是一场大型的饮食活动,更涉及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饮食与面子的关系,在社会性上却延伸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到傣家做客的经历,给了笔者很好的观察、问询和品尝机会与体验。
“赶摆”,类似一种大型的赶集活动,和四川的“赶场”不同,傣族“赶摆”的时间、地点都是不固定的(有点轮流的意味),有些类似都江堰的“春台会”,也形似庙会。届时,来自各地州及外省的流动商贩们聚集在一起,选择一处宽敞、开阔、人口集中的地方(如有影响的寺庙(奘房)),进行商贸、祭祀、集会、娱乐等。
此次“赶摆”的地点设在橄榄坝傣族园附近的一个寺庙旁,时间为5月25日、26日两天,笔者虽是第二天去,但热闹依旧。“赶摆”时,无论男女老少都着民族盛装,女子淡妆浓抹,男子英姿飒爽。“摆”上,最多且最显眼的是各种小吃;其次卖数码产品、玩具、傣装布匹、泰国日化品等商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因为形似“庙会”,便有祭祀活动。寺庙正前方的广场上是隆重的“高升”表演,场地的左侧堆放着不计其数的各式大小的“高升”,近处及右侧摆有几十桌的宴席,中间的开阔处供傣家女子表演祭祀舞蹈,远处则是燃放高升的架台。表演及围观群众之多,场面蔚为壮观。
从笔者参加的客宴和“赶摆”来看,根据食材处理方式的不同,西双版纳傣族饮食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烧烤及包烧类。较为典型的是烤五花肉、烤牛干巴、烤罗非鱼等。傣家人民烤五花肉,是将肉切好后放入各种调料稍加腌制,之后直接将夹有食材的烧烤夹放在木材上用慢火烤即可。罗非鱼的烤法有两种,一般烤整条,可以用作料包烧着直接烤,也可以只放少量盐烤熟后蘸柠檬辣椒酱吃。“摆”上小吃最多的是烤鱼、烤鸡、烤青蛙、烤小鸟、烤黄鳝等,由于天气太热,不宜烤太多,商贩有时“因需制宜”。除了肉类,各种小菜同样可以烧烤,如今的傣味烧烤已成特色,广见于各地的小吃街上。除了烧烤,包烧也是“傣味”特色,这种特色不是指烹饪方式,而是暗含了傣族“地方性知识”的饮食味道,一般用芭蕉叶包裹鱼类或金针菇等菜类,将各种作料放齐后置于火上烤熟。
第二,凉拌类。傣族的凉拌菜以凉拌鸡最为常见,这也是宴席上的“常客”。其做法简单,无非将鸡肉煮熟后切块凉拌,只是作料稍微复杂些。既是“傣味”,就要突出“傣家”特色,一点青柠檬便足够。其次是五颜六色的“傣味泡菜”,有荤有素,荤菜有凉拌鸡脚、凉拌炸猪,素菜食材广泛,海白菜、木耳、黄瓜、香菇、海带、黄花、藕片、土豆、胡萝卜等,也可以凉拌水果,如凉拌青芒果、菠萝、李子、青木瓜等。同样地,傣味凉拌菜最重要的就是柠檬、傣蒜、小米辣等特色作料。
第三,腌酸类。一次笔者入户访谈时遇雨,便在村民家避雨,看见一位刚上门的新姑爷在烤牛皮,打听后得知牛皮是办喜酒时花一万多块钱买的黄牛剩下的,烤牛皮是为了做酸。先把牛皮烤至焦黄,洗干净后煮烂,之后切好、晾干、密封装坛腌酸,放入作料,可以直接吃,也可拿来煮汤。笔者尝过当地的“嘎芋牛皮”,嘎芋杆被煮成沫状,细腻且清香,牛皮白而净,劲道有味,味道巴适得很。还有生肉腌酸,将猪肉或牛肉洗干净后剁碎,或将鱼肉切块或用一整条划开口的鱼,放入盐巴、姜蒜等佐料,在五、六月三十度左右的气温下腌酸四、五天,吃的时候加入葱花、芫荽就完美了。
第四,油炸类。除了 “炸青苔”,傣族也爱吃炸猪皮、炸牛皮。笔者“赶摆”时亲眼见到老板现炸现卖牛皮:将洗干净的生牛皮煮熟后切条晒干,放入油锅里炸至牛皮发泡、变黄即可,猪皮也是同样的做法。吃的时候可切成小段直接吃,香脆而保留原味,也可蘸着酸辣的番茄喃咪,味道更显独特。此外,还有家常的炸鸡蛋或者炸虫蛹,这些都是高蛋白、有营养的副食。
第五,剁生。傣家生食不止腌生肉酸,还有更为“血腥”和刺激的“剁生”。剁生取材较广,可以是常见的鲜猪肉、牛肉、鱼肉,也可以是马鹿肉,不过要求纯精瘦肉。先用铁锤将肉捣烂,再加入各种细碎的作料,反复搅和成泥浆状,可蘸着鲜生蔬菜或者糯米饭吃[11]。不过,吃剁生的人男性较多,从受访者的回答来看,女性因为害怕剁生有寄生虫而不敢吃,而男子吃完后都会喝傣家自酿的烈酒,烈酒可以杀菌、杀虫,故剁生颇受男性喜爱。
除了特色“傣味”,家常傣味中少不了的烹饪方法就是“煮”。除了早点,几乎每顿都会有一个汤菜。常见的汤菜其食材是时令鲜蔬,如小白菜、小青菜、洋瓜尖、南瓜尖,或者山野的水芹菜、苦莲菜、竹笋及其它野菜。上文提到的青蛙小米菜汤、牛肝菌汤等都是傣家特色。因为煮汤时会加入香茅草、薄荷、荆芥、藿香、傣蒜、酸角叶、小米辣等地道作料,因此味道香、鲜而酸辣。
(三)味道喜食“香、酸、辣”
某一族群对味道的偏好总是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关,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资料、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人的生理需求,且具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因此也形成了特征明显的饮食文化区,比如西南饮食文化区偏好麻、辣,长江下游饮食文化区则喜食清淡,东南饮食文化区则偏甜等[12]。陈学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指出,“人的肠胃基因记忆是指相对稳定的饮食习惯经过世代繁衍传承,在体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隐形饮食遗传基因。现代医学实验证明,此种基因一旦在人的记忆成熟期被激活显现,形成胃肠基因记忆,就产生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本性”。[13]
传统傣味以“酸辣”著称,同时也偏好“苦”。这是因为傣族聚居地区天气炎热,湿度大,所以暑热、皮肤病、风湿病常见,而傣家作料如香料草、香茅草、荆芥、芫荽、薄荷、酸角、小米辣、鱼腥草、酸汤果等又具有祛风除湿、发散解表的功能。且常吃油炸、烧烤类食物容易上火,而作料有调和的作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饮食搭配,如雨季宜吃苦味菜,比如苦笋、刺五加、苦莲菜等,这样可以起到清热、解毒、凉血、消暑的作用。
(四)日常饮食伦理与禁忌
彭兆荣指出,“当人类与食物建立了生态关系后,便会衍生出人类与食物之间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即人类通过与食物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秩序性的政治伦理[14]。”这伦理既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涉及人情世故。笔者在与当地村民推杯换盏的往来互动中,了解了些许傣族饮食文化的礼仪与禁忌“常识”。
饭菜做好后,若家中有老人尚未回家,不能擅自动筷子,否则被视为“不敬”,从中可看出傣家尊老敬长的优良传统。傣家人好客,喜欢饮酒,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在一起喝酒时,一开始都要端杯在桌沿洒几滴、用手指弹几下,并念一段傣话,说是敬畏自然、感谢神灵、祖宗给了大家风调雨顺、衣食无忧、来之不易的生活。之后才一起碰杯,用傣话喊两声“水,水”或者六声“水、水、水、水、水、水”,一是为了带动喝酒的气氛,再是表达傣家人民的豪爽与热情。在赶摆当天,笔者随主人家去做客,因为是干亲家,去的时候不宜空手,故主人带着自家酿的米酒和买的贵重茶叶去,礼尚往来,这既是傣家的宾客礼仪,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饮食禁忌是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指某一群体或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自觉规避某种特定食物的传统,极具民族性和历史性[15]。通过对刚生产完小孩的傣家姑娘的访谈,了解了傣家孕妇的饮食禁忌:怀孕期间要忌辛辣,在坐月子甚至当孩子五、六个月时最好都只吃盐巴、鸡肉、猪肉,其他类似味精、姜、蒜、芫荽等佐料不能沾,这与汉族坐月子女性的饮食禁忌大同小异。怀孕期间尤其不能吃芭蕉花,说是吃了会流产。根据笔者查询的资料,孕妇可以吃但要少吃芭蕉花,因为芭蕉花虽然味甘淡、微辛,却是凉性食物,孕妇宜吃性温和的食物。至于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依然有待考证。正是因为饮食禁忌能通过潜在危险可能带来的恐惧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才使它具有维持自然界和人类关系的功能。
“中国的饮食文化与任何其他文化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通过对食物的品尝过程贯彻一种社会伦理。”[16]正是这种“身体伦理”在制约、规范人们的行为及社会生活,在关怀该饮食体系下的每一个个体。
四、结论
每一个民族的饮食及其配套的文化体系都是该民族历史演化的结果,反映着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也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和符号标志。我国少数民族在食物来源、膳食结构、食材烹饪、食疗作用及饮食审美、饮食伦理等方面,都极具地域性、草根性,而显得更“接地气”,更符合生态和环保理念。[17]
改变,是大势所趋;坚守,是发展之道。西双版纳傣族饮食文化的“流变与坚守”是傣族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结果,并随时间制度而呈现出多元态势。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既是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又是由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封闭向开放的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不仅如此,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及价值体系都会发生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会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更为深刻的是文化形态的变迁。
由于较长时间范围内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特点的经济社会转型成为饮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傣族社会传统稻作农耕的生产方式难以适应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傣家人民转变原来单一农耕的生产方式而从事打工、务农、经商等多元工作。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给人们多样的食物及其配套体系的选择,从而在物质层面改变了当地人的“食生活”,有助于改善傣家人的生活质量。
社会转型加剧了人口、信息、资本、技术等的流动,频繁的社会流动同样给傣族饮食文化带来挑战。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口味与饮食习惯,也有各自独特鲜明的“饮食边界”,当差别各异的人们跨越边界、往来互动而进行饮食文化的交流、“交锋”时,外来饮食如何适应傣家人的肠胃、走出傣寨的“傣味”如何适应外地人的口味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旅游业发达的西双版纳,纯正而特色浓厚的傣族小吃、傣味农家乐、傣味餐厅对游客而言,具有极高的吸引力。因此,将民族饮食与旅游活动相结合,定能促进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实现当地旅游的可持续。[18-19]
食物,既是识别某一民族的因素,也是成为某种认同的依据,人们对某种特色饮食的坚守,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某种所属文化的忠诚。因此,民族饮食文化的适应与转型,不仅需要双方破除饮食上的“偏见”,更需坚守本民族传统饮食的文化内涵与意蕴,即饮食文化的精神层面,守住民族特色、留住舌尖的味道、恪守饮食伦理、传承民族饮食工艺、铭记族群记忆,不忘初心,方能发展。
[1] 张光直.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M]∥中国食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 李德宽,田广.饮食人类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
[3] 曼养利村[EB/OL]. 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8165759-8482747.html
[4] 赵荣光,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5] 陈运飘,孙箫韵.中国饮食人类学初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6] 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的传统实践与持续发展[J].民族研究,1997(6).
[7] 王希辉.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8] 征鹏,杨胜能.新编西双版纳风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9] 曹成章.傣族村社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0] 彭兆荣.饮食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 张景明.饮食人类学的实践与文化多样性理论对食学研究的支撑[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28(1).
[12] 陈学智.饮食文化变迁与文化堕距[J].黑龙江科学,2010,1(5).
[13] 彭兆荣,肖坤冰.饮食文类学研究述评[J].世界民族,2011(3).
[14] 刘琼,谢一琼.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土家族饮食习俗与民族旅游经济——以鄂西南咸丰县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15] 韩敏.鄂西土家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探析——特色饮食文化[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