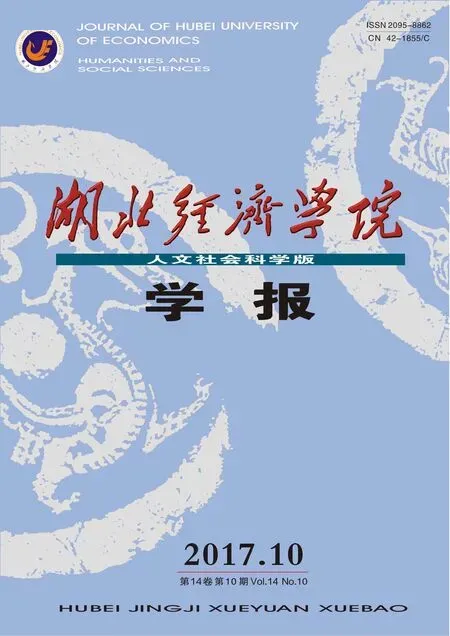《海上花列传》细节描写的现代性辨析
肖 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海上花列传》细节描写的现代性辨析
肖 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小说《海上花列传》的文本的大量的细节描写,是19世纪末年上海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生动记录,小说对当时上海时兴的西洋器具与新鲜的生活方式有详细的描写,但是对于中国传统娱乐活动的刻画也占据了不少篇幅。在新旧交杂的上海,西洋物质与传统习惯交织呈现,时人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着转型,其日常生活方式、心理模式与审美表现等等都受到冲击,但他们的思想与认识并未跟上物质更新的节奏。
《海上花列传》;细节描写;现代性
王德威曾评价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一书“对上海欢场与情场的白描,真切犀利”[1],“以朴素之笔写繁华之事,白描功夫要令五四写实主义大家们相形见绌”[2]。该小说充斥着大量的细节描写,详尽地记录了19世纪末期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百态。小说以花也怜侬的梦境开端,梦醒时他正处“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3],“华洋交界”意味着现代与古典的杂糅、新与旧的交织,在此种空间背景之下,人们的生存体验也处在混乱之中。体验,是指“人们在世界上的具体生存方式及其价值问题”[4],不仅包括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与物质需要,还有思想层面的价值思考。小说描写的对象——世纪末年的人们,一方面追逐着新奇的西洋玩意,随着潮流装点出“新”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留恋于听戏、麻将等传统的游戏,其思想观念在追新念旧的日常生活中显得矛盾重重。
一、“现代”器物的接受与崇拜心理
《海上花列传》中有许多细致的环境描写,由具体人物的室内布置到整个上海的街市景观都面面俱到,作者韩邦庆通过点与面的衔接建构了一副广阔的城市景观图,并“预言上海行将崛起的都会风貌”[5]。生活其间的人们接受并享用着洋灯、眼镜、汽车等外来的西洋器物,体验着“新文明”,洋器的方便性与新鲜感使时人产生出一种极度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不仅是希望“一概拿来”的羡慕情结,也包含了对于神秘未知器具的不安情绪。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器物的部分变化与原有旧物的继续保留,东西、新旧两种不同维度的物质形态共存于同一空间,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就必定体验着东西杂糅、新旧对立的混乱。
第一个出场妓女陆秀宝房间的摆设具有代表性,可以代表小说中大部分女性人物的居住场景:“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画绢灯”[6],既有“着衣镜”、“自鸣钟”这样的西方现代器具,也有“泥金笺对”、“彩画绢灯”这样的中国传统装饰品。空间布置的中西混杂可以看出时人文化心理的混乱,他们在接受、使用现代物质的同时,仍无法舍弃传统物件。在文化价值层面,古代中国人一向存有重道轻器的心理,“泥金笺对”和“彩画绢灯”二者作为生活实用品的意义远不如附加在其物质形态上的“笺对”(文字)、“彩画”(图画)所蕴含的审美、道德意义深远;而“着衣镜”和“自鸣钟”则偏向于实用性,陆秀宝的着装打扮离不开“着衣镜”,宴席聚会离不开“自鸣钟”,实用器物已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重道轻器的观念看似有所变化,但是器和道的地位尚不能对等,器与道的互动性尚未生成。因此,房间的主人陆秀宝的出场就伴随着“一路咭咭咯咯小脚声音”,她本质上是一个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裹脚女性,之所以接受、习惯这些西洋器物,只是为了生活上的某些方便(便于梳妆打扮和看时间),并非真正想要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镜面的反射原理和进化的时间观)。在现代与古典相交杂的时代间隙中,即使人们对具有“现代性”的西洋物质采取接受、认可的态度,但在认知层面上,他们依旧没有关于器与道的互动价值的体认,他们的思维体验依旧保持着古典性。
当小说中的个体生活空间向公共空间延展时,上海街景的铺设显示出这已经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城市。小说第六回中所描写的亨达利洋行就是当时上海众多消费场所的一个缩影:“仲英与雪香、小妹姐踅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顽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7],这段细节描写从小说中人物的视听感受出发,以仲英、雪香和小妹姐三人的感官来展示一个充满西洋器物的世界。他们的直观感受是“陆离光怪”、“目眩神惊”,极大数量的洋器集中呈现使他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神秘世界,他们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习惯于已被接纳的时钟、镜子等少数物品,也没有产生现代人那种对五光十色的都市世界习以为常的体验,而是被强烈的视觉冲击激起内心的惊讶与羡慕。惊羡之余,还要“看了这样,再看那样”,这表明他们三人实际上被洋行中陈设的新鲜器物所吸引,怀着崇拜之心“大略一览”,惊羡体验与崇拜心理蕴含着新的现代性体验,但是待到他们挑完礼物回到自己的世界中时,这种体验也就变成一次值得称道的经历而慢慢消散了。小说第二十九回,通过赵朴斋的听觉简短地刻画了上海的街道情景:“听得宝善街上东洋车声如潮涌,络绎聒耳,远远地又有铮铮琵琶之声,仿佛唱的京调,是清倌人口角,但不知为谁家”[8],汽车声混杂着传统小调,现代物质与古典消遣在上海街头同时并存。体验者赵朴斋内心的纠结并非是对现代文明的留恋,而是舍不得上海那纸醉金迷的生活状态,方便快捷的“东洋车”(现代物质)在小说人物心中不过是日常游玩寻乐(古典趣味)的陪衬品,所以赵朴斋才能在如此嘈杂的街道背景中明确地辨认出那遥远的琵琶声是何种曲调,甚至是哪里人所唱。普通百姓生活的细微之处随着西洋器物的侵入发生了些许改变,对现代物质的欣羡与崇拜并没有太大地影响其审美趣味、思维认识,在文化价值层面上还是被古典性生存体验所主导。
二、“现代”生活方式入侵与恐惧心态
随着西洋器物的引进与流行,洋人的一些生活方式也随之影响了时人的生活。除了家家必备的时钟、镜子和自来火等物,以及出行工具洋车之外,《海上花列传》中还有几处细节描写展示了19世纪末年上海市民别的生活细节,如消费方式、私人保险和新型职业。有些新的生活方式的给人带来便利,也有部分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从受众面来看,这些新鲜的生活形态往往局限在少数有钱人的范围内,并未广泛普及,由此产生“现代性”体验并无代表性。
小说第十一回中出现了“保险局”、“保险行”这一颇具现代意味的保险机制,在发生火灾之后,莲生、小云的第一反应都是“拿保险单自家带来哚身边”[9],这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保险意识。不过,小说中仅此一次提及保险,不能确定当时的保险制度具体情况如何,但即使只限定在小范围的有钱人中,“保险”的出现也已经可以表明当时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入侵程度。而小说第六回则描写了新的消费方式,仲英三人在亨达利洋行购物结束时,“仲英乃一古脑儿论定价值,先付庄票一纸,再写个字条,叫洋行内把所买物件送至后马路德大汇划庄,即去收清所该价值。处分已毕,然后一淘出门,离了洋行”[10]。仲英的付款方式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所谓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类似于如今的货到付款,并且使用“庄票”而非现银达成交易。这种消费方式已经初步具有现代商品社会的特征,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当时能承担得起这种支付方式的只有亨达利洋行这一家商铺,能采取这种方式购物的也只是极少数的富裕人群,难以普及。况且从小说的时间背景来看,洋行往往只是一个兜售“西洋玩意儿”的空间实在,对于时人的意义不过是一个购置新鲜礼物的地方,而在其余大部分时间里,洋行这一空间实在并不会出现在时人的意识层面,新的消费方式也就更谈不上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什么影响。
与现代生活方式同时到来的是外国人,或者可以说是来到上海的外国人以其自身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上海市民既往的生活方式。其中,外国人的留居产生了新型职业类型,小说中两次出现了“外国巡捕”这一职业人群,第一次是第十一回中灭火时,第二次则是在第二十八回中进行捉赌行动。其中对灭火过程的描写更为细致:“只见转湾角上有个外国巡捕,带领多人整理皮带,通长衔接做一条,横放在地上,开了自来水管,将皮带一端套上龙头,并没有一些水声,却不知不觉皮带早涨胖起来,绷得紧紧的。……那火看去还离着好些,但耳朵边已拉拉杂杂爆得怪响,倒象放几千万炮?一般,头上火星乱打下来”[11],外国巡捕使用“皮带”灭火的过程与现在的消防灭火基本别无二致,但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常见场景在王莲生的眼里却显得十分有趣,从“整理皮带”到灭火完毕,他仔细观察了外国巡捕的每个细微动作,连皮带的涨胖也感到有些稀奇。这种惊奇感意味着有些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时还没有成为常态,与时人的生活体验存在脱节的情况,而且王莲生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所关注的并不是这种现代灭火方式的快捷性,而是作为一种观赏趣味来玩味。在进行捉赌行动时,“一个巡捕飞身一跳,追过阳台,轮起手中短棍乘势击下,正中那人脚踝。那人站不稳,倒栽葱一交从墙头跌出外面,连两张瓦豁琅琅卸落到地”[12],这一场面引起众人的恐慌。这种恐惧心理更多是由于在一追一逃两个人之间,追者占据明显优势,而逃者略为凄惨,加上逃者是自己的同胞,追者却是外国人,内心的天平自然就倾向逃者,而觉得外国巡捕十分可怕。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目睹一个外国巡捕追击一个中国人的情景,并未意识到“捉赌”行为的正确性,单从种族角度来判断曲直正反映出时人的认知短浅。如果说对待外国巡捕这一属于“官”类职务的人心存恐惧感尚属小市民的正常心理,那么对普通的外国人依旧持惧怕的态度则表明时人对外来的现代事物仍旧存在抵触情绪,赵朴斋在等候吴松桥时,光是听着门外的步履声就吓得心惊胆战,“这门外常有外国人出进往来,履声橐橐,吓得朴斋在内屏息危坐,捏着一把汗”[13];李淑芳白天见过外国人之后,夜晚却做了与之有关的噩梦,吓得半晌才说出“两个外国人要拉我去呀”[14]。对外国人的惧怕感既不符合古典性体验中的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也不是现代性体验中应有的“人类普遍性与民族特异性双重特性”[15]的并存,将外国人过分妖魔化体现出正处于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时间夹缝中的时人心理。中国的现代性体验“是古典性体验在现代全球性境遇中发生急剧断裂的产物”[16],大量西洋事物与人物突然涌进打破了古典性体验的平衡状态,人们一方面崇拜现代西洋器物,学习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惧怕和排斥其引进者——外国人,认同前者而否定后者,陷入体验的认同危机。
三、传统生活形态的发展与古典性体验
比起对西洋器物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细节描写,小说中更大的篇幅都用来描绘主人公们看戏和打麻将这些传统的娱乐活动,篇幅的分配也是时人日常生活时间的分配,小说中对传统娱乐的大段描写或许可以说明现实生活里人们的多数时间也都消遣在戏台与牌桌上,而上文提及的在洋行购物、买保险和看灭火等颇具现代特色的活动只是偶然所为,作为千篇一律的传统娱乐手段的补充罢了。至于作者韩邦庆对传统生活形态的细节描写,所用笔法也与描绘现代事物时有所不同,其语言更具有古典小说的气质。
对戏台和看戏场景的细节描写在小说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篇幅,小型唱台如在张蕙贞寓所搭建的:“一座小小唱台,金碧丹青,五光十色”[17];稍微大型一点的有如:“在亭子间里搭起一座小小戏台,檐前挂两行珠灯,台上屏帷帘幕俱系洒绣的纱罗绸缎,五光十色,不可殚述”[18];最为隆重的一次看戏活动则在第九回:“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象叫出江南春意。又遇着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礼拜日,有踏青的,有拾翠的,有修禊的,有寻芳的,车辚辚,马萧萧,接连来了三四十把,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19]。以上这些看戏的情境虽然规模不同,但都极富奢华之态,设宴者竭尽所能装点出最豪华的戏台,以丰富的色彩和绚丽的珠宝烘托热闹十足的场面,而身处其间的人们则轻松、自在地交谈畅饮,并不像之前身处现代化的亨达利洋行时那样拘谨,他们还是更习惯于戏台这样的传统娱乐场所,人与环境和谐相融,这种古典性体验才是时人最适宜的。另外,从笔法上看,作者在勾勒戏台场景时,经常使用两个或以上的四字句与多字句结合,以整齐而又错落的语言节奏与设戏台宴宾客的欢乐场景相配合;不同于用大量市民口语对现代场景的纯白描,对戏台场景的刻画往往堆砌蕴含丰富的书面语汇,如 “钗冠招展,履舄纵横”;还直接化用“车辚辚,马萧萧”这样的古典诗句,塑造出的宴会场景与古时富贵人家的宴会别无二致,置身其中所感受到的完全是古典性的生活体验,偶尔接触的那点现代事物早已抛诸脑后。
比起上述关于看戏活动的细节描写,小说中对丧葬事宜的刻画更能体现当时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古典性体验。小说第四十三回中,李淑芳灵堂的摆设十分考究,“客堂中灵前桌上,已供起一座白绫位套,两旁一对茶几八字分排,上设金漆长盘,一盘凤冠霞帔,一盘金珠首饰”[20];出殡仪式也中规中矩,“炮声大震,灵柩离船,和尚敲动法器,叮叮当当,当先接引,合家眷等且哭且走,簇拥于后”[21]。灵堂的摆设物品及其数量、位置均受到严格控制,这些讲究都属于传统延续下来的习惯,因为这些物件的摆放蕴含着某种古老的寓意,如“一对茶几八字分排”可能象征着逝者在另外一个世界将延续好运;送葬过程的描写顺序井然,先做什么和后做什么都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否则会破坏传统仪式的严肃性,所以那些本来在灵位前指指点点的远房亲戚到了送葬过程中也得按规矩 “且哭且走”,即使其内心毫无悲伤之情。丧葬作为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延续千年而固定下来的形式的延续性不可能被外来事物的入侵所撼动,即使李淑芳生前也和其他女性一样离不开衣镜和自鸣钟,也喜爱亨达利洋行出售的那些有趣的小玩意儿,但这些器物绝不可能出现在她的葬礼之上。从灵堂摆设到出殡过程的严谨有序反映出当时社会依旧是以传统礼仪规范为主导,就算西方现代事物侵入到人们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难以渗透到更深层次的生存体验,不论是依旧习惯于以古典戏曲为乐的审美情趣,还是严格遵守老祖宗礼仪形式的价值规范,都体现出现代性难以匹敌的古典型体验。
细节的描写将小说文本的整体拆分、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小细节,相对于小说整体而言,细节描写虽然琐碎,但更趋近“真实”,是对真实人生的再现。《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充满着各型各色的细节描写,从篇幅上看,对传统生活的细节描写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这说明时人依旧习惯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小篇幅的所谓“现代”生活只扮演了陪衬的角色。此外,即使是身处“现代”环境中,时人也并没有相应地产生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只是在惊诧的瞬间感到不太适应,甚至恐慌,其思想与认知跟不上外界物质更新变化的速度。
[1]王德威.半生缘,一世情——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J].想象中国的方法[M].三联书店,1998:181.
[2]王德威.被压迫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J].想象中国的方法[M].三联书店,1998:13.
[3]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
[4]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7.
[5]王德威.被压迫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J].想象中国的方法[M].三联书店,1998:13.
[6]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7.
[7]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5.
[8]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45.
[9]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87.
[10]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5.
[1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87.
[1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34.
[13]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04.
[14]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67.
[15]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4.
[16]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9.
[17]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9.
[18]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52.
[19]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67-68.
[20]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65.
[2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371.
肖柳(1993-),女,湖北天门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