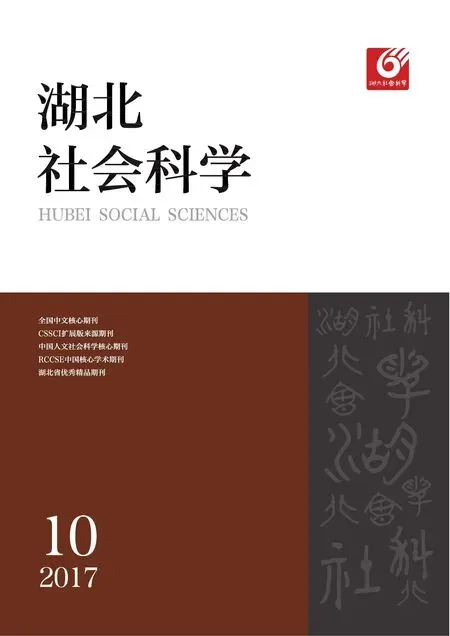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张瑞嵘
(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张瑞嵘
(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指鸦片战争以后活动于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晚清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最先觉醒的一批中国文人。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由于受到“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他们既传播西方科学却又排斥西方思想,固守传统文化却又面临进退失据的文化困境。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在身份、信仰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揭示了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在知识分子思想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西学传播;文化困境;文化保守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陆续开放了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等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城市聚集了一批特殊的中国读书人,美国学者柯文把他们称之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意指受到良好传统教育,主要活动在开放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王韬、蒋敦复、管嗣复、李善兰、冯桂芬和郑观应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大多科举不顺,生活困顿,长期游走于知识分子底层,或从事私塾教育等工作,或受雇于西方书馆从事最早的西学翻译。他们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思想冲突与文化困境,代表了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猛烈碰撞的历史关口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思想转型过程,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与文化的变革。
一、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政治上的屈辱、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是一方面,更为深层的是它打断了中国原有的发展路径,将中国裹挟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新秩序之中,对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乃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就中国版图而言,条约口岸城市的数量与面积微不足道,但是它们却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通商口岸在开始时只是沿海贸易及对外交往的边缘地带的中心,可是在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它们成了斗争的主要焦点”,[1](p231)口岸城市由于西方列强特权的存在而有别于其他城市,它们游离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之外,中外交流频繁,思想控制较为薄弱,不同文化都可以在这里交汇碰撞,这就为造就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提供了历史契机。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加速,经济繁荣,文风昌盛。清以后大兴文字狱,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噤若寒蝉,但依然保持自魏晋以来传承的名士风度,饱读诗书,思想开明,不拘泥于成法。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缘优势和人文传统,当口岸开放,西方思想文化强势介入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率先感知这样的变化,尝试接受不同的观念,理解不同的文化。由于科举的不顺和谋生的需要,他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服务于西方书馆从事西学翻译。与传教士的朝夕相处使得他们更为深入的了解和学习西方宗教、文化与科技知识,思考国家民族的振兴之道,成了中国近代最早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渴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来实现某些变革,改变中国被动落后的局面,但他们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夷夏之辨”深入其心,捍卫名教道统被他们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西方思想文化“入侵”之时,根植于他们血脉中的理念使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与坚持中国传统思想之间进退失据,陷入了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文化困境。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深度的关注与研究。
二、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身份困境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就是身份困境,他们的科举士子身份和西学传播者身份之间的矛盾始终成为一个难解的困扰。科举制度,即分科取士,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打破了基于血缘的世袭制和士族门阀的垄断,使得中下层读书人也拥有了参与政治的渠道。自隋朝诞生以后的千余年来,科举制度不但成了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工具,也是读书人效忠君主,服务国家和实现理想的主要途径。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风鼎盛,自古以来就是科考重地,苏州甚至有“状元是苏州土宜”之说。[2](p236)明清以来士人生员礼遇优厚,入仕以后尊崇的社会地位以及理想价值的充分实现,强烈刺激了读书人的仕进欲望,使得江南地区科考参与人数逐年膨胀。据清代文学家黄钧宰记载:“江南两省(江苏、安徽)为一,与试者多至万六、七,乡试因点名拥挤,停止搜检,竟一昼夜而不能蒇事”;而据林则徐上奏,道光时期江南地区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都要阅卷八百余份。[3](p90)可见江南地区科举士子人数之众。可是,这一地区的科举录取人数却与应试人数极不相称。仅举光绪九年(1881)年为例,江苏、安徽二省的乡试名额只有114名,[3](p90)与动辄数万的士子相比,这点名额可谓杯水车薪。由此可见,严苛的科举考试注定让绝大部分读书人终身被排斥于仕途之外。
可是,当时读书人因循的入私塾,读经书和应科举的士子之路,已经将他们固定在了一个模式化的社会链条之上,一旦科举无望,就意味着理想迷失方向,生活失去依靠。在这批知识分子中,王韬虽然“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通之誉”,[4](p269)但自十六岁以后屡试不售,只能在邻乡授业为生。李善兰自幼独具数学天赋,“年十龄,读书家塾,架上有股《九章》,窃取阅之,以为可不学而能从此遂好算”,[5](p13)却多次应试不顺。蒋敦复虽然秀才出身,“被酒谈兵,以经济才自负”,且自视甚高,认为“大江南北无与抗手”,[6](p103)但之后的科举考试便再无任何进展。管嗣复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为桐城派大家,科考之路也屡次失利。郑观应就更为另类,17岁即来到上海充当洋行学徒,师从传教士傅兰雅学习英文。除了冯桂芬等部分人以外,这批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是在科举考试中铩羽而归。
在科举无望后的经济压力之下,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受雇于西方书馆,从事西学翻译工作。王韬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墨海书馆中从事《圣经》以及其他科技文化著作的翻译,得到了传教士们高度的赞誉,为他在西学传播领域赢得了领军者的地位。查阅《王韬日记》,到处可见他品茗纵酒,谈诗论道,甚至流连勾栏的名士生活记载,可见同时他也获得了比之前开馆授徒更为优渥的待遇。可是,在墨海书馆的西学翻译生涯中,他始终都被一种负面情绪所笼罩,对于所从事的工作也常常给予较低的评价。他认为佣书西舍是“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一失足,后会莫追”,[7](p92)西学翻译“劳同负贩,贱等赁舂,名为秉笔,实供指挥”。[7](p10)这种激烈的偏执文笔却代表了他们当时内心矛盾而又真实想法。他们把西学翻译工作仅仅视为谋生手段,一有机会他们就继续科举考试。例如本绝意科考的王韬于1853年,1856年和1859年又三次应考,但均以失败告终。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江南一带的科考风气,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以及来自于整个家族的期待,使他们始终以儒学传人自居,将科考视为正途,无法放弃位居庙堂之高的人生价值观。这样的理想对于他们投身于西方书馆从事翻译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障碍。放弃科考正途而受雇于洋人,大大的伤害了他们作为中国传统读书人应有的尊严。同时,在当时面临亡国之危的复杂环境下,传播洋人的思想文化也被目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受到了知识界的排斥,一时间“物议沸腾”,“姗笑风起”,[8](p107-108)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是超乎想象的。因此,在从事西学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困扰于读书仕进的传统士子和佣书西舍的“秉笔华士”身份困境中而难以自拔。直到晚年,大半生从事西学传播,致力于改良中国的一代思想家王韬,居然还花费巨资“捐广文”“保太守”谋得一个虚衔,[9](p239)以期为自己一生尴尬的身份划上一个理想的句点。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终身未能摆脱这一困境,实现由传统知识分子向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三、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信仰困境
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中国人始终将儒家思想视为治国方略、社会准则乃至个人的行为规范,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具有绝对统治力的思想。可是,当口岸被打开以后,西方宗教思想传入中国,它所宣扬的许多观念与孔子的教义截然不同,这无形中也挑战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神圣不可撼动的地位,对于当时中国人一元化的信仰造成了冲击。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信仰困境。
早期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受雇于西方书馆。当时在上海等地比较有影响力的书馆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基本上都是由传教士开设,其目的是“在异教徒和其他梦寐民族中传播基督的知识”,[10](p29)通过印刷宗教著作在中国传播宗教思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这批知识分子就不可避免地要率先成为最早阅读、研究和翻译西方宗教著作的人士。
可是,他们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却出现了分歧。墨海书馆在延聘管嗣复翻译《圣经》时,遭到了管嗣复的断然拒绝,据《王韬日记》记载,管嗣复认为“教中书籍大悖儒教,素不愿译,竟辞不往”。他后来还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7](p92)完全将西方宗教斥为“异端”。冯桂芬则认为:“耶稣教者,率猥鄙不足道”,[8](p109)对其进行彻底否定。而郑观应的态度就较为开明,他认为:“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11](p67)表示无须担心西方宗教的传入;而且他还说“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孔孟之正趋”,[11](p243)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宗教也会如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信仰一样,被儒家思想所吸收和同化。
此外,王韬又代表了另外一种折中的态度。与前两者只是语言上的反对与赞同不一样,王韬接受了《圣经》的翻译工作,他认为这不过“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操何业”。[7](p92)这就表明知识分子界对待西方宗教信仰的态度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某种松动,开始参与到西方宗教思想的传播中来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对于西方书馆有所仰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一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理解并接受西方的思想信仰。据美国学者柯文研究发现,在从事翻译的过程中,王韬也试图调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他向传教士们提出“中国人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因此对他进行歧视性的指责是不合适的”,“我认为,每一种宗教都有各自玄想与奥义,在此方面不可能每种宗教都能达成一致。”[12](p24)王韬甚至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13](p13-16)这在当时的传统士林是不可想象的标志性事件。并且在随后几年他还投入到除《圣经》以外的《宗主诗篇》和基督教宣教小册《野客问难记》等多部宗教著作的翻译之中。可是,到了王韬的晚年,他对于西方宗教却渐渐由中立态度转为了排斥,他日记中与基督教有关的记载大多是负面的,甚至有时候还提出了强烈的批判:“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而欲以是训我华民,亦不量之甚矣”。[7](p83)这几乎全盘否定了西方的宗教信仰,而且也相当于对自己的宗教翻译工作甚至入教的行为进行了彻底否定。如此激烈的言辞,出自一位为西方书馆进行了多年宗教和科技文化著作翻译的学者之口,让人匪夷所思。
这样的变化反映出近代中国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宗教信仰的矛盾态度。他们受雇于西方书馆从事宗教著作翻译,这是他们那一时期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而随着他们对于宗教思想的了解,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些思想信仰中包含的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为我所用来改良中国的现状。可是,在更深层次的思想中,“夷夏之辨”的理念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当西方列强一步步入侵中国,其思想文化逐渐在除口岸城市以外地区广泛传播的时候,这批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感更加强烈,“夷夏之辨”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夏”与“夷”的范围从中国与茹毛饮血有待王化的野蛮少数民族间的关系,扩大到中国与远隔重洋的西洋各国之间。对于西方宗教的排斥、理解再到排斥,是这些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从思想上固守传统,抵制西方文化入侵以捍卫自身文化与价值观的必然选择,是他们从信仰上寻求传统文化的精神支点以唤起民众抵御外侮,复兴中华的本能举动,这一矛盾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在他们的思想中所投下的深刻烙印。
四、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落后的局面震动了国人,而在的开风气之先的条约口岸城市,对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感受尤其强烈。郑观应在《易言》自序中写道:“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客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11](p175)他们身处条约口岸城市这样的西学前沿,经常与西方的传教士、官员和商人等人士频繁交往,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试图将其引入中国,以振兴疲弱的国力。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还专门列出了《西学》一章,并认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11](p274)他强调西方科技先进性的同时,把西学的范围主要限定的自然科学领域。而以王韬、李善兰、蒋敦复、管嗣复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服务西方书馆的十几年间,翻译了数十部历史、地理、物理、天文、植物和医学著作,引领了当时中国西学的潮流,开启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可是,与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不同,这批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却强烈的排斥和贬抑。蒋敦复说“天位神器,不可妄干,明正统,重嫡嗣,礼也。英之世系自中国言之,牝朝乱政,异姓乱宗,《春秋》之法,在所必诛”,[8](p107)认为西方国家帝制混乱,帝位男女异姓皆可继承,且政教一体,这是极端荒谬的。王韬认为“吾恐日复一日,华风将浸成夸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西方文化将使得中国道德文化沦丧;他还说“借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天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7](p83)认为西方人不重君臣大义,父子感情淡薄,社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郑观应长期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对于西方国家与中国通商及传播其思想文化的动机也表示高度怀疑,他认为:“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11](p121)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8](p110)他们试图将科技与文化切割开来,借鉴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以振兴中国,而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伦常名教”才是中国赖以存在的立国之本。这种高举“师夷长技”的大旗,科学技术上的大胆引进,文化上却更加趋于保守,成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另一个悖论和困境。
这样一种在现在看来非常奇特的态度,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数千年来,任何一个外来民族征服中国以后,他们最终都会被儒家文化所同化,所以知识分子历来最多也只会有亡国之恨,从来都没有过文化灭亡的危机感。无论身在哪一个朝代,知识分子都可以保持文化上的尊严与自信。[14](p89)可是,“鸦片战争以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中国思想的有用性受到了挑战,而且一旦它的有用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它的真理性的疑问也就不可避免了”,[15](p42-43)这使得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危机感。他们担心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势输入,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风俗礼仪以及价值观念等一切传统将荡然无存,最终为西方文化完全驯服和取代。那是这批饱受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无法容忍也不可坐视的。因此,捍卫中国的纲常名教,被他们看作是拯救天下兴亡的重大责任。他们认为只有保持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同时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可是,中外之间科技与文化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价值观的不断交汇冲撞,文化上的矛盾冲突,使得这批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思想困境。“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4](p266)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注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无法彻底实现文化超越和价值变革,完成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
结语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特定历史环境下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出现,标志着闭关锁国的中国开始了思想与文化的深刻变革。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所传播的西学从江湖之远进入到庙堂之高,日益被统治阶层所重视,他们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许多成了各级政府的幕僚,官办书馆的翻译,甚至出仕为官。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文化,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可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交锋的历史背景下,这批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身份、信仰与文化困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思想转变过程。他们所翻译的大量具有时代意义的西学著作,探索中国富强之路所留下的许多重要思想,为后来的洋务运动乃至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值得为我们深入研究和永远铭记。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龚炜.巢林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欧德良.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地缘成因[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李俨.中算史丛书(第四集)[M].上海:中华学艺社,1947.
[6]王立群.近代上海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J].清史研究,2003,(3).
[7]王韬.王韬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何晓明.略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J].郑州大学学报,2008,(1).
[9]孙邦华.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J].江苏社会科学,2015,(2).
[10]吴义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11]郑观应.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段怀清.试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J].清史研究,2011,(2).
[13][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罗检秋,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4]张瑞嵘.晚清中国译学先驱者的文化认同困境[J].理论月刊,2017,(8).
[15][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7)10-0105-05
张瑞嵘(1976—),男,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唐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