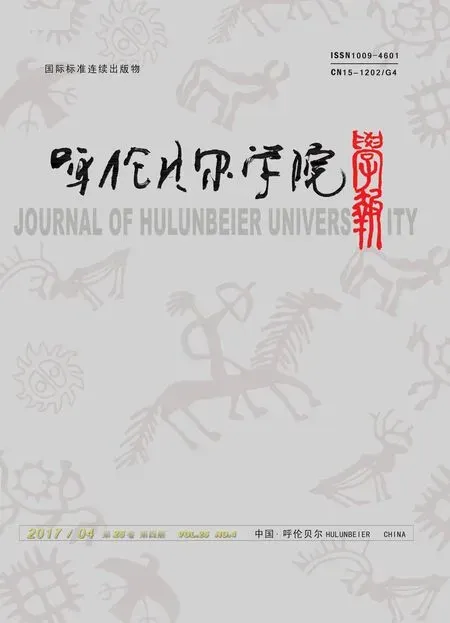村落共同体视域下的社会组织的变迁及其影响
——基于河南省段庄村同庆会的实证调查
潘 琼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1]。传统社会组织曾在村民自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下的传统社会组织却遭遇了困境,难以发挥其效用。此外,稳固的村落共同体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基本条件。因此,探索传统社会组织的变迁及其对村落共同体的影响显得十分迫切。
学术界对维护村落共同体的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究,不同的农村地区在血缘、地缘、信缘、业缘等基础上,产生了巩固着村落共同体的不同的具体因素。1. 血缘关系:杨华以地域为依据,认为单一血缘维系着南方的村落共同体,而族际关系维系着北方的村落共同体[2]。2. 宗教信仰:何倩倩、桂华认为宗教通过其在社区内所处的“同一信仰”的精神地位和所组织的活动加强着共同体成员间关系[3]。周大鸣、詹虚致也认为民间信仰是一定区域内的村民的精神纽带[4]。3. 历史记忆:周丹丹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肇兴侗寨起源故事对于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代村落共同体建构可资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5]。4.独特资源:明清时期随着京西稻“贡米”地位的确立,它逐渐变成了自我和村落认同的基础,在村落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京西稻的停种,无疑弱化了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6]。5. 劳动技艺:蔡磊发现北京市房山区沿村相同的荆编劳作模式,增强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以共同体的形式应对市场竞争[7]。他还指出民间手工技艺的共享来源于共同体意识,但是它也再生产共同体意识[8]。刘铁梁也对北京房山农村进行了田野调研,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村落劳作模式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村落共同体巩固与否,是影响村落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9]。但在这些具体因素中少有人发现民间传统社会组织在维系村落共同体中的作用。传统时期,社会组织的形成得益于稳固的村落共同体,并再生产村落共同体意识,加固村落共同体;而在当代,社会组织的衰败不仅映射了村落共同体的松散,还弱化了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冲击着村落共同体。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变迁对巩固村落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传统时期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
(一)传统时期段庄村同庆会的概况
1. 段庄村同庆会的产生
笔者通过2017年1-3月的调查,发现在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的许多村庄中有一个农村内生的社会组织——花会。鄢陵县文史资料就有记载“后来在各地区还出现了一些花会,正月十五的花会组织甚多,各有绝招。有舞狮会、舞龙会、高跷会、腰鼓会、小车会、竹马会、灯会、玩傀儡戏、打相官等,都是元宵节的群众组织。”[10]但由于一些村庄的花会早已解体,该村的村民对此印象模糊,而且其2000年以后的形态也因其终结而无法探究;一些村庄的花会发展较好,难以观察其受冲击后的形态及其原因。综合各方面的考虑,笔者最终选定变迁中的段庄村同庆会①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如鄢陵县志记载:“农历正月 15日,称元宵节,又叫灯节。是日拜祖先、祭神灵。”[11],当地素有庆祝元宵佳节的传统。传统时期的村民普遍认为正月十五日晚上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庆丰收、拜神仙、求庇护的祥瑞之日。村民们为了向神灵彰显诚意,赢得神灵青睐,本村几个乡村精英商议后决定集中全村的力量举办这项活动,由此就产生了组织、协调该项活动事宜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段庄村同庆会。段庄村同庆会是在以血缘、地缘、信缘、趣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形成的,并为本村村民的信仰、文娱服务的社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将娱乐组织归类为农村传统型社会组织[12]。李熠煜将花会等作为乡村社会团体。[13]俞可平以“职能”为分类依据,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权力组织、服务性组织和附属性组织三类。[14]综合以上分类标准,可以将段庄村同庆会定义为一个传统型、服务型的乡村社会团体。
2. 传统时期段庄村同庆会的运行概况
(1)决策者——乡村精英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5]传统时期的段庄村也盛行着村民自治,乡绅就是本村的“执事人”,这些乡村精英实际控制着乡村的治理。每个大家族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管理能力、热心公益、处事公道、德高望重”为标准推选一位年长的男性作为本家族的“执事人”,这些“执事人”在本家族中承担领导者、决策者、法官的职能,控制着本家族的公共事务。而村落的许多公共事务的决策流程是:首先由各家族的执事人就某项公共事务在本家族内进行商讨,形成最终决策;然后本村各家族的“执事人”再进行博弈、协商,形成他们自认为利益格局平衡的决定;最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同庆会作为段庄村的公共组织,其重要决策包括会首的推选、灯油费的缴纳、道具的购买等都由各家族的“执事人”共同决定。
(2)参与者——全体村民
如果集体行动的单位过大,在组织、协调时会面临较多的争议,花费的交易成本、沟通成本等过高;如果集体行动的单位过小,可资利用的资源较少。具有一致行动力的“村落”是承办传统“花会”活动的最佳集体行动单位,段庄村同庆会就是以段庄村为集体行动单位,其会员是段庄村的全体村民。同庆会的会员有着明确的分工,年轻男性负责体力劳动,如搭建“鳌山”②、挂“吊挂儿”③、表演节目等;女性负责工艺劳动,如制作萝卜灯、“吊挂儿”等;甚至孩子们都积极积极参与其中,到附近村庄扯柏树枝作为萝卜灯的底座。从组织形态来看,它是一种非结构性的软组织,按照约定俗成的传统惯例进行分工,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会员的权利、义务,但面子、道义、传统约束着会员的行为。
(3)管理制度——乡规民约
就每个家族而言,家规约束着家族共同体;就整个村庄而言,村规约束着村落共同体。家规、村规是乡土社会内生的乡规民约,即使没有成文的形式,依旧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乡规民约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教化村民、处理民间纠纷、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是村落共同体的精神依据、行为规范。产生于段庄村的段庄村同庆会,不仅受到本村的村规民约的制约,还要受到当地花会组织的规定的制约,这些乡规民约规范着村民的集体行动,保证了村落共同体集体行动的有序性、一致性。
(二)传统时期的社会组织对村落共同体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于村落共同体的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政治、风俗、文化等场域,而对村落共同体中社会资本的研究较少。而且段庄村同庆会对村落共同体的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体现的最明显。这里采用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6]。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括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因此本文分析社会组织对村落共同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就从分析社会组织对社会信任、村落规范、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着手。
1. 传统社会组织有利于村落共同体培育社会信任机制
非正式组织不是国家力量延伸的产物,而是村民为了实现某种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组织、自发创立的民间社团。村民是社会组织的主体,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成立相应的组织。就个体理性而言,满足村民需求、维护村民利益的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地吸引村民的自愿加入;就个体的非逻辑而言,个体有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将其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17]10。所以社会组织吸引着村民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加强村落共同体内部之间的交流、沟通,增加了村民之间相识、相知的机会。为村民间的相互信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社会信任的培育。此外,村民们每年在同庆会中持续合作的过程也是无限重复博弈的过程,不守信者会遭遇声誉、面子等损失,甚至难以找到合作伙伴,鉴于这些利益的损失,村民们会积极遵循“契约精神”。村民们的持续合作强化了信任,信任又促进着合作,两者是良性循环的状态,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
2. 传统社会组织有利于强化村落共同体的社会关系网络
传统时期,村民之间的合作多是生产、生活方面的合作,而且多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小集团”式的合作。而同庆会的合作是在整个村落集团中基于趣缘的合作,既增加了村民交流的机会,扩大了村民交往的范围;又丰富了村民交往关系的类型,增加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巩固了村落共同体。所以,就村民个体而言,村民们集体行动的过程也是有机互动的过程,有助于加深村民个体之间的感情;就村落整体而言,作为唯一的承办全村集体活动的社会组织,增加了全村村民跨越村组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3. 传统社会组织有利于形成、强化村落规范
在传统的“无讼”社会中,村民由于不熟悉诉讼渠道、难以支付诉讼费用、担心判决不公正等,通常根据当地的乡规民约调节纠纷。在传统社会组织中村民面临意愿相悖和利益冲突时,就会根据当地的传统、惯例确立相应的制度,维护社会秩序。此外,传统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自治性,在社会组织所举办的各种公共活动中,需要村民之间协商一致,形成最终决策。而村民自愿参与、协调利益,最终实现利益均衡、行动一致的过程,就是村民实现自我组织化参与、民主化治理的过程,也是强化、落实村落既有制度的过程。
二、传统社会组织在当代的运作困境及其影响
(一)传统社会组织在当代农村遭遇的困境
1. 村民的参与度低
传统时期,村民们对参与服务型的社会组织具有高度热情,参与度很高。但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下,村民行动趋向于原子化、个体化,村民对于集体活动的热情逐渐削减,参与传统社会组织的村民越来越少。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民们纷纷忙于提高自家的经济水平,村民的行动逐渐开始原子化。尤其是近几年,参与集体行动的村民人数越来越少。就段庄村而言,同庆会作为传统文娱组织,一直受到当地人的热烈追捧,而现在的村民既不愿意参与其中的集体劳动,甚至也不愿意参与赏花灯、看表演等集体娱乐。村民们所漠视的不仅是一个传统活动,更是在漠视传统的惯例和一致的集体行动。既不重视传统,又无法行动一致的村落正面临着共同体意识退化的危机,不利于村落共同体的维护。
2. 传统社会组织分化
贺雪峰在江西安村调研时发现,文化娱乐等局限于一个个村民小组内,村民间交流、沟通的机会少有跨出村组的,所以他们不太熟悉其他村组的村民,整个村庄是一个“半熟人社会”[18]。段庄村也是如此,1990年左右,由于村庄人口量大增,村民观看表演不方便,而且村民的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经村干部商议后,本村同庆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化为四个庆祝单元,每个村民小组独立举办活动。同庆会是本村唯一的社会组织,同庆会的活动也是本村唯一的经常性集体活动。同庆会的这一分化就使得唯一一次所有村民都参与的经常性的集体活动的解散,跨越村组之间的交流机会更少。所以同庆会的分化就预示着村落共同体的分化和村落集体行动机会的丧失。
3. 传统规约的影响力减弱
传统的乡规民约曾在乡村治理中起着“教化、乡治和实际”的重要作用[18],塑造着当地的家风和乡风。而随着大众传媒的进入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多元文化和经济理性也随之进入村庄,传统的规约、惯例遭到破坏。例如,2000年以前村民们共同集资的灯油钱都是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规矩归集体共享,但现在管理费用的积极分子却为己所用,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导致村民出资十分被动。此外,就每个家族而言,家规约束着家族共同体;就整个村庄而言,村规约束着村落共同体,而家规、村规的最高执行者和监管者是“执事人”。但随着“执事人”掌管田契、房契等经济特权的丧失和风俗文化的改变,“执事人”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管理者的地位被撼动,传统管理者所维护的规约的地位也随之被撼动。但真正的权威主体并没有重新确立,真正的民间权威规约也就无从制定,以致村落共同体缺失有效规范。
(二)传统社会组织的衰败对村落共同体的影响
1. 社会信任机制面临解体的危机
社会组织所举办的集体活动的场域是村民之间交换信息的场域,也是村落舆论发挥监督、制约作用的场域。而随着集体活动低效举行,村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关系越来越疏远,村民之间不易也不愿意相互监督彼此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伦理等标准,舆论压力的制约力度减弱。随着舆论功能的失效,不成文的乡规民约也难以发挥其规范效用。近年来,一些不法商人利用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商业头脑等弱点,在农村中选取一些农民作为代理人,在村落中开展传销、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还有一些农民利用农村娶妻难的社会困境,以介绍儿媳作为吸引村民购买保险的营销策略,而遭遇意外的农户却无法获得所承诺的理赔。传统时期的无讼社会以“守信”为前提假设、以良好的信用环境为保障,而当下“守信”的前提假设实效、信用环境崩溃。但农村的信用体系却没有有效的制约、惩罚机制,人情、面子的重要性不及经济利益的诱惑;传统规约的“小宪法”地位丧失;现代法律意识并没有深入人心;现代“契约精神”缺失维护动力。因此,当代农村面临信用危机,社会信任机制面临着解体的危机。
2. 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松散
中部地区许多农村正在面临村庄原子化的危机,村庄原子化是指村民行动趋于个体化,村落共同体的旧有社会关系网络破裂。传统时期,社会组织维护着村民们的利益、名声,是村民集体活动的场域,也是构造、巩固社会关系网络的场域;而随着社会组织的分化和衰败,村落共同体的利益缺失,理性的村民稍经算计就会选择逃离集体行动,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不到维护,遭到了重创。具有联结能力的传统社会组织的衰败使得村民缺乏有机联系的载体,不仅是村组之间的联系甚少,甚至村组内部之间的联系都严重弱化。此外,随着人口的流动,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跨越了村落边界,因业缘、信缘等原因聚集在一起的多种类型的共同体纷纷出现,消解了人们维护村落共同体的热情和机会。所以当代中部的许多村落不再是拥有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共同体,而是原子化程度很高的结合体。
3. 村落共同体缺失村落规范
传统社会组织有利于孕育捍卫村落规范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是村民的代理人,他们通过村落约定俗成的规约处理村民之间的分歧、平衡村落利益格局,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精英作为村庄的杰出人才积极面向城镇,在城镇中工作、生活,较少下乡,使得维护村落秩序的人才流失。虽然村干部在村庄的党政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权力是通过职位所获得的法定权力,而非基于人格、知识等个人魅力所获得的权力,村民难以认同其处理民间事务的权威,以至于村落共同体缺失实施村落规约的代理人。此外,社会组织的参与主体——村民在集体活动中的退出,使得村落规范缺乏落实的社会基础,村规民约、传统惯例难以延续。
三、巩固传统社会组织,维系村落共同体
传统社会组织的变迁是冲击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内部因素,巩固传统社会组织对于维系村落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笔者是在中部农村进行的调研,所以以下措施也是针对中部农村提出的,尤其是城乡结合部或距离城区较近的尚未进入过疏化阶段的村庄。
(一)通过传统文娱组织维系村民间的感情
在群体行动中,个体有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将其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16]10。许多村庄都有传统的文娱组织或文化娱乐活动,在它们没有被当地村民完全遗忘的当下应及时挖掘,以免丧失维系村民情感的历史记忆、宗教信仰、情感寄托等发挥作用的时机。当村干部组织这些传统活动时,可能起初参与的村民多为退休的老人、看热闹的孩子,但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会顺势参与其中。因为活动的举行需要年轻人的服务,这既是村落集体行动的惯例,也是舆论的导向。当这些传统文娱活动得到恢复,深入人心时,年轻的村民也会跟随大家参与其中。因为农民不像城市的公职人员、白领有严格规定的作息时间,在本地小厂房、建筑队、装修队等处工作的村民对自己的工作日有较大的自主权、支配权,甚至可以理解为村民几乎可以自行决定每天是否上班。因此,如果传统文娱活动得到开发、发展,形成集体行动的良好氛围,许多年轻人也会投身其中。年轻的村民通过传统文娱活动这一媒介,增加村民之间的地缘意识;年长的村民通过传统文娱活动这一媒介,唤起历史记忆,增加村民之间的感情。
(二)利用传统组织巩固村落共同体
梁漱溟十分强调团体组织的重要性,认为拥有团体组织的地方具有很强的凝聚力[20]。集体活动在维系村落共同体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集体活动的主角是村落社会组织。传统的社会组织拥有重要的社会资本,其推行难度远远小于现代社会组织。因此,要维持传统的社会组织的运行,增加其活力,提高其在当代农村的地位和作用。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汇演、比赛等方式,打造一个普通大众参与的平台,吸引各乡村重构传统组织,村民以团体的形式参与其中。而且在传统的文艺活动中增加一些当代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如广场舞、健身操等,提高农民参与的兴趣;在传统组织活动中,增加服务于儿童、年轻人的项目,如儿童歌舞、歌手大赛等,完善参与者的年龄结构。通过传统社会组织凝聚人心,创造村民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巩固村落共同体。
(三)在传统组织中发挥新乡贤的作用
传统时期“国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的乡村自治模式得到了历史的认可,其中“乡贤”这一群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当下发达的城中村里,“新乡贤”也在集体经济、村民自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2017年1号文件指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文化。在中部农村,有道德、有文化、有公益心而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乡村能人是现代乡贤的最佳人选。通过建立民主机制,选举出村民普遍认可的新乡贤,并通过荣誉感的树立吸引乡村能人的参与,最后还要建立良好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新乡贤”作用的发挥。
注释:
①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文献查阅、多次访谈,发现鄢陵县各地花会的名称有很多种,而段庄村使用的称谓是“段庄村同庆会”。段庄村同庆会中最重要活动是搭“鳌山”、民间才艺表演、拜天地全神。
② 即花灯架子,总高度将近4米。
③ 由一个个长方形的彩纸剪裁而成,然后由一根根红色的长绳子将其串起来,挂在鳌山附近、街道的上空。
[1]http://www.snkx.org/Article/news/201702/2638.html[EB/OL].(2017-02-6).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
[2]杨华.初论“血缘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南北村落性质比较[J].开发研究,2008(01):95-99.
[3]何倩倩,桂华.民间宗教的公共性及其变迁——基于甘肃中部的田野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15(03):130-138.
[4]周大鸣,詹虚致.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80-88.
[5]周丹丹.历史记忆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肇兴侗寨起源故事考察[J].齐鲁学刊,2016(04):82-85.
[6]刘怡然.食物的消逝与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以京西稻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3(06):138-142.
[7]蔡磊.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京南沿村荆编考察[J].民俗研究,2012(06):106-130.
[8]蔡磊.日常生活、共同体与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一个华北手工专业村的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5):45-49.
[9]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J].民俗研究,2013(03):40-46.
[10]政协鄢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鄢陵县文史资料第八辑[M].许昌:鄢陵县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156.
[11]鄢陵县志编撰委员会.鄢陵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68.
[12]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N].经济日报,2013-03-26.
[13]李熠煜.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J].人文杂志,2004(01):162-169.
[14]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3.
[15]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19-252.
[16]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17.
[17][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18]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6.
[19]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05):51-57.
[20]梁漱溟.乡村理论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