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红旗》杂志及其主编
杨永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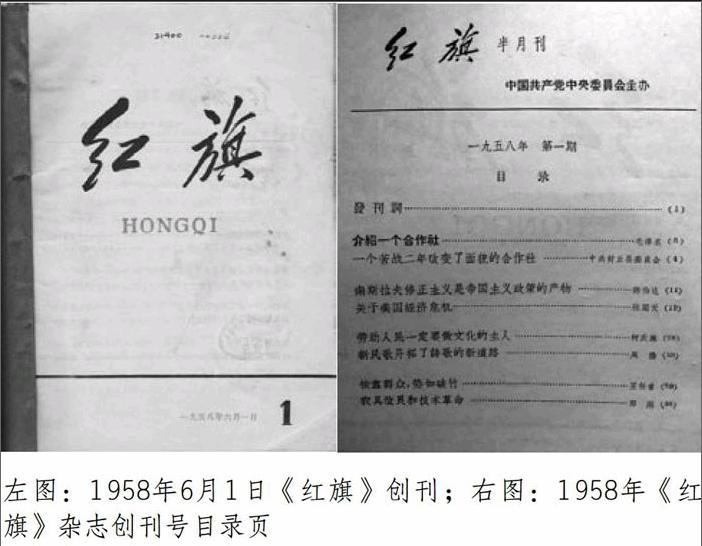

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在“文革”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大跃进”运动、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动者,而其中《红旗》的主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首任总编辑陈伯达并不主持刊物日常工作
陈伯达是《红旗》第一任总编辑,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倡议创办《红旗》时亲自指定的,后经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通过,被正式确定了下来。陈作为《红旗》总编辑的职务虽然被确定下来了,但是他在任期间,“文革”前《红旗》的实际主持者却是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1]三位副总编辑,“文革”初期则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负责。陈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我有几年没有直接管《红旗》了。《红旗》的工作实际由范若愚、胡绳他们管。本来,邓力群也是《红旗》的副总编辑,可后来毛主席对邓力群有意见,说邓力群的哥哥邓飞黄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叫我不要用邓力群。我就让邓力群先到南方去锻炼一段时间。我不直接管《红旗》,重要的事他们还是和我打招呼。” [2]
担任过《红旗》编委的吴江也提到:“陈伯达虽是《红旗》总编辑,但他不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红旗》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总编辑(胡绳、邓力群)和几位编委轮流主持。从写国际反修文章开始,我和陈伯达的接触逐渐多起来。他主持写重要文章时,通常拉邓力群、范若愚和我参加。他给我的任务是‘可以不客气地挑毛病,就是对他起草的文章可以随时提出意见,这大概是因为他发现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的缘故。范若愚的任务则是帮他查列宁语录,因此他每次总是随身携带他那套经他熟读过并在上面夹满标签的《列宁全集》;邓力群不善于属文,但他熟悉党的政策,而且有较强的记忆力,因此他主要参与讨论。这样,无形中形成了‘四驾马车。”他称:“邓力群兼《红旗》秘书长职务,陈伯达把包括人事在内的《红旗》日常事务都交給他。胡绳则代替陈伯达管理杂志版面。”[3]另外,吴江在回忆他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时曾指出:“胡问:《红旗》杂志还有哪些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较高的人?我只说出胡绳一个人的名字,我说胡绳的特点是广闻博识,思维缜密,笔头稳健,尤其有史学底子,《红旗》的重要文章、社论除少数由陈伯达裁定外主要裁决权在胡绳,尤其是关于学术方面的。胡绳不管人事,但待人较宽厚,因此颇有口碑。” [4]而在《红旗》文艺组工作过的牧惠也称,在1961年他调入《红旗》时,邓力群“是常委副总编,实际上是他在那里负责,他是实际主持工作的,但是陈伯达挂名”,“当时是陈伯达、邓力群、胡绳这些人主持《红旗》”,邓力群排第二,胡绳在邓后面。[5]
邓力群、胡绳、范若愚各展所长
在《红旗》杂志社,邓力群“分管经济方面的理论文章”, [6]同马洪、梅行以“许辛学”为笔名合作撰写了大量的经济评论文章。[7]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红旗》在邓力群的主持下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阐释文章,如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红旗》1960年第19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邓力群、吴江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闻师润的《科学的论断和预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红旗》1960年第22期)和《集中力量,各个解决》(《红旗》1960年第24期);肖述、杨甫的《党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红旗》1960年第22期);任会波的《反动派的本性决不会改变》(《红旗》1960年第23期)等,为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正统地位和国际意义作出了贡献。
关于邓力群,吴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邓力群为人有一定胆识,做事也敢承担责任。他颇重权势。对上显恭顺,即对上层领导人谨慎谦和;对下则高傲轻慢,时露霸气乃至杀气。其用人学曹操:凡从我者不管你是什么样人,要高官给高官,要教授给教授,而且常能说到做到;不从我者必要时也敢于‘修理你。邓力群50年代在新疆区党委工作,任宣传部长。中国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尤其是西藏和新疆两地,处理好民族关系十分重要,历史上从来如此。所以开国初期毛泽东十分重视西北地区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50年代新疆区党委在土改问题上犯严重错误,不听中央指挥,擅自采取极‘左行动,乱捕乱杀,造成民族危机。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他认定,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是一个粗人(军人),乱局的策划者主要是当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邓力群。因此,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两次严令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开除邓力群党籍,措辞十分严厉,甚至称之为‘异己分子。当时习仲勋对此事作了冷处理,暂时将邓力群降职,安排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毛泽东从此不再理睬邓,但仍念念不忘其人。邓在办公厅工作期间颇受刘少奇的赏识,可谓失之于毛,得之于刘,然而因此也就为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创办《红旗》时,陈伯达把他调到《红旗》,算是重新又起用了。但是为时不久,当‘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毛泽东又向陈伯达询问邓力群这个人,陈伯达领会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将发动时匆忙将邓力群调离《红旗》下放桂林的原因。” [8]
对于邓力群调离《红旗》的详细过程,吴江说道:“1965年下半年,参加‘四清的人员陆续返回机关,准备照常工作。这时开始发生一点‘异动。陈伯达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邓力群表示很不满意,说:‘《红旗》是秘书长专政,我无权过问。我虽然与邓力群有隔阂,但这次却为邓说了话:‘这不是你安排的吗?怎么又怪起别人来了?陈同样以不满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不再吭声,悻悻离去。隔不多久,大约在1965年年底,突然宣布邓力群调动工作,到广西任桂林地委副书记职,同时调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到《红旗》任副总编辑,代替邓力群。邓力群为此几次找陈伯达和康生,但他们都回避不见。事后我在陈伯达口中才知道,他在起草《二十三条》时,毛泽东突然向陈伯达问起邓力群来,说:‘邓力群现在何处?干什么?还提起邓力群的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兄长的名字。又冲着陈伯达说:‘那次我读书(按:指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几个人共同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你拉他来做记录的吧?陈伯达闻言大惊失色,支吾其词。回来赶紧与康生商量,打发邓力群走路(陈伯达突然散布邓力群搞‘秘书长专政,就是由此而来)。” [9]
胡绳则主要负责《红旗》在学术理论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编辑工作,杲文川在《追忆往昔悼胡老》一文中谈到,“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杜敬‘文革前在《红旗》杂志与胡老共过事,他对记者描述了那时的胡老。‘文革前,胡老在《红旗》杂志任副总编辑,他和邓力群副总编辑轮流值班,由编委协助他工作。胡老在学术理论上抓得多,他修改文章时,既尊重作者的观点,不轻易否定作者好的地方,又从头到尾细细推敲修改,努力提高文章的水平。他的做法有三个好处,一是保护了原作者写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了作品的水平,三是使年轻的编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得以提高。杜敬深情地说,我那时是《红旗》杂志分管农村问题的编委,有时,胡老还组织我们逐字逐句地起草或修改文件,胡老一丝不苟,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令人永远难忘!” [10]
而且,胡绳还在《红旗》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所发文章以“施东向”为名。对此,胡绳称:“有一些文章署名‘施东向,这实际上是个集体的署名。使用这个名字的文章有的与我全无关系,有的则是我参加写作的。” [11]马仲扬在其追忆文章《六十年的战友情》中也提到:“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文化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就是思想界动向的谐音),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经他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 [12]此外,胡绳在《红旗》上还发表了一些署名文章,如《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红旗》1958年第7期)、《关于我国现在的商品生产》(《红旗》1958年第14期)、《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红旗》1959年第9期)、《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红旗》1959年第23期)。不过,对于这些文章,他说:“我在《红旗》上写的有几篇政论文章和不署名的社论,现在都只能属于被淘汰之列。” [13]
而范若愚,这位因其对列宁主义研究较有成就,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赞誉为我国“研究列宁主义问题的专家” [14]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从1958年《红旗》创刊起就担任编委,1965年年底开始担任《红旗》副总编辑。他曾参加起草过中苏论战文章,与胡绳、王力等人参与拟定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在《红旗》任职期间,他在负责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理论文章,如《一个办得很像样子的公共食堂》(《红旗》1958年第12期)、《思想必须适合于客观规律性》(《红旗》1959年第1期)《我们为什么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红旗》1960年第5期)、《列宁论中国革命》(《红旗》1960年第8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红旗》1961年第13期)、《马克思主义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红旗》1962年第19期)。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时代的烙印。
关键文章由陈伯达负责起草
当然,《红旗》虽然由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实际主持和直接管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总编辑陈伯达对《红旗》完全不闻不问。实际上,凡是《红旗》重要的社论、评论员和编辑部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由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尤其是毛泽东要求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这从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红旗》文章的批语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来。而且陈伯达在《红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也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如1958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举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大旗;1958年第3期发表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公社”这一名称;1958年第4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不仅强调了毛泽东的公社思想,而且还重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959年第22期发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则是专门批判彭德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过陈伯达称此文章是中共中央要他写的。他说:“遵照中央的决定,按照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有关讲话,写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里没有我自己的话,都是抄录毛主席的讲话和别人写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的话。我在文章里自始至终仍是称彭德怀为同志的。” [15]
另外,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陈伯达也是亲自过问和亲自处理,可以说关键时刻都是亲自出马的。据吴江称,“‘文革的大批判实际上是由《红旗》开头。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提出所谓‘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是由陈伯达执笔的。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陈伯达由天津结束‘四清回来后不久,在《红旗》发起组织一个所谓‘学术批判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陈自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成员包括王力(中联部副部长,稍后即兼任《红旗》副总编辑)、关锋(《红旗》编委)、戚本禹(《红旗》历史组组长,他刚从中央办公厅调来)及其他共七八个人,其中没有胡绳、邓力群,也没有我。邓力群是因为当时突然被调离《红旗》,下放广西桂林地区。这本是陈伯达、康生在‘文革山雨欲来时对邓的一项保护措施,因为邓力群曾任刘少奇秘书,与刘关系不同寻常。邓突然外调广西,当时许多人被蒙在鼓里,就连邓力群自己也深感委屈。胡绳呢,大概是因为当时他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关系已为人所注意(彭是保护吴晗的,认为吴写《海瑞罢官》并非反党,胡绳也这么看)。”吴江还提到:“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公布后,邓力群也从广西被揪回,加入我们的‘黑帮队伍。……此后,《红旗》杂志虽仍由陈伯达任总编辑,实际上编委由关锋主持,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力、关锋垮台,又由姚文元接管,直至‘四人帮覆灭。” [16]
从吴江以上的回忆内容,可以看出邓力群在1965年“四清”时就因个人同刘少奇的关系而在“文革”前遭到冲击,从而结束了他在《红旗》的主持和领导生涯。胡绳和范若愚,后来也因为参与拟定《二月提纲》的缘故,成为“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的对象,结束了他们在《红旗》的工作。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是《红旗》杂志社中受到“文革”冲击的第一批领导。关于胡绳不再管《红旗》事务的具体时间,他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中曾提到:“我從1958年起担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直到1966年‘文革风潮起来时被罢免,不过至晚从1963年起的几年间我已实际上不过问这个杂志的工作。” [17]邓、胡和范相继被打倒后,《红旗》的主持和领导权就转到了“文革”新贵、毛泽东的新红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的手中,此时的陈伯达真正成为了挂名的总编辑,这一点吴江在上述的回忆中也有所提及。
注释:
[1] 据吴江称,“大约在1965年年底”,范若愚代替邓力群担任《红旗》副总编辑(参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2]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58-259页。
[3]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4]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3版,第17页。
[5]朱健国:《牧惠在2002年(一)》(2005年1月6日),学术中国网站,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635.
[6]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7]相关文章有:《一切经过试验》(《红旗》1959年第11期)、《指标要切合实际》(《红旗》1959年第12期)、《学会更好地计算经济效果》(《红旗》1959年第13期)、《工业生产中的节约》(《红旗》1959年第14期)、《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红旗》1959年第22期)、《保持工业生产在高速度发展中均衡地上升》(《红旗》1959年第24期)、《又是大跃进的高速度,又是有计划的按比例》(《红旗》1960年第3期)、《全面安排 综合平衡》(《红旗》1960年第23期)、《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红旗》1961年第18期)、《进一步健全工业企业的责任制》(《红旗》1961年第20期)、《把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红旗》1963年第2期)、《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红旗》1964年第16期)。
[8]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第116-117页。
[9]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第121-122页。
[10]杲文川:《追忆往昔悼胡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s.net.cn/wyld/y_02_15/y_02_15_7.htm.
[11]《引言》,《胡绳全书》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2]马仲扬:《六十年的战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s.net.cn/zhuanti/husheng/show_News2.asp?id=83067.
[13]《引言》,《胡绳全书》第二卷,第3页。
[14]马原生:《缅怀范若愚同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和品格》,《理论探索》1999年第2期。
[15]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77-178頁。
[16]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第4-5页。
[17]《引言》,《胡绳全书》第二卷,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