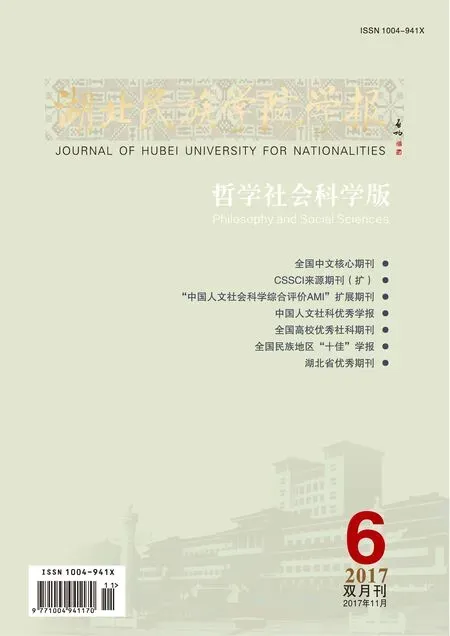远离“城”嚣的乡村赞歌
——论亨利·菲尔丁小说中的田园因素
廖 衡,朱宾忠
(1.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远离“城”嚣的乡村赞歌
——论亨利·菲尔丁小说中的田园因素
廖 衡1,2,朱宾忠1
(1.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在小说中传承了古老而持久的西方田园传统,将英国乡村呈现为与城市对立的美德之地与安乐之所,表达了对十八世纪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突出道德问题的批判。他的三部小说《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与《阿米莉亚》融入了田园退隐叙事模式,沿袭了英国田园诗学对本土化的“阿卡狄亚”的乡村礼赞,吸纳了田园诗学中的城乡对比结构,传承了田园诗学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特质。
菲尔丁;小说;田园退隐;阿卡狄亚;城乡对比
亨利·菲尔丁在小说这一文体中对西方史诗传统的传承早已是中外学界共识*详见Ian Watt 所著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第八章“Fielding and the Epic Theory of the Novel” 、韩加明所著《菲尔丁研究》第六章第二节“《约瑟夫·安德鲁斯》序言的遭遇”及Henry Power 所著Epic Into Novel :Henry Fielding,Scriblerian Satire,and the Consump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2015)。。但其对另一种古老而持久的欧洲古典文学形式——田园诗学的继承却少有学者进行深入地分析探讨*杰夫瑞L.邓肯分析了《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多情之旅》(斯特恩1768)《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哥尔德斯密斯1766) 与《汉弗莱·克林克》 (斯摩莱特1771) 中的乡村理想,指出四位作家都运用了田园诗学传统中推崇社群关系、知足节制与慈善济贫等乡村理想,对抗与批判笛福与理查逊小说中所彰显的个人主义与追名逐利等新兴的资本主义价值观(see Jeffrey L.Duncan.“The Rural Ideal in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1968(3):517-535)。斯奎尔斯曾在专著《田园小说》(1974)中指出菲尔丁小说中对乡村理想的书写预示了十九世纪英国田园小说的产生,但是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大卫·洛奇在《小说的艺术》“地方感”一章中指出早期的英国小说鲜有对“地方”作详尽的描写,“地方”仅仅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和烘托小说人物、情节及主题等作用,并以《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浮光掠影的伦敦描写作为例证[1]57。尽管菲尔丁在小说中对伦敦的描写的确略显简陋,但小说中对乡村作为一种与城市对立的、独特的“地方”与空间的描写却是充满深情、耐人寻味的。这种对乡村的美化书写正是西方田园文学的核心。
对于田园小说的定义和特征,迈克尔·斯奎尔斯 (Michael Squires) 在《田园小说: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及D.H.劳伦斯研究》(1974)给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田园小说是小说的一种次文类,产生于借由多种元素及方式美化乡村生活的田园传统——主要是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从城市及乡村视角对乡村生活的再现;对过往和平与富足的“黄金时代”的怀恋,暗含着由繁入简的隐退及对现代生活的批评。田园小说创造了一个遥远的、界限分明的田园世界: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人们的生活闲适知足。[2]18
由此观之,田园小说继承了田园诗学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立场,沿袭了田园传统的三个核心要素:田园退隐叙事模式、理想化田园空间的建构及城乡对比的主题。十八世纪是英国商业社会初步定型和工业革命发端的时代[3]1,也是英国田园文学完成本土化[4]166,寻求多元化发展的时期。首先,英国乡村空间及其所代表的“乡村美德”与“乡村纯真”由于受到土地圈禁、工商业发展及城市扩张的威胁,引起文人们的普遍关注。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1770)与威廉· 珂柏的长诗《任务》(1785)分别谴责了圈地运动与城镇扩张对安宁和谐的乡村空间的破坏。其次,十八世纪欧洲的风景热促使这一时期的英国诗人开始关注英国的农田、村舍及花园等乡村风景所体现的美学价值。[5]64-75詹姆士·汤姆逊的田园诗《四季》(1730) 最为完美的描绘了宜人的乡村田园风景。其三,滥觞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乡村庄园诗歌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诗作中日臻完善,此类诗歌将传统田园诗学中的“阿卡狄亚”与彼时英国贵族的乡村宅邸对等起来[6]30,赞美慷慨的乡绅及其所辖的乡村美德共同体,表达某种社会和道德价值。
菲尔丁在小说中传承了英国田园诗学中的核心因素,他的三部小说《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1749)与《阿米莉亚》(1751)融入了田园退隐叙事模式,沿袭了田园传统中“阿卡狄亚”式的乡村礼赞,吸纳了田园诗学中的城乡对比主题,传承了田园诗学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特质。
一、离城返乡:菲尔丁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英国当代学者特里·吉福德指出“田园文学基本上是一种退隐的叙事模式(discourse of retreat),要么是简单的逃离复杂的城市、宫廷、当下社会及‘我们的风俗’,要么是对它们进行考察”。[6]46古希腊朗格斯的《达佛涅斯和克洛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桑纳扎罗的《阿卡狄亚》及莎士比亚的田园剧作《皆大欢喜》《冬天的故事》及《暴风雨》都以从宫廷或城市退隐至田园乡村的旅程为主要叙事模式。[7]131菲尔丁的三部小说在整体及插入叙事中都融入了这种“离城返乡”的田园退隐叙事。
在宏观叙事上,三部小说的主人公离开相对单纯的乡村,直接或是在长途跋涉之后进入混乱的都城伦敦遭遇各种诱惑与考验;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美德获得爱情与财富的回报,之后无一例外地选择返回宁静的乡间,与爱人厮守终生。菲尔丁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讲述了俊美的乡间男仆安德鲁斯在伦敦城拒绝女主人的引诱后,在乡间牧师亚当姆斯的帮助下返乡的艰难历程。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的前三章介绍了安德鲁斯所在的乡间社区——主人鲍培爵士的乡村庄园与牧师亚当姆斯所辖的乡间教区。第四章到第十章发生在伦敦,安德鲁斯随鲍培夫人来到伦敦,在拒绝女主人的引诱后被撵出公馆。第一卷十一章到第三卷为安德鲁斯在牧师亚当姆斯的帮助下,从伦敦返回乡间与挚爱范尼团聚的漫长旅程。小说的第四卷发生在鲍培府的乡间教区。安德鲁斯身世大白,与范妮完婚后退隐到生父威尔逊先生所隐居的乡间,“领略乡居的乐趣”,男耕女织,“过着无法比拟的幸福生活。”[8]367-368
在《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中,这种离城返乡的叙事模式表现得更为对称。小说讲述了私生子汤姆在英国乡间出生与成长、到被迫离乡入伦敦城、再到苦尽甘来归乡的历程。从故事空间上看,全书十八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前六卷的故事发生在乡村——英国西部萨默塞特郡的两处乡绅宅邸,中间六卷描写由乡村到京城伦敦旅途中的情景,最后六卷的故事发生在京城伦敦。在全书的结尾,汤姆和苏菲亚“婚后不到两天,就在魏斯顿先生和奥尔华绥先生的陪同下,回乡间去了”[9]976。
不同于前两部主要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阿米莉亚》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伦敦,是一部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10]271全书十二卷,小说的叙事空间主要集中在伦敦城,但乡村却是阿米莉亚和布思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他们在城市历经种种苦难之后的回归之地。在前三卷中,蒙冤入狱的军官布思讲述了自己与乡间淑女阿米莉亚甜蜜却艰难的婚恋历程。由于军队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夫妻婚后生活贫穷,蜗居在伦敦宫廷周围王室司法官的辖区。第四卷布思出狱与妻儿团聚。为摆脱困境,他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职位,却再三陷入权贵引诱阿米莉亚的诡计之中,布思也屡遭监禁(第七卷末与第十一卷末)。当布思夫妇最终以高贵的品质抵御住一切诱惑和罪恶,苦尽甘来,继承了阿米莉亚母亲的遗产之后,他们选择远离纸醉金迷的伦敦,重返阿米莉亚的乡间宅邸,享受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小说中的插入故事也重复着这种远离“城”嚣的返乡叙事。《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中第三卷第三章插入了乡绅威尔逊先生早年在伦敦厮混后归隐乡间的故事。威尔逊先生年轻时在伦敦过着堕落的生活,他衣着浮华、花天酒地、嗜赌成性,挥霍完财产便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昔日的酒肉朋友离他而去,达官贵人们对他避之不及。患难中他与赫丽德小姐互诉衷肠,婚后不久便离开伦敦归隐乡间,用威尔逊先生的话说,“从一个满是扰攘、喧嚣、仇恨、妒嫉和忘恩负义的世界转移到安逸、清净和恩情如海的天地”[8]234。无独有偶,在《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中第八卷中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插入了一段隐居山间的“山中人”的故事。山中人向前往伦敦的琼斯和巴特里奇讲述了他漫长的退隐历程。他本是一个家境殷实的自耕农之子,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却沉溺于花天酒地,债台高筑后竟然堕落到偷窃同学钱财的地步。为躲避拘捕,他和情人逃到伦敦,挥霍掉钱财后遭情妇出卖而锒铛入狱,侥幸逃脱之后又深陷赌场,靠哄弄生手勉强度日。后来偶遇父亲,奉命返乡。父亲去世后,山中人隐居山林,如中世纪的修道士般远离尘嚣。《阿米莉亚》第三卷也插入了一段布思回忆他和阿米莉亚返回乡间耕种田地的故事。 对布思来说,这段乡下平静美好的时光是“无法描述的最大幸福”[11]157,与他们在伦敦的各种复杂困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除了在小说结构中融入从城市到乡村的田园归隐模式,三部小说中的乡村归隐之地还呈现出田园诗学中“阿卡狄亚”的地貌。
二、“天堂府”与黄金乡:菲尔丁小说中的“阿卡狄亚”
自维吉尔以来,西方田园文学将具有古典神话渊源的希腊山区阿卡狄亚(Arcadia)描绘成与宫廷及城市文明对立的“一个简单宁静的农业文明中的理想世界”[12]16;之后,基督教田园诗人将“阿卡狄亚”与《圣经》中的“伊甸园”结合起来,凸显其宗教象征意义。[13]202十七世纪以来随着英国田园诗学的本土化,以蒲柏和汤姆逊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注重表现英国化的“阿卡狄亚”:开明乡绅的乡村庄园与农人的村舍。
利奥·马克斯曾指出“阿卡狄亚”是一种诗人建构的“将神话与现实巧妙融合的象征风景”。[5]13在当代风景研究视域下,阿卡狄亚作为一道汇聚政治道德、审美趣味与宗教信仰等文化意义的象征风景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解读。菲尔丁小说中的英国乡村就呈现出这样一种阿卡狄亚式的地貌:乡村是开明乡绅的“天堂府”,是自给自足农人的“黄金乡”,是一种象征着真、善、美的审美空间、伦理道德空间与神性空间。
菲尔丁将《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中乡绅奥尔华绥的乡村府邸命名为有基督教意蕴的 “天堂府”( Paradise Hall),对其风景描写继承了英国田园诗歌中的如画美学范式,呈现英国乡村“参差多态”的美丽景致。“天堂府”具有鲜明的英国本土特色。府邸位于英国西南部萨默赛特郡(菲尔丁的出生地),是彰显英国特性的哥特式建筑:“在哥特式的建筑中,再没有比奥尔华绥先生的住宅更加壮丽的了。它有一种宏伟的气派,使人望之肃然起敬,很可以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9]17“天堂府”响应了英国十八世纪中期 “哥特复兴”之风,是英国小说中第一个哥特式建筑[14]27,与盛行于奥古斯都时期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帕拉迪奥式建筑形成对立之势,表达了对英国本土文化的民族自信。
“天堂府”依山傍水,俯瞰着“山谷里一片极其动人的风光” (charming prospect):
丛林(橡树)环抱中,有一片美丽的草坪,一直斜铺到房子跟前,草坪高坡处,一股汹涌的泉水从枞树遮掩下的岩石里喷出,形成一道长达三十英尺左右、经年不息的瀑布。它并非阶梯尽然,顺序而下,而是从高高低低、藓苔斑驳的碎岩散石上翻滚下来。冲到岩石脚下,它就奔入卵石累累的涧溪,一路上低跃浅踪,迂回注入山麓下的一个小湖……平原上放牧着羊群,点缀着一簇簇的榆树和山毛榉。湖里流出一道小河穿过形形色色的草地和丛林,蜿蜒曲折好几英里,然后倾注于海。辽阔的港湾外是一座孤岛,这一面的景色到此为止。
山谷右边也是一片平原……几座村庄点缀其中。平原尽头,在古老教堂的废墟上,可以望到爬满常春藤的一座钟楼,以及那教堂残存的部分门墙。
左首是一座秀丽宜人的花园,依着崎岖的山势构成,其丘陵、草地、丛林、流水,无不曲尽变幻之美,安排得极为优雅悦目。但这一切多是出于大自然的匠心,非人力所缔造。再过去,田畴渐次隆起,形成荒山野岭,峰巅高耸入云。[9]17-18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在《寻找如画美》一书详细探讨了自弥尔顿以来的英国田园诗对“参差多态”的如画美景的偏爱。[15]24-32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中的伊甸园是个“幸福的乡村,景色参差多态”,蒲柏的《温莎林》及汤姆逊《四季》都传承了这种“和谐的不和谐”的构景法则,山岚、谷地、平原、树木、溪流、田畴、村庄及废墟等多样化的英国本土景色在诗行里交相辉映。“天堂府”的水(泉水、瀑布、湖、河、海)、木(橡树、枞树、榆树、山毛榉)与石(岩石、碎岩散石、卵石、废墟、荒岭)传承了英国田园诗歌中如画美学的取景模式,呈现了英国乡村“参差多态”的美丽景致,融合了平滑明媚的优美与粗犷幽暗的崇高之美,不仅有柔和平缓的草坪与流水,也有晦暗粗糙的苔藓碎石及令人慕古遐想的废墟和荒岭。“天堂府”中“出于大自然的匠心,非人力所缔造”的花园让人再次联想到《失乐园》中的伊甸园:“乐园里繁花似锦,并非人工巧手造就/不是花床和新奇的园艺,而是自然之厚爱”。[15]24
“天堂府”也沿袭了英国田园诗作中对乡村庄园的道德伦理赋值。在琼森与蒲柏等诗人的乡村庄园诗作中,“乡村庄园已经超越了一个物质的存在,成为正统、和谐与秩序的缩影”[16]67,慷慨的乡绅是美德的代言人和可靠的乡村庇护者。 与琼森笔下庄园主罗斯一样,天堂府的主人奥尔华绥热爱乡村,“大部分时间他都跟一个妹妹隐居在乡间”[9]12;他秉承了庄园诗作中极力赞美的庄园主的责任感、好客与慈善等美德。他时常“默想着上体天意,对造物主的子民,行最大的善事。”[9]18他处处体恤帮衬他所辖范围内的乡民:“他总是殷勤招待街坊四邻,并且常用残羹剩饭周济穷人——即是说,那些宁愿乞讨而不愿工作的人。”[9]14托马斯·卡鲁的《致萨克斯海姆》(1631~1632)这样赞誉庄园主的责任感与慷慨:“你的门口没有守门人/来检查穷人,或者将之摒拒于外;/也没有栓锁;你的大门就是为了/让陌生人进来而修建。”[17]41-42天堂府的大门也是永远对乡民们敞开的:“不论是奥尔华绥先生的家宅,还是他的心怀,对任何人都从不关门;尤其是对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更是如此。只要你这人值得款待就一定请你吃一顿。”[9]36
英国乡村在菲尔丁小说中不仅是乡绅的“天堂府”,也是劳作中自给自足的农人的黄金乡,是一种象征着宁静、纯真和幸福的美德空间。在十八世纪的田园诗作中,简朴的农舍与淳朴的农人被抽象成纯真、朴素及知足之乐的“乡村美德”与“乡村纯真”,例如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追忆村舍所代表的“纯真和安逸”,而威廉·沃农的《茅舍》则赞美了英国乡间朴素大方、宁静安详的农舍,将其比作 “阿卡狄亚牧羊人古老的寒舍”[15]10-11。菲尔丁的小说传承了田园诗作对质朴的乡村茅舍和勤劳知足的农人的歌颂。《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第三卷第四章详细描绘了威尔逊先生自给自足的乡间隐居生活,这种健康、单纯、与家人亲近的生活方式被牧师亚当姆斯称为“黄金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亲自打理的农家小花园清新简朴,“既无花坛喷泉,也没有雕像装饰。唯一的点缀只是一条短短的散步小径,两旁种着荫翳的榛树。” 菲尔丁非常强调自给自足的农人纯真、和谐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威尔逊先生的花园“绝对没有醉心于虚荣的人,却有着各式各样的水果,厨房里用得着的菜蔬也应有尽有”[8]237。他每天在花园里日出而作,在这里至少劳作六小时以上,因而“不必借重医药,始终能够保持健康”[8]237。他和妻儿总是寸步不离,相知相惜。在《阿米莉亚》中,质朴的农舍总是与美德、纯真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牧师哈里森博士乡间 “朴实无华的房屋”被描绘成为“地上的天堂”,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朴素”[11]154,彰显着牧师美好的品德。 阿米莉亚一直劝说丈夫放弃追名逐利的军旅生活,告诉他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一间简朴的村舍就是“天堂”。[11]101布思也逐渐接受了她的观点,常常后悔没有听取阿米莉亚的建议,“选择爱情,居住在一间农舍里”,而去“追求那光耀夺目、令人心醉神迷的荣誉”。[11]111在与腐败的军队和城市官员与显贵的接触中,布思逐渐意识到可贵的乡村纯真与美德:“宫殿有时阴郁沉闷,光线暗淡,而正义的阳光却在一个村舍中灿烂辉煌的照耀着。”[11]128对布思和阿米莉亚来说,乡间的农事时光是他们苦难生活中最为幸福亲近的一段田园插曲。在一连串强烈的反问排比句中,布思道出了乡间生活的种种妙趣:
谁能够描述,早晨的空气给一个身体完全健康的人所带来的快乐呢?谁能够描述,锻炼身体之后精神的焕发呢?谁能够描述,父母亲从孩子们呀呀学语和天真烂漫的胡言乱语中所感受到的快乐呢?谁能够描述,妻子亲切的微笑在丈夫心中所引起的高兴呢?最后,谁能够描述,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妇从彼此谈话中所享受到的那种愉快和切实的慰籍呢?[11]157
布思将乡间务农的生活总结为 “连续不断的爱情、健康和宁静”[11]155,重申了威尔逊先生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偏爱。乡间劳作不仅有益身心,更重要的是乡间单纯的社会环境、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协作方式更有利于增进夫妻情感和亲子关系,是一种道德伦理空间。
乡村在菲尔丁小说中还是一种靠近上帝、修隐冥思的神性空间。从命名上看,《汤姆· 琼斯》中的乡绅奥尔华绥(Allworthy)象征着基督教中全善全能的上帝,他的“天堂府”则是基督教化的“阿卡狄亚”。从造园风格上看,浑然天成的“天堂府”表现出奥尔华绥对上帝所缔造的自然风景的敬畏之心,彰显着他良好的基督教美德,而布利非大尉终日盘算着改建装点这座庄园,则表明了他与基督教相对抗的邪恶天性。[18]356安德鲁斯指出,田园归隐的极致便是基督教的隐士文化,小说中身披兽皮,归隐山林的“山中人” 是西方隐士的代表。同父亲返乡后,他衣食无忧,远离尘嚣,开始潜心研究《圣经》,感悟基督教的力量:“哲学使我们更加聪明,但是基督教却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9]451归隐山林后,他更是全心参道,在自然的万千景象中追寻上帝的恩惠:
我们眼睛看到的哪样东西不使我们想到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慈呢? 旭日不必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放出万道金光,暴戾的狂风也不必从岩穴里冲出,摇撼高耸的森林,乌云也不必猛然裂开,倾注滂沱大雨,淹没田野,来显示上帝的庄严。这些一概都不需要,因为万物之中,一虫一草也罢,不论多么低微,没有不带着伟大的造物主的标志的,不但标示着他的权力,也标志着他的智慧和仁慈。[9]464
不同于威尔逊先生、布思夫妇所感受到的审美与伦理的乡村风景,“山中人”所体验到的乡野处处彰显着造物主的伟大与基督教的光辉。珂柏曾在他的长诗《任务》中点明了乡村的神性特质:“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 到英国十八世纪中期,这种对乡村的依恋逐渐扩展到对山峦、沙漠和海洋等自然景观的热爱。[19]108同时,约瑟夫·艾迪生、爱德华·杨格及菲尔丁等国教会宽容派文人志士通过散文、诗歌及小说文本不断将对自然风景的感官愉悦升华为一种笃信上帝与基督教的神性思忖。[18]355“山中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眼中的阳光雨露、狂风骤雨与一虫一草都饱含着基督教造物主的深情大义。
菲尔丁的小说继承和响应了英国田园诗歌对本土化的“阿卡狄亚”——英国乡村庄园及乡间农舍——的歌颂,乡村在小说中既是开明乡绅贵族的“天堂府”,也是自给自足的农人的黄金乡,是象征着真、善、美的伦理道德空间、神性空间与审美空间。这种“阿卡狄亚”地貌在小说的城乡对比结构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三、纯真之乡与罪恶之城:菲尔丁小说中的城乡对比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20]32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城市文明征服和取代乡村文化的历史。然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知识分子,流露出对乡村文化深深的眷念。在英国田园文学中,这种被燕卜逊称为“持久的乡村传统”[21]20的情感结构常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田园对比。汤姆逊的《四季》对比了“沉湎于烟、昏睡与毒湿”的城市与散发着奶牛气息的乡野田间。[5]69琼生则赞美庄园主罗斯热爱乡村,不受城市与宫廷“恶习和享乐的玷染”[5]40。
哈利特·史密斯指出田园诗学通过“对比简单的、自然的、自给自足的、与世无争的田园世界与虚荣浮华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的批评”[22]301。格伦·A.洛夫也指出田园文学 “不仅涉及乡村风光和自然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批评”[23]74。西蒙·沙玛分析道“乡村生活是腐败、奸诈和城市弊病的一剂解药,这一古老理想总是刺激人们将‘安乐之所’(locus amoenus)乡村化”[24]529。田园文学通过田园类比批判了复杂腐化的宫廷生活及城市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小说中,菲尔丁沿袭了田园诗学中的城乡对比结构,表达了对英国城市化进程中这些突出的道德问题的批判。《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卷首就流露出一种田园类比思维。菲尔丁将作家比为“饭铺老板”,小说的题材“人性”比为菜肴,在上菜顺序的比喻中点明了小说场景的更替:“我们……先托出乡村习见的那种较为平凡、质朴的人性……然后再用宫廷的都会所提供的那些造作、罪恶等等法国和意大利式的上好佐料,加以清炒或红烧”[9]11。与汤姆逊和琼生一样,菲尔丁将乡村视为培育“平凡”与“质朴”人性的纯真之地,而将宫廷都会视为滋生虚伪与“罪恶”的名利场。
菲尔丁赋予乡村慈父般的道德领袖和伦理权威及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善人士。《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中的庄园主奥尔华绥仁慈慷慨,是理想化的开明封建领主的楷模。在他的教导下,成长于乡间的汤姆· 琼斯虽然行为冲动轻率,但性情善良、仗义疏财、勇敢豪迈,是 “善”与“真”的表率。在乡间成长起来的另一位“善”与“真”的化身是与汤姆相爱的乡绅魏斯顿之女苏菲亚。她的美不仅在于她的外貌和形体,更在于她善良贤淑的天性与成长于质朴的乡间淑女所特有的“天真纯洁”。由于在乡间长大,极少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她的“举止之间也许还缺乏一种潇洒的风度,那只有靠上流社会的耳濡目染来养成了。”但是 “为了取得这种风度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苏菲亚身上的这点缺陷却早已为她的天真纯洁所弥补了。”[9]140无独有偶,《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中,博学却单纯的乡间牧师亚当姆斯也充当着道德伦理权威与维护者的角色。亚当姆斯将教区内的居民当作孩子看待:“上帝交给他的堂区居民,他都当作儿女”[11]11,正是在他的道德教化下,主人公约瑟夫才会时时刻刻以亚当斯牧师的教导为准绳,后者实际上成了约瑟夫的道德监护人。[25]145同样地,《阿米莉亚》中的牧师哈里森博士也是他所辖教区的伦理权威和道德维护者。他把教区居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居民们则把他看成自己“共同的父亲”[11]154,每个星期他都要到教区中的每个家庭去访问一次,查问他们的情况,并根据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表扬或指责。在这个牧歌式的田园社会中[25]146,“居民的争吵从来没有发展到打架或诉讼的地步;教区里看不到一个乞丐……从没有听到过一句亵渎神明的诅咒”[11]154。尽管乡村里不乏追名逐利的势利小人与身无长物的上等人,但是乡村中总有以身作则、仁慈宽厚的伦理权威和道德领袖惩恶扬善,是孕育“善”与“真”的希望之地。
相比之下,京城伦敦却是滋生罪恶的是非之地,是赌徒浪子的藏身之所,是缺乏伦理权威和道德感的精神荒原。《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中的“山中人”这样描述伦敦:“这里是忧伤或耻辱……最妥善的隐身之所。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孤独的好处,而不会感到不便……你或坐或行,都无人理会。嘈杂、匆忙、不断涌现的事物都能为你消闲解闷,免得精神受折磨——说得更确切些,免得受忧伤或耻辱的折磨。”[9]442伦敦在“山中人”眼中是孤独、混乱、嘈杂与匆忙的。他的伦敦堕落史为琼斯和苏菲亚在伦敦的遭遇埋下了伏笔。刚到伦敦,堂姐费兹伯特利太太就对苏菲亚说:“把那‘矜持小姐’的性子丢在乡下吧,我敢担保,这种性子和城市是格格不入的。”[9]601此番话再次强调了矜持与纯真属于乡间的观点。当苏菲亚遭贝拉斯顿夫人暗算,差点被费拉玛勋爵强暴,之后拒绝勋爵的求婚时,姑妈魏斯通女士却责怪她不懂得攀附权贵,“有着乡下人那种怕见生人的傻想法”[9]897。初到伦敦的琼斯,寻苏菲亚心切,却被好色放荡的贝拉斯顿夫人诱骗。不同于道德严明的乡间,整个伦敦城的道德观念是模糊含混的,没有像奥尔华绥这样强有力的道德领袖来惩善扬恶。臭名昭著的贝拉斯顿夫人,不仅没人惩治,反而被人奉承:“尽管十分稳重的妇女绝不和她交往,可是整个京城都和她交往。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她是什么货色,然而彼此却心照不宣。”[9]806
《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中的伦敦在菲尔丁笔下也是万恶渊薮的腐朽之地。小说开篇,安德鲁斯刚到伦敦,他的同行兄弟便“竭力教唆他轻视他从前的生活方式,”他的衣着发式都变了,“可是他们没法让他学上赌博、咒骂、喝酒、以及城市里特多的各种时髦的邪恶”[8]16。在安德鲁斯第一次受到女主人的色诱之后,他写信给帕梅拉:“伦敦是个坏地方,友情是这么少,连紧隔壁的街坊彼此都不认识。”[8]22用威尔逊先生的话说,伦敦是一个“满是扰攘、喧嚣、仇恨、妒嫉和忘恩负义的世界”[8]234。
菲尔丁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阿米莉亚》中进一步揭露了现代化进程中伦敦城里的拜金与享乐之风。菲尔丁展示了贫穷的布思夫妇在一个“以金钱为纽带的社会体制中”[26]33的种种生活困境,批判了司法界、军队、监狱和教会的腐败,也深度再现了城市生活的各种“时髦的邪恶”。小说开篇,布思因救人反被巡夜人抓住,送至治安官处审判,糊涂官判糊涂案,无钱行贿的布思含冤入狱。在谈到布思出狱的条件时,狱长交代了监狱与司法部门层层的腐败利益链:“一定得花钱才行;因为在这种时候,人们都指望能给他们塞点钱。” “治安法官大人的书记员会指望得到相当可观的钱……但是警官是会指望得到点钱的,还有巡夜人一定得有一点钱;然后是双方的律师要有结案的费用”[11]170。军队贿赂成风,有钱人的子弟就能受到重用,而像布思这样为国家立了功劳的人却不能得到提拔。在金钱至上的伦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呈现出卡莱尔所论述的 “现金联结”(cash-nexus),不再能够相互信任。布思夫妇在伦敦结识的“朋友们”表面上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关心,有的甚至慷慨解囊,实际上却是各自心怀鬼胎,一度将这对夫妇推向毁灭的边缘。詹姆士少校与某高贵勋爵的慷慨举措掩藏着邪恶的淫欲;嘘寒问暖埃丽森太太、借钱给布思的特伦特上尉竟是勋爵的皮条客;就连与阿米莉亚相知相惜的贝内特/阿特金森太太都利用勋爵对阿米莉亚的爱慕为丈夫谋私利。小说中,藏污纳垢的酒馆、赌场与假面舞会是伦敦社交的重要场所,而监狱则是这部小说中最为核心的象征。在小说覆盖的时间里,布思一直断断续续地遭遇监禁,即便是他出狱后,监狱外的社会仍犹如一个无形的大牢房。[3]254
菲尔丁在在严肃批评伦敦城的各种罪恶的同时,仍将乡村想像为远离和对抗罪恶和腐败的希望之地。当布思夫妇最终以高贵的品质抵御住伦敦的一切诱惑和罪恶,苦尽甘来,继承了阿米莉亚母亲的遗产之后,他们选择远离纸醉金迷的伦敦,重返简单朴实的乡间,在那里享受着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布思回到乡下六个星期后,曾去伦敦偿还了所有的赌债;他在那里只呆了两天,然后又回到乡下;此后,他从没有离家远出三十英里之外。”[11]633
菲尔丁的小说继承了英国田园诗学中乡村纯真与城市宫廷腐败的对照这一主导型母题,小说中的伦敦是充满诱惑和欺骗的道德荒原,而乡村则是孕育“善”与“真”的希望之地,是矫正腐朽的宫廷和城市生活弊端的道德良方。
菲尔丁的三部小说《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弃儿汤姆· 琼斯的历史》与《阿米莉亚》从三方面继承了英国田园诗学中乡村礼赞。首先,小说的整体和插入叙事都沿袭了田园诗学“离城返乡”的退隐叙事模式。其次,菲尔丁的小说也传承了英国田园诗歌对本土阿卡狄亚(乡村庄园及农舍)的美学、伦理及神学赋值。小说中“天堂府”的风景描写继承了英国田园诗歌中的如画美学范式,呈现英国乡村“参差多态”的美丽景致;“天堂府”与多部小说中的村舍饱含着英国田园诗学中乡村化的美德与纯真;乡村在菲尔丁小说中还彰显着国教会宽容派笃信上帝与基督教的神性思忖。同时,菲尔丁的三部小说继承了英国田园诗学中城乡对比这一主导型母题。乡村中总有以身作则的伦理权威和道德领袖惩恶扬善,是孕育“善”与“真”的希望之地,而京城伦敦却是滋生罪恶的是非之地,是缺乏伦理权威和道德感的精神荒原。菲尔丁的小说传承了古老而持久的西方田园传统,将英国乡村呈现为与城市对立的美德之地与安乐之所,对十八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引领了之后表现乡村生活理想的作家如奥斯丁、乔治·艾略特、狄更斯、哈代及劳伦斯。
[1] Lodge,David.The Art of Fiction:Illustrated from Classic and Modern Texts [M].New York:Penguin Books,1992.
[2] Squires,Michael.The Pastoral Novel:Studies in George Eliot,Thomas Hardy,and D.H.Lawrence[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4.
[3]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4] 姜士昌.田园诗的本土化——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乡村书写[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66-171.
[5] (美)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M].马海良,雷月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 Gifford,Terry.Pastoral[M].London:Routledge,1999.
[7] Squires,Michael.Pastoral Patterns and Pastoral Variants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J].ELH,1972(1):129-146.
[8] (英)亨利·菲尔丁.约瑟夫· 安德鲁斯的经历[M].王仲年,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9] (英)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M].萧乾,李从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10] 韩加明.菲尔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出版社,2010.
[11] (英)亨利·菲尔丁.阿米莉亚[M].吴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2] Baldick,Chris.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Z].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13] Abrams,M.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Z].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14] Watt,Ian.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57.
[15]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1760-1800[M].张箭飞,韦照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6] 张金凤.永恒的空间,变迁的内涵——《好兵》与英国乡村庄园文学传统[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5):65-70.
[17]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8] Mayhew,Robert.William Gilpin and the Latitudinarian Picturesque[J].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2000(3):349-366.
[19] Yi-Fu,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20]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1] Moynahan,Julian.Pastoralism as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in English Fiction,1800-1928:From a View to a Death[J].A Forum on Fiction,1972(1):20-35.
[22] Squires,Michael.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as Modified Pastoral[J].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1970(3):299-326.
[23] (美)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M].胡志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4] (英)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M].胡淑陈,冯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5] 杜鹃.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6] 范存忠.英国文学论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毕曼
I106.4
A
1004-941(2017)06-0157-07
2017-07-18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玛格丽特福勒女权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w083) 。
廖衡( 1984- ) ,女,湖北宜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田园文学。朱宾忠( 1963- ),男,湖南郴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