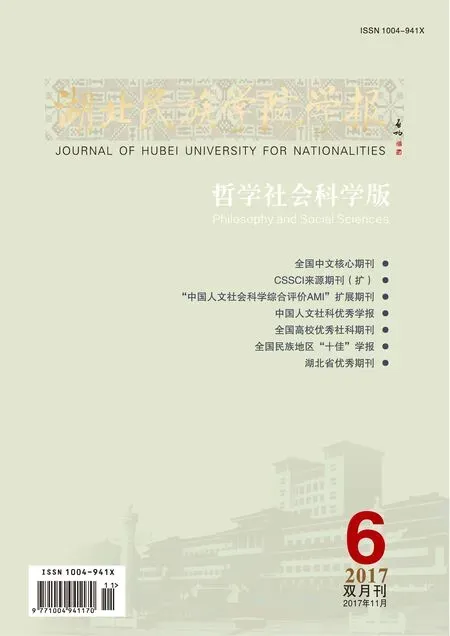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故事新编》的荒诞性研究
骆贤凤,段灿灿
(1.湖北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2.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故事新编》的荒诞性研究
骆贤凤1,段灿灿2
(1.湖北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2.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故事新编》中存在着显著的现代主义荒诞性特征。鲁迅通过对传统人物形象的颠覆性重塑展现荒诞,原本高高在上的神、英雄、民族脊梁、历史先贤从圣坛之上走入寻常的现实生活,他们因无法挣脱繁琐的尘世而叹息,为了生存而四处奔忙。故事将原本存在于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高大人物置于残酷的现实世界,使他们受困于凌厉的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荒诞感。小说叙事的荒诞性与鲁迅的存在主义之思密切相关。
鲁迅;故事新编;荒诞性;存在主义
要对《故事新编》作整体把握,先要从鲁迅的创作思路谈起。《故事新编》从开始写作到完成,鲁迅花费了13年的时间,他的创作心态自然处于一种动态而不稳定的状态中。这一点,从他创作《故事新编》的缘起与思路中就可以窥见。在创作第一篇作品《补天》(原名《不周山》)时,鲁迅本来是希望采用弗洛伊德学说解释人和文学的起源,然而在看到了胡梦华对汪静之《蕙的风》中某些爱情诗的批评后,他的创作思路就起了巨大的转变。关于这一转变,鲁迅是这样描述的:他仿佛看见“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双腿之间出现”[1]。从此,他对《故事新编》的创作仿佛就由“认真”陷入了“油滑”。所谓“认真”,就是鲁迅原本设想的以弗洛伊德学说解释人和文学的起源;所谓“油滑”也就是指《故事新编》中对神话、传说和历史的演绎。鲁迅对于这样的转变存在一些不满,但他又说自己“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也许暂时还有存在余地”[1]。由此可知,鲁迅的创作心态存在一定的矛盾性。鲁迅对《故事新编》的创作从“认真”陷入“油滑”,体现在故事文本中就是严肃庄重性的减弱与现实批判性的增强。原本的宏大主题被取代,鲁迅结合创作时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将历史、神话中的人物置于卑琐无奈的现实中,使《故事新编》的文本呈现出一种荒诞的色彩。因此,荒诞性是《故事新编》一以贯之的风格,它又体现了鲁迅的一种思考方式,即存在主义的思考。 因此,本文将从《故事新编》显著的现代主义特征——荒诞性入手,从人物、情节、环境三方面对《故事新编》的荒诞性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归纳其荒诞的营造与体现,并探讨其与鲁迅的存在主义之思的关系。
荒诞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西方。在文学中,广义的“荒诞”是一个美学概念,它较为宽泛,包含幻想、奇异、古怪、荒诞可笑、无稽之谈等多种含义。狭义的荒诞则是在西方现代社会和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审美价值类型,它的本质含义是不合情理与不和谐,以怪诞、变形的形式表现荒诞不经的内容。荒诞和喜剧不同,喜剧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相悖引人发笑,但荒诞的形式与内容相符合,因此荒诞不可能让人笑。荒诞和悲剧也是不同的,因为“荒诞展现的是与人敌对的东西,是人与宇宙、社会的最深的矛盾。但荒诞的对象不是具体的,无法像悲剧和崇高那样去抗争和拼搏,更不会有胜利……荒诞传达出一种更深沉的不可言说的悲,反映出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与基本情绪”[2]。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对荒诞的定义如下:“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3]加缪对荒诞感则是这样解释的:“一旦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4]这些对荒诞的分析,是在西方现代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讨论的。《故事新编》的荒诞性则是通过鲁迅对古今时空界限的消弭,对宏大故事背景中残酷现实的描写而展现的。
一、对传统人物形象的颠覆
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故事新编》将已经固化的传统人物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塑,使神人性化、使英雄世俗化、使民族脊梁普通化、使历史先贤漫画化,并以此来展现荒诞。
(一)神的人性化
《故事新编》将古代神话故事进行改编,使原本高高在上的神具有了人性色彩,使神人性化。比如《补天》中女娲造人的缘起是“伊”实在无聊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在神话故事中往往神秘莫测,在《补天》中造人的起因则是女娲的一时兴起。女娲因为实在无聊才开始造人以打发时间,这样的设置使得女娲蜕变为一个普通人,而不再具有神话中那种身为人之母的神圣性。当她发现自己造的“小东西”“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么包了身子”,有的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时,她便“诧异而且害怕的叫”,皮肤起了“栗”。当听见这些学仙的道士叩头请求赐仙药的时候,她被闹得心烦,“颇后悔这一拉,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祸”。广阔天地间,作为人之母的女娲因为造人、补天等事件忙乱不堪,困苦不堪,发出了两次“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的叹息,然而作为其子民的人要么请求她赐仙药,要么用“人心不古”“颛顼不道”这样的话回应女娲,又或者是重复女娲的话作为回应,神与民众的隔阂可见一斑。《补天》中最精彩的描写出现在第二部分,也就是《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的“古衣冠的小丈夫”出现的部分,这也是《故事新编》之写作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女娲补天时,那“古衣冠的小丈夫”“顶着长方板”,以“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的理由来责备女娲,见女娲不以为意,便“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这样的描写,无疑深刻地表现了女娲作为神却不被其子民理解的无奈,也狠狠地讽刺了像“古衣冠的小丈夫”一样满口礼义的人物。
女娲的形象在神话中是高大的、神圣的、具有崇高的神性色彩,然而在《补天》中,她像普通人那样行事,像普通人那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原本使女娲形象高大光辉的造人事件,在《补天》中却成了让女娲忙乱而困苦,不禁发出两次叹息的俗事。女娲为造人、补天而疲于奔波,但她的子民却没有一个理解她,神与民众之间存在深深的隔阂。更有甚者,“古衣冠的小丈夫”以所谓的伦理道德标准批判女娲,这样的人物,既可笑又可恨,也是鲁迅对现实中这种人物的一种强烈的讽刺。
(二)英雄的世俗化
与传说中的英雄形象相比,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将英雄形象的光辉性抹去,对英雄人物进行了世俗化的处理。比如《奔月》中善射的英雄羿,不得不为生存奔忙,他绕了三十里路去打猎,只得到三只老乌鸦和一只射碎了的小麻雀,为此不得不看妻子嫦娥的脸色,因为家里一年到头只吃“乌鸦的炸酱面”,而外面全然不像当年“野兽是那么多”。往日的英雄陷入了生存的窘境,使他成为英雄的是他高超的射术,而令他陷入生存窘境的也是他高超的射术,不可谓不悲凉。当他再次拿出射日弓和三支箭时,目光“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让人联想起他往日的英姿,然而这次他射的不是烈焰之日,而是清辉之月;射的不是海味山珍,而是爱妻嫦娥。从一个英雄退化到一个无法挽留妻子的丈夫,这场面已经足够悲凉,然而月亮只是一抖,“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损伤。
(三)民族脊梁的普通化
《故事新编》中对大禹这样的民族脊梁式的人物进行了普通化的处理。《理水》中怀着拯救天下苍生的伟大信念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和“文化山”上终日饱食、 讨论着家谱等无聊问题的学者们形成鲜明对比。大禹历尽磨难寻出的正确的治水方法却被一群腐朽的官员阻挠。“文化山”上的学者、高官厚禄不顾百姓安危的水利局官员和身处困境而不自知的民众均是鲁迅笔下讥讽的对象。然而躬行治水的大禹自回京后,态度也有了改变,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被腐朽的官员同化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于是出现百兽起舞、凤凰纷飞的太平之景,看似欢乐的场景中却深含着鲁迅先生的无限哀情。
(四)历史先贤的漫画化
历史先贤的人物形象与神的形象一样高高在上,《故事新编》则大胆地对历史先贤人物进行了漫画化的处理。《采薇》以一个“吃”字把“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拉下了圣坛,故事题材取自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在《采薇》中周武王灭商建周后,伯夷叔齐便决定“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到华山去以野果和树叶度日,他们还幻想着会有苍术和茯苓可以吃。然而“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奉行天搜”的强盗让他们只能逃去首阳山。入山之后的第一件事仍是吃——寻找食物,经过一番探索,两人将薇菜作为主要食物,还发展出许多做法“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文中还用烙饼的张数表现时间,用烙饼的大小判断时局的变化:如“约莫有烙十张饼的时候”“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功夫”“这不平静却总是滋长起来,烙饼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来了”。这样的设置表现了伯夷叔齐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中心事物,那就是吃。于是,他们计量时间要靠烙饼,判断时局的动荡也要靠烙饼。然而,伯夷叔齐本是舍生取义之代表,文本中却描述他们与食物的密切关系,令他们为了生存而奔劳、困窘,讽刺感油然而生。这样的两个人在首阳山苟且偷生着,最终被小炳君府上的婢女阿金姐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么!”羞得只得饿死。一个普通的婢女很难说出这样的话,她的话当然是从她的主人小炳君那里学来的,发出这种议论的小炳君不过是一个投机倒把、见风使舵的所谓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伯夷叔齐之死,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然而听到那婢女阿金姐的鹿奶故事,便“深深的叹一口气”,“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了不少”,即便有时想起伯夷叔齐,也觉得他们不过是贪食鹿肉的人,由此卸下了心理负担。鲁迅没有对伯夷叔齐二人所坚守的“义”之做明确评价,只是一味表现二人的困顿,让他们在代表生存的“吃”与代表信念的“义”间苦苦挣扎,将二人崇高的传统形象颠覆于卑琐的生活,却把判断的权力交给了读者。对传统先贤的漫画化处理还展现为《出关》中“呆木头”似的老子,《非攻》中成功救宋却被“募去了破包袱”的墨子,《起死》中满口哲学道理的庄子。这些不同于传统历史先贤的人物形象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观感,那么鲁迅为什么对这些传统形象进行改写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应该源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孔孟老庄、墨子等先秦诸子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在创作过程中,鲁迅看到了这些传统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便通过语含褒贬的描写,展现了他个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境遇的理解。
二 、通过情节展现荒诞
通过情节展现荒诞是小说叙事的一种重要手法,《故事新编》也不例外。首先,《故事新编》有着完全不同于神话的情节设置,比如《补天》中女娲为了补天奔忙时,她的子民非但不帮忙,反而冷笑、痛骂,甚至咬女娲的手。女娲造人是宏大的场面,然而她造出的人却只顾进行无意义的争夺。故事的高潮出现在“顶长方板”的“小东西”出现在女娲两腿之间的时候,那样一个小东西却以“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的理由来责备作为神的女娲。他的渺小与女娲的伟大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话迂腐得令人发笑,表现出现实生活中先驱者牺牲自我,普通民众对先驱启蒙者却并不理解的状况,先驱启蒙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明显隔阂。这样的故事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的另一部作品《药》,一边是为民众牺牲的革命者夏瑜,一边是为了给儿子治病而选择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两者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隔阂,民众对于先驱者是无法理解的。《奔月》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神话和逢蒙杀羿等传说与高长虹攻击鲁迅的现实事件相结合,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发出高长虹对鲁迅的攻击之语,将战斗性和批判性巧妙地融于故事文本之中,荒诞感和讽刺感十足。在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中,嫦娥奔月是为了升仙,而在鲁迅的《奔月》中,嫦娥却是因为受不了每天吃“乌鸦的炸酱面”而选择抛弃后羿。
其次,《故事新编》中的故事多以出乎意料的故事结局达到荒诞的效果。《补天》中女娲为了补天耗尽精力而死,忽而禁军到达,在“最膏腴”的女娲的肚皮上安营扎寨,还改换旗号为“女娲氏之肠”。伟大的先驱者的牺牲没有受到民众的重视,反被利用。《理水》中朴素实干的大禹治水回京之后,态度有所改变,开始注重祭祀和法事的排场以及上朝和拜客时的衣着。商家的恐慌消除,市面不受影响,于是“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这皆大欢喜的结局真的如此美好么,未必如此!以乐景衬哀情,才是鲁迅先生的本意。《非攻》中的墨子在成功救宋的归途中,没有众人的欢呼与来自宋国的慰问,一进入宋国就被搜检两回,又被“募去了破包袱”,“淋得一身湿”而鼻塞了十多天。英雄的不受重视与不被理解,可见一斑。
另外,《故事新编》中新奇的时间线索也为荒诞的展现起了作用。一种是显性的,比如《起死》中的杨大本是商朝时期的人,言语间却冒出“保甲”“圜钱”的宋朝、商朝的词汇,时空混乱,尽显荒诞色彩。另一种是隐性的,比如《出关》中老子为了出关竟不得不讲学和撰写讲义,但他的学问不被关尹喜之辈理解,讲义被放在了充公物品的架子上,他学说的价值是由五个“饽饽”的价值确定的,关尹喜之辈还在讨论这五个“饽饽”给得值不值。老子不被重视,他的学问也并不被理解,他的学说只能用俗世中一些事物的价值来确定,他的存在被世俗的现实的眼光打量,他处在一个看似古典实际现实的世界中。
最后,《故事新编》的细节描写透出的价值观也增添了小说的荒诞性。比如,《奔月》中往日的英雄因为高超的射术遭遇生存的窘境,每日只能吃“乌鸦的炸酱面”,还要看妻子的脸色生活;《采薇》中用烙饼的张数表现时间,使得平凡的食物与具有高大形象的英雄圣贤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英雄圣贤们走下神坛,成了为食物而困窘而奔波的普通人。
三 、通过环境描写展现荒诞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古今杂陈、虚实相映的艺术世界,故事“将神话、历史与现实融为一炉”[5],给人以强烈的时空交杂感。
文中自然环境的描写增强了故事的荒诞性,有利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补天》中女娲出场时的宏大场景,“粉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睱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6]“粉色的天空”“石绿色的浮云”“血红的云彩”“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如流动的金球”一般的太阳、“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为女娲的女神形象做了侧面烘托,天空是粉色的,云彩是血红色的,浮云竟是石绿色的,与众不同的色彩令女神的出场显得神秘而独特。接着,女娲只是伸了一下懒腰,天空就忽然变成“神异的肉红”,看不见她所处的位置,她的一举一动都能令天地间发生奇妙的变化,足见女娲形象的神秘与高大。女娲在补天时候的场景则是“仰面是外邪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这既是女娲补天的真实场景,又是对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一种反映,神话传说与现实状况相结合,生成虚实相映的艺术世界。《起死》中“没有树木”“遍地蓬草”的破败荒凉场景为下文颠覆传统的庄子形象做了铺垫。
化合物 3B07:质谱 ESI/MS(negative mode),m/z 246,[M-H]-。 1H NMR(500 MHz,CDCl3,TMS),δ为7.77~7.80(m,2H),7.28~7.31(m,2H),7.08(t,J=8.5 Hz,2H),7.01 (t,J=8.5 Hz,2H),6.59(br.s,1H,NH),4.58(d,J=6.0 Hz,2H)。
其次,《故事新编》中对英雄圣贤的居住环境进行了平民化的处理,减弱了英雄圣贤的光环,增添了他们的平民色彩,有利于对传统人物形象进行颠覆性重塑。比如,《奔月》中对后羿生活环境的一段描写:“暮霭笼罩了大宅,临屋上都腾起浓黑的炊烟”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极为生活化的乡村炊烟图,居住于其中的后羿也平添了一分平民气息,成了为生存而奔走的普通人。
四、荒诞性与鲁迅存在主义之思
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内涵是人先存在于世界上,然后才具有社会本质。“人首先存在着,首先碰到各种际遇,首先活动于这世界——然后,开始限定了自己”,也就是说人存在之初是不具有本质的,他的本质是随着世间的境遇而不断确定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原则是“自由选择”,即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依着自己的想法选择让自己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铸剑》中眉间尺从一个性情优柔、为父报仇的少年,进步成一个为千百万被害者复仇的战士,是因为他受到了宴之敖的鼓舞,这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需注意的是,“存在主义确立于1930年代的德国思想界,在40年代才被移植到了法国,并没有痕迹表明存在主义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传到了中国,非但如此,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中,甚至找不到‘现实存在’这个词语”。[7]因此,我们并不能说鲁迅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我们只能说鲁迅具有一些存在主义的思考,而《故事新编》就体现了鲁迅的存在主义的思考。
下面以《铸剑》(原名《眉间尺》)为例进行分析。“前文本”[8]简单地讲述了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故事新编》则对眉间尺的性格特征、心理变化和替父报仇的过程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尤其是“黑的人”与眉间尺的对话、三头相咬、识别王头、出丧的场面,或壮阔荒凉或气势宏大或滑稽可笑或热闹杂乱,但都深藏着创作者的深沉意味。眉间尺是一个“优柔性情”的刚满十六岁的孩子,文本开头他面对一只小老鼠,在拯救还是毁灭的选择中纠结,仿佛让人看见哈姆莱特的影子,他们同样年轻,同样具有“优柔的性情”,同样在青春年少时担负起替父报仇的命运,同样面对一个强大黑暗的仇人。若按照莎士比亚的写法,眉间尺似乎是不能不失败的,因为他的命运,也因为他的性情。但在鲁迅笔下,眉间尺遇到了神秘冷酷的“黑的人”——宴之敖。他深知眉间尺复仇的命运与注定的失败,他是一个纯粹的复仇体,他说“仗义、同情”是“曾经干净过的东西”,“现在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他不过是要为眉间尺报仇。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带着眉间尺的头用法术诱骗王靠近金鼎,甚至砍下自己的头助眉间尺复仇。“前文本”中简单叙述的“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的部分在《故事新编》文本中被鲁迅扩展出识别王头的过程和宏大的出丧场面,最终结果是三头合葬。
如果从“三头合葬”的结果出发,认定复仇是失败之举,不免有些片面了。文本中对复仇的具体表现出现在“两头相啮”“三头相咬”的部分,宴之敖的歌曲烘托了神秘气氛,场面恢弘壮烈,复仇精神尽显,鲁迅对于这纯粹的复仇行动显然是赞扬的,不然也没必要费许多精力对复仇的具体过程和恢弘气氛作细致描写。眉间尺为了复仇牺牲了自己,宴之敖为了助人复仇也牺牲了自己,这牺牲都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用牺牲换取了替千万人复仇的大义,使自己获得了对不公正勇敢抗争的复仇者的生命意义。总之,他们以自我选择的方式获取了生命意义,在看似荒诞的人生境地中展开了反击。
况且,荒诞这一主题将目光集中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困境,似乎是非理性、反人文的,然而正是由于荒诞的存在,我们才能注意到人性的衰落与荒芜,从而维护人性与人文精神。鲁迅的《故事新编》用荒诞性的表现手法,将笔触深入到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中,通过对传说、史实、神话的“新编”,融入了个人对生命存在之虚无、孤独与困境的认识,深切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高扬起了积极抗争的战斗旗帜。
总之,《故事新编》的荒诞性与鲁迅存在主义之思是一致的。研究发现,在荒诞性的表象之下,鲁迅表现出了积极反抗的人生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9]
[1] 鲁迅.故事新编(插图本).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2.
[2] 王晓旭.美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5.
[3] 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57-358.
[4]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7:6.
[5] 徐顽强.英雄末路的悲叹[J].人文杂志. 1995(1).
[6] 鲁迅.故事新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3.
[7] 山田敬三,魏雯.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5):100-104.
[8] 祝宇红.“故”事如何“新”编:论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9] 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89.
责任编辑:毕曼
I246.8
A
1004-941(2017)06-0146-05
2017-03-17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的翻译伦理研究”(项目编号:11XYY004)。
骆贤凤(1970- ),湖北咸丰人,土家族,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和中西比较诗学;段灿灿(1994-),河南濮阳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化与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