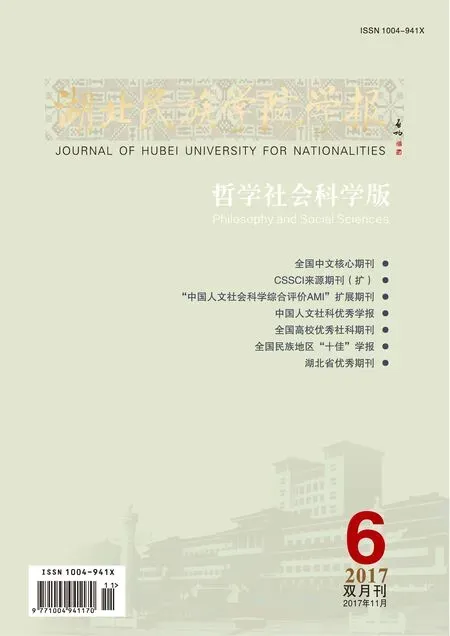记忆、认同与空间
——马萨达要塞①的神话建构
王宁彤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记忆、认同与空间
——马萨达要塞①的神话建构
王宁彤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遗产空间的生产和再现是不同主体的意义建构过程,不仅构成了群体对世界的表达,而且也构成了群体本身,涉及“我们是谁”的问题,是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共识性陈述。以色列马萨达要塞曾一度成为现代以色列的象征,犹太民族形象的核心。在历经锡安主义运动、以色列建国、中东战争和现代旅游发展等不同阶段,马萨达“神话”也跟随历史经历了富有意味的变化。
遗产; 神话; 认同; 空间生产; 多元话语
马萨达,一个被遗忘了近两千年的孤山,在圣地耶路撒冷往南100公里的地方,一侧是濒临世界最低点的死海,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犹地亚沙漠(Judea Desert),就在这片壮观的大地风景之中,一座同样壮观的陡峭孤山拔地而起。这是希律王为自己建造的一个曾经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同时也是一个曾经奢侈无比的宫殿。希律王喜欢享受的天性和对巨大工事的迷恋,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另一座令人惊叹的杰作。要塞上建有37个22米高的碉堡,周围是1500米长的双层围墙,城堡中央建有12个蓄水池,每个的容量都在4000立方米以上。在公元67年爆发的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大起义中,这个统治者建造的坚固城池成了起义者最后抵抗的要塞。起义失败后,犹太人从此离散到世界各地。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这段“历史”被“发现”和“挖掘”,并被视为犹太民族的传统精神和国家的象征——“宁为自由死,不为奴隶生”。马萨达一度是以色列新兵入队宣誓的地方,他们在这里高呼:“马萨达永不再陷落!”以色列国歌也注入了这种回归和争取自由的精神:
只要心灵深处,尚存犹太人的渴望。眺望东方的眼睛,注视着锡安山冈。我们还没有失去,两千年的希望。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
一、马萨达的个人体验
笔者曾两次访问马萨达,每次都对这里的景观感到深深的敬畏。几千年的时光过去了,从死海到沙漠,马萨达的景观有着天然的气魄。
要塞最高处的哨台,在那里只需原地转动360度,就能看到最全最远的景观,一侧是黄土漫漫的沙漠,另一侧就是死海的最窄处,因为海平面降低,已经露出了河床,不远处就是约旦边境。沧海桑田,时间改变着死海的地貌。眼前近处是要塞上的大片废墟,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但是根据残留的断墙和屋基,人们依然能“看到”缺失的部分,那是罗马时代的拱门、哨台、浴场、装饰着马赛克以及有着鲜艳图绘的宫殿,还有宽大的屋舍、巨大的粮仓……
如今这里是以色列著名的旅游胜地,从绝大部分的旅游指南和网络资讯上,我们能看到大致是这样的英雄主义叙述:
公元67年,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统治,在当时巴勒斯坦其他地方的犹太起义纷纷被平复之后,上千犹太起义者和他们的家人退守在易守难攻的马萨达要塞,其中犹太斗士只有200多人。罗马人包围了马萨达,犹太义士以少抗多,经过了三年漫长的抵抗之后,罗马人决定进行火攻。马萨达的起义者认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这时起义的领导者伊利亚沙·本·亚尔(Elazar Ben-Yair)进行了一段演讲:“天亮时我们将不再抵抗,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所爱的人一起高贵地死去。让我们的妻子没有受到蹂躏而死,让我们的孩子不做过奴隶而死吧!把所有的财物连同整个城堡一起烧毁。但是不要烧掉粮食,让它告诉敌人:我们之死不是因为缺粮,而是自始至终我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最后960个反抗者选择了集体自杀:每个男子亲自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再抽签选出十名勇士作为杀死其他男子的执行者,所有人紧抱妻儿躺在地上,接受战友的剑刺。最后剩下的从10名勇士之间选出一人,杀死其他男性,放火烧毁城堡,最后自杀。第二天清晨,准备大战一场的罗马人攻入城内,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寂静比遭遇抵抗更让人心寒:他们历经数年攻下的,不过是一座死城和遍地的尸骸。悲剧发生在公元73年。
马萨达的故事合法性和真实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教授的研究上,他在60年代对这里进行了考古挖掘。伊丹·坎贝尔(Etan Campbell)是马萨达国家公园的主管,在这里工作了四十多年,他曾经有幸接触过亚丁教授。当我们站在哨台高处眺望要塞残留的建筑时,伊丹感慨地说:“我当年是作为志愿者来参与考古挖掘工作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亚丁教授的描述,当他走进这些房间时,四周没有一个人,房子还是保留原来的样子,就像人们两天前刚刚离开。衣服还在角落里叠着,用来做饭的盆还在那里放着。2000年了,这里就像是被冻住了一样。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来这里,这里没有水,罗马人建造的斜坡道攻城的时候已经把当年的储水系统破坏了。即便是贝都因人也会尝试在更高的山上放牧,而不会在这里。所以这里就这样冻结了几千年。这是世界唯一一个保存完整的罗马要塞。”
2001年马萨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给出了如下的陈述:
犹太逃亡者占领了这个马萨达的要塞,最后时刻的悲剧事件让它变成了犹太文化认同,以及,更普遍地说是人类持续反抗压制,争取自由的象征。[1]
二、约西佛斯和马萨达
让人吃惊的是,至今为止,马萨达这段历史的记录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公元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斯·约西佛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争》(TheJewishWar)。在这本书的最后,约西佛斯阐述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立场:“为了那些希望了解罗马人如何同犹太人进行战争的人,我们要用最精确的文字写下这段故事。它的文学成就必须留给读者评说,但就其真实性而言,我毫不犹豫、完全自信地声明,从写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除了对真实的追求,我未有他图。”[2]263
我们暂且把这本书看成是研究唯一可以考证的文本,这样,可以通过一个相对固定的坐标比较一系列的差异:他在书中是怎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它和后来以色列的国家叙事又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在不同的阶段约西佛斯的叙述怎样选择性地运用在国家叙事上,其中选择了什么?又忽略了什么?为什么?
(一)起义者的身份: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战士?
公元67年开始的犹太人起义主要的领导者是几个激进的犹太团体,其中奋锐党人(Zealots)和匕首党人(Sicarii)最为出名。约西佛斯的描述中很清楚地指明是几个极端团体把犹太人带入了注定失败的反抗。虽然约西佛斯并没有对这两个团体有过严格的区分,但是在他的描述中匕首党(Sicarii)的称呼却是始终如一的。
匕首党的名字是从Sicah(小匕首)来的,这是匕首党团体的特殊武器,专门藏在袍子里,在以耶路撒冷为主的地方刺杀亲罗马统治的犹太人,以及反对他们的人。“匕首党被认为是最早宣传和实践政治暗杀的团体。刺杀的方式很简单,把匕首从后脖子插入脑部,或者从后背直接插入心脏,被刺杀者死亡前甚至不会发出一点声音。用近代词汇来说,这是一种有预谋的谋杀和恐怖行动。”*2011年,笔者访谈,曾是以色列国家古迹部负责人的希腊裔以色列考古学者V.Tzaferis所获信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起义爆发后,也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部分在伊利亚沙·本·亚尔的带领下逃到了马萨达,他们一直留在马萨达直到最后。不曾预料在近两千年后,他们成了国家神话的主角,众多子孙膜拜的先烈。
在后来的马萨达叙事中,很少提及匕首党,而是统一地用了奋锐党(Zealots)。“zeal”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自由”,似乎更符合后来故事的叙述方向,这和约西佛斯的叙述方向有着本质区别。
约西佛斯不支持这个团体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眼中,以匕首党和奋进党为首的极端分子“最终,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上帝审判了他们,他们罪有应得。”[2]254而在后来的国家叙事中,以上这些完全没有被提及。
在《犹太战争》中,约西佛斯用非常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很多战役。在其他被罗马围困的地方,罗马人都遇到了猛烈的抵抗,而马萨达并没有任何抵抗的描写。[3]13他们没有正面反抗过罗马军队,也没有抗战到最后一刻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选择了自杀。这多少说明了匕首党习惯于刺杀和恐怖活动,当正面对待罗马军队的时候没有作战的精神。[3]13事实上,马萨达的围困大概也就七个星期的时间。[4]而不是国家神话叙事所描述的:起义者以少抗多,在三年的时间里,英勇地抵抗了罗马士兵猛烈的进攻。
(二)自杀与英雄主义叙事
在《犹太战争》中,约西佛斯频繁使用的字是“谋杀”而不是起义者的自杀。他认为正是极端的犹太分子让马萨达的妇孺老人成了他们极端行为的人质,虽然最后约西佛斯用了比较富有文学描述力和想象力的文字给予了960个他的同胞以一种高贵的“死亡”,但是这并没有背离他对这种行为不赞同的态度——至少是值得痛惜的,而不是英雄主义的。
从传统的犹太律法来看,无论自杀还是谋杀都是违反律法的。除了上帝以外,人没有权利把上帝给予的生命拿走。这似乎也印证了为何纵观大流散历史,在犹太文化和传统的传播中,竟然没有任何作家对马萨达有过丝毫的提及,更不用说是赞扬了。
关于“自杀”的问题,也成了后来国家神话建构中,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部分。以色列人自己也是对此存有疑虑的,甚至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色列国父,第一任总理。也曾质疑用这个以自杀终结的故事来教育年青人是否足够智慧。萨马拉·古特曼(Shmaria Guttaman)是最早对马萨达的故事感兴趣并推动深化建构的主要人物,他在1942年组织的第一次马萨达研讨会中这样说:
我希望带给我们青少年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有战斗到底的意志,而不是去死。我们已经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刻,当隆美尔逼近我们国家的时候,那我们就把马萨达变成一个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象征。[5]
此后,马萨达的英雄叙事渐渐成形。它选择性地整合了约西佛斯论述中的某些部分,那些与“英雄叙事”不相符的部分退出了叙述,或是通过解释被消解。“自杀”成了面对没有选择时的英雄主义元素——为了自由,放弃生命而战斗到最后一刻!
(三)对犹太起义的态度
在罗马人对耶路撒冷的围城开始之后,归顺了罗马的约西佛斯知道抵抗的时间越长,对犹太人和圣城越不利。他沿着城墙向里面的同胞喊话:
你们不仅在与罗马人对抗,也在与上帝对抗! 罗马人进来后,既不会洗劫圣城,也不会冒犯你们神圣的土地……你们这些顽固的傻瓜们!扔下你们的武器,可怜一下你们正在走向毁灭的出生地吧!有人愿把这一切付之一炬吗?[2]200
耶路撒冷陷落几年后,百公里之外的马萨达,犹太人遭到了最后的攻击。罗马人用撞击器砸不开马萨达城墙,决定改用火攻。火刚起来,一阵强北风吹来,罗马人有些惊慌,大风从上面把火吹向他们,眼看着他们的攻城锤就要被火烧毁,罗马人陷入了一片绝望。突然,好像天助一样,风势又转,往相反的方向使劲地刮,把城墙变成了一片火海。上帝的确是站在罗马人一边的。[2]255约西佛斯把罗马人的胜利归于上帝的安排,这些被国家奉为英雄的人在约西佛斯看来正是引火上身的疯子。
以上的历史叙事和后来的国家叙事之间显现出巨大差异,或许我们有必要先来换位思考一下约西佛斯本人的身世和作为历史学家的客观性问题。弗拉维斯·约西佛斯(Flavius Josephus)的原名叫约瑟夫·本·马蒂亚斯(Joseph Ben Matthias),他在加利利一带领导犹太人起义失败后,归顺了罗马,并接受了当时的罗马将军提多的姓。而关于犹太战争的历史记录,其实是他受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的委托,用希腊语写给罗马上层社会看的。为此他被安排在皇宫花园别墅里以便安心写作。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因为战功而享受帝国津贴,甚至在和“不尽如人意的妻子”离婚后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在归顺后一直到去世,约西佛斯都没有回过巴勒斯坦。和《布匿战争》《高卢战争》一样,《犹太战争》一书也反映了罗马人自己对战争的解读。
作为一个耶路撒冷祭司的后代,约西佛斯热爱耶路撒冷,尽管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是“耶路撒冷的叛徒”,并且终其余生都为这种指责而困扰。有学者推断约西佛斯写《犹太战争》这本书也是有他个人的议程:即证明罗马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在为自己投靠罗马开脱的同时,宣称自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忠诚的犹太人。 “我必须容许自己为民族惨遭悲剧而哀伤。就像圣殿的毁灭者提多·凯撒所说的,犹太的毁灭源于内部的纠纷,罗马人并无意放火烧圣殿,是犹太人自己任命的统治者将他们引进了耶路撒冷。”[2]2
那么约西佛斯对马萨达的记述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围困发生的时候约西佛斯其实已经回到了罗马,所以他的写作基本都是来源于二手材料——回来的士兵和幸存者的讲述,以及罗马人的官方记录。马萨达的考古挖掘之后,人们发现很多地理的事实证明了约西佛斯的描述。比如罗马军营的外形结构,关于围攻的坡道,以及要塞本身的细节等等。
但是约西佛斯又是如何具体地知道在马萨达要塞内部发生的事情的呢?他所描写的伊利亚沙在鼓动众人自杀的长达十几大段的著名讲演,有着生动形象和具体入微的描述,匀速念下来需要半个多小时,让人无法排除约西佛斯的描述结合了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并加以文学化的修饰……
一个如此充满矛盾的古代犹太历史学者,他的《犹太战争》却是目前发现的关于马萨达历史的唯一记述,这本书虽然几个世纪前就被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却一直没有受到犹太人的推崇。敏锐的犹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神话,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更是批评它。后者对匕首党人面对罗马人的围攻采取自杀的态度轻蔑甚于敬畏。
那么马萨达的神话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被推到高处的呢?我们有必要打开一段段历史的褶皱来观察其空间的结构和建构。
三、马萨达的重新“发现”
在近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里,从地理学意义上看,马萨达只不过是众多山岩中的一座,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838年,它第一次被两位美国旅行家发现。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中,伴随裼安主义和回归热潮的兴起,马萨达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开始逐渐被“挖掘”。
在1920年代,作家Yitzhak Lamadan写了一首以“马萨达”为名的诗,诗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马萨达永不再陷落”。[5]马萨达象征着犹太人大批地离开一直让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地方,同时也被用来作为群体反抗与奋战的象征。教育部门看到了这首诗有着很高的教育价值,就把它整个编入了1930年代的犹太教科书里。马萨达的诗被这个年代的人们看成是一个在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可以认同的象征至高点,在当时是对整个时代的以色列犹太人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
1930年代,马萨达是巴勒斯坦左翼锡安主义青年团体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徒,而是世俗主义者,对回归圣地,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家园充满着理想和激情。马萨达神话的出现正好符合了犹太起义者的意识形态和自我认同,连接点是种族的、宗教的和历史的,它为一个新形态的犹太国家认同提供一个稳固的、史诗的基础。[3]87他们年轻的思维正是接受了马萨达神话,并且帮助他们准备好战斗到最后,甚至做最终的牺牲、殉难。
1942年,强悍的隆美尔的北非军团快速地从西逼近开罗,而就在越过埃及西奈半岛不远处,一个犹太小群体被法国的维希军队包围在叙利亚北部,从心理上和地缘政治上来说,没有更好的故事更符合马萨达被罗马人的围困了,也“没有比这个故事能更好地表达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恐惧。在那里居住的人认为——这会是犹太人最后的反抗吗?被改变的马萨达的故事创造了犹太人面临致命危险的气氛”[6]。二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压迫屠杀,促使了大批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在1948年建国时达到了高潮,虽然此时的马萨达已经是一片废墟,但是这片废墟甚至比它矗立的时候还要伟大——马萨达神话已经基本成型了。
从地理空间来看,马萨达几乎是被沙漠围绕着。在犹太文明史上,“沙漠”是一种精神净化的媒介和隐喻:摩西出埃及,跨越西奈半岛茫茫沙漠,历经了种种考验磨难来到应许之地。犹太大流散之后的一千九百多年,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又回来了。已故前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曾这样形容建国后的状态:
当时的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土地很贫瘠,沙漠化,到处都是充满蚊子的沼泽,周边是不太愉快的环境,阿拉伯邻居们不喜欢我们的到来。我们没有水资源。唯一的水资源是从约旦河来的,但那里的水更多是公共用水而不是灌溉用水,我们真是一无所有,需要从无到有地去创造……我们唯一拥有的是自己,还有开创的精神。摩西自己就是个不满足现状的人,他领导犹太人离开了埃及的城市,他们需要跨越沙漠。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每一个人,如果你想成就什么,你就必须经历沙漠,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在你的心里。*2011年11月笔者对西蒙·佩雷斯的访谈。
空间结构不仅构成了群体对世界的表达,而且也构成了群体本身,这是按照这种表达来使它本身有序化。[7]布尔迪厄曾强调空间生产是不同主体的意义建构过程,这是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属于”谁的一种认知。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事件——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8]在以色列建国的意识形态下,马萨达旅游景观的文化资本被推动成为一种符号资本,进而成为社会的资本。
建国后,以色列迎来了各国犹太移民的热潮。马萨达的景观空间增加了新的内容:旅游必去的景点;新移民爱国主义的旅游和教育基地。这些来自他乡的新犹太移民,需要连接过去的犹太记忆,并且快速地融入新国家的建设和认同之中。马萨达的旅行计划经常要求前来体验的人必须在太阳升起在死海海平面之前爬上山顶。当淡黄色的沉寂的沙漠开始苏醒,这些可能是从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伊朗、德国等不同地方回来的犹太移民,站在这座孤山的顶上,迎着早晨的微风,手上的电筒还在闪烁,这个神话故事将在这样静谧神圣的情境下被讲述……游客的质疑很容易被这种如朝圣般的仪式所抛开,强烈的国家团结意识在此达成。
作为认同的空间,遗产的再现与传播是“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的重要观念是“传播的仪式观”[9]。空间的生产和文化传播其实是通过符号体系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10]。遗产,可以被同时视为提供地方记忆的公共平台以及供游客凝视(tourist gaze)[11]的旗帜,国家或民族标志的传统文化成为了被展示、“被发掘、被规范以及被公共地肯定”[12]。马萨达提供了一种想象和确认,是自我认同的公共陈述,给人们以“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的同一个民族,拥有同一段历史”的想象,即使这个共同体中的“我们”大多数一辈子都无缘相见。
60年代的考古挖掘,更是让马萨达神话进一步找到了科学的“印证”,并以客观真实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
四、马萨达考古挖掘——破碎物证的拼贴
马萨达最主要的一次考古发掘是1963-1965年间在伊格尔·亚丁(Yigael Yadin) 教授的严密督导下进行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观察:考古产生的解释和神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破碎的物证如何被拼接?事实和神话该如何区分?
在亚丁的学术生涯之前,他的身份是以色列军队参谋长,是建国战争和建国后的军事行动的核心人物,之后成为了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在马萨达进行新兵宣誓的仪式也正是军人兼学者的亚丁的建议。马萨达的挖掘当时成了国家的大事件,不仅以色列军队参与了考古项目,从资源、设备到人员给予了巨大协助,而且有几千名志愿者参与了工作。
考古学者艾瑞克·梅尔斯(Eric Meyers)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作为义工参与了当时的考古挖掘工作:每个马萨达的义工最后都被给予了一枚大奖章,正面写着“我们要成为自由的人”,反面写着“马萨达将永不再陷落”。*美国历史频道制作的纪录片《马萨达》中的访谈。可以看出,这是一次预先设定主题和目标的考古行动。马萨达的考古有着比约西佛斯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有神话,而这个神话是基于对约西佛斯的解释之上的。挖掘者是在用考古来迎合神话,而不是对应约西佛斯的叙述。[13]257
而从马萨达的考古成果中我们也发现,它和约西佛斯的史料记载在众多方面呈现出差异。例如迄今为止并没有在马萨达挖掘出多少尸骨,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考古开始至今,也只是发现了28具人类尸骨,其中的25具是在离要塞几百米远的山脚边,另外的3具的发现地点是在要塞上的北宫——考古学者标记为“地点8”的地方。不少学者质疑马萨达的叙述,为什么其他的900多具尸体不见了?而坚持马萨达神话的人认为:时代久远,不可能从现存中找到完全的物证,争论至今没有结论。
我们所能做的,是从亚丁当年在媒体报道和公开论述中对“地点8”的历时性解释中,来观察这种解释是如何逐渐被逻辑化和合法化地发展出来的:
其一,1965年以色列探索学会出版了希伯来文的资料,亚丁写道:我不能确定这几具尸骨是否是留下的最后斗士和他的家庭,他杀了自己的家人并且点火烧了这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就是伟大的起义者的尸骨。[13]262其二,1966年亚丁用英语出版了一本关于马萨达的书也有对“地点8”这三具尸骨的描述:其中一具尸骨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性——可能是马萨达的一个统帅……不远处的台阶上是一具年轻女性的尸骨……第三具尸骨是一个孩子的。无疑,我们的眼睛所能观察到的是马萨达的一些防卫者。[14]其三,1971年,在犹太文物百科全书里,亚丁写道:这些尸骨无疑是马萨达一个很重要的统帅和他的家人。[15]其四,在1973年(在一次关于马萨达的讲演中)这些尸骨变成了:一位很重要的统帅的遗骨,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就像是约西佛斯所叙述的那样……[16]
可以明显地看出,亚丁对马萨达的解释源于国家“神话”的框架体系,正如他接受采访所说的:“所有的发现都蕴涵着、见证着人和土地的契约和联系。从这个角度看,考古研究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维度……‘考古学’在我看来是加强希伯来人的自我意识。”[17]有趣的是,有关马萨达的考古报告在近30年后的1991年才迟迟出版,而且正好是在亚丁去世之后。当时完全没有被提及的一个发现是,在与人类尸骨中一同被挖掘出来的还有猪的骨头。这对于犹太文化绝对是一个禁忌。有些学者认为,用猪来祭奠更多是罗马人葬礼的传统,重新的研究发现这些尸骨可能是非犹太人,而且也有可能是罗马士兵给予的军事葬礼。
当宣布这些尸骨是失陷的起义者后,以色列决定给予他们国家最高英雄规格的葬礼。这个仪式成了当时令人瞩目的国家事件以及重大的媒体事件。“选择性地运用集体记忆的一个方法,完全出于功利目地压制一些细节,同时高扬另一些。因此,记忆不必是可靠的,但必须是有用的。人们现在诉诸这种重构的记忆,尤其是集体的记忆,以赋予自身一个连贯的民族身份、一个民族叙事以及在世界上的一个位置。[18]167可以说马萨达的挖掘,考古研究者承担起了国家主义规划的重担。
五、神话的衰微与话语的多元
“神话创造”的一种经典模式就是对共同记忆的建构,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曾指出: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记忆绝非机械性的。时间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19]马萨达神话承载了对时间和记忆的选择,“人们与它建立关联,改造它、修饰它、争论它。这是作为个人,民族或是国家的认同被创造和被讨论的方式之一”[20],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修整、重构甚至消亡。
在完全超乎预期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新的历史古迹(如哭墙、大卫墓等)变成了以色列的组成部分。马萨达的神话开始褪色,新的神话开始被创造。在随后的两次中东战争之后,国家开始减少了对马萨达的宣传力度。以色列人本能地懂得“马萨达境遇”——在中东,被阿拉伯国家所包围,前途未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觉到:马萨达孤立于世界的情形与以色列的国家情形有着不言而喻的相似,人们不希望这段没有确切实证的历史影射自己的未来。另一方面,庞大的集体自杀并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英雄故事。
这时候,部分的马萨达神话还是在以色列社会和政治中存在,而部分大众和媒体已经把马萨达的神驱逐出了教科书和官方仪式。[21]曾经是部队新兵们庄严宣誓的地方,现在偶尔能看到工程部队前来做典礼,伞兵等部队已经改在了西墙宣誓,最简单的一个原因,耶路撒冷的西墙已经成了犹太人的另一个“神话”,不仅比马萨达更容易去到,而且有着更多当代以色列的相关性。
约西佛斯的原始叙述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媒体中,甚至是出现在马萨达的导游书上。随着以色列旅游业的逐渐发展,把马萨达作为崇拜对象的一代开始消散,以色列年轻一代对国家遗产更是显示出不关心的态度,在1995年和1998年,以色列本国游客数量减少了26%[5],马萨达从闪着神圣光芒的“国家圣地”变成了一个更多是开放给国际游客的“旅游胜地”。因为和死海临近,在众多国际游客的旅行计划中,马萨达成了死海旅程中的一站。在笔者两次实地访问中,看到的都是旅游大巴来往运输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其中还包括一些虔诚的各国基督教团体,在山顶热泪盈眶地唱圣歌。
1981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马萨达》,因为故事基本忠实于约西佛斯的著述,这部影片很久以来都没有被以色列政府推崇。但是笔者在2011年底造访的时候发现,影片的片段已经出现在了马萨达景区的宣传片中了,宣传片截取了电影原片中最有动感和表现力的几个场景:罗马军队对耶路撒冷气势恢宏的围城以及最后抵抗的部分。大量的逆光仰拍镜头,抽象的光影,巧妙地绕过了微妙的立场问题,创造出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情感空间——当罗马人进入了马萨达要塞,在烟火四起的寂静中,看到的是遍地的尸体……影片长长的特写反应镜头给了彼德·奥图尔*英国演员,曾成功扮演过阿拉伯的劳伦斯。所扮演的罗马将领——富有棱角的脸、蓝色闪烁的眼睛、难以言说的复杂表情,让人印象深刻。对于很多并不计较历史具体语境和故事细节的游客来说,眼前的影像已经足够满足他们这趟探险之旅了。尤其是当他们走出景区观影厅,亲临马萨达现场的时候,相信很多片段会随视线所及浮现眼前,成为残垣断壁的注解。
富有意味的是,在马萨达的礼品店里发现了关于马萨达的唯一影像资料,就是美国历史频道所制作的纪录片《马萨达》(Masada),这是一部观点多元的纪录片,而绝大部分观点是世界各地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对马萨达神话的解构和质疑。一个国家级的旅游景点,出售如此开放的影像资料,似乎也说明马萨达神话语境的失效。
从80年代开始,建国初期国家主义的偏狭叙事开始出现了松动。建国时为了建立犹太人和新土地的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口号之一是“没有土地的人民,来到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 )——显然忽视了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在接下来的第四、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人越来越觉得这些阿拉伯“他者”的存在将会是以色列未来的一部分,需要彼此合作来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人对空间拥有合法性的斗争,“必然涉及重叠的记忆、叙事和物质结构……它至少列示了两种记忆、两种发明、两种地理想象之间格外丰富和紧张的冲突”[18]170~171。
一股反思的力量首先是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里发起,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学者”团体,他们开始对国家叙事、中东战争、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反思,希望能够找到更加公平可行的阿以和平共处途径,国内的话语空间产生了宽容、内省、批判的多元声音。
虽然在近代国际媒体中,以色列的形象总是军事强硬派的作风,但是在国内的社会公共空间,却容纳着不同的声音。这股反思的浪潮带来的是对自我认知的修正,即便它还处在主体空间的边缘,依然是社会公共空间向健康平衡发展的重要部分。
旧的神话褪色了,可能会有新的神话诞生,马萨达从一个地点,到成为一段历史,一个象征符号,再到成为一种旅游景观——观看它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形成了各自的“所指”。黑泽明在电影《罗生门》中传达了相似的哲理:对于同一件事,人们倾向于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观看。是否可以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有立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观看。一个健全社会空间并不是排斥神话的存在——因为它对于一个社会认同符号的形成来说,似乎有种普遍的机制,而且几乎存在于每个国家社会——重要的是这个空间是否足够多元,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以色列文化反思者认为,一个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有不同的叙述,而且这样的叙述越多,它所提供的事物形态才会越全面,越接近客观。马萨达国家神话的构建和消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例证。
[1] Monastersky,Israeli Icon Under Fire[J].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2,December 6:24.
[2] 约西佛斯.犹太战争[M].王丽丽,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3] B.Y.Nachman,The Masada Myth:collective memory and mythmaking in Israel[M].Madison,1995.
[4] Roth,Jonathan.The Length of the Siege of Masada[M].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1995:87.
[5] Klara Palotai:“Masada-the changing meaning of a historical site/archeological site in the reflection of a nation’s changing history”.[2017.8],http://artscapeweb.com/masada.html.
[6] Barry Schwartz,review on The Masada Myth:collective memory and mythmaking in Israe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2.No.4.Jan,1997:1222.
[7] (法)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概要[M].英国:剑桥出版社,1977:163.
[8]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
[9]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10] 陈力丹,张晶:传播:以文化的名义——评《作为文化的传播》[EB/OL].(2013-02-02)[2017-8-06].http://www.doc88.com/p-010966574545.html.
[11] John Urry.The Tourist Gaze[M].Sage,1990.
[12] (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0.
[13] Nachman Ben-Yahuda,Excavating Masada:The Politics-Archaeology Connection at Work[M].Selective Remembrances:Archae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Commemoration,and Consecration of National Past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14] Yadin,Yigael.1966a.Masada:Herod’s Fortress and the Zealots’ Last Stand[M].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54.
[15] Yadin,Yigael.Masada,Encyclopedia Judaica[M].Jerusalem:Keter; New York:Macmillan,1971:1007.
[16] Nachman Ben-Yahuda,The Masada fraud,the making of Israel based on l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utumn,2003,Volume 18:1.
[17] Bamache Magazine[J].March 18,1969:12.
[18] (美)爱德华·萨义德.发明、记忆、地点[A]∥陈永国.视觉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 (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
[20] Barbara Bender,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M].Berg Publishers,1993:3.
[21] M.Pfaffl.Narratives of Bravery and Fear:The Masada Myth[J].Forum Archaeology,2010(Ⅵ):55.
责任编辑:陈沛照
C953
A
1004-941(2017)06-0066-07
2017-09-01
2008年-2011以色列外交部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合作的以色列专题纪录片系列拍摄项目。
王宁彤(1973-),女,浙江永康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人类学、视觉传播、跨文化传播。
① 马萨达要塞(Masada Fortress),罗马统治时代巴勒斯坦的一个要塞,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色列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