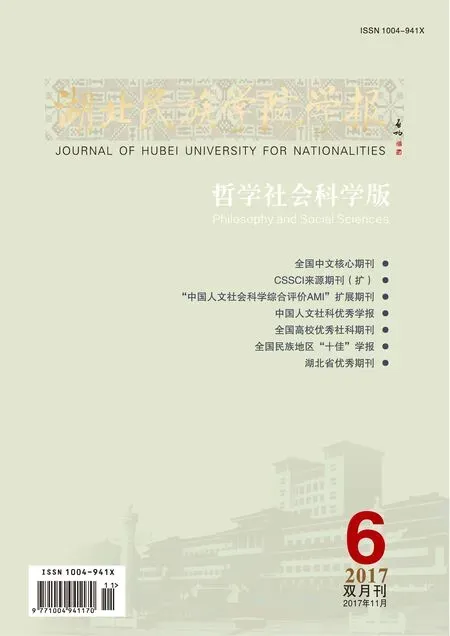论克里斯蒂娃的“世界主义”探索
罗昔明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论克里斯蒂娃的“世界主义”探索
罗昔明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作为以互文理论崛起于国际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克里斯蒂娃,其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未得到深入的探讨。1990年代克里斯蒂娃经历了从早期侧重文本理论到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国际议题,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中,她密集探讨陌生人的身份归属问题及由之延伸的国际政治议题,并将之与共同体、好客、宽容等概念相连结,构筑起一种善待异质他性的论述。以这种论述为基础,克里斯蒂娃聚焦于全球跨疆界文化流动中所蕴含的矛盾空间与内在差异,旨在挖掘善待他者中的政治维度,积极回应全球政治时局的关切,寄望建立一种“过程中的国家”,探求另一番全球化图景。
异质性;启蒙批判;陌生人;过程中的国家
善待“陌生人”及相关的世界主义论述,是克里斯蒂娃20世纪90年代十来年间集中关注的重要议题。除了《我们自己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1990) 《没有国家主义的国家》(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1991)《欧洲主体的危机》(Crisis of the European Subject,2000)等主要著述外,加以一系列访谈、演讲、其他相关重要文献,克里斯蒂娃都持续集中讨论“陌生人”的身份归属及善待问题,使自己日渐僵化的理论学说,重焕生机。然而,相关议题并非是其90年代的全新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她1974年的著作《诗歌的语言革命》。书中她将诗歌的语言阐释与文化批评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加以融合,僭越它们之间的边界,迂回侧击地触及了一些时局问题。正如古柏曼所言,70年代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罗兰巴特以及克里斯蒂娃等人以法国为中心,展开对绝对权威、暴力、主体性方面解构式审思,最终要瓦解的是集权体制与族群暴力的同质化统合思维结构。[1]257但克里斯蒂娃早期侧重拆解文本符号,并未直接探讨政治议题,最多可称之为政治的回响。到了90年代,克里斯蒂娃以明确的政治论述切入异质他者的身份及其在跨疆界文化流动中的归属问题,僭越文本符号导向疆界与单纯哲学式的理论话题,落实到现实跨疆界流动中移民、难民、身份界定问题的关切,触及全球进程中的边缘议题与同质化的论述暴力,强调了此前基本上不正面涉及的共同体、国家政体、宽容、人权与公民社会等宏观政治议题,藉以回应新近的世界政治时局问题。本文的目的,一方面阐明克里斯蒂娃有关善待陌生他者发展脉络的论述,另一方面探讨她如何以这种论述切入全球跨疆界文化流动中的政治议题,藉此考察其“过程中的国家”的世界主义想象。
一
“陌生人”,一般是指相对于一定的个体、社群、民族或国家而言不熟悉的“非我(们)”的他者,包括异乡人或者异域者。而在克里斯蒂娃看来,“陌生人”不仅存在“自我”外部,而且也指向隐藏于自我内部深刻的存在感中的陌生性。她的陌生人观念,是从弗洛伊德1919年德语论文《怪怖者》(Das Unheimlich)中的“怪怖”(unheimlich)一词生发而来。
弗洛伊德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unheimlich的词义及用法。他发现与之相关的词“heimlich”的意义很有趣,它由两层相反的涵义构成,其一是指熟悉的、亲密的、友善的,其二是指未知的、陌生的、被隐藏的。这个具有双重内涵的词,不断在两个对立的意义端点来回滑动,可能走向彼此的反向面,其第二层涵义又衍生出变体形式“unheimlich”,即未知的、令人恐惧不安的,其中“un”被视作压抑、唤起怪怖的表征。弗洛伊德将怪怖与无意识结合起来,指出所谓的神秘、陌生的事物,实为原初那些被压抑元素的重现,它们因压抑和隐藏机制的作用变得神秘与陌生,又因冲破压抑机制而复返。克里斯蒂娃进而认为,那些潜藏或抑制于无意识之中的原初欲望与对异质他者的陌生感与恐惧感,也将在我们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再次暴露出来。所以可以说,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一定程度上即是与我们自身被隐藏抑制的无意识层面相遇。这样一来,重新构建他者以及我他伦理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藉此,克里斯蒂娃指出弗洛伊德“教会我们发掘自身内部的他性”,并指出“外来性是我们身份隐藏的面孔”,“是生活在我们之中且是我们自身神秘不可思议的陌生性”,“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2]191
弗洛伊德向我们表明,我们内在自身是双重的,同时我(主)与他(客)的身份也是可以互换的。克里斯蒂娃将弗洛伊德对“怪怖”词源学的考证,上升为一种抽象的方法论。在重构自我的基础上,她力图重建他者,进而重构我/他(主/客)伦理关系,其旨趣超出通常的文化和社会根源层面,致力于从本体论层面深入探讨陌生他者的身份归属问题。既然我们是自身的陌生人,他者一定也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自身内在的他性,我们也能接受来自异质他者的陌生性。换言之,“如果我们都是自己陌生人,就没有陌生人”[2]192。没有了陌生他者,那么宇宙中的人类就是一个完整、和谐、平等的大家庭。藉此,我们尝试去界分我他、主客角色间的关联,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了。如克里斯蒂娃所表明的,这个身份内在的陌生性能够发掘一个新的伦理和政治。
克里斯蒂娃将对我们内在陌生性身份的思考,重点拓展到某一社群或民族国家中的“自我”与外来他者关系的伦理与政治实践之中,并强调当内部的异质性显露之时,或者当我们与异质他性相遇之时,我们要会协调这种异质性和怪怖感,消除敌对、尊重差异,友好开放地与之共处,让陌生性从根本上不再有疏离感,这也是克里斯蒂娃解构自我、重构我他关系独具的意义。
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路径,克里斯蒂娃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抹平了我他之间的权力不均衡的本质化分野,最终强调的是“他者”不是受“我(们)”宰制的补充或臣服物,而应得到友好接纳。基于此,她重点追溯了古希腊文化、圣经、中世纪文学以及17世纪政治实践中善待陌生的外来他者的传统印记。克里斯蒂娃首先从圣经世界的训诫出发,寻找善待外来者的源头。圣经世界中常见以上帝名义要求“爱他如己”,不能因“非我(们)观念”而排斥外来者,不论是陌生来访者还是外邦人,都是“同胞居民”中的一员。圣保罗将这种宗教信仰带入希腊社会之中,构建起“超越民族与国别的外来者社区”。[2]66类似的,克里斯蒂娃以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为例,表明善待外来者成为古希腊生活方式中潜在的道德规范。她还从思想层面考察了斯多葛学派的“视为己有”哲学逻辑,为善待外来者观念何以生成寻求理论依据。她认为“视为己有”观念,将人类整体视为一个城邦,其秩序受理性法则支配,并强调人类整体最终追求的都是至善,人的善不仅在于个体自然状态的满全,更在于将他人的善视为己有,尽其所能地为他人服务,一视同仁地帮助同类。她进而指出,这种合乎本性的“视为己有”,展现的是一种“和解原则”:“通过成功吸纳所有人(不论血统、肤色或种族),将他们融入我们自身之中……挑战了分立的城邦政治结构,代之以人类第一个包容的世界主义新思想”[2]57。克里斯蒂娃进而思考的是,善待外来者是否仅为一种宗教现实,亦或仅仅是社群中的美德式情谊,而“没能成为一种政治现实”[2]61,又怎样转化为真正的政治需求?克里斯蒂娃将关注的角度转向世俗政治领域。她认为,伴着17世纪国家政体主权意识的兴起,为了政权的稳定,宽容和善待外来者差异性的美德,已初步走向自由权利和国家治理领域。她以思想家洛克为例,坚信斯多葛学派的“和解原则”延续到洛克这里,代表着“人类取得的持续进步”[3]29。
克里斯蒂娃追溯了贯穿整个18世纪之前善待外来者(特别是异域来者)的文化印记。从当代角度论之,善待外来者的思想和行为实践,无论是从习俗规范、宗教信仰,还是最终植根于世俗政治的民主信念之中,归根究底,都是我们在直面国际环境中愈加紧张、冲突乃至暴力时,所付诸的“宽容”问题,这正是克里斯蒂娃所要质疑的层面,也是她分析善待外来者问题中政治干预要突破的地方。
事实上,宽容这一概念的实质,展现的是一种将“先在”占据一定领地或所属物的优越感置于他者之上的强权逻辑。此中,“宽容的门槛”成为一个关键词汇,其意义在于善待的限制性,它表明友好接纳外来他者到何种程度,进而相应地将自己的所占之物(包括领地)适当地扩及他者。这种宽容观念,在克里斯蒂娃善待外来者的相关论述中被解构、被搁置。她在我他/主客相互僭越与置换关系的基础上拓展,探讨平等和谐的论述,抛弃排斥、压迫非我的文化生态,使主人(主体)走向对异质他者的开放。这样一来,善待他者实践中所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界分变得模糊不清,牵动了异质他者的文化“身份”,经由我他彼此互动的过程,呈现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主人的“我”善待外来他者,更应是主客的意义连结于异质他性的身份之中。这里,身份不应视作崇拜的对象,恰是处于对他者开放状态中问题的对象。
克里斯蒂娃并非仅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诠释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鉴于当下频繁的移民、难民等异域流动带来的身份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冲突,试图寻找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进而延展到跨疆界流动中的“世界公民”身份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这对于当今传统的国家概念正经历着强烈的挑战而力图重构之际,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克里斯蒂娃深刻认识到,只有重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等、关爱、“分权”的伦理关系,展开世界主义伦理的可行性探索,才能破除身份问题的迷途与偏向、跨越宽容的门槛,从而走向真诚善待、和平共处而不加以排斥、敌对。在此基础上,她寄望一种政治层面超越宽容门槛的“创造”,将这种宽容伦理最终走向与政治的结合。
二
重返启蒙时代的世界共同体构想,成为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深入探讨善待他者议题的关键参照系。因为启蒙时期的欧洲,面对层出不穷的宗教纷争、政治冲突,启蒙思想家们希望跨越各种异质性的鸿沟,采取一种容忍的态度,与异质他者“永久和平”共存共处。这为克里斯蒂娃将善待他者问题落实到世俗政治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她审视当代跨疆界流动中不同种族、国别、社群之间排斥分裂乃至对立冲突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一个特殊且有益的视角。启蒙时代昭示着一种相对成熟的世界主义框架萌生浮现。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思想家的世界主义及善纳他性论述,对克里斯蒂娃来说尤为重要,牵动其对世界主义政治议题的思考。
当追溯一种令人信服的世界共同体架构的源起时,克里斯蒂娃强调“孟德斯鸠是我的起点”[3]17。孟德斯鸠认为一定社会形成的管制方式、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气候状态等特殊性,形塑了民族国家的异质性与总的精神。同时他指出人类的“社交性”(sociability)特点,提供了不同国家间交际与调和的基础。而当这种“社交性”充分发展时,“民族国家必须让位于更高的政治系统”[2]131,构建一种在社交性和总的精神基础上全球性的联盟组织。由此,国家在一种更宽松条件下持续运作并被重塑的同时,也指向由多价值构成的社区。
在孟德斯鸠看来,总的精神具有异质性、动态性以及被赋予了政治联盟涵义特性,它比民族国家精神更有利、更合理。因为扎根于总的精神基础上的人们,本质上是一种“同盟者而非公民”,人权比公民权更重要。克里斯蒂娃认为,它是“法国政治思想最具威望的创造之一”[3]53。但她也点出孟德斯鸠的世界主义与善待他者论述中的另一命题:“如果我知道什么是对我有用而对我的家庭不利的东西,我往往从我的思想中拒绝它,如果我知道对我家庭有用而不是对我的祖国有用的东西,我将试图忘记它,如果我知道对我的祖国有用而对欧洲不利的东西……我将视之为一种罪行。”[3]57这种等级划分系统,作为克服民族国家局限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表明,欧洲联盟才是他真正的潜台词。在《论法的精神》中,他甚至明确提出欧洲是一个国家的说法。对此,克里斯蒂娃评论道,“如果未来总的精神战胜民族-国家精神,这种多元的社区可能被命名为欧洲”[4]。
与之类似,卢梭的世界主义也体现了一种欧洲替代性身份。克里斯蒂娃在《什么是明日国家》中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在人民权利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强调人民权利先于国家政府而存在,人民拥有抗拒既定国家体制的权力。同时他将这种普世人权延展到国际环境去思考。在对战乱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反思的基础上,卢梭提出维护长久和平、自由平等的欧洲“大联邦论”,其隐藏的动机是从一种普世人权层面的国际主义立场转移到对欧洲他者的拒绝甚至可能是迫害,克里斯蒂娃认为这一思想其实隐藏在革命思想中。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世界主义图景虽未有详尽的阐述,但都深陷于顽固的欧洲化藩篱。藉由对这种局限的反省,克里斯蒂娃转向了康德,寻求一种真正面向全球的普世主义。
康德的《走向永久和平:一种哲学方案》一文,强调地球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都是地球的主人,任何人都有权在异国他乡受到友好款待。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没有人可以独占任何地区,“我们”的“本然”所属物并非完全属于“我们”,“独占”违背自然法则。因此在面对各种国际社会不断出现的迫害与暴力时,要搁置“先占为主”的观念,从家到国的层次,都应保持对他者开放,充分维护外来者的自由权利。这并非仅是一种美德品行或信仰,而是我们本然的义务和责任,亦如来访者也是地球的主人。
康德从同为地球主人的视域,表明所有人既是民族-国别的居民,又具“世界公民”身份,并强调要在“世界公民权”架构下以宽容的姿态建立起尊重外来他者的伦理责任:“所谓世界公民权的概念已不再是夸张的幻想或虚构的神话,而应该是国家或国际权利中的一个不成文的修正条款,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这种公共权利,唯有透过这样的修正条款,我们才能自豪地认为人类正朝向永久和平的目标持续进展。”[5]对康德来说,“修正条款”应成为国家在世界范围构成联系的必备要素和普遍规范。这种规范最终落实为一种“法律世界主义”,它在国家法和国际法之外寻求建立一种世界范围的“立法会”。这是一种松散的国家间的联盟形式,以和平、自愿的方式组织起来,在保障国家公民权的同时也要维护外来者的“世界公民权”。克里斯蒂娃指出,康德的这种法律世界主义,赋予人们一种全球框架下合法流动的权利,同时也能减少囿于自我或群体利益之间不和谐的“野蛮的和非法的自由”[2]293。
康德展现了一种跨疆界不分彼此善待外来者的姿态,而其中最吸引克里斯蒂娃的是,康德的论述中暴露出的“从自然法则到社会建制的滑移”的局限。她指出,也许对康德来说善待外来者似乎是普世且无限的,但外来者的长久居住权需要依赖国家间协定解决。可以说,从“同为地球主人”自然法则的角度,任何国籍的公民到其他地区都能以“世界公民”身份享受同等权利,但又受着国家主权下体制、法律、边界等人为制度的制约。概言之,康德的世界主义与善待外来他者论述,强调了国家之间的协定以及保障这种协定执行的力量(法律、武力等)。克里斯蒂娃充分肯定了康德“在伦理政治、普世法规和哲学术语层面的国际主义精神”,并赞扬他勾勒了一个全球视野的世界共同体美景。但当这类组织成为当下的事实(如欧盟、联合国等)表明这种联盟已经达成时,她又说:“在这种(康德)世界主义中,维护那些不同外来群体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实现。”[2]171
克里斯蒂娃在《我们自己的陌生人》中,通过检视普世人权与公民权问题直接回应了康德等人的世界主义理想。她指出,当今所言的人权观念,肇始于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观念,它牵涉到国家,外邦人、普世人性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毫无疑问,人权观念早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落实为明确的政治宣言,成为检验主权国家民主自由程度的一个标杆。但是克里斯蒂娃在认真审视人权宣言的条款中发现,它一方面提出人生来都是自由与平等的普世人权观念,但又强调这种自然天赋必须基于国家架构下运作,而且只有通过国家这一政治形式行使与保障这种普世化、抽象化的天赋人权。这里,概念明显出现了偷换。克里斯蒂娃指出,宣言第六条中的政治性建制概念“公民”实际上就是从早先第一条的朴素概念“人”置换过来,由此普世人权问题就转化为公民权的讨论,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个系统的内涵与外延都有着巨大的落差。
这一转化带来的落差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因为以国家政体为中心的限制就成为善待异质他者的障碍,具有主权的政体会设定一定宽容的门槛,从而制约践行善待外来者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可能直接成为暴力迫害外来者的人为机器,而往往忽视了还有很多地球居民颠沛流离,得不到国家的庇护,甚至有些人只能身处暴虐体制或无能政府管制之下。这种情况在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尤为突出,不断涌现的世界范围跨疆界的移民、难民潮、旧殖民地回流潮以及其他国际冲突,都引发了人权与公民权的矛盾问题。因此,克里斯蒂娃对这种转化持批判态度,实际上质疑的是人权议题被人为设限,作为人类政治体系行为主体的国家建制阻碍了世界主义理想前进的步伐,制约了我们对外来者的宽容和善待,甚至有时其本身就成为排斥、迫害外来者的直接因素。
康德等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是一种扎根于国家主权框架下的世界共同体想象,虽然突出了人权理念的普世性,希望通过国家间的约定,在无需一种全球政治实体组织的情况下,构筑和平结盟组织,藉以处理国际纷争,但仍不能妥善处理跨疆界流动中善待异域他者问题。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我们更重要的责任就在于,对至今仍束缚着我们省思的启蒙世界主义范型予以回应,谋求构建一种破解国家政体束缚的世界政治运作型态。克里斯蒂娃自视为康德世界“和平”观念的受赠人,但针对启蒙记忆的局限,积极探求突破与进步,一个层面上继承了启蒙记忆容忍、和平与普世人权的论述。她认为,陌生的来访者包括异域者都是“我们”的“同胞”。她在《欧洲主体的危机》中强调,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除了生物起源所连结的语言、宗教、习俗等特质以外,都拥有选择归属哪个社群的自由权利。[6]123另一层面上又寄望跳出启蒙世界主义观念的限制。克里斯蒂娃试图藉由“过程中的国家”的世界主义图景,重构主权国家与异域来者的扭结关系,形塑跨疆界文化流动境遇下更具动态性、开放性的互动范型。
三
克里斯蒂娃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主义著述紧紧抓住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外来异邦人或陌生人的国家是否可能?”[2]127这表明,当作为世界体系运作主体的国家政体成为世界主义理想持续进步的阻碍时,她寻求构建一种以无条件接纳他性为政治与伦理基点的全新世界组构模式。这种新模式,并没有彻底摈弃国家架构,而是将世界主义理想拉回到对国家框架的再审视,致力于重塑国家政治运作模式:究竟怎样的国家模式能够充分容许异质性(外邦人、陌生人、不同种族、不同社群等)自由涌现并能减少甚至避免可能引发的紧张与“内战”?
对克里斯蒂娃而言,社会实体具有过程性、开放性的激进政治性特征。比尔兹沃思(Sara Beardsworth)曾指出,克里斯蒂娃透过“过程中的动能” (transitional dynamic)这样的开放系统来探究社会实体,包容了每一个外邦人或陌生人的差异性,充分考虑到了面对公民社会不同类型矛盾冲突的可能性,确保每个个体或社群的独特性不会化约为普世观念,从而避免社会被一体化、集权化扩张或社会契约的暴力压制,也瓦解了封闭性的公民契约社会的根基。[7]在《什么是明日的国家》中,克里斯蒂娃明确提出了僭越国家主义新的“过程中的国家”模式,这是一种超越国家绝对制约的国际主义位置。
克里斯蒂娃的“国家”构想,深受海德格尔对polis这一古老词汇重新考察的影响。海德格尔强调,这一词通常被解释为城邦,并不十分确切,更合理的解释应是一种连结着特定历史实践的“此在”处所。后来汉娜·阿伦特发展了有关阐释,指出它是一个持续流动着的空间,人们通过每个个体的言说与实践行为集体性构成了这一空间,这种情况可以经由任意“此在”场域产生。他特别强调,它还是一种“出现”的空间,“我向他者出现,正如他者向我出现”[8]。克里斯蒂娃在此基础上,对这个概念予以更深层的拓展,将之描述为自由且多元的持续流动的公共言说空间,是我他/主客彼此向对方出现、相互进入彼此存在状态的处所。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无排斥、中转性的认同空间,涵盖了各种异质性的现代主体。藉此,她构建了一种激进的公民社会理念即“过程中的国家”:国家实体成为变动不居的、过程中公共空间,植根于言语与行动基础上,落实为语言实践的展开。人们聚居一处的集体言说与行动实践构成了这个组合空间,任何个体自身都在语言活动和行动实践中脱离私密的自我空间,经由叙述与行动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实践将自己呈现给他人,融入一个与他者共处的共同体空间,各种不同道德伦理、美学品格、宗教信仰、政治立场都参与其中,构建一种我他(主客)对话关系。这个空间不断向异质性开放,通过持续包纳异质性并不断做出相应的自我调适,型构了一种容许他性无尽涌现的政治空间。[3]41
克里斯蒂娃不仅将“国家”视为容忍种种面向论述的媒介空间,还强调国家是高度的文化表征符号,政治性国家运作模式要在语言与艺术的物质实践(文学活动、艺术创作、各类表演以及其他语言实践)框架中落实。克里斯蒂娃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政治简单视为社会治理问题,而应构建新的权威,将政治视为扎根于差异性、反单一化美学暴政的叙事形式。她指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感官都是复杂多元的,只能以不断重现的隐喻式语言方能寻觅其踪迹。它们并不会在政治叙事中消散,相反会经由隐喻式叙述而返归,从而构成了持续被不可化约的言说与行动填充的政治空间,并呈现去离感性的理性思考与满腹感官经验的日常生活二者间永恒的内部翻转更新状态。[6]47持续的语言书写与文艺创新过程介入政治性的公共言说领域,展露了诸种异质性各自的身份特性,型构了具有一定稳定性但又富有弹性的形塑空间。克里斯蒂娃将国家与文化概念画上等号,指出民族国家的文本书写中,主体性无法被同质化的国家性绝对主宰,常常可见的是各种尝试瓦解一致化叙述行为而具有批评讽刺距离的文字论述。这样曾被压抑的边缘记忆才能重新经由语言与象征系统释放自身并得以被接受和理解。换言之,只有透过实践反叛精神的文艺、哲思以及其他各种文本形式,历经文本中批判立场鲜明的主观经验时刻,书写的他性才能被激活,其内涵方可被理解。藉此,她认为国家空间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的聚合,铭刻着各种感官面向及多样他性的不同经验。[3]44这是一种连续延展的项目方案,构成国家表征体的不断更新、创造的状态。以此而论,不同的语言行为实践、剧场展演、文学书写与艺术创造共同型构了国家的公共空间,藉由叙述行为完成而非纯粹的语言本身。
可以说,克里斯蒂娃将弗洛伊德强调的自身内在的异质性,移植到语言构架下,并通过叙事展开的对话空间容许其充分出场,呈现的是异质性叙述空间成为政治性实践的意义表征。那些曾经被排斥或未知的各种具有感官属性的阴性他者,经由文字书写进入公共言说空间并不断涌现,获得和解与善纳。这也解释了克里斯蒂娃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以文化符号表征法国时,强调“母体”般的“源头”是必需复归却又必然从内部不断反叛翻转的对象,它是我们始终指向但同时必须分离的原初母体。这种批评思考的背后是其理论路径的转换起落。如果说她早期侧重以鲜明的左翼色彩处理集权性的同质化问题,倡导诗歌及其他文本形式上的革命性理论以侧面回应时局。那么到了90年代,她从revolt一词的本义反叛、翻转取代早期激进立场,转向主体系统内部对“同一”偏离、复返、重组不间歇的往复循环过程,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他/主客间对立甚至敌对的革命观,代之以彼此翻转互为主体的新型关系,暴露其内在不可化约的异质性不断涌现。这种更新置换的政治逻辑,破除了自我固着僵化的社会组构体系,揭露了自由的根源所在,充分展现了克里斯蒂娃90年代新的思想重心。
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中的国家”,是一种对未来进步社会的大胆构想,检视了全球跨疆界文化流动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以及不平等的“不均衡的过程”,彰显了自己所坚守的世界公民表征的要义,即倡导宽容、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与生活。这种肯定异民族、异文化的他性之价值的全球伦理关怀,强化了对那些曾被压抑的异质文化和弱势族群的伦理省思,凸显了跨疆界流动中的交互影响与重组。她在90年代后期的一次访谈中说,她所关心的并非怎样规训与压制,而在于绝对权威或同质化中所隐含驱逐异己的暴力。怎样才能解构这种规训及其背后潜藏的暴力,才能充分善纳那些被我们拒斥的异质他者。[1]18这种肯定他性、边缘性的伦理省思,不仅凸显全球文化情境下弱势他者所具有独特自主性与无限创造力,并且暴露了“主体”、霸权论述的排他性与暴力本质。
事实上,从克里斯蒂娃的善待他者论述可以看出,其观念深刻地连结着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正当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被排外氛围所笼罩,恰好也是欧盟渐趋正式成形之时,在面临着移民、难民以及谋职者等大量欧洲外来人员持续涌入时,其内部出现强烈的排外情绪,各国争相制定限制性律令,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法国国内的呼声尤为高涨,法国政府也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给那些移入者施加了各种限制。虽然这类政策备受指责,但排斥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另一方面,作为保加利亚裔法国人的边缘身份,使她体会到在公民权问题上他者的他性容易被中心扭曲、等级化区隔、被边缘化整合甚至抹杀。因此,作为既有着法国知识教育经历和背景,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边缘族裔的血缘身份,必然会深刻影响她对法国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态度。此时,克里斯蒂娃洞察了国家性,特别是法国的国家性明显地暴露在一个日益一体化和暴力化世界中的相关问题。她对法国日益凸显的国家主义、不同族群间的对立以及对外来者的敌视现象高度警惕,强烈抵制保守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势力。这构成了克里斯蒂娃上世纪90年代围绕共同体、公民社会与普世人权讨论的现实基点,藉以积极回应时代关切。
[1] Guberman,Ross Mitchell.Ed.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2] Kristeva,Julia.Strangers to Ourselve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3] Kristeva,Julia.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4] Anna Smith,Julia Kristeva.Readings of Exile and Estrangement.Basingstoke:Macmillan,1996:11.
[5]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26.
[6] Kristeva,Julia.Crisis of the(European)Subject[M].New Hampshire:Alpha Graphics of Pittsfield,2000.
[7] Beardsworth,Sara.Julia Kristeva:Psychoanalysis and Modernity[M].New York:SUNY Press,2004:171.
[8] Arendt,Hannah.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 amp;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198.
责任编辑:刘伦文
D07
A
1004-941(2017)06-0031-06
2017-02-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克里斯蒂娃的中国话语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202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克里斯蒂娃的中国话语研究”(项目编号:2015SJB829)。
罗昔明(1979- ),男,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