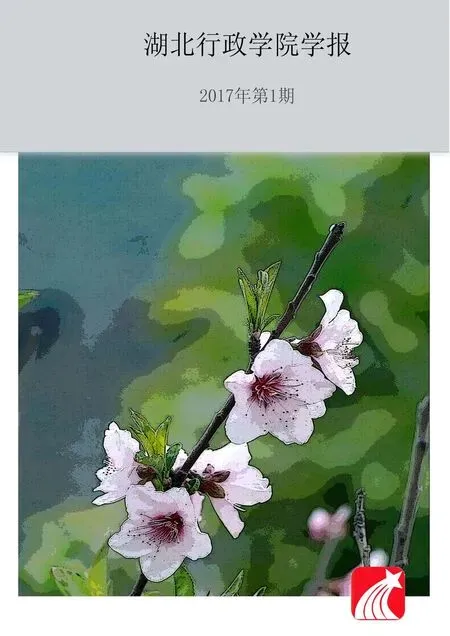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
——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韩瑞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学术综述·
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
——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韩瑞波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当前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环境抗争已成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国外环境抗争的研究重点是环境公正问题,而国内的研究热点则是环境抗争中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及策略。从集体行动理论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可以分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环境抗争;农民集体行动;政治机会结构;抗争话语;抗争心理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17.01.017
近年来,随着中国环境状况的加速恶化,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数量骤增。环境抗争又称“环境群体性事件”或“环境类群体性事件”,本文使用“环境抗争”这一提法。有关“环境抗争”的定义,学界众说纷纭,学者们的主要分歧之一在于环境抗争隶属于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我们把环境抗争定义为民众在遭受环境危害之后所采取的、旨在维护其在适宜的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权利的集体行动抑或个体行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聚焦于农民的集体行动。
就环境抗争的类型而言,大致可划分为两种:一类是污染型环境抗争,即环境污染已经酿成,民众对环境污染事件及其处理感到不满,但由于信访、投诉等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效果有限,随即转向暴力抗争这种极端方式;一类是风险型环境抗争,即污染尚未发生,因为对将来可能造成的污染表示担忧、焦虑、恐惧或愤怒,出于对环境风险的防范而导致的暴力抗争[1],诸如PX项目、核泄漏事件、垃圾焚烧设施等引发的集体恐慌与社会失序。
作为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受到“路径依赖”思维的影响,政府往往会将诸多集体行动的发生视为一种社会病态的产物,将集体行动造成的恐慌与失序看作是对稳定和政权的威胁。这种思维酿成的后果则是强硬的策略产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冲突与稳定在社会中总是如影相随,正如陈明明所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同利益要求表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2](P30-44)。因此,我们应将环境抗争视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以理性思维对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进行学理分析,正是本文试图完成的任务。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
(一)关于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
1.国外环境抗争研究重点:环境公正问题
当前国内外学界将各种理论范式用于解释环境抗争事件的成果已相当丰富。从国外学界的研究来看,环境公正问题始终是国外环境抗争研究的重点。环境抗争中的环境公正问题主要针对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种族和阶层应当享有同等的公民环境权,同时需承担同等的环境风险”[3],环境不公正意味着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或环境利益受损,在此情形下民众就可能通过集体行动的暴力来改变现状。还有的国外学者聚焦于环境抗争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这种互动具体地可以表现为“抗争——镇压”关系[4]或“动员——解动员”的关系。
2.国内环境抗争研究热点:集体行动发生原因与集体行动策略
就国内学界的研究而言,在探求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原因方面,学者们往往将其归结于企业、民众和地方政府之间利益的冲突,体制内的渠道无法迎合民众的诉求,体制外的暴力抗争成为维护民众权益的唯一工具。
也有学者着眼于环境抗争中集体行动的策略问题。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已形成诸多经典的解释框架。李连江提出了“依法抗争”理论[5];于建嵘指出中国的农民抗争已进入依法抗争时期[6];应星在对依法抗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反驳的基础上提出草根动员理论[7]。此外,农民的抗争策略还包括依势抗争[8],以身抗争[9],依情理抗争[10],英雄伦理[11],原始抵抗[12]和混合型抗争[13]等。具体到农民环境抗争的研究上,陈占江基于湘中农村环境抗争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呈现出遭受环境侵害的农民运用的“结盟”与“树敌”、“示弱”与“示强”、“依法”与“依势”、“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农民以争得政治机会、外部资源、伦理道义来增强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与合法性[14]。陈涛等人基于蓬莱19-3溢油事件的个案,指出山东渔民的环境抗争走势受控于农村精英的“造势”与“控势”能力。一方面,农村借助于“造势”策略(利用时势、推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等)来提高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控势”策略(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来防范体制外行为与政治风险[15]。
本文基于现有的文献以及近年来发生的环境抗争典型案例来解读农民集体行动的发生逻辑,旨在进一步丰富环境抗争中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在收集资料和整理文献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索环境抗争中的农民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本文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应该具有一定意义。
(二)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
集体行动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参与者是如何被动员的”。国外的集体行动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来解答这一问题。结构主义论认为,宏观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为集体行动的动员者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政治机会”[16]。资源动员论试图在中观的社会运动场域中寻找有助于提高动员效用、降低动员成本的人际网络和组织性资源等动员结构[17]。文化主义者聚焦于社会心理层面观察个体的微观动员机制,将集体行动视为某种文化现象或话语行动,通过运用框架分析理论来阐释动员者以怎样的方式建构话语体系来动员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参与者[18],或重新厘定情感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比如泰德·格尔提出社会怨恨理论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心理根源,其中著名的解释模型或解释概念是相对剥夺感[19]。显然,以上分析框架都是在社会运动领域来讨论集体行动的,其基本共识在于认定集体行动是由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他们试图找到一种统摄性的解释模型来理解或指导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和革命)。
与日臻成熟的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比,国内学界对集体行动,特别是对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建构和知识积累的阶段。学者们在该领域已作出很多尝试,他们着重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抗争行为。研究者主要分析抗争群体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怨恨情绪、人际网络、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策略、媒体或情感等因素进行动员,探究集体行动发生与发展的逻辑和规律。
集体行动的理论发展主要历经三个阶段:社会运动理论、革命理论和抗争政治理论,这些理论在主流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框架方面具有强烈的进化色彩[20]。蒂利等人系统地阐释了抗争政治理论,他们将抗争与政治联系起来,以动态的视角观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抗争政治是指在诉求者和他们的诉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21](P7-8)。可见,抗争政治涉及诉求者与诉求对象之间的互动,环境抗争作为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抗争模式之一,可以尝试在抗争政治的理论范畴内对其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适用于环境抗争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集体行动作为一种整体性、规范性的概念,是与当前中国情境下研究社会矛盾或冲突相契合的[22]。
二、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
本文主要以上述各种分析框架为参照,同时结合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现状,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将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在下文中,笔者将分别从这三个层次对中国农民的环境抗争进行解释,寻求农民加入集体行动的根源。
(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
任何集体行动的达成,其前提是获得参与者情感心理的认同。一方面,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往往是非理性的。勒庞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解释集体行动中的非理性因素。理性的个人随着聚众的发展逐渐会变得非理性化甚至野蛮,集体行为随即趋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方式[23]。“由于行动者已经被群体情绪感染,集体行为是对领袖人物向群体成员施加刺激的反应。在群体成员丧失理性能力的条件下,具备煽动性的领袖人物借助重复断言等宣传术强化了集体的无意识,控制了群体运动的发展方向。”[24]另一方面,除抗争精英的刻意煽动之外,人们之所以加入到集体行动中,是因为他们总是期冀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能够改变当前的不利处境。
1.怨恨心理
在环境抗争事件中,对环境风险的担忧和对环境污染的愤怒是民众采取暴力抗争的心理根源。对相关企业或政府机构隐瞒环境风险和污染的行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会表示愤怒。比如浙江新昌、陕西凤翔等环境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保护异化为“污染保护”。在此背景下,村民要求关停相关企业,但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导致相关企业照旧经营,最终引发暴力冲突。刘能把这种“怨恨情绪”或“怨恨心理”视为影响集体行动参与者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互动的重要变量[25]。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怨恨心理是集体抗议行动的重要动因[26]。陈涛等人对蓬莱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岛渔民的环境抗争怨恨心理进行文本分析认为,怨恨心理具有特定的再生机制和演化逻辑,包括由“怨”到“恨”,由个体到群体,由分散到集聚,由原生到次生[27]。任丙强指出,这种怨恨心理能够使弱连带的社会网络下的民众在认同上保持一致,进而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28]。此外,制定公共政策的非正式运作以及低参与度,可能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加剧这种怨恨心理。换言之,对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充满怀疑,公众怨恨心理的复杂交织为环境抗争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条件。
2.维权心理
于建嵘提出“压迫性反应”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民维权抗争的“集体动力机制”加以论证,“一旦他们采取了某些针对基层政府和官员的行动,他们就会面对个体难以承受的压力,应对这种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团结相互支撑的力量,通过共同的诉求目标以实现共同身份的认同就成为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29]。农民在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之后最初的反应一般是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举报,也可能会与肇事企业直接协商。若以上方式得不到有效回应,他们会把希望寄托于更高层的权力机关而采取越级上访的行为,但这一行为往往会遭受地方当局竭力打压。由此,农民的维权心理被进一步激化而转向更加激进的策略。随后个体维权抗争演变为集体维权抗争,农民开始团结起来采取“自力型救济”[30]的集体行动:围堵企业、截断交通或破坏工厂逼其停产。典型的案例包括浙江东阳及河南修武环境抗争事件:东阳村民在抗争领袖的领导下在污染化工园区入口架设帐篷阻止物资供应,迫使工厂关闭;修武的数千村民对污染企业进行围堵,导致地方政府对其进行“强行驱散”。环境抗争中的维权心理,源于农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不公正对待,“在目前的中国,以社会公平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往往是社会底层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31]。
(二)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
诸多学者在制度层面将环境抗争归结为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物。塔罗将政治机会结构中的制度要素概括为三个方面:或强或弱的国家渗透能力、排斥或吸纳的国家战略;包容或镇压的国家策略[32]。黄冬娅指出,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机会结构,在国家中心视角下研究社会抗争,必然要考虑国家性质、国家创建以及央地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制度设计[33]。一般而言,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构性政治机会”指的是政治制度为农民集体行动所提供的制度空间及可供选择的路径,我们沿循这一界定,试图从政治机会结构的视角来探究环境抗争中集体行动的制度根源。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的逐渐开放为环境抗争创造了制度空间。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价值观差异、利益差异,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价值分歧与相互竞争以及大众媒体的市场化与国家信访制度的逐步完善,使民众可以借助于这些渠道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之中而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家的制度变迁将封闭的政治机会结构适度开放,导致国家、农民和企业之间形成的利益格局由一体转为分殊,二者的结构转型促使遭受环境侵害的农民不再沉默而走上抗争之路”[34]。童志峰指出,“依法治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强化、大众媒体的日渐开放与行政体系的分化是导致农民环境抗争的重要维度。具体而言,法治话语的强化为农民的依法抗争创造了制度条件,大众媒体的日益开放为环境抗争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分化的行政体系能够降低环境抗争的风险,还可以增强抗争的持续性以及抗争领袖的运作空间[35]。
与此同时,尽管政治机会结构日渐放开,但其发挥的实质性功能还有待商榷。朱海忠基于苏北农村个案的铅中毒事件研究发现,在农民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的“结构性机会”中,基层选举与“乡政村治”、寻求专家学者和环保组织的帮助、环境诉讼以及诉诸信访等结构空间的功能发挥是非常有限的,而相对开放的大众媒体对环境维权事件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抗争中的政治机会结构存在很大缺陷。整体上来说,农民主要依赖的是大众媒体(网络媒体相比于传统的电视和报纸影响更加直接),信访渠道和环境NGO的功能仍未得到有效发挥[36]。
环境NGO在环境抗争中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给予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制定方面较为科学的指导意见,同时对环境政策的执行予以监督。但在环境抗争领域中,当前环境NGO的表现并不突出。在郇庆治的看来,我国的环境NGO处于良好的“政治机会环境”之中,然而在实践中却遇到空前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环境NGO没有主动加入或有效指导近年来明显增多的环境抗争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农民的环境抗争,反而采取了一种观望甚或是“主动划清界限”的立场[37]。
总之,诸多环境抗争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表明,政治机会结构的不断开放为农民的环境抗争提供了更多的制度空间。“政治机会结构”的理论范式与当代中国农民的环境抗争相契合。在特定时期,除政治制度本身的因素外,环境抗争事件的社会影响与媒体压力也会影响到政治机会的开放以及开放程度。实际上,当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被塑造为与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基本生计息息相关的抗争行为时,略显粗野甚至暴力的抗争方式不仅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容忍,而且还有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集体行动不仅是一种结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38](P235-240)。集体行动的文化情境是指社会运动领袖或精英在动员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和身份等文化要素。研究者聚焦于社会运动文化的内部维度,即社会运动领袖或精英在动员时所表达的信念、规范、标记、故事和身份等文化要素[39](P191-212)。在抗争性集体行动中,抗争领袖借助于上述文化要素,向反对者、支持者和旁观者表达怨恨,表述抗争行为背后的理据,以获得采取集体行动的基本共识[40](P91-115)。人们对与集体行动相关的特定事件和情形赋予的意义,是影响社会动员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通过分析集体行动中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性活动来解析动员结果的研究成果已陆续出现[41]。夏瑛指出,每一个集体行动都需要通过话语、修辞和符号等“话语实践”来完成动员。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试图赋予相关问题、事件及其行动特定的意义,这些话语载体成功地传递给潜在的反对者、支持者和旁观者[42]。集体行动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总是处于某种宏观的文化情境之中,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参与者以及塑造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
任何形式的抗争性集体行动都需要建构和选择抗争性话语。蒂利将某一群体所熟知和运用的抗争方式(诸如葬礼抗议、狂欢、砸机器、抢粮、怠工、抗捐抗税、叛乱、罢工、示威、静坐、游行和恐怖活动等有形的抗争行为)总和称为“集体行动形式库”[43]。赵鼎新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资源库”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运动中的各种抗争形式不可能逾越其社会文化的范围,在受社会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行为习惯方面,文化文本成为动员者与参与者的行动惯式[38](P224-228)。周裕琼等人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抗争行为,都必然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抗争话语形式,即抗争性话语形式库,包括演讲、口号、标语、横幅、倡议书、公开信、微博、帖子、博客、纪录片、歌曲、DVD、视频等文字、声音和图像形式[44]。社会运动的动员者或抗争领袖会根据特定的文化剧本来建构他们的抗争性话语。运用不同的抗争性话语,动员者能够建构起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动员和自我定义。在环境抗争事件中,抗争领袖如何在集体行动中作出话语的建构与选择,并在各种话语空间(官方/民间、正式/非正式、传统媒体/新媒体)与政府进行对抗与对话,关系到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否成为可能。在环境抗争的不同阶段,为实现行动动员、共识动员、环保实践、官民对话等目标,抗争领袖会不断调整其策略,以尽可能地争取最广泛的反对者、支持者和旁观者的注意。
以浙江东阳环境抗争事件为例,以老年人群体为主要抗争领袖的动员者采取了各种方式与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展开对话。欧博文和邓燕华将该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称为东阳村民的“抗争表演”,抗争者多次通过葬礼抗议的形式来羞辱县委书记、县长和工作组等政府工作人员。根据邓燕华的田野调查,当工作组进入抗争区域之后,老年人抗争者会穿上白色的长袍下跪磕头,他们经常还会舀起一把泥土,放在某个官员的汽车引擎盖上,在上面插上香或贴上白纸。由于村民的抗争策略不断升级,地方政府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于4月10日派遣了1500多名地方干部和公安人员前往东阳县画水镇清除农民为抵制环境污染而搭建的占道帐篷,最终引发冲突。然而,政府的强硬策略却适得其反。在“4·10事件”发生之后,农民的抗争情绪持续高涨,他们用该事件留下的证据(如警察制服、警棍、头盔、催泪瓦斯等道具)来装饰他们的帐篷。他们的抗争口号中既有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谩骂和诋毁,如“群众屠杀者”、“权力的魔鬼”等;也有对抗争群体的激励,如“坚持就是胜利”、“中央会来救我们的”等。由于抗争策略的激进化,抗争领袖还通过大字报的形式对不参与集体行动或退出集体行动的“叛徒”进行侮辱,称他们“狗摇尾巴取悦上面的人”,或是“没骨气的懦夫”。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抗争形式不断汲取抗争的力量,导致社会的权力关系出现倒置。地方政府最终决定关闭化工园区,农民的环境抗争取得胜利[45]。
从浙江东阳的抗争事件中可以看出,抗争领袖通过选择不同的抗争方式来营造一种文化情境。在这种文化情境中,由于抗争文化氛围的渲染,动员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导致抗争规模的不断扩张。地方政府因惧怕农民的集体行动引起的社会失序而采取强硬的维稳措施,却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该事件中,抗争领袖成功地运用了抗争道具和口号来动员参与者,可见,抗争话语和抗争符号的建构与选择对集体行动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三、结论
对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剖析结果表明,农民之所以能够在环境抗争中被动员起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从一种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中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首先,心理动机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的酝酿为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就是说,心理情绪的一致是农民集体行动在价值层面上的认同基础。其次,制度结构规制着农民的集体行动的操作空间,对具体制度的认同缺失、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怀疑以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塑造着农民的行为选择。换言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政策运行过程的不规范容易引发集体行动。第三,环境抗争的文化情境为农民的集体行动和策略选择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能否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运动文化形式为集体行动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延缓了集体行动的进程,也影响着集体行动的成败。总之,环境抗争中的农民集体行动是心理动机、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共同作用的一种集体行动模式。
[1]汪伟全.风险放大、集体行动和政策博弈——环境类群体事件暴力抗争的演化路径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5,(1).
[2]陈明明.权利、责任与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张金俊.国外环境抗争研究述评[J].学术界,2011,(9).
[4]Mark I.L.Deterrence or Escalation The Puzzle of Aggregate Studies of Repression and Dissent[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87,31,(2).
[5]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A].吴毅.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6]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2).
[7]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2).
[8]董海军.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J].社会,2010,(5).
[9]王洪伟.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J].社会,2010,(2).
[10]罗亚娟.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1]吴长青.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析为例[J].社会,2013,(5).
[12]李晨璐,赵旭东.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J].社会,2012,(5).
[13]陈涛,谢家彪.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16,(3).
[14]陈占江.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5]陈涛,李素霞.“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16]Jenkins,J.Craig,Charles Perrow.Insurgency of the Powerless:Farm Worker Movements(1946-1972)[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7,42,(2).
[17]MaCarthy,John D.,Mayer Zald.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7,82,(6).
[18]Snow,David A.,E.Burke Rochford,Steven K.Worden,Robert D.Ben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51,(4).
[19]Ted R.Gurr.Why Men Rebel[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20]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21]Doug McAdam,Sidney Tarrow,Charles Tilly,Dynamics of Conten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2]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2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4]高春芽.集体行动的多元逻辑:情绪、理性、身份与承认[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4).
[25]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上的观察[J].开放时代,2008,(3).
[26]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4,(4).
[27]陈涛,王兰平.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28]任丙强.网络、“弱组织”社区与环境抗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29]于建嵘.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J].学海,2006,(2).
[30]张玉林.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J].学海,2010,(2).
[31]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J].东南学术,2008,(3).
[32]Tarrow,Sidney.State and Opportunities: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A].Doug McAdam, John McCarthy,Mayer N.Zald.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3]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1,(2).
[34]陈占江,包智明.制度变迁、利益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以湖南省X市Z地区为个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35]童志峰.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基于环境抗争的研究[J].理论月刊,2013,(3).
[36]朱海忠.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寸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37]郇庆治.“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9]Williams,Gwyneth I.,Rhys H.Williams.“All We Want is Equality”:Rhetorical Framing in the Fathers’Rights Movement[A].Joel Best.Images of Issues:Typifying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2nd Edition)[C].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5.
[40]Rhys H.Williams.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Collective Action:Constraints,Opportunities,and the Symbolic Life of Social Movements[A].David A.Snow,Sarah A. Soule,Hanspeter Kriesi.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C].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4.
[41]周明,曾向红.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J].社会学研究,2011,(6).
[42]夏瑛.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J].社会,2014,(1).
[43]Tilly,Charles.The Contentious French:Four Centuries ofPopularStruggl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4]裕琼,蒋小艳.环境抗争的话语建构、选择与传承[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45]Kevin J.O'Brien,Yanhua Deng.Repression Backfires: Tactical Radicalization and Protest Spectacle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5,24,(93).
(责任编辑 李淑芳)
韩瑞波(1992—),男,河北邢台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D638
A
1671-7155(2017)01-0091-06
2016-12-20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0AZZ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