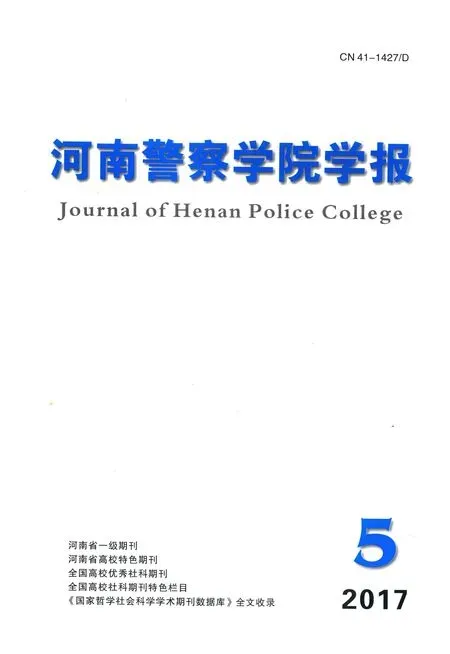论敌人刑法理论影响下的我国刑事立法
郭 玮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论敌人刑法理论影响下的我国刑事立法
郭 玮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呈现出以下特点:风险社会下的刑事处罚前置、特定犯罪刑罚加重及特定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限制。这种立法趋势是敌人刑法理论的反映。敌人刑法理论并不是对传统法治国的颠覆,而是对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学界应摒弃成见,承认敌人刑法理论影响的存在,这是研究并有效利用该理论的前提。
敌人刑法;市民刑法;刑法规范
一、敌人刑法理论概说
敌人刑法理论由德国当代法学家雅科布斯提出。他主张,应把那些持续性地、原则性地威胁或破坏社会秩序者和根本性的偏离者当作敌人来对待[1]。即针对那些所谓具有持久性社会危险性的行为人扩张构成要件,将刑事可罚性前置,同时限制其程序权利,对其大量适用保安处分手段,以控制这些“危险源”,达到保护社会的目的[2]。进而,以“防卫社会”为价值取向,以行为人为基础的刑法理念受到欢迎,而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以行为为基础的刑法理念遭到挑战[3]。
(一)敌人刑法理论的发展
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来源于康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康德认为,由于犯罪,不应再将罪犯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来看待。康德自己声称反对奴役,但针对“因犯罪而丧失自己人格”的人,他也明确提出了例外情形。费希特认为,罪犯的死亡决不是惩罚,而是保障安全的手段。作为法官的国家并不处死人,而只是废除契约。这种事情的进行,不是根据实定的法权,而是出于需要[4]。康德与费希特都较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强调“共同体”安全的维护,对于被视为“敌人”的人,应当通过种种手段消除其危险性。
雅科布斯的敌人刑法理论脱胎于上述思想,但又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将刑法区分为敌人刑法与市民刑法,认为市民虽然现实地破坏或者严重威胁到了社会秩序而触犯了刑法,但仍然具有独立的人格及公民权,享有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权利。国家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也会兼顾甚至重点考虑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注重刑罚的功利主义。而敌人虽然起初具有人格,但若其行为持续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或者行为的严重性导致其市民资格丧失,则不应当享有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权利,用雅科布斯的话来说,就是“原则性地偏离者没有提供人格行动的保障,因此,不能把他作为市民来对待,而是必须作为敌人来征伐”[5]。
(二)围绕敌人刑法理论的论争
敌人刑法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批评者赞同者兼有。有论者指出,敌人刑法理论中“敌人”的概念不明确,不具有可操作性;敌人刑法理论本身有可能成为专制政府镇压异己的工具;将使国家懈怠对犯罪深层次原因的反思;敌人刑法理论的基础不牢靠等。该论者认为,在刑事领域没有敌人与朋友之分,只有犯罪人与非犯罪人之分[6]。另有论者则认为:在敌人的敌对行动中完全不存在任何值得社会宽恕的理由,一些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大规模地杀害无辜的平民,一些人纯粹为了满足自己无底的欲望而有组织地杀人、抢劫和强奸,一些人身为高官在享受着厚禄的同时利用职权疯狂地敛财。这些人的行为证明,他们原则性地破坏了社会的实在法规范,他们根本不是社会的成员,而是社会的敌人。在敌人那里,既不会发生人道问题,也不会发生误判问题,因此,对于敌人,必须杀掉。在敌人刑法中完全不存在敌人的权利,存在的仅仅是人民的权利,宽容和文明都只适用于市民,而不适用于虽然具有生命但是不具有生命权的敌人。主张对敌人宽容,就无异于对守法的市民缺乏最起码的忠诚[7]。还有论者认为,其实敌人刑法无非是说为了实现维护共同体有效存在的目的,要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严惩不贷,这不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的论调吗?现在雅科布斯教授把一个人所共知的观点明确化,并且这样做的目的还可以使得市民犯罪人免受敌人刑法的威胁,却仅仅(或者主要)因为这个观点长了一张看起来似乎狰狞的面目,就激起了无数人的反对。仔细想一想,既然我们可以接受用更为残酷的战争去对待共同体之外的人,又何必对用缓和得多的敌人刑法处置共同体之内的可能比外部的敌人更令人发指的人感到不可思议呢[8]?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论争体现了人权保障与犯罪惩治、功利主义刑罚观与报应主义刑罚观的对立,属价值观的选择问题。
二、敌人刑法理论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虽然有个别可以废除,但主要的问题还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虽然刑罚是“恶之花”,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时代,不会有人喜欢刑罚。但是,共同体要理性地存续下去,就必须坚守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就不能不用刑罚去对付各种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行为。人们当然应当警惕开着“恶之花”的刑罚,但是,人们也必须珍惜结出“善之果”的刑罚[9]。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力量释放出来,一直被忽略的关于现代化的副作用的知识开始走向前台,促成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中国社会已经向风险社会迅速转型,迫使我们不得不直面西方社会已经面临的诸多同质性或同源性的问题。为了实现风险的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刑法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风险社会的需要。无论如何,刑法并非自我封闭的体系,它会随政治与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当前刑法体系已经开始了从惩罚向预防的转换,揭示了预防模型对古典惩罚模型的取代[10]。基本目的的变化意味着刑法价值取向的重大调整,预防导向的刑法体系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这样的价值选择最终深刻地塑造了刑事实践与刑法理论的发展。由于认为只有国家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成员容忍了国家介入社会生活的倾向,国家于是以“维持安全的社会生活”、“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维持平稳的社会生活环境”等为根据,推行“有危险就有刑罚”的扩张性的入罪化原则[1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立法紧跟时代发展,犯罪化一直被作为主流,尤其是近年来的一系列刑法修正案,更是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刑事立法的上述倾向,推动着刑法理论向刑事立法逐渐靠拢,并促成了安全刑法及敌人刑法理论的出现,敌人刑法与风险社会有着实质关联,它们都源于现代频发的危险。作为社会现实的反光镜,敌人刑法理论实际上体现在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之中。
(一)刑法的提前介入逐渐常态化
传统刑法是以侵害犯为核心的刑法,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实害刑法也逐渐向危险刑法转型,现代刑法体系转变为侵害犯、危险犯二元发展的体系,危险犯成为现代刑法的中心概念之一[12]。相应地,危险刑法不再耐心地等待社会损害结果的出现,而是着重在行为的非价值判断上,以制裁手段恫吓、震慑带有社会风险的行为[13]。事实上,危险犯的大量运用,对刑法前置的偏爱已然成为当前立法的趋势,并指引着今后的立法方向。在刑法修正案中,有一系列把危险行为犯罪化的努力,比如《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新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一条将《刑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修改为危险犯,《刑法修正案(四)》第一条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修改为危险犯。除此之外,为了提前预防犯罪,把某种犯罪涉及的帮助行为、资助行为进行了犯罪化,亦是为了预防犯罪。这主要表现在《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条新增设的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八条把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犯罪化,新设协助组织卖淫罪。《刑法修正案(九)》第六条把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犯罪化,设置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14]。敌人刑法体现了社会本位、安全本位,秩序本位,其主张之一便是刑事可罚性前置,即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就施加惩罚,即不仅要将刑法视为报应性事后处理系统,还要视其为事前介入的预防手段,将其触角从现实法益前移至危险形成阶段[15],这与当前危险犯的立法趋势不谋而合。
刘仁文教授对敌人刑法批评道:现代刑法对某些严重的犯罪提前犯罪化,处理预备犯、阴谋犯,这些做法只是针对特殊的“危险源”,在法治的一般原则和核心价值的前提之下分而治之的办法。对待他们,并不是要像对待敌人那样残酷无情,只不过针对各自的特殊机理对症下药而已[16]。事实上,对待危险犯,不论在名义上是分而治之还是视为敌人,都旨在通过刑法前置化提前预防犯罪,及时消除威胁社会的行为,两种方式的本质及目的是一样的。在犯罪化过程中,由于绝对报应主义向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并合主义的嬗变,以及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向,导致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也可能会遭受处罚。刑法的提前介入作为应对敌人的有效方式,有力地回应了破坏社会基本规范的行为,迎合了上述趋势。
(二)加重自由刑,增强刑罚的痛苦感知
目前,我国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无期徒刑相比,差距过大,刑罚的效益只有在刑罚真正体现出公正的伦理价值时才能实现。无论是制刑、量刑还是行刑,都是围绕惩罚罪犯进行的,犯罪人、受害人和社会大众对刑罚的感知只能通过个案进行。死缓和无期徒刑在制刑和行刑上的脱节,使刑罚结构严重失调,让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人及其亲友顿感显失公平,也让包括死缓和无期徒刑案件中的受害人及其亲友在内的广大民众心理失衡,难以体现刑罚公正和人道的伦理底蕴。为了配合限制死刑,就有必要加强死缓与无期徒刑的严厉性,对客观上难以矫正、短期回归社会有危险的“恶犯”,体现“重重”。做好死缓与死刑,无期徒刑与死缓间的无缝衔接,科学配置刑度,坚决捍卫社会的安全和利益[17]。对此,我国刑法立法也给予了回应。如:第一,将两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大大延长了死缓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限。第二,延长了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刑期,将“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分为两种情况,即“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第三,降低了减刑力度,意在通过长时期的考察,进一步验证罪犯“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态度。将无期徒刑减刑后的实际执行期限限定为大于等于十三年,将限制减刑的死缓犯的减刑后实际执行期限限定为二十年以上。第四,提升了被判无期徒刑罪犯的假释适用标准,将假释前实际执行刑期限定在十三年以上,而不是之前的十年以上。第五,将强迫交易罪的刑期由一档调整为两档,最高刑期达到了七年有期徒刑。第六,将强迫劳动罪的刑期由一档调整为两档,最高刑期达到了十年有期徒刑。第七,将敲诈勒索罪的刑期由两档调整为三档,最高刑期达到了十五年有期徒刑。第八,将寻衅滋事罪的刑期由两档调整为三档,最高刑期达到了十年有期徒刑。第九,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期由一档调整为两档,最高刑期达到了七年有期徒刑。第十,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期由一档调整为两档,最高刑期达到了七年有期徒刑。
通过上述立法,不仅进一步缩小了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无期徒刑与死缓之间的距离,也加大了特定犯罪人的自由刑力度,实现了刑法的惩罚功能,体现了敌人刑法理论中的报复色彩。刑法之所以延长上述特定犯罪的刑期,而不是其他犯罪的刑期,主要在于上述犯罪动摇了社会规范的根基,若继续沿用之前的轻刑,则不能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社会秩序亦无法维持。为此,有必要将这些犯罪人置于社会的对立面,用更加严厉的刑罚予以惩治,维护绝大多数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限制特定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诸多方面对特定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予以限制。如:1.限制了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会见权,律师必须经过侦查机关许可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2.规定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刑事诉讼法》的上述修改,充分体现了敌人刑法对于敌人的“讨伐”,即为了保护社会,功利主义将压倒人道主义,即便有侵犯人权的危险,刑事立法还是要剥夺特定嫌疑人的某些诉讼权利。从罪名来看,上述规定主要涉及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等,这些犯罪人社会危害性一般较大,且难于打击及矫正改造,这正是雅科布斯所认为的“根本性的偏离者”,他们怨恨社会,决定脱离社会,遂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了自我放逐。既然这类人选择了与社会为敌,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以牺牲正常公民的权利为代价给予他们正常的司法处遇,而应与其作斗争。当然,即便是打击敌人,也要在法治国的框架下进行,而正是在敌人刑法理论指导下的刑事立法为打击敌人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指南,符合法治原则。
三、应客观看待敌人刑法理论
敌人刑法理论自雅科布斯教授提出起就饱受争议,反对者祭出“法治”、“人权”大旗,认为敌人刑法理论会动摇法治国的基础,滋生刑法肆意,有侵害人权之虞,故不可取。其核心观点就是敌人刑法中的“敌人”概念太过于模糊,政治色彩浓厚,不是法言法语。同时,认为敌人刑法擅自将刑法分为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企图区别对待,但在“敌人”的内涵与外延尚未清晰的前提下妄图建立并行的两套刑事制裁系统是具有极大危险性的,违背了有限政府的初衷。笔者认为,如今我国刑法对正义、秩序与民主、人权的艰难抉择,颇似清末礼教派与自由派的论争。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一百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道德秩序重建方面也一无建树。至于今日,倡言法治的自由派人士,仍动辄教导公众个人有不道德的权利;而将个人自由、权利奉为圭臬的法律人,也以为法治与道德无关,对国家治理实践中利用传统道德和民间习俗的做法嗤之以鼻甚或猛烈抨击。然而,实际情况是,法治未立,前人所忧虑的“人惟权利之争,国有涣散之势”的情形,却已成为现实[18]。要想客观看待敌人刑法理论,狂热的膜拜与盲目的否定均不可取,我们应当立足于当下国情,实事求是地论证敌人刑法理论的价值,探寻敌人刑法理论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契合点。
(一)敌人刑法理论能满足对秩序与正义的需求
秩序是刑法的基础价值,刑法以寻求维护秩序为基本诉求。如果某个公民不论在家中还是在家庭之外,都无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那么,奢谈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19]。只有充分发挥刑法功能,才能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梦醒过来[20]。如果说刑法的基础价值是秩序,那么刑法的终极价值则是正义。罗尔斯认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在目标互异的个人中间,一种共同的正义观建立起公民友谊的纽带,对正义的普遍欲望限制着对其他目标的追逐,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1]。在依法治国时间较短,法治信仰尚未建立,规范意识普遍缺乏,规范体系仍未形成的今天,良好社会秩序及实质正义的实现仍值得我们努力追寻。刑法通过公正地分配权利与义务,且公正地适用刑法,及时保障了正义。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其实就是资源的分配过程,在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良好秩序,合理分配了权利与义务。虽然资源分配公平公正,但难免有权利滥用、违背义务等情形出现,为了保障正义不受破坏,恢复被破坏的正义,刑法有必要公正、及时、有效地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价值。
雅科布斯认为,在当今西方国家的立法中,存在一些并不针对守法公民(他一般称之为“公民”)的特定条款,而是针对潜在的危险人物(他一般称之为“敌人”)。在后者的情形中,制裁并不是为了惩罚之前的错误,而是为了预防之后的恶害。雅科布斯还归纳出敌人刑法的三大特征:第一,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就应当施加惩罚。第二,包含不成比例的制裁措施,比如刑期极长的监禁刑。第三,抑制正当程序的适用。在上述基础上,雅科布斯将刑法分为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市民刑法使规则与社区价值得以存续,其包含两个方面,首先,罪犯有权与社会再次达成和平状态,如果和平状态已达成,罪犯则继续维持他的市民身份。其次,罪犯有义务去弥补损害,这些义务也使得罪犯人格得以存续。换句话说,罪犯不可因自己的行为而抛弃社会义务。而敌人刑法则与危险作斗争,它要求国家与罪犯作斗争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公民有权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去保证他们的安全需要[22]。康德也认为,敌人经常威胁着我们,因为他们不愿与我们一起存在于法治状态,所以,他们就必须离开我们附近[23]。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过度宽容,许多违法犯罪都不再受到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有些甚至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社会对许多行为的评价不再像以前那样统一,反应也不再那么强烈和持久。这种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改造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有好处。但社会对违法犯罪行为缺乏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坚决持久的排斥,也会使一些人因支付的代价降低而更可能铤而走险[24]。这种过度宽容在民生犯罪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我国刑法仍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类罪置于分则前几章,但事实上,没有哪一类犯罪像民生犯罪一样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广泛、持久、潜移默化的影响,民生犯罪俨然已经渗透进了人们衣食住行用的方方面面。近年来,随着刑事立法从国权主义向民本主义的转型,我国逐渐在民生领域扩大犯罪圈或降低犯罪门槛,如食品犯罪、药品犯罪、欠薪犯罪、个人信息犯罪等。虽然立法在逐渐完善,但仍有很多漏洞,我国刑事立法在民生领域仍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协调性有待加强,对民生的保障力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立法内容、立法水平还是立法效率来看,都存在不足。所以,敌人刑法应当在民生犯罪规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维护社会秩序与公民正当权益,捍卫社会正义。
敌人刑法理论也可以解释死刑存在的现状。虽然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有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但目前,“保留死刑,逐步削减,最终废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赞成,为大多数人和司法实践所接受。以此为基础,中国死刑制度改革有了明确的路线图。近年来,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不断废除各类犯罪的死刑,尤其是经济犯罪及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对于贪贿犯罪及暴力犯罪的死刑,死刑的废除进程却步履缓慢,究其原因,对于当下而言,“保留死刑”仍是必要的,这体现了我国刑法对于秩序与正义的追求。对于“杀人偿命”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朝夕间废除死刑是不明智的,极可能会引发私力复仇的泛滥,动摇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心,不利于当前社会的正常发展。敌人刑法为死刑制度的保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敌人刑法理论认为“敌人”是不具有正常人格的人,当然不具备公民权,没有资格与社会再次达成和解,应当被社会永久放逐。死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人是可以被改造”的观点,将罪犯视为无可救药,必须被放逐的人,这与敌人刑法理论不谋而合,只有运用敌人刑法理论,现行的死刑制度才有正当性基础。当然,死刑制度的确存在诸多的缺陷,多年来饱受批评,但不可否认,死刑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捍卫正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是社会良知的最后一道防线。况且,我国自古有死刑的传统,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死刑,“杀人偿命”与“欠债还钱”被人们同等视之,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国外死刑的废除原因、背景复杂,而中外传统与现实迥异,若盲目废除死刑,极有可能水土不服。对于清末盲目效仿外国的“法理派”,梁治平先生有过精彩论述,其认为:礼教派并不反对变法修律,但是,相比于法理派,这一派确实更多考虑习俗、传统、民情,以及教育程度、制度设施、社会条件等当下因素,这使得礼教派的改革论述看上去更“保守”,更讲求现实,也更形复杂。在礼教派人士看来,社会的秩序,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其复杂性超出人们的想象,非“少数人之心思学力规划一时”的能力所能把握。罔顾风俗民情,遽行新法,可能产生人所不欲的连锁效应。说到底,法律为一种社会的制度,其发生与发展自有其逻辑,非人力可以任意改变和支配[25]。其实,除去国情的考虑,死刑的存在,多少会使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仔细掂量,无论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还是从“趋利避害”的人性考量,死刑都是守法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杀手锏,也是守法公民伸张正义的希望所在。
(二)敌人刑法理论不必然损害法治原则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个人利益与公共安全遭遇了极大风险,各种问题涌现,我们能否继续以刑法谦抑为借口掩盖对安全、秩序与正义的真实需求?金德霍伊泽尔认为:传统刑法的目标——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今天已退居幕后[26]。罗克辛认为:积极预防反映在维护和加强对法律秩序的存在能力和贯彻能力的忠诚上,通过向民众宣示法秩序的不容侵犯,强化民众对法的忠诚和信赖[27]。然而,当前的刑事立法与皇帝的新装颇为相似,能工巧匠虽然力图全部由“刑法谦抑”、“人权”、“非犯罪化”等布料织成,但囿于社会发展程度不够、司法资源短缺而没有足够的布料,不得不露出一部分皮肉,敌人刑法理论的布料试图填补空白,但由于布料粗糙难看,很多人宁愿皇帝露出皮肉经受风吹日晒,也不愿承认皇帝对于穿衣的需求。因此,对于敌人刑法理论,我们要在现代化语境下进行分析,客观看待其对于刑事立法的积极作用。
1.对敌人一词的理解不应过于局限
敌人刑法理论的第一眼印象往往戾气横生,也许会使很多人联想到“敌我矛盾与人民内容矛盾”。事实上,这是一种思维定式影响下的狭义理解。深受行为无价值论影响的雅科布斯,将犯罪理解为规范侵犯,认为刑法保障的是规范的效力。雅科布斯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利益是作为规范及有保证的期待来表现,人们不是期待每个人都避免各种利益侵害,而仅仅是期待那些负责的人,并且仅仅在其所负责并充分关心的范围之内来避免利益侵害。如果以命令规范来表示,则这个命令的内容不是“不得造成利益侵害”,而是“不得破坏你作为非侵犯者的角色”[28]。从这个意义上,敌人刑法中的敌人更为接近“侵犯者”、“规范违反者”、“屡教不改者”、“背离社会者”,“危险人物”等概念,而不是敌我矛盾中的敌人。
批评者认为敌人的概念太过于模糊,无法界定。敌人的概念的确无法界定,但原因不在于敌人刑法理论出现了问题。雅科布斯指出,因为立法的局限,市民与敌人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从应然意义上讲,敌人是原则性地偏离且缺乏人格者,与市民应当是截然不同的,但敌人在现实生活中更接近于一种可分割的性质或特征,有时甚至以半个敌人的面貌出现。因无法精确把握,敌人概念的提出似乎多余,但又不得不存在。若欠缺敌人概念,敌人刑法理论就没有了主体,没有了前提,更没有存在的意义。建立在规范论基础之上的敌人刑法理论,必须借助某个概念来区分规范遵守者与规范破坏者,而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局限性,使得敌人(enemy)一词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敌人一词的联想过于丰富与主观,以至于敌人一词无法承受丰富外延所带来的压力,进而影响到了敌人刑法理论本身。具体到我国刑法语境中,敌人一词更适合描述那些屡教不改,动机卑劣,主观恶性较强,对社会危害较大或者危险性较大的人。为了更加科学地界定敌人的内涵与外延,我们不应按图索骥,拿着定义好的所谓的敌人概念到处寻找敌人,而应当从外在表现或涉嫌的罪名去定义敌人,例如“手段残忍”、“损失巨大”、“前科累累”或者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等。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由外而内的界定更有助于敌人刑法理论的发挥,也符合法治国原则。有学者认为,敌人的称谓有可能被专制政府滥用,成为迫害人民的工具,笔者认为这种担忧其实不必。首先,敌人并不是凭空认定的,需要一定的标准。如客观危害、主观犯意、人身危险性等,即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次,敌人刑法更多的是具有立法意义,而不可滥用于司法领域。我国《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一个专断的、充满歧视的、迫害性的法律不可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而司法机关更不可能不对照法律就擅自将某人认定为敌人。很多学者以纳粹德国为例,说明专制政府利用恶法对无辜人民进行迫害。从逻辑上讲,这种观点也说不通,专制政府是利用恶法的主体,也是人民遭受迫害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专制政府这一前提,就不可能产生出恶法,更不可能有人民被迫害的事实存在。
2.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的划分事实上存在
在传统社会中,刑法的任务被确定为保护法益,强调违法性的实质是结果无价值。但在风险社会中,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药品与食品安全事故大量涌现,社会成员在精神上或心理上的负荷也在不断提高。正如贝克所言,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而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毫无疑问,风险社会中对安全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迫切。基于国民安全的需要,刑法的任务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从保护法益向保护国民的安全感与信赖感过渡[29]。虽然刑法谦抑、保护人权、非刑罚化与非犯罪化已经成为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但事实上,现代西方国家在强调对轻微犯罪甚至一般犯罪非刑罚化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集中有限刑罚资源严厉惩治严重犯罪。“轻轻重重”构成了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30]。虽然我国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现有的理论研究往往关注于“宽”,而很少问津“严”,貌似一提到严厉惩治就联想到了严打,进而遭到各种非议。庆幸的是,刑事立法并没有一边倒地偏向于“宽”,仍然兼顾了“严”的一面。自《刑法修正案(六)》起,我国及时对风险社会作出反应,刑事立法逐渐从结果无价值转变为行为无价值,犯罪圈不断扩大,刑法规范逐渐深入人心。刑事立法一方面不断地将一些动机恶劣、危害后果严重且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人归为敌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已经无法容忍某种规范被持续地破坏,刑法将此前并不认为是敌人的人归为敌人之列,在形式上及实质上给予了否定评价。这些变化处处体现着对于规范的维护和对秩序与正义的追求,落实了刑法的规范保护机能。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犯罪圈,扩大刑法干预的范围,严厉惩治某类犯罪,正是建立在现代刑法理念(即保障法)基础之上的。若仍旧以传统刑法观(即惩罚法或刀把子刑法、镇压刑法)为圭臬,则扩大刑法干预范围以替代警察执法(如行政处罚或劳教),无疑是以大巫换小巫,对于公民权利自由而言,真的是“未出狼窝,又入虎口”[31]。
或许有论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刑事法主要是统一的刑法典及刑诉法典,并没有关于敌人刑法单独的实体及程序规定。然而,与其说敌人刑法是实然层面的理论,不如说敌人刑法属于应然范畴。雅科布斯虽曾呼吁:把市民刑法中含有敌人刑法成分的东西剔除出来,分门别类,与把敌人刑法与市民刑法混淆起来相比,给法治国带来的危险要小一些[32]。事实上,敌人刑法并不形式地存在于很多国家刑法之中,而是雅科布斯的设想,雅科布斯看到了恐怖活动犯罪、公害犯罪等具有极大破坏性的犯罪已经严重侵犯了法规范,威胁到了法治国本身,若不认真区别对待,恐怕会破坏民主与人权。从实然的意义上讲,目前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但已经通过种种立法明确表明了对敌人的否定与排斥。
四、余论
敌人刑法理论正视了当前刑事法律为了应对风险社会而作出的种种调整,体现了对于秩序与正义的热切追求。虽然有学者否定该理论的地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确实受到了敌人刑法理论的一些影响。与其空谈刑法谦抑,不如承认对于秩序与正义的渴望,探讨敌人刑法对我国刑事立法影响的程度。因此,承认并客观对待敌人刑法,是我们真正实现秩序与正义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刑法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一步。
[1]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J].法律科学,2007(6):54.
[2]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J].中外法学,2011(1):126.
[3]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J].法律科学,2007(6):55.
[4][德]梅尔.德国观念论与惩罚的概念 [M].邱帅萍,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70,108.
[5][德]雅科布斯.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C]//许玉秀.刑事法之基础与界线——洪福增教授纪念专辑.台北:台湾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3:24.
[6]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J].法律科学,2007(6):55-58.
[7]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J].中外法学,2005(5):613.
[8]何庆仁.对话敌人刑法[J].河北法学,2008(7):97.
[9]冯军.刑法问题的规范理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3.
[10]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
[11][日]关哲夫.现代社会中法益论的课题[J].王充,译.刑法论丛,2008(12):339.
[12]董泽史.危险犯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
[13]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15.
[14]姜敏.刑法修正案犯罪化及限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124.
[15]张勇.民生刑法—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权益保障解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9.
[16]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J].法律科学,2007(6):57.
[17]曾粤兴.刑罚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1-212.
[18]梁治平.礼教与法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9-140.
[19][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45.
[20]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M]. 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56-57.
[2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3.
[22] Carlos Gomez-Jara Diez, ENEMY COMBATANTS VERSUS ENEMY CRIMINAL LAW,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FALL 2008, VOL.11,NO.4:531.
[23][德]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
[2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5.
[25]梁治平.礼教与法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6.
[26][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 [J]. 刘国良,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0.
[27]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 [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2.
[28]劳东燕.刑法中的学派之争与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94.
[29]魏汉涛.刑法热点问题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102-103.
[30]张晶.风险刑法——以预防机能为视角的展开[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98.
[31]卢建平.犯罪门槛下降及其对刑法体系的挑战[C]//赵秉志.刑事法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56.
[32]王莹.法治国的洁癖——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J].中外法学,2011(1):139-140.
DiscussiononCriminalLegislationundertheInfluenceofCriminalLawofEnemyinChina
GUO Wei
(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t present,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China presen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e proposed criminal penalties under the risk society, the aggravated punishment on a specific crimes and the limited litigation rights of specific criminal suspects. This legislation tren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of Enemy, which is not sub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law, but a useful supplement to it. The existing influence of the theory of criminal law of enemy should be acknowledged by academic circles, which should be the precondition of research and effectively application.
criminal law of enemy; civil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2017-04-20
郭 玮(1987— ),男,河南驻马店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2016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
D616
A
1008-2433(2017)05-0097-08
(责任编辑:王利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