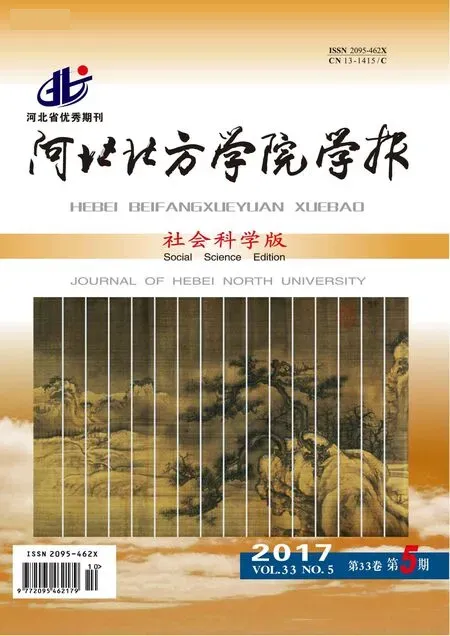陈谦小说对人类心灵创伤的探索
陈 嫚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陈谦小说对人类心灵创伤的探索
陈 嫚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传统的北美华文文学大多在思乡、离散和孤独的笔调中表现外在世界异质文化的冲突与对抗,而美国华人作家陈谦却将笔触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她的小说通过描写一批身在硅谷的中国人婚姻与事业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挣扎,进而探索人类在个体情感、生存困境和历史创痛等方面遭遇的精神困厄。
北美华文创作;陈谦;心灵创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国移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以独特的跨文化视野和个体迁徙经历进行文学创作,记录移民华人的生活阅历和心灵轨迹,构成了新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群体。陈谦正是这一创作群体的后起之秀,其作品也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和关注。
陈谦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广西南宁,1989年赴美深造,后成为硅谷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师,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成为自由写作者。她根据自身的成长经历,以细腻的笔触对一批高科技领域移民女性的心灵进行剖析,进而考究她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先后创作了《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下楼》《繁枝》《莲露》《我是欧文太太》及《无穷镜》等优秀作品。相较于早期北美华文作家作品对中西文化差异和离散情怀等外部世界的现实性书写,陈谦创作的系列“灵魂小说”则着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心灵创伤与情感困境。旅美学者陈瑞林认为,“陈谦真正要表达的并非是曾经的历史或是当下的现实,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个苦痛的灵魂”[1]。她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挖掘和反省,也体现了北美华文文学由表现外在世界转向内部书写的发展趋势。
一、出走:个体情感困局
陈谦的小说通过硅谷白领女性在情感和婚姻上的波折来洞悉人性幽微,以感性形式对两性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她的写作始终盘桓在一个鲜明的主题上,就是华人移民女性的精神苦闷、内心挣扎和现实逃离。”[2]所以,她笔下的女性在个体情感上都遭遇了不同形式的困厄。苏菊和南雁是走出家庭的现代娜拉,她们的出走则是物质(家庭生活)与精神(情感需求)激烈对抗的结果。《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为了过上“有灵性的生活”而放弃一切走出家庭,但之后才发现,在所谓的艺术性生活面纱下还是不堪的世俗,灵性与世俗的生活之间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望断南飞雁》中,南雁不甘于庸常的生活而放弃自己的理想,琐碎的家庭和漫长的岁月也无法抹平她对理想的冲动。由此可见,她们都是情感的缺憾体。
《爱在无爱的硅谷》发表于2001年,是陈谦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中,苏菊是事业有成的硅谷白领,男友利飞是位脚踏实地且温文尔雅的商人,对苏菊更是爱护有加。苏菊拥有常人看来近乎完美的生活,但她却不甘于这种平淡安逸,而是渴望“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生活”[3],追求诗化和戏剧化的人生。因此,在邂逅画家王夏后,苏菊毅然放弃一切,从这种“平庸乏味”中逃离出来。与“贫贱夫妻百事哀”式的传统婚恋问题不同,陈谦思考的是获得“面包”之后的爱情,即当物质条件满足后,婚姻中的两性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所遭遇的危机。因此,陈谦小说中的婚姻只是她思考这一问题的话语场,而在这些复杂的情感纠葛下,她真正探讨的是个体在精神层面的困境。很显然,陈谦塑造苏菊这个人物形象是为了进一步探寻当物质丰盈之后,人类如何去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进而获得个体情感的满足。无疑,探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挣扎,这也构成了以苏菊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的情感困局:理想与现实、情感与责任以及伦理与道德互相胶着,相互牵制。
《望断南飞雁》是陈谦的另一部力作,获得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主人公南雁以“陪读太太”的身份到美国。几经努力,丈夫沛宁在事业上步入新台阶,她自己也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生活渐渐走上正轨。但看上去幸福美满的生活并非波澜不惊,情感上的缺憾带来的创痛瞬间全面爆发。爱情在忙碌的生活中消磨殆尽,婚姻在多方妥协之下难以为继,南雁与丈夫之间愈加貌合神离,而沛宁也始终无法了解南雁内心真实的渴望。体面的工作对她而言不过是“化验室里的那点破事儿”[4]19,无法给她带来事业上的成就感;繁琐的家庭生活以及母亲的期待让她偏离了自己向往的人生,这也是南雁内心痛苦的根本所在。南雁从小就喜欢画画,到美国后多年的家庭主妇生活也没有磨蚀她对理想的渴望。现实生活中情感的失落更加坚定了她追逐理想的决心,最后他抛夫别子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学习平面设计。和苏菊理想化的憧憬不同,南雁的出走更像是痛定思痛后的抉择。但是,无论她作出怎样的选择,在个人情感上都无法实现圆满,或是理想破灭及婚姻惨淡,或是忍受与亲人的离别并背负家庭的指责。
在苏菊和南雁身上,陈谦指出,无论追逐理想还是回归现实,个体心灵都不免受伤。在挣扎与妥协中,逃离眼下的桎梏也许意味着进入另一个围城,而这层层叠叠的精神困顿以及主体在挣扎与妥协中灵魂所经受的痛苦正是陈谦在小说中所呈现的。
二、解蔽:历史创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给那个时代的人和整个民族造成了持久的精神伤害。因此,对“文革”的叙述和反思成为近代华人文学的重要题材。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陈谦在作品中对这段历史也有所涉及。但她对“文革”的反思有另一种自觉,即所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这一历史记忆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创伤以及在这一非常时期中人性所爆发出的丑恶。她对“文革”的反思没有停留在控诉个人或时代上,而是追索这一时代下的人性和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可以讲,陈谦的写作“在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中,当得起另一种‘文革’的故事”[5]。《下楼》和《特蕾莎的流氓犯》讲述了“文革”那段特殊经历给人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与其讲她在反思“文革”,不如说她在反思被特殊历史所遮蔽的人性。
《下楼》以对话的形式描写了叙述者丹桂以及她在交谈中提到的康妮的遭遇。她们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文革”的记忆给她们造成了持续性的伤害。“文革”期间,丹桂的父亲自杀,那时她只有3岁,从此便经常梦见父亲被堵在黑暗的深巷中冲不出来。而康妮的丈夫唐先生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跳楼身亡,受此打击的她再也不肯下楼。丹桂难以摆脱的梦境以及康妮拒绝下楼的怪异行为都是“文革”在她们心灵留下的创口,而时间并不能抹平这些创伤。历史所造成的阴影一直缠绕着她们的生活。长大后,丹桂试图顺着现代医学的藤蔓寻找一条通向心灵的渠道——创伤心理学。她尝试治愈心灵创伤的行为实则也是其心灵创伤的表现,正如戴比教授所说,“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心理创伤,那就是最典型的心理创伤的表现”[6]。
陈谦在丹桂与康妮这些心灵受创个体身上,将“个人创伤的治疗与对历史的反思融为一体”[7]。面对“文革”的创伤,丹桂和康妮采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康妮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来逃避遗忘,而创痛在时间流里却愈加深了;丹桂则直面内心的隐秘与恐惧,亲自触碰心中不可诉说的疼痛。通过两位主人公对待心灵创伤的不同方式,陈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面对历史的过失,回避不仅解不开当下的精神困境,还会带来更深的伤害,只有直面过去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样未来才有可为。这种回望的态度,正是陈谦在小说中竭力想表达的。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陈谦曾说:“在很多人选择忘记的时候,我开始回望。当我有限的目力停留到‘文革’这只庞然大物时,《特蕾莎的流氓犯》记写下的是我的叹息。我们如果肯于自省,又足够诚实,亦有可为。”[5]陈谦以直面历史的坦诚,将被时代遮蔽的一切置于阳光之下,不惧过去,不惑未来,不迷于表象,不执于问责。
《特蕾莎的流氓犯》获得了首届郁达夫文学奖,其颁奖词是:“陈谦的这篇小说从一种特有的个体生命史进入‘文革’,在追述历史对个人成长伤害的同时,又将个人对历史劫难的责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青春记忆,忏悔意识,心理和精神的自我救赎,都被作者结构进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北美的框架里。”[7]少女时期的特蕾莎(原名劲梅)举报了一个“猥亵”她的男孩王旭东,以致王旭东被定为流氓犯,受到严厉的惩罚。劲梅内心深处其实是喜欢这个男孩的。然而,他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的场景引发了劲梅心中的妒忌和愤恨,“她为了她13岁的嫉妒,利用了那个时代”[8],使得原本懵懂美好的青春悸动变得狰狞可怖。几十年来,这个件事犹如怪兽般缠绕在特蕾莎的心头,使她无法释怀。疼痛的记忆给特蕾莎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但陈谦并没有将这些过错推给“时代”以求得个人的自我谅解。特蕾莎多年来内心的“不安宁”正是人性中善与恶之间的激烈博弈,而陈谦说自己写《特蕾莎的流氓犯》“就是要从人的内心,对自己的过失拷问。因为“文革”是每个人的“文革”,这是我意识到的问题。当那种邪恶的风气盛行时,每个人内心里邪恶的东西就可能被唤醒的”[9]。特蕾莎和王旭东的行为在那个特殊时代下是人性阴暗面的一次爆发,而不是集体犯罪或者是社会风气使然。因此,解蔽了历史作为一个集体的过失,是否还能将一切归罪于“时代”而回避个人良知的问责?答案是否定的。
由此,陈谦对“文革”造成的历史创伤的反思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正如汉娜·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所提到的,“集体无法为个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将非常时期的个人的行为归咎于集体,那么就相当于说我们都获得了免责,谁也不需要为历史错误承担责任”[10]。如果集体成为“作恶”的借口,那么人性中的丑恶就可以打着时代的幌子如洪水猛兽般涌出,人性的“恶”被遮蔽,类似的悲剧只会被不断重复。所以,陈谦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声音:是时候来拷问人的良知与灵魂了。
三、选择:存在困境
从人物内心切入进行灵魂思考是陈谦文学创作的一贯风格,“灵魂才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只有它的主人知道,那就是无法遗忘的‘疼痛’和‘叹息’,它像蛇一样一直盘踞在每个人的心里,咬蚀着灵魂里的血肉,而所有的历史或现实的故事只是这些灵魂的陪衬而已”[1]。在前期的创作中,陈谦比较关注个体情感的满足、人物的心理动态及灵魂的痛苦,创作成熟后,她开始尝试通过人物内心的挣扎来探索人类的生存困境。在谈自己创作时说:“我写小说会关注人物的内心,就觉得关注人类生存的困境,永远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1]在《望断南飞雁》中,她通过南雁坚决地走出家庭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意义。人活着不仅是肉体的存活,更重要的是有鲜活的灵魂和饱满的精神世界。就像南雁始终坚信,“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你要去发现它,完成它”[4]12,“人不是随机地给挂在基因链上的一环,活着更不只是传递基因!而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4]45。曹文轩曾指出,人存在着,面对社会与人生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克服的困境,而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哲学或社会学层面表现人永无止境的痛苦。《望断南飞雁》是陈谦对当下遭遇和南雁相同生存困境的人群的精神空间和人生意义的思考;2015年发表的小说《无穷镜》则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类生存状态等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陈谦曾用“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11]来概括“无穷镜”的寓意。换言之,“我”的存在本是虚无的,通过外在的镜像折射而来。在空间上与“我”相对立的诸多他者是“我”可能的诸多“像”之一,也是对“我”影像的某种折射。正是这些“非我”的他者的存在,“我”的存在才得以显现,才有意义。因此,在“我”的无数镜像面前,“我”才能获得其本质认识,进而显示“我”的存在。《无穷镜》中的珊映抱定“要做夜里绽放的烟火”的人生信仰,通过奋斗从上海交大到斯坦福,并在硅谷成立自己的公司,成为3D影像技术领域的领军性人物。而当“成功”的珊映在遭遇婚姻事业的双重危机时,无意间结识了邻家的神秘女子安吉拉,两人惊人的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让珊映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安吉拉就是珊映的一个镜像,也是珊映的另一种可能。同样,郭妍、尼克和康丰都是珊映周围的镜像,也是珊映人生中无法重合的岔口,个体的存在正是在这些多面镜像下才得以显现。由此也衍发出陈谦对于存在的思辨:“我”何以存在?“我”的人生应该是哪种形式?这就是陈谦所探索的人类存在困境,即在人与人的互相关系中,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12]。具体到珊映身上,就是追寻像“烟花”还是像“一炷香”的人生;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实现”;走尼克式的道路还是追求安吉拉式的人生?陈谦在追问时并没有给珊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她笔下的康丰通过攀岩不断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正是作家所要昭示的。人生就是在这种“痛并快乐着”的不断追问中进行,正如西西弗斯一般,向着高处挣扎本身足以填满一个人的灵魂。
陈谦认为,“世界五彩缤纷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千差万别,因为这,就导致很多事情”[1],而外部的所有冲突都是由人的内心生发。所以,她将关于生命与存在的思索投之于人的内心世界,通过书写海外华人的心灵创伤,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多维度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从这种内向性视角里,陈谦所关注的并不局限于海外华人这一群体,她笔下的人物也是整体人类的“镜像”。情感困境、历史创伤与主体存在并不是苏菊、南雁、特蕾莎和珊映这样的个体现象,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局。对整体人类精神世界的观照是陈谦小说对新北美华文文学的超越之处,同时她的“灵魂小说”也为新北美华文文学创作开辟了另一种可能。
[1] 陈瑞林.向内看的灵魂:陈谦小说新论[J].华文文学,2013(2):90.
[2] 丰云.论华人移民中产阶级女性的精神困境:以陈谦作品为例[J].小说评论,2002(3):79.
[3] 陈谦.硅谷丽人[J].小说界,2001(6):62.
[4] 陈谦.望断南飞雁[J].人民文学,2009(12):19.
[5] 陈谦.另一种文革的故事:《特蕾莎的流氓犯》创作谈[J].北京文学,2008(5):21.
[6] 陈谦.下楼[J].上海文学,2011(4):11.
[7] 宋炳辉.陈谦小说的叙事特点与想象力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8):163.
[8] 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J].小说月报,2008(6):87.
[9] 黄伟林.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海外广西籍华人女作家陈谦访谈录[J].贺州学院学报,2014,30(2):7.
[10] 阿伦特 H.反抗平庸之恶[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16:153-161.
[11] 陈谦,王雪瑛.选择:转动命运的魔方:关于长篇小说《无穷镜》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6(3):86.
[12] 何可人.镜像的牢笼:评陈谦长篇小说《无穷镜》[J].南方文坛,2016(3):85.
TheExplorationofMentalPainsinChenQian’sNovels
CHEN M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4,China)
Traditional North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mostly expresses the external world of heterogeneous cultural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n the depiction of homesickness,separation and loneliness,while Chen Qian,an American Chinese writer,focuses on the pains of people’s inner world.Chen Qian’s novels explore the spiritual distress in three areas:individual emotions,historical pains and human survival difficulties by describ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of a group of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between marriage and career,ideal and reality.
North American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Chen Qian; mental pain
2017-04-21
陈嫚(1991-),女,湖北鄂州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作家作品和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I 207.4
A
2095-462X(2017)05-0007-0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70915.1624.006.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7-09-15 16:24
(责任编辑张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