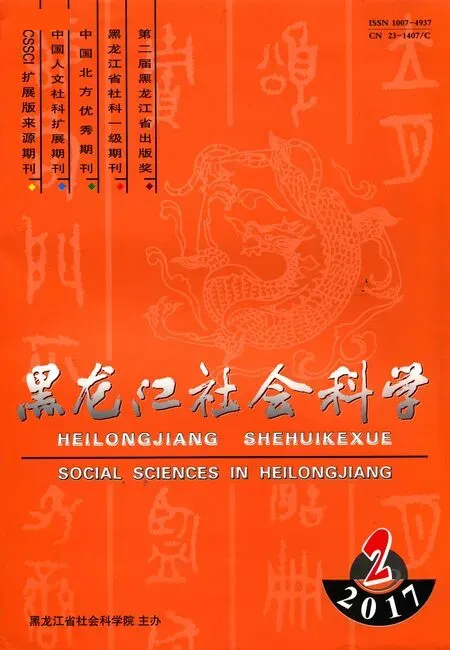民国时期行政审判机构之变迁
谢 冬 慧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1815)
民国时期行政审判机构之变迁
谢 冬 慧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1815)
中国历史上专门筹建和设立行政审判机构的时代当属民国,启动于清末效仿日本而酝设的行政裁判院,真正实践于北洋政府,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行政审判机构——平政院,在中国行政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法律现代化的推进和政治体制的变迁,行政审判机构的重建进入了官方和学界的视野。经过反复的论争之后,行政法院单独设立最终占了上风,并且存续15年之久,是中国近代法制最完备的行政审判机关。民国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审判机构应时而生,顺势变迁,对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与民众权益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政审判;机构变迁;设立争议;民国时期
审判机构作为审判的主要工作场所,它是审判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行政审判机构也不例外。民国时期行政审判机构几度变迁,从清末的行政裁判院到民初的平政院,再到后来的行政审判院、行政法院等,其职能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清末的行政裁判院只是草案设想中的行政审判机构,随着清朝政权而终结。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主管行政诉讼,负责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行为,就行政诉讼及纠弹事件行使审判权。而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法院,是在经历一系列论争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时期行政审判机构筹建和设立的背后,实质上是当时政治力量博弈的写照。
一、清朝末年行政裁判院的酝设
行政审判机构,通称行政法院,用以受理行政争议案件。而专设行政法院是大陆法系的通行做法,*“行政法院最早诞生于法国。法国大革命后,执政的资产阶级,为防止贵族势力盘踞的普通法院藉审判权来干扰行政运作,乃利用‘三权分立’学说,禁止普通法院受理有关行政权的诉讼。……至1899年之后,已成为行政案件可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诉,不必先经部长裁决,且由‘参政院’为最高行政法院。其他欧陆法系国家,也都在十九世纪参照法国之例,建立其行政法院。”参见王泰升《台湾法律史概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2版,第110页。随着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大陆法系的这种法律文化也被继受。清朝末期,随着变法思潮的促动,近现代意义的司法裁判机构也“呼之欲出”,除了普通裁判机构,更有行政裁判机构。1907年9月,清政府依照《日本行政裁判法》草拟《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其前言中表明预设行政裁判院的目的:“今各国有行政裁判院,凡行政各国之办理违法,致人民身受损害者,该院得受其呈控,而裁判其曲直,英、美、比等国以司法裁判官兼行政裁判之事,其弊在于隔膜,意、法等国则以行政衙门自行裁判,其弊在于专断。惟德、奥、日本等国,特设行政裁判衙门,既无以司法权侵害行政权之虞,又免去行政官独行独断之弊,最为良法美意,今采德、奥、日本之制,特设此院,明定权限,用以尊国法,防束蠹,似于国家整饬纲纪,勤恤民隐之意不无禆益。 ”[1]248
清朝末年行政审判机构是“西学”的结果,其直接的“蓝本”是日本。日本依据1890年的明治宪法正式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它是效仿大陆法系的产物,特别是德、奥的模式,在司法法院外专设行政法院进行行政裁判,而这种模式又借助于语言的优势直接影响了清末政府的制度模式。有学者考证:“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在《宪政编查馆拟呈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折》中已经有了增颁行政审判法,设立行政审判院的意向。在厘定官制草案中,已明定设立行政裁判院,并已拟具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2]
《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第1条明确规定裁判的对象:行政裁判院掌理裁判行政各官员办理违法,致被控事件。也即行政裁判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且是专门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机构,因为该草案第11条对审判权做了排除性规定,即行政裁判院不得受理刑事、民事诉讼。根据《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的前言及其条文不难判断,中国最早的行政法院——行政裁判院与其他近代意义的法律制度一样,是西学的产物。对此,国民政府司法院参事于1933年撰文指出:“考行政法院之制,在19世纪中叶,仿自法兰西,及于德意志,更由奥地利以传播于日本。我国往时,北京政府曾有平政院之设,北伐而后,久付阙如。查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约法第22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之权,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6条,规定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至于行政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已由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17日公布,1933年1月5日司法院院令派委员茅祖权负责筹备,此设立行政法院之根据也。 ”*参见王龄希《论行政法院》,载《法律评论》第10卷第24号,1933年3月。
国民政府司法院参事的文章揭示一个史实:民国时期的行政法院虽然表面上直接模仿了日本的行政裁判院,但其深层的根源和范本仍是法国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设置理念及制度。德国“在确定诉讼方法时,只有公法争议才能在行政法院进行”[3]。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因此行政案件理当在行政法院进行审理。
虽然当时对此观念曾发生争议,但清政府后来还是接受设立行政裁判院的意见。1907年“新政”时期草拟的《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明确特设行政裁判院,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形成督察院与行政审判院并存的格局。“督察院以中国传统方式纠正官邪、伸民怨,而行政审判院受理行政诉讼,以近代司法手段救济民权”[4]。理论上如此,但清政府却迟迟没有赋予实践,着手设立行政裁判院。
时隔三年,在立宪思潮*在行政诉讼制度正式见之于临时约法之前,清末最后十年宪政思潮的传播和立宪活动的展开,使立宪思想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影响。立宪思想的内容之一就是,国家机关也应遵循法律,尤其是行政机关的活动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如果行政机关的活动违法而损害了民众权益,民众就可以提起诉讼。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外国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制度也就逐渐地传播到了中国。参见李秀清《从平政院到行政法院——民国时期大陆型行政审判制度探究》,载《中国法律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9页。的影响下,清政府在《法院编制法草案》和《预备立宪逐年筹备清单》中明确设立行政裁判院的决定,但仍未落实到行动中。 1910年12月28日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第2条规定,各级审判衙门掌民事、刑事诉讼案件,而其关于军法和行政诉讼等另有法令规定者,不在此限。所以,各级审判厅无权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而行政裁判院当时亦没有设立,行政诉讼案件该由什么机关来受理,一直成为困扰清政府及民众的问题。
二、民国初年平政院的设立及运行
1912年1月,宋教仁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第14条规定:“人民得诉讼于司法,求其审判。其对于行政官署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则诉讼于平政院。”该草案曾提交参议院,但参议院接受此草案之后,仍主张自行起草,将草案退回临时政府。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1912年10月,发生号称“国民控告官署”第一案的民国大学告工商部总长刘揆一诉讼案。基本案情:民国元年,袁世凯接受民国大学的呈请,同意将前清翰林院的房屋拨给大学使用。及至大学接收屋产时,发现其早已被工商部占用。双方交涉均不相让,大学遂将工商部告到京师地方审判厅,当时刘揆一是第一任工商部总长,因此成为被告。被告方提出,早在民国大学申请之前,国务院已经同意将该地产交工商部使用,因此,“此案原由行政处分而起,与私法上之契约关系绝对不同”,即使是工商部侵害了该大学的所有权,也应该属于行政处分问题,而不是司法纠纷。但当时究竟哪里可作为行政诉讼的机关,谁拥有行政裁判权,一时还不明确,地方审判厅“是否有权兼理行政上之诉讼,并无法律规定”[5]。
民国初年,设立行政审判机构受到广泛关注。据考证,“民国初年,围绕如何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受理行政诉讼、处理官民纠纷,朝野曾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6]。 关于行政诉讼制度模式问题,当时的学者也有过激烈争论,主要有英、美、法模式和大陆法模式两种观点。时任教育部部长章士钊倾向于英、美、法模式,主张不设立专门的平政院,也无须制定单独的行政诉讼法,可以由普通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有关程序对因不法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诉讼进行审理;另一位学者汪叔贤也主张以普通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管辖,但又认为应依行政诉讼法专门程序审理行政诉讼。*参见汪叔贤《论平政院》,载《庸言》1914年第2卷第4期。而张保彝则倾向于大陆法模式,主张单独设立平政院,专门处理有关行政诉讼。*参见张保彝《平政院制度之研究》,载《宪法新闻》第15-16册。争论最后的结果是行政审判采取大陆法系的二元制审判结构,由专门机关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审判机构是平政院。
当时日本只有一所设在东京的行政法院,实行一审终审。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全国唯一的行政审判机关——平政院,也实行一审终审。北洋政府沿着“西学”的道路继续向前走,在司法制度的设置上效仿大陆法系,将行政诉讼、普通民事和刑事诉讼分开,各设不同的法院管辖。很明显,自民国时期开始,政府已有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之分。1914年设立的平政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行政审判机构。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平政院编制令》,以院长1人、评事15人组成平政院。该编制令规定,平政院直隶大总统,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但以法令属特别机关管辖者,不在此限。平政院审理纠弹事件,不妨及司法官署之行使职权。该编制令的颁布标志着平政院正式宣告成立,成为民国初年行政审判的专门机构,并且形成了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二元体制的司法体系。有学者指出:“该法令与清末《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诸多仿佛……平政院的设置可看作是晚清行政裁判官制草案的实现。”[7]可见,行政审判机构的设立自清朝末年《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开始,已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
有学者评价:“当时设平政院,以受理行政诉讼,与今之行政法院,名异而实同,其所以未仿英美等国由普通法院管辖者,在避免司法权侵犯行政权。”[4]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指出:“中国为采用大陆制司法制度之国家,即将行政诉讼与普通民刑诉讼分离;因之,于普通法院之外,需要掌握行政诉讼机关,临时约法及三年新约法均系如此规定。”[8]无论学界如何评论,平政院建立已成史实,它“犹行政裁判机关,所以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也。分记录、文牍、会计、庶务四科,皆直隶于院长,外分第一、第二、第三庭。每庭设庭长一人,评事四人中须有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二人”[9]。
平政院自1914年建立后,其发展并非顺利,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推翻二元制的司法体系,改用英美制,取消了平政院。该宪法第97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司法权,由法院行之。”第99条规定:“法院依法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全部案件交由普通法院来审理,意味着平政院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再为行政诉讼设立专门的机构。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预设,没有付诸实践,毕竟当时的中国法制行进在大陆法系的道路上。
台湾学者黄源盛认为,平政院是中国第一个行政审判诉讼机关,平政院的成立,是中国正式采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创举[10]。平政院的设立,意味着近代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基本确立。平政院成立后,北洋政府相继颁布《行政诉讼条例》《诉愿条例》两部重要的法律,对平政院办理行政诉讼的程序进行规范。
但是,司法经费的短缺,严重阻碍中央及地方法院的建制,也影响到行政法院的留存。学者范扬认为:“关于行政审判,究应设立独立法院,抑即并属司法机关,在性质上,原无一定,要须视其实际上,有无独立设立之必要,以决定之。如或行政诉讼事件,不甚繁杂,一时犹无设立多数法院必要,即将行政审判机关列入司法组织,自成独立一院;或即并设于普通法院,自成独立一庭,概使有特殊之学识与经验者,充当斯职。如是不特无妨碍,且足使其组织简单而易行也。”[11]其实,1913年的《天坛宪草》也主张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即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均由普通法院统管。可见,行政法院的设立并不顺利。
民国初年的行政法院——平政院的设立,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当时法制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为官者视人民为草芥,行政部门及其酷吏残害民众之违法案件屡屡发生,上诉到平政院的案件甚多,平政院进行了大量的审理工作。
三、国民政府设立行政法院之争
民国时期,“国人对于行政审判制的态度有的表示接受,有的则坚决反对”,*参见吕秉仁《宪法中的行政审判制》,载《东北论丛》1948年第1卷第1期。集中体现在对行政审判机关——行政法院的设置问题上。从世界范围看,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机关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行政诉讼之裁判,由司法机关行之者,例如英、美诸国,即属于此,无所谓独立的行政裁判机关之设置。第二,行政诉讼之裁判,设独立的行政裁判机关者,例如法、德、奥、日诸国,其行政裁判机关,与司法裁判机关,分离独立,凡关于行政诉讼之裁判,均属行政法院掌理之。第三,行政诉讼之裁判,由一般行政官署行之者,例如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希腊诸国,关于行政诉讼之裁判,既无独立的行政裁判机关,亦不归司法裁判机关掌理,即由一般行政官署行之。”*参见黄右昌《行政诉讼应归普通法院受理之我见》,载《时代公论》1933年第2卷第57期。也即是说,当时的世界立法存在着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和行政机关三种机构处理行政争议的模式。而在国内,当时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
第一,主张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裁判案件。理由有二:其一,依据宪法原则,人民与官吏,于法律上为平等,即应受同一法律之支配,乃宪法上一大原则,而凡反乎此大原则者,皆应在排斥之列。又查总理遗教:主张“官吏为人民之公仆”,更无分别审判之理。若以官吏身份,即另受特别机关之裁判,是假平等而非真平等也。其二,公法、私法之区别,乃学理上之分类,而非立法上之标准。凡属法律问题之诉讼,司法裁判机关,均应有裁判之权,固不必问其为国家与个人之法律关系。第二,主张行政诉讼应独立设置行政法院受理。主要理由两点:其一,司法官吏之知识与经验,大抵偏重民刑法方面,对于行政法方面之知识与经验,未能充分。其二,行政权与司法权,须分离独立,若令司法裁判机关管辖行政事件之争讼,则当付与以审查行政处分及取消或变更之权,是行政权为司法权所牵制矣。②可见,国民政府时期,行政法院的设置与否存在一定的争议。
国民政府官方一度坚持行政审判由专门法院管理的观点,但也发生一些变化。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曾设审政院,很快又撤销。史料记载:“民国十四年六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于第25次会议决议设立监察院,推鲍罗廷起草组织法;草竣后,提经第34次会议决议通过,交国民政府,旋复于第62次会议加以修正。至十五年十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又将《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为第二次之修正,通过后,即交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此法全文14条,规定监察院之职权凡六:(1)发觉官吏犯罪;(2)惩治官吏;(3)审判行政诉讼;(4)考察各种行政;(5)稽核财政收支;(6)统一官厅簿记及表册之方式。监察院不设院长,置监察委员5人,审判委员3人,并置秘书长,分4科,置秘书长、科长、科员、监察员各职员。”[12]356由史料可以判断:1926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规定将审判行政诉讼作为监察院的职权之一,也就是此后一段时期,广州国民政府的行政审判机关,名为监察院。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合一与分立问题在学界曾产生过激烈争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宠惠的观点。王宠惠作为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于1927年6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1928年8月出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一任司法院院长,他极力主张采用英美法系体制,因此主张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合一。主要理由:“行政法终将与普通法律合而为一,行政法院也终将同样被废止,那还不如从开始就采用英美法系的体制;另设行政法院必将增加国家开支,人民诉讼手续也将更加烦琐;行政法院的审判会有偏袒行政之虞;人民会轻视普通法院,对行政法院也会产生怀疑;实行民权之国,人民与官吏应于法律上平等,即应受同一法律之支配,而行政法即是使官吏与人民在法律上不平等。”[1]257-258在王宠惠那里,行政法院设置的意义不大。
与王宠惠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法院院长的张知本,他在谈到五权宪法体制下的司法建设问题时认为,在审判方面,可在司法院组织之下,设立民事庭、刑事庭及平政庭(或政事庭)、察吏庭(或吏事庭),分掌民事、刑事及平政、惩戒等审判事务,这样的司法院才是真正的五权宪法下的司法院。*参见张知本《五权宪法中的司法建设问题》,载《司法》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396页。表面上,张知本是将民事、刑事、行政等合在司法院统一管理,该观点似乎与王宠惠一致,但具体工作还是分开的,分属不同的分支机构管理,与孙中山倡导的五权宪法理念是统一的。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实行“五权”政治,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明定司法院中,普通诉讼与行政诉讼并立的二元司法体制。这也是当时大陆法系国家共同的做法。“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实行的是行政法庭自成一体、只处理行政案件的体系,作为这种体系的自然结果,行政法以自己独立的方式发展,并不像英美法系那样与普通私法缠在一起”[13]。
这种体制是效仿德国的结果,德国的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系统,它确保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争议,无论是产生于私人之间的纠纷,还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纠纷,都属于司法法院的管辖,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只要受到公共机关的侵犯,都可以向法院起诉。德国这种具有司法性质的行政法院的设置,决定了德国的行政法院以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为己任,以确保德国公民的司法救济权利,更加符合公正审判和实质法治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法院的非行政化,有利于对行政机关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行政审判机构单独设立最终占了上风。
1928年10月20日公布的《司法院组织法》规定:“司法院以司法行政、司法审判、行政审判三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织之。司法行政署综理司法行政事宜;司法审判署对于民刑诉讼事件,依法行使最高审判权;行政审判署依法掌理行政审判事宜;官吏惩戒委员会依法掌理文官、法官惩戒事宜。”[12]354不过,此后司法院下属的四大机构名称就发生了变化,据记载:“旋中央政治会议又将《司法院组织法》加以修改,经国民政府于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此修正案即将组织司法院之‘司法行政署’改为‘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司法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其余均照原案。”[12]355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判断:1928年11月的《修正司法院组织法》将行政审判署改设为行政法院,也就是在司法院之下设立行政法院,与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公务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列。1930年《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第109条明确规定:关于司法审判,设法院管理之。关于行政审判,设行政审判院管理之。其组织均以法律定之。与国民政府组织法相一致,实行普通诉讼与行政诉讼并立的二元司法体制。“我国现行制度,司法诉讼与行政诉讼分立而非混合。凡系形式上属于行政法院所处理的事件,不必尽合于实质上的意义。换言之,即系行政法院对于行政官署自由裁量范围内之处分是否正当。固亦不失为形式上的行政裁判。”[14]“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系直接仿效欧陆诸国及日本创建而成,属大陆法系。”[15]具体说,国民政府的行政法院源自于清朝末年仿效日本筹设的“行政裁判院”。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行政法院受理行政审判案件,也是追随世界各国法院体制潮流的结果。因为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审判“系就个别具体案件,运用法律之谓”,审判属于法院之职权,由其独立行使,不受任何干涉。各国具体模式有所不同:“瑞士、比利时则于司法机关中特设一部管辖之;法兰西则以参事院及州参事会兼管之;日本、奥地利则特设行政法院掌理之;普鲁士则于特设行政法院以外,以州参事会兼之。”[12]1052-1053在行政法最为发达的法国主张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相互独立,“行政法独立于普通法最明显的表现在于行政司法机构与普通司法机构是分立的;但这一分立首要的缘由是这样一种观念,是它促成了特殊司法机构的建立,这就是公共权力的特权”[16]。该行政法影响了德国及后来的日本、奥地利。
国民政府最终直接选择日本、奥地利的模式,《行政诉讼法》第1条明定行政诉讼归行政法院受理,当然该法条的制定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此法依《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3条及《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第1条、第6条之规定,采用日、奥制,以行政法院为受理行政诉讼之机关(第1条)。”[12]1053无疑,国民政府行政法院的设置与北洋时期平政院的设立模式一致,或是顺应了历史的惯性所致。
由上可知,国民政府官方对于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合问题,宏观上采纳“合一论”,即受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院与受理民刑案件的普通法院归属于司法院统一管理;而微观上则实行“分立论”,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相对独立,各自受理属于自己的案件。毫无疑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审判归于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法院是国民政府依法设立的审理行政案件的审判机关。
四、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正式设置
从司法院组织法,很容易判断行政法院的归属,也即行政审判署直隶于司法院,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而早年的平政院则隶属于掌握行政大权的大总统,并非属于司法系统。对于国民政府的行政法院归属问题,《民国司法志》有过相应的记载:“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决定实行五权制度,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分掌治权。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与其他四院立于平等地位。是年十一月,公布司法院组织法,司法院即于同月十六日成立。其直属机关凡四:(一)司法行政部,(二)最高法院,(三)行政法院,(四)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参见汪楫宝《民国司法志》,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1页。
1930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下过一道“训令”,指出速成立行政法院,并且对行政法院成立之前的行政案件的受理机构,提出指导性意见。*参见《第四六号令直辖文职各机关(行政诉讼在行政法院未成立以前得暂行援用旧有之诉愿法提起诉愿由)》,载《国民政府公报》1930年第386期。其实,在行政法院设立之前,国民政府不断收到请求行政诉讼的材料,如1931年在《司法公报》上刊登一公民不服再诉愿提起行政诉讼,因无法院接受被退还材料。甚至针对当时的江苏通海垦务公司及上海唐海山等不服当地政府之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司法院在报刊上直接解释:诉愿事件援用前北京政府施行之诉愿法,其行政诉讼俟行政法院成立后办理。 可见,当时设立行政法院的确是社会实践的需要。
学者郭殊指出:“从清末法制改革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行政法院成为中国近代行政诉讼体制的一种选择。原因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中国法制近代以来即有继受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倾向,而专设行政法院正是大陆法系通行的做法,制度较为成熟,便于法制后起国家学习;第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造成官本位的社会意识,行政异化现象严重,必须设立专门机关,对公民受到行政机关侵权情况进行救济;第三,普通法院的法官缺乏行政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有利于对行政案件进行公正合理的审判。”[17]这种判断也不无道理,很值得信赖。
但是,国民政府司法院成立后,司法机构的建立较为迟缓。由于司法经费的短缺,严重阻碍中央及地方法院的建制。而在国民政府个人关于宪法草案中,对行政案件设置了不同的机构。例如,吴经熊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中,则提议建立国事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统一解释行政法令。遇行政法令之解释与普通法令之解释有冲突时,由国事法院与最高法院各推相等之人数,合组委员会互相讨论,以求统一。又如,在张知本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主张由最高法院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司法院不用设行政法院,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均由最高法院受理,司法行政部处理司法行政,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不属国民大会管辖之弹劾案件。对此,社会各界意见较大,学界提出“行政法院应早设立或在中央法院暂设行政法庭”的建议:“北京政府时代,人民权利受行政官厅违法处分者,犹得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国民政府为革命的政府,转无此种保障人民权利之机关。致数年以来,官厅违法滥权,人民权利,横受摧残,竟无呼颌之门,实属现在政治上之一缺憾。甚望此番三中全会通过从速成立行政法院之议案,使行政诉讼案件,早见解决。如以财政困难,组织匪易,则行政法院原为司法院所管辖,同属司法权之作用,不过一为纯粹的司法,稍有区别。仅不妨于中央法院审判处(最高法院)内,除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外,暂设行政法庭数庭,处理行政诉讼,其评事应由行政法学知识宏富或具有行政经验者担任,则经费既省,责任亦专,未始非权宜可行之计也。”*参见赵琛《讨论几个司法行政组织的问题》,载何勤华、姚建龙《赵琛法学论著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48页。
行政法院的名称在国民政府初期为“行政审判署”,1928年10月颁布的《司法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司法院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及官吏惩戒委员会组成。”按其第6条规定:“行政审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宜。”1928年11月7日,中政会第162次会议改司法行政署为司法行政部,改司法审判署为最高法院,改行政审判署为行政法院[18]。“民国二十年一月,司法院以政局统一,百度更新,审判全国行政诉讼之最高机关,应从速成立,爰拟具《行政法院组织法草案》13条,呈由国民政府令交立法院审议。”[12]1056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6条规定:“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第一次在立法中使用“行政法院”这一机构名称。
1932年民国政府对组织法进行修订,但行政法院的地位没有改变。居正就任司法院长后,于1932年提出《行政诉讼法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并获通过。1932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具体规定行政法院的组织与职权。据史料记载,1932年11月20日,颁布《行政法院组织法》,其他3个机关都相继建立,唯独因经费及法庭问题,行政法院历时4年,至1933年初尚未建立起来。*参见《司法院将筹设行政法院》,载《法律评论》10卷1号,1933年1月22日。但同年2月,情况有所变化,此时的国民政府编制行政法院经常费、开办费支出概算书,5月份该概算书获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开办费1万元,经常费每月1.4万元。*参见中央统计处《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行政法院组织之完成》,1933年11月17日。经费问题解决,行政法院的建立指日可待。
1933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正式成立,院址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具体来说,1933年6月2日,国民政府任命茅祖权*茅祖权,字泳薰,1883年生,江苏海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后加入同盟会。1912年后任国会议员,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江苏省民政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年底,司法院以院令的形式命茅祖权负责筹备行政法院,后出任首任院长。接着任司法院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50年在上海被人民政府逮捕,1952年病死狱中。、于恩波、王淮琛、胡翰、梅光羲、王子弦、王芝庭、王建祖、苏兆祥和叶大澄等10人为评事,其中茅祖权为首任院长,茅祖权与于恩波为庭长。6月23日,也即《行政诉讼法》施行当天,院长茅祖权视事(就职治事),启用印章,标志着行政法院正式成立。*参见《行政法院正式成立》,载《申报》1933年6月24日第9版。
行政法院成立后并未马上受理案件,而是先由院长部署院内行政事项,配备必要人员。1933年6月24日,司法院公布《行政法院处务规程》,其中第27条规定:“书记厅由书记官长承院长命令指挥监督书记官分掌事物。配置各庭之书记官应受庭长评事之指挥监督,每庭得以一人为主任。又据《行政法院书记厅办事细则》,书记厅下辖会计股、文书股、总务股。”同年7月27日,国民政府任命朱锡百为行政法院书记官长。需要说明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初创时的院长、庭长、评事、书记官长、主任书记官和书记官等人员合在一起,规模约在20~30人左右,是当时中央机关中最小的一个部门,知道它的人也很少,以致很多人将行政法院与行政院相混淆。
行政法院在配备人员的时候,非常重视人员的素质和条件。根据当时的《法治周报》报道,关于行政审判的主要人员——评事人选做了专门要求:“依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于行政法院之裁判不得上诉或抗告。第四条规定行政法院之判决,就其事件有拘束各关系官署之效力。是行政法院对于各官署之行政处分,有最终裁判之职权。换言之,人民虽因不服官署之再诉愿决定,或因官署三十日内不为再诉愿而提起行政诉讼,经该院裁判后,行政处分即发生确定力,另无救济之道矣,行政法院既有如此之强大职权,则司此种裁判职权之评事,自非特别注意其人选不可……自以熟识法律而兼富于行政经验者充任之为宜,而此项人才如何罗致,如何配置于各庭,自应予以深切之注意,以期贯彻不法行政之救济主旨。评事之人选,尤应注意其平时之操守。若评事受理行政诉讼,或为威胁,或为利诱,瞻循顾忌,颠倒是非,又何能平反违法之行政处分?又何能谋人民之权利保障?故评事之人选,一方则须其兼富于司法及行政之经验,一方则须其具有不畏强禦守正不阿之精神。”
此外,对法官要求也较为严格,依据1932年4月公布的《修正司法院组织法草案》,考核法院之确定判决,如发现承办法官有违法失职情事,得依法交付惩戒,或加以警告[12]355。那么,行政法院的人员配备就位后,随即正式受理行政审判案件。 1933年8月22日,田成明等人作为原告,因提充净土寺庙产不服江苏省政府决定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法院于第二日正式受理,并于1933年12月8日做出判决(判字第1号),这是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所受理的第一起行政审判案件。
田成明等因提充净土寺庙产不服江苏省政府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案,详见案件史料:*参见《田成明等因提充净土寺庙产不服江苏省政府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案》,载《法令周刊》1933年第192期。
要旨:(一)提起诉愿期间固为诉愿法第五条所明定,但提起诉愿虽已逾期,而在期间以内曾向原处分官署为不服之声明者,仍应认为合法。至书状纵令程式稍有欠缺,而于事件实体上不生影响,自不能据为攻击诉愿决定之理由。(二)行政机关之处分除了在职权范围以内依法得以自由裁量者外,必须有法规之依据。
原告:田成明等83人(详原卷)。
代理人:朱成邦,年龄44岁,江苏省六合县中所乡人;涂晓庵,年龄51岁,江苏省六合县中所乡人。
被告官署:江苏省政府。
原告因提充净土寺庙产不服江苏省政府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所为再诉愿之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到本院审理判决如下:
主文:原告之诉驳回。
事实:缘江苏六合县中所集净土寺管有田山等业,民国十九年五月间,原告朱成邦等指该寺管田山各业。内有凉帽山地涂公保陈兴圣三户绝产,原属地方公产,以举办保卫团需费为词,呈请县政府准予收回,以作防务基金。该寺住持尼开慧则主张:此项寺产系前清末年由地方董甲立约捐助,早经更名过户执业已阈20余年,并非公产,亦具呈县政府,请驳斥朱成邦等之请求。经六合县政府令由第七区区长查明,议覆亦认此项产业原系地方董甲立约归庵执业,惟以防务重要,拟就该产每年孽息中分作三股以二股充作防费,以一股留作庵用。县政府认所拟办法尚属妥协,于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指令该区长,准予备案。即由该区长督饬该乡长副依据办理,惟并未做成处分书,通知关系人。嗣尼开慧得悉,乃呈请六合县党部函县取消成议……
理由:本件再诉愿系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决定,于六月八日送达于原告,当时行政诉讼法尚未公布施行,本院亦未成立。原告曾于同年七月十二日向行政院声明提起行政诉讼,自应认为法定期间内已有合法之声明,仍予受理,特先说明。本件可分两点论究之:
(甲)江苏民政厅受理诉愿是否合法,按提起诉愿期间固为诉愿法第五条所明定,但提起诉愿虽已逾期而在期间以内,曾向原处分官署为不服之声明者,仍应认为合法。本件尼开慧请收取消成议之原呈虽非迳呈原处分官署,然既经由县党部以公文转达于县政府,自应认为已有不服之声明,民政厅受理诉讼尚无不合,至诉愿书状纵令程式稍有欠缺,既于事件实体上不生影响,自不能据以为攻击诉愿决定之理由;
(乙)六合县政府原处分是否合法,按行政机关之处分,除在职权范围以内依法得以自由裁量者外,必须有法规之根据。据本件净土寺所管田山等业无论其来源如何及是否已取得所有权,然历年归该寺管业,则为明显之事实,即令仅属占有亦应受法律之保护。六合县政府仅据一部分人之请求及区长之议覆,毫无法规上之根据,遽为提拔。该产业孳息之处分,自难谓为适法至原告指此项田产原属地方公有主张收回,姑无论所称是否属实,然此乃私权之争,应属民事诉讼范围,亦非行政官署所能裁断。诉愿决定认原处分于法不合,予以撤销,原决定驳回再诉愿均无不当。
依上论结本件原告之诉为无理,由爰依行政诉讼法第21条判决如主文。
从案件史料描述可见,第一起行政审判案件在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成立之前就已经提起,表明此时的行政法院是应社会民众的诉求应运而生。
有学者指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较北洋政府时期的平政院有五大改进:第一,性质上,行政法院属于司法机关,隶属于司法院;第二,组织人事上,行政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纠弹官员违法案件则由监察院与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院长及评事任职资格要求更高;第三,受案范围和审级制度上,凡属行政处分,不论其关于何种事项,均可提起行政诉讼,并可附带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讼,行政法院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但兼采德国、奥地利制度,规定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第四,被告行政官署不派诉讼代理人,或不提出答辩书,经行政法院催告无效,可以职权调查事实,直接判决;第五,关于行政诉讼准用民事诉讼的规定,使该法更为完善。”[17]鉴于这五大改进,有学者指出:与北洋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是中国近代法制最完备的行政审判机关”[4]。
但是,1934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及其修正案只字未提行政法院,而是提到由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表明国民政府对行政法院的职能未予充分肯定。后来的三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都规定,司法院为中央政府行使司法权之最高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公务员惩戒及司法行政。实际上,这里的司法院与1928年司法院的职权是类似的,它是行政法院及最高法院的上级机构。尽管宪法中未提到行政法院,但是行政法院是存在的,这从当年的行政诉讼裁判文书题头“行政法院判决”表述中可以得到验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组织设立的行政法院,存续于1933年至1948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机关,是我国法律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的一次果敢的尝试。”[19]不过,即使设置了行政法院,数量也极为有限,它与普通法院的设置不同。据记载,行政法院仅设于国民政府所在地,各地方既没有设置地方行政法院,也没有设置分院。可以说,国民政府设置的行政法院是属于中央一级的行政诉讼机构,与最高法院平行而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法院,是中国近代法制最完备的行政审判机关。它的创建对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民众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简言之,清朝末年的行政裁判院成为民国时期行政法院的“祖先”,北洋政府的平政院是民国时期行政审判机构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法院则是民国时期较为完善的行政审判机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审判机构应时而生,顺势变迁,实质上是当时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折射出民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理性的行政司法诉求。
[1] 蔡志方.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M].台北:三民书局,1993.
[2] 杨寅.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57.
[3] 于安.德国行政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6.
[4] 张生.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J].行政法学研究,2002,(4).
[5] 吴相湘.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M].台北:文星出版社,1962:479-480.
[6] 沈大明.民国初年关于行政诉讼体制的争论[J].社会科学,2007,(4).
[7] 杨海坤,朱中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艰难的原因探析[J].行政法学研究,1999,(4).
[8]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9.
[9] 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第725卷[G].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70.
[10] 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J].研究汇刊,2000,(4).
[11] 范扬.行政法总论[M].邹荣,勘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221-222.
[12]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下册[M].张知本,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5.
[14] 朱采真.行政诉讼及诉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
[15] 刘铮.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创建问题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16] [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M].龚觅,等,译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115.
[17] 郭殊.中国近代行政法院制度之变迁[N].人民法院报,2003-07-21.
[18] 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357.
[19] 郭腾云.论民国行政法院土地案件的裁判[J].沧桑,2010,(4) .
[责任编辑:肖海晶]
2016-11-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行政权力制约机制研究”(14FFX026);2014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司法管理制度改革与法治江苏建设”(2014ZDIXM017)
谢冬慧(1969—),女,安徽池州人,教授,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从事司法文化研究。
D926.1
A
1007-4937(2017)02-00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