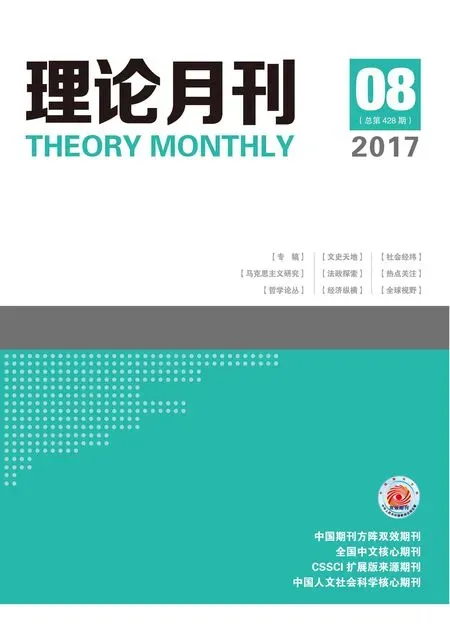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内生逻辑与理论维度
□王学军
(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河南南阳 473061)
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内生逻辑与理论维度
□王学军
(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河南南阳 473061)
先秦道家哲学本质上是我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古典生态哲学。先秦道家生态哲学内生逻辑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万物“同源性”的认识,生态平等观、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知足”“知止”的开发观、“少私寡欲”的消费观都是这一认识衍生的结果,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先秦道家生态哲学有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三个维度。先秦道家认为,“道”是宇宙时空的起源与中心,外显为天道(自然秩序),天道是万物存在、运行的价值来源与最终依据;社会秩序的构建及运行应当符合天道,无为而治方能和谐、均衡、稳定、长久;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精神的超越与自由,人可以通过内心体悟来达到天人未分的自然状态,从而摆脱物质与欲望的奴役。
道家;生态哲学;内生逻辑;理论维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在外在条件无明显变化的前提下,生态系统趋于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组织结构趋于和谐自治,并具有一定的弹性恢复能力。某种意义上,生态学是“专门研究和谐的科学”,为“更有生机的、协调和谐的人类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模式”[1]419-420。生态、和谐两词不仅是事实描述与状态形容,还具有价值导向意义,指向人类合乎自然的本体存在方式。先秦道家以“道法自然”为基本原则,主要表征是“关心自然环境……更加倾向于自然主义”[2]49-50,“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3]14,是我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古典生态学,暗合现代生态学的价值导向。先秦道家生态哲学具有独特的内生逻辑,其理论结构有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等三个维度。
1 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内生逻辑
起源决定本质,先秦道家生态哲学内生逻辑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万物“同源性”的认识。《老子》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3]169这里老子清晰地认识到,“先天地”而生的“混成”物,为天地万物生成的共同源头,即“天地母”。老子面临的问题在于意会之外的言传问题,即对于这一源头,定性之外如何进行命名和具体描述。“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4]488(《庄子·天道》)。老子明显感觉到,在万物本源这一终极问题上语言的乏力,现有词句无力承担这一重任。老子不得不采取另造词义、模糊形容的方式来勉力而为:关于命名,《老子》第二十五章云“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3]169;关于具体描述,《老子》第二十五章云“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169。这种“强字”、“强为”,距离老子心中对万物本源的感知、体悟依旧有距离,只是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背后仍然有不能名、不能言的部分,因此《老子》第一章开头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3]73拨开文字言传的迷雾,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道家对万物同源的认识,道家将万物的本源命名为“道”,由此化生出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233(《老子》第四十二章)。
由万物同源这一原点出发,我们可以梳理、整合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内生逻辑。
一是生态平等观。道化万物、万物同源,万物都是“道”的衍生物,因而万物之间虽有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差别,但都有各自存在的权利、价值和意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不同的生命形式平等地共存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4]577(《庄子·秋水》)。立足“道”这一本源,庄子“齐物论”(主观认识上消除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以达到万物平等的境界)思想也由此而生。生态平等观敬畏生命,尊重各类生命形式,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不再视人类为价值判断、利益衡量、道德评价的唯一主体。
二是天人合一观。从同源性出发,人类自诞生起与自然万物便有着天然的联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79(《庄子·齐物论》)。天人合一的本质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平等交往,互不侵害,“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4]336(《庄子·马蹄》)。天人合一观承认自然万物都具有独特的生命意义和平等的内在价值,人类只是其中一员,不过分夸大人类的优越性、特殊性。人类与万物当和谐相处,相生相长,不寻求人类对自然的单向征服、控制与支配。
三是道法自然观。万物因道而生,都是“道”之一体,各得其所,各按天性发展。《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169这里的“自然”指事物因其本体、本性而具有的存在方式、表现状态、运行方式,即一般所说的“自然而然”。道生成万物,而不加以干涉或主宰万物,“生而不有”,任万物自化自成,道效法、遵循万物的自然,因而《老子》第五十一章云:“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3]260道法自然观强调顺应万物本性,遵循自然规律,体现了对事物多样性的尊重。
四是“知足”“知止”的开发观。道家认为和谐是人与自然相处的理想状态,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能破坏自然万物的和谐。因此,道家强调“知足”“知止”,规范人类行为的界限,即合理利用、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遵循自然万物固有的限度,反对过度开发索取、破坏生态平衡。只有这样,人类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同时不会与自然对立,避免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241(《老子》第四十四章)。
五是“少私寡欲”的消费观。与“知足”“知止”的开发观相应,道家在消费观上强调崇俭、节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3]147(《老子》第十九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咎莫懵于欲得”[3]245(《老子》第四十六章)。道家对放纵物质欲望、不知满足地追求感官享受持批判态度,强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3]118(《老子》第十二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3]241(《老子》第四十四章)。
由上可知,道家生态哲学内生逻辑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万物“同源性”的认识,生态平等观、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知足”“知止”的开发观、“少私寡欲”的消费观都是这一认识衍生的结果。
2 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宇宙时空维度
轴心时代(前800—前200)的东亚地区[5]7-8,道家对宇宙时空的关注远多于其他学派。这里的宇宙时空,主要指道家对人类生存的时空连续系统的源头、演化、极限、秩序等具有终极意义问题的探讨。这是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其“天道”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宇宙起源。老子明确提出“道”是宇宙时空的起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3]169(《老子》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233(《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之初,宇宙开端处于“无状之状,无物之象”[3]126(《老子》第十四章)的混沌状态,时空、万物尚未生成,但已蕴含生机,有萌发之势,“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3]156(《老子》第二十一章)。
第二,宇宙演化。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过程,“无,名天下之始;有,名万物之母”[3]73(《老子》第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3]226(《老子》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233(《老子》第四十二章)。与此相似,《庄子·天地》云“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4]424,《庄子·庚桑楚》云“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4]800,《淮南子·原道训》云“夫无形者,物之太祖也”,《淮南子·说山训》云“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
第三,时空合一与转化。在宇宙起源与演化的基础上,老子认为道生时空,混沌状态下时空合一,不分彼此,时间、空间开始于混沌状态的结束。时间具有无限、运动、变化的特征,空间具有无限、独立、稳定的特征。因“道”而生的天地物我,在时空上具有动态转化的可能性。此即《老子》第二十五章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169
第四,天体运行。在北半球,由于地球自转的中轴为南北极,而北极星正处在地轴的北部延长线上,所以夜晚看天空的北极星几乎是不动的,其他星辰则看似都围绕北极星而转动。此外,由于地球公转半径(约1.5亿公里)远小于北极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约400光年),因而一年四季里,人们立足北半球,看到天空中北极星的位置都是在正北方不动的。因此,从天体的视觉运动出发,道家视北极星为天穹的中心和枢轴①实际上,由于岁差,即地球自转轴周期性缓慢摆动(约25800年一个周期),北极星并不是位置不变的某一颗星。老庄生活的时代,北极星为小熊座β星(北极二),并延续了两千年,即公元前1500至公元500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让当时的人产生永恒之感。现阶段北极星则是小熊座α星(勾陈一)。根据天文测算,公元4000年左右,仙王座γ星将成为北极星;公元14000年左右,天琴座α星织女一将成为北极星。,《老子》第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3]115、《庄子·齐物论》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4]66。这也是道家具有终极意义概念的“道”“无”“一”等词的天文学来源。
第五,哲理化的宇宙秩序论。从天体的视觉运动出发,道家认为“道”是宇宙时空的起源与中心,具有普适性、绝对性、终极性意义,“道是唯一永恒的,因而是绝对宝贵的”[6]232。《老子》第三十九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一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3]221这里的“一”即“道”,天、地、神、谷、万物、侯王皆得道而生,失道而亡。当“道”“一”的普适性、绝对性、终极性被确认之后,道家就将其视为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并试图将过去、现在观察到的、感觉到的、体悟到的各种宇宙时空现象纳入“道”的规范下。
道家认为和谐完美的宇宙、自然秩序是道的外在显现,包括日月升落、星辰运转、四时推移、万物变化等。《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惽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4]735这里的“明法”“成理”“序”,本是人对四时、万物观察、思考、分析、归纳的结果,但道家却视为由道化生的秩序、法则,“天道”(宇宙时空秩序、法则)也由此而生,并成为万物存在、运行的价值来源与最终依据,“既是秩序,也是生万物的实在根基,也是一切存在的永恒原型的总体”[6]232。
3 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社会秩序维度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战乱不断,礼崩乐坏,周礼维系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破坏殆尽,周敬王十年(前510)之后诸侯不再尽力于王事②《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周敬王十年(前510)“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以令役于诸侯”。这是目前史籍关于东周诸侯勤王之事的最后记载。,逐渐进入以诈力相争的战国时代。顾炎武《日知录》论春秋、战国之异云:“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7]749-750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重建或恢复社会秩序成为当时各家学派关注的焦点,先秦道家对此有着独特的思考,构成其生态哲学的社会秩序维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3.1 对以周礼为代表的人为社会秩序的不满与失望
乱世纷争从反面加深了部分人对之前稳定社会秩序的周礼的认同感,如孔子《论语》用“礼”多达七十五次,多次称赞西周制度及其始创者周公,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反对悖礼行为,试图恢复周礼规范下的社会秩序。然而,春秋末至战国作为大转折时期,旧有姬周礼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要,趋于制度化解体,一些士人也不再服膺周礼。从礼崩乐坏、战乱不断的现实出发,道家开始反思以周礼为代表的人为社会秩序,认为其不合天道,并没有天然的合理性,“非天然的制度”[2]179,反而是乱世之源,仁义礼智的负作用明显,因而多加以批判,如《老子》第十八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145。《老子》第三十八章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3]215。《庄子·胠箧》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4]350。
3.2 对人为秩序出现之前的自然秩序的向往
基于对人为社会秩序的不满与失望,道家推崇人为秩序出现之前的自然秩序,时间溯源至三代之前的上古时代,“引导人们远离文明的状态”[8]238。《老子》第八十章描述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云:“小国寡人,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民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345。这是远古蒙昧时代的原始生活状态,民风淳朴敦厚,生活安定恬淡。与此类似,《庄子·缮性》叙述上古人类的生存状态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4]550-551之后则是自然状态消失,“逮德下衰”“世与道交相丧”的人为秩序阶段,“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4]551-552。
3.3 天道与人道关系
道家认为,人间社会当循天道而行,趋于和谐、均衡、稳定、长久,这是一种“合目的性”①此概念来自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这里将它作为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来使用。道家认为,宇宙的合目的性,是自然在其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的总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趋向于完美、和谐的趋势,人间社会也应当如此。合目的性在此具有本体意义,反映了世界运行的可期待性,既是事实描述,也是价值判断。的价值判断。《老子》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3]336这里老子将“天之道”与“人之道”进行对比,认为“人之道”应该效法“天之道”。老子把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的现象归之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自然规律,因此希望人类社会改变“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有道者”当效法自然,做到“损有余以奉天下”。这体现了道家社会和谐和人类平等的思想。然而,现实社会中,人类社会运行法则往往有悖于自然规律,“损不足以奉有余”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固,两极分化,严重失衡,难以长久维系。《老子》第七十五章指出当时统治者与民众的严重对立与尖锐矛盾,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3]330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将导致上下相攻、社会大乱,“民不畏威,则大威至”[3]323(《老子》第七十二章)。
3.4 无为而治
基于上述人为秩序(人道)、自然秩序(天道)的比较反思,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统治者应当节制欲望、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顺应自然变化不妄为,避免过多干预,依靠民众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依靠民众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从而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的幸福最可靠的是通过宇宙自然法则的和谐来促进”[6]239。因此,《老子》第三章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3]86《老子》第五十七章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280
3.5 反智倾向
社会秩序的出现是人类智慧发展、知识进步的结果,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道家用审视、怀疑的眼光看待人类理智的发展,“社会邪恶的事情其实就是文明自身投影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潜藏于这种投影背后的虚假人类意识的一部分”[8]218。《老子》第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3]250这里老子将“为学”与“为道”对立,认为外在的经验知识积累越多,越容易产生机智巧变、私欲妄见。与此类似,《庄子·缮性》云:“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4]547技术、工具作为人类理智的产物,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道家认为它们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损害人心的淳朴,增加人的欲望,从而远离天道,因而反对应有新技术、新工具。老子设想的小国寡民社会,放弃了各种器具的使用,“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3]345,甚至放弃了文字这一人类文明的标志,退至结绳记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3]345。与此类似,《庄子·天地》云:“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愲愲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4]433-434这里道家视机械、机事、机心三位一体,均为道之阻碍。
4 先秦道家生态哲学的个人存在维度
4.1 “以物易性”的异化观
道家敏锐地意识到,人的异化主要源于过度依赖物质力量和过度膨胀的欲望。《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3]118。与此类似,《庄子·天地》云:“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4]453名利欲望改变、扭曲、戕害了人的本性,“人们时常将自身转变为其他目的的工具,正是这一做法,使得人们既危及了自己的生命,又丧失了人们与不可言说的‘道’之间的联系”[8]244。《庄子·骈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9]63,《庄子·缮性》云:“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9]118-119。在物质与欲望的奴役下,人类的肉体痛苦与精神折磨将不可避免。《庄子·齐物论》云:“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9]9
4.2 贵生、养生
尊重个体生命、重视身体保养是道家重要的人生观。关于养生之道,《老子》第五十一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3]260老子认为大部分人不能寿终,一是因为营养过剩、骄奢淫佚,因而短命夭折;二是因为行动不慎,而造成自身伤亡。由此出发,老子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应当顺应自然,少私寡欲,避免身处险地,“清心寡欲的要求,来自长寿的动机”[6]237-238。与此类似,《庄子·养生主》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9]20世人汲汲名利,劳心劳力,即便得享富贵,也并不利于养生,故《庄子·至乐》云:“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惽惽,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9]131
4.3 全性保真
出于对异化的反拨,道家强调保全人的自然天性。即使是右师(《庄子·人间世》)、支离疏(《庄子·人间世》)这样形体特殊的人,只要相貌是自然形成的,“道与之貌,天与之形”[9]41(《庄子·德充符》),人就应该坦然接受,用心保养,不必人为改变。存养本性的人,其代表是“真人”。《庄子·大宗师》云:“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嘐然而往,嘐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9]42-43这里庄子描述了真人的基本特征:真人天人不分、无物无我,重在追求人的自然本性,因而能够全性保真,不被外物和世事所累,“道家的真人在将其自身扩展到与他的自然环境为一体之时,他就越来越顺应物化”[2]65。真(自然)与异化(受变于俗)相对,《庄子·渔夫》云:“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9]250-254。
4.4 逍遥、达生
道家追求个体自由,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精神的自由,这要求人的思想超越具体、有形的物质世界,通过内心体悟直达神秘的终极境界,“正是心灵自身才拥有神秘主义的自我超越能力”[8]241。关于内心体悟的具体方式,《老子》第十章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3]108老子认为人的精神和形体应合一而不偏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这就需要内心静定、洗清杂念、摒除妄见。通过“涤除玄览”,人方能进入主体虚无的内心体道、悟道的特定状态,从而可以反观自照本真的存在,“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5]9。这样人与外在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与此类似,庄子提出“撄宁”(心神宁静,不被外界事物所扰)、“坐忘”(忘记外界事物的存在,达到与“大道”相合为一的境界)、“心斋”(摒除杂念,心境虚静纯一,以明大道)等体道、悟道的方式。关于终极境界,道家追求的是一种天人未分的自然状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79(《庄子·齐物论》),“形全精复,与天为一”[9]137(《庄子·达生》)。人达到这种状态,才能完全摆脱外物之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4]17,享受绝对自由的精神逍遥游,即“精神凌空翱翔的体验”[5]10。
4.5 遗世独立
与贪求感官享受、汲汲名利的世人不同,道家体道、悟道的方式偏于清静无为、淡泊素朴、内观反思,“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5]10。因此,“出身于古代孤寂的思想界”[6]240的得道者,其精神面貌显得与众不同,遗世而独立。《老子》第二十章云:“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3]150这种“独异”的清醒、淡泊,正是得道之人与“众人”“俗人”的疏离和相异之处。与此类似,《庄子·至乐》云:“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9]131-132
综上可知,先秦道家哲学本质上是我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古典生态哲学。起源决定本质,先秦道家生态哲学内生逻辑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万物“同源性”的认识,生态平等观、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知足”“知止”的开发观、“少私寡欲”的消费观都是这一认识衍生的结果,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先秦道家生态哲学有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三个维度。先秦道家认为,“道”是宇宙时空的起源与中心,外显为天道(自然秩序),天道是万物存在、运行的价值来源与最终依据;社会秩序的构建及运行应当符合天道,无为而治方能和谐、均衡、稳定、长久;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精神的超越与自由,人可以通过内心体悟来达到天人未分的自然状态,从而摆脱物质与欲望的奴役。
[1]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9]支伟成.庄子校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8.
责任编辑 梅瑞祥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8.009
B223
A
1004-0544(2017)08-0048-06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WX030)。
王学军(1986-),男,安徽芜湖人,文学博士,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