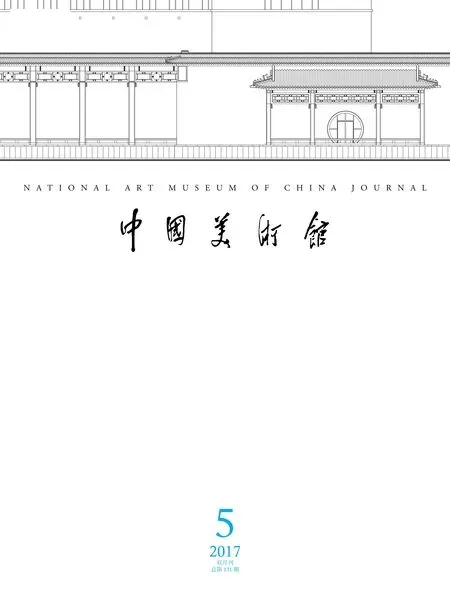视觉文化视域下的湘西宗教美术研究
王洪斌 谷利民
近二十年来,中国宗教美术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相继出版了《中国宗教美术史》《中国宗教美术史料辑要》《中国佛教美术本土化研究》等宗教美术史专著或文献,系统研究了宗教活动或宗教观念表现出来的美术形态、样式及特征。但在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美术研究方面略显单薄,特别是关于湘西宗教美术的研究更少。视觉文化研究属于跨学科范畴,它顺应和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视觉转向,用视觉文化的理论来研究湘西宗教美术,能深刻揭示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蕴藏深厚的文化内涵,亦能进一步探究宗教美术所表现出来的民族风情和社会意蕴。
一、视觉文化视域下湘西宗教美术的历史叙事
19世纪英国艺术理论家约翰·罗斯金曾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辞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的两部书,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艺术之书之所以值得信赖,是因为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实际上是对社会生活和世界的一种认识,艺术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换句话说艺术作品是人类对社会生活或对世界认识的一种物化形态。可见,美术作品具有叙事性,是人类物质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记录和承载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当然,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不像照相机、摄像机那样纯粹地、客观地再现客观事物,而是通过视觉形象把握世界的真实性。美术作品不等同于真实的物质世界,而是将其理想化、典型化、抽象化或者符号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所说,美术作品中的形象绝不是“客观的”,而是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一位有主观态度、审美追求的美术家绘制的。因此,当我们今天来审视湘西宗教美术作品时,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通过艺术审美感受文明与视觉认知,感受仪式体验与文化认同。
研究湘西宗教美术必须以湘西各民族的发展史、民族民俗、宗教文化等为背景来审视其视觉图像。湘西宗教美术起源于早期湘西各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后来逐步发展为驱邪纳福、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等内容的美术样式。因此,要理解湘西宗教美术和挖掘其艺术特色、价值,必须要深入探研宗教美术中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结构。例如,在湘西苗族民间,广泛信奉傩神,一般在秋天举行还傩愿,祈求傩公傩母除病驱灾、送子送财,平安富贵等。有学者认为,现在流行的傩文化是中原汉人傩文化与湘西交界之处的巫文化融合的结果。又如,荆楚文化支流中的梅山文化独具地域民族特色,宋代之前,这里的远古居民过着原始农耕、渔猎生活,形成了带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的梅山文化。梅山地区的居民将其梅山祖师张五郎雕像敬奉于神龛上,逢年过节,进山巡猎、抗击外敌之前都要祭祀。据说张五郎长着一双反脚,倒立行走,飞禽走兽都是他的传令兵。梅山居民以善于射猎著称,每次打猎前都要祭祀猎神“梅山娘娘”,如果不祭祀,打猎就会空手而归或者不顺利。

桃园洞
除了宗教祭祀画外,湘西民间美术中也有大量关于民俗祈福的内容。例如,地处大湘西隆回滩头的年画就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地域色彩。在湘西,素有贴门神之习俗,据《宝庆府志》记载,节序正月一日为元旦,画神荼、郁垒,以御凶神。可见,滩头年画中的门神开始以神荼、郁垒神像作为左右门神。后来随着小说、戏文故事的发展,门神也增加了一些其他人物图像。滩头年画的门神图像的制作因人而异,门神有托货、广货和水货之分。托货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东南亚广大地区,这种年画和其他各地的年画画像没有太多区别,主要是神荼、郁垒,以秦叔宝、尉迟恭等图像为主。广货是指主要销售到两广地区的门神,画像主要以关公为主。水货主要是销售到中国西南贵州、湘西、四川等地,画像内容则以苗族本民族的英雄神像为主,这为滩头年画所独有。显然,苗族英雄神像的门神是为了满足苗族风俗的需要。
除了宗教绘画和民间美术外,湘西的工艺美术也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对美好生活的祈祝。例如,湘西苗族银凤冠非常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明显地体现了其民族的图腾文化和民俗文化。凤冠是苗族17岁以下未出嫁苗族姑娘戴在前额的装饰品,是其婚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银冠上刻凿蝴蝶纹样和苗族对蝴蝶等祖先图腾的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银凤冠一般呈半弧形,构造为一块宽约四厘米,长约三十七厘米的银皮,上端缕空有多枚方孔古钱,具体形式为莲花纹、梅花点、梅花朵等,两头为对称的蝴蝶,银皮上悬有造型栩栩如生的二龙抢宝、双凤对菊和各种花草。银皮下端有9只展翅欲飞的凤,每只凤嘴含叼着一根银细链,3条须,长约五厘米。“鸾凤交颈”“双凤朝阳”往往表现苗族青年男女的爱情主题,“梅花满场”往往表现的是苗族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二、视觉文化视域下湘西宗教美术的视觉张力
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图像时代,视觉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视觉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湘西自古以来巫术、民间祭祀活动盛行,由于过去交通不便、教育落后、民众识字率低,威严肃穆的宗教祭祀活动盛行,宗教美术应运而生。可见,宗教美术来源于原始巫术、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宗教活动和祭祀仪式,是宗教活动中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用品、用具。在过去,湘西宗教美术因为其实用性和广泛需求性,宗教美术工匠和画师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手工技艺而传承。但到了今天,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触角深入大山深处,大部分宗教美术手工技艺失去了实用性和市场,宗教美术作品式微。宗教美术主要作为民俗文化、宗教象征和艺术样式保存下来。其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承载了宗教文化,保留了民族记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湘西宗教美术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和良好的视觉效果。
在湘西宗教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来说,艺术形式与风格变化较少。在构图上,宗教绘画非常饱满,图像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往往采用大小图相结合的方式,主要图像占据中心位置并且要大很多,而次要的图像要小,被放置在主要图像的旁边或者下方位置;在技法上,采用毛笔描绘、勾勒线条,色彩平涂的传统工笔画技法,因而湘西宗教画表现出细腻精美的一面。同时,湘西宗教美术又受到湖南地域艺术样式的影响,湘楚地区传统帛画流畅的线条、瓷绘的写意笔触和湖南木雕的造型风韵都成为了湘西宗教美术艺术特色;在造型上,写实和夸张并存,通常在描绘主神时,手法写实、构图严谨、刻画细腻,同时一定程度保持了世俗化化和生活化特色,很多神像和神祇就是当时世俗的人物形象,春秋战国长沙出土的帛画中就体现了这种特色。湘西宗教美术继续保持了这种传统风格,给清冷的神灵世界引入了一些人情的温暖,而在描写阎王小鬼时,受民间美术造型影响,人物造型怪诞、手法夸张,在色彩上表现上以黑、红、黄、蓝为主的大块面平涂为主,辅以绿、灰、青等,色彩艳丽、冷暖色彩对比强烈,粗狂富有韵味,并且根据内容的不同,巧施色彩。
由于湘西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各异,宗教美术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很大差异。例如,用于湘西民间宗教祭祀活动的祭祀绘画起源于祭祀和宗教仪式,在湖南各地具有不同的名称,湘中称祭祀绘画为“水陆道场画”,洞庭南岸称其为“功德画”,苗汉杂居地称之为“道教风俗画”,湘西苗族称为“神图”等。在绘画的种类上也非常复杂,既有道教、佛教、巫神、自然神像,也有地方、民族神明,由于文化交融,湘西宗教美术图像还出现了诸神交融的情形,为了表现内容丰富的需要,宗教美术的形式和艺术风格多样,这就使得湘西宗教美术图像表现出一定的张力。例如,湘西沅陵县是苗汉杂居地区,流行的祭祀画往往采用工笔重彩,造型写实,刻画细腻生动,色调以红黄为主,辅之以草绿、灰蓝,显得古朴厚重。沅陵县博物馆收藏的祭祀画《桃源洞》(图1),属于祭祖画的一种,正上方是道教太上老君图像,其下据传是出生于桃园洞的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神——傩公、傩母诸神,《桃源洞》描绘的正是傩公、傩母诸神协助太上老君驱邪怪的故事,以歌颂其功德。苗族地区的祭祀绘画既体现了汉文化的影响,也有苗族的特色,除了道教诸神外,流行于湘西苗族民间宗教风俗画《祭家先》(图2)体现了苗族鲜明的风俗,此图上方是主祭家的牌位,下方是体现挑水、生火、做糍粑、臼糯米等为祭祀活动忙碌的劳动民俗场面,再下方绘有祥禽瑞兽凤凰、鹿及奇花异草,烘托出家道兴旺的喜庆气氛。这幅宗教画在造型上随意稚拙,色彩上朱红、中黄、翠绿、钴蓝并重,画面对比鲜明,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诸神像相比,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系列的宗教神图中,因为表现目的和对象的不一样,其造型风格也明显不同,如《文殊佛像》(图3)表现的是四大菩萨之一释迦佛左边的佛像,佛像端庄雍容,手法写实,构图严谨,线条细腻,色彩艳丽。湘西的宗教绘画在表现杂神和阎王、小鬼时,则其手法夸张、造型怪诞,线条粗狂,如《十王佛像》(图4)描绘的是冥界的十殿阎王像,左右对称,在十王之下,是阴曹地府里的割据、割舌、上刀山、下油锅等实施各类刑罚的杂神、小鬼。在色彩上安排上,湘西的宗教绘画能做到随类赋彩,根据内容的需要进行调整,虽然大部分宗教绘画色彩鲜艳,但有些宗教绘画为了营造阴森、恐怖、肃穆的效果,画面色调低沉,气氛幽暗。如,流行于沅陵地区的《十殿阎罗》为了营造阴曹地府的气氛在色调上就显得暗淡古朴,用色以墨为主。
三、视觉文化视域下湘西宗教美术的多元性
视觉文化视域下湘西宗教美术的多元性表现为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湘西宗教美术具有神秘浪漫的湘楚文化遗风。在古老的湘楚文化中,龙凤形象被大量使用,龙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农耕文化有关。在湘西一带,民间每年都会举行祭祀农业活动的舞龙灯,舞龙主要是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太平丰收,当然由于民族和地域风俗各异,湘西各地的龙灯在形制上也有较大差异,如湘西溆浦县的草龙灯被誉为农耕文明的活化石,而慈利县的板板龙灯也极具特色和贴近生活。楚人的先民以凤凰为图腾,认为凤是至善、真、美的神鸟,象征着美好与幸福。因此,在湘西乃至湖南以龙凤为题材的宗教、民间美术作品特别多,不仅功德画、纸马等宗教绘画以龙凤为题材,而且包括少数民族服饰、剪纸、木版画等民间艺术的大量图案都和龙凤有关。

祭家先
二是湘西宗教美术与民间美术的交融发展。宗教的传播往往以美术为手段,民间美术也在宗教的传播中加以发挥,因此湘西宗教美术的出现和发展与少数民族神秘民俗文化等密切相关。即使到了今天,湘西宗教美术仍然和这些因素有关,不过,民众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求生、趋利、避害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祈愿,宗教美术的教化功能已经弱化;又由于宗教美术往往采用了民间美术创作观念、形式技巧以及生活题材,为宗教美术注入了活力,表现在艺术创作形式上更加随意自由,风格清新淳朴,更加富有情感和真诚。
例如滩头年画是极具特色的湘西民间美术,其最早的形式是门神,门神中的神仙题材和巫术、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后来增加《隋唐演义》《桃园结义》等小说戏文题材以及《和气致祥》等吉庆祥瑞题材。在造型上,滩头年画图像古拙,变形大胆洗练、幽默夸张,神态优美生动,线条粗犷,刚劲挺拔,运动感强,强调装饰意味,追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在色彩上,大块面积的橘红、淡黄、玫瑰红与群青、翠绿、煤黑等同类色、近似色搭配,大小面积有机分割,色彩艳丽、鲜明,对比强烈穿透力强;在构图上,饱满简洁,大多对称呼应,大与小、疏与密、虚与实、动与静的处理十分得体,画面统一而不零乱,集中而不堆砌,使人感觉十分舒适。祭祀、祈福等内容的宗教美术也体现在民间剪纸、凿花艺术之中。在民间丧葬仪式中,往往要悬挂或者张贴一些剪纸招魂幡,图案多为花鸟和吉祥纹样,在一些巫术和宗教活动中,也会剪贴一些菩萨和神话图像,如八仙图、乘鹤图、乘凤图等。但在民间剪纸艺术中,更多的是关于祈福、表达美好意蕴等内容。比如湘西芦溪县凿花中的鸳鸯枕花一般都剪贴凤凰牡丹、鸳鸯蝴蝶,表示对新婚夫妻的祝福,祝寿用的枕花一般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文字枕花,是汉文化与苗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三是湘西宗教美术的多元化。过去湘西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加之民族众多,导致湘西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宗教美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吸收全国性的道、佛、儒等宗教文化艺术,也逐步融合了荆楚巫文化和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湘西宗教美术既有汉族文化的影响,也能看到汉族文化与苗族、土家族等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例如上文说的舞龙灯和中华农耕文化有关,但在湘西出现了充满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各类龙灯,宗教祭祀绘画既有刻画生动、细腻的写实风格,也有造型夸张怪诞、线条粗狂的风格,凿纸、剪纸、版画也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风格。

文殊佛像
四、结语
美国学者米歇尔认为视觉文化是关于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它不仅关注图像本身,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视觉经验还可以进行特定的社会建构,使作者和观者能置身其中的文化意义。湘西宗教和其他地区大部分宗教一样,可以说是一种图像的宗教,通过图像来阐释宗教教义、故事和传说,渲染宗教仪式的神秘和庄严气氛。在以往的宗教图像学和艺术风格学的研究中,宗教绘画、建筑、雕塑等被拆分归入图像学和风格学分类中,这将导致湘西宗教美术图像的知觉经验、宗教礼仪空间所构成的视觉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丧失。因此,十分有必要以视觉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湘西宗教美术,将研究的焦点从图像的经典释义转向宗教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其他文化的关联。

十王佛像
湘西宗教美术起源于早期湘西各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后来逐步发展为驱邪纳福、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等内容的美术样式,审视湘西宗教美术,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将视觉图像及相关的文化现象作为整体来架构。通过视觉认知,不仅能感受湘西宗教美术的独特艺术风格及其艺术张力,而且通过宗教美术的仪式体验,能深刻地认知多元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叙事。可见,视觉文化以图像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不仅仅局限于图像,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研究理路,它拓展了宗教美术的研究范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文化视野下的湘西少数民族宗教美术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5BF076;同时也是湖南省教育厅2016年度青年项目“教育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湖南本土美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6B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