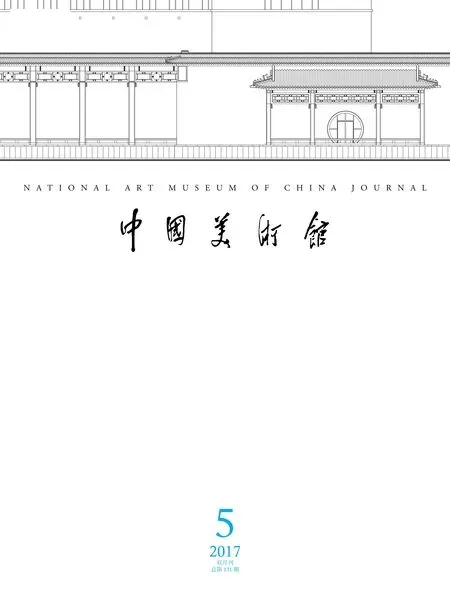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述略
刘文斌 刘洋
一、民族绘画学派的当代意义
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初期,各种艺术思潮纷纭而至,一时画派林立,风格各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已无人问津。此时,如何实现民族文化艺术的复兴,成为摆在哈萨克斯坦学界和艺术家面前的重要课题。1994年,哈萨克国立美术学院任院长、教育学博士У.依布拉格莫夫(1950—2004)教授针对哈萨克斯坦美术发展前景时说,哈萨克斯坦传统艺术与丝绸之路相关联,哈萨克斯坦要在俄苏艺术和中国艺术之间,寻找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艺术。这正是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后学术界对于国家艺术的思考与探索。

卡拉菲亚·基米尔-布拉托维奇·茄利扎诺夫 《竞赛》 布面油彩 150cm×325cm 1960
1996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家独立五周年前夕,出版了对独立后国家建设的思考的著作——《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在2000年12月举行的第七届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了建立“统一文化”的新理念。他认为,经过独立后的十年努力,哈萨克斯坦基本上解决了公民对新独立国家的认同问题。国家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同社会,以及同各民族基于共同的准则与价值观之上而产生的精神和文化的和谐有很大的关系。决定本国命运的不仅是要求文化价值观一致,而且要求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因此,必须在公民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认同的原则,这一点应该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础。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哈萨克斯坦避免发生社会混乱,符合21世纪国家建设与各民族文化相互关系的要求。为此,哈萨克斯坦确定今后要使“统一文化”成为其主流文化。所谓“统一文化”是指以哈萨克斯坦国家文化为核心,吸纳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将四种文化相互补充从而形成“合成文化”。哈萨克斯坦由于地处亚欧大陆的交汇处,民族众多,文化构成复杂,因此哈萨克斯坦必须发挥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板块间相互影响的潜力,而不是设置新的文化障碍。哈萨克斯坦历史上有多种宗教和平共处的传统,独立以来,其在宗教和平对话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哈萨克斯坦统一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体系奠定了基础。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向世界各国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国内教育也在致力于现代化,这为哈萨克斯坦建立统一文化创造了条件,年轻一代是其统一文化的最重要力量。“统一文化”只有在遵循文化之间与民族之间相互容忍的民主原则基础上才能存在,哈萨克斯坦已具备这个条件。

Н.Г.赫鲁多夫 《在山里割牧草》 纸面水彩 67cm×49cm 1930

肯巴耶夫·莫尔达赫灭特·色孜德科维奇《现在是中午》 布面油彩 115cm×17cm 1959
哈萨克斯坦学术界普遍认为,阿贝尔汗·卡斯迪夫(1904—1973)的绘画形式与语言正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代表,并且契合了国家独立后时代发展的需要。卡斯迪夫是20世纪哈萨克民族第一位自学成才的绘画艺术家,他从俄罗斯统治时的牧童、苏联时的筑路工人成长为著名艺术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者,他的成长和艺术之路与哈萨克斯坦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相吻合。卡斯迪夫的卓越绘画创作早就得到了苏联和哈萨克斯坦官方与学术界的认可。1944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苏维埃“十月革命勋章”“瓦利哈诺夫奖”;1954年至1956年,卡斯迪夫担任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3年,哈萨克斯坦为了纪念卡斯迪夫的绘画艺术成果,把原来以乌克兰诗人及艺术家乌克兰塔拉斯·舍甫琴科命名的哈萨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以卡斯迪夫的名字命名。
2004年,在卡斯迪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哈萨克斯坦国家文化部在阿拉木图举行了隆重的国际学术会议,确立了卡斯迪夫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创始人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纪念卡斯迪夫的祝词中写道:“阿贝尔汗·卡斯迪夫用自己的画笔和绘画艺术风格传递了对故乡的无限热爱,他并不认同规定的准则,他用自己的绘画语言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创作,他的一生和他的绘画艺术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学术界对卡斯迪夫绘画艺术的评价是对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价值和意义肯定,是对画家追求艺术理想时的执着与独立思考之精神的肯定,这一点正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石。卡斯迪夫相信的和遵循的是哈萨克草原美学、哈萨克人率真的性格以及朴实的价值观,他在自然“造化”的客体与“心源”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立的绘画意境、意象孕育,完成了他心灵释放和思想与精神的表达,这正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准则。
二、民族绘画学派创始人卡斯迪夫及绘画
1904年前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哈萨克斯坦已经有了现代学校教育,卡斯迪夫就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郊区契尔肯特村一个牧民家庭。卡斯迪夫6岁丧父,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靠编织毛毯、毛毡垫等传统手工艺维持家庭生活。为了补贴家用,8岁时卡斯迪夫成为牧童。绘画成了卡斯迪夫牧羊时唯一可以做的事情,这培养了他细心观察和大胆艺术实践的兴趣。1927年,年满23岁的卡斯迪夫成为铁路工人,由于他工余时常常为工友们画像和临摹列宁像,被工地苏维埃共青团派往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市进行扫盲学习。两年后,卡斯迪夫被组织上安排到专门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培养艺术家的工作室学习绘画,工作室导师是俄罗斯画家尼古拉依·嘎伏里洛维奇·赫鲁多夫(1850—1935)。他在赫鲁多夫工作室里卡斯迪夫学习油画、水彩,看到了和临摹了许多精美的油画作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拓展了艺术视野,更加坚定了终生从事绘画艺术的决心。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使他提前进入了绘画创作阶段,他创作的《驾驶的牛》《木头》《运输马奶酒》《收获季节》等油画作品,得到了导师赫鲁多夫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他参加了苏维埃国家巡回展,作品被莫斯科、圣彼特堡、比什塔克和阿拉木图博物馆收藏。
在阿拉木图的学习结束后,卡斯迪夫作为苏联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艺术家的代表,获得了到莫斯科最著名的博物馆观摩学习优秀经典绘画作品的机会。在莫斯科,他结识了苏联当时最著名的艺术家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并与哈萨克斯坦另一位艺术家阿乌巴格尔·伊斯梅洛夫(1910—1998)一起到莫斯科艺术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到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临摹了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并在莫斯科著名画家伊万·伊万洛维奇·布罗德斯基和安娜·克鲁普斯卡娅·弗尔玛洛夫工作室学习,获得了精湛的绘画技能和对艺术与生活的认识。此时,他创作的革命家和作家的肖像作品入选了全苏社会主义建设者人民艺术家肖像展,并撰写了许多关于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论文章,为他的绘画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卡斯迪夫·阿贝尔汗 《猎人与鹰》 布面油彩 100cm×80cm 1935
卡斯迪夫毕竟是一位普通的牧民儿子,任何洗礼都很难彻底改变他在哈萨克草原上形成的诚恳和朴实的民族秉性。卡斯迪夫深深感知到苏联社会主义给他带来的幸福以及给哈萨克斯坦人民带来的变化,他赞同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发挥每个人所具有的宝贵的创造力,为了健康与长寿而幸福的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和美丽的人类家园相融合”。他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使他获得了新生并心怀感恩,其始终很难忘记哈萨克民族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他不想失去作品的独立思想和精神。他的绘画作品既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所倡导的领袖居高临下的乌托邦的宏大叙事与梦幻叙事,也没有“不墨守成规的苏联艺术”前卫思想。他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他的绘画艺术作品中,只有平静的草原和没有刻意雕琢的现实生活中的平静人生。他既不能完全融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阵营中,又不能不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集体评价”标准进行重新创作或修改。卡斯迪夫的认知还无法与前卫艺术家同道,前卫艺术家也无法认知卡斯迪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中所具有的独立艺术创作思想。
在1940年至1950年10年间,“不墨守成规的苏联艺术”思潮未能如愿,卡斯迪夫也在官方要求下,对自己三十多幅绘画作品进行了修改。其中,油画作品《阿克塞采石场》(1937年)在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后最终完成。此时,卡斯迪夫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法,他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自己看似平静的画面中,他深知,一切虚空的东西都没有生活来得真实。他的创作所表达的是世界美好事物和过程的瞬间,如大地、天空和人。这与哈萨克草原人民的性格有关,在人类悠悠岁月中,长期居住在茫茫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秉赋草原的灵性、智慧,同时把自然、美丽归还草原,在碧草荣枯和穹庐转徙生活环境中,把自己的生活、习俗、文化与草原一起汇聚为一条涓涓河流,大自然赋予的每一束阳光和一草一木,他们都会感受到自然的荣光。他在表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亚至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绘画作品《土厥斯坦至西伯利亚》获得了苏联官方的大力表彰。
卡斯迪夫绘画作品中“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质朴与睿智,表达了大自然中重要的人类生命活动景观中的生活真实与草原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一幅优秀的艺术作品能使人们从繁杂与不安的现实生活进入一种超凡脱俗的空灵境界,体验灵魂深处的伟岸与崇高,享受大千世界的平静与祥和。卡斯迪夫在享受时代的机遇与获得时,努力寻找一种历史与现实、生活与艺术的契合点。对现实的尊重与珍惜正是卡斯迪夫绘画艺术在苏联时期获得成功并被后人记住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正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创立的民族文化基础。
三、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美学特征
把卡斯迪夫作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创始人,这就清晰地界定了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时间概念,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其绘画形式、语言特征、美学理想与19世纪以来俄罗斯向中亚传播西方古典主义绘画艺术之间的联系,为研究民族绘画学派的美学特征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哈萨克斯坦草原美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传统艺术、宗教思想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探讨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美学思想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首先,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时期绘画艺术的生发历程。草原美学对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历史记载,生活在中亚哈萨克草原上的早期人类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匈奴人、乌孙、突厥、葛逻禄、回鹘、哈刺契丹、克烈、乃蛮、钦察等,特别是匈奴人在草原文明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匈奴艺术的主要特征是以程式化的动物纹饰为主,主要作为马具和装备上的装饰,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匈奴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发展了一种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种独创的艺术是为装饰镶嵌在马具和装备上的铜片、银片和金片而设计的,是游牧民的一种奢侈品。这种艺术反应的是典型的草原生活形式,他们既无固定的住地,亦无地产。他们的奢侈品只限于服装的华丽和个人的修饰,以及各种装备和马具等物品的装饰方面。所以,草原美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一方面以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为源泉,另一方面从希腊的源泉中得以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它转移和改变了前一种倾向,朝着以纯装饰为目的的方向发展。

Р.З.尤苏巴夫 《古代面貌》 布面油彩 115cm×100cm 1997
其次,草原美学形成的装饰性艺术既与历史上哈萨克草原曾经出现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交替传播有关,也与其文化艺术在宗教间的相互转换、亚欧地缘文化艺术交错的地域性和多元性美学思想有关。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草原美学形成的装饰性艺术融入了伊斯兰艺术的美学思想,使其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影响下确立的伊斯兰艺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有关,匀称、一致与和谐成为其重要的审美标准。如伊斯兰绘画中的“细密画”、书法、装饰图案中时常常采用花叶饰、几何图形饰等特征即是明证,这些几何图形连续伸向无限之处,并向四方不断扩展,就像广袤无垠的宇宙、沙漠、草原与人类宽阔的胸襟相吻合,并一直影响着这一地区早期建筑、服饰、音乐和工艺美术。
再次,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东扩逐步统治了哈萨克斯坦暨中亚,改变了哈萨克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传播了以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绘画艺术,并开启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种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这些写实主义绘画作品深受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喜爱,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人民也逐步接受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西方绘画体系,为19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世纪以来,俄罗斯、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绘画课程成为基础教育的必修课程,哈萨克斯坦许多业余艺术家接受了学院派的专业艺术教育。以写实为主要特点的现实主义绘画成为其主流艺术,现实主义美学以现实的真实性、形象的典型性、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为依据,表达人类现实变化中的人的精神世界及生活遭遇,从人与所处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系中探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用审美的真实性表达美学理想是构建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的基础,是衍生民族绘画学派的重要资源。
以上是构建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审美思想的三个重要因素,具有地域文化美学的传承性、宗教美学思想的多元性和现实主义绘画美学的写实性。虽然苏联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美学与西方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美学思想不同,但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创始人卡斯迪夫在漫长的绘画创作实践中,构建了其有别于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美学思想。卡斯迪夫清晰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艺术创作中的真善美,由此奠定了民族绘画学派的美学思想与文化价值观。
从卡斯迪夫的绘画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不赞成也不喜欢脱离现实与历史真实,反对追求视觉上虚幻而缺少内心的真诚的艺术创作,无论是代表前卫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均是如此。如20世纪40年代,卡斯迪夫以哈萨克教育家、哲学家阿拜·库拉巴耶夫(1845—1904)和哈萨克第一位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曼格里德·依马诺夫(1873—1919)为创作对象时,以哈萨克草原美学思想把自然与风俗融合中在诗情画意之中,而在创作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阿马戈拉达突击队》(1940年)和鞭挞民族陋习的《买新娘》(1938)作品,则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相链接,构成了民族绘画学派的雏形。卡斯迪夫用飞驰在广袤草原上几千年来草原儿女化身的《阿马戈拉达突击队》的红骑兵,表现了革命者的勇敢与草原骑士的潇洒与浪漫。在油画《买新娘》作品中,观者看不到买卖双方的胁迫,画面中只有阳光普照的山脉和崎岖山道中骑着白马的新娘瞬间流露的含羞和略带不满的表情,伴娘默默地跟随着略显苍老的新郎。
20世纪中叶,卡斯迪夫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共同创立了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作为哈萨克斯坦本土艺术家,他们蕴含了哈萨克草原文化和草原美学的血脉,憨厚淳朴既是他们的性格特征,也是他们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特征。他们在面对草原文明与侵略、奴役以及来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带来的繁荣与冲突时,为了生存的需要,有时候不得不表现出心口不一,但是,哈萨克斯坦人民内心的信念不会改变。无论怎样强悍的对手或者异域文化艺术,都会融化于广袤的草原文化的灵性与智慧、自然与美丽之中,荣归于草原宁静的高雅与广袤的浪漫之中。这对于当代哈萨克斯坦艺术凝聚人心,以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爱恋和民族文化认知是一种精神需求。生活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的人民已经能坦然面对自然更替与生命的轮回以及战争的洗礼。卡斯迪夫作品中散发的正是哈萨克斯坦草原人民的浪漫、民族性格和人生领悟,这正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绘画学派创建的基础与条件,它契合了20世纪末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古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哈萨克斯坦当代美术的复兴与发展,也是“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的历史动力。
(该文为2013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美术史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NDJC105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