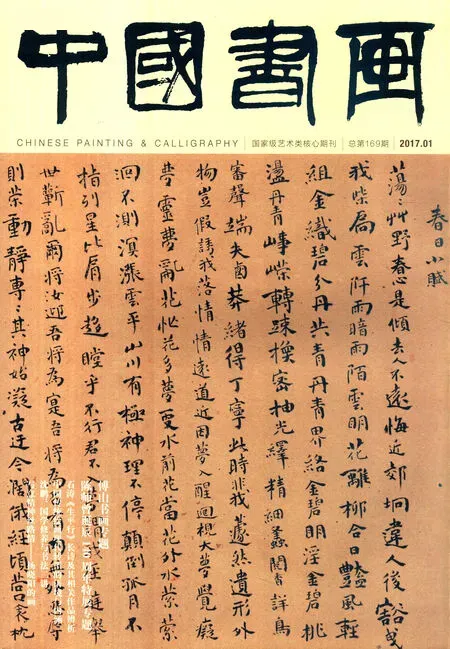大象无形:评杨晓阳的“大写意”
◇ 曹意强
大象无形:评杨晓阳的“大写意”
◇ 曹意强

杨晓阳 鹰笛 190cm×146cm 纸本墨笔 2014年
创新是艺术最可贵的品质,杨晓阳的“大写意”理论与实践是朝此方向的尝试。
在中国艺术的脉络中,“写意”一词随时代与语境而变,有着丰富的内涵,这些含义的共通之处即在于对形似的超越。
实际上,不独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中极少有哪种文化、哪个时代的艺术仅仅以外观的逼肖作为终极目标,而都在某种程度上追求所谓的“象外之致”,不论其归旨指向宗教的神性、自然的真谛,还是自我内心的抽象意趣。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当康有为在欧洲观看到拉斐尔的画作之后,得出了中西艺术“彼则求真,我求不真”的论断。康有为这里的“真”所指的乃是对外在物象的摹写,因而他说“文(徵明)、董(其昌)则变为意笔,以清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他将以文、董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视为写意画,将宋代与元代绘画归入“写真之画”,并将两者相对立。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然而在整个20世纪里,由此发展出的“西方艺术重写实,中国艺术重写意”的二元对立还是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对艺术史的见识早已超越了康有为。尽管我认为用“写意”和“写实”这样的概念来区分中西方艺术过于简率,但纵观中西方艺术史,我们会得到一个整体印象,即中国艺术对于西方艺术而言,不论在对形态的表现,还是在对意趣的抒发、创造者自我的表达等方面,其取向与本质都是“写意”性的。康有为将写真简单地等同为摹写物象,这一看法或受到西方“再现”理论的影响。然而在中国经典的画论著作中,“真”的概念并非“likeness”(肖似),而是意象与哲学层面上抽象的本真,接近于西方所说的“truth”(真理)。荆浩在《笔法记》中主张“度物象而取其真”,彦琮在《后画录》中所描述的“挥毫造化,动笔合真”,即其例证。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更明确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谓非妙也”,“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岂曰画也”。所谓“真”与“气韵”,都是谈造型艺术如何能够超越对表象的摹写,而能真正夺自然之造化。不论是度物取真,以形写意,还是遗物忘形,建构意象,都以对“意”的探求和呈现作为目标。这个“意”是中国文化的独创,如果要在英文中勉强找到一个概念与之对应,则“Idea”(理念或最高形式原型)或可匹配。它既是每个人头脑中的构想,也是终极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正是以图像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它既因人而异,是每个人头脑中的殊相,也是亘古不变,创生万物的共相。无论如何,中国艺术强调“写意”的观念,的确产生了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文人画。

杨晓阳 丝绸之路局部 纸本设色 1994年
西方艺术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资源,便是中国文人画“写意”精神和手法,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上,都与中国艺术传统中的“逸品”风格、唐晚期的表演性绘画以及“禅画”等现象有相通之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艺术反而是通过引入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体系而进入现代的。
由于明清以来一些末流画家借“写意”之名而行“草率”之实,但有草草之笔,粗头乱服之貌。郑燮因此而痛斥“殊不知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同时,受到清末民初“科学主义”与“进步论”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传统绘画中的“写意”因素与艺术上的保守主义一道,一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凡此种种,影响到了今人对中国艺术史的评价与叙事方式。
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把“唐宋传统”视为中国艺术的正宗,到以高居翰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将宋代绘画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将“写意”斥为中国绘画于元明之后衰落的重要原因。“写意”因此而成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这种艺术史观与理论上的踌躇在当代创作中的集中反映,便是近年来以全国美展获奖及入选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画创作中制作化、图像化的泛滥。似乎以照片为底本去堆砌无限的细节,进行工艺化、精细化的图像制作,就可以轻易达到“以形写神”的目标。而实际效果则适得其反,不仅是“无意可写”,甚而连中国画“书写性”的本体语言都已几近丧失。
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其观念层面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很多人犯了和康有为一样的错误,即简单地将“写实”与“写意”相对立,没有搞清楚在中国艺术的优秀传统中,“写真”与“写意”的真正内涵。
在这个意义上,杨晓阳近年来所建构的“大写意”论,对反思当今中国艺术创作中的诸种弊端,以及把握今后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他既意识到“写意”精神在写实主义体系下的衰落,也是从“写意”精神上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资源、新路径。他对“写意”的理解与阐释跳离了技法层面的“工笔”与“写意”,风格层面的“写实”与“写意”的二元对立的窠臼,上升到了整体的文明形态、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我所提出的“智性方式”的高度,将“写意”视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自立的根本所在。
杨晓阳在“写意”这条道路上的探索已历经数十年,积淀了他从西安美院到中国国家画院,在创作、教学、管理中的体验、心得和思考,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现代大写意体系,其雄心令人赞叹。纵观其三十余年来的创作脉络,可以用传统的从写实到写意,再到大写意的风格概念来概括,走的是一条“极工而后能写意”之路。
他1983年所创作的《黄河艄公》与《黄河的歌》,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与其所赖以成长的黄土画派的艺术环境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两件作品均显示出艺术家扎实的造型能力,呈现出来的是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但造型方法却是西方素描的解剖、明暗和光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黄河艄公》饱满的纵向构图、强健的主人公形象显示出米勒的名作《播种者》的影响;而激昂的情绪和撼人的现场感,显然又透出作者对籍里柯、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大师的杰作的深入研究。在《黄河的歌》中,这种高亢的基调则被悠扬的抒情所取代。可以说,这件作品中在情感表达、气氛营造方面较之《黄河艄公》更胜一筹。艺术家用墨色的浓淡、勾与染的交织叠加将画面中心的人物成功地凸显于辽阔的河面空间之中。

杨晓阳 丝路风情 纸本设色 2000年
客观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作品不在少数,其风格与手法均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美国画家怀斯(Andrew Wyeth)的资源,形成了在我国特定的时空语境下的乡土写实主义流派。
然而与同类作品相比,杨晓阳的《黄河的歌》在抒情上自然而深切,平静而厚重,显示出其细微敏锐的感受力与表现力,毫无做作之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细致严谨的写实技法与画面抒情写意的大效果不仅两相无碍,而且相得益彰,从“写实”的人物形象上升到“写意”的整体格调,达到了“以形写意”,“以意造型”的高度统一。这一点,是许多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品所不及的。《黄河艄公》与《黄河之歌》两件作品均在写实的基础上,在场景经营中融入了一定的艺术家个人的想象与虚构,从而使作品更加感人,精神内涵与人文诉求更为饱满充实,而这正为杨晓阳日后对“写意”的理论与实践孜孜以求埋下了伏笔。
杨晓阳对“画外之致,象外之韵”的追求在3年之后的《大河之源》系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在这组作品中,他已不再满足于对人物形象的精确塑造和主题性创作的完整性,而是带入了更多的个人思考,对人性、对民族、对文化之命运的同情与探求,显示出更为独立和成熟的艺术诉求。这种诉求表现在形式语言上,即画面中更为强烈的虚实对比,大胆的光影效果,浓厚的纪实摄影感以及对人物形象和情感更为朴实细腻的刻画。
在此,作为创作者的艺术家与作为其创造物的人物形象的关系是平等的。早年作品中那种明显的创作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画家与人物之间在生命层面上的娓娓相谈。可以说,杨晓阳对“写意”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不断锤炼艺术语言的同时,也升华着艺术家个人的生命意识。
对“写意”的深入发掘同样贯穿于杨晓阳的大型公共绘画创作。从1986年的《塔里木风情》与《阿房宫赋》,到20世90年代的一系列巨幅长卷,再到近几年来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大写意水墨画,艺术家以“民族气派”“中国气象”一以贯之。在形象的塑造、构图的处理上,从中国艺术史的经典名作中吸收和借鉴了诸多因素。如《阿房宫赋》中所采用的《千里江山图》的纵览俯视式构图,以及以石青色为基调,大胆、浓丽而又高古的设色方法。《丝绸之路》《生命之歌》与《远古足音》是杨晓阳在90年代的三件史诗巨制,是他对自我的艺术创作能力与才情之极限的挑战与展示,同时也是他在造型语言与表现手法的层面上进行“写意化”实践的里程碑。这一实践可归结为两点,即具体形象的意象性与造型语言的写意性。在构图方法,尤其在处理局部场景与整体画面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杨晓阳直接取法汉唐,从画像石与敦煌壁画中汲取营养,减弱了画面整体的叙事性,而大量运用铺陈、叠加的手法,着重于构筑恢宏之象、撼人之势与悠远之韵,局部的造型组合之间形成了相互生发、绵延流转的抽象意趣。在造型手法上,杨晓阳在保持基本形体结构准确的基础上,削弱了来自西方素描造型体系中对明暗、光影的表现,而采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法,使人物形象平面化、符号化,并结合了没骨、晕染等技法,增强物象的民族审美意韵。从而,将画面构图的意象性与笔墨语言的意象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创作于90年代末的《高原》系列和《愚公家族》可以被看作是杨晓阳在色彩与线条两种造型手法上进行“写意”化探索的两个标志。在《高原》中,艺术家通过对冷暖色调的娴熟掌控,借助大胆的色彩营造来烘托画面氛围,恰如其分地凸显出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而在《愚公家族》中,画家将线描、没骨、晕染、泼墨等手法予以娴熟的运用,纯粹的线描塑造出具有石雕质感的人物形体,而线条本身又不乏笔力与水墨意韵。可以说,杨晓阳在90年代的一系列巨构与佳作,都表现了他对中国画的文化身份与风格取向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思考,并为他实现“大写意”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若以作文法之“起承转合”论之,那么在杨晓阳的创作历程中,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黄河艄公》与《黄河之歌》可谓“起”,稍后的《大河之源》则为“承”,90年代的《丝绸之路》可视为“转”,而从21世纪初至今的大写意作品则可谓之“合”。这里的“合”正如王国维所说的“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画家在经历了与艺术之“血战”后,瓜熟而蒂落、水到而渠成的结果。从2003年的《关中正午》、2004年的《雪域》《农民工》开始,杨晓阳从“兼工带写”的折中风格进入了“以意写形”的成熟之境。而至其后的《关中农闲》《茶有道》《生生不息》等作品,画家已完全放下了摹写外物的包袱,达到了不拘于形,而又意象弥漫的高度。他将梁楷、石恪风格的大写意人物传统,与汉代石刻的雄浑拙朴的特质相结合,又吸收了西北一带拴马桩、石狮子等地域风格浓厚的民间工艺的体块质感,从而将当代大写意人物画的造型语言带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即画家如何能在从写实性的规范解放出来之后,却还能让形体具有坚实而永恒的品质。这种特质恰如米开朗琪罗所说的那样,好的作品应该能从山上滚落而丝毫无损。与这种形体的结构性相契合的,是杨晓阳对笔墨语言的提炼。在其大写意的作品中,画家以删繁就简的法则处理形体、结构、笔墨,这里的简不是简单,而是“为道日损”的返璞归真。画家尤为强调线条的书写性,既流畅圆转,而又富于顿挫变化。这种韧性和力度既构成了造型的“语法单元”,又搭建起了形体和画面的整体意趣,从整体上使作品超越了“写实”或“写意”在技法风格层面的张力,而建构起一种独立的形式结构,细节与整体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这种意象恰与石涛的“一画论”相暗合,即“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杨晓阳 愚公家族 170cm×185cm 纸本设色 1999年
古罗马的西塞罗曾言:“最能愉悦和最能打动我们感官的东西,恰恰也是我们很快感到厌恶而疏远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很难说清楚。一般说来,新的图画在美和色彩的多样性方面与古画相比,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一开始会迷住我们的视觉,但是这种愉悦不能持久,而古画的粗朴和古拙却仍然吸引我们。正如拉斐尔既被视为古典艺术的顶峰,但也是衰败的开端;而清人赵翼也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贡布里希拈出艺术史中这一趣味变迁的普遍现象,称为“对原始性的偏好”,而正是这种偏好构成了艺术史发展的一股重要推动力。西方艺术史中的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拉斐尔前派,中国元代的钱选、赵孟頫,清代的“道咸画学中兴”,以至20世纪以来毕加索、鲁奥,以及中国画坛对“唐宋正宗”的推崇,莫不如是。“与古为新”既是一种文化的乡愁,也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艺术的特性在于革新,艺术有审美价值标准,但形式绝不可模仿与雷同,正因为如此,任何创新也不可能得到即刻的社会认可,历史会做出判断。如果杨晓阳的大写意试验具有创新意义,那么就有可能为中外伟大艺术传统价值体系所容纳。历史上一切艺术革新都经受了这双重的检验而得以传世。勇气和执着是创新之路的前提,我期望杨晓阳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更大的硕果。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宋建华

杨晓阳 丝绸之路(局部) 纸本设色 1994年

杨晓阳 丝绸之路(局部) 纸本设色 1994年

杨晓阳 黄河艄公 200cm×135cm 纸本设色 1983年

杨晓阳 面壁图 136cm×70cm 纸本设色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