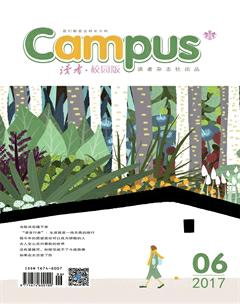古人怎么应对看脸的世界
老猫
自古以来人们对脸就很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说了可能好多人不相信,明朝皇族见人,都是要化妆的。《茶香室续钞》援引明朝的文献说:原以为皇帝的帽子用各种珠宝装饰,但不用翠。可是见藩王家里办喜事,王爷头上簪两枝花,还都是翠做的,即所谓的翠花。一问内侍,才知道皇帝在后宫中也簪花。《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说,他到都城和太监们聊天,谈到皇帝上朝前一定要在脸和脖子上扑粉,这样显得更加严肃。扑粉和严肃沾得上边吗?人家没解释。也许,是因为朱元璋长得不好看,子孙们试图“洗白”,也未可知。
不过也真有不在乎自己脸黑的。这位是名人——王安石。有一天,他的好友兼同事吕惠卿对他说:“你脸上长黑斑了啊,告诉你一个偏方,用芫荽洗洗,就能洗掉。”王安石说:“我只是脸长得黑而已,没长黑斑。”吕惠卿道:“芫荽也能把黑洗掉。”王安石笑了:“我的脸黑是天生的啊,芫荽有啥用呢?”
男人的脸黑点儿不是大问题,要是坑坑洼洼就有点儿麻烦。古人把出了水痘在脸上留下的疤痕叫“痘疤”,文雅一点的名字叫“天黥”。明朝有个文人叫徐渭,有一次他受人所托,要给一幅人物画像写赞语,画上的这位是“天黥”。脸长成了这样还得夸,真够难为徐渭的。徐渭还真有辙,直接写道:瓜啊瓠子啊又白又肥,只能做腌菜;松柏樹干多鳞片,却是栋梁。看您的长相,一定不是瓜瓠,是松柏……
黥是一种刑罚,是在犯人脸上刺字。尤其是在宋朝,使用得比较普遍,《水浒传》里的宋江、林冲等人都受过此刑。魏泰《东轩笔录》讲了个脸上刺字的段子:有个叫陆东的,任苏州通判,并且代理知府行事。他判了一个罪犯,需要流放,就在人家脸上刺了几个字:“特刺配某州牢城”。
字刺完了,手下人提出不同意见:“领导啊,不对啊。这个‘特字的意思是本不该这么干,但因为某种原因破例这么干了。你这不是说,他罪不至此,但迫于朝廷规矩只好发配吗?这不是事实啊。这人本来就该发配,又来个‘特,讲不通,回头上面该追究了。”
陆东一听,吓坏了,立刻把犯人叫来,重新刺字,把“特刺”二字给改成“条准”了。这个倒霉的犯人,受了二茬罪。
后来,有人向上级推荐陆东升官,上级一听他的名字,就说:“陆东啊,知道知道,是不是苏州那位在犯人脸上打草稿的?”
关于脸,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寓言。这个寓言的原创者是唐朝人顾况。《唐语林》说,顾况这个人总是和同事闹别扭。有一次和领导吵完架,气哼哼地讲:“我做梦梦见嘴和鼻子争功,嘴说:‘我谈论古今是非,你个鼻子从来不出声,为啥在我之上?鼻子说:‘咋了?饮食非我不能辨!眼睛对鼻子说:‘我近能看毫端,远能看天际,唯我当先,必须在更上面。接着问眉毛:‘你有啥用啊,还在我上面?眉毛道:‘怎么了?我是没用,就好比主人养的宾客。可没有宾客,就不能体现实力。所以没有眉毛,以何面目见人啊?”
顾况说这话,是挤兑那些高高在上的、毫无用处的家伙,跟眉毛一样,纯属撑门面。有个群口相声叫《五官争功》,灵感来源也许就是这个。
还好,顾况的一番话让领导觉得有道理,对他又好起来了。
唐玄宗时期,有一位安西衙将刘文树,口才极佳,特别善于奏对,唐玄宗挺喜欢他。就一样不好,刘文树长了一脸黄毛胡子,特别像猴子。唐玄宗呢,还就老拿这事儿开他的玩笑。唐书《开元传信记》记载,有一次刘文树又要见皇帝了,事先唐玄宗叫来身边的谐谑高手黄幡绰,叮嘱道:“明天见了刘文树,你给我好好奚落他。”刘文树早知道皇帝憋着坏呢,也找到黄幡绰,送了他好多礼物:“我最烦别人叫我猴子了。你明天再怎么说,也别说我像猴子。”
第二天,当着皇帝和刘文树的面,黄幡绰是这么说的:“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就是你不像猴子,是猴子硬要像你。
唐玄宗大笑,心里也知道黄幡绰肯定收了刘文树的好处,可还是开心了呀,就没再追究。
将军的脸是如此重要,若是长得不给力,上阵杀敌,可能效果要打折扣。《教坊记》和《乐府杂录》都说到了脸的故事,综合一下,是这样的:南北朝北齐的时候,皇帝高欢之孙兰陵王高长恭胆识过人,上阵杀敌,总是最先突入敌阵。就一样不好,他长得有点“娘”,面孔女里女气的,这多影响威慑力啊。高长恭想了个办法,做了个大面具,临阵戴在脸上,这回真是威风八面,百战百胜。这大概就是面具的发端——后来,在一些需要雄壮之气的音乐里,就出现了面具人。比如击鼓,唐朝宫廷里的鼓手都是戴着面具、拎着鼓槌出场的。
类似的事情现在还有,英超切尔西队的前守门员切赫就是一位。2006年,切赫在比赛中被对手踢得颅骨骨折。伤愈后,每当比赛,切赫必戴头套。一种说法是,这是医嘱,必须保护切赫的面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切赫必须戴着头套心里才感到踏实,要不老是有心理阴影。不管怎么说,切赫的这个头套就得永远戴着了,除非他退役。而头套也成了切赫的标志。
拿面具遮住自己,“不要脸”,其实也是为了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