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诗乐同源的大文学传统
刘波,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星星·诗歌理论》杂志“每月诗歌推荐”栏目特约主持人。在《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胡适与胡门弟子》(合著)等。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
2016年10月,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他广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民谣和摇滚音乐人。这可能正是他获奖引起争议的原因:有人觉得他的歌手身份与文学无关,有人认为他写的歌词也是广义上的文学,诸多观点交锋,一个更为清晰的鲍勃·迪伦逐渐浮出水面。虽然摘得最高文学奖桂冠,他依旧那么低调地行事与歌唱,用他带有批判、怀疑、悲悯和人文情怀的语调,诉说着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忧伤。
也许鲍勃·迪伦的获奖,不能完全证明文学的复兴,反倒是给一些人出了难题:怎么对这种跨界进行归类?但这一事件确实又暗示了当下文学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可能性,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当我们坚守的永恒价值在这个时代成为了美学的反面,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为我们提供新的可能?迪伦引起争议,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好事。诗歌和音乐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源头,那就是大的文学传统;它们之间的融合即要打破“各自为政”的封闭态势,拓展创造的边界,由心灵所主导的诗歌与音乐才有诸多可开掘的空间。
一
有人说,鲍勃·迪伦在他七十五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与音乐联姻的一次胜利,而在迪伦那里,音乐只是他表达精神需要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好像并非如此。他的音乐和歌词是高度融合的,甚至不可分割,假如不从更大的文学范畴和更长久的文学传统来看待迪伦的成就,也就很难意识到他的非凡。
于此,就涉及到一个重要命题:歌词在一首歌曲的传播中到底起多大作用?音乐作为艺术,首先是诉诸人的听觉,我们能感受到的是音乐本身的节奏、旋律,而非文字本身所具有的美感;而歌词所带给我们的,正是文字的心灵和情感作用。二者融合会在身心整体上触及我们的感受。如果从唱功、嗓音上看,迪伦肯定不是最优秀的,他的音乐让我们肃然起敬的,还是音乐背后的文字流露出来的精神力量。近二十年前的1997年,迪伦已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当时,他受到了这样的称赞:“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它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确实能带来某种震撼之美,迪伦如果没有他那些诗性的歌词,其音乐的影响力定会大打折扣。因为从音乐本体来看,比迪伦优秀的歌手很多,可唯有他真正以全能的形象征服了我们:他不仅会唱歌、作曲,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出色的诗人。
鲍勃·迪伦是以分行的诗歌形式留在了多数高端读者的心目中,他也是以这种文学音乐人的形象完成了自我的经典化。如果他仅仅只是唱歌,其影响力也就仅局限于流行音乐界,而不会延伸与扩展到文学界。在迪伦的人生中,兰波、迪伦·托马斯、威廉·布莱克等诗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过他的创作。文学作为一种功底,对于迪伦来说,就是他身上的某种内在禀赋和气质,它会给一位音乐人带来强大的气场。迪伦何以在二十五岁就已经获得了那么多人的认可,并持续影响至今,音乐的魔力穿透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种现实与荒诞,来到了一个新的现场,但我们还是沐浴在那个特殊时代的阳光下,愿意聆听迪伦的歌唱,他将思想传递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声音会在时代的后台重新响起。这也是我们认同并接纳迪伦的原因,这位永远的“邻家大男孩”,不仅是以歌手的形象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他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也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所以,当我一遍遍去听他二十多岁时演绎的那些歌曲,并不是为了追求怀旧氛围,这种重返只是一种温习,将那些或感伤、或俏皮、或幽默、或张扬的表达置于内心,去感受一个年轻人如何有充沛的精力去创造那么多闪光的经典。流行音乐是否永远只属于年轻人?它们就是一场青春的事业吗?迪伦至今仍在创作,这一事业他整整坚持了五十年,似乎从未厌倦。这种持续性很多时候会发生在诗人身上,因为美国一直就有老年诗人的形象和传统,包括迪伦的朋友爱伦·金斯堡,另外一位诗人加里·施奈德,皆一生坚持写作,恪守着内心的先锋,并最终活成了一个经典的形象。迪伦也不例外,我們现在看到的多是他年轻时的照片,要么就是他当下的老年爵士形象,这是岁月的恩赐,而时代的烙印,也许是深藏在了他的心里。“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鲍勃·迪伦《编年史》,徐振锋、吴宏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P149,以下引用仅标页码)迪伦如是说。他看似在自嘲,其实,这就是他最真实的感受。他将自己做了精准的定位: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越是被遗忘,越是富有命运感。然而,“词语匠人”留在了当下,也会留在音乐史上,更重要的是,他也将留在世界文学史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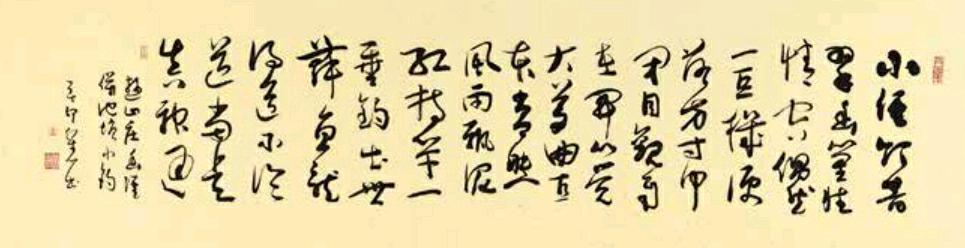
迪伦在音乐与诗歌的跨界上一直是一个冒险者,而在1960年代的美国,他又是嬉皮士文化的闯入者,不是说他深谙时代之道,乐于从社会时事中挖掘创作素材,随手拈来,做深度整合,就是他艺术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对于这种创作惯性,他也有过反思,这正是他曾拒绝和反叛主流文化的原因:我们过于依附自己所处的时代了,而不能更清楚地看待自己,于是,他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对时代进行凝视,直至发现时代的暗处隐藏的那些孤独的灵魂,以及他们所发出的孤绝之声。这种冒险和挑战,对于迪伦来说,才是打破一切束缚并重建另一种抵抗美学的见证,像早期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时代的变迁》《鲍勃·迪伦的侧面》《重访61号公路》等,都有着直白其心的哲思性和速度感。这也是我们对于迪伦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桀骜不驯的青年形象上的原因。虽然他出了那么多唱片,也曾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但他一直如凯鲁亚克所写的那样——在路上,他不仅是一个行吟歌手,也是一个流浪诗人。流浪的姿态唤起了他对世界进行改变的愿望,用文字,用音乐,“把能够相互激发的一些技巧元素结合起来,我能够改变感知层面、时间框架结构和节奏系统,从而赋予我的歌曲以更明亮的风格,把观念们从睡死的状态中唤起,让他们身体内部的神经高度紧张”(P148)。这种如有神助的力量,是迪伦能够把握的状态,他通过内在的改变,来找到体验世界的艺术方式与角度。
二
鲍勃·迪伦以他独特的风格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共鸣于他在作品里所渗透的思想,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的不合作,他的拒绝,这种拒绝乃基于自我反叛之意。“我曾经写过和录制了那么多歌曲,但是现在我好像并没有演唱其中很多。我觉得自己只能胜任其中的二十来首。其他那些太过神秘,幽暗不明,我再也不能在它们上面做出点具有根本创造性的东西。这就像是扛着重重的一包腐烂的肉。”(P150)迪伦的这种自我要求,虽然是阶段性的,但立足于其自身的艺术标高,因为他一出手,就曾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音乐风尚。
迪伦这些年持续性的创作,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启示,这种启示一方面体现在音乐本身,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如何保持恒久的艺术创造力上:从大学开始做音乐,不间断地试图靠近理想的状态,他凭借的不完全是艺术的直觉,还有对这一事业的执着精神。他将艺术当作了人生路上的一束光亮,只有不断地前行去捕捉,才会促使自己顺着那束光亮向前走,这样,无限的创造力助推着他走向民谣的殿堂。可他并没有完全满足于做一个流行乐手,只是以商业挣钱作为目的,他的演出一直是小剧场形式,他的听众和观众也是趋于小众的,对于这种小众化艺术的坚持不懈的探索,最终成就了迪伦的经典性。这些年虽然不像某些明星那样大红大紫,但他始终拥有自己忠实的听众,我相信,这样的创造力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可能还不在于他写出了多少歌曲,而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品味。至少在艺术和文学的精神质地上不降低标准,他放松地做音乐,但又时刻与世界保持距离,以审视的眼光看待周遭一切,这种拒绝里饱含了那一代人严肃的目光。尽管他们也曾经玩世不恭,也曾经嬉皮和雅皮过,但在与时代的契合度上,迪伦几乎是在彻底地燃烧与释放自己。“嘿! 手鼓先生,为我唱一首歌吧,我早已失去倦意,也已无家可归。”(《手鼓先生》)这是迪伦写给一个时代的感伤之词,愤怒,孤独,在忧郁中又带着希望。
当我们听了太多速朽的、快餐式的流行歌曲后,对于迪伦的音乐,会生发出来自灵魂深处的敬意,他是真正在以自己的人生充实艺术的思想内核。即便如早期的《答案在风中飘》,虽然他只是用一把木吉他和口琴演奏,形式简单到粗糙,但如今听来,曲调和旋律是熟悉的味道,而在当时民权运动的特殊背景下,歌词里所蕴含的哲思力量,或许更能抓住我们。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一只白鸽要翱翔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安息/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答案在风中飘//一座山要伫立多少年/才能被冲刷入海/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人要回过多少次头/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答案在风中飘//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清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死亡的人已经太多了/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答案在风中飘
我们以诗歌的标准来要求这首歌词,它同样会显出其在那个时代的拯救性力量。迪伦所设置的追问,是针对所有人,同时也是在问他自己,正是在这样一些当时、现在包括今后可能永远也无法回答的追问中,一位民谣歌手创造了永恒。多少代人会停驻在他所重塑的记忆中,不断地回味那些天问般的句子,可我们又真的找不到答案,它只能在风中飘散,这才是经典的魅力。迪伦后来的很多歌曲,不一定胜在他的演唱上,而是他将所有的歌词都当作有深度的诗在写,这是民谣和摇滚音乐所独有的精神力量。所以,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他的定位才会显出了文艺跨界的自然性——“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这是对迪伦历史价值的重新挖掘,其重点在于他的“新的诗意表达”,新鲜的创造性,也许就在他对自我的颠覆和超越中。虽然他也时常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我做每件事都很快。思考得快,吃得快,说得快,走得快。我甚至唱歌都很快。我需要让自己慢下来……”(P86)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迪伦在私生活上并不检点,尤其是年轻时,情史不断,但这些似乎很少影响他在艺术上的努力。相反,那些女友和妻子,还曾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像《再来一杯咖啡》《她属于我》《低地的愁容女郎》等,大多是迪倫经历疯狂爱情后的结晶。她们成就了一个经典音乐人的地位,同时,也让他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孤独地跨越了一座又一座人生的高峰。
无论是做一个歌手,还是做一个诗人,这两种身份统一在迪伦身上,是恰如其分的,他不用刻意去遮蔽一面而张扬另一面,他只需要真实地面对自己,去寻找新的变化。“我不想过旧的生活。如果可能,我想要理解生活里的事情,然后摆脱它们。我需要学会怎样去浓缩事物和想法。”(P64)从生活中汲取素材,这是多数艺术家在想象中都会面临的选择,而去浓缩事物和想法,则是歌手和诗人必然要掌握的能力。在面对生活的考验时,迪伦以挑战自我的方式去为音乐和诗歌融合营造了内在的紧张感。就像他那些富有新意的歌词一样,也是在深度对比中达到了张力之美。这是我们能从其歌词中获得共鸣的原因,同时也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份精神和美的启示。
三
如果从介入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一个作家需要承担什么样的立场,才能既在社会层面,也在美学层面保持对自己身处时代最深刻的书写?我从来都不怀疑作家们有过这样美好的愿望,但有时往往抵达不了所期待的理想高度。这种错位感有时是隐蔽的,不会刻意或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对世界的认知中,然而,介入性始终是我们评判当下作品的一个标准:只有关注时代,作家才能被称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才能由此获得身份的合法性。对于当年的鲍勃·迪伦来说,他同样也面临着大众的检验,只不过,他比较幸运,他从最初以音乐人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就是因其创作本身是及物的,是有针对性的。那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权运动的反思,在大部分年轻人和亲历者那里获得了心理上的认同,甚至他就是以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而广为人知。可迪伦当时并没有那么渴望以介入的姿态,来完成对自己最初的定位,这样的公众形象,反过来又促使他不得不去面对时代的困境与现实的难题,这正是多数人所遭遇的现实。
可能迪伦一开始并未有那样的精神自觉,但当一切都成既定事实时,其介入者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恰好影响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所刻意流露的反叛气质。因此,他一度还被称为抗议型歌手,这也是很多人青睐他的原因,对于这一貼在自己身上的标签,迪伦未置可否。虽然他也不愿去为自己做这方面的辩护,但事实正是朝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好像每一个重要社会事件的发生,迪伦就应该以他的写作和音乐来发表看法,这在一段时间内,甚至直接影响了他作为一个话题音乐人的创作风格。“不管怎样,我曾唱过很多话题歌曲。写真实事件的歌总是话题性的。你总能在里面找到某种视角,并从中找到某种价值,写歌的人不需要很精确,他可以告诉你任何事,而你会相信歌里唱的内容。”(P85)迪伦并没有否认这种形式所带来的影响,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他必须要有对接时代的勇气,而非玩自说自话的语言游戏。此时,迪伦是一个承担着责任意识的冒险者,他以自己的行为宣扬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针对时代的发声,是迪伦早期艺术创作的一根道义标尺,他在凡俗的生活空间里寻找个体的公正,但对于公共世界的观察,还是让他保持了更为自由的精神。那么,迪伦的精神遗产还在于他并非一个标签化的艺术家,也不是一个被某种团体或流派所限定的诗人,他有着更宽阔的视野和普适精神。
在未获奖之前,诺贝尔奖委员会曾对鲍勃·迪伦做过如此评价:“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这一点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的关注。”不管这样的评价是否有刻意拔高的成分,但迪伦的创作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其歌曲中所呈现的思想力度,就是由当时某些公共话题产生的,而和流行歌手不一样的是,迪伦更多时候是越过了那条时事话题的边界,将写作的触角伸向话题所延伸出来的内在精神上,这样其作品就富有了思想性,而思想性才是能为受众所认可和敬重的前提。
噢,我那蓝眼晴的孩子,你看到了什么?
噢,我那年轻的情人,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成群的野狼包围了一个新生的婴儿
我看见一条人迹罕至铺满宝石的公路
我看见一根黑色的树干鲜血淋漓
我看见满屋拥挤的人群,
他们个个手拿流血的斧子
我看见一架白色的梯子上面被水覆盖
我看见无数个饶舌者,
他们每个人的舌头都已溃烂
我看见无数少年手握刚枪,恶语相加
噢,大雨,大雨,大雨
那可怕的大雨即将来临!
这首《大雨将至》(节选)虽然不完全是由某一社会时事所引发的即兴之作,但深度思考里面还是有着迪伦对一个大时代至为敏锐的审判和预言。这是迪伦作为一个诗人的敏感之处,他能参透时代,以非常形象的表达概括出其中的精髓和大义。“我生活的时代跟那个时代不一样,但在某些神秘而传统的方面看两者还是想像的。不仅是一点,而是很像。我生活在一个宽泛的政治体制里,那种生活的基本心理特点都是这个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如果你把光对准它,你能看见人性的全部复杂性。”(P89)这是迪伦透过政治体制对时代的看法,其自我言说里所包含的政治诉求,也并不完全就是现世的,他同样也从历史线性发展的逻辑对之抱以同情的理解。所以,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理解,在迪伦那里是不成立的,他认识到了其中所潜藏的复杂性,并将它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我觉得从此角度进入迪伦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就不仅仅是看歌词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诗意,而且还要依据他认知时代的一个基本准则,这个准则当是他艺术伦理在作品中的投射。
准则最终还是体现在精神、意志与思想上,比如他创作《政治世界》《荒凉街区》《邪恶的信使》等,看似与音乐人的工作不搭界,但其中有他更多深层次的思考,他保持了艺术和诗歌在创造性上的尊严。就像迪伦自己所言,“似乎从过去的时代继承了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这才是他立足于其中的精神生活。他没有极端地去表现对时代的偏执批判,他还是选择以温和的姿态书写时代的痛苦和哀伤,并试图靠近那些更符合人性的发现与对他人的理解。
四
一旦从音乐角度来定位鲍勃·迪伦,他其实还是一个先锋,而如果我们从社会和历史层面来衡量他的成就,他也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尽管他也创作了那么多关于种族、暴力、反战的作品,但那些暴露和批判并非其最终目的,他还是超越了事件本身,从而获得更高层面的理解,这也是迪伦作品给我们强烈现实感的原因。最终他并未停留于现实的单一层面,而是深入到了历史中,在现代文明的意义上捍卫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
从世俗的角度看,迪伦可能并不认同这一点,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本就是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所应该承担的使命,不必刻意去过分突出它。“据说我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P117)这也许不是自谦之词,他的确是以如此事实为自己找到了实践的依据。他看似为一代人做了代言,可他并未真正融入到这代人中去,他要比他们思考得更全面,也更深远。作为原创型的音乐人,迪伦受到了热烈追捧,同时,也遭遇了很大争议,尤其是他从早期民谣转型为后来的摇滚乐,这中间的变化也遭致误读乃至误解,这种误读更多体现在对他所写歌词的理解上,“确实,我的歌词敲打着人们以前从未被触到过的神经,……我对人们把我的歌词推而广之的做法非常厌烦,它们的含意被颠倒,用来论战,我也被圣化成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的主教,头等重要的人物。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呢?无论怎样看,这些头衔都挺可怕。全都是‘亡命之徒的代码”(P121—122)。这些加之于迪伦头上的各种标签和头衔,不仅让他对这种做法不满,更让我们对他的认识简单化了,觉得其风格就是如此。而一旦某个作家或艺术家被认为风格化了,他的创作可能就会趋于僵化,无法在更阔大的空间里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这种“反叛式”的理解,也是迪伦在遭受了太多误解后迫不得已的一种言说选择,他还是渴望能走出这种封闭式理解的怪圈,找到一个具有更高宗教色彩的全新认知视角,其在1980年代推出的《拯救》《异教徒》等作品,即属此列,相对开放、温和,有着某种唤醒的力量。
那么,我们再由迪伦回到歌词、音乐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会发现他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大文学的传统中尋找并定格自己对世界的回应,对时代的真诚书写。如果说我们听其歌曲,还只是找到了音乐传承的载体,那么,单独将其歌词置于整个大文学史范畴,也能发现其所具有的微妙变化。如果说他早期那些带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歌词,是基于时事的某种浪漫主义回想,那么,他后来的歌词创作就显得相对理性,有时在理性的思考中不乏深深的痛感。“他写下了这个世纪最震撼人心、流传最广、安慰和鼓励最多人的诗篇。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金斯堡如此评价迪伦。不管音乐与诗歌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至少以诗意的一生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守了某种异质性。透过那年轻的声音,我们能感受到一颗曾经激情四溢的灵魂的跃动,他的音乐演绎都是通过歌词这个中介所完成的艺术再创造,这一过程,只有迪伦自己才真正明白其中的艰辛与不易。
至于自己的创作和生存状态如何,迪伦可能一生都在检视,同时他也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无论是早期凭借激情写出了那么多已成经典的作品,还是后期以巡演的方式所带来的小剧场效应,他永远处于在路上的状态。这种状态让他将音乐和诗歌作为了毕生理想,此为他理想主义精神的佐证。“一首歌就像是一个梦,你努力想将其变成现实。它们像是你必须要进入的陌生国度。你能在任何地方写出一首歌,在火车车厢,在船上,在马背上——移动能助你一臂之力。有时候那些最富有写歌天赋的人们从来写不出什么,因为他们老是不动。”(P166)的确,他意识到这样一些弊端后,就让自己处于“动态”中,继而洞察到艺术与文学的敌人,还是在于惰性、封闭和自我满足,在此意义上,最大限度地突破自己,就成为了其日常功课。“你必须知道并理解一些事,然后超越语言。”(P54)超越语言,对于一个音乐人而言,又何尝不是超越自我?就像他曾谈到歌词和音乐的关系,“歌词的语意都存在于语音里。歌词是你的舞伴。它的作用方式比较机械”(P173)。歌词在音乐中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迪伦又意识到了其本身的有限性,这才是他所辩证强调的价值。
——由此角度观之,鲍勃·迪伦是在以常识看问题,即他站在常识的角度挑战了成规,并启蒙了更多的受众。这种启蒙现在看来属于拯救的力量,他虽然没有和世俗生活完全和解,但他还是看到了艺术、文学和世界之间的某种复杂联系。“一个陌生的世界将会在前方展开,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有着被闪电照亮的犬牙参差的边缘。很多人误解了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正确认识过它。我径直走了进去。它敞开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它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P292)迪伦正是以这种赤子之心和孩子般的眼光在创作,在生活,所以,他才能在更纯粹的世界里打通诗歌和音乐之间的界限,自由地穿梭其间,最终重建大文学和艺术交融的新人文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