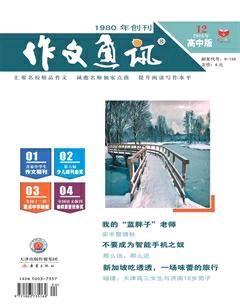看不见的城市
江佳菲
初到新加坡,只见它的现代、繁华,以为它和世界上所有的国际化都市一样,高楼林立。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逛街购物、游玩放松的场所和设施一应俱全。可惜我对这些没太大兴趣。因此,我不算是个适合写游记的人。
或许那些偶见的、隐匿在城市深处的细节,更能让我感受到独属于新加坡的气息。
正值盛夏,我漫无目的地在这座城市里穿梭。阳光明媚得有些晃眼,覆盖了整座城市的参天大树,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新加坡的明亮色调。两侧的住宅楼不同于市中心的高楼,这里的房屋风格整齐划一,外墙上刷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增添了几分生气与别致。不难看出,虽是最普通的居民住宅,也经过了精心设计,匠心独运。在裕廊初级学院的社会发展课上,我了解到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实行已久,它源于李光耀当时提出的“居者有其屋”的口号。这类政府建造的组屋售价比商品房低廉很多,并且有不同的种类和规格。虽然申请政府组屋需要满足很多条件,但它们已成为近八成新加坡人的住所。
作为一个人口组成多元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在分配政府组屋时,会将不同种族的人安排在一起,每栋组屋里各个种族的人数分布都有规定的比例。强制性地把各个种族安排在一起,刚开始可能会有很多摩擦,但时间久了,大家对对方的习俗和禁忌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就会变得更加包容,甚至会互相影响,从而逐渐形成相似的价值观。
加缪说:“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办法,就是去认识里面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以及如何死亡。”诚然,在新加坡的街头,我似乎可以窥探到,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里,历史传统与现代摩登、西方与东方的风格是怎样不断地融合、创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又是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的。
学校的典礼上放着马来语的国歌,人们日常交流通常使用英语,也会遇到亲切地说着汉语的华人,或是学习中文的马来人。对此,刚开始我感到讶异新奇,后来渐渐懂得了这就是新加坡的气质。我不禁陷入思索,究竟是新加坡有独特的魅力,能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和谐相处,还是这天南海北的人本身成就了新加坡多元的城市特色。
新加坡很年轻,从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如今的国际大都市,历史的痕迹深深浅浅地散落在狮城的各个角落。过往的岁月不会喧宾夺主,只待人漫步其中,细细品味之时,才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深情与秘密。
卡尔维诺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从修葺一新的牛车水原貌馆对早期华人移民生活景象的真实还原,到甘榜格南(新加坡穆斯林的聚居区)古老教堂里马来西亚人的生活印记……各族人生活历史的缩影,像是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掌纹,总是隐没在细枝末节处,诉说着此地的前世今生,逐渐成为像血液一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同造就了今天的新加坡。
曾经用来卸货的小码头,如今已成为综合性的商业娱乐中心。克拉码头的夜景令人难忘。傍晚,我乘着小船在新加坡河游览,微风使人沉醉。金碧辉煌的酒店在沿岸闪耀,鱼尾狮喷泉溅起朵朵水花,码头附近人群熙熙攘攘,好生热闹。
而我更偏爱愉快的气息飘浮弥漫的时刻,能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温暖氤氲开来的瞬间。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入屋里,我望着窗外,居民楼里的人们早已忙碌起来,而我只顾欣赏这一场绝美的日出,天空晴朗极了,这座城市仿佛正与我一同醒来,仿佛此刻我真正地融入了这座城市。我这才懂得沈从文笔下的那种温暖洋溢的感觉:“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整座城市在此刻成了一场宏大的隐喻,日光,新生。那些旁若无人的街道,那些渺小又巨大的人,往昔的记忆与今天的繁华在此刻梦幻般交织,展现在我的眼前。不远处河水荡漾,泛起粼粼波光,倒映著我难以尽述的美。我为先前对它所下的鲁莽判断致歉,可新加坡却对这样的偏见不以为意。这座城市有禅道的底蕴。它带着穿越幽暗岁月后的自信,不卑不亢,既不盼望也不愠怒,而是静谧地等待着被人感知,被人真正地发现。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下了一场暴雨。是夏季的雷阵雨,空气闷热潮湿,雨声那样响,仿佛有人从高耸的金沙酒店上倒水下来。不过也奇怪,突如其来的雨使得整座城市的步调慢了下来,雨声衬托着巨大的宁静,将这座城市的轮廓冲刷得更模糊却也更清晰。游人被淋湿躲雨的狼狈、被绿意包裹的惬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交谈的瞬间,浮生羁旅之感,恍然而生。
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新加坡于我也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它会让人产生不断向深处探寻的冲动,它有着铭记幽暗过往并带着历史前行的勇气。这里的人是如此迥异,却又相处得如此融洽。或许,还有我所未见的更多的光风霁月被它深藏于心底,等待着被人发掘。如卡尔维诺所言,在某些时刻、某些街道上,我看到了那难以混淆的、罕见的甚至是辉煌的事物。
我期盼着与它的下一次曼妙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