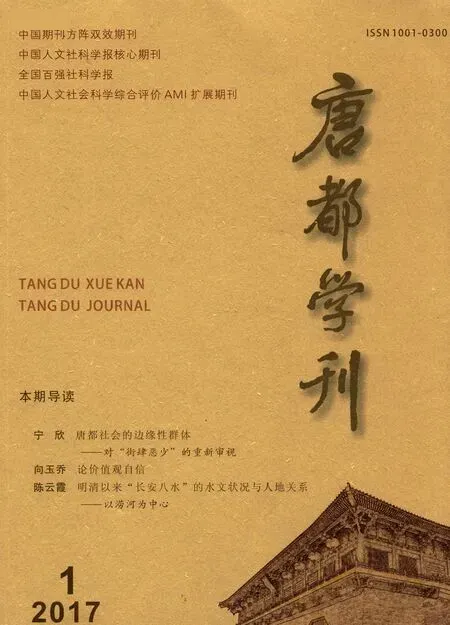明清关中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韩城解氏的家族命运
赵爽英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西安 710127)
【历史文化研究】
明清关中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韩城解氏的家族命运
赵爽英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西安 710127)
在明清宗族研究中,里甲赋役制度对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国家礼制的变革、乡约保甲的地方实践以及宗族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宗族组织的自身演化。陕西韩城解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不仅显示了以上诸多因素对华北宗族的影响,也呈现出明清关中宗族组织的独特性。
明清;关中宗族;韩城解氏
在明清宗族研究中,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对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和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版。刘志伟:《宗族与沙田开发——番禺沙湾何族的个案研究》,《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此外,国家礼制变革*参见[英]科大卫、刘志伟:《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乡约保甲的推行等[1],均对宗族有重要影响。与此相对,日本学者对中国民间宗族组织的关注,则注意到宗族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参见上田信:《地域の履歷—浙江省奉化縣忠義鄉—》,《社会经济史学》第49卷第2号,1983年版;《地域と宗族—浙江省山間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4册,1984年版。瀨川昌久:《村のかたち:華南村落の特色》,《民族学研究》,1982年版,47-1。山田賢:《清代の移住民社會—嘉慶白蓮教反亂の基礎的考察—》,《史林》,第69卷第6号,1986年版。。在诸多有关明清宗族的研究中,华北宗族一直缺少广泛、深入的考察。与华南宗族相比,华北宗族在数量及规模上都远不能相较,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也不及华南宗族。甚至有学者认为,华北无宗族[2],或无成熟发展的宗族[3]。
近年来,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的田野调查显示,华北不少地区曾经存在过大宗族,但是其后逐渐退化,与华南宗族的发展轨迹正好相反,以至于造成了华北宗族不甚发达的印象。本文试图将华北宗族的研究置放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以更细致的历史时间梳理华北宗族的发展脉络,从而窥视明清华北宗族的完整面貌及地域特点。
本文选择关中为地域范围,以明清韩城解氏宗族的发展为研究个案。解氏是韩城大姓之一,1949年之前,这个家族一共编修过五次家谱,分别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清乾隆十五年(1750)、嘉庆二十二年(1817)、道光十八年(1838)、民国九年(1920)。目前,解氏家族保存有乾隆、嘉庆、道光和民国四个版本的家谱。除家谱之外,雍正年间,解氏族人还编有《解氏世行录》*清雍正七年解光爚编,手抄本。,收录了九篇解氏族人的墓志铭,分别为解来聘、解自克、解经雅、解经传、解经邦、解经达、解经铉、解胤樾、解胤植,其在世时间主要集中在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此外,韩城当地文物部门还收藏有解顺宇、解延祚、解朝柱、解几贞的墓碑,其在世时间亦为明清之交。在多个版本的韩城县志中,也有不少与解氏家族有关的记录。除与解氏有关的文献外,韩城当地还有大量金石碑刻存世,时间跨度上起汉魏,下至民国。这些散落于不同地理空间的金石碑文,也间或有与解氏有关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检审地方,及家族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在当地还流传有一些与解氏家族有关的传说,这些均成为研究解氏家族的重要材料。
一、韩城解氏
韩城位于关中平原的东北隅,东临黄河,与山西万荣、河津相望,西、北分别与延安地区的宜川、洛川接壤,南与合阳相接。韩城不仅处在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关中通往东部的重要关口之一。因地理位置重要,韩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较为主政者关注,尤其在金元时期,更因其军事意义而提升了行政级别。从地理环境上看,韩城处于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黄龙山系(梁山山区)占据全境2/3的面积,可耕土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川道。由于耕地面积有限,粮食生产不足,需要周边地区供给,故粮食的商品化程度较周边地区高。韩城山区内蕴藏有丰富的铁、煤等矿产资源,这些矿产在秦汉时已经获得开采,并且在当地形成了冶炼中心。
关中平原因农业文明发育较早,地方社会很早便进入国家建置,地方历史较早与国家相联。折射在家族的发展历史上,则是地方姓氏源流的久远,以及与地方历史相关联的祖先叙事,韩城当然也不例外。如韩城卜氏,因春秋时孔子学生卜子夏授学河西,自称为其后;白氏,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此征战,后子孙留驻,为白氏之源;董氏,西汉秦将董翳封于此,子孙延续;薛氏,北魏薛洪祚及唐薛仁贵均因赐田韩城,为韩城薛氏之祖;郭氏,唐代名将郭子仪在此驻军,子孙留居,为郭氏源头……至于张、梁、杨、牛、陈、卫、徐等姓氏,也多有其明晰的祖先来源。姓氏源流的传说,均与地方历史相勾连,形成了相对确切的祖先叙事。除了世家大族,明清时期,韩城还有不少因经商而显赫的家族,远有“苏、牛、薛、张”,近有“南胡、北党、东丁、西杨”。因商而富的家族,多鼓励子孙科举入仕,故明清两朝韩城人文蔚起,入仕为官者甚众,以致民间有“朝半陕,陕半韩”之说。
在韩城当地的大家族中,解氏曾经显赫一时。明清两朝,解氏家族共出了9名进士(含武进士)、13名举人、14名贡士。尤其是万历十九年(1591)到崇祯十四年(1641),解自克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进士、一个举人、一个贡生,“一门三进士、一举一贡生”的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解氏家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辉煌顶峰。
韩城的地方历史中,目前所见最早关于解姓的记录,出现在金承安四年(1199)圆觉寺铁钟铭文上。此铁钟铭文上详细铸刻了捐资者姓名及所在村庄。这些捐资者中,既有地方官员,亦有寺僧及平民,所录地名大部分至今仍存,其分布几乎遍及韩城辖区各地,甚至包括远离县城的山区村落。在密密麻麻的捐资者中,有“官庄社解五郎”之名。官庄之名至今仍存,位置在距离县城30公里的山区内,是韩城通往北部宜川的中转站。继金代捐资修寺的记录之后,解姓再次出现,是在元元祐四年(1317)《重修汉太史司马祠记》碑中*此碑年代缺残,其碑文中有“□□□年岁次丁巳中秋日立石”,立碑人为“从侍郎韩城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罗里”。元丁巳年仅有元祐四年,故推断,此碑立于元祐四年。韩城“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博物馆藏。,此碑捐资者名录中出现了“解庄解社长”一名。“解庄”之名今已不存,不过碑中所录的其他大部分村名仍存,均分布在韩城东南部的平原地带。由此推断,解庄也应在这一区域。以上两个历史片段,尚不能勾连起必然的历史联系,但是至少说明解姓在金元时期活动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内。
以上有关解氏的历史片段,均未出现在解氏家谱的记录里。关于先祖的面貌,家谱称“本山西稷山人”,关于何时入韩以及初来时的面貌,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重构(后文详述)。
从四世开始,解氏家谱的记录开始变得相对详细。谱记,六世解景智元至正年间曾为总旗,督修胡家寨,因督监严厉,时人传有“不怕知县挞,只怕总旗棍”的俗语。据县志所载,胡家寨即后来的周原堡(现为周原村),是“胡将军驻军处”。周原村至今还有胡姓居住,“胡家寨”之说应比较准确。由此可知,解氏在元代已具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元明换代,关中一带因未遭受战乱侵扰,地方势力得以暂时平安过渡。谱称五世解瑞在洪武五年(1372)被诏行乡饮酒礼,众人推举为上宾,可知解氏在明初依然保有一定的地方声望。不过,随着新朝廷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旧元势力纷纷瓦解。
洪武后期开始,在富户迁移政策及里甲户籍制度的推行下,解氏家族开始发生剧烈变动。谱载,八世解泰、解绰充“明太祖摆驾军”,此后,解泰、解绰后嗣便从谱系中消失。另外,六世解林的去向也值得注意,谱称解林“因事充大同安东卫军”,这一支系亦从谱中消失。家谱“迁灭”中记录了几支流亡支系,大都集中在六至八世期间,这个时间大致是洪武至永乐时期,迁灭原因,或充军迁移,或流落不知所在,由此使已成规模的家族分崩离析,最后仅剩几支留在原籍(见图1)。这些留在原籍的族人,通过里甲户籍的编订,逐渐被纳入新王朝的控制之中。

图1 解氏前六世谱系图,根据乾隆十五年《解氏家谱图》重绘
二、家族谱系的编修
郑振满在研究福建地区家族组织的成因时指出,里甲体系的崩坏,是促使明代大型家族组织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郑先生认为,福建各地的里甲户籍从明永乐年间便已经严重失实,至迟在成化、弘治年间,里甲户籍已经固定化和世袭化,里甲组织逐渐成为户籍管理和差役负担的承包单位。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在家族内部,为了共同管理里甲户籍及分摊有关义务,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把全体族人纳入同一赋役共同体,如此便出现了赋役共同体性质的家族组织[4]。王绍欣在对山西闻喜的户族组织进行研究时也发现,户族亦是里甲赋役制度下催生出的民间组织[5]。陕西关中地区家族组织的形成同样受到里甲赋役制度的影响,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
与福建等地区不同的是,整个明代,关中的里甲制度不仅未完全松懈,甚至还存在不断清理里甲的情况。整体上看,关中东部地区(明代西安府同州辖地)里甲户籍的清理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时期:一是成化,一是嘉靖。成化时,关中大面积灾荒,使人口流失,里甲败坏,于是西安府下各县都进行了里甲的清理与归并,幅度甚大,有些县的里甲甚至裁并掉一半。韩城的里甲数从明初的50甲裁并到40甲。正德时,关中东部连年地震,再次令民户失散、里甲松懈。嘉靖初,明廷特别要求西安府重整抛荒土地*参见《明会典》卷17“田土”:“(嘉靖)八年,令陕西抛荒田土最多州县,分为三等:第一等,招募垦种,量免税粮三年;第二等,许诸人承种,三年之后方纳轻粮,每石照例减纳五斗;第三等,召民自种,不征税粮。抛荒不及三分、有附近及本里本甲本户人丁、堪以均带种者,劝谕自相资借牛种,极贫无力者,官为借给。责令开垦,不必勘报。又令陕西抚按官,将查勘过西安、延庆等府田土,果系抛荒、无人承种者,即召人耕种,官给牛具种子,不征税粮。若有水崩沙压、不堪耕种者,即与免豁。”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万历重修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嘉靖二十二年(1543),西安府内州县再次大范围缩编里甲,韩城的里甲数此时缩编为36里。除了府州一级的里甲整编外,嘉靖四十年(1561),韩城当地还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土地清丈,并进行了相应的赋役调整,将土地视为里甲赋役的主要依据。此后,数任地方官不断清理里甲户籍,严防土地诡寄,形成了相对比较严密的里甲系统。在数次里甲清理中,普通民户家庭不断分籍分户,最终难以形成大家庭,只有那些军户家庭,因明初不分户的规定,始终未遭分户,到一定时期后便会形成大家庭,而户籍仍籍一人之下。目前在韩城当地所见的几份明代家谱谱序,大都自称为军户,如城南村徐氏、渚北村卫氏、张带村张氏等。韩城解氏虽未明确表明军户身份,但是根据诸多信息判断,明代修谱这支也应是军户。
解氏首次编谱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这个时期是关中赋役变革的重要时期。嘉靖二十二年,西安府内各县都进行了里甲归并,嘉靖四十年韩城完成新一轮土地清丈,并制定了按照土地等级纳赋的标准。此时,庞大的家族规模在赋役变革中产生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有序管理家族内部人丁事产,完成赋役摊派。
解氏嘉靖四十三年编谱的主要目的,虽有理清血缘关系的说辞,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有效管理房支人丁。尽管谱序中称,族内此前曾有族人记录前世谱系,但是此次谱系的划分并没有完全遵照自然的血缘关系,而是以均衡人丁数目为目的。其原则是:人丁兴旺的支系可能会被拆分成多个分支,人丁稀落的支系则可能会保持原貌。乾隆谱序称:“前谱六世长分祖,二子一孙,分叙三支,六分祖四子一孙,分叙五支,其余四分、西院,各叙一支。查谱载,当年原因各门地丁多寡不齐,分支派差,以均苦乐。”*参见“续辑家谱记”(乾隆十五年),乾隆十五年《解氏家谱图》,手抄本。这段话说明,嘉靖谱系的编修与里甲赋役摊派有密切关系。明中期里甲赋役制度的变化,同样也是关中家族组织形成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明代的里甲赋役变革中,关中东部有一些做法与其他地区稍有不同,从而影响到了家族组织内部的发展。如朝邑县在正德前开始推行银力二差并行的变革*参见正德《朝邑县志》“田赋”。,万历“一条鞭法”推行时,地方士绅并不接受差徭全部折银的做法,力主银力二差并存*参见“雷士祯代知县赵公条鞭议”,康熙《朝邑县后志》卷8《艺文》。。韩城的做法是以赋代丁,民户粮二石为一丁,军户粮三石为一丁,“丁于是乎稍宽,而赋于是乎益重矣”*参见万历《韩城县志》卷2《赋役》。。解氏族内也有自己的做法。谱记,长分祖解孟(七世)曾掌管族中粮差,起初族中差银照丁均输,他认为如此不拘贫富,十分不公,便告于父曰:
今族中有及食不足而丁差反多者,往往致输纳不给,而富者理应上门,乃反丁少无差,甚非至公。且朝廷设九则门法,正欲富携贫也。今若此,是使富者轻而贫者重也。我思往告,纵不能如九则,当以土田为主,每地五十亩,作丁一当差,庶使富者有携贫之实,而贫者少宽*参见乾隆十五年《解氏家谱图》(不分卷)“支派”。。
解孟的想法是,丁差若按实际丁征收而不考虑贫富,实在有失公允,不如以土地为标准,五十亩为一丁差,这样便可以使族内贫富相携。族内的这个做法是否始自七世解孟,难以确知,但是至少说明,解氏族内很早就开始尝试以土地为标准均平赋役。
在以土地为核心的赋役变革中,里甲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明洪武年初定里甲时,里甲的划分是以户为基础,配之鱼鳞图册,使人地关系清晰。随着里甲的变化以及土地之间的买卖,人地关系越来越混乱,在逐步的发展演变中,土地逐渐成为里甲赋役系统的核心。入清以后,里甲赋役系统继续沿着明后期的路径演变。清初重定里甲,关中同州诸县均采用了与明初不同的方式。如合阳县是“里甲分属田地,每里又分十甲,甲各二十八顷”*参见乾隆《郃阳县全志》卷4《杂记·田赋拾遗》。;朝邑是“大约银百两为一甲,十甲为里,十二里为运,运分为三,里分为三十有六。”*参见康熙《朝邑县后志》卷2《里镇》。韩城的做法与合阳近似,即以土地为里甲编订的标准。
民国《解氏家谱》“新附”里存录了一段有关清初里甲划分与家族关系的记录:
六子后遂为六分,厥后又分为两户,承解泰十甲里长。至大清顺治年间,东户一甲分为五甲,应里长(一甲长分,二甲长分四分,三甲长分,七甲长分西院,八甲长分二分)。西户十甲分为二甲,应九甲十甲里长(九甲五分并西院,十甲六分并西院)。其间有胞兄弟分甲者*参见道光十八年《解氏家谱图》(不分卷)“新附”,手抄本。。
这段被收录进民国谱的“新附”说明,描述的是顺治年间韩城重定里甲的情况,抛开“东西两院”“东西两户”这些让人混乱的俗称,但就清初里甲的划分看,一里十甲之中,有七甲都在一个家族内分派,并非该家族人丁规模庞大,占据一里人口的7/10,而是解氏占有的土地规模为本里的7/10。
但是,大量的土地占有,并未给解氏子孙带来富足和依靠,反而是沉重的负担甚至灾难。在一条鞭法的推行中,关中一些地区的变通做法,使银力二差并存。清初军伍旁兴,几次平乱,陕西均为驻防或调遣之地,民间差役难以解脱,而地方官吏借机渔猎,使临时性的差徭变为长期性的摊派,以至于丁银之外仍有差役。整个清代,虽有地方士绅不断呼吁,沉重的徭役负担始终未革除,成为关中最大的积弊,以至于积重难返。最为重要的是,差徭并不是按照人丁分担,而是以户等来摊派。户等的确定,以“地多而丁少者为上,以丁多而地少者次之”*参见“李朴审编议”,康熙《朝邑县后志》卷8“艺文”。,这样,土地越多则户等越高,所要承担的丁差役银也就越多,造成的结果是,谁拥有的土地越多,谁的负担就越重,沉重的徭役负担甚至会拖垮富家大户。解氏家族大约从清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固然有经商失败的原因,更有大量土地占有带来的沉重的徭役负担对家族发展的阻碍。
清初以土地为标准重定里甲,打乱了前朝以人丁户籍为基础的房支关系,形成了新里甲系统下的家族结构。大约康熙中后期,解氏族人还曾编修过两次家谱:一是由解延祚编修,一是由解全斌编修,两人皆为六分十四世,修谱时间都在康熙年间。但是这两次修谱均未被纳入传世家谱中,族人称其“要皆各据所知,未免缺遗错讹,恐难传世”。族人如此评价康熙年的两次编谱,并非偏见,而是与摊丁入地之后家族结构的再次变化有关。
雍正三年(1725),陕西开始推行摊丁入地,宗族与里甲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乾隆谱序中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个变化:
查谱载,当年原因各门地丁多寡不齐,分支派差,以均苦乐。然均差徭则善,叙世系似属搀越紊乱。况新例丁入粮条,炤地行差,前法寓乎其中,何需仍生枝节?今特厘正,俾观者不以父子分支为疑案,而世次了如指掌矣。由是亲亲长长,敦人伦以迓天庥,顾不善哉!*参见“续辑家谱序”(乾隆十五年),乾隆十五年《解氏家谱图》。
此段叙述显示,摊丁入地之后,以粮载丁,按地行差,家族内部不再需要为均平人丁数目而不断调整房支结构,宗族与里甲赋役的捆绑关系得以松弛,宗族世系回归到原有的血缘关系上。解氏乾隆十五年(1749)的修谱,没有采纳康熙年间的谱系,而是循着嘉靖谱的世系结构,按照明初五、六世祖的房支关系编排世系,形成了东院六分(五世解瑞及六子后嗣)及西院一分(五世解彬后嗣)的结构,并延续至今。此后,家族组织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三、合祀会食与祖先建构
解氏居韩城北原,北原因地狭人多,故人多事商贾。解氏也不例外。明中期,解氏依靠在中原一带的生意,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族。十一世解来聘墓志铭中称,他曾游历汴洛、吴越一带,虽身无官职,却喜藏书,遇好书便不惜重金购买,同时结交仕宦,被称有“廊庙之材”*参见“诰赠兵部侍郎松山解公暨党太夫人墓志铭”(万历二十七年),《解氏世行录》。。解来聘游商的经历扩大了他的眼界,也让他认识到科举入仕的重要性。不过解来聘的儿子解自克、解自修屡试不录,于是他便将希望寄托孙辈身上。在解来聘的严教和期盼下,五个孙子不负祖辈期望,三位接连中举,其后两位也各为举人和贡生。“一门三进士,一举一贡生”的佳话,使解家声望迅速提升。
解自克的第三子解经邦首先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考得进士,六年后,解经邦的两个哥哥解经雅和解经传同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登榜。解经邦、解经传均官至兵部侍郎,解经雅官至山东按察司使。三位进士为解家带来的荣耀非同一般。据称,解氏兄弟在朝为官后,在解家村西通往县城的大道上,有皇帝亲赐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碑石,解经邦、解经传还入祀乡贤祠。其后,解经邦的弟弟解经达于天启元年(1621)中举人,解经铉则于崇祯十四年(1641)为恩选贡生(见图2)。

图2 解来聘家族支系图(十一世到十三世),根据乾隆十五年《解氏家谱图》重绘
解氏兄弟科举入仕的成功,使其父解自克有身份、有条件也有意愿投入宗族的建设中。解自克对宗族建设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促成本宗“合祀会食”的完成。在合祀祭文里,解自克称:
我族自祖宗肇基发祥,人敦庞懿,俗酿雍睦,云仍世承,称关内右族。……盖恒情合欢于杯酒,则嫌疑不生,骏奔于有恪,则匪彝自化,是会族之关风教重也*参见“合祀碑文”,道光十八年《解氏家谱图》。。
“关内右族”的说法其实有些自夸,即使在元代,解氏也还是督修寨堡的总旗,怎能与唐宋时便在当地已具盛名的世家大族相比?不过时代流转,此时解氏家族的崛起,足可以使历史叙事发生改变。
解氏家族的合祀仪式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清明举行,地点就在解氏祖茔。这次合祀仪式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解经邦兄弟的捐助,合祀仪式由解自克主持完成。显然,合祀的目的和编修家谱不同。如果说编修家谱完成的是家族内部人丁事产的有效管理,那么合祀则多少带有标榜正统和显宗耀族的意思。解自克在合祀碑文里对解氏家族的夸耀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子孙们官居高位之时,这种夸耀又是必需的。是年七月,解自克离世,第二年清明的合祀仪式由其长子解经雅主持完成。
解自克墓志铭中,称其“捐多金以鬻祭田”*参见“敕封文林郎诰赠兵部侍郎瑞亭解公墓志铭”,《解氏世行录》。,说明此时解氏已经有了祭田形式的族产。族谱、合祀仪式、祭田,标志着解氏家族初步完成了从家族组织向宗族组织的转变。
除了合祀仪式的完成,在建构祖先的过程中,祖先源流确定愈发显得重要。说不清祖先源流,即便有合乎品官身份的祭祀仪式,家族身份也还是一个问题。嘉靖四十三年谱序中,关于解氏源流如是表达:
予族世居韩之北乡,姓解氏,本山西稷山人。谨考氏族等书,解氏出叔虞之后,本姬姓,武王子叔虞封于唐,即今平阳之域。后子孙有居解者,因以为姓,即今解州。姓字本上声,后讹为去声云尔。按此姓极寡,考之史传,实不多见。惟汉有解光、五代契丹有解里、后汉有解晖、晋时汉蜀有解思明、孝顺事实有解叔谦、宋时有解元、国朝洪武时有解缙,自此之外,则绝无闻焉*参见“家谱原序”(嘉靖四十三年),《解氏家谱图》(乾隆十五年)。。
嘉靖谱序称,解氏自晋入韩,但并未言及何时而来。至于解姓中的名望,则是氏族书上所列举的解姓名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张士佩为解来聘撰写墓志铭时称,“先世曰进者,自稷山徙于韩。其后子孙蕃衍,遂为韩城著姓。”天启三年,解经雅墓志铭则称,“公之始祖讳进者,洪武时由晋稷山徙韩原。”此后,经传、经邦、经达、经铉的墓志铭中,对先祖身世的表达都十分模糊,可知族人对于祖先源流并不清晰。
为了更清楚地建构祖先源流,在首次合祀仪式后不久,三进士赴山西稷山寻根问祖,确定始祖身份。此段经历被记录在山西稷山解氏家谱中:
解氏之姓,由来已久,……及至宋则有解晦、解潜而外,又有我始祖解元焉。余曾读百将传,见载有韩世忠遣解元画金人于潭城大捷事,始知余祖乃为宋之名将也。但世远沼年,塚眠狐狸,祭不丰杰。幸邑侯刘公起褒忠之意,亲至下柏村北督工,而狐狸之害可免矣。然坟茔虽新,祭典尤缺,且互相争讼,几欲废祀。又幸韩城(陕西)有族人三进士来稷山祭祖,闻祭典不丰,自为咎责,因施伍拾金作为春秋奉祀之费。但托金大事几难其人。见余九世祖邦宰及八世祖自新醇谨,遂顷心托焉*参见“解氏家谱序”(同治元年),民国稷山《解氏家谱》,手抄本。。
这份谱序录于清同治元年(1862)的重修家谱序中,其中提及的邑侯刘公,指的是稷山知县刘三聘。刘三聘曾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对解元之墓进行过整修,结合解经雅的生卒,解氏三进士到稷山寻祖的时间应在万历四十四年到天启二年(1622)之间。不过此时虽有邑令亲自督修解元墓地,稷山解氏宗族似乎还未真正建立起来,祖先祭祀并未完成。三进士赴稷山,本打算寻得一个有身世的解氏家族来寻根问祖,但稷山解氏的情况看起来不尽人意。不过,三进士不仅没有放弃稷山远祖的名头,且还出金资助祭典,用意显而易见。
大约清康熙年间,韩城解氏已与稷山解氏实现了联宗。山西稷山解氏谱中载录了一份《韩城解氏谱序》,这份谱序并未收录在韩城解氏的家谱内:
始祖讳进,姓解氏,河东稷山县城市人,先世有兜鍪起家者,人以元帅家呼之。宋、金、元时,遭金兵之乱,兄弟四人,各求避难,二世祖逃往万泉县北牛池村落户,三始祖逃往陕西韩城井头坡落户。……先祖有曰道、曰达、曰通者,料皆始祖之同堂也。我族自万历辛卯开科,始祖十四世孙解经邦明进士,官至侍郎;解经雅明进士,官至廉使;解经传明进士,官至侍郎;解经达明举人,官至翰林。明官甚多,尚未全计。此时贡、监生近七十,难以尽书。如清朝进士解几贞,官至侍郎,尚未离位。其余文武官员,难以备载*参见“韩城解氏家谱序”,民国稷山《解氏家谱》。。
这份经过后人反复誊抄的谱序,首次撰写时间难以判断。不过,根据解几贞墓志铭可知,其在康熙九年(1670)补郎本部,康熙十七年(1678)离世。文中称其侍郎“尚未离位”,那么这份谱序的初次撰写时间当在康熙九年到十七年之间。从内容看,此时的韩城解氏已与稷山解氏实现了联宗,韩城解氏获得了宋代名将的先祖名分,稷山解氏则从韩城解氏那里获得了作为明代显贵的近亲,双方各有所获。在嘉靖谱序里,解元还只是族人从氏族书中引用的解姓名望,而到此时,已成为解氏可以炫耀的先祖了。
四、同居村落的形成
除了家谱编修以及合祀仪式的完成,在解氏宗族的发展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便是同居村落的形成。正是解氏同居村落的存在,才使我们有条件看到关中宗族在清中期以后的重要转折。幸运的是,解氏家谱中存录了不同时期的四幅村图:一为乾隆谱所附“旧图”,一为乾隆谱所附“新图”,一为道光谱所附村图,再一为民国谱所附村图。根据谱中提供的各类信息,乾隆谱中所附“旧图”,应是以嘉靖谱中的村图为基础,不断增添新内容,故显示的是明嘉靖至清康熙时期的村庄面貌。“新图”为乾隆十五年(1750)修谱时所绘,嘉庆谱在此图基础上有所添加,故“新图”显示的是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村貌。道光谱中所附村图为谱中新绘,民国谱中的村图亦为当时新绘,故两图显示的分别是当时面貌。这四幅不同历史时期的村图,为我们窥视解氏同族村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3 解家村图(明末清初),根据乾隆十五年《解氏家谱图》所附“旧图”重绘
“旧图”显示,村西南有一坡道,名“井头坡”,又名担水坡,是始祖初迁之地。家谱中也称,始祖解进最初落脚井头坡。“井头坡”之名现已不存,根据田野踏查,在解家村西南坡下,遗留有数十孔废弃窑洞,应为谱中所记的“井头坡”。大约元中前期,四世敏信离开井头坡,在其北的台塬上创宅居住。此处地势相对平坦,除一面临坡外,其他三面均较为开敞。其后,敏信子孙在此繁衍居住,为今日解家村的前身。
敏信有二子,长为瑞、次为彬,分别为东院和西院的始祖。瑞生六子,建六宅居之。六宅的前三院,为长、次、三子居住,后三院为四、五、六子居住。依“旧图”所示,前后三院居于整个村落的中心位置,村舍及村内主要街巷均围绕“六宅”展开。如此可知,“六宅”是解家村早期的聚落中心,村内住户大部分是“六宅”主人的后嗣(见图3)。
谱记,嘉靖二十二年(1543)时,因地方匪乱,村人据崖修建起三面城墙。城墙的修建,意味着村庄在地理空间上的稳定,而城门的开启与管理,又会加速居住者的社区化管理。
“旧图”显示,村内的寺庙仅有两座:一是关帝庙,在六院之东南;一是观音庙,在六院之南。除了关帝、观音两座寺庙,村内再无其他信仰建筑,更多寺庙集中在村外。村西门外有庙院,集中了关帝、娘娘、法王、土地、观音诸庙。村东门外有一观音庙。另外,村西门南还有一观音堂,村南坡一低凹处有三官庙。此外,村子的东南角还修建有一座小楼,谱称,修此楼是因为风水原因,小楼建成后,村内科举日盛。崇祯七年(1634),族人又在村东南低凹处修建了文昌阁。
墓地在村庄之北,紧邻北门,分老坟和新坟两处。始祖合葬墓及二世祖墓在老坟地,四世后的祖先都葬在新坟地。四世和五世墓均修有墓塔,四世敏信之墓被族人称为“后塔爷”,五世解瑞之墓被称为“前塔爷”。合祀碑、记事碑在新坟地,旁边注文:“清明拜扫两户人在此享献”。
此外,寨堡的位置也需要特别说明。韩城当地因特殊社会环境,各村落普遍形成建寨修堡的风气。在平坦地带修筑起城墙的村庄被称为“堡”,在特殊地形修筑城墙的聚落被称为“寨”;称“堡”的地方多为古村落[6]。寨子一般临乱才有人居住,但若连年动荡,有些住户也会长期居住在寨内。谱记,明天启元年(1621)解家村修筑金城寨,后被称为“老寨”。崇祯八年(1635),“有贼八队领数千人,自延安至韩城,劫掠村堡甚多。在余村居住四十多天,临行将村中房屋尽行烧毁,火光连天,数日不散,合村人民尽避老寨,始得保全。”*道光十八年《解氏家谱图》(不分卷)“记事”。此次浩劫对解家村损伤甚重,但幸有老寨避乱,全村人才得保全。至清顺治元年(1644),韩城山区流寇作乱,族人因老寨避乱较远,又修筑小寨,位置在村之西,与村西门隔沟相望。在村图中,特别注明了前往老寨的道路以及小寨的位置。

图4 解家村图(乾隆至道光时期),根据道光十八年《解氏家谱图》所附“新图”重绘
至乾隆年,解家村的面貌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变动的细节,也颇值得注意。乾隆谱所附“新图”中主要有这样几个变化:其一,村内出现“合族祖祠”。谱记,乾隆五十年(1785)“祖茔”出赀,买本族某旧祠一所,以奉始祖及列祖神主,冬至、元旦拜祀。这个“祖茔”,指的是以祖茔祭祀活动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掌管每年祭祀的活动资金以及与此有关的族内公产。合族祖祠的出现,反映了宗族组织在此期间的变化,后文再述。其二,合祀碑侧注文从“清明拜扫两户人在此享献”变为“清明拜扫合户人在此享献”。从“两户人”变为“合户人”,说明参与祭祀的群体发生变化。其三,西门外的庙院里,增加了财神庙和玉帝宫,并增添了两座戏台。戏台的出现,说明寺庙内的公共活动增多。其四,村西南涝池旁新增一座官房。其五,新开了南门(见图4)。
嘉庆谱中还特别注明,村东南的小楼原系三分解三策私产,“昔年因与祖茔有关,公中出赀修补;后祖茔又出银十两,遂为官物。……今此楼颓毁,不记何年,而基址尚未尽没。族中长老,有欲计重建以扶村脉者,故仍载于图,以昭旧迹……。”小楼当初是因村庄风水原因而建,谱中称小楼与“祖茔”有关,故修补之资全部“公费”;其后,又由“祖茔”出资纳为官物,成为村庄的公共资产。从修补、购买小楼的“资金链”中,能够窥见到宗族与村庄的紧密关系。
至道光十八年(1848)修谱,谱中再次附新村图一张,其面貌与乾隆“新图”基本相同,新添建筑除东观音庙的戏楼外,还在通往县城大道的路上新添了一座石牌坊,其他基本无所更改。至民国,村庄面貌的改观也不大,民国谱所附村图中,只在墓地合祀碑前出现了两座戏台,另外东观音庙及三官庙的规模有所扩大,增添了多座庙舍。
整体上看,明末清初是村庄面貌基本定型时期,其后的村貌基本未有大的变动。相对而言,清中期村内的变化稍多,村内合族祖祠及官房的出现以及寺庙建筑的增建及戏台、戏楼的出现,投射出这一时期村庄管理模式的微妙变化。
五、乡约保甲推行下的宗族演变
乡约萌芽于周朝的读法,形成于宋代的《吕氏乡约》,在明朝开始得到官府的提倡,清代进一步普及。乡约分为绅办乡约和官办乡约两种。绅办乡约是由乡绅倡办,民众自愿加入,不承办公务,不受官府干预。而官办乡约则是指由官府推行,主事的任免须经官府同意,职能上需承担官府交办的任务。一般而言,明末清初的乡约多呈现为绅办性质,清康熙以后的乡约则以官办为主[7]2。在官办乡约的过程中,乡约组织逐渐行政化,并演变为地方性建制。为了便于乡约在各地推行,清代北方相当一部分官办乡约的设置与各地基层社会组织结合,因地制宜,形成了诸多带有地方特点的乡约组织[7]14-18。
陕西的乡约实践也带有地方性特点。嘉靖十九年(1540),陕西按察使莫如忠在推行乡约的过程中,提出了“寓保甲于乡约之中,附义仓于乡社之内”的原则,其用意便是利用陕西民间原有的乡社组织实现乡约保甲的功能。明嘉庆万历时期,同州各县基本都推行了乡约,并普遍出现了“乡约所”的建置。入清,乡约的推行由官绅推动逐渐演化为官方行政化的推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约”的行政建制。延续明代乡约推行的经验,清代乡约的推行也十分注意利用和改造民间原有的社会组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韩城当地的情况看,选择何种民间组织作为乡约的实践单位,是以其在基层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为原则。
在解家村内,解氏宗族的影响力已显而易见,故官办乡约的推行中,利用并改造了解氏宗族。细读解氏家谱,并结合村庄面貌的变化细节,可发现解氏宗族在乾隆年间发生了如下两个变化:
第一,变小宗祭祀变为大宗祭祀。前文已述,在解氏族人的墓地中,合祀碑旁注文有一个细微的变化:旧图注“两户人”,新图注“合户人”。这个“两户人”,应是指东院分出的东西“两户”,并未包括西院在内。如此也可知,万历三十三年解自克促成的清明合祀,拜祀的是东院始祖解瑞,而非始迁祖解进。“合户人”则包括了东西两院在内的合祀,祭祀的对象也从东院始祖变化为始迁祖。解家村是四世敏信迁居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村落”,包括了东西两院住户,两院族人共同参与祭祖,利于宗族组织整合整个村庄的住户。
第二,宗族在形式上更为完备,出现始祖祠堂。前文已述,乾隆五十年(1785),祖茔出赀购买了本族旧祠一所,改建为始祖祠堂。从村图上看,始祖祠堂位于村庄中部偏西位置,除了冬至、元旦的拜祀,也是族内议事之地。按说,解氏全族人的祭祀,是每年清明在墓地举行的合祀,为何还要在村内再建一个祖祠,并增加族人的合祀活动?若是从乡约推行的角度看,始祖祠堂类似于“乡约所”的建置。
“乡约所”是聚众讲约的场所,明代后期已经出现,到清代更为普遍推广。段自成认为,清代乡村的乡约所多分布在寺庙中,单姓村或族约中,乡约所会就村中的寺宇、祠堂为之[7]120-130。祖祠的出现,可视为宗族为配合乡约的要求,专门设置的宗族性质的公共场所。解氏始祖祠堂的出现,是乡约推行的需要,也是乡约对宗族改造的结果,它使解氏宗族呈现出更为组织化的形式。常建华在研究中也指出,清雍正以及乾隆时期,是清朝治理宗族与乡村的重要时期。在乡约保甲的推行过程中,清廷要求在聚族而居的地区以族正发挥保甲的作用,族正成为保甲制的一部分。故常先生认为,宗族乡约化促进了宗族组织化的发展,使其更明晰地呈现出族谱、祠堂和族产的形式[1]。
但是宗族与村庄的紧密关系,在乾隆后期发生变化。这次变化的动因不在制度,而是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村庄内部结构的波动。康熙初年,韩城人口已经开始持续增长,以致“粮丁溢乎甲数”。*参见周原堡张氏“创建祠堂序”碑(康熙十八年)。该碑为残碑,现保留在周原村张天德家中。明末韩城的人口数还是6万,历康熙、乾隆的发展,及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人口数已接近20万,翻了3倍多。人口增长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对于村庄而言,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如何管理日益拥挤的村庄?早期村庄内部,聚族而居的传统使房支之间保持着一定的社区间隔,房支结构与村庄社区之间能够维持一定的对应的关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房支之间杂居、混居情况日甚,同时一些房支因居住空间的拥挤而纷纷迁出村庄,房支结构与村庄社区之间的对应关系也被打破,这使得宗族对村庄的管理也出现问题。清中期以后,随着乡约保甲的深入推行,“社”的组织逐渐取代了宗族组织对村庄管理。
“社”是普遍存在于秦晋乃至华北地区的民间信仰组织,其起源可以上溯史前。张士佩在县志中称,“社者,土之神也;夫人食地之毛,而春祈秋报,此乡社之礼,古有之而遗于今者。”*参见万历《韩城县志》卷六“坛庙”。关中地区“社”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基本面貌一直保存于民间。元代推行社制,逐渐将这种民间信仰组织改造为具有劝农、教化、互助以及治安等职能的基层社会组织[8]。此外,在信仰仪式上,逐渐形成了以“赛会”为内容的乡社仪式。明初推行里社制,对元代社制系统下形成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剧演有所限制,从而使村社组织一度在民间沉寂。嘉靖以后,随着明廷对民间信仰管理的放松,民间信仰复苏,沉寂在信仰系统内的乡社组织也逐渐活跃起来。嘉靖时,陕西尝试“寓保甲于乡约之中”的乡约实践原则,激活了“社”的组织中原本具有的保甲功能。及至乾隆时期,随着官办乡约的深入推行以及人口增长等原因,村社组织普遍出现分化,形成了组织化的村社或赛会组织。
相对而言,以信仰社区为单位的村社模式,比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模式,更能灵活适应人口增长带来的杂居和混居问题。大约乾隆后期、嘉庆初期,韩城当地的村社模式也开始在宗族占主导地位的村庄内推行,解家村便是一例。
谱记,嘉庆二年,因为村庄城墙毁坏,本族乡约解丕祥倡议重修,“官赛及族众各捐赀,而祥督其役”,*参见嘉庆二十二年《解氏家谱图》“记事”。这个“官赛”指的就是村社组织。此次修整城墙,不再是宗族出面,出资者也不是“祖茔”或者“祖祠”,而是由本族乡约发起,由“官赛”以及族众出资,说明赛会组织已在解家村内建立。嘉庆二十二年,解氏再次修谱。此时,韩城已开始推行牌甲制。根据嘉庆县志的记录,当地保甲的编订办法是:十烟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整个辖区分为县城以及东、西、南、北四个乡,各乡人口编审分烟户和客户两种。保甲制编审户丁的形式,无疑对那些以宗族为主要结构的村庄影响最大。解氏宗族与解家村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道光十八年,解氏第四次修谱,谱序称:“余族之谱,屡经续辑,每辑三卷:一存主祭者、一存续谱者、一存做赛者,非不惮烦,以备不测耳。”*参见“重辑家谱序”(道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解氏家谱图》。所谓主祭者,当是宗族,而做赛者,则是村社组织。将族谱存放一份至赛会内,至少说明此时的村社组织已经成为村庄的主要管理者之一,宗族与村社的关系,很可能是宗族隶属于村社,成为村社系统下的民间组织。村社组织的活跃,也使寺庙内公共活动的增加。乾隆后,解家村西门外的庙院内新增了两座戏台,以满足赛会剧演之需;观音庙也修建了戏楼,为乡村仪式的剧演提供场所。在每年的赛会活动中,解家村内的住户被分为东、西两社,这两社与东西两院或东西两户都没有关系。
宗族对村庄的管理职能被村社组织取代,令宗族与村庄的关系日渐疏离,宗族在基层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弱,当地方秩序波动,宗族能够发挥的功能也越来越小。不过,宗族自身也开始发生演变。一种变化是,大宗族分化为小宗族,以小宗为单位进入村社系统,在村庄管理中继续发挥小型社区管理者的作用。由此出现的结果是,不少村庄内的村社划分与各姓氏的小宗族对应,形成了村社与宗族相结合的新形式,一些宗祠与社庙结合,形成“族-社”化的宗族组织。这个变化在韩城当地较为普遍。再一种变化是,宗族与家族企业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族-商”一体的管理形式,宗族的实体意义增强,典型如党家村党氏宗族。不过,关中本地商品经济不甚发达,故此种宗族组织并不普遍。还有更多的宗族逐渐成为血缘的象征性组织,透过文化的延续性,持续存在于基层社会。
道光十八年谱序中,解氏族人称修谱是“念先世遗规,不可废坠”,并历数解氏先祖荣耀,“以表世芳,……以俟后之继起者”。此时的解氏,已经家道衰落,不具昔日辉煌。民国九年,解氏再次编谱,谱序称:
家乘之系,攸关綦矩。或卅年,或卌年,即当联辑一续,时浅简易,庶免失序乱宗,为子孙者,胡敢或忽乎?查自道光戊戌,迄今百有余岁,其所以延久而未续者,虽曰人事,亦天时世运之多阻耳。咸同之世,长发既反,回匪又乱,戎马仓皇,干戈扰攘,编氓流移罔定。光绪三年,秦晋豫连省遭大荒,斗麦价银,竟至四两有零,致版图户口,十存二三矣。现及民国,业经九年于兹,而到处变乱不堪,靡安宁日,此家谱未续之由来也。*参见“续修家谱序”(民国九年),民国九年《解氏家谱图》。
离乱之世,修谱存宗,是延续血脉,重振家道,血缘的象征意义越来越重。解氏先祖曾经荣耀一时,是族人可以不断提及的记忆;寻祖问根,以示子孙,在此时已经成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传统。至2000年解氏再次修谱,此种意蕴更为浓厚。
六、余论
从韩城解氏宗族发展脉络中,可知里甲赋役制度对明清关中宗族的形成与发展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华南等地区宗族发展的脉络近似。但是关中地区里甲赋役变革的地方性特点,也使关中宗族的发展呈现出一些特殊性。比如关中地区明代里甲编审相对谨严,故明代出现的大型家族多为军户家庭,清以后民间才普遍出现大家族。此外,在里甲赋役变革中,关中地区因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地方官绅普遍不支持赋役全部折银的做法,由此出现了带有关中特点的赋役变革模式,比如役银折赋,银力二差并存、以户等定力差,等等,无形中加重了土地的负担,成为“关中模式”的诱导因素[9]。
除了里甲赋役制度,还必须注意到宗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对宗族发展的影响,而这个线索必须与乡约保甲的地方实践结合起来认识。解氏宗族的发育成过程中,解家村也在同步形成。明清之际,乡约保甲的地方实践,不仅加强了宗族与村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推动了宗族组织化的发展,解氏宗族一度成为管理解家村的“代理人”。但是清中期以后,人口繁衍对同居社区的打破,使宗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出现缝隙。此后,关中地区普遍存在的村社组织逐渐成为村庄管理的主要代理人,宗族退出村庄管理。此后,宗族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宗族的发展也开始走向另外一条道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关中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如解家村这样的单姓村并不普遍。相对而言,大部分村落形成时间较早,杂姓村居多。这些杂姓村落经过金元时期村社系统的改造,大都保存了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村社系统。在明清乡约保甲的实践中,村社(乡社)系统因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逐渐成为最具动员能力的基层社会组织。清中后期,随着乡约保甲的深入推行,村社组织成为地方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基层社会组织。这是关中宗族没能持续活跃在基层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关于解氏家族的历史还有两个疑点未得厘清:其一是祖先的真正来源,其二是族群身份。关于解氏祖先来源,无疑存在重构的过程,真正的家族源流是否与金元时期地方碑文留下的解姓足印有关?从12世纪初金人入关,至14世纪后期元明交替,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关中一直处在金、蒙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北方民族人口大规模南下,带来了广泛的民族杂居,习俗相糅,文化相习,地方社会发生较大变化。明清两朝,族群问题在关中民间甚为突出,不乏各族为适应新政权而进行的自我改造。族群问题如何反映在宗族的建构中?宗族的文化表达上,南北又有何差异?有关此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1] 常建华.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71-76.
[2] 兰林友.庙无觅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 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J].安徽史学,2010(1):85-105.
[4] 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2):38-44.
[5] 王绍欣.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G]∥赵世瑜.大河上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211-239.
[6] 青木正夫,上和田茂:韩城地区的寨子[G]∥周若祁,张光.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66-76.
[7] 段自成.清代北方官办乡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仝晰纲.元代的村社制度[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35-39.
[9]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73-84.
[责任编辑 贾马燕 朱伟东]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lan Organizations inGuanzhong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f Xie Family’s Fate in Hancheng
ZHAO Shuang-ying
(CollegeofJournalismandComunications,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Research on cla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shown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i Jia) system as well as tax and corve (Fu Yi) system have produced very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lan organizations,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reform of national rites, the local practice of rural bonds as a neighborhood administrative (Bao Jia) system in the cla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ns and villages, also have exerted certain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of clan organiz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Xie family in Hancheng, Shaanxi Province have not only highlighted the effect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on the clans in North China but also presented a uniqueness of clan organization in Guanzhong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ansties.
Ming and Qing; clans in Guanzhong Area; Xie family in Hancheng
K29
A
1001-0300(2017)01-0088-13
2016-10-12
赵爽英,女,陕西韩城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