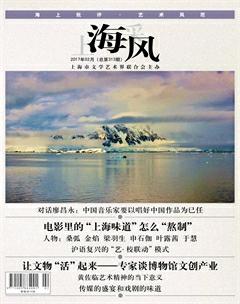我写《魔都》的初衷
徐策

离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不远的地方,沿河有一幢占地约7000平米的巍峨建筑,如果从空中鸟瞰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奇怪的S形。它,就是当年被称为“亚洲(远东)第一公寓”的河滨大楼。大楼堪称一部浓缩的近代史,历史烟云在这儿聚聚散散,许多史书或教科书上的事件、人物和场景,就在这里出现。至今,上海鲁迅纪念馆展厅里悬挂着摄于河滨大楼的大幅黑白照片,见证了鲁迅先生与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远东会议的代表瓦扬·古久里的那次会见。
关于这幢老公寓的传奇与沧桑,以下的“履历表”也许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大楼正式开工,中途因淞沪“一二·八”事变等战争原因,直至1935年才正式竣工;1938年,进入上海的8200名犹太难民中的大部分人下榻于此,这里一度成为接待犹太难民的地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侨民成为主要的承租对象;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影业机构租赁了部分房屋作为办事处,有著名的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米高梅影片公司、雷电华影片公司、联美影片公司和美国电影协会;1949年以后,河滨大楼原先居民纷纷离去,底层一度被用来作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部;1978年,八層的河滨大楼又加盖三层,这让大楼居民徒然猛增到700多户;1994年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河滨大楼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解放前,入住河滨大楼套间的基本全是欧美亚侨民,华人仅占很少部分。这其中,有李鸿章的外孙,黄金荣的孙女,维克多·沙逊的法律顾问等。1949年后,套间居住者除了工商界人士,就是一批高干、科学家、专家等,也有不少名流、艺术家。他们中,不光有历史学家、报界元老唐振常,眼科专家、被称为“东方一只眼”的赵东生,解放日报总编辑陈念云,女画家吴青霞,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等一批著名人士,更有民国时期围棋第一人——围棋国手,曾先后培养了吴清源、陈祖德两位高足的顾水如先生。可以说,河滨大楼既是悲喜交集、瑰丽多变的历史长廊,又是一宗活生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缘于此,河滨大楼被导演们屡屡看中,分别选作主要场景或内景地,先后拍摄了影视剧《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周末情人》《蜗居》《何以笙箫默》《纽约童话》等,周润发、斯琴高娃、王志文等分别在各自的影视剧中担纲主演。
河滨大楼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与时空轮回般的奇谲风貌,也正因为这样,它以巨大的气场强烈地震撼和吸引着我,也就毫不奇怪了。我的长篇小说《魔都》和之前的《上海霓虹》,均将笔墨集中描写河滨大楼。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部多卷式的长篇小说就是在为这幢历史名楼立传。只是为了艺术虚构,对原生状态、创作素材进行提炼与再造,构思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人物关系,构建其活动空间,在作品中才称它为“河滨大厦”。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河滨大楼汇聚了来自不同国籍、国内不同地区、不同乡邦的移民。尤其是1949年后,楼内栖居的绝大部分都是国内移民。这些“新老上海人”所生活的环境比较特殊,老公寓曾经华洋杂处,中西文化交汇。同时,大厦内主楼辅楼又有大房间、小房间之分,前者主人或有地位有名望、或有钱,生活条件比较优渥;后者解放前多为娘姨、厨师、司机、仆役,后来还是普罗大众。小房间类似于“富人区”中的“贫民窟”。这样一来,河滨大厦自然而然,被投射了更为繁复斑驳的人文历史色彩,也镌刻着上海有租界以来市情走向、民俗流变,包含了这座移民之城诸多特有的血脉和品格。大楼居住者或有钱或贫穷,或显赫或寒微,尽管社会阶层、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不同,但在闯荡上海、融入上海的过程中,这些移民个体、家庭,似乎总少不了磨难、挣扎和纠结,何尝不是艰辛备尝呢?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及其家庭,在大楼内外,各自经历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与此同时,在特殊年代,大房间和小房间,所谓“富人”(成功者)和“穷人”,社会主流人群和边缘人群,两者之间也在戏剧性地换位,枯荣转换,盛衰交替。这一切,无不引我思索,令我着迷,让我感动。然而,虽然知道这里也许是一个解读上海值得开掘的富矿,但却迟迟不敢动笔。我深知,对于我这样知识贮备、综合素质有限、功底不深,最主要的是没写过有较大影响作品的人,要驾驭好这个题材,恐怕是不能胜任的。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此之前,其实我最想当一名画家,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练习素描、速写、水墨和油画写生。美院考场的挫败使我颓然收手,留下了一个写满四十几页练习簿纸页的中篇小说《落榜》。意外的是,凭着它,被作协青创会沈善增老师吸收为第二期“青创班”学员——班里就我一个没在报刊上发过作品。文学的迟到者异常困顿艰涩。慢慢地,总算在《收获》《十月》等刊物发表了五六个中篇小说和一个短篇小说,并加入上海作协。九十年代初,从事业单位跳槽,开始新闻记者、编辑生涯,一晃二十多年。
再回首,做文学创作的,人早不是那时的人,杂志也不是那时的杂志了。而我自己,也是年过55岁的“新作者”了。天涯倦客,既然离开这么久,为什么会“归巢”?又什么会斗胆以长卷的样式摹写起河滨大楼了呢?
原因有四:首先,随着年龄渐增,内心却愈来愈多地重返生命的源头河滨大楼。那里,留下了我父辈、长辈生之挣扎的乐与苦、聚与散、浮与沉、生与死,锥心之痛难以释怀。其次,一座城市处于拆迁、一些有价值的老建筑被抹掉的包围之中,房产热又催生了原有城市格局、区域的重组与混搭,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名(如南市、卢湾等)、建筑群(石库门住宅、老影院、老大楼),或消失,或隐匿,或被改头换面面目全非。动迁伴随着人口转移,“老龄化”加大,以及知情人的逐渐故去,使得这座城市无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遗产均面临严峻挑战。还有,游历过欧美亚一些历史名城,往往惊诧或艳羡于那里对老城老楼老路的珍视与保护。已有两三百年,乃至更悠久的地标建筑、历史风貌竟依然能饱览无余,而许多老建筑如巴黎圣母院等,由于跟名著如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挂钩,在现实与虚构、传说与传奇之间,互动起来又会让人意趣无穷,磁铁般吸引大批游人前往揽胜。围绕一个著名建筑,通过追寻发掘梳理与虚构再造,使它鲜活灵动起来,这给我以启发。此外,二十多年的记者编辑生涯,使我又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社会方方面面、大范围接触各阶层人士,从而有了些许积累。
自从举家搬离河滨大楼,多年来,尤其是已过不惑往耳顺之年靠拢,重返生命的源头,成为一种念兹在兹强烈的内在驱动。对出生地和过往的追怀和依恋,似乎变成一种情结。事实上,许多在大楼曾经住过的人,也许都会有这样一种“大楼情结”。对于我,这种情结显然已成为一种无意识——在以前我所发表的那些中短篇小说中,不少主人公的生活场景就在河滨大楼,包括《9㎡》等。不知不觉中,我就在不断地摹写它。
然而,真正打算为河滨大楼立传,这个鲁莽而果断的想法还是着实吓了我一跳。大楼的“履历表”摆在那里:淞沪“一·二八”事变、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政权易手、解放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无不在这幢大楼里引起震荡或波动,勾连起许许多多人和家庭的命运多舛与惊变,这一幅历史画卷或“新老上海人”的移民手卷,內容实在太庞杂太丰富了,要想深入了解它,贴近它,破译和解构它,也实在太难了。幸好我生于斯,在我生活的那段时间长于斯,从小耳濡目染,浸润在那种氛围中,也听到长辈、前辈以及许许多多人讲起它的故事;然后我做了十几年的记者,作为一种生活积累,多年来我有意识地进行寻觅、搜集和挖掘,就像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因为熟悉和亲历这方面情况的人已经不多了。河滨大楼最早的一批住户已所剩无几,我要做的,就是争取一一寻访大楼的“原住民”们。
经过多年来不间断的努力,我有幸接触到了这样一些大楼资深居民:有1949年前就曾在大楼洋人家当“阿妈”的,还有1949年起为大房间资本家、干部、专家、演员等主顾当娘姨的“恩娘”,或楼里当裁缝师傅、电灯匠、洗衣工、小卖部店员等一批人;有当年嫁给南下正局级干部、并曾在大楼里当过扫盲班、民办小学教师的潘老师等,这样的局级干部家属还有好些;有大楼最早居委(起初称为“冬防队”)干部之一的蔡阿姨,她丈夫解放前是执业律师,以后失去工作;有高知背景家庭的亲属方老师等,她亲家两代人三人罹难,其中一位是五十年代副局级专家;有名人名流家庭……这中间,就有已故民国围棋第一人顾水如先生的女儿、外孙。顾家曾在大楼内有两个大套间,被逐后郁郁寡欢,一代国手客死异地,1978年后落实政策,又搬回大楼的加盖层里居住。顾家是大楼高层次居民的一个缩影。
当然,岁月荏苒,人事变易,由于时隔久远,要寻访到许多历史在场的见证人、亲历者并不容易,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魔都》《上海霓虹》故事发生的年代,对我这个生于1958年、50后的尾巴来说,虽不遥远,可也不近,我就像是在写历史小说。对有些历史场景,直接体验、经验虽然没有,好在有许多间接的体验、经验可供借鉴,包括长辈们的忆述,访谈,以及文字、影像、声音、器物等介质的资料。我到外滩上海档案馆去查阅相关资料;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检索、翻阅相关年代的老报纸合订本,还有寻觅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的影像、声音等视音频资料等。只要耐心“打捞”,总能够发现许多宝贝——一些有关昔日上海生活的珍稀视听资料及片子。此外,还有许多老上海影片、老唱片。我还常去旧货摊逛逛,流连藏宝楼、东台路(动迁改造前)、以前思南路徐家汇路等的古玩市场,真假器物都看,尤其是那些早已废弃的清末民国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有了更感性具象的媒资储备。写作时,与故事的规定情景、人物性格特征、情节走向、叙事逻辑相关联,一些细节就会自己跳出来,所要做的只是选择其中最贴切的。细节不是点缀或静物,也不单单是细部(刻画得异常精细,纤毫毕现),而应该是活的细胞,是活体中的一部分,融入流动的情节中,在这样的叙述织体中才有力量。
《魔都》中写了众多家庭和人物,譬如民国“围棋国手”缪镜吾一家;前“坤伶皇后”佟颖倩夫妇一家;电影机大玩家项炳其一家;河滨大厦中住大房间的曾经有钱有势有权人家与住小房间的下层劳动人民。但是,着墨最多的中轴主线,是写娇鹂祖鸿、秉逊舅甥两家人,两个家庭,舅甥两代人分别属于中产阶层(资本家)与普通劳动人民。河滨大楼像上海许多有历史感的公寓大厦一样,见证了沧桑巨变,宠辱不惊。寓居其间的人们,在时代大背景下则是沉浮荣枯总关情,福祸相倚,顺逆互伏,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我要做的,只是把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以绵薄之力,写一写我眼中的上海,也算是留下一份微不足道的个人化的城市观照与心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