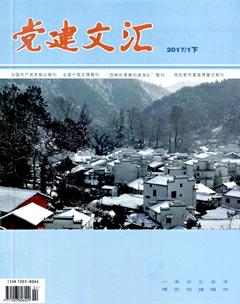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
向贤彪
《群书治要》这部皇皇巨著,是唐太宗委托四位大臣,在对唐之前三千多年历史中数万卷著作辑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用于指导治国理政。有史学家评论说,《群书治要》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用人之要。“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必然众望所归,事业兴旺。
爱才之心是基础。凡在事业上有成就的政治家都十分重才、爱才、惜才。楚庄王访贤用叔敖,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都是脍炙人口的求贤佳话。《滕王阁序》中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句,这“陈蕃之榻”中,就蕴含了一个感人的爱才惜才的故事。徐孺子名叫徐稚,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高士贤人。东汉桓帝时期,陈蕃任豫章太守,到任后遍访贤能,当他听说徐孺子满腹经纶且品德高尚后,十分钦佩,亲自前去拜访,并诚恳地请他到郡府为官。而徐孺子志不在此,重在教书育人,便婉言谢绝了陈太守的好意。对此,陈蕃并不勉强,便常常派人送去衣物用度,还邀请徐孺子到郡府论学献计,秉烛长谈,并特意准备了一张卧榻,专供徐孺子使用。徐孺子一走,陈蕃就把卧榻悬挂起来,直到徐孺子再来,才又放下。后来陈蕃到朝廷当了尚书、太傅,又极力上书推荐徐孺子,对此徐孺子都坚辞不就。“陈蕃之榻”典故传颂千古。这不是一张普通的休憩之榻,而是一面高悬的求贤若渴、招贤纳士的镜子。
识才之功是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讲的是識才之功。欲得人才者,必先有识才之功。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令百官上书言事。太宗阅览奏章时,发现中郎将常何所议二十余事,文笔通畅,透彻合宜,颇有见地。太宗非常诧异,便宣常何问个究竟。常何为人老实厚道,直言禀报太宗说,这奏章是家臣马周所拟。太宗即诏令马周觐见,其间四度遣使催促。待马周来后,太宗与之交谈甚欢,以为人才难得,即授予监察御史一职。从此,马周的抱负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才干得以酣畅发挥,成为唐朝名臣,累迁至中书令,并兼太子老师。“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贵在发现。正因为唐太宗求贤若渴的胸怀和慧眼识人的胆识,让各类奇才为之所用,野无遗贤,官风清正,整个社会才呈现雍容大气的气象。与之相比,历史上用人考察不真、不深而导致战败国亡的故事也不胜枚举。
容才之量是胸怀。唐朝大中年间,杭州刺史一职出缺,宰相令狐绹向朝廷举荐李远。唐宣宗听说李远素有弈秋之好,曾写过“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诗句,认为李远是耽溺于楸枰之人,不可担当此任。令狐绹解释说,那不过是李远赋诗遣兴而已,未必实然。况且李远是个廉洁且明察事理之人,即便沉迷棋艺,劝诫他不可玩物丧志就是了。于是宣宗允奏,任用李远做了杭州刺史。李远到任后“早作夜止,尽心理之”,把杭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政声民意均佳。对待人才,要看大节,看大是大非,不能求全责备。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给干事的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指工作所必需的条件,即硬件,更指人际关系的“软环境”。在这个“软环境”中,领导者的大度、宽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聚才之业是核心。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俩身为仆射,应当广开进贤的门路,然后根据他们的才干,授以相当的职位,这才是宰相该做的工作。近来听说你们听取案情,受理诉讼,忙都忙不过来,这怎么能帮助朕实现求贤的目的呢?”唐太宗对当朝宰相提出的要求,体现了他把识才用人摆在重要位置的胸怀和眼界。人才支撑发展,发展造就人才。没有骏马驰骋的疆场,千里马也难逃老死于槽枥之间的命运;无聚才之业,发现的人才也会流失。古往今来,但凡人才,大都渴望施展抱负,成就事业。领导者爱惜人才、招纳人才,就应像墨子所说的那样:“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说白了,就是留住人才、任事放权。特别是任事放权这一条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