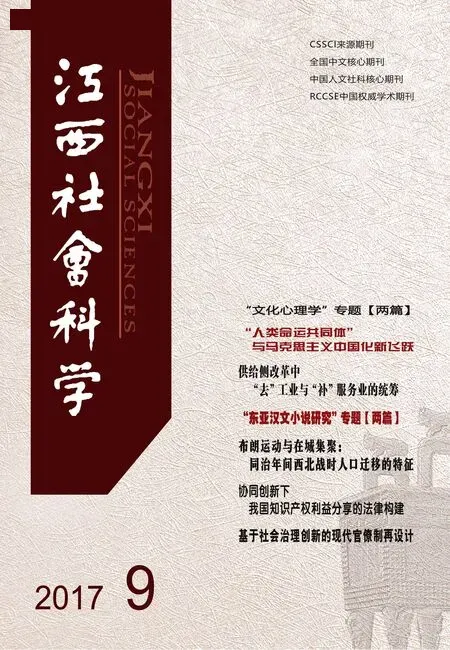逆境与重生:论中国古代遗民画家的艺术观
■常 艳
逆境与重生:论中国古代遗民画家的艺术观
■常 艳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遗民与遗民画家主要集中在元明清之际,伴随着朝代更迭而层出不穷。作为画家所需要的来源于生活的艺术素材却被国家灭亡、自身生存危机的现实境遇所替代,抉择是遗民画家首要面临的问题,出仕和不仕甚至成了评判人格的标准。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古代遗民画家在亡国背景下,面临艰难处境所表现出的绘画艺术观念,从而了解他们在逆境中迷惘、成长与重生的精神诉求。作为一个艺术群体,他们在政治立场、人生观、创作手法上有着近似的一致性,这就可能引发一门新的学科,即“遗民群体文化学”的深入研究。
逆境;重生;古代;遗民画家;艺术观
一、引 言
遗民一般指亡国之民,抑或指改朝换代后仍效忠前朝的一类群体,也可以指代后裔、隐士等。遗民在《汉语大辞典》里的解释有以下几项:亡国之民,前朝留下的老百姓,或指沦陷区的人民;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劫后余留的人民;后裔、后代;隐士;泛指老百姓。[1]由于目前学界对遗民的界定仍存在分歧,根据本文的写作主题,本文所指的遗民主要以在新朝出仕与否加以界定,根据本文的写作思想,在本文中,遗民的定义指的是《汉语大辞典》里的第二种解释,即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也即指一个朝代灭亡后,仍存活于新朝,但在思想上仍忠于先朝或心怀故国之思,消极或不与新朝统治者合作的一类画家群体,亦包括特殊身世或者父辈遭遇而用孝道体现民族气节的画家。
中国的遗民由来已久,从商朝灭亡、西周建立之时,就有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耻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山中的记载,他们两人是中国历史上早期有名的遗民典型代表人物。而进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宋元时期和明清之际,甚至是民国建立时,遗民这一群体更加为数不少。但由于“夷夏之辩”这一传统思想的长期影响,各朝遗民所受的重视和评价却大不相同。宋元之际的遗民因反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被视为是民族气节的象征,引起后人广泛的关注,向来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元、清两朝遗民因不守“夷夏之防”,忠于少数民族政权而饱受后世的指责和讥讽。因此,长期以来,对元代遗民和清代遗民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相比宋、明两代遗民研究的深入程度,这两朝遗民群体的研究可谓是无人问津。[2]
目前,对于“遗民”一词的确切定义还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以是否出仕新朝为标准,有的学者以是否在心里怀念故国为依据。笔者认为,学界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对遗民的定义要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李彦蓉在《清初遗民心态的嬗变》一文中认为:出仕新朝和心怀故国这两种标准都有些模糊和武断,而在心理上对故国的强烈眷恋才是遗民属性的本质[3];余辉在《遗民意识与南宋遗民绘画》一文中指出,界定遗民画家的概念较为复杂,符合遗民画家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必须是前朝的文人士大夫或具有一定传统文化功底的职业画家;他们在前朝已基本形成了适应于当时的道德规范,如忠君报国等思想,在仕途、财富等方面受益于新朝,或在新朝享有富足的生活待遇;追念故朝旧君,对新朝采取回避或抗争的政治态度。
遗民画家不仅是从身份的角度对美术史上的绘画种类作划分,也是因为这类画家的绘画风格与艺术观念因为遗民的境遇有相近之处。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遗民画家也经常与当时的文人画相提并论,是谓高尚的民族气节、坚贞的爱国情怀、苦楚的艺术追求的象征。当然,也有在朝代更迭之际,仍然有出仕新朝或过着和以前同样生活的画家存在着,但这些画家毕竟是少数,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做赘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遗民与遗民画家主要集中在元明清之际,伴随着朝代更迭,层出不穷。作为画家所需要的来源于生活的艺术素材却被国家灭亡、自身生存危机的现实境遇所替代,抉择是遗民画家首要面临的问题,出仕和不仕甚至成了评判人格的标准。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古代遗民画家在亡国背景下,面临艰难处境所表现出的绘画艺术观念,从而了解他们在逆境中迷惘、成长与重生的精神诉求。
二、中国古代遗民画家艺术观的三种类型
宋代之前,朝代更替比较频繁,但是为何在元明清之际才出现大批的遗民与遗民画家?这与儒家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从先秦儒家思想的萌发,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忠孝礼仪的发扬,儒家思想逐渐变成了之后大多数朝代的主体思想,以至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和多年来重文优儒的政策和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重建,造就了一大批忠君爱国之士,促使这些人充满了对国家、对君王的忠心不二之情。如《宋史·忠义传》序言说道:“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4]可见,宋代灭亡后涌现出的大批怀念故国的遗民是宋朝多年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日之功。从宋元之际开始到明清时期,每逢朝代变革初期,都是前朝的遗民画家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绘画表达出自己的焦虑和痛苦的复杂心情,是这些遗民画家的必然选择。此时,他们的绘画风格与艺术观也会与不同朝代以及艺术家的经济状况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他们在故国灭亡后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泪泉和墨写离骚;清贫守志,隐居俗世;曲笔和隐喻相结合的画风。
(一)泪泉和墨写离骚
屈原的名作《离骚》自问世之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遗民画家。这些遗民画家中用泪和墨写离骚,以画明志甚至以死明志的人在宋元、明清之际有很多。他们在故国灭亡之际思想偏激,亡国之痛、辱君之仇郁积在胸不能释怀。更有甚者,奋起起兵或者从军与新朝斗争,希望生逢乱世有所作为。这一类型的遗民画家也被称为激进派,他们在作品中直抒胸臆,借物喻情,将满腔悲愤化作绘画作品本身。
例如,宋元之际的遗民画家郑思肖是当时很典型的例子,他的遗民思想在当时最为强烈。南宋灭亡前,他一心想“为朝廷理乱丝”,南宋灭亡后,他“痛恨莫能生报国”,乃执意“不信山河属别人”,立志若“此身不死胡儿手,留与君主取太平”,毅然更名:“曰:‘肖’(趙字的一个部),曰:‘南’,义不忘赵北面它姓也。隐居吴下,一室萧然,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识焉”。[5]郑思肖擅画兰花、竹、菊花,但是画兰总是孤生,不画根土,人询之,则曰:“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6]“有田三十亩,邑宰素闻精(墨)兰,不妄与人,因给以赋役取之。公怒曰:‘头可得,兰不可得!’”此外,郑思肖在作品《寒菊》中题诗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庭中。”体现出了在南宋政权灭亡后,他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和国破家亡的失落之感。又如,他在作品《水仙》中题诗云“御寒不藉水谓命,去国自同金铸心”。[7]这些题画诗均体现出画家的满腔愤懑无处发泄,只能寄情于画,洒泪写离骚的情结。墨兰图是郑思肖传世至今的唯一作品,南宋遗民画家郑思肖的种种爱国举动,至今还被世间传为佳话。
在南宋画家中,龚开、马臻、钱选、温日观等人,他们的抗元意识又被后朝的王冕、倪瓒等人承袭,例如,元代画家王冕的《墨梅图》只是用单纯的水墨形式和清淡雅逸的用笔生动地传达出梅花的傲骨精神和伟岸的情怀。而在当时,倪瓒、王蒙、马琬、赵原等画家在作品中萧远的意境和豪放的笔墨,是元代末期中国画坛的主要艺术特色。
(二)清贫守志,隐居俗世
遗民画家们大都有着较为厚实的文学修养和出众的艺术才华,在改朝换代之际,他们已然都摆脱了先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笔者认为,古往今来,我国各个朝代的遗民画家们,他们的生存状态不外乎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隐居俗世,二是清贫守志,下文加以具体分析。
隐居是遗民画家们在国破家亡时最常见的生活状态。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八大山人、石涛等画家外,其他大批画家在改朝换代后也大多保持着一种隐居的生活状态。例如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周亮工在《读画录》中感慨“幼禀异慧,生名门,少年举进士”的明清之际的画家方以智,他在“三十岁前极备繁华,甲乙后,剃发受具,耽嗜孤寂,粗衣粝食,有贫士无哦不能堪者。”明朝灭亡后,方以智的画风变得秃笔草草,不求形似,且多做禅语用以自喻。明末清初的画家徐枋出身书画世家,同时也是名门烈臣之后,其父在南都被攻破后投河自尽。父亲死后,加之朝代的更迭,沦落为衣食无着、妻儿继丧、孤苦伶仃的遗民画家,国变的政治环境影响了其绘画风格的改变,徐枋多次在作品中表现江苏吴山与邓尉山的宁寂风光,便是他隐居状态的最好体现。在他的作品《涧上草堂图》中,画面中长松环抱,暗指出他十年不入城市、长期隐居山中书斋的生活状态。
除隐居外,广大遗民画家们的生存状态大多是清贫守志。画画虽然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但他们仍然对卖画谋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如明末画家、文学家黄宗炎(又称“鹧鸪先生”)虽出身名门,但也穷困异常。正如当时的文学家吕晚村在《卖艺文》中说道:“东庄有贫友四:为四明鹧鸪黄二晦木(黄宗炎)、槜李丽山农黄复仲(黄子锡)、桐乡殳山朱生始、明州鼓峰高旦中。”售卖自己的作品由于和画家们的声名息息相关,而他们若常常将自己的画作售于市井之中,就不免落下“俗”的名声。所以遗民画家们大多对卖画采取谨慎对待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们不以卖画为生,其作品风格就会不落俗套,即不去迎合当时市场的需要,而摆脱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则更加体现出其作品的个性和独特风格。
清贫守志和隐居俗世的生活状态,使得这些遗民画家们又被学界称之为“隐士”。所谓隐士,即指有才华和学问、能够有资格出仕却不愿出仕的群体。绘画艺术对于隐士这一群体来说是表现本人思想和气节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借助于绘画艺术来抒发真性情的方式,也同样是文人画艺术的重要特点。
(三)曲笔和隐喻相结合的画风
遗民画家们在艺术创作中典型特征就是作品中时常体现出曲笔和隐喻相结合的画风。在中国绘画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历朝历代的遗民画家们往往通过画作来表达作为遗民的痛苦和悲愤心情。例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是写意中国画中常见的表现题材之一,而广大遗民画家们也常常以它们作为创作题材,他们在作品中或借竹、菊与兰花表达自己的高尚品格,或借梅来比喻自己的气节。郑思肖画兰花,疏花简叶,“其所自赋诗以题兰、皆险异诡特,盖所以抒写其悲愤云”。
在这些画家中,遗民情节是影响他们绘画风格的最重要因素。这些遗民画家多在各个中国画种中通过一些人们熟悉的典故或动植物作为隐逸象征符号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例如在人物画种中,遗民画家们常常表现陶渊明、屈原、水浒人物题材,在花鸟画种中则有很多梅兰竹菊之类的题材。例如,清初的遗民画家陈洪授不止一次地画陶渊明像,以寄托自己对“复国”的向往之情,在他的作品中大都表现了一种怀念故国的沉郁心情和不与新朝统治者合作的消极态度。例如他所画的《归去来图卷》就是规劝他的老友周亮不要在清朝做官。《归去来图卷》分十一段,陈洪授着力于第六段《解印》的描写,他在《解印》一段上题着“糊口而来,折腰而去,乱世之出处”,以此借陶渊明的为人来规劝世人保持气节。[8]
遗民画家们的寓意画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寓事。如南宋遗民画家龚开的《金陵六桂图》哀叹国衰;前文提到的南宋遗民画家郑思肖的“无根兰”和钱选的《梨花图》皆寓意失国之痛;又如龚开笔下着元军装束的墨鬼,则包含有“打鬼复宋”的寓意。二是喻志。例如石涛和温日观常写墨葡萄,发尽明珠愿落草藤之兴;而元初的画家钱选、罗稚川的山水画都寄托了山林之志。众多的这类作品表明了隐喻是南宋遗民画家的主要创作手法。这些遗民画家们的寄寓方式,深深影响了后世文人画家的艺术构思。[9]
在曲笔与隐喻相结合的画风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原名朱耷,字雪个、号个山,后更号人屋、驴、个山驴、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世孙。明朝灭亡后,八大山人隐其姓名,长期隐居在江西南昌青云谱。八大山人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也是清初四大画僧(弘仁、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在中国美术史中简称“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专工水墨画,善书法,能诗文。他的作品大多感觉枯索冷寂,笔下的植物多在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气势,反映出他坚毅不屈的个性特征。八大山人在作品中的署款“八大山人”常常连缀在一起,看起来似“哭之”或“笑之”之状,反映出他面对国破家亡时很是无奈的心境。在八大山人的代表作品《孔雀图》中,石头尖而不稳,孔雀奇丑无比,尾巴上有着三根雀翎。画面上题诗一首:“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八大山人正是利用中国传统画面中的素材,同时经过自己变形处理和艺术创造,突出了一种丑怪的风格,讽刺了清朝当政官员的丑态,这幅有名的《孔雀图》,是典型的以独特绘画语言对当朝官员进行讽刺的精品力作。
三、逆境中求索与重生
我国历代的遗民画家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画派,且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在人生际遇上的共同点是都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痛楚,而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就是知耻而后勇,在逆境中求索与重生。除了我们熟知的“四僧”等遗民画家外,清代初期,岭南地区曾是抗清复明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明代遗民画家活动的中心地区。但先前学界对于这里遗民画家的研究并不深入,在中国美术史中,对于这些画家的记载和描述也远不如“四僧”那般颇多笔墨,因此笔者在此对他们的遗民思想作一重点讲述。
和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明朝灭亡时,崇祯皇帝毅然在北京煤山自缢,这一举动对明朝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明代遗民群体士气比较激昂且人数众多,他们对于新朝的态度也更加抑郁和激愤。在“物换星移”之际,许多士人杀身殉国,而清兵入关后强烈的军事征服和野蛮落后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明代遗民的强烈反抗,南明“王朝”的建立就是典型的例证。
由于南明政权的存在,使得清初的遗民思潮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明代遗民画家们的特殊经历,使得后人编写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如著名戏曲曲目《鹭峰缘》写的就是明代著名遗民画家恽寿平的故事。
明末清初时期,岭南地区的遗民画家们深感亡国之痛,大多隐居山野,以画作来抒发国破家亡的痛楚。他们的作品大多独抒性灵,表现出了一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比如它们的花鸟作品大多都是内心不平之气的发泄,抑或是孤独寂寞百无聊赖的写照。例如当时的进士王世贞在《池北偶谈》中写道:“东粤人材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10]明清之际,和其他地区的遗民画家一样,许多岭南遗民画家为保持清名贞操而遁入空门,这就是岭南士大夫们的僧侣化现象。活跃于广东一带的张穆、薛始亨等人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在绘画上的成就,与“四僧”相比也毫不逊色。
文人画家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往往给人以清高和不堪一击的印象,而在明代遗民画家中却有一些能文善武者。画家张穆,字穆之,广东东莞人,明代末年在岭南的忠烈之士们英勇抗清之际,张穆也曾在广东招募兵马抗清。后因粮饷断绝,他只得回归故里,目睹明朝灭亡,之后隐居不出:“洗心向林泉,所望唯鸾鹤”。他归隐后修筑草堂,寄情书画,通过诗文书画来倾吐怀念故国的一片情愫。张穆特别擅长画马,他大多借马来抒发郁结悲愤和爱国忧世的心情,从其名作《古木名驹图》中可见一斑。在这幅画作中,水流湍急的江边古树下卧着一匹千里良驹,左前腿作起立状,显出欲越千里之势。而周围却以古木、怪石等景物衬托,烘托出一种苍凉悲壮的气氛,张穆正是借助笔墨来抒发自己身怀千里之技而无处施展的忧郁心情。
在明清之际岭南地区的遗民画家中,薛始亨是另一位代表人物。薛始亨,字刚生,号剑公,广东顺德人,他曾在万历年间中举,明亡后隐居不出。薛始亨的外在身份是一位道人,他擅长作画、弹琴、舞剑,有文人学士之风。他通晓经史诗文,画家张穆与之多有交往。薛始亨以画竹石见长,画面多给人以奇气四溢之感。此外,陈邦彦、黎遂球、张家珍等人也是这一时期岭南遗民画家中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的岭南遗民画家,可以说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明代晚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序小修诗》语)这一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们报国无门,又不愿追随新朝,于是只能隐居乡里,寄情于画,从他们那些将客观物象高度提炼的花鸟画等各类作品中,表达出了他们坚贞不屈的真性情和自由精神。这些遗民画家特立独行,通过良驹、山鹰等多个画种来抒发内心抑郁不平之气,形成了独立不群的艺术风格。而他们超凡脱俗的画作,带给我们眼前一新的画风,体现出了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画家这一群体技高一筹的绘画才能。
总而言之,纵观中国历史,虽然有大批遗民画家曾顽强地反抗过新朝的统治,但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不能因此否定遗民抗争的内在精神,他们的抗争,是对前朝忠心耿耿的表现,也是对自己在道义上的表态和交代。
四、结语:“遗民群体文化学”及相关研究
从本文的中国画研究角度而言,遗民画家的群体涵盖中国画领域的多个流派和各个历史时期,即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画派里,或多或少地都有遗民画家的存在,以身份对画家进行分类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惯常思路,这种分类不但蕴含了时代特征,还蕴含了时代褒贬,例如文人画、院画、行家画等,它们均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绘画者的身份。[11]所以我们不能像明清中国美术史那样以画家的身份为基础,给这些遗民画家们以标准的门类划分。遗民画家们在成为遗民前,他们的身份也是不尽相同。因此,从本文的论述来看,作为一个艺术群体,他们在政治立场、人生观、创作手法上有着近似的一致性,这就可能引发一门新的学科,即“遗民群体文化学”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各朝遗民并不只是存在在绘画领域,在政治、文学、历史等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仅就绘画领域的遗民画家群体研究而言,例如明清交替之际遗民画家字号的不断更改,南宋时期的遗民画院,等等,都是以前研究不多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因此,绘画领域的研究只是遗民群体文化学这一整体研究的一个方面和缩影。遗民群体文化学的研究大有文章可做。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遗民文化的艺术成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遗民文化的系统深入研究任重而道远。
[1]汉语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柴文俊.元明时期元代遗民生存状态[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3]李彦蓉.清初遗民心态的嬗变[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5.
[6]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9)[M].“郑思肖”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元)王逢.悟溪集卷[M],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8]杨飞飞.明遗民人物画和山水画的象征符号[J].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2).
[9]余辉.遗民意识与南宋遗民绘画[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4).
[10]杨飞飞.抑郁不平之气——清初岭南遗民画家中的故国之思[J].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2,(6).
[11]付阳华,王云仙.明遗民画家的“遗”与“逸”之辨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责任编辑:易 斌】
J110.9
A
1004-518X(2017)09-0245-06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汉唐中外美术交流史”(16CF164)
常 艳,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