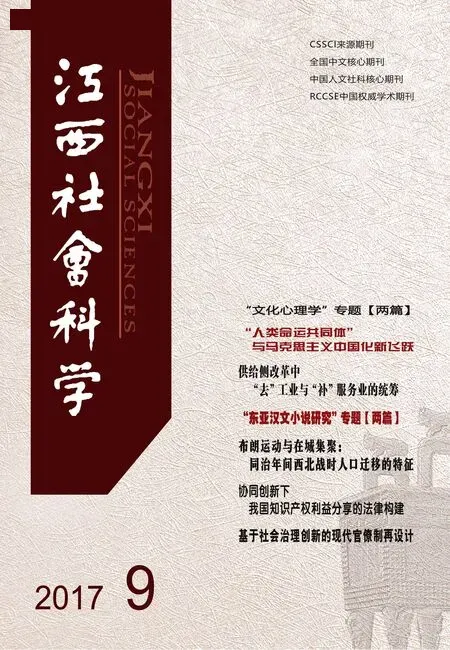文化心理学视角下中国人的和谐与幸福
■钟 年 王堂生
文化心理学视角下中国人的和谐与幸福
■钟 年 王堂生
当前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源于西方文化,但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是共通的,中华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源。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人们的幸福主要取决于在个人、他人、家庭和天下三个层次和谐与否。在个人层次,心理学展开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研究,“美美与共”当可作为己心关系的和谐之道;在他人层次,中国人通过深层的心理特质传承着传统文化的资源,从而更容易获得幸福的真谛;在天下层次,中国人当有主流文化的自信,以中国文化心理学造福天下。这三个层次实现和谐和幸福的问题应当被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家文化则是中国人很具代表性的本土资源,将自己、他人与天下联系起来,有益于全人类心理资本的建设。
文化心理学;中华文化;家文化;心理资本;和谐幸福
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角度看起来,无非是对三种关系的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这几种关系作了更简单的总结。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之为“生态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称之为“世态关系”,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称之为“心态关系”,费先生认为他自己一生就在做这“三态”的研究。据费先生自己说,他早年在家乡做的“江村经济”的调查,算是“生态”的研究,中年做社会学的工作,算是“世态”的研究。到了晚年,费先生到曲阜去参观孔林,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孔林片思”。[1](P3-7)后来在《孔林片思》这篇文章里,他谈到在曲阜的孔林中穿行与许多古人“相遇”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这辈子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第三种关系亦即人与自我内心关系的研究,或曰“心态”的研究实际上被忽略了。所以费先生觉得他应该补这样的课,包括整个社会学也要补这样的课。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就是费先生所讲的心态层面的问题。我们会结合心理学和中华文化的研究来讨论中国人的和谐与幸福。即从中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中国人的和谐与幸福。[2]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也算是将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是中国文化心理学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和论证。结合中国文化讨论中国人的和谐与幸福,可以提出“个人、他人、家庭和天下”三个不同层次的思考。应该说,如果在这几个层次都能达到和谐状态,中国人是能够感受到幸福的。近年来心理学尤其是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以及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3],例如东方人思维中整合的倾向与西方人思维中分析的倾向,由此推论,这种差异也会表现在幸福感上。从“个人、他人、家庭和天下”三个层次入手,就是考虑到中国人思维的这种倾向性。
一、个人层次:己与心
中国传统文化里儒家提出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修身”,涉及的就是心理学个人层次或曰自我层次的问题。在心理学中,个人和自我的话题主要包括:“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自己,他们希望如何思考和感受他们自己,以及这些自我思考和感受如何塑造并引导行为”。[4](P13)按照前述三种关系的划分,这一层次的问题也可以称为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关系,或者叫心与己、己与心的关系。
心理学对自我的关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今天还产生持续性影响的自我讨论主要是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的名著《心理学原理》(1890年)的第10章做出的。[4](P35)除了詹姆斯,其他心理学家也做过很多关于自我的研究,包括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研究。例如大家熟知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很早就做过关于自我发展的时间维度的研究。他谈到人一辈子的发展,自我的发展、人格的发展有很多的冲突,这样一些冲突都是人们需要解决的,他将这些发展分为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两性期等。[5](P211-220)弗洛伊德之后的一些追随者,例如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也做了很多关于自我人格发展的具体阶段的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婴儿期(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冲突)、儿童期(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学龄初期(主动对内疚的冲突)、学龄期(勤奋对自卑的冲突)、青春期(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成年早期(亲密对孤独的冲突)、成年期(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成熟期(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6]
另外还有对自我空间维度的研究。弗洛伊德就做过人格方面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结构性分析。后来心理学对自我的研究,也有所谓物质自我、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的一些讨论,还包括主我——客我、现实的自我——理想的自我等探究。这些研究都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包括认识人类的个体。在自我心理学的研究中,包含了一些不同的研究路径,或者叫思考。简单地说,我们把它称之为“我思故我在”型的研究路径和“对他而自觉为我”型的研究路径。“我思故我在”型更偏向西方人的自我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我自己就是我自己,跟别人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知道我自己的存在,是因为我在思考、我能觉知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自我是很个体的事情。但是东方人在自我观念上恐怕有另外的思考路径。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叫“对他而自觉为我”[7](P21),是说人们获得自我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别人在,别人犹如一面镜子,人们从中照见自己。正因为有别人在,人们才获得了对自我的一种认识。这与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社会心理学坚持一个基本的理念,即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互动,就是说自我永远是跟他人在一起的。
还是费孝通先生,讲过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费先生在晚年就文化自觉提出了十六个字,也可称作“十六字诀”。费先生提的这十六个字,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P15-22)。费先生这里讲的,是文明与文明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如果寻找其心理学的意义,这同样也可以看作自我与自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处之道。每一个个体、每一个自我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各种程度的自我中心,会“各美其美”,但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美人之美”,只有当人们“美美与共”的时候,也许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群体里的不同自我,才能比较和谐地相处。
二、他人层次:人与己
在个体之后,我们来讨论他人这个层次。他人层次在中国人的理念里面是讲“人与己”的关系,或者叫“己与人”的关系。孔子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样的话。不过,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可能略有差异。在西方的思维方式中,会更多地强调个体、自我,即“己”,包括诞生于西方的心理学中也一直坚持个体这个基本的立场范畴。但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谈论“己”的时候,是有“他”(或者“人”)在的。
从自我的发展来看,心理学家发现其实自我最开始是没有的。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跟动物差不多,没有自我的观念。自我观念的形成跟思维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心理学家发现,某些代词的使用,是儿童自我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例如说“我”和“他”。当儿童学会了说“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意味着他们将“我”(己)和“他”(人)做了一个区分。所以,“我”这样一个代词的使用,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的萌生的标志。
心理学也做了好多关于他人的研究,其实整个的社会心理学,包括文化心理学,都是在研究人们是如何与他人在一起的,或者是在研究他人对个体的影响。如上所述,西方心理学是偏于个体立场、自我立场的,是个体的心理学或者说是自我的心理学,但是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发展,让这样一个个体的、自我的心理学认识到,光谈个体和自我,恐怕也有很大的缺陷。例如大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都在证明他人对个体的极大影响,例如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s)、其他人的评价等。[9](P38-40)他人构成了一种情境,人们会发现,当处于他人情境中,个体在意识到别人存在的时候,能更好地意识到自己,包括凸现自己所承担的角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例如儒家的传统理念)提倡人们做讲仁义道德的人。在这里,“仁”是一个枢纽、一个核心。从某种意义上看,“仁”其实讲的就是“二人关系”,这是一种基本的关系,恐怕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人当然也关注自我,但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能力,叫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即以自我认知为基础去认知他人,这大概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提倡的一些基本能力。这样一些能力,包括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观,现在也有心理学家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予以说明。
近年备受关注的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是可以也应该和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例如,人们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传统文化中也可能有不适合于今天的东西、有糟粕性的成分。那么心理学的意义在哪里?心理学的意义就在于,可以用科学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哪些传统的东西可以在今天的社会里适用、哪些已经不适用。另外,当人们在讨论中国人还能不能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不能继承国学传统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中国人是否依然具备继承这些传统的心理基础?
譬如,近百年来呼吁重视传统文化的人士中流行一种断裂论,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已经断裂,具体表现为大众都不学习传统、不使用传统了,例如大众都不读四书五经了,甚至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之类的蒙学读物都没多少人读了。如果这样看,似乎真是有断裂,但问题是这样的断裂可能只是表层的断裂,表层的断裂在几千年中华文化史上随处可见,先秦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站在心理学的立场,更重要的是检视深层的心理是否断裂。如果当今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心理与历史上前辈的思维、心理发生了断裂,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断裂。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今天的中国人不一定在思维、心理上和自己的前辈间出现了断裂,相反,倒是有种种思维、心理上的连续性可以清晰把握。
心理学做过不少研究,证明中国人或者是东方人在很多地方,确实有一些特点跟西方人不一样。例如在东亚,儿童养育的实践就让这里的孩子与西方的孩子不一样,父母“对各种关系的强调促进了对他人的关怀”,而由于如此“关注感情和社会关系,在孩子们必须调整他们的行为的时候,这会有助于孩子们预先考虑到他人的反应”[3](P37)。研究还证明这样的结果会延续到成年人身上。
这类的研究还有很多,包括心理学中的自我的概念。心理学家提出有依赖的自我,也有独立的自我。[10](P224-253)中国人是比较符合依赖的自我,甚至包括整个东亚都是依赖的自我。西方人比较接近于独立的自我。这样的自我概念的差异能够用多种方法检测出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朱滢教授就做过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发现东方人的自我概念包含母亲成分,中国人与自我有关的记忆并不优于与母亲有关的记忆,而是处于同一水平;西方人的自我不包含母亲成分,所以英国人、美国人与自我有关的记忆优于与母亲有关的记忆。[11]
在与中国文化、中国人相关的研究领域,文化心理学也获得一些初步结论,例如中国人的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的问题。海内外学者的联合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五个认识与评价维度,这五个维度分别是联系性(中国人习惯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性)、变化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不变的人物和事物)、矛盾性(承认矛盾是中国人认识论的基础,矛盾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折衷性(折衷是中国人处理矛盾时常用的方法,中国人总是避免极端选择)、和谐性(中国人不愿意与人冲突,尽可能与人在外表上一致)。[12](P257)这样一些观点,以前也有人讲过,譬如哲学家、文学家,但是文化心理学的结论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量表测试后,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是有着实证基础的。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他人的关注、依赖自我的特点以及思维的整体性,都可以看出今天中国人的心理与我们前辈心理的连续性。心理是文化的底层,判断文化的断裂,要从底层来衡量。文化心理学的方法,为人们深入文化底层、把握文化心理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如果说上述讨论指出了中国人表现在文化上的心理特点,回到和谐与幸福的话题,西方人讨论幸福,更多讲的是个体的、自我的幸福,比如说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包括马斯洛(Abraham H.Maslow)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ed)理论,也说得很清楚,那是叫“自我”实现。马斯洛画过人们需求的金字塔,底层是较宽的,越往顶端越窄,颇具个体自我的意味。但是中国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哪怕是基本的需求和动机全人类也有很多的不一样。[13]中国人的需求不一定是马斯洛标示的那种金字塔,中国人在高层的需要动机的表现上与西方人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自我实现、中国人的需求表达,可能跟西方人不一定完全一样,全人类也是如此,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都可能自有特点。西方的积极心理学也认为:“帮助建立和维持相互依赖关系的特质对东方人达成他们的目标可能更有价值。”[14](P42)最有可能的是人类在基础的需要动机上,就是说在生理的需求上、在安全的需求上是差不多的,但是越往上走,走到社会文化性的需求上,便可能殊途了。美国人、中国人,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很可能都有自己的特点。
既然中国人关于自我需求动机的一些结构特性,跟马斯洛提出的结构特性有可能不太一样,那么中国人的幸福追求,也许有独到之处。中国人讲幸福,经常讲“同乐”,自我和他人、群体乃至天下一起乐,所谓普天同乐。汉语中有各种各样的“与共”——美美与共、欢乐与共、荣辱与共等。中国文化提倡助人为乐,讲集体主义,讲奉献精神;还有关系维护,鼓励帮人与被帮——我们可以帮人,我们也可以被人帮,被帮的时候产生的感激、感恩之心,也能够增进幸福感。西方幸福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的幸福感从哪里来?一开始认为收入与人们的幸福感相关,但是研究做到最后发现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很小甚至没有相关。那么到底什么因素与幸福感关系密切?最后发现,是积极良好的关系与人们的幸福感相关更大,也就是说我们从关系那里获得了我们的幸福,从我们的好朋友那里、我们的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最基本的幸福。[15]
三、天下层次:天与人
我们再从天下的视角检视和谐与幸福的问题。天下是一个很宏阔的概念,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人谈论天下,包括谈论天下概念包含的内容。将人与天下放到一起,就涉及中国人常说的天人关系。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天下概念一直在变化。先秦所说的天下,和后来的天下概念就很不一样。[16](P425-478)当然,心理学更感兴趣的,主要不是思想家们对天下概念的讨论,而是一般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就是说,天下概念的历史演变,是思想史研究的话题,而心理学家关心的,是一般人到底接受一些什么样的天下观。
从这个立场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在讲天下宇宙的时候,可以将天下宇宙与自己讲到一起。例如中国人对宇宙的基本解释,以前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上下四方谓之宇,往来古今谓之宙”。从这个解释不难看出,作为基本的前提,人是包含在宇宙天下当中的。因为“上下四方”“往来古今”都是相对概念,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说宇宙。想要在前人的言论中找到类似的话太容易了,宋明以后儒学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话,例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类。
中国人熟知的一句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是用责任把个体与天下联系到一起。若干年前中国印制的世界地图上常常写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字样,也是上述理念的延续。那么,一个个体(匹夫)可不可以跟民族、国家、世界、天下这样大的事物勾连联系起来?心理学中关于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整个利他行为中最后起作用的还是个体基本的责任意识(这里有著名的“旁观者效应”的研究)。[9](P432-473)有了责任,个体与他人、与群体、与天下就可能结合起来。在这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又为中华文化的传统观念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天下是大的背景,匹夫是小的个体,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体,社会心理学也发现个体和他人、组织、天下有联系。古语云,“达则兼济天下”,这话可以倒过来,叫“兼济天下则达”。今天有个词很流行,叫达人,达人就是很成功、很快乐的人。当人们能够兼济天下的时候,也许真的就很快乐了。西方的积极心理学也认为:“帮助建立和维持相互依赖关系的特质对东方人达成他们的目标可能更有价值。”[14](P42)其实,讨论幸福快乐,跳出自我的追求和局限,反而会获得一种更大的快乐,这个应该不分东方西方,此种快乐幸福也许可以称之为天下之乐,这应该是更持久、更坚实的一种快乐。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也到了总结中华文化对全人类意义的时候了。世界史从来都把中国边缘化,曾任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过这样的问题:到底谁是世界史的主流?世界史的一个错误是把非连续性文明当作主流。古代的四大文明如今就剩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中断了。但是在西方世界史里从来都把中断的西方文明当主流,而把中国历史当边缘。难道连续的不应该是主流?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追求、有这样的研究胸怀,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主流,因为中华文明起码五千年没有中断过。
四、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和谐与幸福之道
由天下的话题可以讲到中华文化对全人类的价值意义。从文化心理学来看,关系可能是一个。中国人觉得关系太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一生就是在处理种种关系。关系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因为人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不可以脱离关系而生存。例如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家庭,就是人际关系的结合体。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默多克,利用数代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材料,在耶鲁大学建立了全世界的文化档案,即“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从文化档案里,他分析出一些文化的基本单元,这些单元都是全人类普遍存在的,这些基本单元里面就有家庭。家庭文化是所有的文化包括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家庭很有意义,家庭对每个人心理上的影响有很多,比如家人、家园、家乡这些概念,甚至包括祖国,祖国就是家乡,祖国(motherland)就是父母在的地方。所有这些观念都跟家庭有关,这些观念构成了人们的根基情感、凝聚了对群体的认同,每一个人的家园感对自我的支撑都极其重要。
家庭对于人类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单位或机构。每个人出生之后,第一个社会化的机构就是家庭这个单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家庭网络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初的庇护、也提供最初的教育。家庭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这大概是人类的原创,是在文化社会中形成的制度。不同地区会因为文化的差异,家庭的具体表现也有很多方面的差别,但家庭这样一种组织单元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回家几乎是全人类都共有的感动。当然,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是家文化的传承者,中国人可能更为看重家庭,在中国文化里家与国几乎同等重要。
通常人们说家庭的重要性,会说亲如一家,会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汶川地震发生后,人们互相救助,都是建立在根基性情感基础之上的。大家是有联系的人,当然应该互相帮助。这是家庭很重要的心理意义,是家庭给人类带来的信念和幸福感。人们最初的情感训练就是在家庭里,那是人类获得的最初的心理资源。中国人常说的父母双全、夫妻恩爱、子女孝顺等等,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获得幸福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里家一直是中心性的。你是谁家的?你姓什么?人们在交往中总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姓氏跟家有关系,一个人表现不好的时候会说他没有家教。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又缺失,甚至家里没有沟通的时间,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认为家庭教育的作用十分大,因此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家教、家训方面的书籍。中国人一贯认为,父母应该通过自己的行为给孩子很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给孩子好的、有文化的家教。
中国的传统教育,很关注家庭教育,一直在讲如何一方面加强内部教育,另一方面在外部争取很好的环境,这都是中国基于传统的家庭教育形成的自觉意识,留下许多家庭教育读本。《三字经》一开始就是讲教育——中国人的教育就这样从家庭开始。每个人都会背“人之初、性本善”。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讲家庭教育,讲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孩子怎么孝敬父母。“二十四孝”中有若干个故事发生的那个地方,最后命名为“孝感”。在中国,对父母的孝可以说是家庭原则里很重要的心理原则,这也是中华文化贡献给世界文明重要的精神宝藏。
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家园感丧失。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给全世界的感觉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移动,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大都市,从大都市到海外。最近几十年有好多中国人已经移民国外,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移民,在全世界这样的现象很罕见,以致到现在中国人越来越丧失家园感。家园感给人们很多基础的支撑,家园可以提供马斯洛理论中那些最基本层次需要的满足,一个民族没有家园感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中国人是特别喜欢讲家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发展出关于家的各种文化,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17]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常常也是在家中体现的。家是中国人很重要的本土资源。在中国文化中可以看到家庭的枢纽作用。虽然西方思想中有一些对家庭轻视或忽略的说法,但中国人应该告诉全人类,家庭也许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每个个体的生活轨道,最后拯救了我们的世界。中国的家文化如此丰富,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充分利用好家的本土资源,将有助于构建今天的家庭幸福,最后助益于全人类的幸福。
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家庭的文化心理学话题,家庭文化其实是过渡,从个体心理学过渡到胸怀更宽广的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就是从个人到天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思想提倡“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齐家”之后便是“治国”,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例如“国家”,也会讲“家国”。把自己与他人、组织、国家、天下等联系起来可能会带来快乐,中国人的快乐一直和更高、更大层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日本著名的经营大师稻盛和夫说:“人类什么时候会感到内心充满深切而纯净的极致幸福感,那绝不是在私益获得满足的时刻,而是在利他充分发挥的时刻。”[18](P162)文化心理的特征让东方人有本事体会这个道理,共情同理,强调共和同,都是东方人擅长的感知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西方人中是相对欠缺的。中国人从小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就饱受这样的训练,有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能力。心理学实证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视甘苦与共、荣辱与共、美美与共、普天同乐为美德,而且确实有如此践行的能力。人们这样做的时候,真的体会到了快乐和幸福。以志愿者为例,他们奉献了,换回了快乐和幸福,他们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付出。心理学家做过研究,做好事的回忆会增加幸福感,助人者会更快乐。
张光直先生在其《考古人类学随笔》中写道:“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19](P55-56)差不多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孙中山写的是“心理建设”。[20](P105-161)我们认为,现在中国也要提倡心理建设,尤其是当今中国人,心理建设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发展。一个大国,最重要的表现恐怕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在全世界领先,而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民是否具备大国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大国的思想和大国的文化。我们今天的心理建设,可以扬长,也可以补短。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同理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关心他人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等,很可能在全世界是卓越和突出的。这样一些思维资源,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总结,很可能成为我们积极的、优秀的心理资本。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提出一个概念,叫心理资本。[21]人类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以前多在讲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现在要提倡心理资本的建设。
在人类的各个领域,都需要一些积极的心理资本,才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走向未来。优秀的心理资本,很有可能是对全人类、对整个世界有益处的一种资源。像天下之乐、天下关怀包括对他人的关怀、积极想象等,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积极性所在。我们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帮助,大家在良好的关系中共同成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积极的一面。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有必要成为我们今天心理资本建设的一些基本任务和内容。助人为乐、分享快乐、天下之乐,和别人一起快乐幸福,快乐分享之后并不会减少。当然,并不是人们不考虑自己,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仿佛自己越是在给别人有所牺牲的时候,心里特别觉得痛快、酣畅、开展。反过来,自己力气不为人家用,似乎应该舒服,其实并不如此,反是心里感觉特别紧缩、闷苦。所以为社会牺牲,是合乎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生活更能有力!”[22]果能如此,则一方面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可以佐证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也可以对整个世界的学术界包括对全人类有一个基本的贡献。
[1]费孝通.孔林片思[J].读书,1992,(2).
[2]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增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3](美)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M].李秀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4](美)乔纳森·布朗,玛格丽特·布朗.自我[M].王伟平,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5]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论评[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6](美)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8]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9](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侯玉波,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0]Markus,H.R.and Kitayama,S.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91,Vol.98.
[11]朱滢,张力.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J].中国科学,2001,(6).
[12]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杨国枢.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4,(1).
[14](美)C.R.斯奈德,S.J.洛佩斯.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M].王彦,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15]Diener E.,et al.The New Science of Happiness.TIME,2005,(3).
[16]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A].刘岱.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C].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
[17]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8](日)稻盛和夫.活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19]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北京:三联书店,1999.
[20]孙中山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1](美)F.路桑斯.心理资本[M].李超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2]梁漱溟.朝话:人生的省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胡 炜】
G05
A
1004-518X(2017)09-0014-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传播与演变机制研究”(13 BXW053)
钟 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堂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