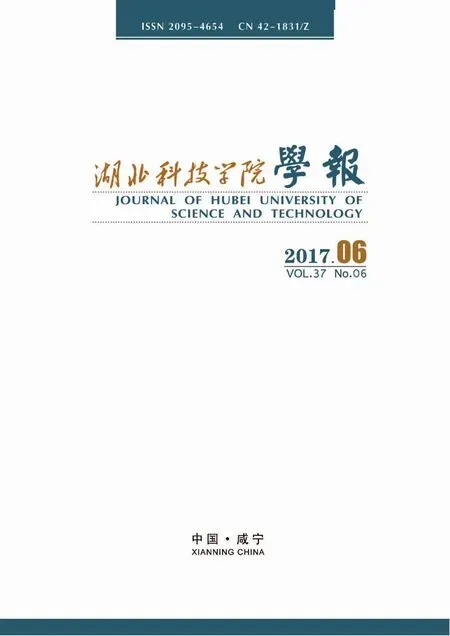“再校园化”叙事
——新时期校园小说的新变
王艳文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再校园化”叙事
——新时期校园小说的新变
王艳文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研究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的校园题材小说的变化,是以20世纪50-70年代的校园儿童小说为参照物。通过回顾20世纪50-70年代的校园小说,发现新时期校园小说是在50-70年代的“去校园化”基础上冰点再起,呈现出“再校园化”的文学特征。
去校园化;再校园化
批评家程光炜说:“‘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将对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规范的颠覆和改写视作自己的文化使命,换言之,它们都在将‘摒除’这一当代文学的传统作为新的‘理想文学’或者‘纯文学’的革命性开端。” 儿童小说亦不例外,下面将以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为参照的,来分析新时期儿童小说创作在校园述题材方面相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变化与不同。
论述新时期儿童小说中校园生活题材的新变,并不是说新时期儿童小说相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来说没有继承,校园题材本身就是一种传统题材,只是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新变。这种新变表现为从20世纪50-70年代的“去校园化”过程转变为新时期以来的“再校园化”描写。下面先简略回顾“去校园化”过程,以便更清晰地对比出新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再校园化”新变。
一、“去校园化”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少年儿童被誉为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革命的接班人。对他们的教育必不可少。1949年中国共产党委托青年团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其“目的是团结教育广大少年儿童……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少年儿童被视为革命胜利后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来进行培育。20世纪50-70年代校园生活题材的小说就是描写少年儿童的校园内外生活,目的是对他们进行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
正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校园生活题材的儿童小说中,儿童小说作家不厌其烦地讲述或描写少年儿童端正学习态度,努力学习,积极上进,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组织的校园生活场景。只有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个组织,才能获得革命接班人的合法化身份,由此也才能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红领巾”业已成为少年儿童的代名词,于是许多儿童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习惯于做好事不留姓名,他们常常做出这样意味深长的答谢:“要问我叫什么,请叫我红领巾。”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有这样的论述:“‘少先队文学’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既以其鲜明的时代生活内容……有别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文化语境中的校园文学……它以充满感激、崇拜、青春的激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新人新事新社会,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倡“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于是很多少年儿童从校园走向农业社,成为小社员、小生产能手与小技术员。陈子君在概述1957以来极左思潮的泛滥时指出:“当时片面机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不仅使学校生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锐减,而且造成图解各项中心运动和具体政策……” 校园生活题材的儿童小说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农村生活题材的儿童小说却大量出现。
到了“文革”期间,学校的“农业社化”或“军营化”倾向越来越强烈,置身校园的少年儿童越来越不满足于呆在校园进行常规的日常学习,而是在“学农”和“学军”的政治号召下逸出了常规的学校公共生活秩序。这必然会加剧校园生活题材小说中少年儿童生活的成人化和社会化进程,而他们纯粹的学生身份与校园生活开始潜在地失落或缺位。即使是在那些描写和讲述当时中国少年儿童校园生活内部状况的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的依然还是被校园外部生活或社会公共秩序所强力渗透的政治化生活场景。就这样,校园题材的儿童小说便进一步淡出儿童文学领域而完成了“去校园化”的过程。
二、“再校园化”新变
新时期校园生活题材的儿童小说又大量出现,这种“再校园化”的情形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新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与调整。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高考制度的恢复又燃起人们远古已久的旧梦。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又被激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高考制度的恢复,改革开放的刺激与市场竞争的残酷,使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高考,考上大学。但是随着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不只出现在高中、初中、小学阶段,甚至还出现在幼儿园。我们常看到一些标语与口号,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就是其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教育观念的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淡出儿童小说领域的校园题材在新时期再度繁荣兴盛起来,占儿童小说的半壁江山。
(一)对分数的重视
在新时期儿童文学领域,儿童小说中的校园题材描写开始有了新的内容,再也不是20世纪50-70年代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德育而是关注分数考上大学的智育。20世纪50-70年代德育开始是强调好好学习,成为遵纪守法的接班人或者成为做好事不留姓名的红领巾,关于如何教育接班人,防止变颜色,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 号令一下,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工厂,走向农村,按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而新时期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智育,是唯分数论。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呆着,就算放学或者寒暑假,也是在学习中度过。为了提高分数,学生学习时间被无限延长,甚至是减少必要的休息时间,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最后分数控制着学生,学生被迫服从高分的需要,分数才是最重要的,学生成为获取高分的物质性工具。
学生成为学习机器。如王蔚的《别对我说什么青春期》中,“一门门功课堆在那儿,拿定主意要压扁你,我不过是个对付功课的小机器一架”。 学生在老师的监视下,没有一丝闲暇时光。在张成新的《三点半放学》中,学校偶尔一次三点半正点放学,不用加班加点。可令人沮丧的是班主任于老师却挨家挨户地查访,把他们逮了个正着,并告诫他们:“你们考虑的应该是抓紧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别光想着玩”。 为了分数,学生自己也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如韩青辰的《梅子青雨时》中,“我每天只肯花七个小时休息,包括吃饭睡觉上厕所,其它的时间都用来复习,连上厕所路上的五分种都被我精巧地利用起来,或者背一段难背的政治问答,或者记一种复杂的数学公式”。 再如匡湘凤的《同桌》中,“我”的同桌学习非常刻苦,“课间十分钟,她总是分秒必争,埋头苦学”。 就是在上学路上,她都带着记有满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与代数符号的小本子,好随时翻看。有一次差点被一辆疾驰而过的东风大卡车挂住。
除了延长时间之外,还有一招是提高学习的强度与紧张度,甚至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吴艳梅、李树松的《柳絮飘来的时候》中,“上到初三,学习更紧了,东雪觉得自己有些吃不消了。” 东雪还只是“吃不消”,更有甚者是日渐消瘦,甚至病倒。在章郁的《高三那一年》中,“我”像陀螺一样飞快的旋转。成天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讲义,一捆捆的试卷,成千上万道演算题。“没有过真正的星期天,没有过真正的假期。”因为加班加点的学,“短短的时间,张爱芬整个儿地瘦了一圈,小巴颏都尖起来了……婷婷却在考前的一个星期躺倒了” ,住进了医院。可见高中紧张的生活节奏让学生付出健康的代价。为了考上大学,他们有的还疯狂得不计后果。玉清的《跑,拼命地跑》中,临近高考,佳佳转到边远地方去参加高考,那里可以降100分。于是没转学的陈宝拼命地学习,无限地延长学习时间,缩短休息时间。后病倒去医院打点滴,为分数不顾一切的她走火入魔,居然想出缩短必要的休息时间,以打点滴来维持生命的学习方式,这种饮鸠止渴的方式使她身体极度虚弱,最后精神崩溃住进了精神病院。李树松的《白色鸟》中,李琛的同学许文丽的身体已经吃不消了。医生说:“许文丽得的不是什么器质性病变,她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造成的,这种病叫做癔病性截瘫”。 医生还说如果学校再给他们这么大的压力,他们就会吃不消,有的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为可见了分数,他们不顾身体,不计后果,不但是健康受损,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张微的长篇小说《雾锁桃李》是新时期反映苦不堪言的学子生涯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校园小说。小说描写临江中学为追求升学率而分快慢班,不同层次的班级在师资与教室的配置上都不一样,于是学生自然地被分成三六九等。成绩好的学生唯恐被人赶上,担心退步被降到慢班,成绩差的学生为争取进入快班,加班加点,因为只有进入快班才有升学的可能性。结果快班学习成绩好且心地善良、宽容懂事的纪志萍,因长期贫血和过度疲劳,突然昏倒,最后医生也无回春之术,纪志萍英才早逝。慢班的秦芬则因起早摸黑,压力过大,劳累过度,在踏入考场之际患上精神分裂症。《雾锁桃李》表明在现存教育体制下,无论是成绩好还是成绩差的学生,他们活得都不轻松。吴秀明认为此小说“真实地描述了儿童学习生活日见恶化的生存状态” 。
描写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有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刘建屏《今年你七岁》、郁秀的《花季雨季》,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小说。
新时期虽然倡导素质教育,但是在高考指挥棒下,教师仍然只照本宣科,教学依然是填鸭式的灌输。学生要完成没完没了的作业,应付没完没了的考试,为的只是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不要掉下去。分数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任何对分数不利的因素都会遭到无情的扼杀与严厉的惩罚,目的是尽可能把性情各异的学生纳入到统一追求考分的模式之中,变成单面人,成为考试的机器。学校对分数的一味强调,家长对分数的格外重视,使学生也开始为这分数而活,于是校园生活对少年儿童来说是苦不堪言的。正如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所评:“‘五四’时说礼教吃人,现在人们看到,学校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教学方式原来也吃人。在唯高考,唯成绩,唯分数的教育观念的指导下,人们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生命的和谐,忽视童年生活的丰富性,使人从小就趋向单维的人,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
(二)对心灵的关注
新时期校园小说的新变一方面描写少年儿童苦不堪言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致力于学生内宇宙的探索。“到了新时期,儿童小说创作题材领域空前拓宽,作家们越来越热心地关注儿童生活图景,学校题材已不局限于表现少年儿童如何学习和生活,而且深入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力图传达他们的思想与情愫。”
秦文君与杨红樱等人的校园系列的童年小说,如《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淘气包马小跳》等,反映了当代小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如马小跳与路曼曼是冤家对头,在《同点冤家》中,马小跳和路曼曼,天天都有战争要发生。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一般是以路曼曼胜利而告终,马小跳则常常与倒霉、委曲、被冤枉连在一起。但是在事情的发生过程中,马小跳也常常有得意之时。总之马小跳在学校与同学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时让马小跳欣喜万分,有时让他沮丧不已。马小跳与他的同学们就这样笑着,闹着,渡过他们在学校的每一天。贾里与贾梅等人亦或如此。
与童年小说相对的少年小说,则主要描写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心理情感。在20世纪50-70年代,校园题材不曾涉及到青春期少年的情感问题,其一是因为那时校园题材的儿童小说都是童年小说,没有少年小说,所以没有少男少女的感情波澜。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整个文学环境使然。成人小说中对私人情感问题的描写都是刻意回避的,更何况教育至上,德育当先的纯洁得像蒸馏水的儿童文学。
新时期最早反映少年心理情感的小说是丁阿虎的《今夜月儿明》,小说以走出青春期的解丽萍回忆的口吻来讲述那段经历,并对其做出否定性的判断,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学能像她一样,走出了那段迷茫期,但小说对主人公青春期复杂矛盾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随后有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笔触深入少男少女的内心深处,作细致入微的描写,不再作道德的评价。后来类似的小说从原来的看守、否定、压制到强调正视、认可、引导这种青春期感情的萌动。如韦伶的《出门》、吕温清的《多彩的小河》、韦娅的《中三女生心中事》、程玮的《今年流行黄裙子》、秦文君的《橙色》、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三三的《香豌豆的春天》、张成新的《洁白的耐克》、长篇小说有韩青辰的《梅子青雨时》、王巨成的《穿过忧伤的花季》、殷健灵的《纸人》、谢倩霓的《喜欢不是罪》等等。新时期校园题材小说大量描写青春期的欢欣与苦恼,苦闷与彷徨,表明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那种封闭狭隘落后的意识,不再让少年觉得自己有多罪恶与龌龊,让他们意识到这是正常的生理心理现象,引导他们顺利地走过这段非常时期,体现出对少年儿童心灵的关怀。
从上面列举可看出新时期儿童小说中校园小说,一改20世纪50-70年代渐趋衰落的局面,呈现同“再校园化”的叙事特点。“再校园化”叙事在内容也逐渐向儿童外在的真实生存状况与内在的心理情感方面进行深入地挖掘,真实而深刻地呈现出当代学子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校园小说对分数的重视,使得各种功课、作业充斥着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少年儿童的游戏权被剥夺,与自然接触的时间和机会被减少。他们无法在蓝天下尽情地挥舞自己的胳膊、舒展自己的身体、渲泄过剩的精力,少年儿童的游戏天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朱自强指出:“儿童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儿童生态被破坏,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童年的身体生活被挤压甚至被剥夺。” 生态的破坏本指为了这一代人的幸福而过度的开发属于下一代人的自然资源,带来自然生态的破坏。朱自强所说的儿童生态的破坏指的是为了少年儿童成年时代的幸福而牺牲他们童年时代的幸福的作法。“以童年阶段的幸福来换取成年阶段的幸福是不合理的人生设定,成人社会不能拿一个孩子的童年生命阶段去作他另一个生命阶段的牺牲。” 他们童年时代应该在玩耍中度过,可是新时期校园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顽童,而是一个走在成长道路上匆忙的赶路人,这是“再校园化”叙事给我们留下的思考。
[1] 程光炜.姿态写作的终结与无姿态写作的浮现[J].文艺争鸣,2005,(4).
[2] 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63.
[3] 陈子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M].济南:明天出版社,1991.169.
[4] 蒋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189.
[5] 王蔚.别以我说什么青春期[A].徐德霞.一路风景(小说卷6)[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90.
[6] 张成新.三点半放学[A].张美妮.中国当代儿童小说精品文库(上)[M].天津:新蕾出版社,2003.553.
[7] 韩青辰.梅子青雨时[A].徐德霞.一路风景(小说卷5)[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28.
[8] 匡湘凤.同桌[A].徐德霞.一路风景(小说卷3)[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206.
[9] 吴艳梅,李松树.柳絮飘来的时候[A].徐德霞.一路风景(小说卷3)[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80.
[10] 章郁.高三那一年[A].徐德霞.盛世繁花(小说卷3)[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347,353.
[11] 李树松.白色鸟[A].徐德霞.一路风景(小说卷4)[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2007.165.
[12] 吴秀明.浙江新时期文学三十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182.
[13] 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17.
[14] 蒋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362.
[15] 朱自强.让心为新鲜的一切而跳———儿童教育与童年身体生活[N].中国教育报,2007-03-27.
[16] 田媛.“童年生态”在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回归[J].齐鲁学刊,2013,(3).
2095-4654(2017)06-0055-04
2017-10-28
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项目“当代儿童小说中儿童生存空间透视——基于儿童发展价值观的视角”(2015JB124)的成果之一;湖北科技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空间分析”(2016-19XB015)成果之一
I058
A
余朝晖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